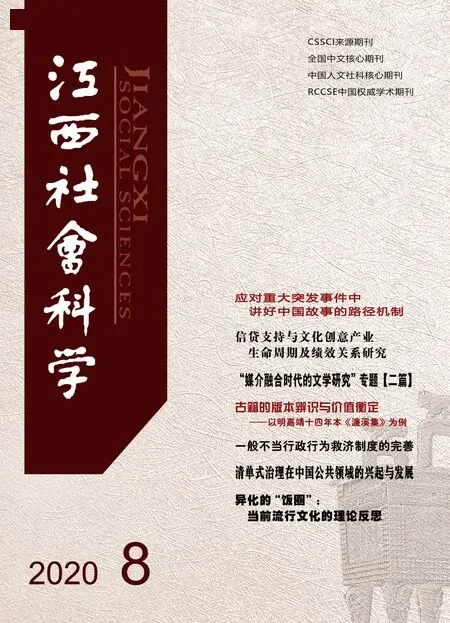现代图景与都市大众: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市民话剧
2020-02-11■李冉
■李 冉
作为话剧“黄金十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民话剧在“孤岛”时期形成了自身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了多方关注。市民话剧的发生、发展虽然不完全符合“五四”知识分子对话剧启蒙性和宣传性作用的想象。但它仍是现代性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它呈现的现代都市成为左翼戏剧、国防戏剧之外更为鲜活的图景。在职业话剧的推动下,市民话剧和观众互动,与观众共情,被观众接受。同时,作为小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市民话剧又积极参与到海派文化的建构发展之中,呈现出现代性的表征。
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了一本关于上海近代史的专著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33年后,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上海出版。墨菲选择上海作为理解现代中的钥匙,是有理由的:
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正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1](P5)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北平是传统的文化中心,保持着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价值和品味,南京是新的政治中心。上海则同时崛起为具有与北平不同的价值和趣味。上海是现代的、通俗的、大众的、商业的、摩登的,以工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为主的新兴文化中心,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共生,成为上海“海派”文化的特征之一;上海又是传统的、保守的、混杂的,在现代与经典之间穿梭徘徊。
市民话剧是理解上海文化的一个方面。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产生于城市居民公共生活的市民文化开始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中。财富、摩登、紧张、逼仄的上海都市生活,发展出独特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特别是“孤岛”时期①,放松、宣泄成为市民文化消费的重要诉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画坛、剧坛都在发生剧变。同时,“孤岛”受到英法美和日本的管控,现代启蒙思想的传播必然存在阻碍。在职业话剧的推动下,市民话剧和观众互动,与观众共情,被观众接受。它没有高亢的调子,却在话剧大众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都市“风景”:市民话剧中的现代叙述
1925年,卡尔·索尔在《风景的形态学》一文中将“自然风景”和“文化风景”的概念加以区别,认为地理学应当通过地理景观的多样性来研究区域性的人文地理特征。于是,风景作为一种视觉对象,具有了物质性和观念性两个维度,前者强调“自然、物质的形态,完全通过劳动或其他关系产生”,后者强调“社会关系的代表,由各种媒介表达”[2](P45-46)市民话剧中的“风景”,可以被看作是“自然风景”和“文化风景”在舞台上的再现。日本学者炳谷行人将艺术作品中的风景视为“认识装置”,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察,尤其人们“以全新的范式将自我投射到客观景观风景中的结果。”[3](P25)如此说来,市民话剧成为折射和展示主体内心世界的载体,意义也在观众欣赏和认识舞台风景的过程中得以不断产生和循环。“风景”本身不产生意义,但由于被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便也成为社会历史环境的微观表现。
1928年,美国记者斯诺初到上海,他惊叹于上海的“风景”,一边叙述着“大片宁静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很像美国东海岸或法国城镇最好的住宅区”;一边描绘了普通市民的都市生活:“上海商业区的街道乍看起来同样也像是一个古怪的马戏场,熙熙攘攘,活跃得令人难以置信……永安游乐场里同时演出十多台戏,传出假嗓子的尖声演唱……还有千百艘点着灯笼的舶板,在月光映照、严重污染的江面上就像是点点黄火!”[4](P18-19)这里提到的“永安游乐场里同时演出十多台戏” 就是传统戏曲和文明戏的同台争辉的情景。永安天韵楼的这种演出模式一直延续到1941年“孤岛“沦陷。永安天韵楼虽然不是最正规的话剧剧场,却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的话剧成为城市“风景”的形式。一方面,在演出和接受的相互影响中与市民共同完成了舞台表现艺术的展示;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之中,市民话剧成了城市现代“风景”的一部分,观看的同时也被观看着。
毋庸置疑,话剧不可能像镜子一样客观反映现实中的城市空间和叙述,但它有个特点是无法忽视的:展示都市的影像风景。剧院和剧本中的空间构建起一种市民性的上海想象,该想象一方面带领观众逃离现实、又反映现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现实。1938年10月,上海剧艺社演出《人之初》,导演吴仞之用节光器控制光的明度,用脚光造成的面部阴影来表现人物的品性和惶惑心态,有效表现了剧中人物。1941年,天风剧社在璇宫剧场演出《上海屋檐下》,舞台光用点示式照明集中表现在进行中的戏剧情景,而让其他演区处于暗部,从而使各个演区在光的照明中逐一展示,更好展示了格子间的布局。“孤岛”末期加入天风剧社的知名电影导演费穆,在1942年1月天风剧社解散后,又在此基础上吸收新艺、银联的部分成员组建上海艺术剧团,他将电影手法移植到话剧舞台上,将电影和戏曲的表现手法融合为一体,创造性地在话剧舞台上加以试验和探索。电影技巧与戏曲元素的加入,增强了话剧的艺术感和表现性,不断催生出新的艺术技巧和美学范式,丰富了观众对于都市风景的现代性视觉体验。另外,夏衍的《愁城记》,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单行本并由上海剧艺社公演。《愁城记》从剧本文学到舞台艺术都展示了都市上海独有的“风景”,洋房、亭子间是上海市民生活最富特色的建筑;风云变幻的外汇市场、汇丰银行都体现了上海作为远东最重要金融中心的实力;婉贞夫妻从北平逃难至上海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上海环境的相对“稳定”。同时,《愁城记》和《女子公寓》《上海屋檐下》一起,共同构成了最后“走向远方”的模式。
无论是《上海屋檐下》里的格子间与灶披间,还是《愁城记》的两层洋房和广告画,都是物质建筑和文化空间的共时呈现。“虚构”的舞台背景通过道具、构图、视角、运动等方面呈现“写实”或“虚构”的内容,这些内容或多或少包含着都市“风景”,建筑、风俗等示了都市的自然和社会性特征。短时间内积聚了极多财富、人口的“孤岛”,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变革的中心。市民话剧作为一种“对话”方式,被引入参与到城市现代性表达中。在“看”与“被看”之外,剧院以及剧本中的空间还试图构建起一种市民性的上海想象,这种上海想象将不同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逃离现实、反映现实、制造现实的剧场“景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际会的上海,职业话剧、业余话剧、左翼话剧等与上海的土壤交融,可以说,他们首先是属于时代、社会和国家的。而市民话剧这一支从都市生活深处涌出的脉流,才是属于上海的。
二、人的“现代化”:女性市民的觉醒与出走
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无疑是“五四”之后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思潮之一。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通过《新青年》传播后,一批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出走剧”相继诞生。不过,鲁迅不久后撰文《娜拉走后怎样》质疑离家出走对娜拉的意义,他认为,娜拉出走后“免不掉堕落或回来”。二十年后的上海,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似乎更为复杂了。繁荣的都市给女性提供了多种职业可能,但也爆发出更多矛盾,无论是酒场舞女、纱厂女工,还是知识女性,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们在都市环境之下践行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是曲折迂回、充满艰辛的,却在重要意义上显露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千疮百孔。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作为上海剧运的领导者之一,于伶组织实践了上海左翼戏剧的战略转移,即从带有强烈政治倾向转为满足一般市民需求,适应置身于“此时此地”的上海市民心态。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护进步戏剧家免受当局镇压;另一方面是争取市民观众,开展更有效的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伶创作了都市女性戏剧《女子公寓》和舞女题材戏剧《花溅泪》和表现“租界”市民苦难遭遇的现实主义戏剧《夜上海》,成功塑造了交际花、弃妇、女职员、舞女、逃难者等在困境中挣扎向上的女性形象。虽然后来于伶本人极力试图忘却这类缺乏昂扬斗志的作品,但相较于他的早期剧作《汉奸的子孙》,《女子公寓》等因更加贴合市民阶层,迎合大众消费而显示出独到的价值。一方面,高亢的左翼戏剧通过大众文化之途逐渐渗入到上海市民的心中;另一方面,这类戏剧更加关切都市背景下人物个体的命运和灵魂,试图通过多种视角发掘现代女性的意义和价值。
《花溅泪》是一部以舞女为题材的剧作,不仅文学性强,演出效果也好。《花溅泪》的广告词为“中国第一场以舞场为背景的舞女大悲剧”,多少有些吸引眼球的噱头之嫌,却从侧面表明以于伶为首的上海剧艺社在“孤岛”话剧大众化和职业化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大众化”曾是左翼剧联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里,“大众”一般指“工农大众”“劳苦大众”,并不包括居住在城市底层的普通市民。戏剧大众化,意味着离开都市名利场的中心漩涡地带,到底层去、到郊区去、到农村去,事实上,左翼剧作家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们和熊佛西都受到梅耶荷德的启发,又都信奉功利的实验主义,不停采取“试错”的办法,一出戏观众看不懂,不妨换一出;国语听不懂、就用方言、土话。但总体而言,左翼剧作家偏爱各种煽动剧而抗拒其他类型的戏剧。到了“孤岛剧运”时期,左翼剧作家意识到,煽动剧虽然在一定情形下使观众大快人心,但大部分时间都会觉得很假,这当然就失去了煽动的效果。淞沪会战后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上海战时状态的结束,市民得以回归日常生活。“孤岛剧运”自然不能如“左翼运动”样继续开展下去。
《花溅泪》的演出是“孤岛”戏剧回归人性、回归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反映。剧中的主要人物皆为舞女:米米、曼丽、丁香、顾小妹,作为悲剧主体,她们中有的自幼被亲生父母卖掉,有的被公子哥玩弄情感致使堕胎,有的被情人所骗执迷不悟相约殉情自杀,最后在彼此的帮助下走出阴霾,重新开始生活。其中,玩弄、蹂躏顾小妹的公子哥是对入侵者日本和英法列强的一种隐喻,尽管未婚妻在情感和肉体上背叛了他,但在利益面前,亲情不值一提。而“孤岛”的存在,正是日本向英美列强妥协的产物,尽管它们各怀鬼胎,却还是为了一己私利挂着一块破烂的遮羞布,四年后在更大的利益诉求趋势下,这块遮羞布被狠狠撕下。这样的隐喻不止一处。“工作”时的米米在歌厅唱了一首她所上的补习学校先生编写的《舞女曲》,透过《舞女曲》,于伶描绘出他对上海都市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的理想认知,有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职业、国民、责任,成为都市现代女性的关键词。显然,于伶借用《花溅泪》这个通俗的外衣包裹了一个严肃的内核,即女性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战争时期的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这其中至少包含两个问题,一是现代女性的生存和解放,二是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花溅泪》选取的是特殊的舞女群体,她们赚取收入,却与一般的职业女性不同,因为她们的收入主要取决于男人的喜好程度,从根本上说,所谓的职业和经济独立完全摆脱不了男性的掌控,这是她们的悲剧的根源,因此,摆脱男性控制成为完成自我救赎的必经之路。这样看来,米米最后走上抗日前线,成为看护并偶遇昔日恋人——投笔从戎的东北青年,如此结局的设置也就不显得那么理想化了,毕竟作为一个市民话剧它还兼顾了“孤岛”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事实上,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在国家面临灭亡或被列强肢解的危机情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话剧宣传的紧迫目标。但暂时“安全”居于一隅的上海“孤岛”市民不愿在消遣的时候承受如此沉重的话题,毕竟,经历了晚清、军阀割据、民国的“孤岛”市民还没有在短时间养成现代市民对国家和领土完整重要性的认知,对他们而言,由族裔民族主义意识控制下区分的苏北人、宁波人、本地人,或者汉族与少数民族人群,才更符合中国历史变迁的逻辑。
在《上海屋檐下》之前,夏衍创作过舞女题材的剧本《都会的一角》,此后因历史剧《赛金花》和《秋瑾传》声名大噪,而《赛金花》更因题材突出和创作构思精妙被认为是“国防戏剧的力作”。不过,夏衍本人并不十分满意《赛金花》,他坦言“《赛金花》前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5](P226)《赛金花》之所以受到观众的追捧,很大一个原因在于舞台表现的炫目。得益于早年的先锋戏剧经验,夏衍不仅要求《赛金花》在幕前放电影,还要在幕后放黄烟,使观众能闻到火药味,以扩大戏剧表现力。而这种“噱头”的手法受到左翼剧作家的批评,认为其存在“形式主义”和“右倾”的问题。郑伯奇在《〈赛金花〉的再批判》中指出:“强调本剧的讽刺性,极力使它大众化,大胆地说罢,那就很容易流为文明戏,噱头固然可以卖钱,但就革命地立场讲,那该是所谓‘右倾’的罢。”[6](P50)郑伯奇的批评表明,左翼剧人对大剧场演剧流于“庸俗化”的担忧。夏衍因此下定决心写出更写实的作品。
1935至1941年间,夏衍对“小市民”群体关注颇为深切,从《都会的一角》《重逢》《上海屋檐下》《一年间》《赎罪》《娼妇》《心防》到《愁城记》,他一直尝试在为这些都市小人物寻找出路,1940年,夏衍把这些戏编成一个集子,因为全是写“小市民”的东西,就把这集子叫作《小市民》,当年7月剧本集《小市民》由桂林新知书店出版。夏衍曾经这样解释《小市民》的由来:
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起眼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情感……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要争取他们,单单打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我写的地方是上海,是沦陷区,是一个古旧的家。[5](P312)
值得一提的是,“孤岛”时期的张爱玲曾谈到她对“小市民”一词的看法,“我这种拘拘束束地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第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布条”。[7](P3)夏衍笔下的小市民显然超越了张爱玲所谓的小资产阶级范畴,囊括了普通甚至底层贫民。1944年,《杂志》的一篇文章曾这样给出“小市民”的内涵:写字间的小职员,保险公司掮客,女打字员,接线生,从事证券交易者等等。[8](P169)夏衍早期的几部戏偏重宣传意义,手法也谈不上高明。经过刻苦钻研,包括苦读曹禺、田汉剧作等,夏衍终于在《上海屋檐下》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物和主题:“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逼真的人生世象、心灵的痛苦与企求,鲜明地展现了自己新颖独特的戏剧观和成熟的艺术个性,于社会画面和人物心灵地描绘中呈现朴素、洗练、深沉的风格。”[9](P620)这部剧以离开监狱的革命知识分子匡复回到上海和妻女团聚,却发现妻子已和当年他托付的朋友同居的故事为线索,刻画了都市上海社会的一群小人物。“这种生活我比较熟悉,我在这种屋檐下生活了十年,各种各样的小人物我都看到过。”[5](P229)
同样,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没有口号式的宣传,剧中人物有着鲜明的个性气质和时代烙印。夏衍对《上海屋檐下》非常满意,他说“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探索。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5](P232)这部剧中的女性都是最底层的市民,她们不摩登,没有商业气息,无法传达外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女性的现代性想象,但她们在格子间的日常却是都市现代生活的最贴切表达。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室内马桶、拥挤的灶披间等等,充满了现代生活的气息。这种现代市民生活气息和都市摩登氛围共同营造了都市现代女性。其实,“上海屋檐下”这个剧名也很值得品味,此剧名是受到外国戏剧《巴黎屋檐下》的启发,“屋檐”既是一种遮蔽,又有“寄人篱下”的意味。显然是对上海当时所处环境的一种隐喻,1937年4月,战争尚未爆发,但东北地区已沦陷近6年,同时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对中国方面更大规模的入侵一触即发。事实上,《上海屋檐下》的首场演出正是受到淞沪会战的影响而不得不取消。一方面是压抑,一方面是启蒙,发现“人”、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比外在形式现代化更深刻、更复杂的命题,毕竟,不是建几座摩登大楼、穿几件海外时装、喝几杯现磨咖啡的就能实现的。杨彩玉为了爱情和理想离开家庭,她不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但她是支持者、协助者,为了追求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赢得现代革命的胜利,如娜拉般出走的杨彩玉并没有获得理想中的独立和解放,相反,陷入更大的深渊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孤岛”时期的话剧作品中,除了上文论述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女性作品,另一类历史故事类题材也对女性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孤岛”时期,诞生了一批以女性为主角的具有强烈民族国家意识的历史剧。如《明末遗恨》(又名《葛嫩娘》《碧血花》)《洪宣娇》《大明英烈传》《洪宣娇》《杨娥传》等,在这类作品中,女性通常坎坷的命运、拥有坚强的意志和令人悲愤的结局,能够极大地调动起读者和观众的情绪,激发起战时民众的强烈共鸣,深受民众欢迎。与现实主义的市民女性形象较比,历史剧中的女性趋于典型化、而非个性化。这些历史故事和人物通常已被观众熟知,甚至有些还直接来自于戏曲,与观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她们自出场就显示出民族赋有特定的使命。而市民女性题材的话剧则更体现了的“人”的解放等现代性问题,更加关注女性个体的命运。从这点上来看,作为“孤岛”时期同样受到观众欢迎的市民话剧和历史剧,二者的内涵和任务是不同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造就了空前繁荣的“孤岛话剧”。
三、磨炼与抗争:“此时此地”的演出
“此时此地”的说法最早出现在《给SY》一文中,这是1938年于伶市民话剧《花溅泪》的初版暂序,SY即指夏衍。文中这样写道:
这是此时此地,企求一用的排演台本,是未完成的稿件,是临时用的版本。但愿有朝一日,能把我未吐出的对话,应织入的张本,重新写排出来,让《花溅泪》的面目与骨骼一新,以谢我辱渎杜工部“花溅泪”这三个字的罪愆吧!……有一位先生看过《女子公寓》之后,说过,“有些地方胆子太小,语焉不详,殊不痛快。”SY!我们能语焉详,痛且快的时候,当不在远了吧!我迎着这将临到“孤岛”上来的一九三九的新年,虔诚地祈祝着。[10](P240)
很快,《花溅泪》再版,于伶又写《再给SY》,探讨上海剧艺社和“孤岛”话剧的前途。半年后,夏衍看到这两篇文章,加上对李健吾《关于上海剧运低潮》一文的共鸣,他写了《论“此时此地”的剧运》作为回应,并发表在《剧场艺术》杂志上。文章中,夏衍这样解释“此时此地”:
我,对于此时此地的剧运,是同意于将这阶段规定做“磨炼”的那期的,“八一三”以来,中国的剧运可以大致说,已经完成了普遍化的第一阶段了,紧接在这一阶段之后,我们的任务是在如何才能使这普遍化的戏剧能够作一步更大的前进了,普遍,同时更要深入,这是我们的课题……我如此说,并不是表示了我们对此时此地之环境的让步,相反,这正是我们“抗战建剧”的必要的过程,我们的工作方式应该是永远地抵住,永远地反拨着压力的弹条,我们需要的是坚韧,获得一种坚韧的性格,我以为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磨炼是必要的。[11]
前文提过,于伶的《花溅泪》是一部舞女题材的市民话剧,由这部剧引起于伶、夏衍、李健吾等人关于上海“孤岛”时期戏剧运动的现状和发展是有原因的。于伶、夏衍、李健吾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而负责排演《花溅泪》的上海剧艺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业话剧团体,它的上级领导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据黄明回忆:“在文艺方针政策上,根据戏剧方面党员和群众都是职业从业人员的特点,不仅有帮助群众谋生的需要,也有利用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组成合法剧团、组织就业的可能。特别是当时敌伪‘中华电影公司’已在拉人下水,更需要有一个阵地,团结、巩固我们的演员编导队伍,以粉碎敌伪的阴谋。”[12](P170)
从单纯依靠剧本文学到强调演出是“此时此地”的“孤岛”剧运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提高演出质量,提升话剧作为综合艺术的舞台表现力,剧运负责人组建剧团、创办杂志,同时为了不暴露行踪,还推行“事业化”策略,“就是要我们经营的剧团和刊物,采取做生意的做法,有一套经营管理的机构与制度,注意营业的盈亏,既把我们的事业消溶于群众的面目之中而不暴露自己,又在经费开支上获得支撑,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能争得生存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再来开展革命的艰巨工作”。[12](P170)《花溅泪》的成功,不仅依靠于伶创作的优秀剧本,还得益于演出团队的精心打磨。该剧公演伊始,主演夏霞就在《申报》撰文畅谈她对于伶创作的共鸣:“我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戏,——是事实,是真实的暴露……我钦佩他……他每每的暴露了社会中那些黑暗丑恶的角落,他永远的是为那些被压迫者呐喊呼号,我们都知道他还藏了一肚子没有说出来的话……为了他,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希望他能将话尽量说出的日子快快的来临吧!”[13]另一主角蓝兰也以“给一位舞国里的友人”为题探讨底层舞女的价值归属和出路问题。两位演员,从不同角度参与这部戏的艺术实践和问题建构,呼应了夏衍对于剧运应强调提升演出和演技,而非依赖剧本的观点。通过创作、演出、接受等多方面的理论总结回顾,《花溅泪》以先头部队的姿态拓宽了“孤岛”剧运的试验范围。于伶认为:“《花溅泪》不仅是一个暴露舞女私生活的剧本,同时更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怎样才能使上海6千多个以跳舞为职业的姐妹们,不走上像米米,曼丽和顾小妹的路。”[14]
事实上,夏衍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1927年,夏衍翻译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由此走上文学道路。这部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被夏衍译介到中国后对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在1928年到1934年间,夏衍克服重重困难,热情昂扬地翻译出版了日本早期普罗作家的小说和戏剧以及高尔基等苏联作家作品,这些经夏衍翻译的作品很快成为当时渴望进步、寻觅革命道路的年轻人的精神导向。《上海屋檐下》无疑蕴含了夏衍对女性和进步革命青年出路的双重思考。在夏衍本人和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革命和市井之间的碰撞。在救亡和启蒙的语境下,上海这样一个充满海派文化特质的都市中,除了启蒙话剧、社会问题剧到左翼话剧、国防话剧这条脉络,还存在着市民话剧。进入到“孤岛”时期,政治性、启蒙性愈加敏感,市民话剧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有学者曾指出:“五四时期,在清算旧戏和文明戏的时候,钱玄同、刘半农、陈大悲、沈泽民等人即提出建立‘人的戏剧’、‘民众戏剧’等口号……抗战后期的话剧创作,不仅重新确立了人在市民戏剧中的核心与主体地位,而且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深化了五四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通过表现人来影响人、塑造人,在认同市民社会的前提下,得到了话剧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思想、文化、经济资源,从而化解了话剧主体建设与社会功能两歧的张力,把话剧推向完全成熟的境界,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最受市民爱戴的新兴民族戏剧。”[15](P110-111)上海“孤岛”时期的市民话剧因其对“人”的深刻探讨而被视为现代话剧成熟的表现之一。作为市民话剧中的杰出代表,夏衍在战前的创作转变带动了抗战时期上海左翼创作从政治性到人性的转变,并涌现了一批经典作品和深刻市民形象。我们无法想象,市民话剧倘若离开了上海要如何发展;与此同时,上海也不可避免地被市民话剧所形塑。无论是城市研究还是话剧研究都无法绕开它们的关系。然而,因其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话剧自身发展的局限,市民话剧所表现的现代性某种意义上说仍是模糊的。例如,从身体与现代性经验的关系看,市民话剧作为沟通身体和现代都市生活的媒介,在形塑市民的现代知觉范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话剧的表演方式很大一部分吸取了戏曲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是被程式化了的动作表演,带有更多的表演性质,因此,与西方戏剧相比,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演员更加内敛含蓄,对于身体的表现也选择了更加委婉的表现方式。又如,在女性与公共关系的塑造上存在限制。通常来说,空间中的女性被侵犯与欲望化使之不断遭受谴责,与此同时浪漫化的女性气质往往受到讨好,被讨好的原因在于正面的、纯洁的、浪漫的女性形象是新兴意识形态的再现。这两种形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市民话剧中女性观众和年轻男性观众的认可,话剧在舞台上重新塑造市民女性形象,对大众认知进行自发的修正。
历史的发展是多头并进的,话剧史亦是如此。无论是只阐述话剧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强调市民话剧的发生发展机制,都不可能对市民话剧做出最全面的说明。市民话剧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了自身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了多方关注。同时,作为小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市民话剧又积极参与到海派文化的建构发展之中,呈现出现代性的表征。通过现象深入肌理,触及市民话剧的内在深处,对于全面认识上海的现代图景和都市文化有着积极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上海“孤岛”时期上演的以表现上海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话剧。对于上海“孤岛”时间段的界定,本文以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保留英法租界自治,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