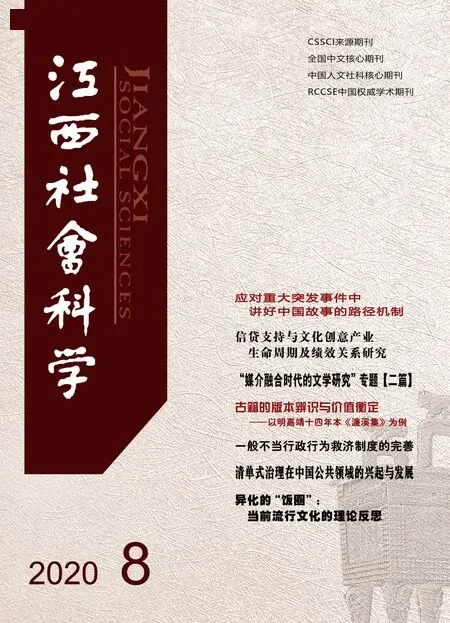文化与制度的耦合:见义勇为的儒学表达与法律助推
2020-02-11■伊涛
■伊 涛
借助于法律助推见义勇为,其实就是要助推儒学理念获得实践,因为见义勇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儒学内涵。通过彭宇案可以发现,借助于法律助推见义勇为具有必要性;通过小悦悦事件则可以发现,助推儒学理念获得实践具有可行性;两案进一步凸显出见义勇为的实现概率。良好的法律必然是文化与制度的良性耦合。儒学与法律以一内一外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促使儒家原有的秩序构设框架(克己复礼)展现出崭新的面貌,相较于儒学一直居于前台,责任豁免的权利则始终处在后台或者备用的位置。
自彭宇案和小悦悦事件先后于2006年和2011年发生以来,社会各界时常追问,若是看见有人倒地受伤,到底应不应该搀扶,能否通过法律来扭转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1]西方存有可供参考的先例,尤以美国加州1959年制定的《撒玛利亚好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最是引人注目,因为它所讲述的事情与发生在中国的情形高度相似,意在鼓励人人都能如同耶稣口中的撒玛利亚人。①但中美国情不同,若是直接鉴取美国《撒玛利亚好人法》,未必合适。时至2017年,在《民法总则》的立法过程中,各界越发追问能否运用本土的文化资源来鼓励见义勇为。②习近平总书记早就倡导,“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2]。儒学属于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基因,要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继承和发扬。立法机关也作出了积极回应,要让“《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契合传统美德”[3](P1315)。落实到具体的制度设计,就是既要鼓励人们对不负有救助义务的他人实施救助,还要降低人们因救助他人而惹上麻烦的风险,即避免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这就需要通过赋予一定的责任豁免权的方式保护善意救助者不受责任的追究,《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而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已沿用成为《民法典》第184条。
批评者固然会认为该规定所要调整的事项原本应该由道德来应对,涉嫌越俎代庖,而且若要依据它行事,恐怕会耽误前往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化正规治疗的最佳时机,但又完全认同立法对它的功能所做的预期。笔者想要指出,借助于法律助推见义勇为,其实就是要助推儒学理念获得实践,因为见义勇为本身就属于儒学范畴,而且它的发动和实现具有丰富的儒学内涵。鉴于彭宇案和小悦悦事件正是展示人际交往何以尴尬的标志性事例,故可借助于两事件展开探讨,甚至可以检验出,借助于法律助推见义勇为具有怎样的必要性,是否契合于本土已有的相关立法经验,助推儒学理念获得实践何以具有可行性,儒学的存身是否只能依赖立法的认可。其间还凸显着见义勇为能否实现的概率问题,若是仅凭儒学理念即可实现见义勇为,法律助推的意义何在,儒学与法律的互动能够引致怎样的秩序构设框架,责任豁免的权利在儒学上获得妥适的表达。良好的法律必然是文化与制度的良性耦合。作为一种完备的理论,儒学是具有终极关怀的,责任豁免毕竟是一种可以用来解决纠纷的制度,势必需要反思,它能否进入到儒家的终极关怀,获得实现的向度序列。
一、见义勇为的儒学表达
孔子有言:“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勇即勇于担当。孔子又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勇者成为仁者,要受到其他事物的引领。子路曾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曰:“君子义以为上,有勇无义是为乱。”(《论语·阳货》)勇要受到义的规制。孔子亦言:“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张载在《正蒙·中正》中曾言:仁、知和勇,天下之达德。勇德被推崇为人人皆应具备的重要德性。显而易见,见义勇为在社会上备受赞誉,高度契合儒家的理念。
在儒学的论域内,伸手扶助面临困境的亲人,属于伦理层面的理所应当,意味着见义勇为的发生只能面向非亲人,以至于如何应对非亲属关系貌似完全无涉家庭伦理方面的儒学理念,实际上并非如此。孔门弟子子夏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四海何其广大,实无可能到处都有亲兄弟,但可以把他人当作亲人来对待。孔子有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其中的第二句,即儒家的恕道理念,意指双方皆以自己是否接受同类事物来为各自的举止和互动确立尺度或者边界,并非只能局限于亲属关系和家的范围。张载亦曾指出:以爱己之心去爱人则尽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意指把老吾老和幼吾幼的情感类推至他人老幼,举斯心加诸彼。“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各种论断皆说明,只要把非亲人拟制为亲人,视他亲为己亲,即可达致在邦如同在家,所引致出来的正是家庭伦理的外溢,即原本存在于亲人中的伦理由家内溢出,在家外的非亲人中获得展现,其间的基本逻辑和内容则是爱的起承转合式的传递。何谓起,即起于对自己的亲人有爱;何谓承,即主动地施予非亲人,让他们有所承接;何谓转,就是拿捏着面对亲人的爱转向去面对非亲人;何谓合,即合于人人相爱。“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如此一来,就需要把非亲人面临困境视为亲人面临困境,无可推卸地予以帮扶。
儒家的其他理念即使无法直接关涉伦理外溢,但仍会发生间接联系。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能够彰显出来的正是不计回报乃至无所预期的全情付出,即缘何关切和帮助他人,只是基于自身内在的恻隐,并不关涉身外的回报预期。恻隐之心的发作,即便不带有百分之百的必要性而表现为不得不,恐怕仍是带有非常强的必要性而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必须,所引致的就是一种全情付出,而且在人人皆是如此的层面上定义自己与他人的关联性存在,最终在人之为人的层面上定义自己。搭救孺子的若是其他孩童的父母,那就表现出了幼吾幼的类推。“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恕道呈现为一体两面的忠道,亦可产生类似效应。诚如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有学者指出:“欲立欲达犹如孔子好学不厌,立人达人如同他诲人不倦。”[4](P165)前者还囿于自身范围,后者则把目标所向和价值所求推向了其他人,意味着人们在成就自己的时候,有必要成就对方,甚至以彼此成就的方式来成就自己,帮人就是帮己。
综合来看,见义勇为所具有的儒学内涵并非只是事关自身,它的发动和实现所涉及的儒学理念极其多元。尽管各种理念可以在《论语》等儒学文本中获得呈现,但孔孟并没有说过它们只能依赖文本来承载。孔子曾提及六言六蔽,其中之一,便是“好仁不好学,蔽于愚”(《论语·阳货》)。好仁与好学并非同一件事,好学的意义在于除蔽,不学不足以全明其理,有了它,好仁能够更好地实现,若是没有它,好仁的实现效果或许会差一些,但不意味着完全实现不了,说明好仁并非只能来自于好学。如果说阅读文本属于好学的一种方式,那么好仁就并非只能立足于文本阅读才能够获得实现。文本其实只是儒学理念获得集中表达的书面载体而已,它对理念的承载并不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好仁完全可以置身于文本阅读以外。“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既然固有,何必非要通过文本外铄于我,说明人们的日用常行原本就属于促发儒学理念获得滋生的沃土。是否如此,不妨再到具体事例中去检验,至少就彭宇案和小悦悦事件来看,借用儒学解读它们,具有充足的有效性,而且能够凸显出通过立法助推见义勇为原本就需要面对儒学的理论依据。历史法学派曾强调,法律总是需要与特定民族的文化、行为方式等紧密相连,甚至结为一体,共同塑造着特定民族的根本禀赋[5](P7),社会法学派亦曾主张,立法就是要把本国本土社会中的规范提取出来定则成典[6](P67)。通过研磨两件事例即可发现,善意救助责任豁免制度的诞生固然肇因于非常具体的现实需求,但也脱离不了理论依据的辐射范围。
二、见义勇为的未曾实现与法律助推
就彭宇案[7]的案情来看,在上车下车极其拥挤的公交站牌前,彭宇把倒地的徐老太扶起后,又和她的家人把她送到了医院。徐老太一方随后指出,受伤系因彭宇相撞,想要索赔。彭宇一再言说当时并未相撞,发现有人倒地,若是视而不见,就不会惹来麻烦,自己的搀扶行为和帮忙送医都属于见义勇为。一审法院作出层层推理:如果彭宇想要见义勇为,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徐老太的人,徐老太的家人到来后,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说清事实经过,自行离开,在和徐老太的儿子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不会把钱借出去。如此一来,徐老太受伤确系彭宇相撞,但并非故意,理应分担,判定彭宇赔偿徐老太损失的46%。判决一出,各界做了相反的推理:彭宇完全可能会认为关注人身安危要比抓住肇事者更为重要,而且何尝不曾想过离开现场,但徐老太的儿子曾向他求助,还说自己没有带钱,在他看来无非只是几百块钱,就借了出去。
不难看出,各界致力于从道德肯定的维度塑造彭宇,使得他貌似能够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对待徐老太,判决则显示出徐老太一方并没有像对待亲人似的对待彭宇。无论何种法律活动,其实都不能与大众的道德认识相悖,一旦相悖,就会让人们感受到恶。[8](P81)司法机关的意见输出原本具有权威性,但恶的判决违背了法律的扬善精神,致使社会大众的善恶判断模糊不清,以至于眼前的社会无论被法律冠以何种美妙的称谓,恐怕都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样子。[9](P140-154)尤其是面对一审推理,各界解读出的寓意无疑是法院支持好人难做乃至做不得的社会风气。[10](P246)这就有意无意间凸显出仁爱亲人与仁爱陌生人的完全不同,前者可以基于血缘关系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后者却至少需要通过推及表现出来。孟子固然主张仁者无不爱,但在后面毕竟又紧跟了一句,急亲贤之为务。爱的起承转合式的传递何以可能,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所起而又有所承,尤其是其中的转,一方施予需要另一方承接,但非亲人终究不是亲人。就此看来,唯有起、承、转的三大环节同时畅通无阻,方才能够确保合于人人相爱。且不说三大环节全都存在实现的难度,哪怕只是其中的任何一环受阻,原本的传递就会支离破碎,继而无所谓传递。
即使各方都认同见义勇为本身具有褒义属性,但争议的发生在儒家看来原本就在所难免。孔子曾言:“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此道非彼道,各人自有取舍,必然会发生彻底的歧路分化。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尽管他们面对着同一件事,但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价值持守。孔子又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别人不理解我,我却不埋怨,君子本来就诞生在人们难以具有相同的道德判断的交往情境中,如果人人都成了君子,终究致使君子人格具有了廉价品性,那就无所谓君子。道德判断一旦出现差异,就会表明道德本身并不具有必须性、高度的同一性和稳固性,而是具有应当性、高度的离散性和可破解性。具体体现为,任何人的任何一种判断,首先都会以第一人称获得表达,即我认为应当怎样,以此为基础,接下来才会出现我是否认可你的判断的情况。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反而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反应。任何人倒地受伤都会在身体上产生疼痛,尽管人们的耐受程度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生理反应本身必然存在,否则就只能说明受伤部位正在或者已经失去原有功能。无论是谁,若是发现有人受伤,其实都能感同身受地知道伤者的身上存在疼痛,就有可能会见义勇为,或者已经那样做了,但在是否相撞和帮忙救助的问题上,人们的判断毕竟不同。彭宇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致力于促成双方和解,徐老太一方最终同意减少赔偿数额,撤回了起诉。和解的背后其实是调解,借用调解促成和解,有时正是法院和办案法官规避风险的一种策略。直到多年以后,彭宇承认确系自己撞倒了徐老太。说到底,儒家倡导的见义勇为固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它未必总是能够获得实现,仅凭道德来维持人际交往并不可靠,借助于法律予以助推便获得了必要性。
善意救助责任豁免不曾存在于《民法总则》出台以前,的确是一种崭新的制度,但该制度的出台无疑根植于儒学土壤。一审中出现的责任分担,法律依据正是适用于其时的《民法通则》第132条,即双方若是都无过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担,完全不同于第106条规定,因过错而侵害他人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学者指出,后者在各国法律中极其常见,前者则具有中国特色,彰显着中国人所看重的人际关系并不是西方式的个人权利,这难免就放低了在双方权利的对垒中凸显出来的过错追究,实为借据于儒家恕道作出的创设。[11]根据儒家恕道的理论:我不愿意受到损害,想来你同样如此,你若是因我受伤,而我并非故意,不妨分担损失。无过错责任分担制度由《民法总则》并延用于《民法典》,无疑可以成为可资借鉴的经验。责任豁免制度的诞生其实只是让法律契合儒学的已有立法序列。
三、见义勇为的已然实现与法律助推
就小悦悦事件[12]的基本情况来看,路况摄像显示,某天傍晚,两岁女童小悦悦跑到马路上玩耍时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又被一辆货柜车碾压,两位司机都选择了逃离。接下来,先后共有十八位路人路过,有的只是有所张望,最终选择视而不见,有的虽有所迟疑,但还是漠然而去,有的行色匆匆,更是没有救援,直到陈贤妹的出现,小悦悦才被救了起来。时隔片刻,家长赶到,一起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相较于肇事司机和十八位路人,陈贤妹的确应该获得赞誉,但她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作为人应该做的见义勇为。尽管她不识字,难以从事收入可观的工作,靠拾荒为生,但辞却了各界提供的奖金和善款。她曾明确表示,最为重要的就是救人,当时根本没有想别的,并不曾想要获得金钱,更不是想要借机出名或者出风头。[13]显而易见,陈贤妹的举动完全契合于儒家所说的孺子将入井的事例,从头到尾呈现出的正是不计回报乃至无所预期的全情付出。如果她同样是位母亲,那么她的举动又契合于家庭伦理的外溢,实现了幼吾幼的类推和爱的起承转合式的传递。
同时,她的举动还契合于儒学的最为核心的理念,即仁。有学者指出,仁者亦人,人必须彼此以人相待,认可他人属于与我同等重要的主体。[14](P93)发现有人倒在血泊中,若是视而不见,其实不仅没有表达出人们应当相互关爱的态度,更是践踏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尺度。所谓仁者爱人,就是指人际交往中蕴含着一种旨在促发人与人应当相互确证和关爱的力量。陈贤妹无疑能够算是儒家所肯认的勇于担当的仁者,更是以义为上的君子。在君子人格属于稀缺资源的社会环境中,君子称谓只能被用来赞誉那一小撮人,在道德情操上的确难能可贵。另外,陈贤妹更是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了一番儒家的忠道理念,即她在自身范围内把陌生人放置到了并非无关紧要的位置,恰与孔子在自身范围内好学不厌如出一辙,同样属于欲立欲达,她把关爱情怀发挥出来,让小悦悦在离世前获得了来自于血缘亲情以外的温暖,又与孔子在自身范围外诲人不倦如出一辙,自当属于立人达人。
正如孟子所言,“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何须识字”,关爱他人的品格原本就来自于自身固有的向外发挥。既然自身固有,那就不会完全受制于社会环境是否趋于恶化,环境再恶劣,其实都无法彻底泯灭人的本性。有的人何以没有向善,恐怕只是因为本性被遮蔽,并不意味着全盘丧失。若是早已全无,又岂是通过立法就能够拯救的,立法助推的意义并非是要往人们的身上重新注入本性,而是只在于除蔽和唤醒。毫无疑问,在《民法总则》出台以前,社会上原本就潜含着若干儒学理念,而且早已在有意无意间获得了实践,既不以人们事先获知为必要,更不需要当事人明确言说自己是儒者,甚至不需要人们必须具备阅读儒学文本的能力。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在人际交往中确立和陶冶自己作为人的品质,就具有了加入儒家门庭的潜质。如果又以爱人的情怀展开交往,那便已经是儒者。各种文本在社会上流传被阅,固然可以助益于人们提高情操,但在自由度上,终究不如儒学理念自身原本就能够在人们的日用常行中获得实践,意味着即使要通过法律来助推儒学理念获得实践,其实全无必要配套性地加持对儒学文本的高举。诸如陈贤妹等人,既然关爱他人的品性肇始于自身原有,那么在面对小悦悦以外的其他人的时候,自然同样会伸手援助。见义勇为一旦在频次上带有了多次性乃至日常性,就会演化为助人的习惯和乐趣,使得助人者能够感受到助人为乐,日后更加乐于助人。助人越是趋于表现为一种习惯,助人时就越是能够抛开自身以外的任何条件,使得助人在习惯的层面上成为一种必然。何以至此,就在于一旦不再助人,就会使得当前的所思所行与以往的习惯发生断裂,继而无法再借助于习惯的连续性来定位自己,更是挑战了原本一直由习惯来加以持续维护的道德觉悟。
立法机关对儒学的助推,其实同样不以事先获知儒学为必要,更不需要具有明确的认可和接纳意识,只要能够立足于社会提取相应的理念,迟早都会在无意中或者悄然间触碰到儒学。若是事先曾有获知,再予以明确认可,那么所认可的就并非只是儒学本身,更是认可儒学理念一直存在于社会,并且一直在为社会的发展供应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十八位路人冷漠的表现给各界带来的感受可谓一人向隅,满座不乐,恰恰就是在此时,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正是儒学,陈贤妹毕竟就在事中和眼前。人何以为人的根本问题越是受到考验,就越是能够证明儒学不仅有能力而且一直守护着社会发展。满座不乐的氛围中,无不酝酿着让法律助推见义勇为具有必要性的认知。善意救助责任豁免制度并不是诞生在社会风气早已全盘糟糕的时代走势中,甚至正是因为仅凭儒学理念原本就能够引致出见义勇为,方才让它具有了能够获得落实的可行性。见义勇为若是从来都不曾获得过实现,它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法律总不至于要去规定一件在社会上无法发生的事情,尽管它的问世和后续的长期存在作用于人际交往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否认它并非处在孤军奋战的状态。
四、见义勇为的实现概率与法律助推
见义勇为能否实现,在小悦悦事件和彭宇案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其间难免存在着概率问题。尤其是在前者,除了原本就应该承担责任的肇始司机,路过现场的,包括陈贤妹在内共有十九人,见义勇为的实现概率仅为十九分之一。更有甚者,据调查,尽管人们都认为冷漠绝非人际交往的应有状态,但只有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若是在场一定会救助小悦悦,有27%的受访者表示可能会伸手援助,有16%的受访者表示拿不定主意,更有7%的受访者表示不会伸手。[15]正如现实主义法学派所言,在一种异质而且持续变迁的社会情境中,当主体性沉思转向主体间的交互行为时,本来就极易混生出一种意在反对尘世认知能力有限的人类妄谈究因、绝对和必然性的发展势头,取而代之以偶然乃至可打赌性的怀疑论气质。[16]拿不定主意或者只是可能会伸手,意味着人们对救人后将会出现何种不确定的情形存有疑虑,追根溯源,甚至不需要展示更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仅从彭宇案的发生来看,早已在各界引发了阵阵恐慌,致使包括彭宇在内的任何人再次看到有人倒地,难免就会在思考上产生一种该不该搀扶的可打赌性游移。若是搀扶,但又害怕事后被讹诈;若是不搀扶,终究挑战了自己的德性觉悟。唯有赌定被扶一方事后不会讹诈,才有可能把德性觉悟发挥出来。十八位路人选择漠然而去,但又毕竟有所张望乃至迟疑,皆属于可打赌性游移的具体表现。
陈贤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没有选择从众,况且她所做的并不是一件难度系数较高以至于别人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而是一件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做到但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人何以为人的儒家的最为核心的理念,在十八位路人的态度中已经变得模糊了。何谓最为核心,通常是指已经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无法再退步的起点或者原点式理念。责任豁免权诞生的意义正是,在人何以为人的定位渐显模糊的时候,有针对性地让人们确保自己的确是人,它所要扭转和破解的,则是救与不救之间的可打赌性游移,即使无法让后者彻底消失,仍要为人们选择前者而壮胆。各界曾给予陈贤妹高度赞誉,恰恰又说明社会上原本就存在着对见义勇为的明确认知,于是责任豁免权的诞生并非要教导人们怎样才能够见义勇为,而是意在通过提供制度支持的方式,让人们免除后顾之忧,以便于更多的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见义勇为。
只要能够见义勇为,即可具有责任豁免权,意味着行为中潜含着儒学理念能够成为权利获取的根本缘由,说明法律规定与儒学理念可以依循合二为一的走势发生合并。有必要强调的是,就此并不会产生一种超乎于儒学和法律以外的新型儒学理念,更不会产生一种介乎于儒学与法律之间的新型非法律规则,而是只会产生一种与其他法律规定相类似的规范,无过错责任分担制度亦是如此。被法律吸纳的儒学理念仍旧会在法律以外保持着自身原有的独立性,意味着仅凭儒学理念即可实现见义勇为的情形仍旧会存在,儒学与法律还会发生松散性合作,以并行的姿态共同作用于同样的社会问题。概率问题一旦显示出来,免不了需要归纳出两者以怎样的方式合作,即它们同时处于被选用的状态,仅凭儒学若是能够引致出见义勇为,权利就无法获得出面应对的机会,唯有在儒学未必总是能够发挥出作用的时候,权利才有可能会出面,意味着儒学通常居于前台位置,权利则置身于后台,儒学是否足够有效,能够对权利由后台进入前台产生引擎作用。
尤其是并行合作,潜含在其间的人际交往秩序框架,完全契合于儒家的相关论断。孔子有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如果说礼乐实为外在于人的制度或者规范,那么仁便是内在于人的德性。孔子固然是在强调礼乐以仁为基础,但点破了存在着人而不仁的情形,即仅凭内在的德性来维持交往未必可靠,人一旦不仁,哪怕是礼乐都无可奈何,说明仅凭外在的规范来维持交往同样未必可靠。孔子又言:“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己无疑同样指向人的内在,交往的维持则需要克己与复礼的内外结合。无论是让克己涵涉复礼,还是相反,一内一外的构设都是一种稳定的存在。此种框架,至今虽有演变,但已经获得了彰显。尤其是就陈贤妹的表现来看,内在的德性无疑获得了精彩的发挥,演变的地方只是体现在外在的规范上,诸如是否涉及侵害他人的问题。在孔子的论域内,通常需要借助于礼来评定,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经由古今社会转型,礼早已式微,在当代则要借由法律来评定,而且法律同样具有外在于人的属性,区别只是在于,它囊括着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是传统的礼所不曾具有的。在当代社会,便出现了德性与法律一内一外相结合的秩序构设框架,意味着传统的克己复礼已经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框架的形成得益于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塑造,若是只考虑到前者的推崇,就会使得儒学只能依赖自身以外的力量被放置于社会。既然可以被放置,那又何尝不能被去除,意味着儒学的存身要取决于被放置与被去除的拉伸,难免就降低了它源于自身的自主性。唯有认可它并非只能从立法态度中借机谋求存身,而是属于社会自身的原本自带,方才可以促使它的自主性获得强化。
五、见义勇为的法律助推与终极关怀
正如美国的《撒玛利亚好人法》展示出来的那样,西方通常需要借助于基督教来谋划人的需求。有学者曾指出,区别于中国社会一直把儒家的忠恕理念视为道德金律,西方则把金律定位在上帝的承诺上,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别人,方能永生。[17](P295)如是观之,西方人的互动总是加持着上帝的隐形在场,人际对话中潜含着神人对话,尤其是在甩开了中世纪式的教会对人的捆绑以后,人人都可以和上帝独立沟通,哪怕只是作为凡俗社会的一种个体化存在,都可以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终极关怀和温情,接受来自天堂世界的光亮投射,人际交往如同炒豆那般即可,无论怎么加温烹炒,豆与豆始终都保持着明确的独立性。中国人的需求若是无法从基督教那样的超验信仰中获得满足,势必就会依赖密切的人际交往,即便孔子被视为圣人,都要置身于凡俗社会,更何况是其他芸芸众生。人们只能呈现为一种关系化的存在,谋求抱团取暖,只要彼此珍视儒家言说的正能量,就会让交往展现出煮粥般的状态,各种粮食颗粒在水的凝合中相互牵连,共同塑造着营养混融的社会环境,意味着中国人需要从儒家那里获得终极关怀。
孔子有言:“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但人能弘道,不能因为知者甚少就要放弃弘道的希望。正所谓,儒学从来都不企望超越人性,但一直致力于完善人性。[18](P871)孔子又言:“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若真心求仁,就切莫以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子贡曾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同样的道理,爱的起承转合式的传递一旦遇上阻力,立即就会显示出人人相爱存有限度,极力凸显着爱有差等。既存在人人相爱乃至爱无差等的走向,又存在爱有差等的困顿,两种说法并存,其实并非自相矛盾,而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言说的,如果说后者指涉现实的话,那么前者就指涉理想。正如学者所言,现实的人通常不会满足于现实,总是想要把眼前的现实变成理想中的现实,各种实践活动就是要促使世界变成按照人的理想所创造的客观存在。[19](P121)理想与现实的并存,凸显着两者具有前后递进的关联走势,尤其是理想,何以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指引方向和提振引领。
孔子谈仁论德,无疑能够为人们的日常交往提供一种立基于现实而又面向理想的维度,甚至直接给出了值得憧憬的图景。孔子曾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卫灵公》),说明儒家的理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未曾获得全面实现。历史的河流裹挟着它翻涌而来,时至今日,仍旧没有人能够把人人相爱的世界全面地放置到世人的面前。人际交往的尴尬事件何以能够引起阵阵恐慌,反向说明人们致力于寻求一种善美的社会景致,如果早已不再寻求,那便无所谓恐慌。现实越是糟糕,越是能够反衬出理想何其绚烂,就越是吸引着人们孜孜以求。如果说当代人依然把旧时理想当作当前乃至未来要去实现的理想,那就可以说人人相爱本来就属于儒家的永恒追求和终极关怀。儒学何以能够自古流传至今,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它一直对人们的善美追求予以觉悟和守护。尽管彭宇案把理想一举打碎,但陈贤妹的举动又能够托举出理想,甚至可以产生能近取譬的示范效应,势必会促发人们对理想愈加确信,彰显着理想并不等同于空想。
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法总则》出台以前,陈贤妹就已经做出了责任豁免制度想要助推的义举,说明儒家的理想和终极关怀并非只能受到法律的助推才可以获得落实。即使在《民法总则》出台以后,若是仍旧有人见死不救,也不能作出惩罚,因为责任豁免制度的功能释放只是在于鼓励和激励,并不带有必须性和强制性。唯有已经涉嫌见义勇为,却引致纠纷,才可以成为免责的依据。这说明它只是一种可以用来解决纠纷的制度,避免出现助人者毫无权利可言的状态,并非要致力于让纠纷在社会上彻底消失。纠纷是否会消失,终将取决于儒家的理想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落实。责任豁免制度的出现,正是要修补社会上对儒家理想的持久追寻中出现的缺口。若无纠纷出现,它就不会被拿来适用,意味着即使到了应对纠纷和儒家理想如何实现的层面上,它仍旧居于后台位置,前台出现的则是儒学,因为纠纷的产生原本就肇始于针对见义勇为所发生的争议。儒学与法律通过前后台接力的方式作用于理想的实现。
总而言之,通过法律助推儒学理念获得实践,至少具有五种层面的意义。其一,促使与见义勇为相关的各种儒学理念获得了制度的加持乃至崭新的载体,不再像《民法总则》出台以前那样,只能寄身于人们的日用常行,并且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在儒学文本中。其二,在《民法总则》出台以前,儒家的理想和终极关怀哪怕能够获得落实,但只是借助于概率较低的民众自觉,立法力量参与进来,无疑是要让儒家化的社会秩序获得大面积的实现。其三,法律原本只是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依据,只要问题能够获得解决即可完成任务,一旦携带上了儒学元素,势必就会把儒家的理想和终极关怀囊括在自身,甚至具有了更加远大的宏伟目标。其四,转型中国的绝大多数法律制度都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只有极少量的来自于本土创设。外来法律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切于中国社会,哪怕仅凭历史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提供的理论,都足以引发质疑。借用儒学塑造制度,恰恰能够起到就地取材的功效,可以助益于法律更接地气。其五,自20世纪以来,儒学屡遭批判,前有新文化运动,后有批林批孔运动,即便某些法律制度早已有所吸纳,恐怕都未必能够获得各界的一致认可。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所产生的实为倒逼效应,鼓舞着各界恢复对儒学的确信。责任豁免制度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能够以更加有力的姿态,打破此前人们面对儒学难免还是会讳莫如深的制度壁垒,让儒学的古今传承可以借力于立法的推崇。
注释:
①据基督教《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交代,耶稣曾言,有人半死不活地躺在路上,路人视而不见,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路过时,给那人包扎了伤口,还带回旅店里照应。
②关于见义勇为,在儒家的义利二元界分中,凡是不以取利为目的,勇于担当的助人乃至救人,都可以算是见义勇为,甚至包括一切好人好事,范围较为宽泛。法律上强调的则是,极易引起争议的紧急情况下的助人,甚至关乎人的生命健康等重大情由。情由若是较轻,仅由道德即可独立应对,原本就不易进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在《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立法的过程中,社会各界一直关注一些典型案例,在展开讨论时,以言说前者更为常见,也更接近流行性社会认识,因而本文便顺沿此语境界定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