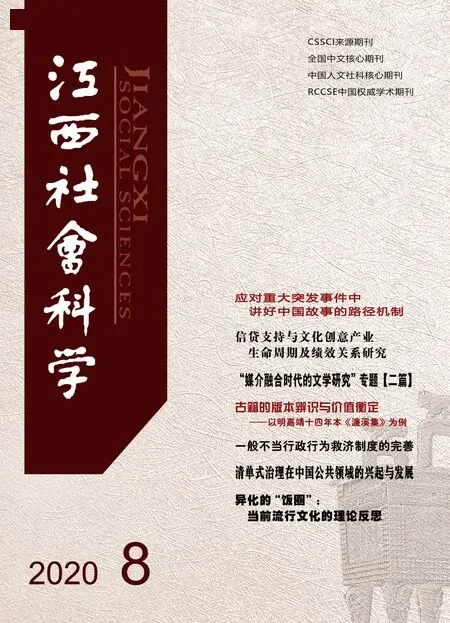媒介融合语境下文学之“危”与“机”
2020-02-11乔世华
■乔世华
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文学命运的思考,离不开媒介这一聚焦点。首先,纸媒文学的衰落趋势明显,这与印刷媒介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不得不把话语权让渡给新媒体大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终结。其次,普通读者获得了更多的文学评判权,其审美趣味得到了专业读者的尊重,对于重新审视文学经典和认知作家作品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文学的媒介属性得到凸显,“媒介文学”得到正名,同时倒逼人们对文学本质问题展开更多有意义的思考。
媒介既是技术,也是讯息,更是动力,其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崛起和壮大就得益于晚清之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快速发展。当我们提到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徐志摩、梁实秋、戴望舒、林语堂等闪耀的文艺群星及其作品时,不禁会想到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青年》《语丝》《创造》《小说月报》《申报》《晨报》《大公报》《新月》《现代》《论语》等各种报刊,以及以这些报刊命名的文学社团、流派和奖项。可以说,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媒介史。故此,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思考文学的命运问题,现代媒介这“第五要素”亦应作为一个聚焦点。毕竟,“技术,从其起源时刻开始,就与人类本质属性互相联系”“人类内在的精神组织特性一旦形成,技术手段就会支持和放大人类的表达能力”。[1](P11)
一、纸媒文学的衰落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2](P135)80年前张爱玲在时代变动、文明交替之时发出的如是感慨,放到今天来看,更像是对文学写作在媒介融合时代遭到冲击的精准预言。2000年,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中国作过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演讲,其中有关“文学终结”的看法一时引发学界热议:“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3](P132)这是他在对电信业强势崛起和印刷文明渐次衰落的事实有了足够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同时期,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马原也表示“小说已死”,甚而以“博物馆艺术”来形容小说,后来还对此有解释说明:“我说‘小说死了’,是说小说在公众广泛接纳和阅读的意义上越来越不重要了”“读图永远比读字更直接,一个画面比一部长篇小说更有力”。[4](P55)的确,当人们有了更多或者更好的文化选择如电影、电视、戏剧、游戏、资讯、网络以后,为什么一定要把阅读小说作为不二的选择?
印刷文明培养了人们阅读文字的习惯,也构筑了人对文字的敬畏心理:“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5](P47)与此相关联,文学受重视、对人发生重要影响的案例比比皆是:托尔斯泰被视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据称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卡逊《寂静的春天》激起人们对环保问题的强烈关注;鲁迅弃医从文以疗救国民;一些青年因为阅读了高尔基、蒋光慈或者巴金的小说而动念投身革命……类似文学改易人心或改良社会的说辞、案例或许会有夸张之处,但文学导引人精神成长、帮助人认识社会的巨大功用是不必否认的,毕竟文学是人们重要的情感表达场域和宣泄通道,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受万众瞩目是当然的事情。进而言之,文学能够如此风生水起,实得益于赋予其安身立命场所的纸媒的发达,得益于纸媒长久以来所汇聚的社会公众的热烈目光。不过,当更多新媒体出现并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纾解和分流了纸媒承载思想认知、提供言论表达空间的功能后,纸媒的受关注度也随之下降,纸媒文学的影响力被削弱,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不可能一边读狄更斯、亨利·詹姆斯 (Henry Janmes) 和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一边看电视或者录像带上的电影。”[6](P17)
“媒介融合”的提法很容易让人只注意到不同媒介之间“相爱”的温情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相杀”的残酷一面。其实,即使是在印刷传播时代,纸媒之间的相互竞争也都是不争的事实。90年前,当法国文学史家保罗·阿扎尔注意到一些成人唯一的阅读媒介是报纸而非图书时,就表达了“对书本的捍卫”的强烈愿望,极力主张培养儿童拥有终身与书本相伴的习惯。[7](P2)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报刊上关于“连环图画的害处”“连环图画为害最烈”“教局会同警厅取缔连环图画”的新闻报道和“小人书影响小学生甚巨,教育当局亟宜改进”“请当局取缔连环图画”的呼声屡见不鲜;抛开其时连环图画内容上可能的怪力乱神不说,这当中透出一个很显然的信息:同为纸媒,连环图画比纯文字读物更容易吸引眼球。
至于媒介融合时代电子媒介之间的竞争、电子媒介与纸媒之间的竞争,更是有目共睹。尼尔·波兹曼在写作《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时,还是电视蒸蒸日上、咄咄逼人而印刷文化步步后退让出地盘的时代,那时他就注意到把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二者结合起来的电视“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有着很强的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5](P104-105),因而慨叹“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8](P8)。继电视之后相继出现并甚嚣尘上的网络、掌上电脑、手机等新媒体发威之时,印刷文明遭遇的困境只会雪上加霜。近十年间国内已经有超过一百家报纸关门歇业,《译文》《大家》《万象》《天南》等文学期刊也先后停刊。国外情形同样不容乐观:“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3](P137)俄罗斯最古老的文学刊物《文学报》在最盛时期每期有650万份发行量,而在今天只有20万份发行量,其总编尽管相信“报纸不会消亡”,但也还会为数字阅读正在取代纸媒阅读而感到无能为力:“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吸引年轻人读报纸。我每天都乘坐地铁。记得以前,地铁上每个人都手持一份报纸,而现在没有一个人看报,所有人都在看手机。当我看到有年轻人在读《文学报》的时候,我甚至想给他们点钱,好让他们继续下去。我在大学里教新闻学,大学生也不读报纸,报纸文化已经过去了。”[9]就在2020年春天,有着67年历史、期发行量曾高达700万册的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亦宣布停刊,并计划未来向数字媒体转型。《花花公子》的纸刊“终结”与未来的数字化“新生”,都更像是印刷媒介从话语大权独揽到把权力让渡给新媒体的一个缩影。
当人们有了更多的精神文化通道可以走,阅读文学作品就自然成为众多选择中的一种而非唯一道路。要了解当下世间百态,一张新闻报纸未必就比一部文学作品的信息量少,而可以即时获取各种渠道消息的手机甚至令报纸、电视、广播、电脑相形见绌;要消遣娱乐打发时光,阅读一本小说不见得就比看电影、追肥皂剧观、电视真人秀节目或刷手机高明多少;要抒发愤懑或喜悦之情,在网络上发帖子、在公众号里留言、在微信里发朋友圈,可能要比暗寓褒贬、曲里拐弯的文学表达来得更及时迅速,显得更透明敞亮。希利斯·米勒正是在看到了纸媒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颓势后,而发出了“文学终结”的预警,因此其实际指向的是纸媒文学。对于文学本身,希利斯·米勒还是充满信心的:“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6](P7)只要人类有情感生活与思想表达的需要,则文学当然会伴随人类命运始终,至多就是表现形态和涵盖类型会有不同。口语传播时代里应运而生的说唱文学,并没有因为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或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就偃旗息鼓,在今天依然强劲地生存着,只是不再独占鳌头而已。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始于17世纪末的西欧,那时回忆录、历史书、书信集、学术论文等都属于文学范畴之内,把文学只限于诗歌、戏剧和小说属于更晚近的事情。[6](P8)同样的,中国今天所认可的“文学”是在20世纪初得自于西方“文学”概念的启发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之前相当长时间里,“文学”都指的是文献之学,亦即关于古典文献的学问,至于今天被我们视作文学之大宗的“小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不受待见,要到了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后其地位才得到大幅提升。
回到纸媒文学的话题上来,纸媒文学的危机说到底是人对文字和文学阅读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早就存在,或者表现为对经典著作的盲视和拒斥,或者表现为对影像追逐的热情胜于文字。而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媒介融合时代,人对需要走心动脑的文字阅读的轻慢、对能让阅读富有尊严与仪式感的纸质媒体以及这背后的庞大文学历史的冷落,只不过令阅读危机表现得更严重罢了。不过,纸媒文学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毕竟其身后有着数百年历史、已形成相当威权和公信力的印刷文明在为它做背书,更何况媒介融合时代也需要各种类型的媒介争芳斗艳、多元共生以全方位地满足不同人群读、视、听的需要。即使有一天纸媒黯然退场,也不过意味着文学找到了一个能更好地安顿自身的合适媒介而已,就像当初文学弃繁重的龟甲竹简不用而选择了轻便廉价的纸张那样。
二、读者地位的提升
与纸媒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电子媒体的春风得意,互联网和手机正独领风骚,已成为当下我国成年国民阅读中高度依赖的主要电子媒体。“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的相关数据就指出了这样的阅读现状: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9.3%,较2018年的76.2%上升了3.1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在12年间保持持续上涨的态势,从2008年的24.5%,增长到了2019年的79.3%。[10]虽说数字阅读还不可能完全取代纸媒阅读,但数字阅读却在加速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和阅读生态,并且赋予了普通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使之能点赞打赏、畅所欲言,可与作家、评论家、编辑等专业读者及其他读者之间展开即时迅速的对话。
在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之前,评判作家作品的优劣,往往是专业读者的事情。普通读者若是没有一定的专业训练,不经过严格审核层层筛选,很容易缺席文学裁判。一些文艺评奖活动如“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百花奖”等虽也会向普通读者敞开意见大门,但最终往往会在专业读者的操控下定下乾坤。因此,很长一段时期,文学“读者”的概念实际上是被少数专业读者构想出来的,即或有时一些批评文章会刻意标注出读者的“工农兵”“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之类的平民身份,也很可能实际操刀者是某位理论家或权威读者。也就是说,在纷繁的文学现实面前,普通的大众读者通常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到媒介融合时代,普通读者可以在网站、留言板、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公共空间直抒己见,表达个体的阅读喜好与诉求,而世界也乐于关注普通读者的声音。于是乎,普通读者不再单向度地被作家、批评家塑造和引导,其同样也会引导和重塑作家、批评家。譬如,本来一本令编写者们自鸣得意的图书早就编排印刷就绪,只待时机成熟推向市场,在声誉和金钱上赚个盆满钵满,孰料在预热推介过程中遭遇到天南海北读者一片吐槽声,这本“书”随即就胎死腹中、烟消云散。又如网络文学作家在更新连载作品时会特别关注追更读者的即时阅读反应,读者对后续作品情节走向和人物塑造的建言献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会被作者照单全收,如纯洁滴小龙之写作《深夜书屋》;或者会被作者刻意违逆,如噬纸狂魔之写作《神臀证道》。夸张一点说,普通读者对一本书或者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握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利。当普通读者发表批评意见的渠道畅通,引领文艺争鸣、命名文艺现象、为中意作品“打Call”的权利,就不再专属于专业读者了,普通读者亦可置喙。对某个文学奖项评奖是否公正的认知,就某某作家是否有资格得奖的讨论,对作家之间笔战是非的评判,或者对“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诗歌的命名,普通读者都是最活跃的“吃瓜群众”。专业读者不屑不愿不敢也无暇无心关注的文事,普通读者偏像那横冲直撞的黑旋风一样善于也敢于从中寻找到兴趣点,虽说没有专业读者长篇大论的四平八稳架势,虽只是三言两语也未必有什么学理性,却爱憎分明、快人快语、一针见血,绝不云山雾罩、吞吞吐吐、口蜜腹剑,这种“酷评”给文艺带来的活力与批评生态格局上的改变,是值得肯定的。
正是因为普通读者能直陈己见,其与专业读者在文学见识上的分歧得以浮出水面,而他们之间审美上的罅隙与分裂恰好是值得探究的富有意味的地方。譬如金庸武侠小说、杨红樱童书、郭敬明青春文学等,会被相当一部分专业读者认为去纯文学甚远,会被批得体无完肤,而普通读者却对他们的创作爱不释手,令他们的作品一印再印。又如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张悦然主编的《鲤》等青春文学刊物以及“国民刊物”《读者》《故事会》都是不会入专业读者法眼的,但在上万名网友打分评选出来的“年度文学刊物十强”中,这些刊物与《萌芽》《小说选刊》《收获》《人民文学》《译林》《青年文学》等纯文学刊物同聚一堂,甚至《最小说》还高居榜首。再如由众多网友吐槽投票推出的“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行榜上,《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 等经典赫然名列前十。类似文学认知分歧在早先就可能存在,只是普通读者无缘发声,遂得以长时间被掩盖,唯有到了媒介融合时代,普通读者的真实阅读取向、体验、意愿和兴趣才能得到彰显,其对既定文学秩序和既有文学经典的“离经叛道”才可能得到公示,文学阅读和接受的真实图景才水落石出。在从前,作品经典与否、作家称职与否,完全由专业读者来评判,但专业读者在这当中是否推敲人际关系、能否剑走偏锋、有无挂一漏万,这都很难说。但看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被一代又一代专业读者反复书写,诸多作家在文学史书中时隐时现,评价时高时低,即可知道专业读者并不总是目光如炬、慧眼识英才。掌握话语权的人不一定掌握真理,古今中外诸多名家经典初时不被专业读者理解的例子同样可以佐证这一点:儒勒·凡尔纳的《气球上的星期五》连续遭到15家出版社退稿;司汤达期待《红与黑》能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后被人理解;惠特曼《草叶集》常常被文坛大腕们不屑一顾地掷进炉火中;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最开始并不被认为是好作品;陶渊明、杜甫、威廉·布莱克、爱伦·坡、本雅明、卡夫卡等生前文名寂寞……因此,普通读者的声音与专业读者的论断和衷共济、此消彼长,可避免其中任一方对某部经典或者某个作家作品评价的一锤定音。毕竟,在文学鉴赏和评判方面,专业读者并不总是全知全能、大智大慧,普通读者也并不总是目光狭隘、根基浅薄,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既可以美美与共,也可以各美其美。因此,如果我们能“兼听”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阅读反馈,则可得“明”,获得对作家、经典、文学史更清晰、客观、准确的认知。这该是媒介融合时代之于文学的一大福音。
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之间出现阅读分歧很正常,也并非不可调和。专业读者可帮助普通读者提高文学修养,普通读者的阅读意见也不会对专业读者毫无助益。事实上,媒介融合时代,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与喜好得到了专业读者的足够尊重与“迁就”,成为专业读者衡量经典、评判作家的一个重要参数。到今天,金庸、杨红樱、郭敬明的文学作品或者被认证为经典,或者得到研究者的首肯,或者获主流文学界的青睐——《人民文学》和《收获》等权威期刊先后刊登郭敬明长篇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和《临界·爵迹》,这都是传统文学势力适应时代审美风尚变化而向普通读者“示好”的表现。所以,我们也不必奇怪,麦家那部依旧例该归入通俗小说之列的《暗算》、金宇澄起于网络的小说《繁花》先后问鼎茅盾文学奖,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文学评委闻时代之风而动走出象牙塔、正视普通读者阅读趣味而适时调整评判标准,自然会有这样的评奖结果。“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5](P44-45)于是乎,一时代有一时代所认可的文学、所欣赏的作家,一时代也就有一时代所弄潮的读者、所追逐的风尚。而且,普通读者的评判会激发专业读者对“经典”品质或作家资质进行认真探讨的热情,进而活跃学术气氛,譬如北大教授对“四大名著”不适合孩子阅读的认定,譬如复旦教授将绝大多数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列入“不必读”书单,譬如农民、工人、月嫂等草根写作者的作家身份认定。没有普通读者地位的提升和相应审美诉求的表达,上述“异端”声音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媒介融合对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开展对话的有效促成。
三、媒介属性的凸显
印刷传播时代,众多文学期刊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学场域即文坛,对此场域表示认同的编辑、作家、评论家等专业读者形成了文学圈子以及相应的审美标准。值得提及的是,文学期刊当中还有严肃与通俗、纯正与商业之等级、品质差异,就像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哪怕期发行量超百万册、拥趸者众也还是不权威,某些纯文学刊物哪怕只发行几千几百册、门可罗雀也还会是文学高地的标杆,后起之秀唯有在这样的权威纸媒文学圈子里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才算登堂入室。但媒介融合时代,作家发表作品的途径已不再局限于文学期刊这“自古华山一条道”了,写作者既可以直接出书走市场,也可将作品放到网站或者博客上与人分享,更无须担心没有专业读者来为自己作品买单或喝彩,只需大众读者认可,哪怕是孤芳自赏。当然,在抱持传统观念的专业读者看来,承载文学肉身的期刊、图书和网络这三种媒介还是有质量等级的参差的:级别最高的是期刊,走市场的图书等而次之,网络是最不入流的,即使网络拥有再多的浏览量,即使图书卖得再好,即使纯文学期刊门前冷落车马稀。2006年发生的“韩白之争”就很好地证实了文学界存在着的这条“鄙视链”。
2005年白烨在文学杂志《长城》上发表《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后还无声无息,但当他转过年来将该文挂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时,立刻遭到了“80后”的韩寒在新浪博客上的迎头痛击,二人间自此所发生的论战以及后来相继加入这场“厮杀”的众多作家评论家们的意见大都是发表在网络(博客)空间上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媒介融合时代,纸媒(文学期刊)的影响力要逊于新媒体。同时,这场引人瞩目的“韩白之争”实则关乎到了作家、文学的“资格认证”问题。遵循印刷传播时代文学游戏规则的白烨坚持认为,“80后”作家唯有先在权威纸质文学期刊上亮相,才算真正走上了文坛,否则,就算在出版社出再多的书,都还只是文学“票友”。但在韩寒看来,能在公共媒介上发表文学作品,就都应该被视为作家,而且绝不应该以作品见诸何种媒介——是期刊还是图书抑或是网络——来判定质量的高下优劣、作家身份的真伪大小:“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因此,韩白之争的实质是文学观念之争、文学媒介认知之争。而当现代电子媒介迅速获取舆论高地并强势介入文学后,文学的媒介属性得到了再清楚不过的彰显,媒介文学被很好地正了“名”。
以网络文学为例。当其刚刚在网络上露出尖尖角之时是被视作文学性的网上游戏的,但在今天已然名正言顺,有众多研究者在为建立网络文学专属的评价体系而绞尽脑汁。中国网络文学已被认为堪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和韩剧相媲美,其活力、受关注度、市场占有份额等均非昔比。历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上网络作家收入之高令人咋舌,这证实了网络文学受众之多;众多的热播影视片改编自网络文学作品,这说明网络文学影响力之高;在全国性的青年作家会议上网络作家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各省市纷纷成立网络文学作家协会,研究网络文学的专家学者和机构越来越多,有为选拔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而设立的诸种专门大奖,甚至就连传统权威文学奖项也对网络文学网开一面,这些均可以证明网络文学所受到的重视和礼遇。事实上,如果要获知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景象,也唯有将纸媒文学与网络文学这两种媒介属性不同的文学放在一起考察才足够客观全面。可以肯定,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写作、阅读、研究格局所造成的强有力冲击还会继续,文学版图的重新绘制势在必行。这一切不能不让我们认同如是的判断:“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5](P32-33)
印刷传播时代,作家是人群当中少数可以在纸媒上拥有话语权力的人,因而会得到“无冕之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各种加冕,那情形就与从前文言至尊时代把持文坛的书生对只会操持大白话的众多引车卖浆者流造成威压之势一样。但当媒介技术发展到可以为人的文字表达提供畅通渠道时,则赋予了全民写作以可能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我手写我口”,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抒发自己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之情。就像桀骜不驯的韩寒在“韩白之争”中所公开声明的那样:“别文坛不文坛,每个码字的都是作家,每个作家都是码字的。”这当然褪掉了笼罩在作家和文学身上的神性光环,有让作家平民化或文学普泛化的“危险”,但这对促进文学品质的提高不无好处。写作不再是专业作家的特有权利,人人都拥有了言说的空间、阅读的意愿和写作的欲求,文学最广泛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得以形成。那些顶着“国家一级作家”“获奖诗人”或作协主席等桂冠的专业写作者与凡夫俗子比较起来理所应当技高一筹,若是专业作家吟诵出来的诗句被发现不过是用回车键分行的大白话、是围绕着“天上的白云”、超市里的梨来回说的车轱辘话、是“自慰自乐管不住”的打油诗,则他们的身份和写作当然要遭到普通读者的质疑与耻笑。换言之,媒介融合时代,以文学为主业的写作者需要才与位匹配、名与实相副才行,这还意味着文学写作要郊寒岛瘦、字斟句酌,切不可随意涂鸦、下笔匆匆。
其实,媒介融合时代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倒逼”人们重新认真思考文学的本质问题。在过去资讯稀缺之时,文学是很好的认识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载体。可是,当无孔不入的媒介携带着大量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新闻资讯铺天盖地而来之时,人们会发现,不必借助文学也照样能够清晰地认识世界、了解人生,而且很多时候,现实要比文学作品更富有戏剧性更刺激更充满悬念,生活真相要远远超出作家的想象极限,不必添油加醋,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复制现实,我们就可以得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悲剧、喜剧、正剧、闹剧、荒诞剧、惊悚剧、悬疑剧、宫斗剧,我们照样能品出生活百味、参透人心诡谲、读懂人性复杂。这是广阔的现实、无边的生活以及无处不能抵达的媒介给文学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如果作家依然满足于对现实的机械拷贝的话,则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文学区别于各种八卦消息、花边新闻的特质是什么?文学该怎样处理自己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才可能不被奇闻怪事所覆盖和替代?
我们由是可以更进一步思考“何为文学”和“文学何为”这样既古老又现代的常思常新的严肃话题,也许会因此寻找到理解当下文学世界、打开时代生活之门的钥匙:文学刊物经年累月推出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某些公众号上宣称“真实”的博得超高阅读量的泪目文章,是否都是在瞅准了人们对“真实”和“故事”的双重阅读渴望后的虚实难辨的“应需”之作?文学体裁的“三分法”或者“四分法”是不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文学发展的实绩而需要理论出新了?某些作家热衷于动用“魔幻现实主义”或“神实主义”来书写现实,是否为了避免对现实的机械复制?某篇小说堆积与拼贴了各种社会新闻,是否因为著作者发现自己对世界的想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脱出生活如来佛的掌心?某个困守家中的作家所写的都市日记引发的究竟有多大代表性和多大价值的激烈争执,是否意味着人们对“真实”或“典型”的理解歧异?当人工智能写作成为现实,微软“小冰”都能编程出让人似懂非懂的“阳光失了玻璃窗”一类的诗歌时,我们是不是该对现代汉语新诗写作及评判标准有一个再认识?文学脱胎换骨,文学研究凤凰涅槃的机会也许就随之出现。
要知道,在人类传播活动先后经历的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几个时代里,文学都因应着媒介变化而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形态。在口头传播时代,口语媒介支撑下的说唱文学当然是宠儿。在文字传播时代和其后的印刷传播时代,语言文字构建起的文学大厦则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权。到了电子传播时代,媒介无处不在,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移动终端等群欢共舞,文学亦随着媒介触须的四处探伸而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延展与变身。既然媒介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则依附于媒介之上的文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会随着所依附的各种媒介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就是一切被标为文学的东西”[6](P22)。因此,除了传统的纸媒文学外,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小说)、网络文学乃至于微博、微信公众号、APP客户端等平台上的段子、文案、说书、短视频、抖音等,也都尽可以被收纳在“文学”之筐内,就譬如那把生活过成一首诗、全球粉丝过亿的中国乡村美食博主李子柒的网络视频,就完全可以被认定是“文学”。“是什么推动了世界文学一次又一次的巨变?通常是每当有人对某种简单的、被贬价为略低一等而不被重视的艺术形式善加利用,令它发生了蜕变。”[11](P7)那么,媒介融合时代是不是已经用它那无形之手暗暗拨转了人们对文学观念的认识,文学出现巨变的历史拐点是否已经或即将到来?遭遇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学将会因此获利还是得弊?迎来的会是危机还是机遇?
因是之故,我们不但不会对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前景感到悲观,反倒因此发现文学创作的视域无限宽广、文学研究的天地充满玄奥。我们应该还记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对这个世界和有关这个世界的文学书写的期许:“我很好奇。很想知道出生在网络、手机、电邮和微博的一代代年轻人将用怎样的文学去表达这个人人都时刻‘连在网上’、‘社交网络’侵害到个人隐私的世界。”[12](P61)的确,世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它的五光十色,时代让我们意识到有多种多样的媒介形式和表现手段可资利用,艺术的多种可能性正在向我们敞开,那么,开启一段值得期待的文学旅程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