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与石城镇粟特部落徙居敦煌考论
2020-02-03郑炳林黄瑞娜
郑炳林 黄瑞娜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新唐书·地理志》及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寿昌县地境》《沙州伊州地志》等都记在唐初至武周时期位于罗布泊地区的石城镇一带居住着一支粟特人康艳典部落,他们大概于唐朝贞观年间从中亚迁徙到石城镇地区,将石城镇一带的鄯善人驱赶到伊州纳职县,康艳典部落成为石城镇的主人,其后代一直担任唐石城镇使的职务,主持石城镇的防务工作。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唐开元年间沙州敦煌县管辖有由粟特人组成的从化乡,经学术界研究推测,从化乡的粟特人是由从罗布泊地区的石城镇迁徙而来的粟特人建立的,我们从敦煌文献的记载得知,从化乡最少有两个里四个村落组成(1)P.3559《唐天宝年间(750)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29-241页。,我们从晚唐五代敦煌文献的记载得知,敦煌文献记载的康家庄、安家庄、石家庄、曹家庄、罗家庄、石家庄等都是从化乡管辖下的村落,这些村落分布在敦煌城周边地区,即城南园、城北园、城东园、城西园和东水池、西水池、北水池或者城南庄、城北庄、城东庄、城西庄等粟特人聚落(2)参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村庄聚落辑考》,收入《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历史文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62页;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与聚落》,《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8-190页;Zheng Binglin, Non-Han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Settlements in Dunhuang during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Les Sogdiens en Chins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5, pp. 343-362.。这些粟特人是什么时间迁徙敦煌的,迁徙的原因是什么,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曾就从化乡的出现与石城镇康艳典部落迁徙敦煌有关,并认为迁徙的时间是唐神龙年间突骑施阙啜忠节帅部进入且末河流域,随此而引来了吐蕃兵向塔里木盆地东部的进占;粟特人聚落在石城镇的消失与阙啜在这一地区的劫掠同时发生,推测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人在受到阙啜的暴力威胁时迅速逃往敦煌以求得沙州刺史的保护(3)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收入氏著《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0-376页。。但是未能就敦煌粟特人聚落与石城镇康艳典部落的关系提出直接的资料证据。我们在对《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进行研究发现,康贤照祖上就是石城镇人,是康艳典部落后裔。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敦煌粟特人聚落来源及其原因进行梳理。
一、《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与石城镇粟特人康艳典部落
康艳典部落徙居敦煌,直接记载是P.3556《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P.3556《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集》第一篇篇首残缺,篇末亦无撰写题记。第一行曰:“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沙门)”,由本卷《都僧统氾福高和尚邈真赞并序》福高僧官结衔为:“大唐敕授归义军应管内外都僧统充佛法主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又曰:“洎金山白帝,……遂封内外都僧统之号,兼加河西佛法主之名。”《都僧统陈法严和尚邈真赞并序》记载:“爰至吏部尚书秉政莲府,大扇玄风,封赐内外都僧统之班,兼加河西佛法主之号。”由此看来,“河西管内佛法主”乃都僧统加的号。赞文称“河西教主,莲府英贤”,当是敦煌某位都僧统。又按P.3556第二、第三篇乃是继康贤照出任都僧统的氾福高、陈法严,疑此篇乃是康贤照的邈真赞。序文曰:“[石]城名宗,敦煌鼎族。”不记载其姓氏源流,P.4660《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康秀华邈真赞并序》记载“伟哉康公,族氏豪宗”,亦相同。又按序文内容,绵帐上方画弥勒佛、诸菩萨,下方画有其形影,可知此篇乃供养像题赞。此篇诸家皆略而不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3556集文一卷(两面抄)。有氾和尚、陈和尚、贾和尚、曹法律尼(曹大王之侄女)、灵修寺尼张戒珠(张议潮之孙女)等邈真赞,又张氏(张淮深之女)墓志铭、清泰三年曹元德转经疏等。”P.3556是由多篇废弃文书粘连在一起抄写邈真赞,其中康贤照、陈法严邈真赞背面书写的是《沙州诸寺尼修习禅定记录》,这是一篇前后残缺的文书,中间有“乘:圆戒”字样,表明这是大乘寺等待出家女性沙弥尼修习记录,记录了部分出家尼修习问想甄别兼判的记录,是道场度僧尼的必要环节,每人一行,前面是问想记录,后面是甄别兼判成绩。1992年我们在辑录这篇文书时将其定名为“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邈真赞并序”,主要是根据第一行残文“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4)参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69-369页。,而后学术界将其定名为“康贤照邈真赞并序”(5)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伯希和劫经录”:“P.3556a 康贤照邈真赞 按:此依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定名。”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6页。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有录文,并定名为《康贤照邈真赞》,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第213-214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6-317页)有录文,沿用饶宗颐定名。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8-249页)有图版,并定名为《康贤照邈真赞》。参照诸家研究定名,我们将这篇邈真赞定名为《河西管内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荣新江《敦煌邈真赞年代考》(见《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362页)认为这篇赞文撰写于902年前后。。康贤照,敦煌大云寺僧,乾符三年至六年接替唐悟真出任都僧录,根据P.2856V《唐景福二年癸丑岁(893)十月十一日沙州某寺纳草历》、P.2856V《乾宁二年三月十日营葬都僧统榜》、P.4597V《光化三年、四年杂写书函》、S.2614V《唐年代未详(895)沙州诸寺僧尼名簿》等记载,景福二年前出任副僧统兼都僧录,乾宁二年(895)唐悟真圆寂后出任都僧统。又根据S.1604《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沙州节度使帖都僧统等》《天复二年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天复二年河西都僧统贤照下诸寺纲管徒众帖》的记载天复二年康贤照仍然任都僧统,荣新江认为天复二年是康贤照与交替年代(6)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70-78页。。我们根据S.1073《唐光化三年(900)四月徒众绍浄等请某乙为寺主牒稿》记载:“(前缺)请某乙为寺主。右件僧,戒珠圆浄,才智洪深,善达时机,权谋越群,凡庭葺绩,藉此良能。伏望都僧统和尚仁明,神笔判差,希垂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光化三年四月日徒众绍浄牒。”都僧统指的是康贤照。S.2574《唐天复五年(905)八月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大行充寺主状并都僧统判辞》记载:“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状。众请大行充寺主。右前件僧,徒中俊德,务众多能。顺上有波骤之勤,训下存恩恤之义。本性迅速,无羽同飞。边鄙鸿基,实藉纲要。伏望都僧统和尚仁恩详察,特赐拔擢。伏请判凭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天复伍年八月日灵图寺徒众义深等牒。徒众灵俊,徒众,徒众政信,徒众惠,徒众,徒众灵□,徒众义深。状称多能,无羽能飞者。若阙六翮,岂可接云而高翔也。然来意难违,便可□□。□日。贤照。”(7)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92-899页。都僧统康贤照与都僧统氾福高的交替年代应当在天复五年八月之后。康贤照担任敦煌都僧统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
《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记载敦煌康氏家族的郡望称:
[和尚俗姓康氏,香号贤照。乃石]城名宗,敦煌鼎族。□□□□□□,□□不恋烦嚣。长习捐簪,□□□□□□。遂得鹅珠进戒,皎皎以秋月齐圆。□□□□,□□以春花竟彩。精通万法,辩□□(若河)决争流。奯晓千门,谈如倾盆竞涌。莲花三座训迷邪,指中道真如;师子五升化昏愚,悟顿途性相。谈空才暇,乃思有相之因;随众分身,故表众生之果。况知色尘号假,色方示有;成生法体号空,应法还为寂灭。(8)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892页。
这是敦煌文献中将敦煌粟特人康氏同石城镇康氏联系起的最明确的记载,虽然文献记载有残缺,但是“城名宗敦煌鼎族”很清楚,而“城”字最有可能与“域”写混,无论是西域还是石城,都是对康氏家族族源的追述,我们经过仔细辨认,应当是“城”字而非“域”字,因此城字前面所残缺的应当是“石”。这里追述的康贤照家族族源是从石城镇迁徙而来的,因为从康艳典起到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康氏家族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石城镇担任镇将阶段,康贤照追述他们这个家族史是为了表明他们家族在唐朝时期的地位不一般,只有是石城名宗,才能成为敦煌鼎族。P.4660《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康秀华邈真赞并序》记载:“伟哉康公,族氏豪宗。”《都知兵马使康通信赞》记载:“懿哉哲人,与众不群。”(9)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375、430页。P.3258《祈愿文》记载:“康公骏豪迎机,挺用济时;耿介不群,指挥无滞。”这些记载都表明敦煌粟特人康氏家族出身不同一般,能够与敦煌的大姓豪宗李氏、索氏、阴氏、氾氏、张氏并驾齐名,号称敦煌的豪宗鼎族。此后敦煌粟特名人辈出,康氏家族除了康秀华之外还有都知兵马使康通信“懿哉哲人,与众不群。刚柔相伴,文质彬彬。尽忠奉上,尽孝安亲。叶和众事,进退俱真。助开河陇,效职辕门。横戈阵面,骁勇虎贲。番禾镇将,删丹治人。先公后私,长在军门。天庭奏事,荐以高勋。姑臧守职,不行遭窀。”也是敦煌的名人。除了康氏之外,安氏家族也是敦煌的名望家族,最初的归义军节度副使安景旻等就是其代表。敦煌的粟特人部落后裔,除了康贤照外都没有记载其族源,康贤照的这一记载对于我们探究敦煌粟特人部落的源流和从化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是从石城镇迁徙而来的,而石城镇的粟特人是何时徙居而来的?有关罗布泊石城镇粟特人康艳典部落徙居石城镇的相关记载主要保存在敦煌文献和《新唐书·地理志》中,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罗布泊地区粟特人康艳典部落是何时迁徙到石城镇的以及石城镇康艳典部落在罗布泊地区的活动情况。首先是《寿昌县地境》和S.367《沙州伊州地志》的记载,他们的成书年代和记载内容基本接近,《寿昌县地境》记载到石城镇地区的粟特人康艳典部落:
石城,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去长安六千一百里。地多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弟,更名鄯善。随(隋)置鄯善镇。随(隋)乱,其城乃空。自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据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名其城曰兴谷城。四面并是沙卤。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属沙州。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
新城,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汉名弩支城。东去鄯善三百三十里也。
葡萄城,康艳典筑。在石城北四里。种葡萄于城中,甚美,因号葡萄城也。
萨毗城,在镇城东南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置筑,近萨毗城泽险,恒有土蕃、土谷贼往来。(10)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寿昌县地境》撰写时间是后晋天福十年开运二年(945),为州学博士翟奉达为寿昌张县令撰写的,记载寿昌县史事的下限是建中初年。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康艳典部落于贞观中东迁鄯善之后,共修筑了石城、新城、葡萄城和萨毗城,其中石城、新城和葡萄城就是指罗布泊三城。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除了个别字之外,与《寿昌县地境》相同:
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此城中,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路]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11)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5-66页。
另外P.5034《西州图经》残卷新城、葡萄城、萨毗城也记载东徙的粟特人康艳典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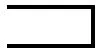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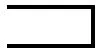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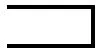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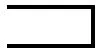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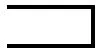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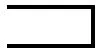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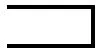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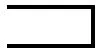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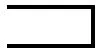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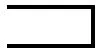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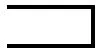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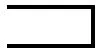
这个记载应当要详细于《寿昌县地境》和《沙州伊州地志》的记载,而且比较正确,很遗憾由于文献的残缺,留下的内容非常有限,就从这些有限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前二者的内容都是抄写本卷而来的。特别是关于葡萄城的得名,是因康艳典种葡萄于城中而得名,足以体现出来其记载价值之高:“二所葡萄故城,并破坏,无人居止。一城周回二百五十步,高五尺以下。右在山头,垒石为城,去平川七百步,其山无水草树木,北去艳典新造城四里。一城周回一百四步,高五尺已下。右在平川,北去艳典新造城四里。”(13)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49页。就是说康艳典在原来的两所破坏故城之外又重新建造葡萄城。我们从这些记载得知,康艳典部迁徙到石城镇地区之后,主要占据石城镇、葡萄城和新城等三座城及距离遥远的萨毗城。葡萄城和新城处于石城镇通往于阗道路上,萨毗城是经由播仙镇进入吐蕃境内的交通关隘。
粟特人康艳典部落在石城镇的活动情况在《新唐书·地理志》也有相应的记载:“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1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1页。康艳典占据石城镇之后,唐命康艳典为镇使,大约与播仙镇同时建镇,时间为上元中(674-676)。
康艳典部落迁徙石城镇的时间,我们根据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伊州纳职县:“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15)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8页。这里记载鄯伏陀从唐初从鄯善返回,具体时间我们根据伊州部分记载:“贞观四年首领石高年率七城来降,我唐始置伊州。”(16)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6-67页。应当发生于同一个时间,即贞观四年(630)。这也可以从《元和郡县图志》伊州纳职县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谓鄯善为纳职,因名县焉。”(17)[唐]杜佑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0页。《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伊州:“纳职 贞观四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1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4页。《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纳职,下。贞观四年以鄯善故城置。”(1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46页。既然鄯伏陀是唐贞观四年从鄯善迁徙回伊州纳职县,其迁徙出鄯善的原因肯定与康艳典部落东徙石城镇有直接关系,或者就是康艳典部落将鄯伏陀部落赶出鄯善而投降唐朝建立石城镇。
石城镇的设置时间,《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唐朝在西域局势进行推断。根据《新唐书·西域传》焉耆记载:“太宗贞观六年,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突骑支请开大碛道以便行人,帝许之。高昌怒,大掠其边。……高昌破,归向所俘及城,遣使者入谢。”(2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29页。直到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西域入朝路线要么经高昌走大海道或者伊吾道,要么经焉耆直达敦煌的大碛路。就是说行经鄯善的道路还没有重新开启,因此石城镇也就没有设置。后安西都护郭孝恪平焉耆,行军路线仍然经过西州走银山道,而不是经鄯善北上进攻焉耆,康艳典部落还没有归附唐朝政府。唐朝平定焉耆完全改变西域政局的格局,为控制西域南道创造了条件,从焉耆往南就很容易控制鄯善。唐朝政府平定龟兹,将安西都护府迁徙到其都城,统龟兹、于阗、碎叶、疏勒等四镇,鄯善就成为唐朝管辖范围,康艳典部落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归附于唐朝政府。高宗时期,“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麴智湛为都督。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诸国风俗物产,诏许敬宗与史官撰《西域图志》。上元中,素稽献银颇罗、名马。”(2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32页。《寿昌县地境》及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鄯善于“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22)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61、65页。康艳典就是这个时期出任石城镇使。
唐朝设置石城镇很可能与防御吐蕃西进、隔断吐蕃与西突厥合势反唐有很大关系。“贞观九年,诏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积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彦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甄生盐泽道,并为行军总管,率突厥、契苾兵击之。”(2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25页。从行军总管中有鄯善、且末、盐泽道看,唐朝采取东西合围。其中“大亮俘名王二十,杂畜五万,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万均督锐骑追亡数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马饮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马秣雪。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2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26页。吐谷浑灭亡之后,吐蕃遂有其地,乾封初年,吐谷浑在吐蕃逼迫之下投降唐朝,唐朝政府准备将其部落徙居凉州之南山。咸亨元年吐蕃入侵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安西四镇并废。唐派遣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蕃,“王师败大非川,举吐谷浑地皆陷”,遂徙吐谷浑于灵州,置安乐州。上元二年(675)吐蕃遣大臣论吐浑弥请和,上元三年(676)吐蕃攻打唐鄯、廓、河、芳等州。石城镇实际上就是为了防御吐蕃进入唐西域地区而设置的军镇,同时设置的镇还有播仙镇。
唐高宗上元二年之后,粟特人康艳典部落一直担任石城镇使,根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廿祥瑞蒲昌海五色记载:
蒲昌海五色。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清明彻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奴身等欢乐,望请奏圣人知者。”刺史李无亏表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谨检《瑞应图·礼升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傔 海夷也。’天应魏国,当涂之兆,明土德之昌。”(25)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9页。
相同内容的记载还见载于P.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蒲昌海五色:
蒲昌海五色: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得石城镇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水清明彻(澈)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奴身等欢乐,望请奏圣人知者。’”刺史李无亏奏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谨检《瑞应图·礼升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傔[海]夷也。’天应魏国当涂之兆,明土德之昌也。”(26)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35页。
从《沙州都督府图经》歌谣的记载时间是“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件如上讫。”是否证实《沙州都督府图经》的撰写时间应当是载初元年(689)之后。另外记载到五色鸟是武周天授二年(691)、日扬光庆云是天授二年冬至日、白狼是大周天授二年,应当说撰写于天授三年(692)或者更晚。但是文书没有使用武周所造新字,因此《沙州都督府图经》应当是武周以后撰写的作品。这个记载说明武周时期石城镇的镇遏使还是由粟特人康艳典部落的后裔所控制,康艳典部落仍然居住在石城镇一带。
二、唐中宗唐西突厥在西域的交恶与石城镇康艳典部落的内迁敦煌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咸亨四年(673):“十二月,丙子,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苏定方之西讨也,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接吐蕃,北招咽麪,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2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71-6372页。不久弓月、疏勒投降唐朝,上元元年(674)年于阗王伏阇雄也来朝。上元二年正月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同时吐蕃遣使请和。唐朝乘机在故楼兰设石城镇,隶属沙州寿昌县。次年闰三月吐蕃攻打唐鄯、廓、河、芳四州,“乙酉,以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将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以讨吐蕃。”(2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仪凤元年(676),第6379页。当年十一月改元仪凤元年。《新唐书·裴行俭传》记载:
上元三年,吐蕃叛,出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改秦州右军,并受周王节度。(2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08《裴行俭传》,第4086页。
播仙镇就是唐与吐蕃关系恶化后为防御吐蕃而设置的,是唐蕃关系紧张的产物,设立播仙镇就是为了加强凉州道防区,也可能就是为配合凉州道行军元帅的抗击吐蕃的统一行动而进行的行政改置。具体实施这个军事设置的可能是时任瓜州刺史薛仁贵,《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上元中,坐事徙象州,会赦归。高宗思其功,开耀元年,复召见,谓曰:‘往九成宫遭水,无卿已为鱼矣。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卿虽有过,岂可相忘?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卿岂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挥耶?’于是起授瓜州刺史,寻拜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3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第2783页。《新唐书·薛仁贵传》记载薛仁贵兵败大非川,被贬象州刺史遇赦回来不久,高宗召见薛仁贵,“今辽西不宁,瓜、沙路绝,卿安得高枕不为朕指麾邪?”(3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第4142页。拜其为瓜州刺史。指的就是经过南道对西域的交通道路,石城镇和播仙镇的设置就是这个时间。瓜州刺史兼瓜州都督,兼管沙州,统属于凉州大都督管辖,石城镇和播仙镇设置既可以说是凉州都督所为,也可以说是瓜州都督所为,凉州都督府派兵直接驻守播仙镇,实际上就是由瓜州都督派遣的沙州兵驻守,而以石城镇的西域康国人康艳典之后裔为石城镇镇遏使,负责管理石城地区。石城镇和且末镇的放弃亦与唐蕃在西域的争夺有很大关系,应当说是唐蕃争夺产生的直接后果。敦煌写本P.5034《沙州图经》记载:
□□□。□□且末国,王都且末城……
□□土地草木畜产与石城□……
□□同。自汉已后,其名不改,随……
□□□吐谷浑,置且末郡,管……
□□凉州兵士等弃镇归敦煌……(32)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49页。
石城镇应当与播仙镇同时放弃的,就是敦煌文献记载播仙镇“凉州兵士等弃镇归敦煌”。要得知石城镇、播仙镇的废弃时间,我们只能从唐蕃在西域地区关系、西域政局变化中寻找。陈国灿认为唐神龙年间突骑施阙啜忠节帅部进入且末河流域,随此而引来了吐蕃兵向塔里木盆地东部的进占,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人在受到阙啜的暴力威胁时迅速逃往敦煌以求得沙州刺史的保护(33)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收入氏著《敦煌学史事新证》,第370-376页。。
武周时期唐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已经展开,长寿元年(692)九月:“初,新丰王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与审礼皆没于吐蕃。赞普见孝杰泣曰:‘貌类吾父。’厚礼之,后竟得归,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3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元年(692),第6487-6488页。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蕃遣使和亲,武则天遣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吐蕃遣使入请,唐以“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力,使不得倂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无俟斤亦当以归吐蕃”拒绝吐蕃。吐蕃对西域四镇、十姓占领,必须经由石城镇、播仙镇管辖范围,或者经由萨毗城绕过石城镇、播仙镇。另外就是经由大小勃律进入西域地区。我们经过研究认为石城镇、播仙镇的放弃与突骑施阙啜忠节关系不是很大,而是与突骑施娑葛与唐关系恶化有直接关系。
根据《旧唐书·突厥下》记载神龙二年(706)乌质勒卒,“初,娑葛代父统兵,乌质勒下部将阙啜忠节甚忌之,以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任势,密遣使赍金七百两以赂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使至其境,阴与忠节筹其事,并自致书以申意。在路为娑葛游兵所获,遂斩嘉宾,仍进兵攻陷火烧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头。”(3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第5190-5191页。叙述事情经过很简单,我们从中很难了解事情原委和经过。《新唐书·突厥传下》也记载这个事件,同样不是很清楚,神龙二年乌质勒死,长子娑葛代父统兵,“俄与其将阙啜忠节交恶,兵相加暴。娑葛讼忠节罪,请内之京师。忠节以千金赂宰相宗楚客等,愿无入朝,请导吐蕃击娑葛以报。楚客方专国,即以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经制。嘉宾与忠节书疏反复,娑葛逻得之,遂杀嘉宾,使弟遮弩率兵盗塞。安西都护牛师奖与战火烧城,师奖败,死之,表索楚客头以徇。大都护郭元振表奏娑葛状直,当见赦,诏许,西土遂定。”(3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第6066页。从中我们得知,唐派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到阙啜辖境,冯嘉宾与阙啜往来书疏为娑葛游兵所得,就是说娑葛的势力也到达了阙啜辖境。娑葛遣其弟遮弩盗塞,这个边塞城镇很可能就是指播仙镇和石城镇。另外《旧唐书·宗楚客传》也记载了这个事件:
景龙中,西突厥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不和,屡相侵扰,西陲不安。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晋卿、处讷等各纳忠节重赂,奏请发兵以讨娑葛,不纳元振奏。娑葛知而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3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2《宗楚客传》,第2972页。
显然宗楚客是娑葛制造边患的始作俑者,因此监察御史崔琬劾奏宗楚客等称:“潜通猃狁,纳贿不赀,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丑问充斥,秽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状难测,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贼臣,取怨中国。”(3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2《宗楚客传》,第2972页。因此阙啜行贿宗楚客等而制造边患是朝廷中人尽皆知的事情。《新唐书·宗楚客传》记载:
景龙二年,诏突厥娑葛为金河郡王,而其部阙啜忠节赂楚客等罢之,娑葛怨,将兵患边。(3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09《宗楚客传》,第4102页。
宗楚客受阙啜忠节贿赂而阻止授予娑葛金河郡王而引起兵患。《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详细记载事件的经过和原因:
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努等帅众犯塞。
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
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招十姓,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忠节然其言,遣间使赂楚客、处讷,请如以悌之策。(4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二年(708),第6625-6626页。
郭元振闻其谋,上疏极力反对,但是宗楚客等不从,建议以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冎而杀之。”(4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二年(708),第6627-6628页。娑葛陷安西,断四镇路,唐置军焉耆以讨娑葛,最后唐朝不得已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战争以娑葛胜利结束。河口指河流的终端,指河流注入海洋、湖泊或者其他河流的地方。郭元振栅河口是指疏勒河汇入于阗河的地方,而阿史那忠节迎接嘉宾于计舒河口的位置是指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的地方,《水经注》河水注:“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42)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页。根据敦煌文献P.5034《沙州图经》记载蒲昌海:“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合,东注蒲昌海。”郭元振栅河口在于阗河与葱岭河汇合之地,而阿史那忠节迎接冯嘉宾的地点在塔里木汇入罗布泊的地方,而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的地方,正好是石城镇到焉耆交通路线的必经之地:石城镇“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43)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48-49页。唐朝派遣冯嘉宾等经过石城镇地区前往安西都护府,阙啜在石城镇北部的计舒河口迎接冯嘉宾一行,而娑葛就是在计舒河口对阙啜和冯嘉宾等进行伏击,将他们全部俘虏。因此计舒河口很可能是唐河西节度使和安西节度使管辖范围的结合部,双方都属于防守,娑葛才能袭击成功。
《旧唐书·郭元振传》也记载这个事件的详细经过:
先是,娑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屡相侵掠,阙啜兵众寡弱,渐不能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卫。移其部落入于瓜、沙等州安置,制从之。阙啜行至播仙城,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以悌谓之曰:‘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资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贶二公,请留不行。乃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既得报雠,又得存其部落。如此,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阙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阗坎城,获金宝及生口,遣人间道纳赂于宗、纪。元振闻其谋,遽上疏曰:……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阙啜之赂,乃建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持玺书便报元振。除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便领甘、凉以西兵募,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进马使娑腊知楚客计,驰还报娑葛。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时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栅不敢动。阙啜在计舒河口候见嘉宾,娑葛兵掩至,生擒阙啜,杀嘉宾等。吕守素至僻城,亦见害。又杀牛师奖于火烧城,乃陷安西。四镇路绝楚客又奏请以周以悌代元振统众,征元振,将陷之。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元振奏娑葛状。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奏其状,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称西土未宁,事资安抚,逗留不敢归京师。(4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第3045-3048页。
《新唐书·郭元振传》记载事情的经过,神龙中,“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愿和,元振即牙帐与计事。会大雨雪,元振立不动,至夕冻冽;乌质勒已老,数伏拜,不胜寒,会罢即死。”子娑葛以为郭元振计杀其父,谋勒兵袭击,次日郭元振素服往吊,“至其帐哭甚哀,为留数十日助丧事,娑葛感义,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
乌质勒之将阙啜忠节与娑葛交怨,屡相侵,而阙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宿卫,徙部落置瓜、沙间。诏许之。阙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经略使周以悌,以悌说之曰:“国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独行入朝,一羁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宝赂宰相,无入朝;请发安西兵导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请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铠马以助军,既得复雠,部落更存。阙啜然之,即勒兵击于阗坎城,下之。因所获,遣人间道赍黄金分遣宗楚客、纪处讷,使就其谋。(4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第4363页。
郭元振知之,上疏反对,但是疏奏不省。
楚客等因建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以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代元振领甘、凉兵,诏吐蕃倂力击娑葛。娑葛之使娑腊知楚客谋,驰报之。娑葛怒,即发兵出安西、拨换、焉耆,疏勒各五千骑。于是阙啜在计舒河与嘉宾会,娑葛兵奄至,禽阙啜,杀嘉宾,又杀吕守素于僻城、牛师奖于火烧城,遂陷安西,四镇路绝。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动。楚客复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遗元振书,且言:“无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阙啜金,欲加兵灭我,故惧死而斗。且请斩楚客。”元振奏其状。楚客大怒,诬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子鸿间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归京师。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4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第4364-4365页。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乌质勒部将阙啜与娑葛因交怨而屡相侵并势力不支,郭元振为了缓解双方矛盾,建议将阙啜部落迁徙到瓜、沙间安置,并追阙啜入宿卫。这本来是很好的策略,因经略使周以悌唆使,阙啜行贿宰相无得入朝,而没有得到实现。唐朝政府中以宗楚客为代表的主张扶持阙啜联合吐蕃、拔汗那攻击娑葛,削弱郭元振在西域的权力,用御史中丞冯嘉宾安抚阙啜、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用牛师奖代替郭元振掌握镇守四镇的甘、凉兵士兵权。双方密谋的地点是罗布泊地区,阙啜计划与冯嘉宾、吕守素等会合于计舒河口,皆因被俘害而罢,牛师奖死后谋用周以悌代替郭元振也未能实现。
唐朝政府安置西突厥阙啜部落于瓜、沙等州,石城镇、播仙镇实际上就是安置阙啜部的主要地区。唐初瓜州沙州属于凉州都督府管辖,贞观初年唐玄奘从瓜州偷渡出境,凉州都督李大亮就行文瓜州刺史捉拿。瓜州建都督府,沙州刺史由瓜州的都督调遣,直到沙州建都督府之后地位有所上升。唐神龙年间安置阙啜忠节瓜沙等州,实际上瓜沙都属于凉州都督管辖。唐将阙啜部安置在西起播仙镇、石城镇东到与瓜州毗邻的莫贺延碛一带,或者西起且末河东到瓜州南山等地。阙啜忠节部落是游牧民族,将其安置在播仙镇、石城镇是唐朝的主动行为,并不构成对唐朝播仙镇、石城镇的威胁,阙啜部落到达播仙镇,经略使周以悌应当还是当地军镇的最高统帅,没有他的默许,阙啜根本不敢攻打于阗坎城。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康艳典部落是城居商业农业居民,阙啜不可能也不敢对其形成暴力威胁,而且阙啜不惜率兵攻打坎城掠夺金宝以贿赂唐宰相宗楚客,不敢对近在迟尺的石城镇、播仙镇下手,就说明当时石城镇、播仙镇等还在,很可能是其强力后盾。阙啜在计舒河口迎接冯嘉宾等,就说明原属于石城镇康艳典部落的地域,已经成为阙啜部众活动的地域。娑葛在计舒河口一带杀冯嘉宾和吕守素等,俘虏阙啜。根据《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记载
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称:“我与唐无恶,但雠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4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二年,第6629页。
唐朝置军焉耆,就是以为焉耆地处南道与中道交汇之地,表明焉耆以南的播仙镇、石城镇非唐所有。唐中宗景龙三年:
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请降,庚辰,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4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第6636页。
《旧唐书·中宗纪》记载景龙二年:
冬十一月庚申,突厥首领娑葛叛,自立为可汗,遣弟遮弩率众犯塞。……癸未,安西都护牛师奖与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败绩,没于阵。……(三年七月)壬午,遣使册骁卫大将军、兼卫尉卿、金河王突骑施守忠为归化可汗。(4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中宗纪》,第146-148页。
《新唐书·中宗纪》景龙二年记载:
十一月庚申,西突厥寇边,御史中丞冯嘉宾使于突厥,死之。……癸未,安西都护牛师奖及西突厥战于火烧城,死之。……(三年)七月丙辰,西突厥娑葛降。(5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中宗纪》,第110-111页。
至此,唐朝与突骑施娑葛之间纷争结束,唐朝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承认突骑施娑葛的地位。应当说通过这次战争,娑葛已经控制了石城镇、播仙镇,凉州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弃镇归敦煌,石城镇的康艳典部落也是随着凉州兵士弃镇归敦煌而东迁敦煌,唐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从石城镇迁徙而来粟特人部落,就在敦煌城周边地区设立了以粟特人为主的从化乡。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经略使周以悌帮阙啜谋划联合吐蕃、拔汗那攻打娑葛,因娑葛行动迅速,吐蕃和拔汗那都没有参与到唐与西突厥娑葛的战争中。因此石城镇粟特人部落的东迁敦煌和播仙镇凉州兵士弃镇归敦煌与吐蕃没有关系。
三、沙州敦煌县从化乡的设置与粟特聚落的形成
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的形成时间,陈国灿根据吐鲁番出土来自敦煌又记载从化乡的大谷文书记载有张令端和曹子节及从化乡,认为这是从该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张令端的墓葬,根据同期文书墓主人张令端卒后入殓,时间应在唐景龙(707-710)以后,又根据《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认为长安三年(703)三月敦煌尚无从化乡,认为从化乡残文书只能是长安三年三月以后至景龙间的文书,敦煌从化乡也只能出现这个时期(51)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收入氏著《敦煌学史事新证》,第371-372页。大谷文书记载:“(前缺)子总张令端……叔牙,从化乡百姓……之节等(后缺)”。。敦煌文书P.2803《唐天宝九载(750)八月——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记载敦煌十三乡中有从化乡:“从化乡,叁佰玖拾伍硕贰斗壹胜。”(5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45页。直至唐天宝九载从化乡仍然存在。P.3559《唐天宝年间(750)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记载唐敦煌县从化乡最为详细:
贰佰伍拾柒从化乡。壹佰壹拾柒人破除。贰拾叁人身死。……叁拾伍人逃走。……贰拾柒人没落。……叁人虚挂。……叁人废疾。……贰拾叁人单身土镇兵。……叁人单身卫士。……壹佰肆拾人见在。壹拾人中下户。……壹拾人下上户。……贰拾人下中户。……壹佰人下下户。(5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229-241页。
差科簿记载下中户曹大宾服色役为市壁师、下下户康令钦服色役为里正、罗奉鸾服色役为里正、安突昏服色役为村正、安胡数芬服色役为市壁师、何抱金服色役为村正、罗双利和罗特勤服色役为村正。根据此纸缝后贴为唐天宝九载敦煌郡仓纳谷牒十六件,故确定该卷文书为天宝年间。另外我们根据敦煌地区安城祆祠的出现作为敦煌粟特人聚落建立的标志,《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安城祆:“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祆神,又称安城大祆,是敦煌的杂神之一。如果说安城的修建与祆神同时,就像敦煌古迹二十咏记载的“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即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与祆神神祠安置是同时,那么《沙州都督府图经》的撰修时石城镇的粟特人聚落已经迁居敦煌,且《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没有使用武周新字,表明其撰成武周之后,为开元初增补而成,开元之前敦煌已经修建了祆教神祠,而从化乡就是这个阶段设置的。经陈国灿先生研究,敦煌从化乡的出现时间正好在唐中宗神龙年间,与突骑施阙啜在这一地区劫掠骚扰遥相呼应(54)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学史事新证》,第373页。实际上与突骑施娑葛在罗布泊地区俘虏阙啜忠节、杀冯嘉宾和吕守素等占领该地区有直接关系。
随着唐朝政府与娑葛关系的改善,唐朝政府在这个地区的军政机构很快就恢复了。特别是景龙三年娑葛与其弟遮弩关系紧张,“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讨娑葛。”(5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第5191页。突厥默啜用遮弩讨擒娑葛,遂与娑葛俱杀之。突骑施娑葛对唐朝的威胁解除,很可能这个时期石城镇、播仙镇的建置得到回复。但是突骑施进入罗布泊地区并生活在这里成为既成事实,并长期生活在这里。敦煌吐蕃文献Ch.73.xv.4号文书从第45行到末尾记载:
紧接着现在的时间是借贷和征税时间。当这个三百六十年的时间过去的时候,汉人国家西边,一个大湖的遥远岸边,那里出现一块陆地,一位黑脸王乘坐一辆战车,耀武扬威六十载。汉人被其征服,黔首向其效忠。当此王统治六十载过去时,于Bug-chor汉人的沼泽国内出现一小邦的陷落,一名叫大突厥(Drug-chen-po)的人消灭了汉人的黑脸王和Bug-chor的王。汉区和Bug-chor的两族人为王所征服并交纳税赋。大突厥王统治了七十二年。此七十二年之后,东西突厥开始打仗。首先西突厥……。(56)[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70页。
文书中记载到的大突厥王,就是指生活在这里的突骑施部落。
直到唐天宝年间,唐与吐蕃为争夺播仙镇、石城镇还进行过战争。根据P.5034《沙州图经》记载有:“□□年,□□都尉即令□且末城。”就是说播仙镇经过一次废弃之后,又重新设置,同样石城镇可能也在废弃之后又进行重新设置。这些军事措施应当说与粟特人康艳典部落没有任何关系。播仙镇和石城镇的重新设置,很可能是天宝初年。《旧唐书·尉迟胜传》记载:“尉迟胜,本于阗王珪之长子,少嗣位。天宝中来朝,献名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还国。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击破萨毗播仙,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改光禄卿,皆同正。”(5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44《尉迟胜传》,第3924页。《新唐书·尉迟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尉迟胜本王于阗国。天宝中,入朝,献名玉、良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归国,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击破萨毗、播仙。累进光禄卿。”(5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10《尉迟胜传》,第4127页。这次战争大约发生在天宝八载(749)(59)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172、179页。。很快吐蕃再次占领萨毗城、播仙镇,天宝十三载(754)封常清再次击败镇守播仙的吐蕃守军(60)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奏凯歌六章》,[唐]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3-154页。。萨毗即萨毗城,这里经常行经吐蕃,因此萨毗、播仙是吐蕃攻打西域的重要军事据点。《新唐书·郭虔瓘传》记载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安抚招慰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持异,交诉于朝,玄宗遣左卫中郎将王惠赍诏书谕解:“或云突骑施围石城,献所致也;葛逻禄称兵,虔瓘所沮也。大将不协,小人以逞,何功可图?”(6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33《郭虔瓘传》,第4544页。开元年间突骑施曾出兵围困石城镇。这里仍然是唐与突骑施、吐蕃争夺的重要军事据点。
我们通过对《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及相关文献研究得知,唐贞观四年康艳典率部落迁徙到石城镇,唐上元二年防御日渐强大的吐蕃对西域威胁,设置了石城镇、播仙镇,并将其隶属沙州,归凉州都督府管辖。以康艳典为石城镇使,此后康艳典后裔一直担任石城镇使,直到天授年间。唐中宗神龙二年突骑施乌质勒死,长子娑葛代父统众,乌质勒旧部阙啜不服而发生战争,阙啜兵败部众被安置在罗布泊地区,阙啜贿赂宗楚客得到唐朝政府支持,岂图攻击娑葛,反而被娑葛击败被俘虏,唐将冯嘉宾等被杀,娑葛占领罗布泊地区。在突骑施娑葛的军事打击之下,石城镇的粟特人康艳典部落随着驻守播仙镇的凉州兵士弃镇归敦煌,唐朝政府为了在敦煌安置这些从石城镇迁徙而来的粟特人,专门在敦煌城周修建了安城祆祠,设立从化乡。从化乡规模最少有两个里四个村落,同时负责敦煌市场的贸易管理。吐蕃占领敦煌后从化乡被取消,但是粟特人的势力仍然存在,归义军时期敦煌仍然保留很多粟特人聚落,控制敦煌地区的商业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