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恋曲与悲歌
2020-01-30戴建华
戴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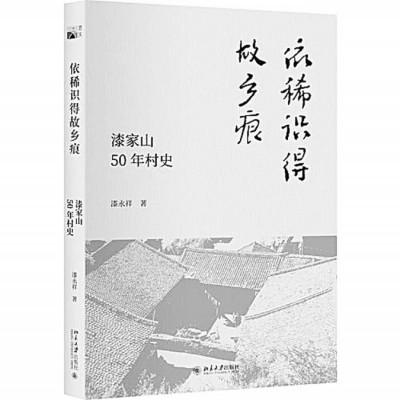
《依稀识得故乡痕——漆家山50年村史》漆永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三年前,在微信朋友圈里每天跟读漆永祥先生回忆家乡的文字,欲罢不能。后来中道辍笔,不胜怅然。客岁,闻将出书,又不胜期待。今年,漆公惠赠,终于可以一气读完。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国史、方志、族谱、家乘,汗牛充栋。但似乎从来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村史。有之,请从《依稀识得故乡痕——漆家山50年村史》开始。
漆公生于斯长于斯的漆家山,位于甘肃省定西地区漳县马泉乡紫石村。“是黄土高原上一个贫寒闭塞的小山村”。所谓50年,是从作者出生的1965年算起,当时漆家山13个家族25户人家130位村民,到作者动笔写这部村史时的2015年止,13个家族63户476人。当然,统计未必“绝对准确”。在今天,许多人连曾祖父的名、曾祖母的姓都忘了,即使是作者魂牵梦绕的地方,做这样的田野调查也并不容易。
村史逾20万言,分三卷。上卷记自然环境、医疗卫生、农林畜牧、人口移民,中卷叙文化教育、公共娱乐、婚丧嫁娶、节日方语,下卷为村民小传。漆家山在山之南,村子东西及下沟皆为阳坡地。天然形成的大坡塆以及高峻的山岭,挡住了冬天的寒风。日照充足,温暖湿润。农作物有小麦、青稞、豌豆、土豆,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当归、党参,牛马猪羊饲料有苜蓿、蔓菁等。上世纪70年代,村子周边数十年长成的大小森林,遮荫蔽日,环境优美,但一穷二白,缺医少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中期,这十年是漆家山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时期。然而,“回民富了贩羊,汉人富了修房”,“从盗伐森林开始,至滥垦耕地,腰斩行路,挖绝药材,啃尽草皮,十年前后,漆家山就由山清水秀、五谷丰登转而成为光山秃岭、灾害频生、干旱缺水、农田不兴,百余年祖宗培植之基业,瞬间荡尽”,“本村的女孩子不断地嫁出去,而少有外村外地的女孩子娶进来”,以致2011年春,漆家山一半的村民远离故土,移居新疆,而“留下死守,只有无助的绝望”。
昔时的漆家山,“风俗纯美,守望相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即便是‘破四旧的年代,漆家山仍过年迎接祖先,烧香磕头。大年初一,家族男丁,都挨家磕头拜年”。“外面世界的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但对这个封闭古朴的小山村而言,却过着苦焦饥困而又安宁平静的日子”。作者“记得80年代中期有一年,大年初二晚上,和我同岁的高狼娃(嫁紫石沟)因阑尾炎误诊耽延,不幸卒于县医院。当时她的父母刚好去医院探视,半道伤痛昏厥在九眼泉路上。村人知悉后,竟然不约而同备了骡马,下山去接”。于是“看到一幅今生难忘的画面:七八匹骡马备着鞍,鞍上铺着各家平日舍不得盖的花花绿绿的新棉被。只有一匹骡子上骑着高氏母亲,多人左右扶持;高父自己走着,也被一群人围着。后面一溜空鞍的骡马跟着,缓缓排沓而来,骡马的项铃被有意卸下来,没有了往日一路铃声的欢快,人声咽泣,时继时续,在白雪皑皑的大山衬映下,更显得气氛沉重,悲伤萦结。当晚全村无人燃放烟花爆竹,沉浸在悲伤痛绝之中”。而今,村子里却赌博成风,欠债无数,“家中鸡犬不宁,或父子反目,或兄弟阋墙,或夫妻别异,或子女辍学。百怪千奇,无所不有”。“饭吃饱了,衣穿全了,屋建好了,可是精神丢了,魂灵没了,风俗坏了,乡情失了”。
语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作者为漆家山人立传,“多数是文盲,还有民办教师、林业工人、杀人凶犯、打工丧命者等,他们的事迹平淡无奇,却又独一无二,各色人物,运命百般,悲欢离合,生死无常,漆家山就是一个当代中国边鄙山区农村的小小缩影”。在这些人物中,“太爷老师”是知识的火种,他的艰辛劳作使村里三代人脱了文盲,村里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都是他的弟子,作者正是在他的启蒙下,努力向上,考上大学,成了教授。作者的祖父,是地道的农民,一年四季,燃着火盆,喝罐罐茶。他“处事公允,能守中道”,是乡里人望。随着太爷和祖父的离去,火种熄了,火盆灭了,“他们带走了一个山村纯朴自然的时代”。而对众乡亲,即使是刑余者,作者也含有深深的“了解之同情”。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般的村史。事无巨细,洋溢着丰富而生动的乡土风情。
这也是一部饱含深情的村史。作者写道:“上大学后,每年暑期回家,返校之时,母亲总是给我煮两碗新豌豆,煮几个新洋芋,这是她给儿子最好吃的山珍。老母亲坐在门墩儿上,看着儿子剥食,絮絮叮嘱不已。我默无所言,尽量多吃,以安娘心,事毕拜母,掩面而别,再入人海,复自茫茫矣。”大山养育了作者,作者回报一部心史,封底寄语仿佛“稿竟说偈”:“编史记事,存史乡梓。权慰本心,并告父老。魂牵梦绕,念兹在兹。村史既成,载歌载泣。凡百君子,敬请观览。呼号答拜,感何如之。”
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部村史。“今日世风,非今非古,不惠不跖”。譬如种树:倘若一枝枯死,掰下来烧掉;一棵树死,砍掉它重栽。但如果土壤坏了,风水坏了,就不会再有枝繁叶茂。“脱贫”必须深化,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精神的。“如果说中国是座宝塔,那么像漆家山这样的农村就是塔基,任你玲珑琮璜,巍巍插天,然塔基不稳,终将崩塌”。这是殷忧,是呐喊,如果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甚至观人风者的注意,可以告慰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多灾多难的父老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