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林语堂的那些事儿
2020-01-25刘少勤
刘少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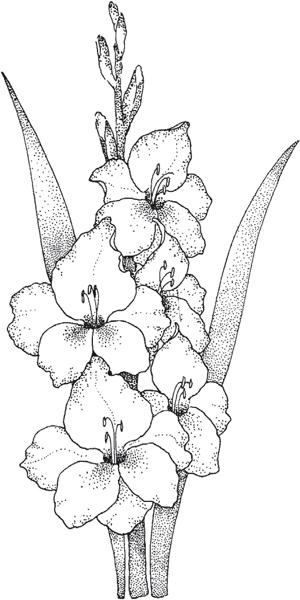
彼此的投合
鲁迅和林语堂往来频繁,“林语堂”在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次数有几十次。两人有时在杂志社见面,有时在饭店与其他友人共餐,有时双方带着家人互相登门造访。彼此书信交流也不少,不过,双方都没有当一回事,大部分信件遗失,《鲁迅全集》收录写给林语堂的信仅有四封。
鲁迅大林语堂十多岁,差不多高一个辈分。一方没有摆长者的架势,另一方也落落大方,没有晚辈的拘谨,一直平等交流,并无年龄的挂碍。
两人同为语丝社成员,都是《语丝》的台柱子,发文多,质量高,备受读者瞩目。彼此欣赏对方的文才,也能体贴对方的思想和情怀。林语堂在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以“鲁迅”为题,用地道的英文写评介文章,称鲁迅是现代中国思想最深刻的作家,同时夸他文笔奇崛、雄辩、富理趣,又多诙谐。鲁迅也赏识林语堂的文采。当美国记者斯诺要鲁迅说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随笔作家时,鲁迅开了一张清单,只写了四个人,林语堂是其中之一。常说文人相轻,其实真能相重的也还是文人。内行才能看出门道,看出手法的高低,看出品质的优劣。
在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中,两人一度配合默契,惺惺相惜。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闹学潮,同是大学老师,陈源等教授与当局站在一起,贬损学生,诬蔑鲁迅等人煽动闹事。林语堂和鲁迅一道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甚至比鲁迅还要激烈。在学生与军警冲突时,他亲自上阵,举着砖头干仗,结果被军警打伤,额头上留下伤疤。事后,鲁迅、林语堂都发表文章纪念牺牲的学生。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情感浓烈,笔调深沉、精炼,写尽了悲和愤,早已是名文,无人不晓。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知道的人不是很多,《林语堂自选集》、别人编的《林语堂文选》都没有收入。文章确实写得有点仓促,文义有些单薄。林语堂在文中展示了杨德群英文课的一篇作文,很稚嫩,中国式英文。大部分中国学生刚开始写英文都是这样,本来没什么,但人已牺牲,不必亮其短处,写她的长处更好。文章不长,所引杨德群的作文占了很大的比重,不是很协调。也许林语堂后来意识到了,自编文选不收此文,在《林语堂全集》中才看得到。不管怎么说,林语堂公开发文纪念学生,态度真诚,用心良善。
围绕“落水狗”要不要打的问题,鲁迅和林语堂曾经讨论得不亦乐乎。林语堂认为已经落水,不要再打了。鲁迅意见相反,说落水狗上了岸,不改本性,还会继续伤人,后患无穷。鲁迅讲述了血的教训。王金发是革命党人,手下抓住了顽固的保皇分子。他宽宏大度,释放了对方。后来逃脱的敌人不但不感激,反而恩将仇报,与权贵合作将王金发处死了。林语堂听了鲁迅的意见,很快改变了想法,还特意作了题名“鲁迅打落水狗”的漫画登在报上,赞赏鲁迅。
宋庆龄和蔡元培牵头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林语堂、胡适和杨杏佛等人是核心成员。鲁迅和林语堂热心参与组织的活动。当组织调查国民党监狱的人权状况,要求释放政治犯时,胡适坚决反对,退出组织。林语堂没有跟风,和鲁迅一道坚守信念。国民党特务杀害组织总干事杨杏佛,杀鸡儆猴。尽管有特务盯梢,鲁迅和林语堂都去了灵堂哀悼杨杏佛。
林语堂写独幕剧《子见南子》,搬上舞台表演后惹了一身臊。一班遗老遗少摆着卫道士的面孔兴师动众,讨伐林语堂。有的写文章叫骂,有的游行示威。在他们看来,林语堂写孔子见到南子,被对方的美貌吸引,一时忘情,有损孔子的神圣和庄严,是大逆不道。鲁迅厌恶腐儒们的叫嚣,也同情林语堂的處境,写文章反击,力挺林语堂。林语堂一向敬重孔子,只是想打破历来被统治者装点过的虚假形象,还原孔子作为常人的一面。鲁迅看待孔子,与林语堂大体一致。
鲁迅一度在北京难于安生。他得罪了当权者,上了暗杀名单,生命危在旦夕。此外,他与许广平相爱,很难面对母亲选定的那位原配夫人朱安。这个时候,林语堂向他伸出了援手,聘任他为厦门大学教授。鲁迅来了以后,人际关系不协调,居住饮食也不习惯,只待了三个多月便离开厦门,奔赴广州中山大学。尽管如此,鲁迅一直惦记着林语堂的深情厚谊,为自己倏忽而来倏忽而往感到内疚。
彼此的冲突
鲁迅与林语堂后来有了些冲突,主要不是因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出于文化态度和思想信念的分歧。
两个人为生活中的事争吵,只有过一次。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欠鲁迅许多版税,一直拖延,鲁迅自然有意见。在一次几个人聚餐时,鲁迅谈到李晓峰的为人。林语堂不知内情,为李先生辩护了几句,说是另一个出版商张友松挑拨,才引发了一些作家与李晓峰的矛盾。鲁迅以为林语堂的话冲着他,对号入座,动了怒。双方都是文人性情,敏感,容易动情绪,起了争执,毫不足怪。这不过是生活中的小插曲,事情过去了,双方依然是朋友。鲁迅曾对曹聚仁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有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林语堂也很诚恳地说起他与鲁迅的关系:“我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际,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林语堂说得很明白,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绝不是因为“私人意气”。考察鲁迅与林语堂几次冲突的具体情形,可以看得更分明。
一、翻译之争
林语堂中文、英文都好,鲁迅很看重,叫他多翻译,林语堂回答得很生硬:“等我老了再说。”
翻译和创作哪个重要,两个人的态度不一。鲁迅有出色的创作能力,却一向低调,认为外国的优秀作品很多,自己比不了。与其写平庸的东西,不如翻译别国好作品。鲁迅热心翻译,投入大量时间,从早期与弟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到生命最后一年译《死魂灵》,从未间断,译作三百多万字。尽管鲁迅创作的数量也不菲,但他用于翻译的时间更多。他在翻译中寄予了特殊的厚望。他想输入新的文学技巧和手法,供文学青年借鉴,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力,打破闭门造车的窘迫,让新文学不仅有其名,更有其实。他想输入外国语言的词汇、句法和各种表达形式,促成汉语的改造,刷新语言的面孔,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拥有一门易学易懂又多姿多态的语言。他还想输入新的思想,改造国民的灵魂。林语堂却觉得,写自己的东西比译别人的东西更有价值。林语堂很看重自己的创作,不愿为翻译牺牲宝贵的时间。林语堂是生活的趣味主义者,只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创作给他带来快乐,叫他兴奋,而翻译实在勾不起他多大的兴趣,他没法做到像鲁迅那样,为了某种社会责任感去做乏味甚至是不胜任的事。林语堂想,有一天创作热情消退,创作能力丧失,再来弄翻译也不迟。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行当,选择人生努力的方向,林语堂的态度无可非议。不过,他的回答触到了鲁迅的痛处。当时无数人攻击鲁迅是老人,拿年龄说事儿,好像年老是一种罪过。林语堂说者无心,但在鲁迅听来,“等我老了再说”这句话很刺耳,很扎心。
鲁迅担忧,林语堂糊里糊涂地带着一帮人写文章,插科打诨,制造噱头,把一切都变成玩笑,让人对统治者的冷酷和残暴视而不见,无意中充当了帮闲。在《帮闲法发隐》中,他引用哲人克尔恺郭尔讲的寓言故事:一天剧场着火了,丑角在台上喊“着火了”,观众哈哈笑,以为是玩笑。丑角看火势加重,高声喊“着火啦着火啦”,观众又是一阵喝彩,最后所有人死在火海中。克尔恺郭尔警告小丑化的娱乐文化,可能会毁掉人类。
鲁迅反对林语堂把小品文当作逗乐的工具,满足于娱人娱己,放弃文人救世的热情和责任。“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三、“标点古书评点古书”之争
鲁迅旧学功底深厚,治学严谨,他辑校了许多古籍,如《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文钞》等等,一丝不苟,少有破绽。相比之下,林语堂的旧学积累要逊色很多,治学态度也较为随意,不是那么认真。林语堂携手刘大杰标点《袁中郎全集》,错误百出,闹了笑话,也误了读者。先秦两汉的文章读不通,可以原谅,但明清的小品文也没读懂,乱点一气,确实说不过去。有的句子文义不复杂,刘大杰照样点错。比如袁中郎原文应是“色借日月,借青黄,借眼,色无常”,被标点成“色借,日月借,青黄借,眼色无常”,错得离譜,说明标点者自己不懂装懂。类似的错处不胜枚举,鲁迅看不过去,写了多篇文章抨击轻浮的做派。这部书虽是刘大杰标点,但林语堂任校对,没能纠正那么明显的错,难于推卸责任。林语堂自己写文章,引明清小品文照样错,鲁迅一眼就看出来。在《说个人的笔调》中,林语堂引陈其志的文章,原文本应是“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被点成了“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鲁迅说,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示出来了。“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招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林语堂和刘大杰丢了面子,心里自然不舒服,却无从辩驳。
对传统小说,鲁迅细心阅读,认真体悟,凡所评点精辟、允当,广为学界引用。《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至今无人能超越,连鲁迅生前的论敌也很钦佩鲁迅对众多小说要言不烦的评断。林语堂的表现恐怕就叫人难以恭维。他竟然说中国古代末流的小说《野叟曝言》语言华美,见识不凡。鲁迅著文批驳,针锋相对:“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鲁迅以为林语堂先生并没有认真读,不过是拿老实人寻开心。这一回林语堂又落单了。他的说法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林语堂文学创作很上心,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却有些三心二意,打马虎眼。不解详情,不说也就罢了,他偏又爱说,结果荒腔走板。素有乾嘉考据学派功力、爱较真的鲁迅,在这一点上与他扞格不入。
四、“让娘儿们统治”之争
林语堂发表《让娘儿们干一下吧!》,提出要让女人来统治世界。他说,男人好斗、好战,让世界不得安宁。历来战乱频繁,跟男性统治者恶劣的本性有关,女人更爱和平,更务实,尽管彼此也会打架,不过是抓抓脸而已,不像男人动辄使枪弄炮,叫生灵涂炭。要是由女人做主,天下就会安宁许多。
林语堂的看法幼稚,也不合实际。中、西方都出过女皇帝,中国有武则天,俄国有叶卡捷琳娜二世。英国更特殊,有多个女皇,而且在位时间都很长,最有分量的要数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每个国家的历史事实都说明,女皇统治下天下并没有更和平。林语堂把女性过度理想化,鲁迅很不以为然。
鲁迅同情妇女,力主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他写过不少文字鞭挞传统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披露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遭遇。但他也反对美化妇女,他目光如炬,看到男人的种种丑陋,也看到女人身上的诸多弱点。他批评一些阔太太和富小姐倚仗男人的势力骄横、撒泼,欺凌弱者。他指出,蹂躏女人最甚的往往也是女人。在许多家庭中,虐待媳妇的正是婆婆,不是公公。媳妇现在受尽凌辱,等到十年熬成了婆,再来欺凌下一代媳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指使女流氓镇压女学生的是女校长杨荫榆。女校长不比男校长仁慈,倒是更狭隘,更狠毒。鲁迅痛批那位杨校长。
鲁迅不是一味地袒护妇女,这恰是最可贵的地方。当代中国庸俗的女权主义者一听到别人挑剔女性的毛病,立马扣“男权主义”的帽子,指责对方性别歧视。她们写文章大骂男人,把男人说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是否也算性别歧视呢?天地造化,男女各异,阴阳互补,两性天然地各有优点,各有缺点。普遍来看,男人较粗心,女人更细心。人际交往,女人更敏感,更容易受伤。生活小节,女人更关注,更容易较真。拼大力气的活,显然男人做更合适;而有些细致的活,女人做得更好。冷静分析两性的特点,让两性取长补短,平等相处,是人类的大趋势。
鲁迅写《娘儿们也不行》反驳林语堂:“娘们打起仗来不用机关枪,然而动不动就抓破脸皮也就不得了……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鲁迅说,争吵和打架在女人统治的国家更剧烈,我们的耳根,更是一刻也不得安宁。鲁迅并不是说女人不能当领导,只是说现行的体制不变,女人来统治,没有任何意义,没准还要更糟。在文中,他还说让半男半女的太监来治理,就更不行,比如叫魏忠贤来做皇帝,天下百姓日子就没法过了。
鲁迅死后
林语堂与鲁迅有过几次争执,发而为文,彼此都动了肝火。大家都是凡人,要说心里毫不存芥蒂,恐怕不合实际。但是,双方都是有胸怀的人,从没忘记对方的优点和功绩,更没有去抹杀。
鲁迅死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感情诚挚。他回顾两个人的交往,不讳言双方的摩擦,也不纠缠个人的恩怨;不存心贬低,也不廉价赞誉。对鲁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持论公正。林语堂与周作人私交更好,但是论起周氏兄弟,他把鲁迅看得更高。他说周作人老是抄书,把别人的东西当自个儿,而鲁迅的文章总是绽放个人的锐见卓识,又不乏诙谐之趣。林语堂精通英文,不仅能说,还很能写。他的英文写作能力,照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说法,比一般美国本土作家还要强。移居美国后,林语堂写了大量英文专著介绍中国文化,在欧美很畅销,一印再印,当时多数欧美人士几乎是靠读他一个人的著作了解中国。林语堂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林语堂为欧美读者编了一本书,叫《中国文化读本》,选录中国最有代表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庄子等人的精粹言语,而中国现代文化部分基本付诸阙如,只有一个人入选,就是鲁迅。林语堂把鲁迅杂文中精彩的段落译成英文编入其书。鲁迅与孔子、老子等圣哲伟人隔着几千年的时空并列,可见在林语堂的心目中鲁迅地位有多高。可惜林语堂这本英文书国内看不到,鲁迅研究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提及。有汉语鲁迅,地位很高,不必多说;有日语鲁迅,地位也很高,鲁迅生前,日语鲁迅文集早就印行。鲁迅死后,日语《鲁迅全集》很快出版。相对而言,英语鲁迅声名不大。鲁迅在英语世界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林语堂功不可没。
(选自《书屋》202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