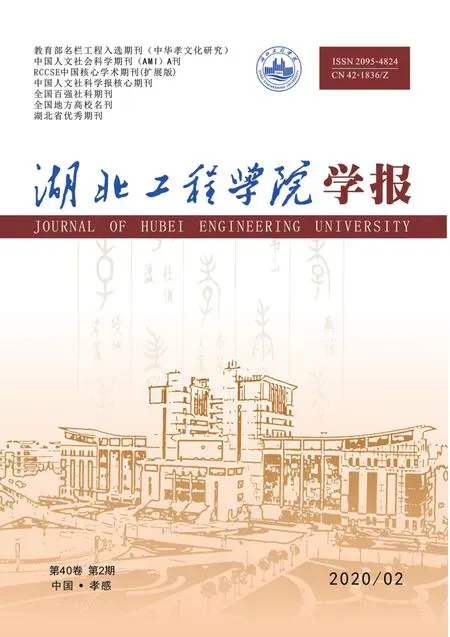漂泊与回归
——论托宾小说《布鲁克林》的女性成长叙事
2020-01-19肖美良
曹 卉,肖美良
(1.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湖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1955-)是自约翰·班维尔以来最受尊敬的爱尔兰作家之一。他的文笔优雅恬淡,内敛含蓄,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其作品主要关注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等主题。继处女作小说《南方》(TheSouth,1990)之后,托宾又陆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其中小说《黑水灯塔船》(1999)和《大师》(2004)先后入围布克奖最后决选名单,后者还荣获 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2006)。
2009年,托宾的新创长篇小说《布鲁克林》(Brooklyn)一经出版就入围2009年布克奖的初选名单,并荣获了当年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这是托宾迄今为止最畅销的作品,由约翰·克劳利导演的同名电影《布鲁克林》也于2015年在美国上映。托宾是一位擅长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源自于自己童年的生活经验,小说《布鲁克林》也不例外。托宾在一篇题名为《一部小说的起源》(TheOriginsofaNovel)的文章里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布鲁克林》的创作灵感。《布鲁克林》既有爱尔兰小镇的乡土气息,又有全球化浪潮中的异乡人故事[1],但更多是一位爱尔兰小镇姑娘在美国纽约的成长性故事:从一个生活在阴影中的人变成了一个完全体验生活的人。小说自出版以来,托宾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家丽莎·席林格所言,托宾是“一个专家,一个沉潜情感的耐心渔夫”[2]。
目前,国外已有学者从文化分裂等主题探讨了以往人们对爱尔兰移民的刻板印象,探讨了托宾对爱尔兰流散主题的解构及对当代爱尔兰叙事中的颠覆及其去神话化过程[3];也有学者聚焦小说中的隐性行为,认为世界主义是爱丽丝社会融合和婚姻前景等背后的隐性驱动力。[4]国内学者或从男性作家的角度描述了移居他乡的女性特征[5];或从文化身份建构解读了爱丽丝的身份认同问题[6]。然而,相关研究大多从较为宏大的文化认同或身份建构等主题展开,鲜有关注小说中移民语境下的女性成长主题。其实,小说虽仍然关注移民经历和回家的困难,但在创作意图上显著表现了女性在追求自由和责任的过程中,思想和情感上发生的变化和成长。因此,本文从女性成长叙事的视角,探讨了移居美国的女主人公爱丽丝,在青春韶华、由内而外地不断探索中,如何实现了个体的蜕变成长之路。
一、自我意识的觉醒:小镇乡土的自我循环
20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内忧外患,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也陷入了焦灼。恩尼斯科西小镇可谓是当时爱尔兰社会的缩影,对于爱丽丝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绝非易事,这是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虽然爱丽丝做事利索,聪明好学,但是她深知,“至少在目前的恩尼斯科西,无论资质多好,也找不到工作”[7]8。当小镇杂货店老板娘凯莉小姐向她提供一个站柜台的工作时,爱丽丝虽然对这个“邪恶的化身”嗤之以鼻,但是一想到“有总比没有好”,“妈妈也会为此高兴”,她便无法拒绝这个“赚钱的路子”。[7]4可见,小镇的生活虽然安逸平静,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职业发展的机会非常有限。
爱丽丝在杂货店短暂的工作经历是她对自己“卑微存在”的一次深刻体验。爱丽丝和凯莉的第一次交谈,就是一个强弱悬殊的较量。爱丽丝希望自己能“想出几句聪明话”[7]3来应对凯莉小姐,觉得自己的无言以对是“一副昭然无礼的样子”[7]3,气场和自信心被完全碾压。工作之余,与好友南希去雅典娜神庙参加舞会是爱丽丝在家乡小镇唯一的娱乐活动。亭亭玉立的少女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了遐想,当然也梦想着出现一位有钱有身份的英俊王子为之倾倒。跟南希一样,小镇上的很多姑娘参加舞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寄希望于嫁入豪门望族,步入上流社会。托宾通过描写爱丽丝和朋友参加舞会的场景,巧妙地揭示了小镇生活的封闭和狭隘。在这种局促的小镇空间里,小说中的众多单身女性仍然期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攀附性的婚姻观在小镇上还十分盛行,很多年轻女孩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放弃了自我的独立和成长。
对于爱丽丝来说,家乡恩尼斯科西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被注入了难以名状的情感内涵。虽然这种情感已经融进了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镇上的“黑暗、寒冷和美丽的空寂”[7]9,也让爱丽丝清楚地预知自己单调而乏味的未来。土生土长的爱丽丝,从未踏出过小镇的一寸一土。在那个圣诞节的清晨,全家欢聚一堂,她无法用更温暖热情的词语去形容当时的故乡。父亲去世之后,三个哥哥也相继离开去了伯明翰,这个“家”更缺少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爱丽丝把自己将要远赴美国的消息告诉凯莉小姐的时候,不但没有得到半句祝福,还遭到了冷嘲热讽,连玛丽也没有跟她道个别。爱丽丝深刻地意识到,如果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余下的日子必将毫无惊喜,“认识所有的人,有同样的朋友和邻居,在同样的街道上有同样的日常活动。找个工作,然后结婚,辞职,生子”[7]22。这样的日子意味着往后的生活无论自己如何努力最后的结果都将殊途同归,生活在表面。传统又封闭的思想壁垒使她毫无反抗之力,“空寂”的村落就算是再熟悉美好,依然存在着令人生厌的落后之处。面对这种空洞的乡土气息,爱丽丝如果放弃了追求自我的勇气,迟早也会逐渐陷入无限而又狭隘的单调重复之中。
爱丽丝虽然生在小镇,却是个有抱负有追求的年轻姑娘,即使在凯莉小姐的杂货店里,也没有停止过对自己未来办公室白领工作的向往,尤其看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之后,她更加厌倦小镇生活的自我循环。在小说的第一章,弗拉德神父到访过后,爱丽丝心想:“她还有这样一种感觉,做普通的工作,拿普通的工资,但那些去了美国的人,她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发财的。她想搞明白自己何以会有这种想法:那些生活在英国的镇上人怀念恩尼斯科西,而去美国的人都不想家。他们活得愉快而自豪。她想知道是否当真如此。”[7]20可见,托宾通过这种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将爱丽丝内心的挣扎和困惑,以及对美国生活的向往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之后,逃离的种子在小镇姑娘爱丽丝的心里已经悄然生根发芽。对于这样美丽的、勇敢的年轻人来说,崭新而美好的生活就像成串地挂在枝头的果实,只要努力踮一踮脚就能够到,离开的想法早已拿定。与弗拉德神父见面的几周之后,爱丽丝收到了一封来自布鲁克林富尔顿街巴尔托奇公司的书信,“信笺是浅蓝色的,抬头位置有一幢大楼的凸纹水印,使它更显得有分量和价值,比她之前见过的信纸都更有说服力”[7]821。对于爱丽丝来说,这封书信不只是一封单纯的书信,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邀请函。此时,小镇的乡土气息在那“一幢大楼的凸纹水印”面前,显得格外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
二、社会规制的觉知:纽约城的秩序与自由
与家乡恩尼斯科西小镇相比,纽约是一座多种族聚集和多元文化碰撞的繁华大都市,这里汇聚着千千万万前来逐梦的炽热青年。对于每一个告别故乡安适和落寞的异乡人来说,理性地对待这里发展的机遇和残酷的竞争,尽快地熟悉陌生社会的运行规则,积极融入这个全新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存在意义,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必修课。
正如巴尔托奇小姐第一次和爱丽丝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人一视同仁。我们欢迎每一位走进商店的人”[7]47。家乡小镇是一种熟人制社会,而爱丽丝也很早就识清了它的闭塞狭隘和庸碌前景。相比之下,在纽约布鲁克林,爱丽丝则必然要面对陌生社会中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在小说的第二章,爱丽丝在度过了一个最难熬的夜晚之后,在餐馆就餐时可以找到一个没人能对她脸上的表情说三道四的座位。走在大街上,街上人来人往,她没法轻易超过,而到富尔顿街时,“人群像是足球赛后退场一般拥来。即使是常速步行也挺艰难”[7]56。这些情景都是家乡小镇那个熟人社会无法想象到的,在布鲁克林,总有一种无形的规范保障着有形的秩序,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唯有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严格的遵守。
或许,规则的严苛会使人们彼此产生某种距离感,但爱丽丝仍然盼望房客中能有个知心朋友,听她倾诉思乡之情,或者帮她提供一些可能的建议。但是,她似乎总能从他人的行为中品出一丝防御和戒备的意图,这可能是陌生社会里大家固有的谨慎态度和自我保护意识。不久,爱丽丝也开始辩证地看待任何可能会蒙蔽自己的种种表象,而这种能力是能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获得最大确定性的成长本性。
当房客戴安娜和麦克亚当小姐在她面前肆无忌惮地说着新房客多洛丽斯闲话的时候,爱丽丝不愿参与其中,并“坚决地在她们面前关上了门”[7]98。在参加舞会时,爱丽丝为了摆脱多洛丽斯,突然间决定要“站起来走到他们队伍中去,自信地朝他们微笑,仿佛他们是老朋友一样。她挺直了背,让自己显得大大方方”[7]101。可见,爱丽丝在处理这些事务时表现出的果断和从容,是她在这个陌生社会里逐渐成长的结果,而成长带来的自信和经验能让她在纷繁的世界里不断武装自己,待人接物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除了应对外部世界的自信之外,女性的成长还体现在面对内部的个人情感层面。在移居布鲁克林之前,爱丽丝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被设计或者支配的,甚至连那次越洋之行也是在姐姐罗丝和弗拉德神父的安排之下才得以成行。爱丽丝从踏上邮轮的那一刻起,就 不得不独立面对眼前的各种困难,在布鲁克林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也在不断地培养着她的独立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丽丝将面临着情感独立性的成长挑战。在小说中,托宾通过爱丽丝与意大利裔美国人托尼的感情线引出她在情感方面的成长历程。爱丽丝与托尼在舞会上相识,两个年轻人是在一点一滴的接触中互生情愫,但并没有小镇舞会上那种令人生厌的攀附性动机,只有两个自由平等灵魂的惺惺相惜。
不难看出,托尼对爱丽丝的深情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虚伪,也经受了爱丽丝的各种考验。他们的爱情没有海誓山盟的贞烈,却有着细水长流般的细腻和柔美。当周末托尼带着爱丽丝去看电影的时候,令她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让她去坐后排位置,而是随她高兴,而且似乎喜欢坐在中间,那里视野最好。看电影时,他用胳膊环着她,有几次对她小声耳语,但也就仅此而已”[7]113。托尼总是体贴地照顾着爱丽丝的所有情绪,像花骨朵一样包裹着花心,内心成熟,外表孩子气。读者从两人的相处中能感受到生命与生命之间是共呼吸的,一方能够体会和包容另一方的小情绪。托尼对她的一往情深她已完全领会,她也在心里默默许诺要永远珍惜他,她弄清楚了爱情中自己想要的东西。难能可贵的是,爱丽丝摆脱了小镇上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勇敢地直面自己的情感生活,独立地作出了爱情乃至婚姻的选择。在这个陌生的社会里,自由而芬芳的爱情之花却能够在无情的规则和秩序之下尽量绽放,这恰恰说明了布鲁克林的魅力所在。小说中的这段爱情叙事,巧妙地衬托了爱丽丝在情感方面的自我成长之路。
三、主体性的生成:自我的设计与超越
女性的成长历程中最富有人文内涵的是主体性的生成,“每个打算为自己生存辩护的人, 都会认为他的生存含有一种不明确的需求,即超越自我、参与自己所选择的设计的需求”[8]。在《布鲁克林》里,爱丽丝的成长必须以完成女性的主体性生成为目标,从生活到工作,再到情感等各个方面,成为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践行者。
移居海外意味着选择和失去,当逃离小镇的兴奋随着离开前的准备工作而慢慢消退的时候,爱丽丝心中也有过纠结和不舍。不舍的是仍然留在小镇的母亲和姐姐,爱丽丝知道她的离开会增添母亲内心的感伤和牵挂,也知道姐姐罗丝肩上的担子将会愈加繁重。看着小女儿快要离开身边,出去闯荡,母亲的面容浮起的“阴暗的神情”[7]23,这是自从父亲过世几个月后,爱丽丝从没见过的。当然,她更不舍罗丝,她渐渐意识到“罗丝在帮她办妥出国之时,也放弃了真正的希望:离开这个家,有她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庭”[7]24。其实,罗丝的离开或许更加容易,这在小说的一开篇对姐姐性格和能力的描写就可以明显看出。爱丽丝心里明白,自己的离开是罗丝舍弃自由、自我牺牲换来的,她希望自己不要辜负姐姐的期望,这个因素也将成为往后奋发成长的源动力,为后文身处陌生世界遭遇迷惘时的坚韧埋下了伏笔。
姐姐罗丝在爱丽丝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启蒙者的作用。无论是“迈着轻快的步伐下班”[7]1,还是在化妆镜前“细细端详自己,涂口红和眼影”[7]1,姐姐的一言一行都为爱丽丝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成为她学习的榜样。
追梦者都是怀着迷惘和不安踏上自己的探索征程,爱丽丝真正担心和恐惧的是,“她将永远失去这个世界,她将再也不会在这个普通的地方过寻常的日子,她的下半辈子将与陌生事物搏斗”[7]24。然而,爱丽丝是幸运的,这份幸运来自姐姐为她指路引航,也来自于她自己的深刻领悟力。在赶去利物浦的船的路上,罗丝一系列似教科书式的交际活动给爱丽丝做出了典范,而爱丽丝独特的天分也让她很快能活学活用,就在与罗丝分开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感谢他时,语调和罗丝差不多了,温文亲切,又带着点距离感,但毫不羞涩,这是一个女子充满自信的语调”[7]26。
来到陌生的布鲁克林之后,爱丽丝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改变,这一点连她自己都出乎意料。小说中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当爱丽丝刚刚抵达布鲁克林公寓的时候,她以新来乍到者的身份与几位爱尔兰的房客和房东交流时,一开始总是躲躲闪闪,不时地露出几分胆怯和羞涩。但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爱丽丝逐渐开始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跟她们自由地对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基欧夫人给爱丽丝换房时,面对房东的“咄咄逼人”[7]79,爱丽丝却“回敬目光,没有退缩”[7]79。
爱丽丝的成长并不只是局限在与房东和房客的交往中,在自己的学习和职场生活中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成了有趣的切割面,是生活将她打磨成了一颗熠熠 生辉的钻”[9]。爱丽丝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渴望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她不愿在众人排挤中做一个懦弱的傀儡,这种改变是发自内心的,是处处碰壁之后寻求生存的强烈本能。就像当初不甘心只是在凯莉小姐杂货店柜台工作一样,爱丽丝当然也不满足于百货大楼的工作,她渴望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业务和专业能力。因为她深知,这是在布鲁克林这个陌生社会所必需的生存技能。在弗拉德神父的帮助下,她毫不犹豫地利用工作之余参加了夜校的学习。除了学习簿记和会计学方面的知识外,这段夜校经历也让爱丽丝收获了更多的自信和从容。当爱丽丝鼓起勇气向法律授业教师罗森布鲁先生寻求帮助时,那场轻松自如的对话,让她“对自己感到惊讶,竟然一点也没结巴,连脸都没红一下”[7]91。面对学识广博的资深教授,她的表现不仅礼貌,而且自然,还有几分风趣,她似乎感觉到自己已经渐渐融入了这里。这给她带来了莫名的自信,每一次点滴的变化和成长,都给漂泊在外的自己更加坚定而厚实的信心。
爱丽丝的勤奋好学并不是平白无故地生长出来的,她的家乡爱尔兰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她不断学习、追求进步的优良品质。在这个陌生的纽约布鲁克林,作为异乡人的爱丽丝,白天勤勤勉勉上班,晚上一丝不苟苦学。众所周知,家乡爱尔兰有着优良的教育制度和优秀的教育理念,而爱丽丝显然继承了爱尔兰人终身学习的可贵品质。她努力寻找着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学习的渴望和冲动在她的世界中,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在纽约城,她仔细地观察着家乡从未见过的时装和用品;在百货大楼,她能够娴熟地跟各种顾客打交道,工作经验与日俱增;在布鲁克林学院,她全心投入到薄记课和会计课的夜校学习。
繁忙的工作和繁重的学习让她变得充实,虽然束缚疲惫却没有忘记出发的理由,孤独思乡时没有忘记离开的初衷。她已经一改踏入美国时游离于表面的漫游状态,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洞见这个全新的世界,也慢慢地与未来世界开始相识和相遇。
正当爱丽丝陷入热恋,暂时遗忘了思乡的孤独时,姐姐的意外离世给了她沉重的打击,她决定回到家乡。再次出现在恩尼斯科西的爱丽丝,有着不同于小镇的“时髦”,说话也有些许美国腔调,“也带回了近乎于魅力的东西”[7]183,她甚至还发现“有个女人在看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和皮鞋”[7]168。显然,托宾正是借助对比的手法进一步突显布鲁克林的生活对爱丽丝从内到外的重新塑造,因为“真正的女性成长之路,就是一条女性打破各种樊篱获取经济自由、摆脱精神依附走向人格独立、超越心灵闭守探求自我实现与主体自由的坎坷之旅”[10]。
显然,爱丽丝的成长并没有结束,她需要在恩尼斯科西和布鲁克林之间,吉姆和托尼之间,做出自己艰难的抉择。她内心反反复复地在异乡和家乡中辗转,异乡是不安分的理想,而家乡则是不甘心的安逸。爱丽丝的犹豫和挣扎,甚至后半段与吉姆那似有若无的感情,其实是回到了熟悉安全的环境后一种具象化的表现。其实,那并不是爱情,而是对异乡未知的本能逃避。当她回到爱尔兰时,当初选择美国的理由再次浮现,而此时对布鲁克林的思念又变成了新的乡愁。当那个凯莉阴阳怪气地询问她在纽约的婚事时,她先是一愣,后是惊恐,最后是愤怒。凯莉站在道德制高点削断任何与这个小镇旁枝斜出的东西。爱丽丝虽有自己已婚的事情被人察觉的担忧,但更重要的是,她觉醒了,猛然发觉这个小镇其实还是和原来一样的腐臭不堪。最终,“她回布鲁克林了”[7]202,这是爱丽丝新的更彻底的自我成长和超越。相比第一次离开家乡来说,这次重返纽约,回到托尼的身边,则是她自己独自做出的抉择。正如爱丽丝所思考的那样,“(她回布鲁克林了)这句话对听到它的人意义越来越浅,而对她却越来越重”[7]202,因为这将成为其女性主体性生成的重要标志。
四、结 语
凭借娴熟的语言表达和微妙的细致刻画,托宾塑造了一个爱尔兰小镇姑娘在漂泊和回归之间徘徊的成长故事。作为夹在两个不同文化世界之间的爱丽丝,直到小说的最后一页,才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情感真正在哪里,而那又将成为她新的成长起点。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不仅仅呈现了一个青涩的小镇姑娘逐渐走向成熟独立,不断自我成长和自我超越的人物形象,也映射了无数移民女性成长生活的真实写照。不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对在全世界移民大潮中已经、正在或即将定居国外的少数族裔群体来说,小说的成长叙事必将唤起他们不同程度的心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