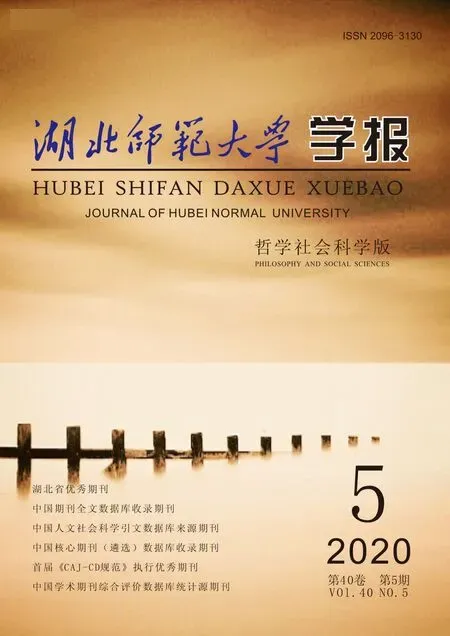乘之愈往,识之愈深
——胡海容《此心安处》谈片
2020-01-19胡光波
胡光波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002)
这是一个游子的自白,也是她馈赠故乡的厚礼。
胡海容女士生于鄂东浠水,自幼为大别山神灵荫护,受惠于长江故土的人文灵秀,时得父母师长的指教督查。此后,求学精进不已,任教读写不辍,未尝有一日怠懈。几经辗转,今托足于西北某一名校,虽与家乡悬隔千里,然魂牵梦绕者仍是鲜活生动的家乡人事,使之时时觉得温馨宜人。惟其如此,她以文字将其定格,不仅能心神安宁,也能驱散庸常生活的竞噪喧嚣,在独处时得以细品久违的酸甜苦辣,从而获取奋发自为的刚勇之气。
作者长于自然乡野,一直受底层民众朴质的熏染,温良恭俭让构成其性情的本色。成岁后虽久居大都市,但对生命最初也最深的体悟,乃源于养成其品性的故园山水,而神秘诡谲的楚风、旖旎多态的民情,则早已沁骨入髓。因地域文脉的影响,她于文似有夙缘:初怀文学幻梦,少时勤写日记,以览察寸进;后读书札记以辅教,下水作文以练笔,多方磨砺思想的触角;一俟入大学,视野更为开拓,心胸愈加坦荡,而笔法亦遂之摇曳多变;近来拜网络之赐,广取各地文友之长,其清思之细密、雅趣之真淳和祈尚之邃深,远逸于昔日。不过,前多年写作还是触事随想,四下点染,虽机杼自出,而头绪纷纭,思无所主。步入中年之后,常援才人以自励,一种写作的使命感萌生,意图渐趋明朗,遂聚思对焦,而怀旧思乡之旨一线贯通于众作之中。结果,就成就了这情意缱绻的《此心安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第1版)。
该书五辑四十四篇文章,有童年生活写真、人伦挚爱体味、师友情谊重温、读书甘苦自尝,叙说急缓得宜,文笔轻灵柔美,即使每述不堪不适者,都能情绪自控,分寸拿捏,绝不蓄意渲染,措笔多出之以白描:环境氛围,意在还原自然历史的原貌,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人物言行,意在保持其性格品性的本真,凸显其于己的潜在影响;难得的是,作者不将个人置身事外,仅以观察者的视角记录,而能作为参与者回溯既往,感思多般,使所述之事逼近客观,而其中所蕴含的人情物理,随着作者素淡的笔触一一自然彰显,力求史实逻辑与思想逻辑契合。末辑虽命曰“灯下漫笔”,蓦瞥似为感时伤世的急就之章,像《后会无期》分为几个片断,有对友情变味的惆怅、对少艾暗恋的回味、对同好夭亡的伤痛、对至亲辞世的心哀、对离别难会的无奈,然其余各篇,细读则是叙事为先的精心之构,如军营情结的难解、佳书际遇的冷热、金庸武侠的血性等,只不过述说时忍不住一摅殷殷之情,如从谈猪引出“穷莫丢猪,富莫丢书”古训,从论生日说到作为女儿身的尴尬等,让人读来骤惹一腔枨触,顿发几声喟叹,似与作者感同身受,欢戚与共。
毫无疑问,第一辑《故园东望》的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是一篇“纲领性”文章,它是作者前半生成长求学、遭逢家变的缩影,也定下了全书的情感基调——默默的眷顾,悠悠的感伤;长久的向往,不尽的感念。让我们以此为基点,徜徉于作者所编织的文字世界,以揣摸其生命之潮向,感受其精神之脉动。
海容女士小时与母在山村,十岁随父至县城,为了成家赴外县,父母去世后去读研,先南下玉林谋生,后北上西安落户。几十年来,曾四处奔走,可谓风尘仆仆,栖惶无定,但成年后所遇光景、所遭人事均一闪而过,居留心底深处、未有丝毫泯亡的,是故乡的蒲扇红枣、蟹膏花生,儿时的雪人雪仗、轮渡棉田,以及家乡连绵的山丘、平整的田畴、曲折的河汊和幽静的芦荡,还有熟谙的乡音和无拘的笑语。随着双亲的去世,自己也远赴异地,日居月诸,不仅未冲淡儿时的记忆,过往的一切反而更为清晰,正如年老的歌德所叹:“眼前的一切,仿佛已跟我远离;消逝的一切,却又在化为现实。”(《浮士德·献诗》)不经人事的青年常骛高驰远,鄙弃家乡的粗鄙,希望早点脱身贫瘠,享受异地的荣华盛景,而屡吞浊水、迭遭横逆的旅人,常在受挫遇阻、身心两疲之时,倍觉家乡山水的稳实宽厚、父老的恩惠深湛,可以终生依倚。司马迁曾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贾生列传》)此乃才人罹不平之事所发的浩叹,其于精神的求助,诚似于教徒托举双手,向神灵的拜祷。当今承平日久,人久习于逸乐,锥骨痛心之事虽少,然不如意者总有八九,处于异乡若非有佳友推心,惟抽足自反,退居本心,从家情乡意中,汲取生存的伟力,独抚结痂的伤痕,苦痛方得稍释。自古以来,故乡亲情为人歌咏甚多,揆诸中外地缘历史和文化传承,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但立足于今世,当不拘于昔人嗟叹,若能以善心入世,以诚意待人,就能涤除烦虑,推己及物,民胞物与,视天下为故乡,则四海之内皆兄弟未必不可。但是,与我们血缘相拈、情感互通的故乡,仍是滋养我们肌体功能的补血露。可喜的是,作者以罗田为第二故乡,而玉林、西安则将成为第三、第四故乡,因为不管如今在否,曾经发生的一切,都永难为忘川所冲刷,会在生命的某些时候,不思而至,启人慧智,予人以情感的慰藉,故虽无故乡之名者,并非不具其实。
当然,思乡离不开自然风光,但作者重点描述的无疑是情与爱——家人之爱、师友之谊和同学之情。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普通人,他们在作者的成长历程中,或为情感的支柱(家人),或为精神的助力(师友),或为思想的益友(同学),或为灵肉的良伴(丈夫)。正是有这些人的佐助携承,作者视坎坷的世路为平夷,将命运的颠簸当考验,在心劳力拙之时,能及时消除沮丧,信心饱满,精力充足,对乱我情者淡然以处,以冷静之心逆难料之事,绝不放弃夙志宿愿。就这样,她由稚气丛生到英姿勃发,终致沉稳练达,而最初形成其人格根柢的,是含辛茹苦、鞠育其成的双亲。
海容女士父母的婚姻,本于媒妁之言,初无任何了解,年不到二十即订终身,就如过去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夫妻一样,正因此也埋下了婚后种种不幸的宿根。其实,其父最初谋得小小公职,还得力于舅舅,虽然为家里老人所阻,但其母全力支持。为在单位站稳脚跟,父亲一向卑以自牧,谦恭谨微,自奉甚薄,因为那一点点薪水,要维系一大家的生计。因其长年在外,养老育儿等一应营生,只能为母亲所一手独揽。如果能以敬老惜幼、田间辛劳换得家人的尊重还可慰,但母亲婚后三年未孕,即使家人未明言责备,也常自怨自艾,甚至想净身出户。所幸后来连生四胎,儿女齐全,但家累亦大。因长期分居,遇事不得沟通,父母时常发生冲突,免不了口角。面对父亲的恶言暴语,母亲向来低眉顺眼,委屈以承。平淡的夫妻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来。直到发现母亲癌症已到晚期,父亲才如梦初醒,感到亏欠妻子太多,但为时已晚,惟尽力服侍,补赎过失,弥补缺憾,以至于得了老年痴呆症。上辈人的婚姻及其生活,基于其时的社会习惯和乡俗里习,多以传宗接代为第一要事,尤其在农村承继家业、以续香火是人们挥之不去的观念,故母亲的悲剧难以避免,加上父母婚前缺乏沟通,又长期两地分居,见面一言不合,即磕碰冲撞,平日难以相互温存,而甜言蜜语更羞于出口,这种粗糙朴陋的夫妻关系,之所以能维系一生,且依循大多数人的生活惯性而前行,其情感的纽带是一天天渐长的儿女,个人情趣和精神生活空间几乎为零。父辈这种生活状态,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似乎可悲可哀可叹,因为他们既非相爱而结合,也无结婚而后恋爱,他们的思想错位,情感不在同一频道,精神的维度宛若霄壤,但他们毕竟历尽苦难,终生相守,既赡养老人将其安然归葬,又培育儿女使其自立而存,可谓甘愿牺牲自己,只求成全一家,以完成赓续家族的神圣使命。旧式婚姻虽有悖情违理之处,但两人在长期生活中,从陌生到熟悉,从不容到相忍,最终产生亲情,扶携以老,未必逊于所谓两情相悦者。较之于今日一些男女,婚前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而婚后稍不如意,即大打出手,你朝秦暮楚,我得陇望蜀,离婚亦夺儿攘女,争财产头破血流,于公堂吵嚷不休,于此之时,当初所谓爱情焉在?与之相反,父辈这种捆绑式的婚姻,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餐之以不幸,偕之以痛苦,其情感的凝聚力非所谓自由恋爱者所可比,因为它在生死攸关之时,能涉险历难,同舟进济。就此而言,今人切莫盲目自喜,一味替昔人悲鸣,因为自身缺乏精神的内应力,一遇风吹草动,难免处处露怯。《骨肉情深》一辑十分之七记父母,后六篇均看作是第一篇《无言的爱》的补充扩展,衍伸细化。读者如能合而观之,当体会父母于儿女体贴爱护之深,惜乎当我们年长明理之时,已不及回报他们,过后而思,隐隐之痛遍及周身。
《师友情重》一辑,既有大中小学的老师、同学和学生,也有社会人士如画家、理发店主与朋友等。从作者自述得知,她自求学毕业、步入社会,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迁移工作地点,曾遇到不少尴尬甚或阻力,几度迷惘不定,对那些违己情志的人事,内心极为拒斥,而又无奈其何,偶尔对所操之业亦犹疑不定。但是,现在事过境迁,在重理记忆之时,她将那些惹人不悦者都一一剔除,只选取让人舒心、令人怀恋、激人振作者,将事情的原委徐徐道来。记人善于选取其生活细事,将师长的谆谆教诲、同辈的融融之乐和盘托出,让人觉得世态虽有炎凉,人间犹存温暖。如作者在华中师大攻读教育硕士,因爱好文学与三位中文老师结下不解之缘:古代汉语老师周光庆,一向韬光隐晦,低调为人,从无炫功自显之举,而执教严肃不苛,不容嬉戏,作者毕业后每自消沉,都得其书信以自励;古代文学老师戴建业,讲课旁逸斜出,风趣幽默,平素亦开诚坦荡,自己深受感染;写作老师晓苏,与学生不分你我,关系融洽,上课随手点染,随机启发,对自己创作鼓励有加;甚至连丈夫的博士生导师张波,除对她夫妻工作的变换关怀备至,还消解其对现在工作性质的疑窦,并对其写作长短直言不讳。如果说大学老师对其创作影响甚巨,那么中小学老师则对其人格的初定、人生的规划,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像数学老师吴洁华、语文老师潘新民,把她引上求学之路,至于其他人,在与其交往之中,多能从中汲到人性良善者,如与《学海回眸》一辑并读,当两相补充,而其中所写的中学校长佘建设尤其值得一提。
我在中学任教数年,与作者经历类似,深知一校之长,官虽不大,但在其所管范围内,乃一言九鼎,执掌生杀予夺,年轻人如稍有忤逆,他可轻易判定其生死(留置本校或贬黜他处)。我毕业之初,分于一所重点中学,因多方原因,一年后即和其他七人被排挤,其时颜面全失,声誉尽毁。究其原因,有个人工作不力之处,也和校长为人强硬独权、行事苛责不无关系(其他原因兹不缕述)。但是,佘校长之言行举动,则显示其开明民主、公平正直、与人为善的工作作风。起初,作者未婚夫在佘校长所在罗田一中,自己则在浠水,虽然邻近,毕竟生活不便。要想同处一地,跨县调动手续烦琐。此事征之于佘校长,他给他们出了不求一步到位的权宜之计:先从浠水调入罗田普中,然后等条件成熟,再入罗田一中不迟。基于她的工作业绩,加上校长的帮助,一年后终于夫妻团圆。入校后,佘校长热情主持其婚礼,对她职称评定,也不另眼相待。其实,不仅对她自己,而且对其丈夫,校长都一直青睐有加。校长发现他有能力,力排众议,让丈夫当上班主任。丈夫研究生毕业回来,校长又考虑到他的性情,力劝他放弃乡镇工作,到学校政教处做管理。当作者考上研究生,丈夫已找到一个高校,想双双调动工作时,校长又出于对其前途考虑,欣然同意放行,并为他们公费读研、本需赔偿而向上级申述缘由,要求支持财力不丰的夫妻二人。从佘校长的所作所为,可清楚看到:基层领导固然有颟顸自大、刚愎自用者,一旦权柄在手,对下属刻薄不公,也有深明大义、心地良善者,正因为他们秉持公义,故常能于关键时刻,拒逆流,布清风,彰显人性的光辉,毕竟良善乃人之本性,不计庙堂或草野,都有萌生的机缘,而这种善性之光一旦照拂年轻人,不但他们终生受益,也会自然将其承继,并进而发扬光大。行文至此,我在为作者生途庆幸之余,也为自己当年所伤而悲。
胡海容女士自二十岁入世,历经几番风雨,终于迎来雨霁天晴。她目前家庭幸福,生活平顺,儿子学业亦有成,但不愿清福独享,枉费多年的苦斗,想以日积月累的劳作,实现少时的创作梦,使人生更为丰盈充实。正如自序如言,她正式写作始于中年,与少年成名者相比似晚,但其起点比他们高,因为有此前的知识涓积和生活摧折,其文字没有一丝轻狂自喜,更多的是沉稳诚真,其宽容之性正如其名。我相信,她对文学创作,只要目标恒定不变,往后每发一矢,必能破的,其斩获将会更为丰厚,绝不负其平生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