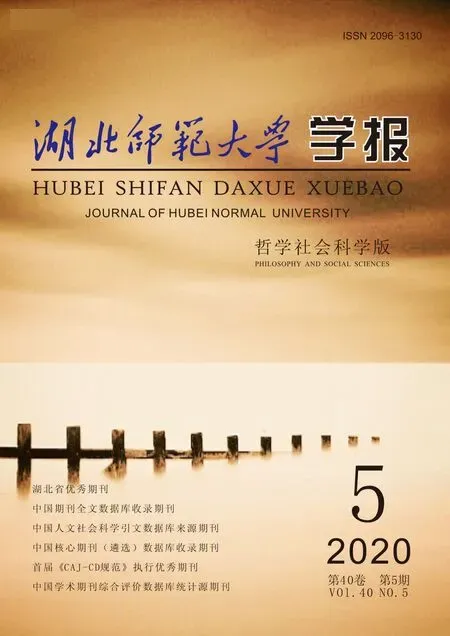论《红煤》中农民生命状态的困境与突围
——兼及“十七年”农民形象叙述的历史延续
2020-01-19王再兴石玲君
王再兴,石玲君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湖南怀化市辰溪县船溪学校,湖南 怀化 419500)
刘庆邦的小说以乡村和煤矿为主要题材,以诚实为创作风格,笔触始终聚焦在底层人民之中。《红煤》讲述了农村青年宋长玉奋斗的历程,并以此为线索展示相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况。这部长篇延用了《神木》的题材,但绝不是《神木》的复制品。作者摆脱了一贯的创作模式,由单一的苦难叙述转向了对生命状态的解读,自其出版以来获得了相当多的关注①。事实上,人文关怀在刘庆邦的作品中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他一贯的创作原则。《红煤》既是刘庆邦对人性的深度关怀,也是他对农民个体生命困境的描绘和思考。近些年来,底层文学得到不少的关注和讨论,也遭遇到一些质疑,本文从“物质”和“身份”的困境入手,争取对这些话题有所回应。
一、“物质”的困境
刘庆邦表示过他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此种诚实包含了多重意义,《红煤》是一个窗口,刘庆邦通过这扇窗口展示了他所认识的世界——困顿着的世界。作者当年曾经说过矿工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他对中国煤矿的了解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红煤》是他对煤矿生活的深刻反思。小说描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私营煤矿行业发展带来的困境,即矿工的高死亡、自然的高损耗,以及工人的低回报、事故的低曝光,等等。
第一重困境:小说中矿工的高死亡、自然的高损耗。首先是矿工的高死亡率。我国是煤矿生产大国也是煤的消费大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年至80年代,为计划经济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为粗放发展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为煤炭行业整顿治理时期②;目前处于第四个新的阶段。《红煤》主要以第二阶段为故事背景,小说以宋长玉的个人奋斗为线索,揭示了当时高速而混乱发展的煤炭行业带来的困境。此阶段有个显著的特点,即改革开放后,因各项政策的实施,市场趋于活跃,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逐渐增大。为了满足需求,国家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得益于市场的变化和政策的改革,私营煤厂挤退大型国营矿场,占据了主要市场。小说中的红煤厂矿以及振兴煤矿是当时粗放型产业发展的写照。大多数矿场经营者为了利益的最大化,把矿场的开采承包给工程队,然后按照生产量来支付工资。工程队为了扩大生产量,往往选择减小成本和提高工作时间。盲目的生产加大了事故发生的概率。小说正面描写了三起矿难,具体情况如下:
在唐洪涛的设计和安排下,事故的善后处理进行得比较顺利,一共才花了不到十八万元,也没有出现泄密的情况。[1]
红煤厂矿几乎每年都死人,每次死了人,宋长玉都采取私了的办法解决,这个办法省钱,省事,弄好了还可能被评为安全生产矿井。[1]
这个事故不要让上面的人知道,他们私下里处理。具体处理办法是,没出来的人是哪个包工队的,由哪个包工队负责给家属一定的赔偿。[1]
小说中提及的三起事故,总死亡人数为24人,包括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一起。《红煤》创作于前述煤炭行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因第二阶段政策的放松以及市场的变化,粗放型煤矿行业得以急速发展。这种情形下的高速发展往往难以避免工人的高死亡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0至2007年我国煤炭行业共发生事故27416起,死亡45162人,平均每百万吨煤死亡3.04人[2]。另一方面,在所有重特大事故中,矿难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同等的生产条件下与其他行业相比,煤矿产业的事故爆发率和死亡人数是令人震惊的。如根据《劳动保护》的统计结果,2001年上半年爆发了59起重特大事故,死亡人数1086人,其中矿难事件占总事故的50.8%,矿难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54.2%[3]。其次是自然的高损耗。矿工的生命安全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是作者刘庆邦描写的主要困境;然而在主要困境之下,还隐藏着他对自然环境的担忧。宋长玉曾两次带唐丽梅到红梅村游玩,第一次是在红煤矿出现之前。此时的红煤村满目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宋长玉成为红煤矿场的厂长之后,带着唐丽华故地重游,红梅村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河流枯竭,河床龟裂。因为缺水,山上的树木枯死,曾经的旅游胜地不复当初。自然景象衰退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红煤村出现了水井枯竭的现象。村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事实上,开挖煤矿极易导致地面下沉,滑坡,崩塌,泥石流,地下水疏干以及水污染等环境问题。譬如,西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供给地,但是西北地区本身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据有关统计显示,2010年西北地区煤炭开采与加工转化废水排放量达到5.4~9.0亿吨,预计2020年将达到12.1~17.4亿吨[4]。煤矿产业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将是长期存在的。近些年来,我国煤炭生产及消费的总量在全球仍然是最大的。庞大的产业背后,是劳动者的困境,也是自然环境的困境。
第二重困境:小说中事故的低曝光、矿工的低回报。小说叙述的高死亡率和高损耗,并不意味着高曝光和高回报。低曝光一方面是因为矿工话语权的缺失。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看起来拥有讨论的自由,实际上却找不到表达的途径。宋长玉选择以厂长给矿工发伞的故事为题材写稿件,单纯是因为这样的题材贴合《矿工报》的需求。通讯员的现场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只是按照剧本走个过场。作为厂长的唐洪涛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新闻”;但是宋长玉向上级投诉唐洪涛的不公,他的声音却像失去了媒介一样消失在真空之中。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大多数都是沉默的,话语的丧失使得许多矿工成为矿难沉默的死者。低曝光也意味着高瞒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煤矿行业伴随着高发的灾难,这个行业的劳动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刘庆邦承认行业的特殊性,死亡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是可以商榷的。《红煤》中宋长玉、唐洪涛对矿难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代表着当时尤其是私营煤矿行业的普遍做法。矿工因事故死亡与矿场老板受相当的惩罚是构不成等号的。死亡人数必须达到一个连行业内部都觉得惊人的数字,并且在他人无法掩盖的情况下,这些受难者和矿场责任人才可能获得合理的对待。否则死者往往不过是以不高的赔偿金抵换了只此一次的生命。他们甚至用死亡为雇主打造了一条通往“安全生产矿井”称号的光明大道。小说中是这样,现实中类似情形也多见,如2002年山西省繁寺政府与金矿经营者联手谎报死亡人数,试图封锁消息,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家属一度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5]。这样最终得以曝光的瞒报事件有很多。曝光了的是可以统计的,有一些却了解起来比较困难,那些沉默的死者基本上已经无法统计了。
另一方面,当时的高风险并不等于高保障。在特定社会氛围下,矿工这一群体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生命安全很难得到有效且有力的保证。尤其是农民矿工,工作环境差、时间长,劳动对身体伤害大等,都容易对他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二次伤害。如2007年淮北地区的一线矿工的日工作时间为12至14个小时,每月工作26至31天。一线矿工的最高工资在2000左右,二线工人的工资基本为1500左右[6]。工资少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矿场的基础设施和医疗保障难以跟上。小说开篇着重描写了矿工洗澡的细节,矿场有淋浴的设备,但是都已损坏,无法使用。澡池水质浑浊,黑中泛白。矿工只能用这样的剩水洗衣服,洗衣与洗澡同在澡堂,原本浑浊黏稠的洗澡水在脏衣服的催化下迅速变质,散发出难闻的臭味。除此之外,长期作业还会使矿工们患上矽肺、关节炎和腰肌劳损等职业病。尤其是矿场的私营者,为了效益还隐瞒工人的体检结果。相比情形下,如美国同样为世界煤炭出口大国,但是其矿难爆发相当少,存活率大。2000 年至2007年,美国矿难死亡人数为241,百万吨死亡率为0.027人[2]。在美国矿工与警察同属于高风险职业,工人各项待遇与警察一样都很高。这与当时我国矿工的生存状况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
二、身份的困境
按照汪政和晓华的定义——底层文学是“为底层”的文学和“底层写”的文学[7]。《红煤》具有底层文学苦难叙事和现实发露的普遍写作特点。但是书写苦难不是鉴赏苦难,发露现实也不代表排斥光明,《红煤》对困境的思索是基于对个体人格的提升。刘庆邦以可见的困境为开端,进一步讨论到个体精神上的困境。他认为个人困境源始于身份的区别和歧视所带来的压抑。
宋长玉们的精神困境,主要源于身份的压抑。作为文化符号,“命名”代表一定的含义,理性意义和情感意义都包含在内。《红煤》存在着许多关于身份的词语,其中暗含了对农民工身份的区隔和歧视,形成二元对立结构。在理性意义上,这些身份命名形成互补关系,它们绝不是单独存在的,有甲方必有乙方与之对应,如农民轮换工——国家正式工,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农民——工人,农民子弟——领导子女,村民——村干部,普通工人——领导干部,等等。同时这些身份命名也不是偶然和片段地出现的,而是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以第一组词语为例,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农民轮换工”包含了以下义项:农民、轮换、农村户口、没有优待,等等;而“国家正式工”则包含了不同的涵义:国家、正式、优越、城市户口、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等等。小说中六组成对比关系出现的身份词语,在情感意义上也是呈递等关系的。首先,是弱势身份对原初身份的歧视。宋长玉本人对第一种身份(即“村民”)非常排斥。他的身份历经从村民、农民、农村户口,到干部家属、厂长、城市户口的转变,个人奋斗都是为了逃脱第一种身份。他对第一种身份的厌恶根源于该身份所附带的歧视和压抑。其次,是强势身份对弱势身份的歧视。文中唐洪涛、唐丽华正是因为宋长玉“农民轮换工”的身份,才漠视他的感情。而现实语境中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工”这一词语随之而生。各地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一群体的调侃代称。在南京他们被称为“二哥”“二姐”;上海人则称外来务工者为“江北人”。“二哥”“二姐”的说法由“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演化而来,突出了农民的原初身份。“江北”意味着贫困、愚昧、野蛮、落后[8]。这些代称都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首先来看单一性弱势身份的压抑。身份命名成为个体的便签,在社会交际中,个体在他人眼中就被简化为单一的身份;被贴上标识的农民不仅进城难,而且处于被拒绝的状态。通常,弱势身份起点较低,可选路径较少,付出的牺牲却相对较大。《红煤》如实写出了矿工们的生存困境,作者通过矿工子弟、农民对煤矿劳动者的不同态度,证明了这一点。小说中的一些人对矿工这一职业怀揣着不同的态度。一类是乔集矿正式工的子女,他们不愿下井,宁愿游手好闲,在家啃老;另一类是宋长玉这样的农民轮换工,与矿工子女相反,农民轮换工对矿工这一职业怀抱着极大的热情,甚至千方百计想留在矿场上。二者截然不同的选择是基于身份的不同。进城难,而进城后弱势身份受到来自民间的歧视和体制的区别对待。比如各种民生新闻中农民工让座频繁被拒或被羞辱,已不鲜见。弱势身份在制度上也是如此。个人被区分为城镇户口——农业户口,本地人口——外来人口。制度以此为基准把人划分为“制度内”与“制度外”,相关的各种权利、福利和保障的分配也随之而异。上世纪1980年代前农民进城受到严格管制,未按照计划转入城市的被称为“盲流”。至今农民进城后仍然面临着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区分对待。农民工的子女入学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滞后发展等等,都体现了制度的区隔性质。
其次来看身份压抑产生的影响。身份压抑对受压抑者的精神世界有着极大的扭曲。首当其冲,身份压抑使得弱势群体产生自卑感,即便成功者也不例外。少数人通过努力改变了身份,但是长期以来的压抑和歧视,使得他们在精神上陷入困境,挫折感和自卑感如影随形。小说中宋长玉在事业成功之后,仍旧无法摆脱原初身份带来的伤害。他和唐丽华的对话道出了他的困扰:
“丽华姐,到今天我才比较了解你,你很高贵,也很高尚,和你相比,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我觉得你把城里人和乡下人绝对化了,乡下人也有不少优秀的,城里人也有渣滓。判断一个人怎么样,不能看他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还是要看这个人本身。”
“你说得对,也许这就是我的局限。”
“你就很优秀嘛!”
“我有时候还是很自卑。”
“为什么?”
“我也说不来,莫明其妙的,突然就自卑起来,还有些伤感。”[1]
身份歧视带来压抑和自卑的同时,也极易使被压抑者产生身份的迷失。大多数人的想法或者优势群体的想法通过“区别对待”渗透到生活细节中,对灵魂本身构成奴役。受到奴役的人渐而失去了自我的辨别能力,向他人的喜好屈服,最终甚至完成了自我的异化。《红煤》中的宋长玉本是权利的被压迫者。他的成长环境遍布了各种权力,在他所见的现实里拥有权力就意味着享有了快乐。在宋长玉成长的不同阶段,村支书、唐洪涛担任着权力的代言人。从唐丽华到明金凤,宋长玉的个人奋斗都是建立在夺取权力上。她们是宋长玉获得权力的砝码。宋长玉将逃离困境与获得权力联系起来,将权力等同于身份,把“身份”的成功转变当成自由、快乐、幸福的唯一出口。他由权利的被压迫者,最后异化成了权欲的崇拜者。
再次,身份歧视带来的另一重负面影响,是切断了各种身份、不同阶层间的良性互动。身份的区别造就了身份认同的焦虑。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指出:“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就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9]强烈的排他性诱使个体寻求身份认同,寻求认同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转变自己的身份。弱势身份要冲破身份的局限,通常免不了做出牺牲。宋长玉奋斗的动力在于想得到主流的身份认同。但是主流群体具有的身份认同切断了与其他身份的良性互动,因此相对于对立阶层的排他性和本身弱势的地位,弱者的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主流之外的人通过单纯的努力和常规方式,往往无法突破身份的阀限。宋长玉的个人奋斗印证了这一点,他的成功建立在对爱情的利用上。他通过爱情获得权力,最后通过利用权力实现身份的转变。小说开篇有一段关于宋长玉的心理描写,他认为光靠努力是不够的,要想留在矿上必须要有关系。宋长玉所指的关系是两种身份间沟通的桥梁。他个人奋斗的两个关键点都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的寻求上。第一次是追求唐丽华,但是唐丽华因为宋长玉农民轮换工的身份拒绝了他;唐丽华的父亲、厂长唐洪涛也因此恶意开除了宋长玉。第二次是追求红梅村村支书的女儿明金凤,宋长玉的崛起建立在村支书女婿的身份上。代表弱势群体的宋长玉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也获得主流群体的接纳,但是在道德上他付出了牺牲。宋长玉是成功突破的极少数,小说中还存在着无法突破身份的典型。无法突破身份的人为了逃避强势身份的排他性,只有选择逃离和躲避,囿限于自己所属的身份群体。这种选择造成积弱的现象。杨新声,是普通工人也是道德的良好化身,但是随着乔集矿的败落,他的生活日益窘迫。又如孔令安,他无法在现实中成为干部,只能在意念中完成梦想,最终陷入疯狂。
此外,身份认同带来的强烈排他性由于切断了不同身份间的良性互动,极易导致暴力的滋生。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底层的“社会报复”。社会报复既包括成功者的,也包括不成功者的复仇。成功者指的是已经实现身份转变的人,宋长玉是他们的代表之一,暴力的因子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在成功之后展开了对当初压迫者的报复,最后竟然越出了压迫者的范围。他举报唐洪涛,利用权力换下宋海林,欺骗唐丽华,欺压矿工,罔顾工人的生命安全,等等。宋长玉个人奋斗的成功是作者对底层人民突围的批判性畅想。但是宋长玉的个人成功无益于群体的发展,他无法终止暴力甚至孕育暴力。那些无法转换身份的人,在特殊情况下则可能通过恶意伤害他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在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城市犯罪主体中,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刑事犯罪的主体部分,大约占到50%以上,有些城市更高达70%左右。”[10]而“外来人口”,几乎就是“农民”的别名。
一般意义上,“突围”被认为是应对困境的策略。困境是常在的,处于身份困境之中的人,也往往身陷“物质”困局中。刘庆邦认为爱是突围的一种途径。他在文本中设定了两位“善”的化身,即杨新声和明金凤。杨新声所代表的是“宽容”“博爱”。明金凤作为出现在宋长玉感情生活里的第二个女人,代表的是对爱情的坚贞和无私。他们在小说中象征着刘庆邦对纯粹的爱的呼唤。宋长玉陷入危机,给予他救赎的是闪耀着美好信仰的人;他人生的转机得益于杨新声的关怀和帮助,以及明金凤的爱情。但是追寻爱的救赎,并不是倡导弱者的苟活哲学。刘庆邦鼓励战斗。刘庆邦深受沈从文和鲁迅的影响,《红煤》既有沈从文对神性的向往,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了鲁迅战斗的姿态。卢军在所著《救赎与超越:中国现当代作家直面苦难精神解读》中指出:“鲁迅把‘反抗’作为个体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把义无反顾地执着于现实斗争作为人生存的内在需要。”[11]在相对的环境下,受优待的身份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和艳羡的对象,拥有它就如同拥有特殊的冠冕,受压抑者则处于主流之外。受到身份压抑的人对于此种现实有着不同的态度,具体可以分为消极接受、消极反抗和积极斗争三种。杨新声是第一类人物的代表。这类人物的特点是安于所见的现实和实际的身份,个人的努力无法突破身份的囿限。孟东辉和孔令安是代表“消极反抗”的人物。这些人受到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的限制,无法做出有效的对抗。例如作为外来务工者,为了弭平差异努力消除外地口音,大多也属于这一类型。刘庆邦鼓励个人战斗,宋长玉的个人奋斗就是最好的证明。宋长玉是积极斗争的代表,他的个人奋斗是个人突破身份阀限的典型文本,单从物性层面而言他是成功的。宋长玉的失败不是因为战斗,而是因为他的暴力基因推动他在精神层面上已经迷失得太远了。
三、结语
刘庆邦经历过农民、矿工、记者等多种社会角色,他对现实的反映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红煤》是其对于社会现实的描绘与思索。他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展现了底层人民的困苦艰辛,更向人物的精神层次掘进,在描写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愤懑的同时,也展现人性的异化与温情,并在此基础上呼吁平等以及人性的复归。小说以宋长玉的个人奋斗为线索,展示了在当年特殊的条件下,煤矿产业以牺牲生命和自然的方式换取高速发展,以致难以避免职业的高风险与低回报,事故的高死亡率与低曝光率等。刘庆邦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苦难批判。他以新的角度对底层人民的命运展开了拓展性的畅想。在指出物性困境的同时,刘庆邦也挖掘其形成的原因,他以“身份”为切入点阐述。单一的弱势身份标签阻隔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个体的精神困境。诚然,发露苦难与困境并不等同于批评的恶意,描写暴力也并非鉴赏暴力和暴力施加给他人的痛苦。刘庆邦认为“爱”是突围的方式之一,人应当保持对美好信仰的追求和尊重,但是个体突围也需要保持战斗的姿态。他否定苟活哲学,鼓励身处于困境的人们积极去进取。实际上,这一切都与“十七年”时期农民的命运和前景形成了遥远的互文及回响。
注释:
①除了典型的将宋长玉与《红与黑》中的于连进行比较以外,《红煤》的研讨也比较多样化。比如,有的研究者从权欲的角度分析了《红煤》,但认为它的表现过于“温情”,批判不太全面;有的研究者认可《红煤》的欲望书写主题,并认为小说强化了人性批判的力度,关注了社会变革对农民生存方式的冲击,等等。参见沈新燕:《从权欲叙述看作品精神内涵——以〈沧浪之水〉、〈城的灯〉、〈红煤〉为例》,《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第2期;王海涛:《在生活的底层掘进——评刘庆邦长篇新作〈红煤〉》,《当代文坛》2006年第4期。另有研究者认为,《红煤》控诉了多数暴虐对底层人民的影响,宋长玉的结局也体现了刘庆邦“对现实的无望的重构和重构的幻灭”。 陈富志:《批判与重构——评刘庆邦的小说〈红煤〉》,《名作欣赏》2007年第12期,等等。
②《中国煤炭行业发展历程》,《国际煤炭网·煤炭市场》(2008-03-12):http://coal.in-en.com/html/coal-1803180389170568.html#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