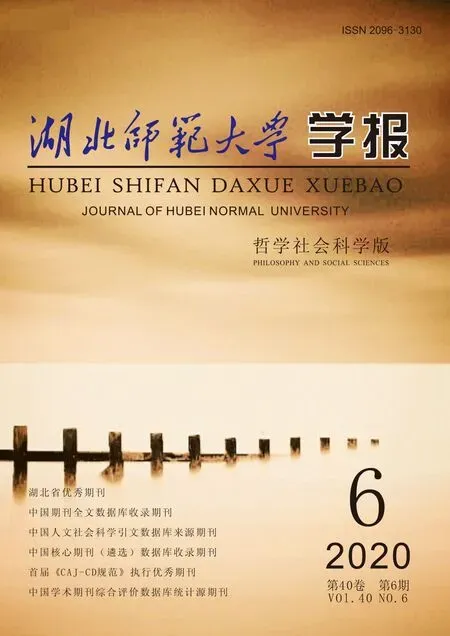法惩、言劝与防疑:明代和奸的治理方式
2020-01-19李庆勇
李庆勇
(济宁学院 社会科学部,山东 济宁 273155)
和奸,俗称通奸,指男女双方在婚姻之外自愿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因为和奸既不合礼,又不合法,历来被视为淫邪之行,受到社会和家庭的禁止。对于和奸现象,明代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家族、家庭,都力图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采取措施,应用惩处、劝喻、防范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消除这一丑陋社会现象。
一、法律的惩处
和奸行为,违背国家法律,于法不容,因此这种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明代,以《大明律》为首的法律,对不同的和奸行为做出了不同的惩罚规定。
古有十恶不赦之说,而和奸就为十恶之一,《大明律》将“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①作为十恶中的内乱,但对和奸者处罚较轻,以杖为主,《大明律》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刁奸,杖一百。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二千里。”②在五刑中属于较轻的刑罚,比强奸也轻很多。如邝学鹏与陆氏和奸,并通陆女,陆女羞愧自缢,虽鹏之罪不胜诛,但和奸止杖,邝仅受到杖枷,《盟水斋存牍》记载:“审得邝学鹏与陆氏有奸,并通其女,为黎寿喜所见,女羞自缢。乃陆氏不恨学鹏之因奸致死,而反迁怒于寿喜主人之黎昌奇。昌奇双瞽,岂行奸之人哉?淫妖母女聚麀,又架词渎宪,罪不胜诛。除陆氏痛饱桁杨外,学鹏杖不尽辜,请加责枷示,以殉国中之行淫者。招详。”③
对于和奸的妇女,其夫可以将其嫁卖,但不许卖给奸夫,《大明律》规定:“奸妇依律断罪,从夫嫁卖。”④“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若嫁卖与奸夫者,奸夫、本夫,各杖八十,妇人离异归宗,财物入官。”⑤无论是否嫁卖,奸妇与奸夫所生子女归奸夫收养,《大明律》规定:“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⑥本夫愿与奸妇继续生活者听其自便,如董金凤妻周氏与马方和奸,周氏仍归董金凤,《折狱新语》记载:“审得董金凤者,乃董元化族弟,而马方则金凤妻周氏之奸夫也。……周氏逐野鸳而厌家鸡,姑重责免拟,仍归董金凤完聚。”⑦
和奸之行,为人不齿,奸妇对本夫无异于奇耻大辱,因此法律将本夫视为受害者,本夫的过激行为往往会得到宽宥,将奸夫、奸妇杀死亦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亲夫在奸所杀死和奸之人无罪,《大明律》规定:“凡妻妾与人通奸,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⑧实际判例也是如此,成化时期,通州县民于奸所杀死奸夫奸妇,初判绞,后改判无罪,《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十二年六月)庚辰,通州民被人奸其妻,即奸所执之,为其妻所护持而逸出,追杀之,并杀其妻。刑部拟以罪人已就拘执,而杀者法当绞,大理寺详审以闻。上曰:‘既奸所获之,当时杀死其勿论。’”⑨张守禄与侯节妻杨氏和奸,侯节于家中将张杨杀死,李渔就认为张杨死有余辜,而侯节有不辱之气,《资政新书初集》记载:“张守禄私通侯节之妻杨氏,一乘其夫之远出,一乘其妻之他往。私申中篝之好,敢为同梦之甘,不虞侯节之夜归也;小家门扉,一推而入,两人犹在睡乡也。侯节怒气填胸,授梃而挞之,登时毕命,保正邻佑之目睹可据。及委官就尸所而验之,下体裸赤,不挂一丝,禽兽之行,死有余憾。侯节编氓而有不可辱之气,本县锡红迎示境内,以寒淫奔之胆。”⑩
和奸行为,一般是在男女自愿基础上发生的,没有强迫的行为。但在习惯看法上,和奸的责任主要在女方身上,女方的罪过要大于男方,这是与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相对应的,尤其是在贞节观念浓厚的明代,讲究女子从一而终,故对于和奸的女子更是罪不容诛,杀之而后又快,好像和奸都是女子一人挑起的,杀奸妇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义举。洪武时期,一少年与有妇之夫私通,因见妇人丈夫关心此妇甚切,遂厌恶此妇无情无义,将之杀死,法司即以杀不义之人赦免少年,《菽园杂记》记载:“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门自炫。有少年眷之,因与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五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复还,以衣覆其妻,拥塞得所而去。少年闻之,既与狎,且问云:‘汝夫爱汝若是乎?’妇言其夫平昔相爱之详。明发别去,复以暮期。及期,少年挟利刃以入,一接后,绝妇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报其夫,归乃摭拾素有讐者一二人讼于官,一人不胜锻炼,辄自诬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见其夫笃爱若是,而此妇忍负之,是以杀之。’法司具状上请。上云:‘能杀不义,此义人也。’遂赦之。”嘉靖时期,山西保德州人崔鉴杀死与父亲和奸的魏氏,也因义免死,《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己卯,山西保德州人崔鉴年十四,以其父私于邻女魏氏,斥逐其母,不胜愤,乃手刃魏氏杀之。有司谳上其狱,法司议鉴以母故陷大戮可悯。上曰:‘鉴幼能激义,其免死,发附近徒工三年。’”从这两个事例看出,在和奸与杀人,违法与卫道之间,法律已屈从道德,情理之义超越刑事犯罪,杀人转化为正义行为,说明为了维护伦理纲常,即使做出违法之事也可以不被法律惩罚。
和奸行为,本无道德可言,理应受到惩罚,本夫将奸夫、奸妇杀死被当作正义行为,而如果奸夫、奸妇将本夫杀死,则错上加错,罪大恶极,往往会处以极刑,且奸妇的刑罚重于奸夫,奸夫处斩,奸妇凌迟,《大明律》规定:“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对奸妇的惩罚重于奸夫,说明在和奸行为中,将主要责任归于女方。现实案例所判与法律无二,如湖南丘氏与叔袁应节和奸,被夫袁应春撞获,将夫杀死,丘氏凌迟,袁应节斩,与《大明律》规定完全吻合,《湖湘谳略》记载:“会审得袁应节之奸嫂丘氏,不第岳丈王国义之投词足为确证,即亲兄袁应春于奸所撞获,拉齿伤额,尤为左騐矣。丘氏以淫孤,恨夫阻,乘其醉,而手刃之,且假盗妆举火焚屋,计图架祸卸罪。此尤物中之最毒,而狡者尚可令之偷生于人间世耶。应节,杀兄虽未与谋,而埋刃投词尽属巧节,况兄之凶终谁生厉阶?磔氏,斩节,允当其辜,监决。”奸夫杀死亲夫,奸妇即使不知情,也会处以死刑,如湖南孙氏与刘古楫和奸,刘古楫杀死孙氏之夫胡允节,孙氏虽不知情,仍处以绞刑,《湖湘谳略》记载:“会审得刘古楫恋奸表弟胡允节之妻孙氏,而卖弃发妻,谋溺允节,真孤淫成性,狼毒马心者耶。允节之尸虽葬鱼腹,而楫之父帖,见存氏手,即氏留帖待证,杀夫似不知情,然而起由奸夫,死何异自杀。斩古楫而绞孙氏,各不为枉,监候详决。”
纵容别人和奸者,也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如果丈夫纵容妻妾与人和奸,丈夫与奸夫、奸妇同等处罚,《大明律》规定:“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问刑条例》规定:“凡买良家子女作妾并义女等项名目,纵容抑勒与人通奸者,本夫、义父同罪,于本家门首,枷号一个月发落。”如果官吏纵勒妻妾与人和奸,则削职为民,《问刑条例》规定:“军职纵容抑勒女及妻妾并子孙之妇妾与人通奸,及奸内外有服亲属,典雇妻女与人,并奸同僚妻女,但系败伦伤化者,问发为民。”《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十一月乙亥)山西按察司副使章绘奏:‘军官多纵勒妻妾与人通奸,丧廉耻,坏风俗,宜例以败伦伤化削职为民。’从之。”
对于不同的和奸主体、和奸行为,法律也有轻重的区别。针对发生在家庭内的和奸行为,会根据亲疏远近做出不同的判决,关系越近,判决越重。如和奸亲男之妇就重于和奸义男之妇,《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三年六月己未)刑部尚书金濂奏:‘奸义男妇者,洪武、永乐以来有论依奸子孙之妇应斩,有论依奸妻前夫之女应徒者,情犯相同,议拟不一,伏乞圣断,永为遵守。’三法司奉诏议:‘亲男与义男情有亲疏,若将奸义男妇与奸亲男妇同罪,恐亲疏之情不分。今后有犯前罪者,宜比奸妻前夫之女徒罪科断。’上曰:‘通奸者准拟徒,其男与妇仍断还本宗,强奸者处斩。’”如与义女和奸者,刑部尚书王惠迪建议重罚,《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庚戌,刑部尚书王惠迪言:‘凡民间乞养义女,虽非己生,然皆自幼抚养,同居而食,已有尊卑之分。若帷薄不修,有伤风化,宜比同宗无服之亲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其女归宗。请著为令。’从之。”
对于与未成年人和奸者,如奸淫幼女,则以强奸论,《大明律》规定:“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与官员孀妇和奸者加重惩罚,如陈葆源和奸官员孀妇并侵占其住宅被革职杖枷,《盟水斋存牍》记载:“审得陈葆源一贱吏耳,辄敢宣淫相宅,奸其孀妇,奸其笄女,急扑杀此奴犹不足快通国之愤。乃古槐深巷,谁无门第,凄凉之感,而并为此奴踞而有之,凡有人心能不投袂而起,准照原价取赎幸矣。复以修费加断一百二十两,岂法之平乎?追给原卖主,再拟革后之杖,并请加责枷示,以儆淫吏之为不法于国中者。覆详。军门批:陈葆源以贱胥污辱相裔之妇,踞其第而迁其主,法当重处以泄士绅之愤。第既经徒革,姑重责二十五板,枷号二个月,依拟赎发。”
和奸之人,若受外界迷惑而发生和奸行为,可减轻处罚,《大明律》规定:“若媒合容止通奸者,各减犯人罪一等。私和奸事者,减二等。”如果妇女受丈夫、家长逼迫而与人和奸,可免于处罚,《大明律》规定:“抑勒妻妾及乞养女与人通奸者,本夫、义父,各杖一百,奸夫杖八十,妇女不坐,并离异归宗。”
对于和奸的老年人,亦不重惩,如刘茂所就因年已垂尽,外发开恩,准其纳赎,《盟水斋存牍》记载:“若夫强奸族侄女刘妙娘,通奸张仲达妻蔡氏,强奸张孔明妻杜氏,奸情暧昧,无可深求。况本犯年已垂尽,即有之亦成往事,不欲复点纸笔,以污宪案也。总之,本犯雄据一乡,目无三尺,僻壤自恣,夜郎不知有汉也。以诈骗城旦之足以示惩,念奄奄一息,准其纳赎,亦法外之仁耳,具招解详,岭南兵巡道转详。察院蒙批:刘茂所武断自雄,跳局恣逞,徒有何辞?依拟追赎发落,库收缴。”
对于和奸行为,明代法律态度上是不能容忍、绝不姑息的,并列为十恶之一,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赦的。但作为你情我愿的和奸,法律惩罚亦相对宽松,多以杖枷为主。如果因奸发生命案,则将法理倾向本夫一边,本夫杀死奸夫、奸妇无罪,奸夫、奸妇杀死本夫则处死刑。同时针对不同的和奸主体、和奸行为做出轻重不同的判处,近亲和奸、奸淫幼女者重处,被逼和奸、长者和奸者轻罚,体现出法网无情和法外施恩的结合。法律的这些规定,编织了一张大网,针对不同的情况,对犯奸者加以惩处。
二、言语的劝喻
在重视道德的传统社会,和奸与道德要求背道而驰,与道德礼仪的精神大相径庭,有悖道德,有伤风化,因此在一片社会指责声中,有人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教,劝喻和奸者远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宿命论宣扬天理循环,因果报应,是古代社会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式。明代也将宿命论作为警戒不良行为的工具,宣扬和奸有违世俗道德,自然也就违背天理,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必然遭到天命的惩罚,使其心存敬畏,收敛自己的违天行为。凌濛初将和奸行为归咎于世人好色,并告诫世人要戒淫戒色,不可淫人妻女,如此方可阴德厚报,惠及子孙,否则就会遭受天谴,减算夺禄,以因果报应警戒好色之人不要贪淫纵欲,污秽女子,他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说:“说着人生世上,色字最为要紧。随你英雄豪杰,杀人不眨眼的铁汉子,见了油头粉面,一个袋血的皮囊,就弄软了三分。假如楚霸王、汉高祖分争天下,何等英雄!一个临死不忘虞姬,一个酒后不忍威夫人,仍旧做出许多缠绵景状出来,何况以下之人?风流少年,有情有趣的,牵着个色字,怎得不荡了三魂,走了七魄?却是这一件事,关着阴德极重,那不肯淫人妻女、保全人家节操的人,阴受厚报,有发了高魁的,有享了大禄的,有生了贵子的,往往见于史传,自不消说。至于贪淫纵欲,使心用腹污秽人家女眷,没有一个不减算夺禄,或是妻女见报,阴中再不饶过的。”
明代着力宣扬和奸的恶行,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奸不会有善果,和奸者想结为夫妻以求长久者,也不会得到上天的成全。凌濛初认为,夫妻姻缘,前生所定,在世之人,不可抗逆,而偷情和奸,背天逆理,即使千方图谋,亦会无果而终,不但玷辱了家风,还会危机自身性命,以和奸之人前世无缘今世也不会有好结果告诫世人远离奸情,他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说:“话说世间齐眉结发,多是三生分定。尽有那挥金霍玉,百计千方图谋成就的,到底却捉个空。有那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似司马相如的,分定时,不要说寻媒下聘与那见面交谈,便是殊俗异类,素昧平生,意想所不到的,却得成了配偶。自古道:姻缘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会里来。见得此一事,非同小可。只看从古至今,有那昆仑奴、黄衫客、许虞候,那一般惊天动地的好汉,也只为从险阻艰难中,成全了几对儿夫妇,直教万古流传。奈何平人见个美貌女子,便待偷鸡吊狗,滚热了,又妄想永远做夫妻。奇奇怪怪,用尽机谋,讨得些寡便宜,枉玷辱人家门风。直到弄将出来,十个九个死无葬身之地。”话虽如此,但世间毕竟有和奸之人修成正果、结为夫妻的,凌濛初将此归结为和奸双方的前世缘分,他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说:“说话的,依你如此说,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便个个死于非命?看官听说,你却不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说,就是些闲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缘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缘凑着,自然配合,奸骗的保身没事,前缘偿了,便可收心。为此也有这一辈,自与那痴迷不转头、送了性命的不同。”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非常重视夫妻关系的稳定性,二者结合在一块,就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不离不弃,相伴到老,夫妻恩爱一生是他们理想的婚姻结局。明代人们也是非常重视夫妻间的互相忠诚,以此架构稳固的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的家庭秩序。夫妻忠诚,要求双方不能相互抛弃,男子富贵不忘糟糠之妻,女子不离不弃危难之夫,切不可做负心之人。凌濛初就以负心不得好报来提倡夫妻终身相倚,不做对不起对方之事,这其中当然包括和奸之行,他在《二刻拍案惊奇》中说:“话说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负心的事,所以冥中独重其罚,剑侠专诛其人。那负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间。盖朋友内忘恩负义,拼得绝交了他,便无别话。惟有夫妻是终身相倚的,一有负心,一生怨恨,不是当耍可以了帐的事。古来生死冤家,一还一报的,独有此项极多。”
和奸行为,多是激于一时之情,激情过后会隐藏很多不稳定因素,导致悔不当初的遗憾。陆人龙认为,和奸之时,男女只为一时之欢,而将其他因素抛之脑后,偷情之后,这些被忽视的因素重新被审视,不但加速偷情双方感情的瓦解,而且还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伤害,导致既不容奸夫(妇),又不容家庭的双害局面,他在《型世言》中说:“人只试想一想,一个女子,我与他苟合,这时你爱色,我爱才,惟恐不得上手,还有甚么话说!只是后边想起当初鼠窃狗偷的,是何光景?又或夫妇稍有衅隙,道这妇人当日曾与我私情,莫不今日又有外心么?至于两下虽然成就,却撞了一个事变难料,不复做得夫妇,你绊我牵,何以为情?又或事觉,为人嘲笑,致那妇人见薄于舅姑,见恶于夫婿,我又怎么为情?故大英雄见得定,识得破,不偷一时之欢娱,坏自己与他的行止。”陆人龙的说教,旨在让和奸之人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认清利害,考虑周全,不要让偷情心理蒙蔽理智,并认为和奸不但不会恩爱,还会给双方带来无尽的猜嫌,以致相互憎恶而背道扬驰,以此告诫世间男女远离此行为,最后以此行为导致身败名裂、无家可归的严重后果警告和奸男女莫越雷池。陆人龙之言考虑比较周到,分析相当有理,对和奸之人无疑是当头棒喝,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和奸,关乎一个家庭的荣誉。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是社会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家庭的荣誉关系家族的声望,若有和奸事情的发生,这个家庭连系家族、宗族在当地的地位无疑是下降的,因此,无论是小户人家,还是名门大户,无不对这有损名声的事情避而远之,一些家庭通过家训的方式,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警劝、严惩和奸者。庞尚鹏在家训中警示家庭成员远离淫欲,《庞氏家训》说:“淫纵伤生,当刻骨痛戒。”曹端在家训中对犯奸的妇女或劝令自死,或赶出家门,《家规辑略》规定:“女子有作非为犯淫狎者,与之刀绳,闭于牛驴房,听其自死。其母不容者,出之,其父不容者,陈于官而放绝之,仍告于祠堂,于宗图上削其名,死生不许入祠堂,既放而悔改,容死其女者复之。”其家庭对于发生的和奸行为,除了尽力遮掩以外,还要对当事人严加处罚,以表明自己对和奸之事的不姑息,与和奸之人划清界限。
为了遏止和奸行为,明代注重劝喻的方式,或以小说说理,或以家训警戒,贯穿着因果报应,体现着罪不容诛,表明着绝不姑息,以此让和奸男女心生畏惧,心存敬畏,非礼勿践,弃淫卫礼,以期实现悬崖勒马、遵礼守德的效果。
三、严防男女之疑
和奸是基于双方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而如果双方素不相识,则和奸就无从发生,因此为了防止男淫女邪的事情发生,避免男女双方的交往就成为古代社会防和奸的基础手段。明代社会千方百计地阻止男女交往,避免女子与家庭以外的男性接触,此即严防男女之疑之说。
明代社会将严防男女之疑看作是防止男女奸情的有效手段。李渔认为限制男女交往是未雨绸缪,男女不相近才会阻塞逾礼犯分,他在《十二楼》中说:“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觉得此愿不了,就活上几千岁然后飞升,究竟是个鳏寡神仙。此心一遂,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也还是个风流鬼魅。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说还有什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所以惩奸遏欲之事,定要行在未发之先。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只是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吕得胜也将男女避嫌当作防人言语的必要手段,他在《女小儿语》中说:“古分内外,礼别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语。”
严防男女之疑强调女子守身如玉,要求女子重视名节,继续向女子灌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闺范·女子之道》中说:“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疑,然后可以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何者?丈夫事业在六合,苟非渎伦,小节尤足自赎,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暇,万善不能相掩。”严防男女之疑强调女子从一而终,要求女子对丈夫矢志不渝,继续向女子灌输“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女范捷录·贞烈篇》认为:“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慷慨捐生谓之烈。”
严防男女之疑主要是隔绝男女的交往。叶春及指出男女有别,男不应入内室,女不应出外门,应该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石洞集》记载:“礼始于闺门,男女必有别,妻妾必有序,宫室必辨外内。男子毋得昼寝于内,妇女毋得踰阈行市。虽奴牌亦必动遵礼度,其有贞节,众共歌扬,以为闺门之助,闻于有司。”明成祖徐皇后除要求男女不言语、不对目外,还要求男女走不同道,食不同桌,《内训·女教篇》中说:“男女当远,嫌疑早避,不亲授受,不相游戏,食不共案,眠不共榻,衣不共架,栉不共匣。”
古代社会,讲究男女有别,女子抛头露面,则为男女接触提供了条件,而不让男女出门是不可能的,因此防奸的重点就落在妇女身上,而防范的主要方式则是将妇女限制在家庭里面,不让妇女出门,如《明史》说:“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许相卿也要求女子不应该抛头露面,尤其禁止妇女游山拜寺,《许云村贻谋》指出:“女妇日守闺阃,躬习纺织,至老勿逾内门,下及侍女,亦同约束。如有恣性,越礼游山上坟,赛神烧香,炫露体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孙必泣谏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明太祖就以牛麟之妻抛头露面、陪人吃酒而与人私通为例,说明女子抛头露面多招致淫乱,他在《大诰武臣》中说:“男子妇人,必要有分别。妇人家专一在里面,不可出外来,若露头露脸出外来呵,必然招惹淫乱的事。而今有等愚夫愚妇,好生不守道理,把风俗坏了。便如曲靖卫指挥牛麟,他在云南讨一个妇人做妾,每日与同僚官吃酒,便着这妇人出来同座吃酒,因此上被指挥柳英诱引私通,教本妇将毒药毒死牛麟。有这等无知的,妇人家如何着他与男子汉吃酒,吃一会酒了,自家的性命也被人害了。若是有分别呵,那里有这等事。指挥柳英与那妇人,都将杀了。今后敢再有这等的,拿住一般罪他。”
严防男女之疑的重点放在妇女与外界的交往上,甚至兄弟来见也要一言一动必合乎礼,《内训·女教篇》中说:“兄弟来谒,见不逾阈,有故而出,必掩其面。”尤为限制妇女与社会闲杂人等的交往,明代突出表现在对三姑六婆的憎恶,将三姑六婆视为淫祸之源,禁止其进入内室,吕得胜说:“三婆二妇,休教入门,倡扬是非,惑乱人心。”姚舜牧说:“女尼、卖婆等尤宜痛绝。盖此辈一出入,未有肯空手者,而且有更不可言者。”黄标认为:“夫六婆所欲得者钱财耳,得其钱财,则门内之隐皆可宣扬于外,得其钱财,则户外之情又何难巧传于内乎?甚至内外相通,逾墙钻穴,在所不免。由此观之,任用六婆是犹开门而招淫也。”妇女不得不与外界联系时,或通过儿童传话,陈龙正指出:“门路出入有定规,凡近内门户,仅容十二三岁儿童传语,出入过此,即当禁足。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或云板木鱼传声,庞尚鹏说:“僮仆十四岁以上,不许入后厅。凡内外传呼,击云板或木鱼。”
严防男女之疑,在男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般是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限制其行为。曹端家庭规定:“吾家男女,七岁以上,不同席,不共食,以严其别。”孙植家庭规定:“男十岁勿内宿,女七岁勿出外。”方孝孺指出:“树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时;七年异男女,八岁分尊卑。”许相卿说:“男十岁,勿内宿;女七岁,勿外出。”庞尚鹏说:“童子年五岁诵《训蒙歌》,不许纵容骄惰;女子年六岁诵《女诫》,不许出闺门。若常啖以果饼恣其欲,娱以戏谑荡其性,长而凶狠,皆从此始。当早禁而预防之。”《温氏母训》说:“贫家无门禁,然童女倚帘窥幕,邻儿穿房入闼,各以幼小不禁,此家教不可为训处。”姚舜牧说:“家人内外,大小防闲,不可不严。凡女奴男仆,十年以上,不可纵放其出入。”
严防男女之疑,还要避免公与媳、嫂与叔的过多的接触,警惕逾礼乱伦的发生。曹端家庭规定:“今人有翁伯之尊,于新妇之手自接小儿,有乖礼体,切宜深戒。今人所以坏男女之礼者,莫甚于嫂叔及大小姑之夫,吾家男女于此尤宜谨之。”
为防奸情发生,明代在限制男女交往上可谓是下足了功夫,既强调防疑的重要性,又制定出条条防疑的措施,以至限制妇女除丈夫之外的一切异性交往活动,甚至在男女儿童时期就强加防范,可以说为防和奸无所不施,以求家门清肃,家无丑行。
由上可见,明代和奸治理措施比较严密,采取惩处、劝喻、防范的手段,从国家、社会、家庭编制出一张治理大网。这些措施互为表里,彼此呼应,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来达到消除奸情的目的,以求人人守礼,家门谨严,社会风气淳正。这些措施出发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些措施也具有合理性,能够起到震淫慑奸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措施并不恰当,采取捕风捉影、竭泽而渔的方式,反而过犹不及。总体来看,明代治理和奸的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注释:
①(明)刘惟谦:《大明律》卷一《名例律·十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明)刘惟谦:《大明律》卷二十五《刑律·犯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③(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目录二刻《谳略·奸淫邝学鹏等一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7页。
④(明)刘惟谦:《大明律》卷十九《刑律·人命·杀死奸夫》,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⑤(明)刘惟谦:《大明律》卷二十五《刑律·犯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⑥(明)刘惟谦:《大明律》卷二十五《刑律·犯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⑦(明)李清:《折狱新语》卷五《淫奸·不法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4-345页。
⑧(明)刘惟谦:《大明律》卷十九《刑律·人命·杀死奸夫》,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⑨(明)刘吉:《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803-2804页。
⑩(明)李渔:《资政新书初集》卷十一《判语部·奸情六》,载《李渔全集》第十卷。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