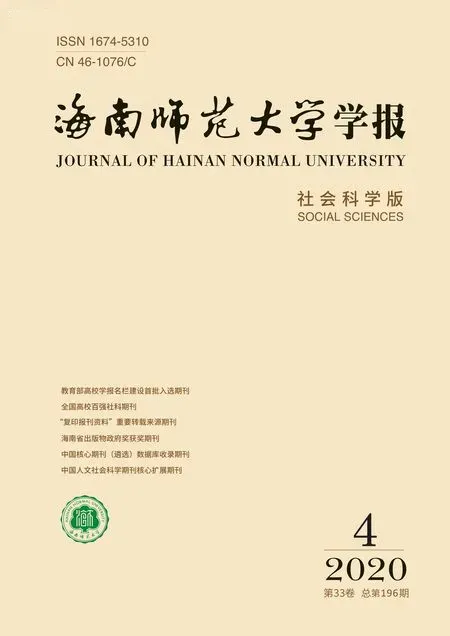论《地下铁道》中的奴隶制与人性书写
2020-01-19李宇笛
李宇笛
(华中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科尔森· 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小说《地下铁道》(TheUndergroundRailroad)以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东南部为背景,讲述了身处佐治亚州种植园的女黑奴科拉受尽奴隶主和其他奴隶的压迫和凌辱,在废奴人士的帮助下,搭乘秘密的“地下铁路”途经了五个州,一路向北的逃亡故事。小说采用非传统的历史讲述方式,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位移和跳跃,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南北战争前夕不同州的不同社会面貌,也体现出身处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不同人性:有为谋取私利而买卖、虐待,并试图通过“非人化”手段对奴隶们实施永久控制的奴隶主;有为报复和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断抓捕奴隶的猎奴者;有企图通过绝育以达到对黑人人口控制的伪善白人;有为生存而不得不服从来自奴隶主和其他奴隶的压迫和凌辱的奴隶;还有身处奴隶制社会中变得麻木而盲从的大部分白人。通过对人性的剖析,小说不仅对残酷、血腥的奴隶制进行了批判,还揭示了奴隶制与人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奴隶制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源于人性的弱点,同时,奴隶制又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小说自2016年出版以来便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有许多学者从历史或政治学角度对小说重现的奴隶制历史进行分析,通过美国黑人在困境中对文化身份和种族意识的建立历程,探索小说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义;还有学者从现代叙事学角度入手,分析小说的现代写作手法以及还原历史的书写方式。但纵观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对小说表现的人性主题研究还不多,尤其是对奴隶制与人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而这正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奴隶制的根源入手,分析人性对奴隶制的推动作用,再通过研究奴隶制对人与社会的影响,揭示小说体现的人性意识。奴隶制废除已近160年,《地下铁道》从人性的角度再次对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的源动力进行分析,研究人性对个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在反思奴隶制的同时,对人性的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也对人性的意义和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人性:奴隶制的根源与动力
小说《地下铁道》中的奴隶制书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至暗时期,是对整个黑人种族的沉重打击,也是对美国社会的讽刺和教训。作品通过奴隶制对人性进行深刻观察,实际上是对永恒的人性问题的思考。从根源上看,奴隶制是建立在负面人性之上的,它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人性中的利己私欲、控制占有欲、生存欲和“平庸之恶”等非理性因素。
小说首先揭露出奴隶制依靠的是强烈的利己私欲,奴隶贩子和奴隶主们为了谋取最大利益,对黑人奴隶进行毫无人性的买卖、压榨和凌辱。小说主人公科拉的外婆被奴隶主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经过多次转卖,最后来到佐治亚州,一生受困于此,终日起早贪黑,白天采摘棉花,晚上像牲口一样和奴隶们一起睡在大木屋里,还常常受到主人和其他奴隶的欺辱。科拉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奴隶主的残暴而出逃,不幸死于沼泽地中。科拉小小年纪就饱受奴隶主和监工的鞭打和凌辱,亲眼目睹奴隶主对女奴身体上的凌辱和逃亡后被抓捕回来的奴隶被残暴处死的场面,以及仅仅因为不小心撞洒了奴隶主特伦斯的一滴酒而遭到暴打的小奴隶。奴隶主特伦斯不断为提高棉花产量而进行改革,将奴隶们生产的速度和效率标准提高,达不到标准则要受到残酷的惩罚。同时,特伦斯还企图控制奴隶的婚姻以确保生育出强壮的奴隶更新换代,并向外出务工的奴隶征收新税。“他要榨干每一块钱的潜力。当黑色的血就是金钱,这个精明的商人知道怎样把血管切开。”(1)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New York: Random House LLC, 2016, p23.由此可见,奴隶是奴隶贩子和南方种植园主手中最有价值的财产,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压榨奴隶们的所有价值,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
其次,小说中奴隶主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使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将奴隶“非人化”,以达到完全占有和享用这些财产的目的。例如,为达到从思想和行为上完全控制和占有他们的目的,奴隶主们会把奴隶原来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姓,以体现自己的权威;或像对待牲畜一样让奴隶们站好队挨个儿检查他们的身体、牙齿、劳动能力。还有的奴隶主为了完全从精神上控制,切断奴隶们学习一切文化知识的可能,见到有奴隶看一眼有文字的通告,便刺瞎他的双眼,对待逃跑后被抓回的奴隶,更是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当众惩罚和杀害,以警告其他想要逃跑的奴隶。不仅如此,即使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拥有了当地政府承认的自由身份,仍然时刻受到白人的监控,成为被白人偷偷利用的工具。当更换了新身份的科拉以为自己已经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的时候,却发现那些对自己看似友善的白人只不过是在利用黑人的身体做各种病毒实验而已。他们再三建议她绝育,甚至开始威胁她的人身安全时,她才终于意识到,白人是想通过绝育的手段实现对黑人人口数量的控制。至此,奴隶主对奴隶实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昭然若揭,控制和占有也使奴隶逐渐丧失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而被迫沦为奴隶主的财产。
在小说中,这种控制与占有欲还表现在统治阶级对普通白人的思想控制上。科拉逃到北卡罗来纳州之后发现,除了路上挂满的被吊死的黑奴的尸体,这里的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黑人。每周五晚上市民们都会聚集在广场上,听参议员也是奴隶主的贾米森的演讲。贾米森煽动群众,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号召群众为了州的正义与自由的建设,为了不受北方的干涉和所谓黑人的污染而驱逐或屠杀全部黑人。在他的鼓动下,在场群众群情激昂地处死被抓到的黑奴,为猎奴队员鼓掌欢呼,积极举报废奴分子,孩子们甚至告发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实际上,贾米森只是为了维护自己阶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以不断向普通白人洗脑或用刑罚恐吓废奴人士。可见,奴隶主的控制欲不仅体现在对奴隶的绝对占有和思想控制上,也体现在对同为白人的思想控制上,以便制造奴隶制得以繁衍的社会文化场所。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洗脑,奴隶制才得以在美国南方诸州长期延续和发展。
除了利己私欲和控制占有欲之外,小说中描绘的基本的生存欲也是奴隶制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小说中提到,在南方的许多州,黑人数量已经超过了白人,也发生过小规模的起义,但都被镇压下来。大部分种植园内的黑奴们敢怒不敢言,受尽奴隶主和监工的百般凌辱却不敢有反抗和逃跑的念头,多是由于深感成功希望渺茫,并且随着1850年《逃亡奴隶法》实施,奴隶主有权采取一切手段追捕逃亡奴隶,一旦被抓回则是死路一条。所以奴隶都梦想着逃跑,但出于求生欲,大部分奴隶只能像科拉的祖母一样,被压榨完最后一滴血汗,最后死在种植园里。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同一个种植园的奴隶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奴隶主和监工争宠或侵占别人的财产。母亲去世以后,科拉就马上被母亲的宿敌阿娃排挤到最底层奴隶居住的“伶仃屋”,仅有的两平米菜园也遭到布莱克的觑觎,科拉不得不以死抵抗。不仅如此,在南方各州,一旦发现白人窝藏或帮助逃亡的奴隶,便不仅会受到鞭刑和罚款,甚至有丧命的风险。因此,在北卡埃塞尔得知丈夫将科拉带回家并藏在阁楼,一直表现得非常冷漠和厌烦。“她的确秉持着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比人高尚的思想惹来杀身之祸。”(2)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oad, p195.埃塞尔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白人,虽并不真正歧视或厌恶黑人,甚至从道德上反对奴隶制,同情奴隶的命运,但为求在社会中生存下去,维持体面的生活,不得不保持冷漠态度,遵守法律。由此可见,生存欲既是许多黑人奴隶被迫被奴役,而或惨死在种植园内,而或苟且偷生、劳作终生的原因之一,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环境下白人不得已而做出的生存选择,两方面因素的交织成为了奴隶制度得到延续的重要原因。
小说还揭示了在奴隶制度下产生的“平庸之恶”对其本身的巩固和推波助澜作用。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在讨论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时,她给这个术语下了一个定义——“漫不经心的轻举妄动,或无可救药的混乱,或是自鸣得意地重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和毫无内容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当一个人因没有思辨能力、判断能力而盲目或麻木地服从权威时即会产生“平庸之恶”。在小说中科拉所途经的几个州如南卡、北卡、田纳西等地,大部分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奴隶制度的盲从和集体无意识即体现了这种“平庸之恶”。在北卡罗来纳州,公园上演的戏剧讲述的是奴隶后悔逃亡,回到种植园,祈求仁慈的奴隶主原谅的故事,面对如此虚假的剧情,观看的市民们却信以为真,大声喝彩;年纪轻轻的男孩以加入抓捕黑奴的巡查队为荣,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群争相成为志愿者,抢着在绞死女黑奴的绞刑架边充当帮手。在权威制度的统治下,他们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残暴无知。同样,在特伦斯的种植园中,奴隶之间的关系也充满“平庸之恶”,相互的压迫和歧视无处不在。种植园仿佛一个微缩的人类社会,充满了关系政治,奴隶之间不仅缺少同情和怜悯,反而为争宠而相互排挤和告密。从奴隶主那里受到剥削和凌辱之后,他们不仅没有选择反抗,反而转向身边更弱小的同胞进行发泄和报复。在面对威胁和欺凌的时候,也没有人会伸出援手。科拉11岁就被赶到了“伶仃屋”——整个种植园最底层的奴隶住的地方,之后备受艾娃等人的欺负,14岁又被其他黑奴强奸。她感叹道:“白人会把你吃掉,但有时候黑人同胞也同样会把你吃掉。”(4)Colson Whitehead,The Underground Raiload, p54.综上可见,在奴隶制度下,这种“平庸之恶”将人性的邪恶和破坏能力充分暴露出来,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下罪恶的帮凶,也都是其受害者。相对于赤裸裸的物欲,控制欲和占有欲等,“平庸之恶”所凸显的人性中的盲从、麻木和残酷具有更为广泛、持久的特点,更将奴隶制的罪恶推向了极致。
综上所述,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人性负面因素之上,它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人性中的非理性。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根源在于对理性认识不深和运用不够。他把负面的人性或人性之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是人的心灵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方面的软弱,或者说人的本性的脆弱;第二种是把非道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杂起来,即不纯正……第三种是人心的恶劣或者堕落,即采纳恶的准则……”(5)李秋零:《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译本导言》,[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xix页。由此看来,《地下铁道》对奴隶制问题的重现实际上是对永恒的人性问题的思考。正是人性中的负面或非理性的因素诸如私欲、控制与占有欲、求生欲、“平庸之恶”等导致了奴隶制的生生不息,在美国废除奴隶制的道路上才会出现反复和困难。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的问题超越了肤色或种族,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也就破解了关于种族主义是源自和根植于白人的神话。
二、人性的毁灭力量:奴隶制的负面影响
《地下铁道》中有这样一幕:监工康奈利因为一个奴隶在看有字的东西,就把他的两只眼睛挖了出来,让所有有心学习白人语言的奴隶们都产生了永恒的恐惧。奴隶主为实现对奴隶的绝对控制,维持自己的地位,往往会从精神上恐吓他们,并避免他们接触一切文化知识和所有可能影响或导致他们反抗和逃跑的因素。谭惠娟教授认为:“白人在剥夺黑人人性时,并非采用一种直笔的方式,而是先从语言上将黑人刻板化。当黑人被称chattel或pickaninny时,这些白纸黑字记载着他们从哪里来,正在遭遇什么,就是他们自身的隐喻。那就是,黑人作为人的身份和价值在白人眼里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6)谭惠娟:《论拉尔夫·埃利森对黑人人性的剖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科拉的外婆被黑人同胞抓住卖给白人贩奴者,也曾试图自杀,后经多次估价和转卖,终于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一件商品,命运已没有改变的可能,彻底放弃了逃跑的念头。住在伶仃屋的女人们,受到来自奴隶主和其他奴隶们的双重压迫和欺辱,强奸和殴打使她们神志不清,生下来的孩子发育不良或死掉,她们在黑夜里一遍又一遍呼喊死去孩子的名字。在这样的摧残下,奴隶们受到的精神创伤是恒久的,他们长大后很难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无法形成正常的家庭观念和道德观。放弃了逃跑和反抗念头的奴隶们,白天面对的是身体上的惩罚,而夜晚等待他们的则是无尽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暗自哭泣,又因噩梦和悲惨的记忆而发出尖叫。即使是逃离了种植园的科拉,在每一次面对好心的白人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胆怯和恐惧。可见,奴隶制是对黑人奴隶身体和精神上的直接摧残,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行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剥夺。奴隶们已经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社会意义上的“非人”,毫无自由和权利,更没有历史或未来可言。
小说还揭示了奴隶制下白人自身人性的异化。小说中奴隶主终日想着如何压榨奴隶的最后一滴血汗,在暴利的获取中过着糜烂和空虚的生活,不仅丧失了同情和怜悯之心,甚至以羞辱和惩罚奴隶为乐。奴隶迈克尔的主人对鹦鹉着迷,于是决定训练他像鹦鹉学舌一样背诵《独立宣言》,每当有宾客来访的时候,便让他当场背诵。迈克尔对内容一概不懂,只是被当做娱乐表演的工具,当主人腻烦了他的表演,便将他卖掉。奴隶主伦斯特为了惩戒逃跑后被抓回的奴隶安东尼,特意请来诸多种植园的奴隶主和记者等,一边大摆宴席,一边将安东尼身上涂满柏油,当场在刑具上慢慢烤死,为他流泪的奴隶还要遭到鞭打。在场所有的白人却都觥筹交错,尽情享用着大餐,竟然丝毫没有被这场面败坏胃口。他们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已被种族极权主义完全抹杀,黑人奴隶在他们的眼中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根本属性,只是供白人压榨和消遣的工具而已。庞好农教授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其实是一种种族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要颠覆黑奴的人性。“其实,在白人颠覆黑奴人性的过程中自己的人性也发生了异化,种族性成了虚无的存在。”(7)庞好农:《从〈地下铁道〉探析怀特黑德笔下恶的内核与演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作为奴隶主的白人虽然在物欲和控制欲等方面得到了满足,但在心理和精神上却更加空虚,只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谋取更多的利益,丝毫没有人性中最基本的正义和道德感。同时,白人在人性上的异化也加剧了他们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造成黑人作为人之属性被扼杀,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人性也加速异化。
当个体的人发生人性异化时,就会导致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堕落。《地下铁道》里描写的美国南方奴隶制社会,展现了在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和道德原则,同时也揭示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是如何在强大的系统力量和情境力量之下堕落的。许多普通人出于生存需要对统治阶级服从,在集体无意识的麻痹下,摒弃了个人的道德感、正义和良心,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堕落的一部分。比如,医学院的学生史蒂文斯,为换取学费减免和工作机会,不得不上夜班,同时兼任为解剖课盗尸的任务。但病态的悖论一直困扰着他,因为“他的专业是延长生命,现在却暗地里盼着多些死者。”(8)Colson Whitehead,The Underground Railrod,p137.但出于医学院的压力,他不得不到处寻找盗墓者、采取骗尸表演,甚至直接偷尸体。他接触了许多因为生活沦落而不得不以盗墓偷尸为生的白人,没有受过教育,也毫无社会地位,却仍旧把“黑鬼”的蔑称挂在嘴边。讽刺的是,整天念叨黑人臭不可闻、智力低下的医学生们,却在拿起解剖刀的同时,让黑人以死晋级人类,与白人平等,对人类医学做出的贡献甚至超过白人。还有以捕奴者里奇韦为首的巡逻队,原本是一群到处杀人放火、打砸抢夺、粗鲁无礼的罪犯,却在当时的美国成为了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和奴隶主们的得力助手,甚至受到群众的尊敬,于是更激发出他们人性中最残暴的一面。里奇韦认为猎奴事业是对良好社会秩序的维护,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势在必行,“这就是伟大精神,它如神圣的线轴般连接着人类的努力——如果你能守住它,它就是你的。你的财产、奴隶、土地。”(9)Colson Whitehead,The Underground Railrod,p79.在对这种精神的盲目理解下,他对自己的猎奴事业充满热情,随着抓捕的奴隶数量的增加,荣誉和名声也越来越大。他的成功也让越来越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从而加入迫害和追捕黑奴的队伍中。可见,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个人的人性塑造是密不可分的,个人的异化可能只会对其周围环境和他人产生一定副作用,但当绝大部分个体都发生异化,摈弃道德良心,则会引发严重后果,致使整个社会失去理性的制约,逐渐堕落和退化。
奴隶制对美国非裔种族身份、历史的构建和发展,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强大的破坏作用,其影响不仅持久,而且超越了时代。《地下铁道》中,某些白人为了为自己奴役黑人的行为开脱,故意将黑人形象丑化、刻板化,并将奴隶制美化成造福于世的手段,以达到高人一等和“合理合法”地蓄奴的目的。西泽的前奴隶主并不赞同奴隶制的通行理由,但她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如果一下子解除他们的奴隶身份,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她把奴隶主比作仔细又耐心的眼睛,给奴隶们指路,教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因此她继续安心的蓄养奴隶,以自己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帮助”。北卡罗来南州的政府官员也公开宣扬白人至上主义,既想享受黑人的劳动成果,又怕他们的反抗和暴动,企图将他们驱逐出州。“在决定脱离联邦之后,南方统治集团利用其拥有的舆论对奴隶制辩护,鼓吹白人种族优越论;美化奴隶制,将其粉饰为一种仁慈、善良的制度,为蒙昧无知的黑人的福祉而进行行为管理;强调奴隶制是南方社会稳定的基础。”(10)李杨:《美国“南方文艺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4页。在当时的美国,这是白人为了稳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牟取暴利所采取的政治手段,也是他们对黑人实现长期控制和剥削的方法。这为美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埋下了伏笔,也为白人以政治和经济等手段凌驾于黑人甚至其它少数族裔之上提供了借口。奴隶们及其后代们都成为了社会阶层中不被接受或长期遭到歧视的人群,他们的遭遇构成了北美殖民地的非裔美国历史。但他们却长期被边缘化,迟迟不能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直到20世纪的民权运动之后才逐渐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平等。这严重阻碍了非裔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也明显与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扬的“民主、平等、自由”精神相违背。因此,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奴隶制是人类发展史中耻辱的一笔,是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标志着人性的倒退,其影响长达几个世纪。
三、对人性的反思:改造人性与构建理性社会
《地下铁道》是一部人性的寓言,揭示出奴隶制背后真正的操控者——人性,以及人性中的非理性所能造成的极恶,从而达到重新认识人性,理解人性问题的永恒性和重要性的目的。小说围绕科拉的旅程切换了五个州的不同场景,讲述她的所见所闻,偶尔也通过科拉之口对奴隶制进行控诉,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批判奴隶制将人性的问题置于前景,更深刻的反映出人性扭曲的恶果,体现人类不断认识人性、改造人性的重要性。
人性中非理性因素被放纵或是被约束,所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科拉所在的种植园便是人类各种欲望交织下的畸形产物。在这里,人性中非理性的部分没有任何约束,被无限放大:奴隶主肆意买卖、占有、凌辱、惩罚奴隶,一边通过奴隶的无偿劳动获得最大物质利益,一边通过占有奴隶满足政治、社会需求,获得种族优越感,使自己的控制欲、占有欲,甚至变态心理得到满足。奴隶们在求生欲的作用下忍受日复一日艰辛的劳作、刑罚、辱骂和噩梦,形成永久的精神创伤和不健全的人格,却要通过相互打压、相互竞争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得到高人一等的错觉。相反,科拉是种植园中唯一理性的人物,她能理性地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境遇,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并保留着人性的光芒。她能为争取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而勇敢地面对大个子布莱克的挑衅,用坚定的眼神击退对方。即使后来其他奴隶搬弄是非,造谣污蔑科拉,她也只是暗暗记在心里,从不采取报复,也从不与众人同流合污。她乐于照料年幼的奴隶们,也许是因为自己不幸的少年时期,她对他们关爱有加。当主人准备用手杖抽打男孩切斯特的时候,她不自觉地被强烈的情感紧紧抓住,“在她身上为奴的那部分及时拽住她为人的那部分之前,她已经做了肉盾,扑到男孩身上”。(11)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d, p34.科拉的灵魂没有被奴隶制湮灭,人性中善的一面足以让她战胜恐惧,直面对抗人性中的恶,这也是小说中透露的一丝希望。
踏上逃亡之路以后,科拉所见所闻的都是人性中的欲望和罪恶,途经的每一个地方都交织着恐怖与阴谋。每个人都是统治阶级利益笼罩下的一颗棋子,白人遵守规则以保全自身,或从中获得最大利益;黑人则是位于最底层的棋子,他们为美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的牺牲,却从未被看做个体的“人”。“被偷来的身体在被偷来的土地上劳作。这是个永不停息的无论在任何时代,机器,锅炉里加的是血”。(12)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d,p117.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其他人种,都是强大强大物质利益机制下的牺牲品,在各种欲望的冲击下不断异化,导致伦理道德逐渐丧失,内心麻木空虚,失去了人性中最基本的理性、善良和正义。
小说从科拉的视角对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东南部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审视,对人性的认识跨越了地域和种族的界限,它不仅是决定科拉生死的关键,也是每一个人都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每一次当科拉遇到陌生人的帮助,她心中总会交织着恐惧与不安,不知道这一次的帮助究竟是好心还是圈套。她终究是幸运的,因为每一次当她选择信任对方,对方也都愿意冒生命危险去救她。她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她的历程不仅呈现出历史,还反映了现实。科拉的逃亡经历和清醒客观的态度使她成为了小说中人性的审视者,展示出不同境遇下的不同人性。小说看似讲述的是奴隶时代的逃亡故事,却将着眼点聚焦于永恒的人性问题。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作家精心挑选和塑造的,尽管他们的选择和命运各不相同,但这些人物既是典型时代背景下的典型人性的体现,也是作家所关照的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人性体现。人性问题不仅仅在奴隶制时期得以凸显,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任何时期,它都是对历史和人类文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量。《地下铁道》中表现出的负面人性正是起源于人性的贪婪、占有欲、控制欲和盲从等非理性因素,当人性的弱点被利用、被放大,而且不加以约束和控制,就会对个体、他人,甚至整个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由此可见,小说所探讨的人性是一个永恒且意义深远的话题,时刻且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类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无论何时,人性都是人类自我迫切需要不断面对和改造的对象。
小说也揭示了人类面对诸多复杂的人性问题时,应当保持理性。小说的主人公科拉是理性的化身,她的生存和逃亡经历揭示出,要使人类摆脱愚昧、无知、落后,走向成熟,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充分运用人类的理性。《地下铁道》中大部分的人物形象,无论奴隶主、奴隶、蓄奴州的白人甚至是自由黑人,都迷失在政治强权和种族主义之中,理性或意念对他们而言都失去了意义。只有科拉身上仍保留着血性,使她敢于面对强大的男黑奴的挑衅,守住自己仅有的象征自由的土地,愿意冲上去帮小黑奴挡住主人的杖斥,哪怕受到皮鞭的毒打。这也是黑奴恺撒当初为什么选择带科拉出逃的原因:“曾受过教育的恺撒,同样也明白自己同科拉一样是‘流浪者’,带着科拉会让他有‘爱’归属感,否则他终将一直流浪。正是科拉身上具有‘爱’的人性部分,这种异于当时大多数丧失‘灵魂’的人们的特质。”(13)孙燕:《人性·镜像:对〈地下铁道〉超越种族问题的解读》,《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年第2期。科拉是小说中理性与自由精神的象征,只有拥有它们的人,才有勇气逃离奴隶主的魔爪,才有识破伪善和邪恶的能力,也才有真正实现自由的可能。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原始积累时,认为其实质便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阶级本性。人类要摆脱这种危险的境地,就只能在人的本性中去寻求出路:“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14)[英]霍布斯:《利维坦》, 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6页。这也就是说,人类的情感给人带来各种欲望、希望、恐惧和满足,但正是由于有理性,便会给人们提示“自然律”(natural law),这就是人类趋向和平的关键。
因此,和谐和理性社会的建构离不开人性的改造,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更依赖于人性中理性一面的推动作用。康德曾说:“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的本性之中,二者的根本对立就在于意念,即对待道德法则的态度。”(15)李秋零:《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译本导言》,[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第xix页。换句话说,善与正义是否能够战胜非理性中的欲望,取决于意志的选择,取决于一个人对人性的认识和掌控。只有当个体的人能够约束人性中负面的部分,释放正面的能量,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这也许就是奴隶制最终得以消亡的关键因素,也是人类文明能够延续和繁荣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地下铁道》所描绘的奴隶制无疑是一项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罪恶,无论对个人、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文明来说,都是一种摧残和倒退。在当时的美国,因为人性中非理性因素得到放纵,各种欲望交织膨胀,湮灭人性中正义、善良、平等、自由等理性的一面,导致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堕落,而社会的退步则会引发更严重的人性异化。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成为了扭曲的人性的受害者。《地下铁道》创作于奴隶制结束150年之后,其背后有着对美国社会新语境下的人性的回应,即通过对人性问题的反思,表现人性问题的永恒性和重要性。小说揭示出,与其警惕奴隶制本身,不如关注奴隶制的根源——人性。奴隶制的消亡和人类平等、自由、和谐的实现都依赖人性的力量,人性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而且是关系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构建和维护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只有回归和倡导人性中的理性,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