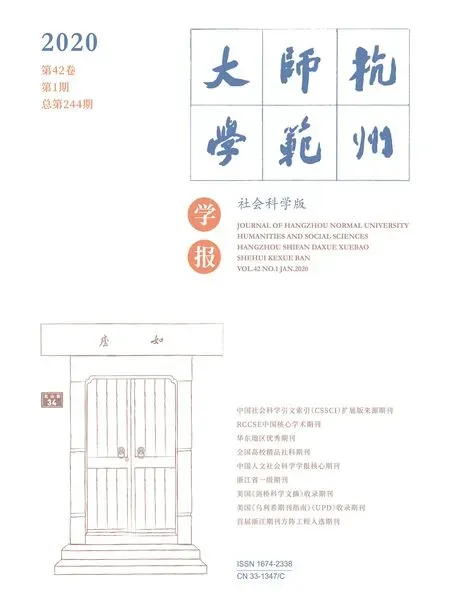“异端”的思想史考察
2020-01-19新加坡劳悦强
(新加坡)劳悦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新加坡 119260)
一、前言
“异端”一词今天往往都带贬义。所谓“异”,乃指异乎所谓“正”之意。“端”既不正,遂更引申为所谓“邪说”,故不可取。孔子(前551-前479)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第二》)原文并无“异”与“正”的对立,但自汉代起,经师已视“异端”为“奇巧他技”,贬义甚明。洎宋,旧说更多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为异端“非圣人之道”,“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1)朱注引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又引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7页。“圣人之道”,即是正道。程朱以“攻”训“治”,而“已”则作虚词。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孙奕则以“已”为实字,作“止”解,而“攻”转为“抨击”之意。抨击异端,其害可止。然而,两解尽管相异,但同样以“异端”为攻者所研究或批评之对象。事实上,宋代以前注家亦莫不如此。清代焦循(1763-1820)和宋翔凤(1779-1860)标举新说,以“异端”为一事本身之两端而非攻者所研究或批评的对象。事物犹如丝线,必有两端。“攻乎异端”实指为人治学应当注意同一事物必具两端,方可共成一体,若偏治一端,必有其害。本文从思想史立场出发,实事求是,追溯“异端”一词自春秋迄明清历代的诠释,辅以训诂考证,以求孔子原话的真意。
二、“异端”原义与汉儒解释
据现存文献,孔子以前,“异端”一词似乎并未见用。与孔子同时的郑国邓析(前545-前501),深于名理,主张刑名之治,相传他说过:
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移,非古之辩也。[1](P.3)(2)传本《邓析子》真伪尚有争议,但春秋末年,甚至逮及战国,“异端”一词别有用法,则可谓无疑。
毫无疑问,邓析所论乃针对辩谈而言。“殊类”与“异端”对言,分别指不同性质的言说类别或概念范畴,“别”和“序”就是将言说和概念加以区分,俾使各自为类,条理井然。《列子·力命》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2](PP.201-202),所谓“操两可之说”似乎是指原来分属“殊类”和“异端”的不同说法,经过邓析迂回曲折、反复无穷的辩说,最终或可以殊途同归,因为辩说的目的在于“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通意”而不相乖,则“异端”伦序或许有别,但不妨互通。(3)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资治通鉴》载:“齐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座皆称善。公孙龙由是遂绌。”见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3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 115页。据此,邓析子所言确指辩谈,而其说到战国诸子争言竞起,党同伐异之际,仍然见重。邹衍对“异端”的理解,显然并非矛盾难合之谓。(《史记·平原君传》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中有邹子之言,当为《通鉴》所本。)荀子显然视邓析为辩说家,他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尽管荀子从功用立场批评邓析,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怪说”“琦辞”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跟邓析别殊类、序异端,使不相害相乱的辩谈本领无疑有关,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3-94页。反观孔子所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当指处事的通则而言,显然并非针对辩说而发。由此可见,“异端”一词在春秋末年本非术语,言人人殊,因此并无固定之义,其实际意涵必须由其文脉来决定。
一直以来,学者都忽略,“异端”一词其实孔子弟子子贡也曾使用。《孔子家语·辩政》有以下一段对话:
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来远。’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同,然政在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鲁君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此三者所以为政殊矣。《诗》云:‘丧乱蔑资,曾不惠我师!’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也。又曰:‘乱离瘼矣,奚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哉?”[3]《辩政》,PP.161-162)
首先,“异端”并非术语,显而易见。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4](《论语·为政》,P.53)所谓“以德”乃从根本原则而言。子贡见夫子问同而答异,遂疑“政在异端”,所指乃为政的实际措施,如“节财”“谕臣”“悦近来远”等事。措施因应特殊情况而定,“各因其事”,但根本原则不会因此而变。本是一,可以前定;末是多,难以预料。然而,本末必须一贯。有子尝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论语·学而》,P.48)“孝弟”为仁之本,“孝弟”之行则端绪众多。《论语·卫灵公》载孔子问子贡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4](《论语·卫灵公》,P.161)这段对话出自孔子与子贡,当非巧合。子贡以为孔子的学问在于“多学而识之”,“多学”亦即他本人所谓“异端”。夫子谓“予一以贯之”,犹问同而答异,但原则始终不变。
问同答异,夫子随机设教,《论语》中屡见不鲜。对于这一设教的实践,孔子本人的说法就是“言岂一端”。《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载:
孔子尝,奉荐而进,其亲也悫,其行也趋趋以数。已祭,子贡问曰:“夫子之言祭也,济济漆漆焉。今夫子之祭,无济济漆漆,何也?”孔子曰:“济济者,容也,远也;漆漆者,以自反。容以远,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则何济济漆漆之有?反馈乐成,进则燕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于是君子致其济济漆漆焉!夫言岂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当也。”[3](P.574)(4)同样的对话也见于《礼记·祭义》,文字大同小异。见《礼记注疏》,收入阮元《十三经注疏》第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809页。
论祭祀的态度,“谨悫”与“济济漆漆”尽管不同,但要视乎祭祀人的身份和场合,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孔子说“言岂一端”,“亦各有所当”。从与祭者的立场言,祭祀的精神在于敬诚,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以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4](《论语·八佾》,P.64)至于“奉荐而进,其亲也悫,其行也趋趋以数”,正是祭神如神在的实际表现,如此才能及交神明。祭祀以后的相关礼仪,则属于有司之事。“谨悫”与“济济漆漆”实即祭祀时敬诚的精神,因与祭者的身份和场合不同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体现,也就是祭的“异端”。孔子论祭犹如其论政,采取的都是“各因其事”,“言非一端”的立场。事实上,“异端”一词本身既非术语,并无固定意涵,邓析、孔子和子贡的用法有所不同,这正是“言非一端”的明证。
然而,正如邓析所说,“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言虽多端,但并不妨碍其意指互通。此意也见于孔子以后的《商君书》。《商君书锥指·开塞第七》: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5](P.53)
王道、臣道各为一端,言指各异,但所依循的准绳则一,故知与力不同而可以并行不悖,善用则均可征诸侯、王天下。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此处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5)《商君书》所载是否全属商鞅之言,尚可商榷,但其书出于孔子之后,当无异议。因为君臣虽然异道,互为“异端”,但并非对立,反而共成一体。
及至西汉,汉武帝(前156-前87)对于“异端”的看法,依然继承此意。《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制曰:
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武帝所论的前提是“同条共贯”的“帝王之道”,而他惑于虞舜、文王有逸劳二端之殊,治世有质文二端之别,故疑帝王之道异指。武帝所谓异指,实即“异端”,而“异端”又同属帝王之道,而非别有治世之道。
“异端”一词的早期用法以及其观念意涵,分析如上,至于《论语》“异端章”的经师诠释则不传于世。与武帝同时的司马迁(前87年卒)却意外地为后人留下重要线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7]( P.228)
太史公显然以历史实例来解释《论语》“异端章”。依他所说,孔子作《春秋》自有其微言大义,但传诸弟子,则各有所得,“人人异端”,又“各安其意”,专攻一己所得而不顾同门所受,遂“失其真”。夫子微言既失,斯为其害。太史公训“攻”为“治”,而“异端”则指同一事体的不同意指,而非异于此一事体的另一事体。异端本身不为害,害乃由于安于专攻事体的一端而忽略其余,犹如瞎子摸象,最终全体之真遂蔽于一偏之见。孔子论政,问同答异,亦犹弟子传述同一《春秋》之微言,各有所见而异端纷起,可见太史公对“异端”的理解深得夫子之意。
司马迁的看法亦见于稍后刘向(前77-前6)、刘歆(前46-23)父子的《七略》而为班固(32-92)所承。《汉书·艺文志》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6](第6册,P.1746)
诸子九流十家都从备载王道的王官之学中“各引一端”,易言之,九流十家是“异家”,而一以贯之的则是王道。“异家”实即司马迁所谓的“异端”。异家各推所长,以“崇其所善”,但所善适成其蔽短,所言殊异,譬犹水火,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支与流裔”即是“端”。必须强调,“异端”既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因此原来并无贬义,而毋宁是客观的描述,指的是同出一源的不同支流。此外,由于异端“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因此自然各有蔽短,若专攻一端而忽略其余,正是太史公所讲的“各安其意,失其真”,“斯为害已”。“异端”并非属于不同体系的对立面,更非与某一既定正统的互相矛盾的学说。
语言文字的意义随时代而变,“异端”一词也不例外。“异端”原来不涉褒贬,但大约在西汉中叶开始衍生贬义。与太史公同时的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在其《封禅赋》云:“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风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尧,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7]( PP.1229-1230)文中“异端”当指异于唐虞以降,下及姬周之王道教化,或足以影响其盛治的主张,似乎已略带贬义。又《汉书·武五子传》载,“戾太子据,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6](第9册,P.2741) “异端”一词应出自当时史官所记,若出自班固,则时在东汉初年。戾太子宾客所进的“异端”当指《公羊》《谷梁》以外的种种异说,也未必跟《春秋》有关,而史官之意似乎以为不可取。自此以下,“异端”在东汉的一般用法中便成为贬义词。《东观汉记·张酺传》载:“张酺(104年卒)拜太尉,章帝诏射声校尉曹褒案汉旧仪制汉礼,酺以为褒制礼非祯祥之特达,有似异端之术,上疏曰:‘褒不被刑诛,无以绝毁实乱道之路。’”[8](P.693)张酺所言非关经术,足见“异端”实为一般用语。逮于汉末,荀悦(148-209)曰:“经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之节,在于四时五行。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则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及至末俗,异端并生,诸子造谊,以乱大伦,于是微言绝,群议缪焉。故仲尼畏而忧之,咏叹斯文,是圣人笃文之至也。”[9](P.437)与刘向父子和班固不同,荀悦视诸子百家为“异端”,妄造缪议,以乱经典大伦,致使微言大义由此而绝。
现存汉儒的《论语》训释,未见“异端章”的解说,但汉末儒者以经解经,援用《论语》“异端章”为说,适有孤例。此时“异端”已成贬词,经师解释此章,竟然随俗。《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二年》:“惟一介断断焉,无他技。”何休(129-182)注曰:“一介犹一槩;断断犹专一也。他技,奇巧异端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又《礼记·大学》引用同一段传文,郑玄(127-200)注曰:“他技,异端之技也。”[10](《礼记注疏》,P.988)何、郑同时,均治经学,何休似乎直接以“奇巧他技”来解释孔子所说的“异端”,而郑玄或未必然。(6)《礼记·中庸》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玄注曰:“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见《礼记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第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880页。此外,何休当以“攻”作“攻治”解。何、郑都是东汉中叶以后人,说法与司马迁不同,未可遽作定论。事实上,与何、郑同时的王符(78-163)对于“异端”的理解别有一义。《潜夫论·叙录》:“人天情通,气感相和,善恶相征,异端变化。圣人运之,若御舟车,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叙‘本训’第三十二。”[11](P.480)“本训”所讲的“本”即天人合一之本,“异端”就是天人合一中天与人两端,亦指善恶相乘的两端。易言之,异端同属一体。“异端变化”即指人天之间情通,互相感应,人间的善恶足以气感上天,于是上天以灾祥谴告,所谓“变异吉凶,何非气然” [11](P.368)。
汉儒通经致用,在议论实际政事的时候,常常引经据典以为说。《后汉书·范升传》:
时尚书令韩歆(39年卒)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12](卷36,PP.1228-1229)
范升此处讨论《费氏易》和《左氏春秋》是否应该立为学官,他所谓的“异端”乃相对于“本”而言,而此“本”则在于孔子编定的《五经》。易言之,异端就是不得孔子《五经》本旨的经艺传说,而“攻”亦作“攻治”解。范升卒于明帝永平年间(57-75),早于何休与郑玄,他对“异端”的理解似乎与何、郑不尽相同,而且他抨击《费氏易》和《左氏春秋》恐怕与现实的政治目的有关。(7)范升既视《费氏易》和《左氏春秋》为“异端”而加以抨击,则“攻乎异端”之“攻”实应作“攻伐”解,与他的议论中的解释不同。
与何休、郑玄同时而稍早又有延笃其人(167年卒),既精专《左氏传》,又与郑玄同门,从马融(79-166)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3](PP.93-94)(8)本传谓笃“少从颖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典深敬焉。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见范晔《后汉书》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03页。桓帝时,儒者争论仁孝之先后次序,延笃的意见最为通达。他说: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本根充实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2](卷64,PP.2104-210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延笃认为有关仁孝之辩的各种议论,同是“异端”而且都能“互引典文,代取事据”。显然,“异端”不单毫无贬义,更且“可谓笃论”。究其原因,仁孝犹如树木之根叶,“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本根充实为先”,“二致同源”,不可偏废。仁孝“同质而生”,合成一体,其源则在于人心,“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由是观之,仁孝不啻人心之两端,相对互言,各为其异。仁孝二德本身性质如此,则辩论两者关系的争论,自然也互成异端了,因此,延笃认为“仁孝之辩,纷然异端”,“可无讼也”。易言之,若偏执仁孝先后,则无异于“攻乎异端”,自然“斯害也已”了。延笃对“异端”的理解,从词义看,与子贡最初的用法一般,而从义理论,异端共成一体,则又与同时的王符契合。
“延笃本传”载:“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12](卷64,P.2103)虽然仁孝之辨并非对答帝问,但延笃持平之论,必然也是他根据自己对《论语》的心得而来。然而,延笃谓仁孝二致同源,或许也受到西汉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启发。《春秋繁露·仁义法》云: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着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谓之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二端之政诡于上,而僻行之则诽于下,仁义之处可无论乎?[13](PP.249-256)
仲舒所谓春秋“二端之政”即在于治人与治我,而所以治人与我则在于仁与义。人我与仁义各为两端,但共成一体,而非互相对立,畸轻畸重。所谓“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若误认人我对立,仁义相隔,就是“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了。人我、仁义只有先后不同,董仲舒必定反对只讲人我、仁义的其中一端,因为这正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延笃论仁孝,连先后都不可强辩,但他兼顾全体,不偏一端的看法则与仲舒无异。
必须指出,延笃对“异端”的圆融理解,其实与其人的性情修养关系至大。本传载他当京兆尹时,“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 [12](卷64,P.2103)可见他性宽仁恕物,以百姓之心为心,又能包容异见,采纳他人之长,所以治内官民融洽,和气一团。因是之故,延笃剖析仁孝,并非纯作理论之分辨,对于仁孝的不同体现,他都逐一以历史人物为例。纯体仁孝者,虞舜、颜回是也。偏而体之者,公刘、曾参是也。再者,他更以功与德论仁孝,功、德归属全体之两端,但无分轩轾,所以说“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
延笃个性耿正,并非乡愿。史载:“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159年卒)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 [12](卷64,P.2104)延笃不以个人仕途得失而顾忌直言。至于论经,他也自有主张,而非依仰时流,不辨唯阿。范晔(398-445)称赞他“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 [12](卷64,P.2108)。明乎此,我们可以肯定延笃对仁孝关系的看法并非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事实上,他认为“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显然就是从他对人性的了解而来,这不关乎训诂,不但与当时争论者“互引典文,代取事据”,迥然殊别,更且远出经义的瓜葛而直入孔门以实际人生论仁孝的堂奥。他的见解其实反映出他本人开明通达的性情。延笃因上奏梁冀一事,“以病免归,教授家巷”。后来他的好友在京师向公卿推荐复任,但他为书婉谢,书云:
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已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12](卷64,PP.2106-2107 )
延笃复书,发端即引孔子《论语》言命。(9)《论语·宪问》载:“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8页。这并非他所谓的“引典文,取事据”而已,他实效法孔子为人,所以“来命虽笃,所未敢当”。他免归之后的生活,清楚显示他的人格风范。他晨起即诵读经书,日入则朗咏《诗》篇,兼及“百家众氏”自谓“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这是何等的胸怀气象。孔子尝言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孔子以学无常师著名,(10)《论语·子张》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3页。而延笃则涵泳“五经”百家众氏而不知天地之存,不识人我之别,岂非他师法夫子的成绩?书末以知足善止作结,却是老子“知止不殆”之教。延笃包容经学百家众氏,并非空谈。试问,以延笃其人,又如何会敌视百家众氏,以为“奇巧他技”之“异端”,必攻伐之然后可。
延笃对“异端”的了解,可谓深得孔子的真义,但汉儒未必人人同有此见,何休、郑玄或已持异。由于魏何晏(195?-249)集解《论语》并未辑录,其他汉儒的看法无由得知。何晏本人对“异端章”作注曰:“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者也。”[14](P.36)说法大概受韩歆、何休和郑玄的影响而适好与延笃相反。南朝皇侃(488-545)疏释何说,亦步亦趋,疏曰:
此章禁人杂学诸子百家之书也。攻,治也。古人谓学为治,故书史载人专经学问者,皆云治其书,治其经也。异端谓杂书也。言人若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故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为害之深也。又曰:“‘善道’即五经正典也。‘有统’,统,本也,谓皆以善道为本也。‘殊途’,谓《诗》《书》礼乐为教也,途不同也。‘同归’,谓虽所明各异端,同归于善道也。诸子百家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归也。”[14](PP.35-36)
何解、皇疏以后,“异端”变成与善道殊趋,无益教化的虚妄杂学。程朱理学盛行,“异端”便非“圣人之道”。直到清代中叶,异议几乎阙如。
三、训诂补证
综上所论,自春秋至汉代,“异端”一词本身并无定义。汉儒并未直接解释《论语》“异端章”原意,而何休以“奇巧他技”等同孔子所说的“异端”,却未陈实据。至于“攻”字之义,汉儒皆释作“攻治”,未见例外。从训诂而言,《说文解字》卷三“攴部”:“攻,击也。”段玉裁注:“《考工记》:‘攻木、攻皮、攻金’,注曰:‘攻犹治也。’此引伸之义。”[15](P.125)据此,汉儒所用乃引伸之义。何晏《集解》此章虽然未采汉儒说,但注云“攻,治也”,当有所承。又《说文》卷十“立部”:‘端,直也。”段注:“用为发端、端绪字者叚借也。”[15](P.500)卷七“部”:“,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根也。”段注:“题者,頟也。人体頟为冣上。物之初见卽其頟也。古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废,乃多用为专矣。《周礼》‘磬氏巳下则摩其’,之本义也。《左传》‘履端于始’,假端为端也。以才、屯、韭字例之,一,地也,山象初生,一下则象其根也。”[15](P.336)从端字的造形看,可知植物初生已具上下两端,因此有发端、端绪之假借。发端谓在下之根,端绪则指在上初生之象。《说文》卷十三“系部”:“绪,丝也。”段注:“者、艸木初生之题也,因为凡首之称。抽丝者得绪而可引,引申之,凡事皆有绪可缵。”[15](P.643)丝自然有两端。又卷十四“金部”:“鏠,兵也。”段注:“兵械也。,物初生之题,引申为凡物之顚与末。”[15](P.711)物之顚与末又成两端,凡物皆然。又卷六“木部”:“干,筑墙木也。”段注:“谓两头也。假令版长丈,则墙长丈。其两头所植木曰干。”[15](P.253)又卷四“肉部”:“唇,口也。”段注:“口之厓也。”[15](PP.167-168)口自然亦有上下两端。综合《说文》有关文字,“”(端)必然成两,即所谓两端,其或不然,则特有所指,如鏠为兵,为艸木初生之题。最重要的是,必出自同一物之两端,而非与他物互为异端。
《说文》卷三“异部”:“异,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段注:“分之则有彼此之异。竦手而予人则离异矣。”[15](P.105)所谓“分之则有彼此”,亦即未分之前,本为一体而无分彼此。甲骨文“异”字乃象一个人身鬼头,两手张开的人,故有怪异之意,但必须注意,尽管人身鬼头,实属同一个人,而非两件异物,拼凑一体。鬼头怪异,乃相对人身而言,上下不同所致。从字义看,“”必然包括两端,而“异”本就一体之内,身首各处一端,遂分上下彼此,更且鬼头人身,即所谓“异”。易言之,“异端”并非别有他物,异于所指之物。“异端”乃同一物之两端,互相为异。如欲研究一物,必须兼明其两端,不可偏废。若专治一端,只见鬼头,不见人身,或只见人身,不见鬼头,全貌不识,即所谓攻乎异端,则必然致害。段“注”引《考工记》谓“攻木、攻皮、攻金”三者皆需用刀。《说文》卷七“宀部”:“害,伤也。从宀从口。宀、口,言从家起也。丯声。”段“注”:“人部曰:‘伤、创也。’刀部曰:‘创、伤也。’……会意。言为乱阶,而言每起于袵席。”[15](P.341)害,伤也,而伤又为刀创。犹有进者,刀创肇自家内,起于袵席,而非从外入,可见害之所成,实生于所攻之物本身,因为所攻仅其一端。以偏概全,曷能无害。
四、文脉与义理
训诂已明,我们可以从文脉进一步考察。循文释义,“异端”固然未必指“奇巧他技”。何休、郑玄虽或可以自圆其说,但仅属可能,或者更是附会。《论语·子罕》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此处两端指鄙夫所问之事而言。朱熹注:“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4](《论语章句·子罕》,P.111)以经释经,“异端章”与“鄙夫问我章”可以互相发明。一事之两头,各自独立,故称两端。两端对言互指,则互成异端。客观而言,曰两端,朱注所举正是两端的具体例子;从关系而言,不同的两端互相构成异端。其实,两端、异端并无二致,分别只在文脉,因此,“叩其两端”不可作“叩其异端”,而“攻乎异端”也不可作“攻乎两端”。朱熹千虑一失,未能察悉互文对读之发明。
从义理考虑,若“异端”一词出自《老子》,则何休、郑玄“奇巧他技”之说,自可成立。《老子》第十九章谓:“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五十七章又曰:“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至于第七十四章则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反对奇巧,言之再三,若有所谓“异端”,当指异乎“无为”“无欲”之妄作。然而,孔子并未反对奇巧。“子不语怪、力、乱、神”[4](《论语·述而》,P.98),奇巧不在其中。《论语·阳货》载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4](P.181)博弈或可算作奇巧,但孔子谓犹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此,弟子子夏也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4](《论语·子张》,P.188)奇巧若属小道,亦未在排斥之列。再退一步而言,即使所谓“小道”绝不可取,孔子大概也只会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4](《论语·卫灵公》,P.169)(11)朱注曰:“不同,如善恶邪正之异。”此说未必便是孔子原意,若然,则尤其可见夫子包容“异端”的雅量。因是之故,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他只是批评,并未抨击。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5页。,而必然无抨击之意。总而言之,“异端”若作“奇巧他技”解,义理上即与孔子思想枘凿不合。道不同,即肆意攻击,亦与孔子性情殊不相侔。
上文所述,清儒所见,亦有雷同。戴震(1724-1777)首先指出,“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言业精于专,兼攻两头,则为害耳。”(12)见《东原集》,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4页。以“事有两头”释“两端”,可谓直截了当,但戴氏并未提出训诂证据。(13)戴说当袭自朱熹。《中庸章句》云:“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中庸章句》,戴震倒背如流,不可能不知朱熹有此说,但戴氏不采取朱子取中之意而偏袒何休专一之说。再者,他以治学宜专精,兼攻两头则为害,与夫子之原意,适得其反。戴说可能从何休《公羊》解启发而来。何注“惟一介断断焉,无他技”曰:“一介犹一槩;断断犹专一也。他技,奇巧异端也。”戴氏既谓一事之两头为两端,则两端无疑指同一研究对象,而非别有一物,故他未以“他技”为“奇巧”,这是戴说与何解不同的地方。孔子言学,特重恒德。《论语·子路》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4](P.147)朱注谓“恒,常久之意” [4](《论语章句·述而》,P.99),故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4](《论语·子罕》,P.114)恒可以专心致志,但专心者不必能恒,故孔子许人以恒而不以专。(14)孔子当然并不反对专心致志,但文献所及,未见其特别有所表扬。先秦儒言专者则有孟子、荀子。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见《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31-332页。《荀子·性恶》曰:“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3页。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4](《论语·述而》,P.99)(15)又《论语·雍也》载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冉求所缺乃恒德而无关专心。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7页。然则戴氏所释实不合《论语》原旨。攻乎异端与攻乎两端,意思迥然不同,文脉之重要,于此可见。
《中庸》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4](P.20)郑玄注云:“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戴氏补注曰:“执其两端,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全体无遗弃也。其斯以为舜乎,言舜之知而又如斯,是以为大知。”[16](《中庸补注》,PP.55-56)过与不及固以同一标准为据,戴说引申郑注,强调全体,舜之大知实由于此。此说其实正合本文所论之义,但可惜戴震未能由此悟及异端与两端实指一义。(16)戴震三十多岁时尊崇程朱理学,尝言:“自程子发明‘格物致知’之说,始知《大学》有阙文。凡后儒谓‘格物致知’不必补,皆不深究圣贤为学之要,而好为异端,其亦谬妄也矣!”见所著《经考附录》卷4,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张岱年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546页。此处,戴氏“异端”一词乃有明以来理学家习用之义,即以违于正道为异端。及其学成,力反理学,而程朱学说不再是正道,则又提出本文所讨论的另外二说,连朱熹对“异端”的解释也企图一并推翻。
焦循(1763-1820)显然洞悉戴氏“兼攻两头为害”一说之误,故未遵从,但他受其“事有两头谓之异端”以及“两端为一物之本末首尾”一说所启发。焦氏说:
异端犹云两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此即发明《论语》之义。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有两端则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则有以摩之而不异。刚柔,两端之异者也。刚柔相摩, 则相观而善。[18](PP.134-135)(17)《韩诗外传》所言,实撷取自《邓析子》,原旨关乎辩谈,而并非发明《论语》之义。说见上文。
焦氏所言,别出心裁,理畅义广,关键在于其能洞悉“异端犹云两端”。司马迁谓异端各安其意而失真,与焦说声气可通。但焦氏并未提供训诂证据,所举《韩诗外传》,用意也在于其能发明《论语》之义,而并非以其为训诂之确证。焦氏悟及《中庸》“两端”与“用中”之关系,从而抉发“异端章”的真意,并贯通孔子所主张的中庸之义。换言之,焦说似乎从义理反求训诂,而非据训诂而明义理。此外,焦氏又云:
唐宋以后,斥二氏为异端,辟之不遗余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之文,未之能解也。惟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异端反是。孟子以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为执一而贼道。执一即为异端,贼道即“斯害”之谓。杨墨执一,故为异端。孟子犹恐其不明也,而举一执中之子莫。然则凡执一者皆能贼道,不必杨墨也。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19](P.37)
此说已非斤斤于“异端”一词之义,而更贯通《论语》《孟子》以证成孔子之为学做人之道,畅快明达,颇类延笃。清儒有关“异端”之说,当以焦氏为准绳。(18)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论语》研究之殿军,而对于“异端章”,详引焦循和宋翔凤二家之说,并谓“焦说尤有至理”。稍后宋翔凤(1777-1860)又承焦说,并补充了三种文献证据,即郑玄对《中庸》“两端”的解释以及《左传》本文,并进一步阐发“异端”与中道以及中出于权之理据。宋氏说:
《中庸》记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注云:“两端,过与不及。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谓执者,度之也。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不及而能用中。中则一,两则异,异端即两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19)《左传·成十三年》:“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见《春秋左传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460页。有所治而或过或不及,即谓之异端。攻乎异端,即不能用中于民,而有害于定命。……又云:“《孟子》言‘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者,能用之谓也。过与不及,则有轻重,必有两端,而后立其中,权两端之轻重,而后中可用。不知有两端而权之,则执中者无可用,而异端之说转胜。故异端之炽由执中无权者致之,是以可以立者,尤贵乎可以权也。”(20)引自宋翔凤《论语发微》,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07页。
宋氏谓中之用在权,固有可取之处,但其实亦非其创见。朱熹早已说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4](《中庸章句》,P.20)宋氏之贡献在于其能联系“两端”与“异端”而说中说权,但他的说法实则受到朱熹和焦循深刻见解的启发而来,而其枢机则仍然在于他看出“异端即两端”。
跟戴震“业精于专”说一般,宋说也从义理立论而资借训诂,足见戴氏提倡“训故明而后理义明”的解经方法,(21)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云:“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志所同然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见《戴震全书》,第6册,第505页。连他本人以及受其启发的学者都并未严守不违。当然,义理训诂相因互借,并不始于清儒。宋儒如朱熹早已如此释经,尽管明代理学家群相痛斥佛老为“异端”,以致“异端”一词几乎与佛老同义,但也有学者实事求是,解经主义理而又兼顾训诂。比如,章世纯(1575-1644) 《四书留书》卷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条云:
说之异者,足以相济,不必足相伤也。知其一端,不知其他端,徒以异己而攻之,失其所济,丧己之利矣。攻之而说不得成,败人之功矣。为学为治,皆不可也。鸡鸣狗盗智者,犹或存之,为有济于一旦也,故善用道者,不弃恶,恶且不弃,况或俱美者乎?是欲有天而无地,好山而憎渊也。(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34页。
章氏显然发挥《论语》义理,但与理学家不同,他尽量照顾原文字义,虽然未能如清儒提供经文互证,仍不失为合乎训诂的持平之论。《四书留书》六卷在《明史·艺文志》列为子书,归入儒家类,而《四库全书》馆臣以为失当而复置于经部,(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是编说《四书》者六卷,又《内集》一卷,乃所著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然说《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世纯自序,后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节耳。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今割其《内集》《散集》,别著录,而说《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锐,其诂释《四书》,往往于文句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于训诂,而亦未尝如良知者流滉漾以自恣,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7册,第709-710页。但馆臣以解经体裁立论,若实事求是,则章氏解经主义理,昭然无疑。
五、结语
近代学人对“异端章”的解释当以钱穆先生(1895-1990)为最精当深刻。其说如下:
攻者,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也。或说攻,攻伐义,如小子鸣鼓而攻之。然言攻乎,似不辞,今从上解。异端者,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及彼,仍一线也。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为异端,从此端视彼端亦然。墨翟兼爱,杨朱为我,何尝非各得一端,而相视如水火。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义别有指。此盖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也。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知全体,务求相通,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歧途亡羊,为害无穷矣。……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也”。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端,则偏而不中矣。[20](PP.50-51)
钱先生的训诂根据,前贤多已言之,但他指出以“攻伐”释“攻”则“攻乎”似不辞,或为其独见。(24)“攻若”作“攻伐”解,习惯上似乎在宾语前不加“乎”字,至少古籍无此用例。相反,若作治解,虽然先秦文献并无其他“攻乎”的用例,但“治”字本身则可以在其宾语前加一“乎”字,如“治乎人”“治乎民”“治乎内”之类。无论如何,钱先生的看法精彩之处在于其能使训诂义理互相发明,从而揭示孔子思想在生活中实际体现,使读者由此能够想见夫子其人其生命,乃不致胶着于文字层面,而失却夫子为人和治学之真精神。若追源溯流,钱先生的解经路数其实与东汉延笃前后呼应。
最后,对于《论语》“异端章”本意的解释,本文尝试提供一项补充。上文提及义理关乎文脉,自汉代至当今,学者讨论此章,兼顾全书义理者有之,深究“异端章”本身的文脉者亦有之,但我们还可以针对“异端章”在《论语·为政》中的前后文脉和义理,进一步论证孔子的本意。“异端章”之前一章与后一章分别为: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前一章论学与思不可偏废,若专攻一端,则非罔则殆。后一章论知与不知相因而成知,前人似未留意。朱注曰:“但所知者则以为知,所不知者则以为不知。如此则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亦不害其为知矣。”[4](《论语章句·为政》,P.58)《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朱子似乎有见于此,以为夫子之意在于求无自欺。笼统而言,朱注未尝不通,但若切实深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意指在知,而不在诚意与慎独。然则,知之与不知在此章中当与“是知也”之“知”有关,而并非各自独立的两个情况。凡人所知固然以其他一些相关知识为条件,但同时也由于对更多的相关知识的无知所致。若对所有相关知识一一知晓,则或许会察觉到原来的所谓“知之”,只是片面的知识,甚至可能全是误解。然则所谓知之,其实必然以不知为前提。严格而言,自觉有所不知,然后所知才能确然,尽管未必能够兼照所知对象的全体。所谓确然,即自知所知以有所不知为前提,因此所知有其局限,或许更是权宜和暂时的看法。能够认识到所知与所不知实际互相滋养,即是孔子教诲子路时所讲“是知也”的“知”。知之与不知同为求“知”必需的两端,可谓“知”的“异端”。鄙夫问孔子,对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随后叩其所问之两端而竭焉,若由此生知,则此知即从夫子的“空空如也”的“无知”来。但此由“无知”而生的“知”有其局限性和暂时性,未必可以时时奉行。“知”既有其局限性和暂时性,则必然会随时而变化。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21](《寓言》,P.952)此虽是寓言,但正准确道出孔子对“知”的认识,而可作为本文所论的旁证。
学与思、知之与不知同样讲一事兼有两端,不可偏废,因此,“异端章”言治学必须兼顾一事之两端,夹于前后章之中,并非偶然。《论语》中内容相关的章节连类并置,颇有其例,殊不罕见。事实上,“学而不思章”前的四章也同样与兼顾一事两端之意有关。原文如下: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温故”与“知新”乃为学一事之两端,若能兼顾,则可以为师。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4](《论语·里仁》,P.74)《中庸》云:“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4](P.24)言行不可偏废,君子慥慥焉。君子周而不比,比则由于偏私之故。君子不器,正求其周全不偏。“异端章”的本意与其前后章节的文脉和义理可谓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P.166)恕是善处人我之道,不坚持己见,也不勉强他人,双方俱得。孔子以为终身可行,因为恕则兼容,不会攻乎异端,以致在人生道上,窒碍难行而成斯害。(25)关于孔子兼顾两端的一贯思想,可参看劳悦强《孔子的两端思想》,《比较视野下的先秦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梁秉赋 、李晨阳主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6年,第265-286页;又刊于《儒家文明论坛》第3期上册,傅永聚、马士远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0-203页。
现代学者重新诠释经典固然必须讲求文字器物的客观实证,但若偏废义理,则不啻攻乎异端,以《论语》而言,既失孔子思想之一贯,更无以见其为人论学之全豹,此所谓斯害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