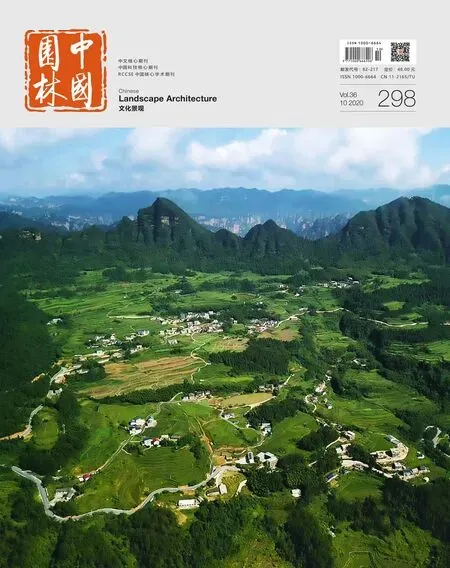“连接自然与文化”①:西方哲学背景下的全球议题
2020-01-18史蒂文布朗撰文
(澳)史蒂文·布朗 撰文
韩 锋 程安祺 译
我住在一个叫“格京塔”(Gozinta)的乡村农场,占地60hm2,距离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80km。农场位于低至中等陡峭的山坡上,主要植被群落为开阔的脆性橡胶林。那里有东部灰袋鼠、红颈袋鼠、沼泽袋鼠、普通袋熊和短喙针鼹鼠等多种乡土动物,以及超过90种被记录的鸟类。该地区拥有超过20 000年的原住民历史,位于恩古纳瓦(Ngunawal)、贡贡古拉(Gungungurra)和尤因(Yuin)3种语言文化族群聚居地的边缘地区,在19世纪20年代曾被殖民入侵者(主要是英国)占领②。博罗溪(Boro Creek)是一条狭窄的间歇溪流,流入肖尔哈文(Shoalhaven)河。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博罗溪附近出现了第一座农舍及其附属建筑。我的农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种植橄榄树,边缘处用作绵羊、牛牧业养殖以及农作物的种植,是一处自然环境和文化历史深刻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人文地理领域。该学科加上风景园林学、园艺学、建筑学、人类学、人种学、地理学、考古学、生态学、艺术史等学科领域的概念,引领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的文化景观保护实践的发展。如今,随着遗产内涵的拓展、技术的进步、气候变化及可持续等环境挑战的影响,以及对于更好地理解和阐释人与场所、景观、非人类物种之间联系的迫切需求,文化景观的实践已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遗产保护领域,文化景观的理念与遗产地的管理与安全保卫紧密相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遗产保护已经从关注建筑、城市中心以及考古遗址转变为涵盖越来越多样化的遗产形式(如非物质遗产、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和外太空遗产),同时开始关注越来越大的地理区域。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设立“文化景观”作为文化遗产的新类别[1]。委员会根据西方文化框架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分类:人类有意设计和创造的景观(以历史园林和公园为代表),遗址景观和持续演进的景观或活态景观(包括乡村或城市),以及关联性景观(象征或精神)[2]。
正如澳大利亚人文地理学家莱斯利·海德(Lesley Head)指出的那样,文化景观概念不是凝固的,而是“随时间发生变化,并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学科和不同政府背景下有着一系列不同理解”[3]。根据大量的相关文献,文化景观可以总结为三大类意义[4]。
1)文化景观作为物质实体。从物质或有形的意义上讲,文化景观是地球上部分被选定的、经过人类-生态互动(或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区域。
2)文化景观作为概念和过程。在此,文化景观不仅是有形的场所(或物质实体),而且其内涵更加广泛,可以包含关联性和象征性景观、虚拟空间以及城市历史性景观等。
3)文化景观作为方法和工具。虽然文化景观方法论可能不像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5]方法那样明晰,但文化景观研究中有大量的实践方法:例如景观特性描述、景观考古学、传记和生物水文学方法、文学表现、世界遗产方法[6]、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的《遗产提升工具包》(Enhancing Our Heritage Toolkit)[7],以及各种保护区管理方法。
世界遗产保护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方(即欧洲和北美)思想的普遍影响:自然环境和文化历史是相互分离的领域。也就是说,“自然”与“文化”是二元的、对立的,彼此分离的。考古学家和遗产学者丹尼斯·伯恩(Denis Byrne)指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自然二元论是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因此讨论文化-自然议题对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相遇具有开创性意义。[8]”
世界遗产就是将“自然”与“文化”分离的系统之一。举例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提名程序和实践就是基于这样的分离[9-10]。这种分离在“突出与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的评估标准中很明显,6项标准适用于文化遗产,4项适用于自然遗产。即使是“混合遗产”类别(即满足一项或多项文化和自然标准的世界遗产),仍然保持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将它们视为相互联系的。虽然《世界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经实施了48年,但是《公约》[9]仍然将这2个领域视为分离。尽管在1992年设立了“文化景观”遗产类别,并于2005年建立了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文化景观独立名单,这种分离状况仍然存在[11-12]。
在本文中,我将重点介绍2 个全球性非政府组织,IUCN 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的工作,以及二者为“架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桥梁所做的合作努力。IUCN和ICOMO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2个机构都认识到有必要对混合世界遗产或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的提名地进行联合评估。直到最近,这类评估还是各自分开进行的。我重点介绍这2个全球性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推广他们在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为更好地连接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治理和管理实践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引领作用。
1 IUCN:向文化转向
IUCN于1948年10月5日在法国枫丹白露成立。
作为第一个全球环境联盟,IUCN将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召集在一起,其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它的目的是鼓励国际合作,并提供科学知识和工具用以指导保护行动。如今,IUCN拥有1 300多名成员(包括国家、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组织),以及15 000多名国际专家。IUCN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多样化的环境保护网络,持续领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其作为实施巴黎气候变化协议(Paris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等国际协议的关键手段[13]。
IUCN自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拒绝将景观的文化性与自然性平等看待。早在成立初期,IUCN就倡导“荒野”(wilderness)和“堡垒”(fortress conservation)概念和保护模式,两者均导致了原住民和其他公民从保护区内被(通常是他们的社区家园)驱赶出来。
这种状况直到1998年IUCN“保护地非物质价值”(Non-Material Values of Protected Areas)工作组成立,才发生显著的变化。2003年,工作组将其名称更改为“保护地文化和精神价值”(Cultu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of Protected Areas,CSVPA)③,该名称的更改与在南非德班(Durban)举行的IUCN第五届世界公园大会有关。此次大会上,原住民谴责IUCN以往的自然保护实践,对IUCN在承认和尊重原住民的权利、责任以及保护方面提出了挑战[14]。
为了使保护区包括半自然、农业和城市景观这些类别,IUCN在1994年提出了6类保护地分类体系[15]。2008年,IUCN对此分类体系进行了修订,其中的2个类别强调了人类创造力的作用。
第V类 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区:这类保护区经过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产生具有显著而重要的审美、生态、文化和科学价值,安全保卫此类相互作用关系的完整性对于保护和持续地区发展以及相关的自然保护和其他价值至关重要。
第VI类 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区:第VI类保护地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系统、栖息地和关联的文化价值、传统自然资源管理系统[16]。
2012年,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IUCN世界保护大会上,提出了一份关于IUCN和ICOMOS协同合作的提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将自然与文化融入世界遗产体系[17]。
2 ICOMOS:向自然转向
ICOMOS成立于1965年。在成立之初,ICOMOS通过了《威尼斯历史遗址保护和修复宪章》(Venice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以下简称《宪章》)。《宪章》是一部于1964年由一群遗产保护专家(主要是建筑师)在威尼斯制定的保护导则。《宪章》为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框架,但未提及“自然”或“自然遗产”。ICOMOS从最初对历史建筑的聚焦,经过55年的发展,其关注点已包含多种类别的文化遗产,这在其29个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中可见一斑[18]。
ICOMOS的任务是保护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促进将理论、方法和科学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该组织拥有约11 000名个人成员、300名机构成员、110个国家委员会成员以及29个国际科学委员会。
在总的历程中,ICOMOS并未有效参与到自然遗产的保护,而是延续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分离的传统西方观点。不过,一些ICOMOS的官方文件也承认自然和文化存在某种交叠关系。例如,澳大利亚ICOMOS的《巴拉宪章》(Burra Charter)指出[19]:
1)宪章可以“适用于所有具有文化价值的场所类型,包括具有文化价值的自然、原住民和历史场所”(序言;在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2中也有提及[20]) ;
2)“场所具有广义的范畴,包括自然和文化特性”(第1.1条;解释性说明);
3)在“某些文化中,自然和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第5.1条;解释性说明)。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指出[21]:
1)遗产地包括其自然环境(第2条;注释);
2)某些类别的遗产,例如文化景观,可以具有重要的自然价值(第3条);
3)遗产的保存状况与其自然和文化特性有关(第17条;注释)。
3 IUCN-ICOMOS在自然-文化融合上的合作
自2013年以来,IUCN与ICOMOS开始探索更紧密的合作方式。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学习和创造新方法,集中认知和支持重要陆地与海洋景观的自然、文化和社会价值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特征”[22]。这项工作正在进行的2个关键项目是“连接实践项目”(Connecting Practice Project)和“自然-文化/文化-自然之旅”(Nature-Culture/Culture-Nature Journey),这2个项目我都参与了[23]。
2013年10月启动的“连接实践项目”是一个合作项目,旨在定义新的方法和策略,在世界遗产体系中进一步融合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迄今为止,该项目共经历了3个阶段④,每个阶段都基于与特定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和社区的合作[24-29]。3个阶段的研究目标和遗产地分别如下。
第一阶段(2013—2015年):此阶段采用“边做边学”的方法,在“考量自然和文化价值时制定更内在关联的策略”,同时对“IUCN和ICOMOS的实践和制度文化”进行批判性评论[29]。核心成果是在IUCN和ICOMOS之间建立了合作的工作程序。第一阶段的世界遗产研究案例是蒙古阿尔泰山脉的石刻群(Petroglyphic Complexes),埃塞俄比亚的孔素(Kongso)文化景观,以及墨西哥的圣卡安(Sian Ka'an)生态保护区。
第二阶段(2016—2017年):该阶段总结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加强世界遗产地治理和管理的实践性措施”[29]。《遗产提升工具箱》这一原来被用以评价自然遗产管理有效性的工具,被应用于文化遗产地[7,30]。该阶段的世界遗产研究案例是匈牙利的霍尔托巴吉(Hortobágy)国家公园、南非和莱索托的马洛蒂-德拉根斯堡(Maloti-Drakensberg)跨国国家公园。
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此阶段的重点是生物文化实践、农业景观及世界遗产对于遗产地变化的管理。预期成果是相关概念和术语草案[25]。这一阶段的世界遗产研究案例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艾恩文化遗址(Cultural Sites of Al Ain)、塞内加尔的萨卢姆河三角洲(Saloum Delta)和中国的红河哈尼水稻梯田(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文化景观。
从“连接实践项目”发现,IUCN 和ICOMOS如要更好地融合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作,需要在工作中进一步考虑3个问题。首先,需解决IUCN和ICOMOS内部以及2个机构之间的体制与实践分歧;第二,提升专家和机构的能力,促进对遗产自然和其价值的整体认知;第三,修订世界遗产治理和管理政策框架和指南[29]。其中一个突出的关键,是要具备制订真正融合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管理规划的能力。
与“连接实践项目”并行运行的另一个项目是“自然-文化/文化-自然之旅”(以下简称“自然文化之旅”)⑤。该项目包括IUCN和ICOMOS领导层的一系列对话和会议。第一次“自然文化之旅”于2016年在美国夏威夷举办的IUCN世界保护大会上举行,第二次则在2017年在印度德里举办的ICOMOS大会和科学研讨会上举行[30],2次会议的成果文件均总结了工作、讨论和思想成果[32-33]。随后,在全球各地的会议上举行了许多这类“旅行风格”的活动。这些自然与文化的对话,从全球层面到国家和地方各级,不断细化、具体化[34]。
2020年10月1 —10日,拟在悉尼举行的第20届ICOMOS大会和科学研讨会(GA2020)将是“自然文化之旅”项目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中,IUCN和ICOMOS将签署一项协议(或备忘录),认可2个组织之间有必要继续合作,在地区、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工作中更好地融合自然与文化。但是,由于全球COVID-19大流行,澳大利亚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国际航线受到限制,何时恢复正常无法确定,这一重要的全球会议已推迟至2023年9月。
4 为什么IUCN和ICOMOS关于自然-文化的合作工作是重要的?
我认为有2个主要的原因(虽然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西方思想与哲学中自然与文化的分离,对包括原住民在内的非西方的国家和社区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影响。中国学者韩锋提供了很好的案例。韩锋描述了文化景观概念在中国的世界遗产理论和实践领域所遭遇的困境,特别列举了庐山和五台山2个世界遗产例子[10,35]。从本质上讲,两者都是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体系中的“文化遗产”的一种形式),反映的是“景观中的自然与宇宙信仰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35],而不是中国最初申报的“混合遗产”。换言之,将这些世界遗产地提名为(自然与文化分离的)“混合遗产”,其价值核心有悖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这项合作工作强调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分离式管理会导致立法、管理和实践无法在遗产地奏效。以世界遗产地塔斯马尼亚荒野地(Tasmanian Wilderness,澳大利亚)为例,它符合3项文化遗产和4项自然遗产标准,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混合世界遗产[36]。同时,它受到国家或地区级别多种自然和文化立法保护(包括将原住民与“历史”或非原住民文化遗产聚居地的分离式保护),其中包括《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1999)》(Commonwealt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塔斯马尼亚州的法律如《自然保护法(2002)》(Nature Conservation Act)、《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管理法(2002)》(National Parks and Reserves Management Act)、《历史文化遗产法(1995)》(Historic Cultural Heritage Act)和《原住民遗产法(1995)》(Aboriginal Heritage Act)。理想情况下,《塔斯马尼亚荒野地世界遗产管理规划》(the Tasmanian Wilderness World Heritage Area Management Plan)应将其文化和自然价值进行整合性规划[37]。但是,跟许多此类规划一样,即便规划将此遗产地称为“杰出的土著文化景观”,规划中的文化与自然价值管理仍是分离的[37]。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呼吁抵制“荒野”一词,“荒野”一词的意思是“空无一物”(empty),歪曲诋毁了塔斯马尼亚超过40 000年的土著居住史[38]。因此,在当前的立法和管理上,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保护仍然是分离的。对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紧密相互关系的认知,无论在管理分类上,还是在西方文化与土著宇宙观之间的重大差异认知上,我们都知之甚少[39]。
5 现在往哪里走?
自2013年以来,IUCN和ICOMOS合作开展的融合自然与文化工作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果,并且影响越来越广泛。但是,包括世界遗产和大多数保护区系统在内的西方体系,制定真正能融合自然和文化的管理规划和治理体系的能力仍然不足。对自然-文化遗产价值进行整体性评估并以此作为管理行动的基础意味着什么?全面融合自然与文化的管理规划有哪些模式?现有的管理文件是否真正地融合了自然和文化,而不是仅将它们集结起来归置于一个文件之中?此类工作对西方国家始终是一个挑战。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的领导者来自那些自然与文化未被或至少没有被严重分离的地区。我建议原住民社区、地方社区,以及他们的知识、经验、语言和世界观,应该在进一步推进“自然文化之旅”工作中占有核心地位。
最后,回到我的澳大利亚乡村住所,我热衷于从事这样的工作——为我的乡村制定管理规划,将文化和自然的属性、价值以及保护行动相互关联起来。
注:本文是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写作的。疫情有着一个显著的“积极”方面,那就是全球空气质量的改善、碳排放的减少,以及为这些世界遗产,无论是文化、文化景观、自然还是混合遗产提供了“喘息空间”,这些遗产地通常都有大量的游客。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CROM)准备了题为《COVID-19——ICCROM关于保护遗产的呼吁》的宣言(COVID-19:Call of ICCROM for Protecting Heritage)[40]。该宣言呼吁遗产工作者齐心协力,寻找利用遗产作为后COVID-19时代恢复社会与增强韧性的方法。对我而言,这包括运用文化景观方法,整体保护文化和自然价值。
注释:
①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这一复合词来定义人类、非人类、超越人类(例如精神、创世祖先)的要素和景观是紧密关联的(即一体或相互作用的);而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一词的含义是自然和文化是对立与分割的2个领域。
② 译者注:Ngunawal、Gungungurra和Yuin语言群体为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土著聚落。
③ 此工作小组于2009年成为IUCN 永久“专家小组”(Specialist Group)。
④ 第四阶段正在计划中。
⑤ “自然-文化之旅”(Nature-Culture Journey,NCJ)常用于IUCN作为该项目领导组织时,而“文化-自然之旅”(Culture-Nature Journey,CNJ)用于ICOMOS作为该项目领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