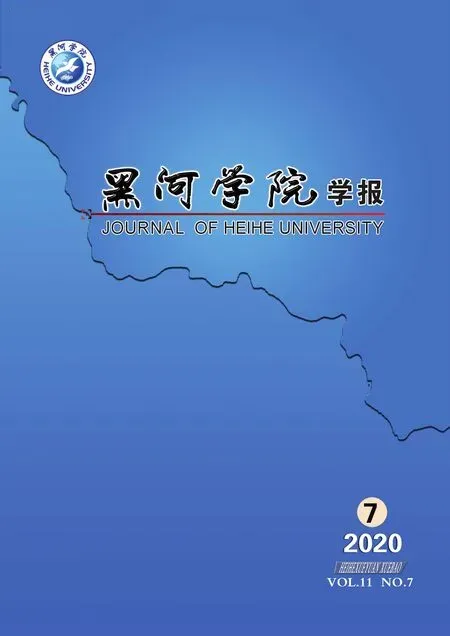1928年黑龙江人民反对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
2020-01-18佟银霞赵悦辰
佟银霞 赵悦辰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1928年5月,日本乘济南事变东北军撤退的机会,迫使张作霖同意延长吉敦线,关于此事外间很少知道。但10月报纸传出日本与中方将于双十节签定正式条款。这一消息传出后,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爆发了反对日本修建吉会铁路的斗争。其中哈尔滨各社会团体率先“电请奉方恳请解约”[1],反对吉会铁路的修建,并由初期的请愿运动发展到流血事件,引发了东北三省及全国援助东省保路运动的浪潮。虽然当时报刊对此事件进行了多方报道,但由于此间中国政局动荡,再加上日本政治势力强大,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黑龙江人民为抗路斗争而做出的努力。
一、黑龙江人民奋起反对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
1928年l0月11日,哈尔滨各团体,如地方自治协进分会、滨江自治励进会、自治协进支会、县农会、教育会、教育局、实业局财务处联名转电张学良反对延长吉敦线修建吉会铁路[2]。据说哈尔滨各团体的这一行动是受吉林省各团体的委托,但通过电文也可以看出,哈尔滨并非和吉会铁路毫无关系。在电文中哈尔滨各团体指出:“吉敦线如延长到会宁,其东面将和拥有清津等大港的朝鲜铁路相连,不仅吉林省的富源,即中满、北满货物亦必通过奉海、洮昂,打通各线被吸收过去,同时中东铁路亦将成为培养线,从而使得北满工商业中心哈尔滨受其掣肘而萧条下去。”[3]接着东三省各地各团体为此事“先后去电力争”[1]。随着事态的发展,哈尔滨基本上还是很平稳的。1928年11月1日,哈尔滨自治协进会、教育会等十余团体为反日筑路保持国权起见,在道外教育会开小组会议,成立抗路联合会。11月3日,哈尔滨各团体各学校在哈尔滨总商会开市民抗路联合会,除通电国府及东三省当局外,拟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游行[4],并就如何开展运动进行协商。11月4日,他们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表示坚决反对借日资修建铁路[5]338。同日哈尔滨市初中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召开会议,成立哈尔滨学生保持路权联合会[1]。决定在三日之内举行反对修建吉会铁路的游行和演说[5]338。11月5日来自各校学生约6 000人举行示威运动[4]。
除学生运动外,黑龙江各界深表同情,成立绅商学工联合会[6]。同时,农工商各界组织黑龙江路权自主会,“以期唤起共同奋斗,结果促成市民大会两次,接连游行示威,民众每次参加少者四五千人。”[7]但黑龙江地处边远,所有下情苦难上达,黑龙江路权自主会特派遣于成泽偕东省旅京同志代表到中央党部向政治会议请愿,并议决保持路权办法及应付外交方策[8]。可见,在反对修建吉会铁路斗争初期,哈尔滨主要采取请愿的方式,因此,东北当局对哈尔滨的护路运动没有采取长春、吉林那样的镇压措施。那么为何哈尔滨的护路运动没有长春、吉林那样激烈呢?①关于吉林省人民反对日本修建吉会铁路的斗争,参见佟银霞的《1928年吉林人民反对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主要是历史条件及地理条件使哈尔滨成为一座国际开放城市。哈尔滨之所以能在较快的时间内,由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变为“商贾云集,车水马龙”[9]的城市,肇始于中东铁路的修建。据1930年调查,哈尔滨市内的各国商号共有2 087家,其中华商937家,俄商674家,日商264家,德商65家,英商63家,美商31家,法商22家,其他国家31家。②傅恩龄.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下册)[M].南开中学自印,1931:405。中国商号数量虽多,但多为门市零售,日英美德法等国均以批发为营业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哈尔滨的商业市场。商业的发展使哈尔滨成为一个国际开放的城市。
这种国际性与开放性使哈尔滨民众对外国文化及外国势力习以为常,没有过于激烈的排日行为。虽说哈尔滨属于吉林省管辖,但占市区主要部分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归东省特区管辖,实际上处于吉林省管辖之外。由于来自原沙俄的侨民较多,所以,东北当局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措施。与此同时,由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哈尔滨的工商资本家对俄国势力采取了接纳、认同的态度,并将这种态度作为促进地方发展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使本地没有排外主义倾向,反而产生了如何发展当地经济的地方主义思想[10]469。
此外,从当时来看,哈尔滨独立于奉系军阀,形成自有的地方经济,这点使本地势力派无意支持张学良政权。张作霖所任命的东省特区长官张焕相自1926年1月上任以来,积极推进特区内主权的回收。从张焕相的角度来看,借日资修铁路意味着主权的进一步丧失,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另据资料显示,张焕相和东省铁路督办吕荣寰关系不和,据说张焕相企图利用学生运动排挤吕荣寰,所以,相对于吕对学生的冷淡态度,张采取了相当同情的态度[11]170。然而张焕相的做法却招致张作相的不满,哈尔滨的学生运动最终遭到了吉林省警宪的镇压。
二、抗路运动引发流血事件
1928年11月9日,哈尔滨学生2 000余名再次进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特区外沿的关卡时,遭到50名滨江县警察及30名陆军士兵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导致学生中有8人重伤,数百人轻伤。对于死伤人数,哈尔滨9日晚通信报道如下,受轻伤者有数十人,受重伤者数人[12]。《黑龙江历史大事记》称,学生受重伤8人,轻伤140人,有43人住院治疗。①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黑龙江党史资料(第5辑)[G].1986:148 。但张学良电京报告情形中指出无人员伤亡情况,受伤者均系磕跌所致[13]。
从以上报道中,可以想象到赤手空拳的爱国青年和荷枪实弹的军警肉搏的惨状[12]。同时,也可以看到当局对学生实施了镇压,虽然张学良进行了辩解。而实施镇压的应该是接受了张作相的命令才实施的。因为在该事件发生之前,张作相就指示采取强硬的方针,当时滨江镇守使丁超数日前便往返吉林,接受张作相的指示,事件发生当天早上刚刚返回哈尔滨。
另据报道,11月9日哈尔滨事件发生时,特区行政长官张焕相,道外警厅长高舜臣等均到,意在劝导学生仍各回校,并向道外警察长官表示请其不为过[4]。滨江道道尹也于10日晚遵照张作相的指示,回到哈尔滨宣布对学生运动采取一律镇压的措施[11]171。哈埠特区教育厅更发出通电,“禁止教职员学生等参加各项运动,……并下令将学生联合会、教职员会即日解散”[14]。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张焕相因“事前整顿不严,事后督战不力”[15]遭到罢免,但吉林省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却受到全国的非难。
三、各界声援黑龙江人民的抗路运动
惨案发生以后,东北各界爱国同胞纷纷声援哈尔滨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出现了“援助东省保路运动”的声浪[16]。如《红旗》报刊认为,该运动实与“五四运动”先后辉映[17]。《江苏党声》一方面誓死为哈尔滨殉难烈士复仇,做东三省革命民众的后盾;一方面请求撤去张学良的国府委员职务,由中央直接与日本交涉,誓死力争东三省路权及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12]。黑龙江市民组织黑龙江东三省路权自主会。教育界中学生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4]拜泉县保持路权后援会提出了“收回一切利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发出“中国统一万岁”的呼声。②黑龙江省拜泉县保持路权后援会宣言[Z].辽宁省档案馆:JC10-1734。长春、吉林、奉天等各地民众对于抗路运动“誓非达到目的不止。”[14]东三省旅沪学生呈中央政府请保路权以救国文[18]。京沪北平各地党部及旅京沪北平各地东省同乡,“亦皆愤起声援。”[14]有的还为此间民潮作诗,“城火池鱼祸已连,国棋步步让人先,呼声惊破倭奴梦,壮气冲开辽水天,豆满江头争筑路,长白山上倡民权,徒薪曲突谁云拙,鸣鼓群攻策完全。”[19]
在全国舆论压力面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一方面下令对此事进行调查,并派人看望受伤的学生,提供了1000元的治疗费用[5]338。同时接受了代表提出的四则要求:一惩办凶手;二赔偿损失;三保证以后不发生同样事情;四准许学联成立,保障爱国运动。
11月13日,东北当局撤换了东北特别区长官张焕相,由张景惠接替。24日,滨江县知事李科元、滨江警察厅长高齐栋各予记过一次。③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黑龙江党史资料(第5辑)[G].1986:148。另一方面,在事件发生之后,张学良在全国的非难声和责问声中拼命地为自己辩护说:“警官只是放了空枪,未出现死者,对于伤者的医治也在进行中。”[11]170当日本会晤张学良提出吉会路问题,为避难就易起见,张亦表示非其职权所及者,无由过问[20]。但严行拒绝并否认与日本签订了局部协定。吉林司令官张作相在对各中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训话中指出,绝对尊重民意,合官民全力自行建筑。”吉林交涉员钟毓氏表示,“吉会签字决不由吉负责。”[21]当然张学良的这些举动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保持派系之间的平衡和争取民众拥护都是必要的。但奉军官兵镇压学生运动所造成的流血事件对他的形象是极大的打击。
总之,1928年黑龙江人民反对日本修建吉会铁路的运动虽然由初期的请愿运动发展到流血事件,但引发了东北三省及全国援助东省保路运动的浪潮,展现了东北人民抗路运动的决心。此间黑龙江人民的抗路运动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与一般此类运动相同,范围广,参加阶层多,如抗路斗争从黑龙江、吉林扩展到东北其他各地,乃至北平等邻近地区。除学生外,其他各阶层民众及团体也加入保路运动中,出现了抗路联合会、路权保持会、路权自主会、路政自主会、路权后援会、市民抗路联合会等各种组织。
二是外界支持不大。哈尔滨民众为争路权举行示威运动,并酿成惨案。但后来除上海下级党部,东三省留沪学生、杭州党部、首都学总会打几个放空枪似的通电外,也就无声了[22]。对此,时人评价:“最近日本政府以恫吓手段,向张学良要求吉会长大两路修筑权,引起民众重大反抗,致酿流血惨剧,南中人士,方歌舞升平,殊少注意。”[23]
三是此次抗路示威运动,只有多数的学生与一部分商人参加。所以,只有号召更广大的工农群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保障。”[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