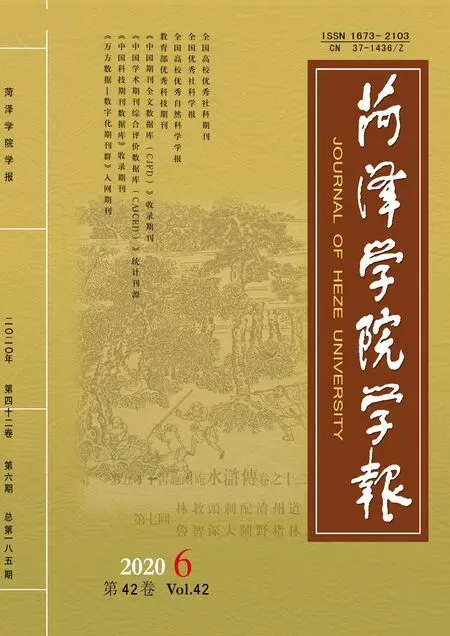再现文本景观:水浒文化与近代鲁西南乡村社会*
2020-01-18李庆华
李庆华
(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菏泽274015)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人们共同享用和共同学习的风俗、信仰、价值及全部创造的总和,即是一个国家或地域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东西。一种文化产生后,也形塑着地域社会,给一个地域社会提供材料与蓝图,能够解释一个社会的全部价值观和规范体系,让人们有了行为标准,并通过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信仰信念和社会舆论等手段实施社会控制。《水浒传》主要描述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占据山东西南部一带,“替天行道”对抗朝廷,后被宋王朝招安,受朝廷驱策,征讨辽国、王庆、田虎和方腊,最终大部战死疆场,主要人物死于非命的故事。这本来是一部演义小说,和历史上真实的宋江起义经过真相相差甚远,但由于《水浒传》的广泛流传,历史真实反而被小说中建构的故事所遮蔽。《水浒传》描述的许多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现象都传承到了近代,近代鲁西南的社会环境、社会控制、民众的应对和心理机制等和《水浒传》描述的有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近代鲁西南地区诸多方面和《水浒传》描述的相似性考察,探究水浒文化对近代鲁西南社会的影响,旨在考察近代山东西南部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为理解近代鲁西南社会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黄河决口与地方变乱:地理环境的相似性
无论是北宋还是近代,鲁西南都曾遭罹黄河决口之害。晋开辽初年(944年),黄河在滑州(旧滑县)决口,“侵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著名的梁山泺就此形成。北宋时期,黄河又二次决口注入梁山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滑州之河复决,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泺”[1]。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发生第三次大改道,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2],这时水泊湖面宽广,号称“八百里蓼儿洼”。“政和中(1111-1117年),剧贼宋江结寨于此”[3]。这就是《水浒传》中所描述的宋江起义军的根据地在现实社会中的原型。
1855年黄河决口于河南铜瓦厢,这是黄河第六次大改道,当时汪洋泛滥,巨浸滔天,自菏泽、濮州以下,东阿、寿张以上各地俱被淹没,当黄河初行山东之时,既无固定河道,也无明确的流向,到处泛滥,四野漫流。根据董龙凯的统计,山东西部自咸丰五年至同治十三年20年间,仅咸丰十一年没有出现被灾记录,其余各年或多或少皆有灾情发生。其中鲁西南菏泽、濮州、范县、寿张、阳谷、郓城、东平、曹县、单县、定陶、城武、金乡、嘉祥、鱼台、济宁、汶上、巨野17州县为河水漫流州县,鲁西东阿、聊城、茌平、博平、清平、观城等为非漫流州县[4]。滔滔黄水在平原漫流无阻,生活于其中的百姓生活之惨可想而知。
黄河决口前,黄河为鲁西南平原一道天然屏障,太平天国军和捻军几次欲过黄河北上,均为黄河所阻。决口后,黄河天险尽失,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捻军乘机北上,进入山东,攻城拔寨,连续攻克鲁西南数个州县。在外部势力的阑入下, 本地“土匪”乘势而起,配合了太平军和捻军的行动。“会粤贼由丰工渡河,飘忽驰骋。连陷金、巨、郓、谷、莘、冠六县。……同时土匪樊拷得、王三托盘嘴众六七百,纷扰郓、濮。土匪解广业等众二、三百,纵横巨野。土匪耿新等驰突东阿。土匪李三杠子、王五胳膊、魏大汉等蹂躏阳谷,土匪陶三相、王方云、杨二帽缨、张广居、马心宽等,乘乱踞金乡”。[5]此后,每当黄河决口,几乎都有“强壮沦为盗贼”之现象,导致地方动荡不安。
二、乱世与欠度社会控制:历史背景的相似性
《水浒传》中塑造的宋江形象及其故事不能当作历史的真实看待,但历史上的宋江和宋江起义确有其人其事,史书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6],“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 官军数万无敢抗者”[7],宋江在山东西南部梁山泊起义之时,正是宋徽宗统治时期,皇室衰颓腐败,贪图享受,滥用坏人蔡京为宰相,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逼得许多人铤而走险,盗贼四起。而国家采取招安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北宋王朝兵力不足,内地州郡尤为空虚,故社会控制力严重不足。这种社会历史大背景和晚清鲁西南非常相似,近代鲁西南地处直隶、河南、江苏、安徽、山东数省交界处,民风彪悍,官府对此处的统治和影响力相对薄弱,而且自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山东东部由于处于同日本战争的前沿,清廷鉴于朝鲜和辽东军情紧急,故当时将鲁西南曹州镇、兖州镇的军队都征调到了山东东部,及至日军攻占威海,山东巡抚则多次要求曹州镇、兖州镇和济宁州招募兵勇,选拔将领,奔赴前线。河防诸营也先后开拨,以致战后出现了“海防已松,河防吃紧”的局面,山东巡抚要求归复河防营旧制[8]。
而在近代警察制度尚未建立前,军队起着维持治安和安靖地方的作用,鲁西南由于兵力空虚导致盗匪蜂起,汶上县传教士韩·理加略描述了此时鲁西南社会乱象,“大批军队从内地开拔到沿海地区,许多城市和村庄失去了皇帝军队的保护,成为唾手可得的猎物。所谓‘强盗’绝大部分属于贫穷的农民,他们因为90年代的自然灾害基本上倾家荡产了。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抢劫和偷盗成了唯一的生存之路”[9]。
战事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结束后,曹州府、济宁州、兖州府由于征募兵勇较多,被裁士兵返家,更增添了许多不安定因素,山东巡抚李秉衡对此忧心忡忡,“曹、济各属向称盗薮,兼以关内、外所撤营勇半多曹、济无赖之徒,难保不麋集为患。必须重兵震慑,以遏乱萌”[10]。
民国时期,若一地军队撤防,随之而来的则是土匪蜂起,社会秩序丕变。如1918年濮州因“自客岁撤防,土匪乘机披猖,百数成群,到处抢劫”[11]。1918年因“月前张检阅使奉令南征,抽调去一师一混成旅,益觉匪众兵单,不敷分布”,“综计东省现在之匪,兖曹及东临一带不下十余股,共约数万人”。“东省匪患自上年辨兵被遣,毛匪乘机勾结,日渐蔓延。虽经随时分别剿除,迄今未歼灭。昨电请派兵协剿,迄未邀准。不早铲除,恐酿成巨患。本省匪患既深,丰砀邻匪又虞窜入。派重兵至少一个混成旅来东助剿,俾靖匪氛”[12]。由此观之,民国时期军队依旧是地方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军队的撤防会导致地方秩序的失衡。而鲁西由于社会控制欠度,导致社会失序,动乱频仍。
三、筑圩建寨:防御方式的相似性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刻画描写了北宋末年华北农村的一些村寨,为加强防御修筑了城墙和壕沟。如强夺梁山战马的曾头市,三村结盟战梁山的祝家庄、扈家庄和李家庄。《水浒传》曾描述祝家庄的景观:“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山岗,四下一遭阔港。那庄正造在岗上,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墙里四边,都盖窝铺,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13]村庄内部都有一个家境富足,实力雄厚的寨主,掌握着大量的土地、房屋等财富,拥有一支或私人或村庄集体豢养的庄丁,负责护院、看青、防匪等治安工作,寨主在村庄内部是代表全权,对外则是全权代表。小说的叙述虽然不能作为历史的真实看待,但也却反映了北宋时期华北一带村寨的概况。村寨这种防御外敌入侵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进入近代以来,因时局动荡,大江南北各地多修村寨以图防御。尤其是鲁西南一带,地处华北大平原,地势平坦,一马平川,一旦黄河失守,则无险可阻,兵匪更易成患。山东督办团练大臣杜就曾上奏清廷,在山东各州县修筑土圩,“请于省城关厢及各州县地方,一律修筑土圩,共图保护,意在坚壁清野。”[14]很快,受到战乱威胁的鲁西南各县村镇,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经济力量较厚实的村庄相继修起了圩寨。光绪年间《新修菏泽志》中记载了菏泽地方修筑圩寨的缘由、过程和作用。
当时菏泽县下设有69都,“都下有集有寨,夫寨之设也,今无几时矣。咸丰之初,粤匪倡乱,窜扰湖湘,破金陵,蔓延江皖,驰骤兖豫之域,震惊畿辅。贼踪飘忽,昼夜疾驰三百里,势若风雨,兵力不能及。蒙台之间,土匪蜂起。于是方面重臣仿古人坚壁清野之法,条其说檄,行州若县,而州若县之民犹或难之。盖当时富者惜财,贫者惜力,承平日久,惮兴大役,及贼至,民无所逃匿,剮剔割剥之惨,所过糜烂,民情崩裂。既乃愤急合并村落,相地立碉寨,增壁垒,裹粮兴筑,昼夜不少休,于是一州县之地多百余寨,少亦不减数十。其后,贼果无所得食,大困。而天心亦厌乱矣。”[15]显然,为了防御太平军和捻军以及本地土匪的骚扰抢掠,菏泽民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修筑了大量碉寨,当时诸多村庄都以“某寨”为名,菏泽69都下以寨为名的村庄共有103处,如成庄寨,孔楼寨,高村寨,吴店寨等等。这种圩寨从晚清到民国在鲁西各地愈修愈多,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一道景观。如何思源描述过鲁西南曹县一个村寨的例子:“我在青年时代(1912年左右)就亲自看见一个例子,……曹县有个地主朱凯臣,他家朱庄是个寨子。他住在中间一个砖围子里,周围都是他的佃户,此外还有几个‘下庄子’。佃户耕他的地,住他的房子。”[16]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县政建设实验区要求各村高修寨墙,深挖壕沟,做好战备工作,提出“各县于五十户以上村庄各修土寨一座,限于1936年3月1日开工,7月1日完工。”[17]1930—1940年代在鲁西南城武县工作的共产党干部总结出城武北部地理社会状况的四句话,其中之一就有“有村皆有寨”,即是说因土匪猖獗,地方不靖,每村都建有土围子即寨墙用来防御[18]。
在圩寨里面,由于政府对鲁西南地区的鞭长莫及和盗匪活动的猖獗,为了自保,一些富室便以村庄为单位,自发组织起民团或者秘密结社,如“大刀会”“红枪会”等。许多富农大户抗拒缴税,与地方官府形成对抗,不少人还参与了食盐或鸦片走私,并与土匪发生冲突。随着公共秩序的崩溃,武力成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因素,许多问题的解决最终依靠武力而不是法律来解决,整个地方社会呈现出半武力化、准军事化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村寨变成了组织严密、能攻易守的军事堡垒。[19]“村村筑围,庄庄成寨”[20],村庄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村庄内部处于某个富裕家族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一个个像独立的诸侯领地一样的村庄集结起来便构成了山东西南部社会。
施坚雅曾提出一个以村庄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认为一个村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会经历一个从“开放”到“关闭”的“周期”。在一个朝代兴起之时,社会秩序重新建立,商业化随之而来,在行政和商业方面显现出较多的向上流动,这是村庄的“开放”形式。这是一个从“政治”到“经济”“社会”的开放过程。当朝代开始没落,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缩小,骚乱增加,贸易体系受到破坏,村庄也因匪盗及叛乱的高涨而必须设立看青和自卫组织,最后产生武装内向社团,也就是最极度封闭的共同体。于是,“关闭”的过程,就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顺序而进行。[21]鲁西南众多圩寨高挺、深沟水壕环绕的村庄,正呈现出国家处于没落时期的村庄共同体的景观。
四、逼上梁山:应对模式的相似性
《水浒传》中刻画了大量的官逼民反的人物情节,如林冲、杨志、武松等人的遭遇。近代同样有许多个案,如纵横冀、鲁、豫三省的巨匪范明新,《申报》说他是“曹州府人,初为农户,好交游,因受乡董欺诈,愤而为匪”[22]。民国时期,阳谷县境内有宋长胜为代表的义军,“据说,宋传胜是山东郓城县人,是梁山第一把交椅宋江的后人”。他操法精练,枪法娴熟,屡立战功,因和一位依靠裙带关系当上排长的人争连长职位,被人耍诡计愚弄,而该排长当上连长后又滥施淫威,激起士兵反抗,宋长胜击毙该连长,率士兵起义。他爱护百姓,杀富济贫,屡败官兵[23]。这些人在未成为土匪前,很多属于乡村中的“劣势阶层”,或者说是“弱势群体”。他们或者衣食无着,走投无路,或者受到不公平对待,无法申诉。在这种情况下,为混口饭吃,为得到公正待遇,拉杆为匪就成为他们惟一的武器。
鲁西南是水泊梁山的故乡,受梁山好汉影响很深,这里有许多被官方称为“土匪”,但在当地却被称为“义军”或“义民队”的队伍。如民国七年(1918年),刘长久、张四奎、谷德林、白脸王三、梁玉环、油清海等,聚众2万余人,打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帜,揭竿而起。他们“架票”主要以贪官污吏、强室富豪为对象。他们的规矩是:不虐待被架的“票”;不准采花盗柳;不准抢拿东西;不准压迫百姓;委托百姓办事要付给代价。因之在乡民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曾经在1920年黄河决口之时把自己的人马投入黄河护防、抢险之中,历时三个月,险工处均修做了埽坝和护岸,河堤终于化险为夷。此项义举,深得沿河民众人心,咸称他们为“义民队”。但因为请愿时冒犯了大名道道尹,不久他们即被以盗匪的名义遭到镇压[24]。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这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颇具侠义心肠的土匪称为“社会土匪”。他认为:“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25]这些人之所以获得农民阶层的支持,是因为土匪们至少承担了对当地的有限保护责任,发泄了农民对官府王法戒律的无言怨恨。
近代距离《水浒传》成书的年代间隔也有数百年之久,但鲁西乡村的自然与社会景观以及人们的应对举措何以和《水浒传》的描述会有如此多的相似性?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因素值得考量。
首先,自北宋末年至晚清时期,乡村社会结构未发生多大的变动,民众的应对也多是传统应对方式的继续。如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文化,包括一切的风俗、礼教、政法、伦理等,“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26]。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27]显然,自北宋末年至近代,中国广大乡村生产方式上仍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文化的变异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在鲁西南这样一个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们的活动空间比较狭小,社会结构也比较简单,对环境的应对也更多是承继了前人的方式方法。故自北宋末年直到近代,鲁西南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灾变的因应之道和心理机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次,鲁西南乡村受《水浒传》影响很深,水浒文化在鲁西南具有很好的社会化环境。
曹州府民性剽悍,在历史上不乏劫富济贫、落草为寇之先例。而这些草莽英雄的故事在鲁西南得以世代传播,也是土匪亚文化——盗匪文化得到盛行的重要表现。如隋唐演义中的程咬金劫皇纲(程咬金原型人物在今济宁市梁山县的斑鸠店),在河南瓦岗寨起义,其事迹在鲁西南口耳相传;唐末黄巢(菏泽冤句人,在今菏泽市西南)率众8000余人响应王仙芝起义,横行大半个中国,险些推翻唐王朝的统治;徐鸿儒借大乘教在郓城起义,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寿张人王伦领导白莲教起义,爆发在清王朝鼎盛之际,给统治者不小的震动。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更是在鲁西南流播甚广,还有其它如《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侠盗故事的口耳相传。久之,劫杀为富不仁者,与官府对抗成为某些民众心目中“英雄”的象征。乡村崇尚武力、崇拜英雄的文化氛围也是盗匪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根源。
这些演艺小说人物评价的尺度标准显然和官方尺度有很大的差距。如按照演艺中的叙述,秦琼本是一名捕快,却和北方各路的重要盗匪头目都有交情,并私自放走了抢劫皇杠的盗匪,最后落草为寇。如此一个县衙捕快,和黑社会相勾结,在正统观念中应是一个典型的“吏役中的败类”,但在民间传说和《说唐》中,秦琼却被赞誉为“赛专诸、似孟尝”的“江湖大侠”。宋江,按《水浒》中所塑造的形象,也是郓城县的一个刀笔小吏(押司),私下给抢劫“生辰纲”的盗匪通风报信,本该受到谴责,但被江湖人士誉为“及时雨”。这些民间传说和小说所宣扬的是不同于官方正统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一种绿林亚文化。这种越轨亚文化对形塑底层国人的性格、行为方式具有很大作用。“20世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扶危助困、轻视钱财的‘及时雨’宋江。因为文字和印刷把一种地区和口头流传的方式固化成了一个民族的永久流传的模式。”[28]傅斯年在描述鲁西地区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时,即指出“义和团是水浒、封神演义、包公案、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书中的人生观化合成的宗教。”[29]这几部书都对江湖侠义道称颂赞美,对一些武艺超群、杀富济贫、为朋友两勒插刀之江湖人士予以褒扬,显然鲁西南底层民众更多受到这方面思想熏陶。
以上几部书中的人物如程咬金、宋江、黄天霸等绿林好汉都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最后接受朝廷招安,博得封妻荫子的结局等诸如此类的情节。这对于民间社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许多民众也是迫于无奈最后走上反叛的道路,心中也不想一生为盗为匪,而是幻想着有朝一日接受招安,获得荣华富贵,“想当官,杀人放火等招安”是这些人的心理。
除演艺小说外,民间戏剧也有不少以这样的侠义英雄为题材。而乡民们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更多来自于闲暇时节听老人“说大书”,民间俗称为“拉呱”。一些老人把自己从前辈听到的故事通过拉呱(口耳相传)的方式传给下一辈。在这些故事中,都习惯于“对造反者予以讴歌与赞美”。青年人受说书唱戏所传播的文化熏陶,崇尚的是游荡江湖、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对为富不仁、贪财好利之人则充满鄙夷。他们接受的思想资源除了宗法的、宗族的儒家思想观念外,就是这种“侠盗”思想资源。当灾荒和社会动乱到来,生活无有着落,传统的宗族思想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时“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就会被利用来改造自己的命运。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近代鲁西南深受《水浒传》中这种越轨亚文化影响,在自然环境、圩寨修建等物质文化层面和《水浒传》的描述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在社会历史背景、地方人士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道德、习俗、行事方式上也具有文化的传递性。但不等于说鲁西南只受到水浒叛乱文化的影响,其实《水浒传》展现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讲求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对鲁西南民众影响也很深远(当然鲁西南民众接受忠孝节义思想也非完全通过《水浒传》这条途径)。但当鲁西南乡村面临着灾荒和变乱,生活无以为继之时,水浒文化中的叛乱思想就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但显然这种文化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反而使社会运行发生严重的障碍、离轨和失控,使得整个鲁西南社会处于重度社会失范状态。
注释:
本文所指的鲁西南,主要指今天山东的菏泽市、济宁市所辖各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