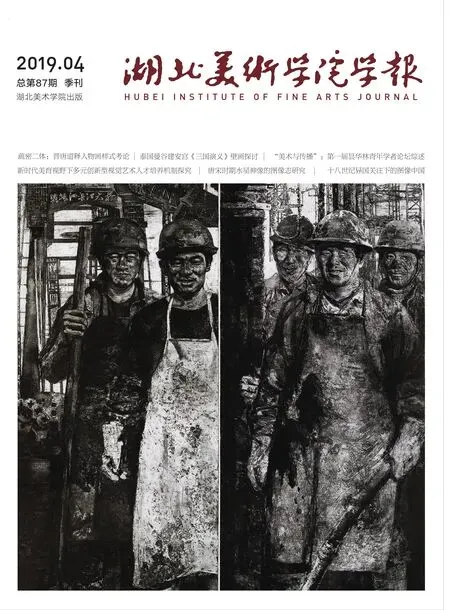十八世纪异国关注下的图像中国
2020-01-18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赵阳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 赵阳
经由洛可可艺术风格所展示的中国世界,是奇异的中国,是魅惑的中国,是西方眼见的中国,然而却已不再具有中国的本质与真实。中国风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脉络之中,从来都不是重要的艺术流派,但却在奇妙的混杂与交融中,揭示出西方艺术的真实本质,成为西方知识的建构参照。本文运用视觉文化再现论述,分析洛可可中国风作品的生成脉络与关键性的交流关系,以及其所涉及的知识建构及欲望累进。
一、中西交互观看下的他者再现图像
中国相对于雄辩的欧洲,是沉默的。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身份形塑在当代文化研究论述中多有批判。首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认为,他者与自我之见的二元对立形成的差异是意义建构的基础,唯有与他者产生对话,意义才能形成。他者对于自我主体以及性别身份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因此,他者的再现是以自我主体为依归的建构,是具有对照性的指认,也是具有显著性的优越。东方在西方的知识建构与视觉图像中的文化再现是有历史脉络可循。后殖民理论学者扎伊尔德(Edward Said,1935-2003)①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精辟地论证东方图像在西方知识系统自启蒙以来的建构过程,并且指出所谓的东方实际上是建立在西方帝国所建构的主观想象之上[2],东方的概念在本质上已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西方人为建构的身份,是西方所想象的东方,也就是符合西方自我社会本身需要的他者幻象。
对于中国明清历史从事深入研究的西方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提到,即使中西交流频繁,中国依旧没有被全面构建于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之中,而仍是西方主体对比差异之下的他者,他者身份之成立是西方主体因自我建构所需,进而利用中西之间文化差异来区分我与他的疆界。根据以上的梳理脉络,他者再现的论述除了建构主体性,此自我—他者、阳性—阴性、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是以简化的方式在观看差异的复杂性。正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曾质疑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也都将价值判断、权力、优越、欲望等概念一并编码进去。[3]因此,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之于主体建构便成为了一种表征性的实践,在二元对立之下的一系列特征不仅是被当作分类和评价体系而存在,并且是作为生产机制,以确保主体内容上的单纯与形式上的可见性,依此,主体的中心地位便得以确认。[4]他者身份的建构涉及主体性与权力关系运作,东方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反映出西方在形象、概念、性格与经验上的殊异与优越。
德国知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除了从事古今中国研究与中西文化比较之外,亦深入分析欧洲文化之下的异乡、异地、异国情调等与他者相关概念的形成,并且经由将异的概念与女性他者做连结,以说明在西方的男性本位意识中,东方是异国女性的象征,是西方男性自我原始欲望的企图。因此,在西方的知识建构之中,他者的存有对于西方主体自我的建构与辨证是有其关键性。据此,关于他者的论题也就被提出:在西方的知识论述构成中,他者究竟是在怎样的时空背景历史进程之下所形成的异己,他者如何转化成欲望的对象,或者,这个欲望对象其实是自我意识的反射。以下就十八世纪中国之于法国所代表的他者性与异质性,论证在文化再现上与艺术表现上,法国艺术家进行中国风设计创作所展现的审美意识与文化精神,是由西方知识系统与视觉政体(scopic regime)②规范之下的典型化的异国风情,并且是在西方审美品味与社会型态之中所陶冶出的西方化的中国趣味。
(一)典型化的异国风情
中国风设计作品在法国洛可可艺术审美与启蒙思潮的引领之下,于视觉艺术中传达西方对于他者文明的印象与投射,并且反映法国洛可可社会与文化特征。欧洲社会对于异国风情(exoticism)的关注及再现与西方主体建构有本质上的连结。西方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并非指涉实质存在的西方社会,而是指向建构西方社会的本质,它提供了认知与言说的方法,也就是建构出一套知识系统以供使用。[5]在西方自我本位的评断之下,西方之外他者文化的意义与位阶便是由西方所决定,而他者文化的再现是透过他者论述所生产的知识与意义,所谓他者论述即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所有涉及他者意义建构与行为实践的一组论述。[6]自我主体为了与不相属于自我范畴内的他者划清界线,经由命名、归类等论述方式,区分自我与他者之不同。
十七世纪时欧洲便出现了一种知识型(episteme)变化,也就是一种认识论的变化──人可以在所处的世界中看见自己。十七世纪中叶,认识与整合世界的方式已脱离类似性原理,而是以知识建立起一套同一性(identity)与差异性(difference)的观看视野。[7]在这其中,即可发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错辩证以及权力关系。十八世纪洛可可法国流通的中国风艺术创作,欲呈显的异国情怀所具有的典型化特征,可经由标志性与模板系统两条进路加以分析。也就是,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1-1770)画作中所运用的具有象征意涵的中国标志,以及彼勒蒙的设计作品中具有趣味性质的中国人物和对象模板。
布歇画中的中国人物都具有鲜明典型特征,看似中国但又不是中国,不是中国所能指认的中国,但却是西方所明确再现的符号中国。也就是说,此典型化的中国人物外观不尽然是真实中国于审美凝结后的造型,而是西方以自我为主体为他者所建构的样貌。综观布歇所绘的中国风作品,虽然运用的媒材广泛,但是,在主题或是造形选择上,却重复性很高,人物形塑出鲜明的典型化的形貌,如瘦脸、杏眼,男人光头结辫,留有八字胡,头戴草帽,女人梳着发髻,衣着交领宽袖的华丽衣物。[8]根据台北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明(1940-)在《自壁毯图绘考察中国风貌在十八世纪法国艺术中的发展》文中的资料归纳,布歇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呈现出以下十二种具有约定性、象征性中国的标志:
1. 八字胡
2. 草帽
3. 遮阳伞
4. 宝塔、浮屠
5. 凉廊
6. 祭台与宝座的华盖
7. 香炉
8. 瓷人
9. 瓷皿、瓷瓶
10. 人力车
11. 椰子树
12. 珍禽蟠龙
这十二项典型化的内容映照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且这些标志性对象所拼凑出的景致总像是一幅描绘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气候下的奇异人物,展示雍容华贵之姿态并且欢乐地从事户外活动的图画。根据布歇于1743 年绘制的底图所制作的中国挂毯系列,共计六件作品,皆可见以上所列之典型化标示对象。如《中国市集》画面背景除了绘有中国宝塔,还有一棵巨大且枝叶繁茂的椰子树,树前设有华盖顶的宝座,坐上有位中国官员与随从,脸上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那两撇八字胡,画面中心焦点是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衣着华丽且手持团扇,端坐于由车夫所拉的人力车内,似乎正专心观看这热闹的市集景象,市集内人潮聚集,似乎也在观看这位美丽女子所构成的愉悦风景,画面周围罗列一些瓷制器皿,洋洋洒洒,热闹喧嚣,观者于此画中可感知是美好富足的中国视界(图1)。事实上,这些简化之后的典型并不是为了在视觉上再现真实样貌,而是为了异化他者,利用艺术手法将他者的殊异具体标示以彰显我与他之别。
以上所罗列之十二项典型标志,对于西方人而言,象征中国也代表中国的人、事、物,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内容所展现的是非常局限且极为片面的中国样貌,甚至是扭曲了的中国印象。法国洛可可艺术盛行的中国风在名称上虽然清楚地标示中国,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却与真正的中国艺术差距甚远。中国风在艺术风格上展现的,实际上应该是法国十八世纪的社会现象与时代品味,并且是服膺于西方艺术审美与文化架构下的西方化的中国趣味。
(二)西方化的中国趣味
虽然布歇的洛可可风格作品在当时十八世纪法国画坛蔚为风尚并形成时代风格,但是在当时重要的启蒙学者兼艺评家狄德罗批评他画中的低俗情欲以及虚假荒谬之后,布歇的作品便被认为道德沦丧所以艺术价值不高而缺乏该有的重视。法国艺评家巩固尔兄弟在十九世纪时重新评估了布歇于十八世纪装饰艺术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布歇中国风的画作是将中国转化为法国洛可可范畴中的一种艺术表现。也就是说,经由高超的描绘技巧以及精巧的画面营造,布歇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是符合西方艺术标准的,即使是以西方之外的异国为描绘主题,画面中所展现出的整体风格是西方的,而当中的趣味也是应合了西方人的观看欲望。
艺术史学者霍纳尔在研究洛可可中国风后,也认为布歇的中国风的壁毯作品基本上是欧洲风格的诠释。无论从空间表现,人物图像还是从画面背景来看,布歇的画作都具有典型的挪用与融洽东方意象的痕迹。艺术史学者在研究中国风作品中的西方化趣味时,也注意到布歇与华多画作中西方审美意趣与中国图像符号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布歇力求用形象表现的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他想象的中国,他以精湛的技艺将西方场景改头换面,使之富于亚洲风情。
他的《中国庭园》(见图2)是幅游乐图,其中瓦托(Watteau)(华多)的影响超过了种族特色。
仔细观察,布歇画中的异域色彩,来自几个容易捕捉的细节:像直柄团扇、光滑的头顶、盘紧的发髻。但是,那位抱着棕榈枝欣赏美人对镜梳妆的中国青年,是华多游乐图中常见的人物,只不过是东方化了而已。[9]
Ellen G. Landau 对于布歇作品的研究指出,1743 年的中国挂毯系列(Chinese Hangings)呈现出六个东方场景:宴会(a repast)、市集(a fair)、舞会(a dance)、渔钓(a fishing party)、打猎(a hunt)、梳妆(a toilet),虽然是描绘中国的活动景象,但却类似于欧洲的田园风格的牧歌场景。十七世纪法国迷恋中国事物的风尚于布歇的中国风作品中得以窥见,他的创作灵感可能是取材自为乾隆皇帝服务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作品,但是他按照当时法国社会的审美品味于作品中表达的异国想象氛围却是显而易见的。

图1 中国市集 1750 布歇

图2 中国庭园 1742 布歇
如同霍纳尔于其研究中所判准的,中国风设计是西方艺术风格的产物。因此,基本上,欧洲中国风设计的特点在于,为了适应欧洲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背景,对于欧洲的传统艺术风格以及审美趣味加以借鉴并挪用,企图在西方艺术作品上营造出时代氛围之下的异国风情与中国趣味。
十八世纪洛可可的中国风设计除了经由典型化的标示符号堆栈出异国风情之外,亦表达西方化的中国趣味,此中国趣味乃是西方审美意识下的产物,于艺术造型与内容上,皆符合西方古典艺术规范与洛可可时代品味。剖析中国风作品中西方审美的中国趣味可由画面构成与画作内涵两个层面审视,于画面构成中,展示舞台(theater)、野宴(fete galante),此两类地点;于画作内涵上,表达殷勤得体(courtesy)、情色欲望(desire),此两种的西方文化精神。
无论是舞台构成或是野宴场景,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画作都不免表现出十八世纪法国的文化精神与时代情感之中所蕴含的殷勤得体与情色欲望。十八世纪法国社会强调行为举止上的得体(decorum),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由强烈的社会道德所束缚,男性对女性的殷勤与礼节有规范可循。

图3 中国情侣 1742 布歇
就此而论,在对待女性的议题上,西方男性认为男性对于女性表现出殷勤有礼是文明高尚的社会行为,以此有别于野蛮国家。因此,为表现教养与风度,男性与女性交往时,应表现出绅士风度与殷勤的态度。因此,在华多与布歇的画作中时常表现出十八世纪洛可可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态度上的殷勤得体,以及求爱时展现出露骨的情色欲望。布歇于1742 年创作的《中国情侣》(The Chinese Lover)(图3)便描绘了一对中国男女有如巴黎贵族般的互动姿态,尤其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殷勤有礼的举止,女性对于男性的亲吻手背的情感响应,将女性的尊贵与优雅尽现眼底,此男女间交际的礼仪与合宜都是典型法国生活的反映,即便是运用艺术巧思将中国符码错置在中国的刻意营造之中,观者仍旧可以察觉出中西交融的异国情趣,且辨识出根植于欧洲社会文化建构的精神本质。
相较于中国仕女形象趋于静态的意象表达,对女性的欣赏与仰慕所形塑出的冰清玉洁与高贵典雅③,西方艺术自古以来画面中的女性形象,从夏娃、维纳斯、圣母玛利亚到尊贵的女王和女伯爵等,与时更迭,透过知识建构、意象形塑与性幻象等作用,持续不断地呼应着男性欲望且影响着男性对于女性亦步亦趋的渴求。如此西方本位式的、男性中心式的建构,造成女性形象既遥远又那样地令人渴望、引人遐思,近乎幻象般的媚惑[10]。在西方的观看标准之下,布歇画中的中国女人是具诱惑力的,因为她们代表了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看之下,产生幻想的对象,以及投射理想的所在。如同德国学家顾彬析论西方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异”,他认为在西方,“男人代表着一种秩序,一种纪律,他们根本无法享受自由,有时甚至自我压迫。对男人来说,女人是处于他们的世界之外,女人是美丽和自由的象征,代表一种还没有被异化的生活”[11]。因此,女人是男人所欲求的自由及其欲望,而异国女性则更是西方男人所渴慕的自然及其媚惑。
二、中西彼此交融下的阴性特质展现
中国风设计的系列作品作为视觉再现形式,可视为制造中国的主要元素,或西方文化将理想主义和异国情调附加在中国文化之上,并藉此将中国确立为他者的手段。为辨认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在西方再现系统中,“白”是属于主要类别,“黑”有别于“白”,则是归属于其他。依此推论,在西方中心的思维与想象之下,西方白种人是具有雄性特质的自我,而东方之下的中国是具有阴性特质的他者。然而,十八世纪洛可可艺术的表征却是偏向阴性质地的,此阴柔的特征或许是出自于对雄壮巴洛克风格的翻转与替代,但是,最终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十八世纪法国社会中贵族女性的关键地位与中国思想的启发结果。
(一)洛可可艺术的女性赞助者以及沙龙文化
西方艺术史学者们在分析中国风设计作品时,认为十八世纪法国洛可可艺术所表现出的女性化特质与中国印象的阴性质地相呼应。于是,中西相互交融,在风格上混杂且融变成为特殊的设计风格,以展现当时法国社会对阴性气质的标举与对异国情调的时尚追求。
因为法国特有的情妇政治与沙龙文化,十八世纪法国贵族与菁英女性们的形象包覆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光环,并拥有足以与男性匹配的甚或凌驾于之上的社会地位以及知识能力。此时的法国贵族与菁英女性们是有权力的,其力量是足以支配皇室和大众的文艺喜好的,例如,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便是十八世纪最有权力的精英女性,她个人的好恶与偏爱影响时代审美,她个人独特的艺术品味展现在她的服饰装扮、器物使用、赞助事业、收藏陈列等,也就造就了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艺术品味。
根据 Sheriff 与其他西方艺术史学者的论述,或许蓬巴杜夫人的对于知识的喜好仅止于虚浮装饰,但是,对于女性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在画面中是清晰可见,女性的权力经由知识得以提升,且进而力转乾坤,将十八世纪的时代审美品味转向了带有阴性柔美气息的精致与知性。
在西方观点之下,东方是具有阴性特质的异域。东方化身为一名风情万种的异国女子是西方浪漫时期诗歌与散文等所表达的自然浪漫想象,大自然之母(Mother Nature)是西方文艺中常见的阴性象征,因此,饱受文明荼毒所苦而渴求重返自然境地的文艺人士,经由文学艺术创作以歌咏自然的女性温婉与自由,女性东方便是作品中时常被挪用以譬喻阴性的自然质朴与自由奔放。相对于西方自我主体,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表达异国女性的感性与欲望,并象征阳性西方置于二元对立之下的阴性特质。当检阅西方文学与艺术作品中,作家及艺术家对于西方域外的东方或是中国的描述,不仅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遥远的存在,并且是静态的、凝结的、非时间性的、可再生的与阴柔的。洛可可艺术在风格特点上便带有纤细、娇柔、清雅,并同时具有阴性气质与异国情调,且洛可可艺术风格的主要造型元素中展示的S 形和曲线美,在路易十五时代的艺术家运用之下,专以表现女神与宫廷贵妇的阴柔、典雅与丰腴之美。
洛可可的缀饰风格于当时法王路易十五颓糜奢华的时代氛围下,非常受到欢迎以及重视。伴随启蒙思潮,法国女性精神生活变化最重要的表现是文化与艺术沙龙的繁荣。近代法国的沙龙文化兴起于十七世纪上半叶,在巴黎,才学之士聚集到女才子或是学界名流的客厅里,评论新书、琢磨语言,或鉴赏艺术。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交中心在巴黎,沙龙便是巴黎人社交的中心,而沙龙女主人便化身为巴黎社交圈的焦点人物。
德特罗伊(Jean-Francois de Troy, 1679-1752)于1730 年绘制的油画《阅读莫里哀》(The Reading from Morliere)即展示了十八世纪法国典型的沙龙场景(图4)。此画描绘五女两男的沙龙聚会,人物衣着华丽,展示当时巴黎最时髦的服饰衣着,沙龙内的室内装饰也展现出当时的艺术品味,其中摆设洛可可风格的家具、屏风、壁炉等。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沙龙逐渐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各阶级的汇集场域,傲慢的贵族阶层和富裕的资产阶级在此空间里平等相遇,以礼相待,相互交换意见。沙龙的社会功能首先是文学批评的中心,任何一部想要面世并获得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必须通过沙龙的评比。启蒙时代丰富的知识成果与哲学成就几乎都与沙龙的盛行有密切关联,启蒙文学与思想的巨作几乎都经历过沙龙的启发、评论与传颂,因此,法国的贵妇人与沙龙女主人们在帮助启蒙思想家推广思想改革上有显著贡献。

图4 阅读莫里哀 1728 德特洛伊
沙龙社交生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吸引力,此中,主持沙龙的女主人成为巴黎文人的总指挥,她们以自己的优雅、高贵、殷勤、贤能、智能等质量统治着现实社会等级中高高在上的男人们。由女性主持的沙龙打破教会、学院和政府对于审美情趣的操纵与垄断,自由发表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拥有文艺批评的权利与义务,于此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示着法国思想言论自由的发轫,也引导了沙龙文化的文学、政治发展走向。
沙龙的主持人有时是出身高贵的巴黎名女人,且具有足够的知识以维系沙龙内的对话、引导话题、作出评断。当时几乎每座沙龙都有位特殊知识分子,例如狄德罗之于德毕内夫人(Madame d'Épinay, 1726-1783),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联 1707-1788)之于内克夫人(Madame Necker,1737-1794),伏尔泰之于夏特雷夫人(Madame de Châtelet, 1706-1749)与杜·德芳侯爵夫人(Marquise du Deffand,1697-1780)的沙龙一样。[12]男性知识分子参与沙龙的份量与人数有时几乎超越女性,但主持知识盛宴的仍是沙龙女主人。
因此,在这样一个文化与思想冲击的时代,这些出类拔萃且领导群雄的女性赞助者及其所主导的沙龙文化哺育了启蒙的辉煌,也培育了法国文化的高雅基因,并且使得当时的艺术与文化皆散发出迷人的阴柔质地。
( 二)启蒙思想家对于东方思维的关注与认识
西方文艺理论在探析中西文化本质时,经常采用的文化与自然、阳性与阴性、西方与东方此二元对立策略以凸显文化差异,是建基于以西方社会为基础的认知论之上的文化建构,仍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批判之下所再建构的对照方式。当西方文化面对异质的东方文化,所形成的碰撞与融汇,在哲学思维与文化精神上的回望与反思,转化出的精神意识是更加强化的自我提升与跃越。十八世纪时欧洲启蒙运动将视角扩及全世界[13],其所眼见的视界是全新的发现与全然的差异,欧洲的优越与卑微全都显露在全世界的对显当中。是故,关注他者使得自我文化的优与劣皆更为显著,以求改造与革新,而中国便是当时法国所急欲借鉴的文化范例。
启蒙思想家经由中国,企图整合与改造欧洲,也就是经由中国反思欧洲,振衰起弊。对照政局纷乱的欧洲,中国俨然成为启蒙学者所希望的理想政治社会典范,此由外而来的中国作用激化内在的需求,正如法国社会学者兼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1951-)所说的“一种从域外进行的解构”(une déconstrustion du dehors)[14]。欧洲启蒙学者对于中国的热爱与认识,终究对于自身西方文化的通盘检讨,也就是经由对中国的研究,来坚固西方传统价值,肯定其自我文化。法国启蒙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与取径,以孔子的形象与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孔子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体现了启蒙学者期待通过理性的建设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君主以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的希望,而尊崇孔子思想的中国君主似乎是实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于是,在社会批判与文化改革的复杂心理推演中,孔子在欧洲思想启蒙的洗礼之下被神化了。[15]法国启蒙针对的是思想上的改造与主体性的建构,而中国儒家思想对于国家统治的作用,提供了法国启蒙社会思想改革的沃土。欧洲主体性的自我建构则是藉他者特质的标举,以强化欧洲主体意识本位,也就是面对西方之外的异质文明的冲撞,架起自我防护框架,巩固西方自我本位价值,针对其所需借鉴中国,以建立更强大的西方。
然而,中西文化的本质性差异得以成立,乃经由西方认识论运用二元对立分析中国不同于欧洲的文化特征,因此,当欧洲文化中自我强调的是为阳性特质,便对照出于中国文化的阴性气质。中国的阴性气质的联系除了来自欧洲对于中国人特质的臆测之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强调“天道”与“自然”所形塑出的大自然气质,而西方文化中一贯视大自然为母,所谓Mother Nature 便是西方赋予自然的拟人化形象,西方学者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常以强调自然的母性特质为圭臬,认为女性因其生理上的孕育与滋养的功能,在本质上便比男性更接近自然。[16]于是,女性代表自然,而强调天地自然的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认识之中便呈现出阴性质地。
西方自然建构的阴性趋向使得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偏向阴性,认为中国人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强调与实践皆具体体现在社会文化之中,是与自然亲和且按照自然规律生活的温良人们。实际上,中国文化上具有阴性特质的判断,不单有来自西方的指认,在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也强化了阴性意识。④例如中国美学思想针对“道”的论述是趋向于阴性思维,且“道”在老子心目中是具有阴性特质。因为当老子论“道”,非常强调它是万物之母的属性,老子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且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据此,在中国的老子哲学中,“道”身为万物之母的形象呼应了西方大自然之母的意象。其次,老子论“道”亦强调其柔弱的形象,且当他说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便归结“道”的基本特质为阴性的柔弱。再者,老子给予“道”的正面价值在《道德经》中多有强调,此正面价值的赋予也传达出中国传统美学对于阴性气质的称羡。[17]99-101按此,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的女性多以柔美、纤弱的姿态出现,正是源自于中国思想家与知识分子对于阴柔特质的赞颂与推崇。再者,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神仙风度的向往,亦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对于人体审美与对人物风度气质的重视,其结果形成了中国文人对于男女人体审美的趋同,也就是男性身体倾向阴性化的审美观感。[17]96言而总之,中国传统美学的阴性趋向是根植于哲学思维且凝结于艺术审美之中,相对于西方社会价值与文化精神中张扬的阳性特质,中国所散发的阴性质地便成为西方首要确认的殊异特征,于是,当西方向外援引中国文化与思想,并于视觉图像中再现,沾染阴性特质的他者形象自然显影。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热衷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当时的研究命题之一,即便启蒙思想强调人的理性,中国自然观照的合谐境界,针对当时西方社会的检验亦多有启发。伏尔泰也认为,中国人讲的“天”或“理”,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并且,中国自然审美观照体现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生活经验,在伏尔泰等启蒙学者们眼中,中国哲学相较于西方神学,是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的,是合乎自然的。[18]
与西方理性经验与神学思想为主调的认识论相较之下,中国认识自然是透过直觉体验去掌握自然,张法分析道:
中国古人的认识论可以说是儒家的实用理性和道家的经验直觉的互补。它可以简括为三点:一、是清醒的、理性的,不是宗教迷信,自有一套功能性“逻辑”;二、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直到悟出最精微处;三、在现实中是有效的、有用的、有利的,施之于社会人伦,用之于自然天道,都能见出实际的功效。
由以上推论,可见中国与西方在对于自然的认识有本质上的差异。中国在社会中即可实现自然的作为。
然而,西方却总是把文化与自然对立,人要脱离文明才能够体验自然。启蒙思想中,人的主体性建立凭恃的是与物的对立、与他者的对立,而与人相对立的自然,便是“他者的统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领域、其他的旅行景点”[19]。因此,自然被归列为他者。自然在西方艺术表现中,在此时便描绘出自我相对应于他者所投射出的统驭与征服欲望。由此验证,十八世纪洛可可艺术中的风景画所表达的是个人可欲的、可亲的自然,而中国风作品中的开放景致与自然景观也是西方针对他者异域所铺陈设置的人间乐园。
三、异域凝视下的中国视界
十八世纪法国洛可可艺术中可见的中国视界,是在西方主体建构之中所对显出的他者世界。异国凝视之下所显现的渴慕与欲求都在中国风艺术作品中挥发,其在洛可可艺术沃土中培植出的极致表现,进而影响了尔后西方装饰艺术的动向。观者在面对中国风作品中可直接感受到的是一个异质的、混杂的观看经验,看似中国却又不是中国,看似西方但又指涉中国,唯一可准确析辨的是作品中浓厚的异国风情表达,是来自西方凝视异国的审美趣味。而此审美趣味其来有自,最主要的源头是来自西方自古以来对于神秘东方的臆测与怀想。当审视东方意象于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形塑脉络,可发现西方知识系统建构在地理与文化上,通过标示东方的存在,以确立西方本位意识之下的主体位置。西方认识东方世界的途径,除了经由上古知识档案中对神秘中国乐土的描述之外,自大发现时代开始,通过航运的拓展,西方对于世界有了初步的实质掌握,中西文明之间交相汇集所生的震撼造成知识系统与视觉经验上的扩大与变异,也触发了西方迈向现代的因子。十八世纪法国人眼中的富丽中国,不仅是法国与当时世界各文明相对照之后的事实陈述,也是法国社会体质自我检讨与期许的心理投射,因此,在当时启蒙思潮与洛可可艺术的培育之下,中国经验在思想上与视觉上都呈现出关键性的影响。
法国洛可可艺术承继巴洛克艺术的优美与高雅,然而却在承接欧洲古典审美中出现了轻妙的转折。此转折之所以形成的原因,除了来自于法国社会内部旧势力的脱轨与资产阶级的兴起所引发出革新思想,另外,更重要的是源自探索世界而大开的眼界看见了中国的美好与富裕,而此富裕与美好正是洛可可享乐社会所希望的。在此,中国文化与洛可可品味相合,中西文化彼此便揉和出了特殊的审美趣味,此茁壮自西方艺术土壤却相异于西方古典传统的风格,其所沾染的异国情调,不仅深得当时欧洲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喜爱,也进而绵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一时之间,欧洲对于中国工艺爱不释手且为之痴狂。
法国洛可可艺术作为西方艺术风格脉络中的一环,理应表现当时代的审美凝结与艺术成果,然而,洛可可艺术却不同于先前的西方艺术风格,在视觉上再现出历史脉络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洛可可艺术的中国风作品不仅清楚标示他者文化的身影,也试图在应和西方艺术审美之下展现他者的异国风情。他者图像的再现是洛可可艺术中的中国风作品所表达的主调,在中国风貌的描绘中,不仅记录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质与典型,也说明西方不同于中国的本质与趣味。中国一直是西方知识与文化建构的对照与观望对象,中国风作品的中国描绘是西方观看中国的具体呈现,然而视觉图像中所呈现的却不单只是文化汇集与时代品味之下的展演,更多的是暗藏于视觉图像之下的精神推演与心理机制。中国形象在中国风作品中被化约为符号与标志乃是西方自我主体为标示我他分际所建构的事物秩序,而中国形象在中国风作品中的挪用与置换却是西方艺术审美架构下的文化精神实践,借用中国样貌以巩固西方文化的优越与高雅,在此,中国仅作为符号与表征以标示时尚品味与艺术趣味。
法国洛可可艺术家进行中国风作品创作,基本上是欧洲风格的表达与诠释,是源自西方社会文化的需求与触发,也就是说,于中国风作品中视觉再现的中国乃是就西方社会本身需求相应而生的他者幻象。因此,中国风作品中的中国是沉默的被诠释者,而西方是雄辩的、主导的、凌驾的诠释者,中国的再现身影之所以混杂且怪异乃因此身影的塑造,只见中国皮却不见中国骨,骨架的构筑脱离中国,是建基于西方审美意识与社会需求的中国形象,因而,此形象所显现的不仅是规范自西方知识系统与视觉政体之下的异国风情,也是培育自西方文化系统与审美意识之下的殊异品味。然而,十八世纪法国热切注视中国,在社会各层面上皆积极借鉴中国,中国影响深远,中国文化与艺术是启蒙根源也是贵族爱好,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在西方人眼中所展现的灵妙与华丽恰巧与十八世纪洛可可社会所崇尚的慧诘与享乐相合,西方视野之下的阴性中国亦与洛可可社会所标举的阴性气质相合,整体而论,十八世纪洛可可艺术中的中国风是时代风尚也是审美凝练与文化精神的展现,是中西文化交流汇集的极致表现,也是雄性西方凝视阴性中国的感性表达。
西方凝视异域在中国风作品中传达出西方中心的权力与欲望。西方在十八世纪时,视野扩及全世界,在世界的大地图中发现新世界,触发新的视觉经验并累积新的知识,也因新世界的发现映证出他者与自我的差异,关注我他分际与差异也就张扬了价值判断之下的优越与卑微,于是凝视异域所产生的欲望表达逐渐成形,权力位阶也渐形构筑。视觉图像便提供了一个具体检验的领域,在图像中,二元对立框架之下的欲望与权力关系得以构筑,而观看与被观看之间的对话与辩证关系得以传递。西方作为观看者与主体,参与观看实践并建构意义。因此,通过检视暗藏在图像之中的观看交换的欲望表达与权力关系,不仅确立了西方观看主体的位置与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位阶,并且说明西方知识系统、文化范式与精神本质。西方作为观看主体为中国制造图像意义,当分析中国风作品中的造型、配置与构图,可发现西方眼中的中国是西方凝视异域的感性符码与欲望指涉,十八世纪法国洛可可艺术家通过艺术表现描绘如实似幻的中国,图像中国不仅具体呈现西方人心中的乌托邦、人间天堂或世外桃源,也暗自透露出西方本位意识之下统摄他者之域的欲望。
中国风作为法国装饰风格表现时代品味之中的审美凝结,在西方传统审美标准下,艺术性或许不高,因而得不到该有的重视,即便如此,中国风设计作品当中,还是有其特殊意趣。就中西文化艺术交流观点上来判定,中国风的确是有特殊且关键的定位与意义。其作品在视觉表现上所涉及的中西文化精神之间交换与融汇,可经由他者概念的导入,论证西方塑造中国风貌是西方确立自我本位的策略,经由二元对立辩证,形成我他分际并划分层级,因此,中国风作品中的中国图像,不仅展现中西交流情境的混杂趣味,并揭露西方知识建构与文化精神当中对于他者文化的再现形象。
注释:
①扎伊尔德(Edward Said, 1935-2003)是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也是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扎伊尔德以他提出的东方主义最为世人所知,他认为这本书汇集了西方对东方的很多基本预设。
②视觉政体(scopic regime)指的是西方视觉主义传统之中,用以建构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文化规制的运作准则,形成了一个视觉性的实践与生产系统。转引自雅克·拉康:《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吴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 页。
③“关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形象的讨论:请参见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意识》,《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94-110 页。
④樊美筠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存在着高扬女性、讴歌女性、为女性张目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还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明显,已形成了一种悠久的传统。这一尊崇女性的传统不仅体现在美学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的思想和意识中,而且凝结在中国传统美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中。”转引自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