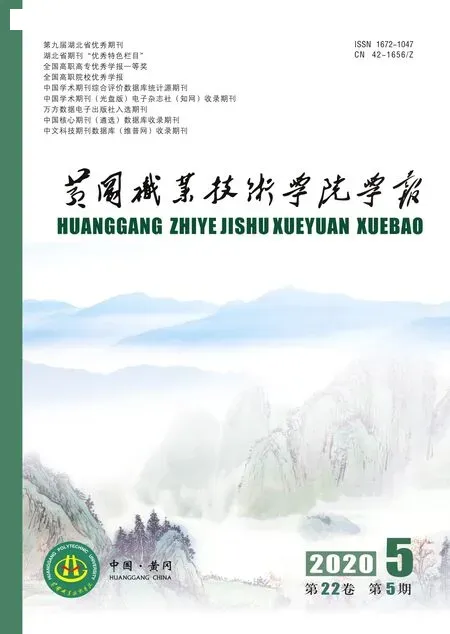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民族自信——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文化思潮探源
2020-01-17叶季夏
叶季夏
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民族自信——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文化思潮探源
叶季夏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文化思潮,反映了中国社会大变局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深深忧虑。透过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种种诘难,今天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自信的本质就是民族自信。回顾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思想主张,弄清其源流,探讨其得失,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反传统文化思潮;探源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创造的全部生活方式的总称。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通俗地说,就是人怎么过日子的问题。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民族自信。因为不同民族的人创造出不同的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怎么过日子是人的事情,自信也是人的事情。
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其实就是中国人对家国的文化认同和对自我的人格肯定,表现为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中华传统文化。家族(家庭)制度、孝道、儒家学说,都是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密切配合,决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
在传统文化中,家庭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把家庭生活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和人生幸福的实现形式,以家族兴旺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以成家立业光宗耀祖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即所谓家族主义。
孝是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人所谓的孝道,就是以孝为道。以孝为道蕴含着中国人以家庭(家族)为中心“慎终追远”的生存智慧: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子女既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家族事业的继承人,应该为家族传宗接代、开枝散叶。
儒家学说是家族主义的理论形态。儒家学说以家族主义为根据,构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系统,将孝道置于核心的地位。儒家又用家庭关系来解释社会关系,为家国的统一性提供了证词。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是一家之君,君是一国之父,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1],适用于父子关系的孝道同样适用于君臣关系。“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这个“本”就是责任和义务。孝是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忠是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各就其位,各尽其责,各守本份,天下自然太平。正所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所以,在儒家学说中,孝道是齐家治国的“至德要道”,可以“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在家族制度、孝道、儒家学说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把家国作为生活的共同体,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独特价值。中华文化是家国文化。[2]中国人的家国思想根深蒂固,家国情怀一脉相承。中国人的“国家”是以国为家的概念,而“民族”的概念也是在家族、宗族概念基础上的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其实就是中国人对家国的文化认同和对自我的人格肯定,表现为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
二、近代中国人的自信力发生问题,源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问题
传统文化是鼓励生育的文化。中国人有好生之德,认为多子多福。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创造的历史。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朝庭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人头税,兑现了“新增田亩,永不加赋”的承诺,大大解放了人口生产力,中国人口迅速增长达到空前的规模,终于形成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国力强盛的时候没有理由不自信。当大清国的国民沉浸在康乾盛世的繁华景象当中的时候,所谓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自然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但是,那个时候事情已经在起变化了。人口增多生活压力自然也会增大。因为人是要吃饭的,要吃饭就得种地,而土地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哪怕是在太平年景,中国社会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起来。人口问题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康熙皇帝就曾担忧说,“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自给?”清代学者洪亮吉更加明确地指出,在一个家庭当中,生活资料的增长常常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子又生孙,孙又娶妇。“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一味地鼓励多生孩子,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3]
在中华民族的生存还没有出现全面的危机之前,对于人口问题的担忧似乎还显得有些多虑。但是,全面的危机很快就出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外患不断,中国社会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问题开始积重难返。再经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闹,满清朝庭的统治基础也发生了动摇,一度岌岌可危。中国历史进入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代,而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也愈发艰难了。于是,有人把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结为“人多之害”。汪士铎感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开地之力穷矣!”对于造成“人多之害”的思想文化根源,汪士铎认为,是中国人“喜丁旺,谓为开族”,多子多福的思想,以及早婚的旧俗。
到了清末,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病得不轻。究竟病根何在?自然需要加以诊断。
明恩溥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在1890年代出版后,风行一时。这部中国问题研究专著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素质诊断报告。
根据明恩溥的诊断结论,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数量问题,一是素质问题。中国人口太多了,同时中国人的素质也存在着诸多明显的缺陷。造成问题的原因,跟中国的家族制度、孝道、儒家学说都有极大的关系。毕竟,中国人大多还固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哪怕是穷困潦倒也一定要为家族传宗接代。于是,人口问题就成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当中的一个死结。
严格来讲,人口问题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而是人类共有的问题。明恩溥抓住中国的人口问题大做文章,主要不是担心低素质人口的大量繁殖造成了中国人的生活贫困,他所忌惮的是中国人移民海外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明恩溥提醒人们说,中国人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民族“可以单独占据这个星球的主要地方,乃至更多的区域。” 因此,“中国人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比起现在来,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紧迫。”
如何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呢?明恩溥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心中没有上帝,所以,用基督教的上帝信仰取代儒家孝道的祖先崇拜,用基督教的原则改造中国的家族制度,乃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也是“命令人们生养众多”啊。何况事实上,西方殖民史和基督教传教史,本身就是一部人口扩张对外迁徙的历史,基督徒的人口繁殖能力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差啊。凭什么基督徒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就是天经地义,而中国人移民就不行了呢?不得不说,明恩溥的研究结论是贬低了中国人的素质,否定了中国人的人格,最后也否定了中华民族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此,即使我们承认明恩溥对“中国人的问题”的诊断结论是正确的,也还是无法接受这个外国人给我们开出的文化药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口达到了“四万万五千万人”,大约占到了当时全球人口总量的1/4。一些社会学者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当中的根本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暴露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中矛盾冲突的一面,也必然地把人们的思考引向以家族制度、孝道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鼓励生育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说,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发生问题,源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发生问题。
三、清朝末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家庭革命”的主张是反传统文化思潮的早期表现,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生存危机意识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深感亡国灭种的危险。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签订《马关条约》,以及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并迫使中国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舆论空前地活跃起来。中国人为什么只是一盘散沙?如何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以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带着这样的问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目光盯上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和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思想。
1903年,梁启超在考察了美国社会之后,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就是“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4]西方国家实行市民自治,中国实行家族自治。中国人不能摆脱家族制度的束缚,自由往来于城市,有族人资格而无市民资格,造成“中国人的缺点”,就是心中有家族无国族,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对于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所以,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必须改造中国的社会组织;改造中国的社会组织,必先改造中国的家族制度。1903年,黄遵宪《驳革命书》中也认为,“吾考中国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规模,古所谓宗以族得民是也”。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迁徙,“今日无论何乡何村,其聚族而居者并不止一族”。如果家族之间沟画太明,必致树党相争,不利于邻里团结。“故族制之法,施于今日,殊不切用”。
1904年,由留学日本的江苏同乡会主编的《江苏》杂志第七期,发表了署名为“家庭立宪者”的文章《家庭革命说》。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女子世界》杂志刊登了主编丁初我的文章《女子家庭革命说》。中国知识分子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的革命要“家庭先革命”的主张。
家庭革命的对象,是中国的家族制度和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思想。《家庭革命说》一文指出,“若我中国二千年来,家庭制度太发达,条理太繁密;兄弟、夫妇之间爱情太笃挚;家法族制、丧礼祀典、明鬼教孝之说太发明,以故使民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而读书,而入学,而登科,而升官发财,而经商,而求田问舍,而健讼、私斗、赌博、窃盗,则皆由家族主义之脚根点而来。”古代圣贤帝王之所以设教以提倡家族,原以为家族是国家的雏形,斯有家族主义方有国家思想。孰料事与愿违,中国的家庭制度和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思想反而妨碍了中国人的国家思想的形成,家族竞成国家之坚敌也。故家庭革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摆脱家族的圈限,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从事于政治的活动,谋取个人的事业;二是破除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思想,形成民族主义国家思想,以凝聚国家力量。
家庭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基础工程,跟社会政治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政治之革命,由国民不自由而起;家庭之革命,由个人之不自由而起。”政治之革命是要争国民全体的自由,家庭之革命是要争国民个人的自由。有民族思想者,必不肯受家族的圈限,欲为政治上的国民,必无以全家族之孝行。革命的步骤,是欲政治革命,必先革家族之命,以其家族之有专制也。欲革家族之命,必先革一身之命,以其一身无自治也。
辛亥革命之前,民族主义(或称国家主义、国族主义)迅速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1905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感慨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5]正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家庭革命”的主张。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家庭革命”的主张是反传统文化思潮的早期表现,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那个时候的民族民主意识,其实就是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当时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认为是中国的家族制度和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思想妨碍到民族主义,造成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局面。他们希望通过“家庭革命”,改变中国人的“家人”身份认同,形成“国民”身份认同,促使中国人的家族共同体意识上升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他们要求在制度设计上确立个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取消家庭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使国民直接于国家而不间接于国家”[6],从而达到合四万万国民为一大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增强国家力量的目的。那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之辩,基本上还是遵循“移孝作忠”的思路,对于传统文化的诘难尚未达到非孝批儒的程度。
四、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是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大爆发,反映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深深忧虑
新文化运动是思想文化的革命运动。革命的对象是以家族制度、孝道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反对传统文化?当时主张新文化的代表人物给出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条。
(一)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纲常伦理妨碍平等人权的新信仰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1916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及更名之后的《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论文《吾人最后之觉悟》和《宪法与孔教》。他指出, “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自由、平等、独立的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所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儒家三纲之义起于礼别尊卑,以孝道为“人类治化之大原”。在古代宗法封建社会,这一套伦理纲常自有其合理性,但是,以此来组织社会国家,并不能适应今日竞争世界的生存。我们要在今日竞争世界生存下来,必须组织现代的新国家新社会。现代的新国家新社会的基础,是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要建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就必须打破中国人的长幼尊卑的思想,必须破除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纲常伦理。
(二)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
吴虞是新文化运动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916年《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发表了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阐述了家族制度、忠孝伦理和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指出忠孝思想是奴隶思想,儒家道德是奴隶道德,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倡儒家学说提倡孝道的目的都是愚弄人民。“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三)家族制度和礼教是“吃人”的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端,指出了儒家“仁义道德”背后掩盖的人吃人的事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之后,吴虞写成《吃人与礼教》一文,对鲁迅的这篇小说的思想作了引申。他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原来“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他说,“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所谓新文化就是西方现代文化,所谓旧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胡适明确主张“全盘西化”,他指出,中国人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承认自己事事不如人并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学习。要“全盘西化”就要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能够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必须非孝批儒,推翻传统文化以家族主义为根据以孝道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形态的价值系统。陈独秀指出,新旧文化的根本区别是价值观念不同;旧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家族本位主义”,新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个人本位主义”;新文化运动的行动目标就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主张,把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对立了起来。在新文化启蒙思想家的叙述中,家族是个人的牢笼,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孝道以家族共同体的名义绑架了个人自由,以族权和父权剥夺了人权,以男权压制了女权。因此,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从未获得过人的正当权利,从未获得过人所应有的尊严。这种叙述固然是揭示了一部分的事实真相,但也仅仅是一部分的事实真相,而且,这一部分的事实真相,并不能代表个人与家庭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家庭是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家庭关系是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家庭的养育功能无法完全替代,亲情在个人的成长当中也不应该缺失。这是个人与家庭关系的主要方面。罔顾这个主要方面,夸大个人与家庭关系的对立,把家庭说成是个人的牢笼,说成是压制人权的专政机关和个人人格独立的障碍,虽然也可以言之凿凿(毕竟“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不幸的家庭又比比皆是,对于家庭“罪恶”的指控从来就不缺少证据),但还是难免以偏概全。
在中国鼓吹“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很容易激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但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个人本位主义”真的能带来幸福吗?一个人可以不结婚生子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庭生活总要胜过无家可归的独身生活。“个人本位主义”作为某些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它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味口,甚至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陈独秀还特地声明,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伦理,批评孝道,并不是教唆子女抛弃自己的年迈的父母,“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新文化运动是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大爆发,反映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深深忧虑。那时,传统文化(所谓“旧文化”)被认为妨碍了个人的自由幸福,妨碍了民族的生存发展,妨碍了国家社会的文明进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寄托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
五、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今天,我们所谓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说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何来“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文化自信真正的难点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传统文化在其现代转化过程中,先后遭受过人口问题的诘难、民族主义的诘难、个人主义的诘难,种种诘难皆源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担忧,伴随着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寄托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透过传统文化遭受的种种诘难,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自信的本质就是民族自信;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其本质就是对身为中国人的自信,对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自信。
回顾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思想主张,弄清其源流,探讨其得失,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借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名义,否定中国人的人格,否定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曾经,我们提到传统文化,都是“愚昧、专制、封建、奴隶的道德、吃人的礼教”这样的负面评价。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要么是想做奴隶而不得,要么也只是做稳了奴隶,从来就没有做成人,从来就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照这种说法,对自我没有肯定,对身为中国人感到羞耻,崇洋媚外,自信就很成问题了。
我们今天谈论文化自信,涉及到传统文化的部分,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不能孤立地谈论文化自信
学习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坚持中国道路,这几个事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学习传统文化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厚植家国情怀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关键,坚持中国道路是树立文化自信的目的。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去接触它亲近它,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就认识不到它的独特价值,分辨不出哪些是“优秀”传统文化,哪些是“不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立场标识中华民族的立场。一个中国人,丢掉了中华文化的立场,缺乏家国情怀,没有国家民族认同,不忠不孝,所谓文化自信必然是言不由衷。当代中国人的自信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上,自信的目的是坚持中国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离开了中国道路,忘记了民族复兴的使命,谈文化自信也就毫无意义。
第二,不应抽象地谈论文化自信
我们今天谈论文化自信,只是关心抽象的理论问题吗?当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问题,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民族竞争依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丧失了精神上的独立性,那它还能有什么前途呢?一个自身都难保的民族,又怎么能够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呢?又如何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所以,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仅仅看成是古玩字画一类的东西,只是供我们品评鉴赏而不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丝毫的联系,事实上,传统文化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它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决定着我们的家国认同和身份认同。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就是坚守家国的价值。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要落实在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上,落实在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上,落实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第三,我们谈论文化自信,还必须对反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作出回应
对于反传统文化的主张视而不见,不作回应,这是文化不自信的一种表现。我们承认,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也有它的历史贡献。我们承认,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为我们所用。譬如我们今天讲孝道,不仅是讲孝敬自己的父母,还要讲“老吾老及于人之老”、“幼吾幼及于人之幼”,更多地提倡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大孝”,孝道中的宗法血统意识则应该淡化。但是,对于反传统文化的某些观点,也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明辨是非,合理取舍。我们反对一些人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批判传统文化的某些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奉为至理名言的做法。社会在发展,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面对的社会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一百年前特定历史环境中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当成是万世不易的定论。
1934年,鲁迅发表文章,提出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接力奋斗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用事实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今天,中国人的自信力又在哪里呢?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当代中国青少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正是中国人的自信力的突出表现。从这里看,我们对当代中国人的自信力有着充分的自信。
[1]孔子.圣治章第九[C].孝经.北京:中国人口 出版社, 2016.
[2]学习领会“七一”讲话,坚定文化自信之二文化自信是总源头[EB/OL].中央纪委监察部, 2016-09-04.
[3](清)洪亮吉.治平篇[C].洪北江全集·意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01-01.
[5]孙中山.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N].民报,1905-11-25.
[6]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N]. 帝国日报,2015-04-30.
2020-07-03
叶季夏,男,湖北罗田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
K261.2
A
1672-1047(2020)05-0079-06
10.3969/j.issn.1672-1047.2020.05.20
[责任编辑:蔡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