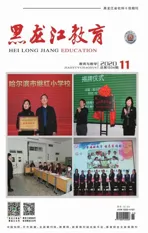疫情过后,日本课程观带给我们的思考
——读“G20 国家教育研究丛书”有感
2020-01-17依兰县三道岗镇中心校唐吉峰
依兰县三道岗镇中心校 唐吉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大国,先人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办学、治学遗产,然而,我们要坚守传承民族教育文化精华,还必须要有国际视野。
日本的基础教育以其公平与质量而广受世界关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依靠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实现经济的复苏和高速增长,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历经战后复苏、高速增长、稳定增长和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等不同发展阶段,高质量基础教育的迅速普及和均衡发展,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战败初期,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日本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于1947 年制定了《宪法》《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使日本民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为日本经济复苏和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教育为先导,将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并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纵观日本基础教育发展历程,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贯秉承教育立国的基本国策,以公平、优质、惠及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推动日本近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凭借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产业经济的振兴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劳动者,为实现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在疫情来临之时,日本从容应对,无论是应对灾难的能力,还是日本国民卫生素质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或许这本书中所陈述的“食育”课程和“防灾教育”课程能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
一、实施“饮食教育”,提高公民综合素质
学校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日本的学校给食也不例外。通过颁布学校给食法,促进各学校营养摄取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通过学校配餐的实施,加深学生对日常生活中饮食的正确理解并养成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将学校配餐作为一项教育活动丰富学校生活,构建温馨和谐的社交关系以及合作精神。目前,日本的学校配餐已经被作为对学生进行饮食教育的主要渠道。进入21 世纪,日本认为,要培养少年儿童丰富的心灵和健康的体魄以适应未来国际竞争,同时将保证国民终生健康生活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21 世纪的日本学校配餐的功能,已经从提供餐饮救助、饮食保障上升为进行“饮食教育”的重要内容。
日本最早的学校配餐为生活贫困家庭没有条件自带午饭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饭团子、烤鱼、咸菜等作为午餐。作为一项善举得到充分肯定,而学校配餐对于学生身心成长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也得到了充分认识,使得学校配餐迅速传遍了日本。
学校配餐的意义和作用,因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改变,从最开始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增强体质,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逐渐演变为通过学校配餐为师生搭建起心灵交流的平台,让学生体验集体生活,培养协作、互助的优秀品质。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儿童饮食无规律、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学校和幼儿园、托儿所等教育机构,作为推进儿童饮食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重要职责。学校和保教机构的有关人员,要利用一切机会和一切场合积极推进儿童饮食教育。通过学校配餐,一方面对孩子进行饮食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家庭的饮食生活和饮食教育。因此,加强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区、学校与保教机构之间的饮食教育合作具有重要意义。2005 年6 月,日本颁布了《食育基本法》,将学校教育中的“食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德育、智育、体育同等地位。同时,在“饮食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培养国民对饮食文化的思考,实现健康饮食的生活目标,促进城市与农村的对流与共生,构建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以此来达到振兴区域经济,继承和发展日本丰富的饮食文化,促进环境友好型食品类产业链的发展,促进合理消费,提高日本粮食供应的国产比例等目标通过“食育”进一步提高人们对“饮食”的认识,感恩自然,感谢为自己提供饮食的所有产业和所有人,践行健康饮食生活习惯和健康人生。
二、建立防灾教育常态化课程,提高危机应对力
日本是世界上第五大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多发国。自2000 年以来,占全球20.5%的里氏6.0 级以上地震,发生在仅占全球面积0.25%的日本国土上。频发的地质自然灾害,促使日本较早出台防灾减灾相关法律,建立完整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反应机制。一次次的灾害经历,反复强化着日本国民防灾减灾意识,常态化的防灾训练,使人们在地震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准确有序的紧急避难和自救措施,有效减少地震灾害损失,这和日本中小学校开设防灾减灾教育课程分不开的。
2011 年3 月11 日里氏10 级的东日本大地震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壮观一次,地震引起的海啸给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其中也包括在校学生和校舍等学校资产损失。然而,据日本2011 年度防灭白皮书统计,在总遇数超过18580 人的地震海啸灾害中,1~19 岁学龄入口的遇难人数(女生171 人,男生165 人)是全部遇难人口年龄段中人数最少的。这让日本人进一步认识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要性,更多的学校自发地开展各类防灾减灾教育、训练和挑战。在地震发生时,位于重灾区的岩手县大船渡市立绫里小学的所有学生即将结束一天的课程,正准备放学回家,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全体教师迅速集合所有学生,在校长的果断决策和指挥下,按照日常防灾演习的线路迅速撤离到高处避难。当教师带领学生按照常规训练转移到离学校较近的大船渡车站站前广场,校长和教师根据此次地震的震感的强烈程度和所在区域的地势,果断做出继续向山上转移的紧急决定。途中有家长希望接走自己的孩子,被校长断然拒绝,将全校所有师生带到地势较高的山坡上。当海啸过后,小学的校舍和车站的建筑物已被翻滚的浊浪吞噬,几乎被夷为平地,而全校师生却安然无恙。这得益于该学校坚持不懈的防灾训练,得益于日本中小学校健全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常态化的防灾减灾教育。绫里小学的案例并不是偶然的,这所处在岩手县大船渡码头附近的小学,长期坚持防灾教育。学校组织学生、家长和当地居民共同绘制本地区、本街道、本社区以及各个家庭的防灾地图,制定灾难发生时的避难线路和紧急联络规,建立应急机制,定期演练,做到让每一个学生和家长对紧急防灾减灾的应急心中有数,临阵不慌,有条不紊地撤离到安全地带、根据当地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强海啸的自然情况,绫里小学2004 至2007 年的防灾教育计划一直以“疯狂的大海”为主题进行海啸灾难教育。学校的防灾教育起到了显著的效果,通过学校反复训练和宣传,增强学生、家长以及当地居民防灾减灾的自觉意识,形成学校协调有序的灾难紧急应对机制,得到了本地居民的理解与支持,提高了学生防灾自救的能力。学生通过训练,不仅掌握了海啸发生时,如何到高处避难的自救方法、向家长和本地区居民发出海啸警报的方法,同时增强了对生命的理解与热爱。学生家长和当地居民通过观看学生自编自演的节目、宣传展板、海啸资料等发放的材料,那些早已风干了的对海啸的记忆再一次被唤醒,增强了学生的防灾意识。通过训练,学生对危险警报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立即采取行动,居民对海啸的防范意识增强了。绫里小学的防灾训练得到当地媒体,以及日本NHK 电视台的联合报道,媒体的宣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使学校防灾教育得到日本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将防灾减灾和危机对策预案写入学校教学计划,坚持防灾教育和防灾训练常态化,以真实情景训练学生和家长有效避难,将灾害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大限度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并尽快恢复教育活动,是日本中小学校防灾减灾应对灾害危机的根本方针和主要经验。
三、后疫情日本课程观带给我们的思考
1.未来的学校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需要国家力量整合,建立科学的课程标准,可定制,可个性化,学校提供多样化一切可学习资源,社会、家庭和学校联动开发的课程全民学习,提高公民素质,为未来培养有理性又有人性的合格公民。
2.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让生命百态尽显,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面前,不同的价值观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生面前,但是公民良好的素质决定应对疫情结果,所以我们的公共卫生课程和设施建设更应加强,学校更应担起传播健康理念,引导全社会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责任。
3.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灾难可能随时发生,日本的防灾教育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更值得学习借鉴,提出适合年龄段的防灾目标,最终完成以培养生存能力,自救、互救、灾后重建、心理疏导等为中心任务的防灾教育课程,这应该成为国家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行政手段推进教育公平,以教育立法保障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恰恰是值得国际借鉴的“他山之石”。自19 世纪下半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开始,日本就以教育立法为先导,设计了完整的学校制度和管理体制。基础教育本身不仅仅是目的,它是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承载着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使命,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日本发布的《21 世纪教育新生计划》《教育振兴基本计划》等规划蓝图式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处于后工业社会的日本,更关注的是顶尖人才的培养,以及如何通过人才培养成为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先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国际竞争的时代”,日本基础教育改革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全球化的今天,日本的课程改革实践将给世界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