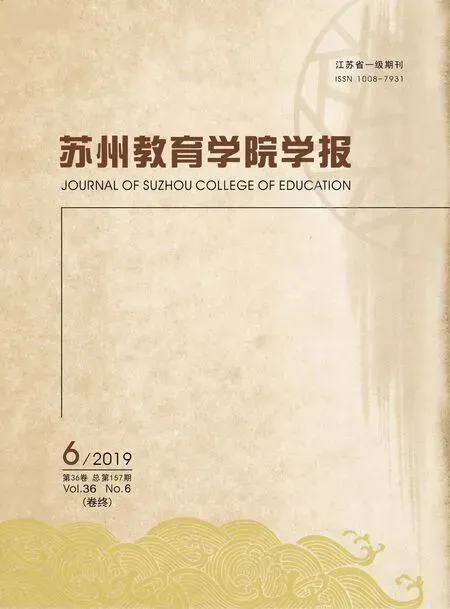“找一找我们身上的后遗症”
——王彪长篇小说《你里头的光》研讨纪要
2020-01-15杨剑龙张晓英王晓明万士端
杨剑龙,王 彪,张晓英,王晓明,万士端,等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2.《收获》杂志社,上海 200040)
2018年12月4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杨剑龙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①参与本次研讨的博士生有张晓英、万士端、郝瑞娟、李秀儿、王晓明、林玮、杨雨,硕士生有王慧、李俐、刘晶晶、冀婷君、温武。一道,同作家王彪就其长篇小说《你里头的光》②《你里头的光》发表于《江南》2016年第6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单行本。进行了研讨,以下为研讨会发言内容。
杨剑龙:在当代文坛,王彪一直以灵魂的探究和苦痛的描写为己任。在小说创作历程中,王彪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庄园》[1]、《致命的模仿》[2]、《隐秘冲动》[3],有长篇小说《身体里的声音》[4]、《越跑越远》[5]、《复眼》[6]。王彪的长篇小说大多描写人生的苦难:《身体里的声音》描写“文革”武斗中父亲之死和后来母亲的出走;《越跑越远》讲述高中男生梓青和中年戏子红云的畸恋以及红云自缢而死;《复眼》描述昆虫爱好者不经意间卷入了蝴蝶标本的境外走私案。王彪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你里头的光》[7]通过描写“文革”及当代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与复仇,探究现实伤痛中的历史后遗症,是对“文革”后遗症的深刻反思与生动呈现。
一、历史后遗症
杨剑龙:在小说《你里头的光》中,王彪将两代人的情爱与复仇交织在一起,让“文革”暴虐化的集体无意识融入下一代的血液,从而袒露出历史后遗症中的现实伤痛。在小说后记《找一找我们身上的后遗症》中,王彪写道:“写下这部《你里头的光》,为的是不再遗忘,也为的是寻找过往的苦难留下的现实伤痛……‘文革’暴虐化为集体无意识而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都成了有着这种基因的转基因族类。”[7]
杨 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有关爱情、人伦的故事,但是,小说所叙述的并非是一个唯美的、令人心向往之的理想的爱情故事,也并非是一个合乎社会规范的、良性的道德人伦体系。小说将主要背景放在“文革”中:陈米海对高红梅的追求,高红梅对齐国耀的欣赏进而结为夫妻,叶美丽与严英才的完美结合,齐国耀对阮霏的爱慕,甚至包括陈小安对齐梦飞的爱慕……在看似完美的表象下,却掩盖了一幕幕令人痛心的现实。高红梅见齐国耀一心追求阮霏,居心叵测地检举齐国耀,并将检举之罪转嫁给陈米海;齐国耀得知真相后,对高红梅施以暴行;陈米海趁齐国耀出逃、高红梅陷入低谷时,强行与高红梅发生关系;在严英才不在家的情况下,刘建东强行与叶美丽发生关系,并使叶美丽生下了他的儿子严杰;陈小安在遭遇齐梦飞的绑架和邱成的强暴后,身心俱碎。这让我们禁不住控诉“文革”对人心灵的迫害,以及“文革”余毒对下一代人的残害,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小说人物及自身在道德及人伦维度上的拷问和反思。
张晓英:“文革”隐退在小说背后,像一个幽灵,若隐若现地浮于文本中,捉弄每个人物的命运,人物被无形的手推着,如同上帝手下的棋子一般被随意拨弄。正如高红梅在小说中所言:“人可以遗忘历史,可是历史没那么容易就翻过去,它总是以另一种方式跟你不期而遇。”[7]齐梦飞、严杰以及陈小安是历史罪错遗留下的果子。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它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出现,继续存在于当年亲历者的生活中,同时也对后代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重新审视“文革”,许多作家以回看的姿态呈现、反思当时人们的种种做法,重拾对理性的呼唤。这部小说将目光转向当下,过去的因结成了现在的果,历史遗留的问题又该如何处理,是否已清除了人们身上残留的暴虐基因?能否与历史和解,摆脱过去的阴影?对于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对过去、对历史,我们不应有意无意地遗忘,集体暴虐的时代应该带给我们更多反思。
林 玮:王彪老师这部作品以“文革”为主题,延续了20世纪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风格,但同时也描写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恩怨情仇,因此也兼具反思的当下价值。在历史事件被官方话语纳入时代大叙事后,个体的恩怨延续到了下一代,没能因此而消弭。理性与非理性的纠葛,人生的困顿和对救赎的渴望在代际中传递。这让我想到,反思历史从来都不只关乎历史,我们对历史的反思蕴含着对当下的认识。因此,书中两代人的恩怨也不仅与“文革”有关,更直指当下,理解历史也即理解当下。这部小说让我感受到,过去的“伤痕”与现在的“光”的追寻是紧密相连的。
李秀儿:在读作品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作者到底想要说什么,想告诉读者什么。“文革”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文革”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的见证者今天就在我们眼前,人的内心生出的恶的因子有没有遗传下来?遗传了多少?我们有没有在不知不觉中隐藏了这种思想倾向?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我认为这部小说有青春文学、成长小说的一些特点。
刘晶晶:《你里头的光》这部小说情节性很强,节奏很快,读的时候有一种快感,场景故事来回切换,这种叙述方式颇有电影蒙太奇的效果。小说描写的仇恨与伤痛又给人一种压抑感,很少看到温暖的情节。我发现王彪老师的年龄与小说中两个男主人公是相同的,在1976年这个动荡的年代里都是16岁。文学来源于生活,这部作品是不是有您自己生活的投射?毕竟“文革”离现在有些遥远了,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感受到“文革”带给上辈人种种难以磨灭的伤痛。
万士端:王彪老师的这部小说以两代人之间的情爱与生活纠葛构成了平行又不时交织的复式结构,以两代人之间的报复为明线,以反思“文革”后遗症为切入点,以爱与宽恕为终极目标。您的小说读来让人痛苦,读后却让人思考。正如刚才同学所言,“怀旧”是不是构成了您这部小说的主调?
王 彪:我写这部小说,一是出于对过去生活的纪念。在小说里面,有一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小说中描写的自杀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因此,这部小说有我的一些经历,包含了我对那个时代青春的记忆与伤痛。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想在这部小说中表现我对当代社会的感悟。我认为我们现时代的人性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表面上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文革”时期的人们通过权力赋予的天然的、合法的暴力——抄家、打人、批斗,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当今社会表面上没有激烈的斗争,但实际上权力和金钱滋生的暴力没有改变。以前有偶像崇拜,现在没有崇拜吗?我认为,如今的偶像崇拜比任何时代都更严重。我们崇拜什么?崇拜金钱,崇拜权力。人性所具有的暴力、嫉妒、仇恨、荼毒,在现在的环境中并没有被削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那个时代骨子里的很多东西并没有消失,这也是促使我写小说的另一个原因。
二、宿命与复仇
杨剑龙:《你里头的光》虽然也写了“文革”期间同辈人——齐国耀与陈米海、丁文浩与刘建东、严英才与刘建东等人——的情仇,特别是前者对于后者的仇怨,但是作家着重描写后辈子女为父辈复仇。虽然向前辈子女——无辜者——复仇的方式和做法都有些过分,但是作家执意对“文革”后遗症作深刻反思与生动呈现。
王晓明:这部小说的多线叙事结构安排得很好——爱恨纠葛与时空交错。“文革”时期,小镇中学的学生在生发爱情、友情以及师生情的同时,也遭遇了同伴的告密和出卖,甚至遭遇毁灭性打击。“文革”的暴行彰显了人性深处的恶,折磨毁灭了父辈,又像病毒传染贻害了下一代,将齐梦飞、陈小安们带入纠缠不休的仇恨中。为了复仇,年轻人也误入歧途,铤而走险:严英才、齐国耀、刘建东、严杰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高红梅、叶美丽也经历了种种绝望。整部作品通过互相纠缠的几组人物和上下两代的关联,把时代洪流中个人为了生存、为了尊严、为了爱情而努力抗争的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直击人的灵魂。
张晓英:齐梦飞、严杰都是在外来因素下得知父亲的往事,齐梦飞无意中得到了父亲留下的日记,加上母亲的背叛带来的屈辱感,使他对陈米海产生强烈的恨意,但他无法直接向陈米海讨债,便将仇恨转向陈米海的女儿陈小安,将“文革”的审讯形式挪用到陈小安身上,以对她的侮辱完成对父辈的复仇。严杰从丁校长的步步引诱下得知了父亲自杀的真相,多年来一直隐忍不发,潜伏在刘建东身边,当他以为完成复仇时,却陷入了俄狄浦斯式的结局。他们都自认为以“正义”的方式为父辈复仇,但他们复仇的对象都发生了偏移,他们报复的都不是自己真正的仇人,在革命历史的影响下,他们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
温 武:小说有明确的复仇主线。小说中的仇恨肆无忌惮地蔓延,就像一片杳无人烟的荒野。正如鲁迅所言:“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8]细数下来,三条复仇主线贯穿全书:齐国耀与陈米海互相攻讦、严杰隐忍报复、齐梦飞报复陈小安。故事在四角恋中展开:陈米海喜欢高红梅,高红梅喜欢齐国耀,齐国耀喜欢阮霏,阮霏无一喜欢,最后嫁给了父亲战友的儿子。少年情愫包裹着鸩毒,从陈米海伙同盗卖公社稻种被揭发、齐国耀成立“兄弟帮”、高红梅揭发“兄弟帮”开始,毒素便慢慢发酵,直至后来齐国耀和陈米海相互报复,齐国耀破产跑路偷皮鞋身死,陈米海入狱,刘建东、严杰身死,这一幕悲剧才最终落幕。老一代的撕咬固然惊心动魄,但新一代掀起的报复浪潮更啮人心,严杰的复仇最为惨烈。老丁——鬼魅般的人物、老一代的失利者——隐忍了几十年后化身“竹叶青”,以略近撒旦的形式引诱着严杰复仇,精心为严杰准备饵食,只等他吞下去。在老丁的引诱下,得知真相的严杰坠入黑暗中,从而走上复仇弑父的道路。故事中的人物貌似都得到了最初想要的——齐国耀得到了阮霏、陈米海得到了高红梅、严杰得以复仇……然而宛如用镊子揭开未成痂的伤口——爱情、亲情、家庭、事业面目可憎,梦想与青春支离破碎。
郝瑞娟:我在读这部小说时,被小说所描写的人的内心的黑暗所震动,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可言,是那么不真诚,从“文革”时期的告密、背叛、尔虞我诈,到当下社会表里不一的奉承,为了金钱利益的利用。小说中高红梅因爱生恨的揭发、陈米海对拿到团市委文件的齐国耀的冷嘲热讽、齐国耀利用资本对陈米海的报复、档案管理员丁文浩设局让严杰知道真相、严杰对刘建东的表面尊重内心怨恨,都让我们看到了自私卑琐的人性,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世界是否还有光亮。
另外,除了复仇所表现出的人性之恶,小说还表现了很多社会层面的问题,呈现出更加深刻的意义。小说提到的学校围墙坍塌的豆腐渣工程、假药假疫苗背后医疗机构的腐败、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问题,都真实存在于当下社会中,小说对当下现实的指涉令人深思。无论是对齐国耀、陈米海等人金钱崇拜的极致描写,还是作为政治官员的刘建东、陈米海与商人王顺微妙的利益勾连,抑或是一心向佛的世外高人闵师傅为了成为政协委员的委曲求全,都让读者看到了社会的不堪与黑暗。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倾向。
李秀儿:读这部小说,让我始终感到难受,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心中都有一个小账本,有个小九九,而且很执拗。陈小安之外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仇恨和对抗,即使是齐国耀和陈米海这两个曾经拥有过纯洁、真挚的爱的男人,心中对爱和青春的美好记忆,也被岁月和仇恨给磨光了。恰恰相反的是,那些因爱而生的恨,却被牢牢地铭记、被遗传,直到陈小安出现,这些仇恨和对立才得以和解。
张晓英:在阅读过程中,我有一点儿感到疑惑:齐梦飞与齐国耀之间没有表现出父子二人的直接接触,齐梦飞只是看到了齐国耀留下的日记,从而得知过去的事情。这和严杰不同,严杰出生时,他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但齐国耀死时,齐梦飞已经16岁了,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小说并没有明显表现出父子二人的交往,这一内容比较模糊。如果齐国耀没有从小向齐梦飞灌输一些革命的思想,一个16岁接受过教育的孩子,单单靠一本日记,能产生如此强烈的革命式的复仇意识吗?齐梦飞性格的形成是突变的,他知晓自己的母亲与陈米海偷情,加上得知父亲与陈米海过去的恩怨,有理由产生这种复仇意识,但与严杰的复仇相比,在细节上有些弱化,不是很顺理成章。
郝瑞娟:我也有这种感受。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简单梳理了其中的两条线索(见图1),从这两条线索中可以看出,小说中戏剧化的情节与电视剧的特质很相似,人物命运有着明显的被安排的痕迹,这是否与您作为编剧的经验有关?

图1 《你里头的光》小说线索
王 彪:我以前写小说,之后从事编剧,这部小说是我写剧本后的第一部作品,我想试试看我还能不能再写小说。很多人做了编剧后,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我发现我还能写,但并没有非常好,所以同学们的批评我觉得非常到位。可能潜意识里面,电视剧对我的影响还是有的,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上有一些类似电视剧的元素,这也是我以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杨剑龙:小说中作家让人物都陷入情爱的纠葛中,让父辈沉陷在“文革”的泥淖中,你争我斗、你方唱罢我登场,从而结怨结仇,却让儿女辈承担复仇的重担和承受被复仇的虐待,从而表述作家对“文革”罪孽的反思,尤其对“文革”后遗症的深刻反思与深入谴责。
三、罪孽与拯救
杨 雨:作家并不只表现了黑暗,也为这一迷局的终结给出了答案,即相信爱就有未来。剔除与宗教救赎有关的成分不论,“相信爱”体现了对自己的接纳,同时也包括对他人的接纳,只有相信他者的存在,才能为我们提供反观自身的最佳参照。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只有仇恨和自我,看不到他者的生活,这个人只会一步步走进自己设置的陷阱中,轻则心灵受创,重则人心俱亡。在这部小说中,陈小安的形象及生活轨迹颇具意味:她是一个长相平凡、毫无亮点可言的灰姑娘,但是,在受到迫害之后,她不但没有被仇恨所挟持,也没有抱怨。就是这样一个灰姑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具备自知的优良典范,“平凡中显示伟大”[9]这句话用在陈小安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张晓英:这部小说讲述的人物基本上都处于罪与罚的状态中,小说各个人物的命运互相缠绕在一起,在受罪的同时也在赎罪。陈米海追求高红梅,因偷卖大队稻种被学校处分,失去了往日的风光;齐国耀成立“兄弟帮”,成为学校风云人物,之后却被打成反革命小团伙头目,最后却为了一双皮鞋把命丢了;刘建东从被整到整人,一直升到了副市长;然而之前东山再起的丁校长却成了“三种人”,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运动使“人变成鬼,使鬼变成人”。小说中两个受伤害最大的女人——叶美丽和陈小安——都选择了原谅。叶美丽选择向儿子说出真相,以为坦白一切能够得到解脱,重新获得自由,可是却没想到严杰受不了这样的刺激,被车撞死。如果说严杰是被动接受真相,陈小安则是主动探寻。她受到《圣经》的影响,从赞美诗中获得力量,选择用爱来摆脱过去,在法庭上说出事实的真相。陈小安没有像过去时代的人们那样互相告发、颠倒黑白,她选择了正视现实。她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彻底原谅齐梦飞,但她心中充满爱,她相信用爱能解决问题,在爱里没有惧怕。小说采用这一美化方式处理矛盾,将希望寄托在未来身上,以爱来化解仇恨。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在她受到如此屈辱后,是否真能如小说所言挣脱时代的阴影?小说所呈现的黑暗力量何等之强,这一人性之美显得既珍贵又微弱。
郝瑞娟:王彪先生曾在《面对灵魂的说话声》一文中指出:“现代人身上早已千疮百孔,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10]小说中的人物都在挣扎着,命运多舛、大起大落的齐国耀,外表光鲜、有苦难言的陈米海,罪孽深重、不得善终的刘建东,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高红梅以及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阮霏,他们都陷在命运的泥潭中不得解脱,这背后可能是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也可能是爱的纠缠、欲的膨胀。小说将上一代的恩怨延续到下一代青年的身上,两代人的生活际遇中都有苦难和伤痛,这种痛不仅是身体上的摧残与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戕害与打击。在小说行将结束的时候,陈小安用她的善良和宽恕结束了两代人的恩怨,从小说情节上来看,这一“真话”的表达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但从现实层面来看,陈小安的谅解真实可信吗?或者说陈小安这束心灵之光、人性之光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少?
王 慧:相较于陈小安,更令我感兴趣的是阮霏。她和余华《兄弟》里面的林红很相似,开始是被万人钦慕的美女,后来都生活得不是很如意,拜倒在金钱下,拜倒在她们之前所厌恶的人的膝下,这是一种讽刺。对陈小安这个人物形象,我感觉她对齐梦飞的爱铺垫得不够,有点突兀。
冀婷君:纵观小说脉络,有两条并行的人物线索:一条是以叶美丽、刘建东和严英才等人为代表的父辈,另一条是以陈小安、齐梦飞和邱成等为代表的年轻一辈。作为年轻一辈的陈小安,最后宽恕了一切,找到了出路,当她走在街上,听到圣乐,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心中充满了光,从中可以看出小说宗教救赎的意味。与陈小安相比,叶美丽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中。小说特意让叶美丽也去寻找宗教救赎,但叶美丽原本认为六根清净的云林寺,闵师傅却为了获得政协委员的地位有求于她,叶美丽最终没有获得佛教的救赎,陈小安却寻求到了基督教的救赎。小说是不是有意设置对比?在作家看来,陈小安在被绑架过程中受尽凌辱与折磨,我在阅读时感到特别痛苦,为什么她不起来反抗呢?为什么她要这么容忍?小说是否是刻意塑造陈小安这样一个圣女似的能包容一切不公和苦难的人物,从而为“文革”中的苦难代言?
万士端:大家都很关注您对陈小安这个人物形象的处理,这个人物似乎还不够饱满,其言行及思想还不是那么令人信服,您在创作这个人物时有着怎样的考虑?现在回过头来反观这个人物形象,您又有什么不同的理解和感想?
王 彪:我没想到大家今天很多讨论是围绕着陈小安的,当初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这个人物一点儿都不重要,后来在写的过程中开始变得重要。我当时的侧重点实际上是父辈以前的故事,但是后来就变成前后平衡的关系。小说中的陈小安选择了相信,因为相信所以能够解决问题。我并不认为我在小说里面表达的观点大家都能接受,但对我来说,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陈小安的想法就是我当时所想的,面对这样一个局面、这种仇恨,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从小说本身来说,陈小安后面的力量确实还不够,按理说,应该再有一些铺垫,小说人物还没有达到更为饱满的程度,但我认为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很多同学的焦点都聚集在陈小安身上,在之前有关这部小说的研讨会上,对陈小安也有很多讨论,这个形象如果能够更饱满、更具有吸引力一些,说服力可能会更强。“文革”后遗症怎么来解决?法律能解决吗?我们的钱更多了,能解决吗?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陈小安所做的选择,便是我寻找的出路。
我在“后记”里谈到了以色列,犹太民族非常值得关注,他们有坚定的信仰,所以能做到许多其他民族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小说里,写到的也不完全是犹太教或是基督教。为什么佛教不能使人获得拯救?
王晓明:小说讲述的复仇故事不同于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或哈姆雷特式的复仇——好的坏的统统毁灭,小说还有“光”,还在找寻出路,生发出希望。陈小安的内心世界和信仰跳脱出来,对她的描写具有宗教意味,她喜欢听赞美诗、巴赫的音乐、《马太受难曲》等,在饱受虐待和摧残后,心中依然有爱,能在法庭上勇敢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小说开篇引用《圣经》,“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7],陈小安放下了仇恨,用她的爱和宽恕来化解并终止复仇。就像小说题目《你里头的光》一样,陈小安内心有光,她自己本身就是光。正如您刚才所言,这是您有意的安排,寄托了您的希望。好的小说要细细品味,读一遍只有浅显的认识,读两遍也许感受会深一些,要多读几遍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心。
温 武:小说的主旨在于控诉与揭露。我们时常说“药”在时间里,然而对于这场浩劫来说,遗忘便是背叛。如小说的后记:“写下这部《你里头的光》,为的是不再遗忘,也为的是寻找过往的苦难留下的现实伤痛。就像一个人得了病,看上去被时间医治,已然痊愈。但疾病的后遗症却在隐秘的身体里常常发作,代代相传,如同病毒进入基因,‘文革’暴虐化为集体无意识而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都成了有着这种基因的转基因族类。”[7]然而在时代的伤痛中,作者还是给予了读者光亮与温情:陈小安选择了宽宥齐梦飞,终于使这莫比乌斯环出现了断口,给予其力量的是宗教。同样受到老丁“要么批斗别人,要么被别人批斗”[7]的挑唆,了解真相的陈小安发出了“我不想成为你们那一代……”[7]的呼声。小说以宗教的“药”来解时代的毒:“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7]时代或许冰冷,但爱始终贴近肉体,温暖人心;命运或许无公理、无正义、无目的,但爱却自有重量。时代是喧嚣热闹、不足为凭的戋戋表象,内核是遗忘的本能。感激您的沉重,“为了忘却的纪念”[7]是一种真正必不可少的品质,如您所说:“只要不遗忘,也许我们还有希望。”[7]
李 俐:这部小说写了一个悲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受到命运残酷的伤害。“文革”结束了,但因“文革”而产生的恩怨一直在悄悄地拨弄着每个人的命运,他们一直都没有摆脱高中时代恩怨情仇的影响。让人感到窒息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也因为他们当年的爱恨情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说中陈小安身上的那种“大爱”给了人们救赎的希望,爱能化解恨。如果社会上兴起“爱”的文化,也许历史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
杨剑龙:王彪在谈文学创作时说:“只要想想人的脆弱有时比人的勇敢还要强大,我们就没有理由感到轻松,人的本能,人性的缺陷从另一意义上造就了人类历史,它真切得让谁摸上去都为之颤栗。”[10]王彪的小说创作关注人的本能和人性的缺陷,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长篇小说《你里头的光》同样关注人的本能和人性的缺陷,呈现出作品人物性格刻画的独到之处。虽然王彪在小说中努力寻找救赎的出路,但是对于人性本能和缺陷的探究与把握,成为这部作品的独到之处。
王 彪:我愿意给出一条出路,因为我不是在20年前写这部小说,20年前我会写得很残酷,可能结尾会更惨,那时候我更关注人性黑暗的一面。实际上我比较喜欢写小说,喜欢去发现人性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小说的价值有时候大过其他文学体裁,因为它对人性的探求是其他体裁没有办法深入和达到的。小说讲述的人物的想法是什么?他又会怎么做?在我看来,这些都特别有诱惑力,特别有挑战。
现在,当我写社会、写人性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思考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办。实际上这部小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意识,想要探讨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文革”的后遗症浸润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骨子里,这个现象不是单纯写出来就够了。对我来说,以我现在的年龄和生活阅历,我不单要写出来,还要想出路,哪怕没有说服力。“文革”可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有些问题用文学的形式来反映,深浅不一,作家的想法也不同。我想,不管怎么说,历史不能忘却,就像通常说的忘却了历史等于背叛,确实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