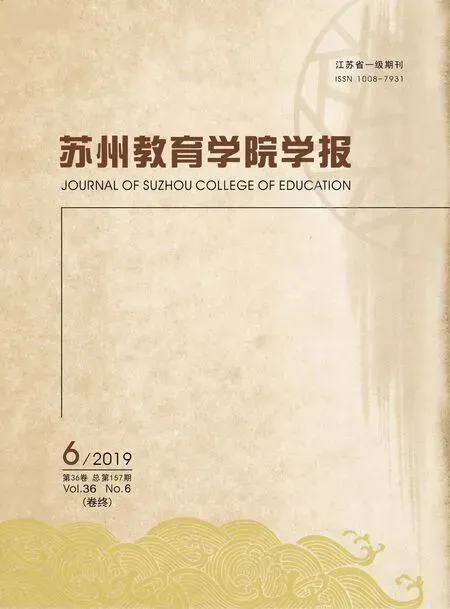抗日战争背景下文学期刊的生存策略
——以《七月》《万象》为中心
2019-02-22战玉冰
战玉冰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抗日战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方面,中国的文学版图随着政治版图一起被分割为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上海“孤岛”等几大区块,形成了“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1]的实际局面;另一方面,中国文坛又进入了一个“共名”[2]时代,民族战争与抗日救国成为这一时代绝大多数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而在不同的政治地域背景下,因所处政治经济环境、主编个人风格、报刊生存发展策略等差异,中国知识分子们所创办的文学刊物如何回应这一时代的共同主题?本文以国统区的左翼同人刊物《七月》和沦陷区的综合性刊物《万象》为中心,试比较分析两种差异较为显著的文学刊物是如何分别表达自我诉求并回应时代需要的。
一、时代困境: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困难与政治审查
《七月》1937年9月11日创刊于上海,周刊,主编胡风,发行人为费慎祥,同年9月25日第三期出版后停刊;1937年10月16日在汉口复刊,改为半月刊,主编仍为胡风,发行人改为熊子民,由生活书店代理发行;自1938年1月16日起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发行人仍为熊子民;1938年2月1日第八期发行人空缺;自第九期开始,发行人改为张鸿飞;1938年7月16日第三集第六期(总第十八期)出版后停刊;1939年7月,杂志在重庆复刊,续出第四集第一期(总第十九期),同时改为月刊,主编依旧是胡风,由华中图书公司代理发行,一直到1941年9月第七集一二期合刊(总第三十五期)出版后终刊。
再联系精神品格与《七月》一脉相承的《希望》杂志:1945年1月创刊于重庆,主编胡风,由五十年代出版社代理发行;到1945年12月第一集第四期时,改为三联书店重庆分店发行;1946年5月4日迁到上海后出版第二集第一期,主编仍为胡风,发行人为胡国城,由中国文化投资总公司负责发行;1946年10月出版第二集第四期(总第八期)后停刊。[3]
从《七月》到《希望》,我们可以看出杂志发行城市随着战线后撤/推进而不断迁移;其代理发行公司和发行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杂志发行周期很不稳定,且《七月》由周刊、半月刊,到月刊,最后到两月合刊,总体上呈现出发行周期逐步延长的趋势。这种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和政治原因。《七月》与《希望》办刊城市的变化轨迹(《七月》:上海—汉口—重庆,《希望》:重庆—上海),正好呼应了国民党政府“后撤—前进”的军事复归路线;而发行人与发行公司(《七月》: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华中图书公司,《希望》:五十年代出版社—三联书店重庆分店—中国文化投资总公司)的不稳定与发行周期的逐渐延长,更直接体现出了战争时代社会的动荡不安、经济条件的艰难及由此带来的办刊困境。
除了战时环境的逼迫、社会动荡与经济困难之外,《七月》与《希望》也随时面临着国民党政府严格的政治审查。《七月》在武汉复刊后曾申请改名为《战火文艺》,未能通过审核,仍沿用了《七月》一名;《希望》在创刊之初原本取名《朝花》,最终也因未被批准而被迫改名《希望》。
再来看看几乎同时代的上海的《万象》。从编辑来看,《万象》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24期(1941年7月第一年第一期至1943年6月第二年第十二期)主编为陈蝶衣;后19期(1943年7月第三年第一期至1945年6月第四年第七期)由柯灵接编。直到1944年12月柯灵被捕,最后一期《万象》一直拖到1945年6月才出版,之后便宣告停刊。
相比于《七月》发行城市、发行人、发行公司的极不稳定,立足于上海的《万象》似乎稳定得多,发行城市的固定不变自不必说,老板平襟亚也一直未更易,从《万象》创刊伊始便一直负责杂志的发行与经营工作。在《万象》第三年第一期《二年来的回顾:出版者的话》中平襟亚(秋翁)曾明确说:“回想到前年的初夏,本人一时兴起,接受了蝶衣兄的建议,出版发行这一份综合性刊物。”[4]而据王军《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研究》一书中所展示的数据:上海“孤岛”时期,陈蝶衣主编的《万象》发行量一度达到两三万册,远远超出了当时四千册的平均水平。
由此看来,《万象》似乎并未像《七月》一样受到战时社会动荡与经济困难的影响,而有着固定的发行城市,自始至终的发行人、发行公司以及颇为可观的发行量。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受战争影响,上海印刷工人工资上涨、工期拖延,尤其是纸商囤货居奇,暴抬纸价,这些都对《万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我们在多期《万象》的“编辑室”栏目(陈蝶衣执笔)和杂志老板兼作者平襟亚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印刷成本提高与纸价“直线上腾”的抱怨和担忧。①《万象》第一年(1942年)第八期 “编辑室”中就写到了印刷工期拖延及印刷成本的上涨:“承印《万象》的印刷公司,因粮食恐慌而解雇大批工友,以前只要四天就可以印齐,现在却需要延展到十六天。因此杂志要分先后两批排印,在工作效能方面,不免大受影响,而印刷费却又增加了几近一倍,上期仅需一千六百六十元,本期起增至三千一百元。于是不得不略增售价,这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希望爱护本刊的读者,能谅此苦衷。”参见蝶衣:《编辑室》,《万象》第一年第八期,1942年。
除了印刷成本的提高,纸价的大幅上涨也对《万象》造成致命打击。《万象》第一年第十期“编辑室”写道:“贪婪的纸商不断的以抬价为压榨文化界的武器,其面目之狰狞真叫我们望而股憟。上期所用的报纸,是以每令八十五元的代价购得的,这已经是比创刊号出版时涨了两倍,但到本期已经涨到每令一百七十元。”[5]平襟亚发表在《万象》上的《不得不说的话》中,也对纸价暴涨有很多抱怨:“何况目前纸价竟一度抬到一千八百元一令,当我草此文时,还得一千五百元以上。”平襟亚还在文中预测了如果纸价继续上涨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突破二千元一令的大关时”,《万象》只能停刊,这“真是我们出版界的末路了,同时也是文化界的严重威胁”。[6]由于平襟亚完全负责《万象》的发行和运营,所以他讲的这番话显得格外可信。简单比较下陈蝶衣1942年“编辑室”与平襟亚1943年文章中提到的纸价,我们会发现,仅仅一年多时间,纸价已经从85元一令上升到1800元一令,并仍在迅速上涨,其涨价的幅度与速度实在令人震惊,难怪平襟亚会专门写下《书贾与纸商》[7]严厉声讨纸商囤纸和通货膨胀。
那么发行量可达到两三万册的《万象》究竟能否抵挡住这战时经济失衡和物价暴涨的冲击呢?平襟亚在《二年来的回顾:出版者的话》中对《万象》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成本核算,文中说:“(每令报纸五百张,若依九百元一令推算,每张合需国币一元八角。)本刊(《万象》)每册用四张报纸,合计需七元二角。每册印刷费一元一角。每册稿费编校等费合计一元。每册铜锌版费扯二角。每册封面底页五角。每册装订费二角,以上合计每册成本拾元另二角(此系确数)。若售十二元一册,批七二五折,实收八元四角,每册应亏折一元八角,即以两万册算,每期应亏折三万六千元。而广告之收入,仅每期两千余元(以往包给毛子佩兄),相差甚巨。”[4]据平襟亚这段话来看,发行量为两万册的《万象》,除去制作成本与发行成本,杂志销售收益一期亏损要高达三万六千元,广告收益仅为区区两千元,完全无法弥补杂志销售环节中产生的巨大亏空(此时纸价还是按九百元一令核算)。也就是说,《万象》杂志虽然销售量领先于当时的上海滩,但其仍处于一种高度危险的资不抵债的经营困境中。因此陈蝶衣在《万象》第二年第一期“编辑室”中无奈地说:“现在我们只有出版一期算一期,如果一旦因无法支持而夭折,就只有请读者们原谅了。”[8]
与此同时,处在“孤岛”及沦陷时期上海的《万象》也面临着日伪政府的严格审查,主编柯灵的被捕和《万象》最终被迫停刊就是最好的说明。
综上,《七月》与《万象》两份杂志,虽然一个在国统区中不断迁移、漂泊、“居无定所”,一个在上海沦陷区内保持着发行的稳定与发行量的“辉煌”,但二者都不得不面对时代的困境,即如何应对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困难与政治审查。只不过《七月》所遭遇的战争逼迫、社会动荡与经济困难更为直接,战线的后撤与城市的沦陷直接导致了杂志被迫不断转移地域,连续内迁,并且发行公司也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相对而言,《万象》受到的战争影响是间接的,战争带来的市场混乱、纸价飞涨也从根本上打击了《万象》,甚至使《万象》主编在销量领先的时候就担忧杂志社随时可能倒闭关门。这两份受战争环境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文学刊物,其刊物定位和内容选取也都相应地呈现出与战争时代主题或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关系与生存策略。
二、刊物定位:同人杂志与综合性刊物
《七月》与整个民族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从刊名上就可以看出:“七月”二字正是为了纪念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而《七月》与战争的关系,主编胡风在第一集第一期《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代致辞》一文中作了更为清晰的说明:“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这只要看一看九一八以后中国文学的蓬勃的发展和它在民众精神上所引起的巨大的影响,就可以明白。”[9]
主编胡风对杂志的影响贯穿始终,是杂志的核心与灵魂,因为《七月》的作家群体——很大一部分成为后来的“七月派”作家——就是一群围绕在胡风周围的年轻人。胡风在这篇类似于杂志发刊词的文章中表达出的他对文学与战争关系的态度,颇能代表《七月》的主张和立场。
胡风办《七月》(包括后来的《希望》)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思想,胡风认为:有必要继续在中国办一个好刊物,通过刊物团结一批青年作家,为中国的新文艺增加新的血液,从而能够把中国文艺向前推进。因此《七月》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同人杂志”的办刊方针,甚至比此前的《新青年》《创造》等刊物在“同人”方面走得更远。“七月派”诗人绿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曾提到:“胡风是以一个理论家的身份,不辞辛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编辑杂志,是有某种大的寄予在里面。”“和胡风思想不一致的人,一般不可能在胡风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10]在推动胡风为《七月》倾注心血的同时,这种“大的寄予”也使得他筛选稿件的标准格外严格。关于胡风对《七月》的影响,张玲丽《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一书中有着非常准确的概括:“胡风性格中的自信、辩驳气质,以及领袖欲思维对于这两份刊物的独特气质具有直接的影响。”[11]
面对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以胡风为核心,以《七月》杂志为阵地,一批气质相通的青年人——阿垅、丘东平、舒芜、路翎、田间、贾植芳等聚集在一起。他们直面战争,以小说、诗歌,特别是报告文学,直接表达对战争的看法,书写自身的战争体验。从这些年轻人的创作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们受到了胡风“主观战斗精神”文学理论的影响。路翎的小说、田间的诗歌、胡风的理论,三者所表达出的精神气质方面的高度一致性,正是胡风“同人刊物”理念及“以一本杂志聚集一批年轻人”想法的最佳实践与证明。
与此同时,《七月》与战争关系的密切还体现在杂志社举办的三次座谈会中。1938年1月16日、4月24日、5月29日,《七月》社分别举办了三次座谈会,主题分别为:“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仅从主题就可以看出《七月》对战争现实的深切关注和直接参与。李怡在《阿珑诗论的文学史价值》一文中概括了七月派诗人“试图在壮大情绪之流中充实新诗的底蕴”[12],完全可以扩展为对整个《七月》杂志的一种判断——《七月》(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理论文章等)试图在“壮大情绪之流中”充实民族战争中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底蕴。
相比于《七月》的“直接反映战争”与“同人办刊”的定位,《万象》从对战争的表达方式到“综合性办刊”的编辑策略都体现出更多的间接性。
从杂志名称来看,杂志果然不负“万象”二字,从作家到作品都称得上是“包罗万象”。在《万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晦庵(唐弢)、鸿蒙(王统照)、李健吾、赵景深、阿英、芦焚(师陀)、叶绍钧 、黄裳、端木蕻良与平襟亚、孙了红、周瘦鹃 、徐卓呆、王小逸、张恨水 、张爱玲、予且(潘序祖)、包天笑等人的名字或并置或交替出现,场面蔚为壮观。而在作品内容上,《万象》既有孙了红的“侠盗”小说,也有柯灵改编的剧本,更有师陀“果园城记”系列小说,还有讲述战争科技与生活科技的科普文章,以及大量关于上海掌故的知识性内容……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刊物。吴福辉在《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中,从期刊编辑类型角度指出《万象》代表了海派文学刊物由新潮型向综合文化型的转变,可谓一语中的。[13]
而将此前彼此风格倾向都绝不相同的作家作品包容在一本杂志里的做法,《万象》主编陈蝶衣还试图从理论上为之寻求合理性解释。陈蝶衣在《通俗文学运动》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本来只有一种。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不曾有过分歧。可是自从‘五四’时代胡适之先生提倡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遂有了新和旧的分别,新文学继承西洋各派的文艺思潮,旧文学则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虽然新文学家,也尽有许多在研究旧文学、填写旧诗词,旧文学家也有许多转变成新文学家,但新旧文学双方壁垒的森严,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4]陈蝶衣在这里试图找到中国新旧文学产生分歧的根源,并以“通俗文学”这一概念来抹平中国新旧文学之间的差异。而《万象》杂志对于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家作品兼容并蓄的态度,就是陈蝶衣这一理论主张指导下的成功实践。当然,《万象》之所以采取综合性的办刊方针还有很多现实的考量,比如身处“孤岛”,外地作家投稿困难,稿源紧缺。保证稿源充足正是《万象》容纳各类作者的现实性考虑之一。[15]除了作者方面的考虑之外,对读者如何更容易接受杂志内容,扩大杂志影响力的相关思考,也促使《万象》采取兼容并包、雅俗齐聚的综合性办刊策略。此外,在当时日伪政权审查颇为严格的上海,借助一些软性的、大众化的内容无疑也是《万象》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万象》时被称为“上海沦陷时期爱国进步作家的‘堡垒掩体’”[16]465。而《万象》这座“堡垒”之所以能够在沦陷区前后坚持四年,与其曲线“委婉”的办刊策略有很大关系。
当然,《万象》的编辑和作者还是想积极反映、表现“战争”这一时代主题的,只是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不是像《七月》一样直接呈现“铁”与“火”的生活,渴望用思想力与感受力去“熔铸现实”。“《万象》的编辑一方面强调要‘不背离时代意识’,要‘忠于现实’;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在这纷乱的年代有一个安逸的文学阵地而窃喜。陈蝶衣在《通俗文学运动》中说:‘现在是个动乱的时代,战云笼罩着整个世界,烽火燃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在这样的非常的时期中,我们还能栖息在这比较安全的上海。在文艺的园地里培植一些小花草,以点缀、安慰急遽慌乱的人生,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17]与此同时,陈蝶衣在《通俗文学运动》一文中还提到《万象》“不能正面批判现实,但指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14],这也是它在上海沦陷区日伪政权统治下不得不采取的生存策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间接反映现实,“曲线”表达反抗,是《万象》在当时客观条件下作出的既主动又被迫的选择。
类似地,同样在上海沦陷区苦苦挣扎的《大众》月刊在《发刊献词》中也说:“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亦觉不忍再谈。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勿骂我们低级趣味。”[18]其中欲说还休、半遮半掩、吞吞吐吐的言辞和态度,是和《万象》一样的无奈和苦心。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说:“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品格与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以报纸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了政治体制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和所谓的‘文学性’。”[19]从这个角度来看《万象》《大众》及当时很多沦陷区文学期刊(顺应表达政权意识形态的除外),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日伪统治政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一种挑战,它们出版的每一期杂志其实都有意无意地为扩大公共言说空间的边界进行着有效的实践,而《万象》对于新旧雅俗作家作品采取的最大限度的包容,也正是为扩大并稳固自己在公共言说空间中的一席之地作出的积极努力。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万象》等沦陷区期刊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和策略,展现出特殊时空环境中爱国主义丰厚且多元的意义内涵与实践可能。
一方面是《七月》杂志的“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9],另一方面是上海《万象》“在这样的非常的时期中,我们还能栖息在这比较安全的上海。在文艺的园地里培植一些小花草,以点缀、安慰急遽慌乱的人生……”[14]两份刊物对战争分别采取了直接面对与曲折表现的不同表达方式。而这种由于所处政治环境不同(国统区与沦陷区)所导致的对战争时代主题表达策略上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两份杂志的定位与办刊理念。《七月》因为直面战争而选择了同人办刊的方针,因为同人所以纯粹,因为纯粹而使刊物更富斗争性与战斗力;《万象》则由于间接委婉地呼应战争的时代主题,进而采取了综合性的办刊方针,“综合”可以团结更多作者,“综合”可以影响更多读者,“综合”也可以借助一些“软性”的东西包裹并保护其“坚硬”的内核。而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传统的角度展开观察,《七月》更多地继承了此前中国文学杂志特别是“同人杂志”的传统,《万象》则更能体现出20世纪40年代“雅俗合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特色。《七月》与《万象》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两种文学杂志的传统与特点,而这种差异化的刊物定位是由于二者所处的不同政治环境及其面对战争时代主题时采取的不同表达策略所致。
三、内容特色:“战士作家”与“侠盗鲁平”
在内容上,《七月》出现了一批“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有着切身战斗经验与经历的作者。据王丽丽《七月派研究》一书介绍,《七月》作者群中的阿垅、丘东平、曹白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参加过1938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阿垅所属部队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属的教导总队”,参加过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战斗,其本人在闸北有过七十三天的战争体验,所以才能写出《闸北打了起来》这样极具真实感与现场感的报告文学。丘东平则是先随十九路军正面参战,1938年加入新四军后,开始转为敌后的游击战生活,这样独特的战斗经历,也在丘东平两篇最著名的小说《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我们构筑的阵地,我们自己守着!》中有所体现和表达。在《七月》上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曹白,其很多作品都表现了江南游击战斗生活,但丘东平参加的是经过改编的新四军先遣支队,编制归属于“正式的国防军”,而曹白参加的则是江南水乡自发崛起的民众抗日武装。[20]68
三位有着战斗经历的作者,在《七月》上通过报告文学或小说来展现他们实际经历过的生活,就更加富有可信度与感染力,其作品也可称得上是我们前文中曾说过的《七月》直面战争、反映战争、表现战争的众多作品中最有力的一部分。王丽丽在《七月派研究》中借用鲁迅《〈毁灭〉译后记》中对法捷耶夫的评论来评价阿垅、丘东平与曹白可谓恰如其分:“这几章……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20]68
相比于《七月》直接刊登前线“战士作家”的亲身经历,《万象》上的文章委婉得多,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孙了红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鬼手》《窃齿记》《血纸人》《三十三号屋》《一〇二》共计五篇“侠盗鲁平奇案”。曾经明确拒绝刊载武侠小说的《万象》连续刊登“侠盗鲁平”的故事,值得深思。武侠小说在《万象》上消失了,但“侠客”的“任侠”精神转移到了“侠盗鲁平”身上,而“侠盗鲁平”身上的反抗精神自然也寄托了《万象》编辑与作者群体某种不能直言的复杂心境。[21]侦探小说最初被引进中国,和现代法制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很多文人也曾想象过借助侦探小说来普及法制观念。但在鲁平身上,法制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传统中国的“任侠”精神。“在眼前的社会上,贼与绅士之间,一向就很难分别;甚至有时,贼与绅士就是一体的两面。”[22]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一个浑身充满正义精神的“侠客”,一个讲求结果正义大于程序正义、“不择手段”锄强扶弱的“盗匪”,这种隐性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的想象性的否定与颠覆。
如果说文学作品中的“侠盗鲁平”是一个被神奇化了的人物,那么其创作者孙了红身上则尽显现实炎凉。孙了红曾患咯血症而没钱治疗,《万象》发布了孙了红病危的消息,呼吁广大读者捐款为其治病。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上海沦陷区作家生存之不易,也能看出《万象》杂志与其作者群体良好的关系和深厚的情谊。此外,孙了红的遭遇完全可以看作上海沦陷区作家群体与文学刊物实际处境的一种表征①当时和孙了红一样生活窘困、贫病交加的作家还有叶紫、万迪鹤、顾明道、洪深、王鲁彦等;此外,入不敷出,经营捉襟见肘的《万象》杂志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贫病无力的“孙了红”。,回过头再来看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就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孙了红、《万象》及上海沦陷区文学界某种不能明说的心声。
由于《七月》与《万象》在抗战时期所处政治区域的不同,两份文学刊物所受战争时局的影响和其主动/被迫选择的应对策略皆有所不同。《七月》正面遭受战争的影响,其刊物发行城市、发行人、发行公司一直变动不居,而物质层面的不稳定恰好又与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与经济困难密切相关。由此《七月》及其后来的《希望》以胡风为核心,以同人为纽带,从刊名到作者,从文章内容到座谈会,处处采取一种直接关乎现实、正面表现战争的办刊态度。相较而言,《万象》身处沦陷区,没有像《七月》一样不断迁徙及变更发行人与发行公司,但战争对于《万象》的影响是间接且更为隐蔽的,《万象》回应与表现战争主题的方式,从兼容并包的作者群体到包罗万象的文章内容;从陈蝶衣等人试图以“通俗文学”抹平“五四”以来新旧文学之间的鸿沟,到其实际上被誉为“上海沦陷时期爱国进步作家的‘堡垒掩体’”[16]465。《万象》为了团结更多作者和影响更广大的读者,借助“综合刊物”的定位来躲过日伪政权的审查。作家孙了红的现实处境,和其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侠盗鲁平奇案”,则构成了以《万象》为代表的上海沦陷区文学界的现实处境与内心诉求的一组绝好的隐喻。
总而言之,《七月》与《万象》因其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以呼应时代主题。《七月》因为直接,所以有力;因为同人,所以纯粹。《万象》则由于综合,才得以扩大影响;由于委曲,终得以存在四年。而这两份文学刊物的方针定位和办刊策略,恰好构成了我们理解文学期刊如何应对战争时代主题的两种途径,无论哪一种,都是当时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主动/被迫作出的选择。它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爱国追求,用最契合自身实际境况的经营策略,不遗余力地实践了“文人爱国”的多种可能。
四、余论:《七月》与《万象》编辑与作者群体的最终命运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七月》更多延续了“五四”以来“同人刊物”的办刊传统,而《万象》则采取了一种偏向市场的综合性刊物定位。无论哪一种办刊方式,1949年后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为代表的,由政府财政支持的,被纳入政府行政机构与党的组织双重体系中,体现国家文学思想的国家级文学期刊。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万象》之类包罗各类作家作品的文学刊物从此难以继续存在或再度出现。一方面,大量《万象》作者流散港台海外;另一方面,即使留在大陆的《万象》作者也受到接连不断的阶级或“左右”的划分与冲击。流散海外的作者的声音自然被屏蔽于大陆之外,而那些被划入“敌方阵营”的作家当然也不可能与“我方阵营”的作家在同一文学平台上发表作品。
至于《七月》,其“同人刊物”的办刊理念在“五四”以来虽然早已不算新鲜事,《新青年》《创造》等文学期刊已经为“同人刊物”提供了大量范本,但在民族战争的大环境中,在各方都在追求所有作家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时代背景下,《七月》不断以“同感者”“同道” “伙友”等词语来强调刊物自身的“同人性”,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不团结”与“不合时宜”。而这种“不团结”到了1949年后,就慢慢被批评为“宗派主义”,并最终由文艺论争越格上升为政治批评,“同人杂志”最终也演变成“胡风小集团”,甚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使这批作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长达数十年的牢狱之灾。[23]虽然到1982年随着诗集《白色花》出版,“七月派诗人”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但此时的“七月派”作家已经从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变为鬓发皆白的老者,而胡风在弥留之际不让自己的外孙报考文科的遗言[24],则留给我们无尽的感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