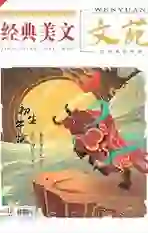以素穆的诗,自我拯救
2020-01-14曾子芊
曾子芊

露易丝·格丽克,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曾获美国桂冠诗人头衔,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将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诗人露易絲·格丽克,获奖理由是“因她清晰可辨的诗意之声,以其素穆之美促成个体存在的普世性”。此前,文章多将颁奖词中的“austere”一词译为“朴素”,在格丽克的诗集中译者范静哗看来,“朴素”似乎不够准确:“朴素是不加工、不精雕细琢,但格丽克的特点是一种主动追求的素净、肃穆、瘦索。”她的一本中译诗集名为《月光的合金》,书名也反映了诗人月光与合金般冷静的语言质地。
在耶鲁大学任教的露易丝·格丽克,1943年生于纽约,属于学院派的小众诗人。不过,自1968年出版处女作诗集《头生子》以来,格丽克至今已著有12本诗集和1本随笔集,获遍各种诗歌奖项。
“得知格丽克获奖,还是有些意外的。”另一位格丽克的中文译者柳向阳说,“因为鲍勃·迪伦近几年才刚刚得过,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作家得奖的频率也并不高。”虽然感到意外,柳向阳表示这也符合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纯文学的传统:“从文学的序列上来看,诗歌是纯度最高的文学,就像是理科中的数学一样。”
│神话世界与现代社会的融合│
初读格丽克的诗,译者柳向阳就震惊于她的疼痛:
我要告诉你件事情:
每天,人都在死亡。
而这只是个开头。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柳向阳在序言中总结。格丽克的诗大多关于死、生、爱,而死亡居于核心。在第一本诗集中,她写道:“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一直到1990年第五本诗集《阿勒山》,“死亡”都在反复出现,她对人生这一注定会踏上死亡的旅途充满兴趣。
“我从会写作时即开始写‘死亡。”格丽克在采访中提到了这一点——她对死亡的书写从十岁的时候已开始,也正是在十多岁的年龄,她希望自己能成为诗人。格丽克曾在《诗人之教育》一文中透露过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早年经历: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开杂货铺谋生,但几个女儿都读了大学;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格丽克的父亲,拒绝上学,想当作家。但他后来放弃了写作,投身商业并获得了成功。在父亲身上,格丽克也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父亲需要坚持的不是写作,而是对自己的潜力深信不疑。”格丽克的父母都敬慕智力上的成就,她的母亲尤其尊敬创造性天赋。格丽克回忆说:“如果我们哼个不停,我们就上音乐课;如果蹦蹦跳跳,就去学跳舞。诸如此类。我母亲念书给我们听,很早就教我们开始念书。”
还不到三岁,格丽克已经非常熟悉希腊神话。一开始是父母为她读,后来她逐渐能够独立阅读。古希腊众神和英雄们的故事强烈地吸引着格丽克,对她来说,“这些故事形象比街区里的其他小孩要生动”。它们以及童年阅读的插图中的某些画像,成了日后她诗歌的基本参照。在格丽克的印象中,父亲最拿手的是圣女贞德的故事,“但最后的火刑部分省略了”。
“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会从早年的记忆中汲取养料。”格丽克说,在她身上很明显的便是她在童年时读过、听过的这些睡前故事。在格丽克的诗中,她不断重返希腊神话,在神话的外衣下,唱着冷静肃穆的歌。
《草场》中的不同人物都可以和《奥德赛》的人物谱系一一对应;被冥王掳走的少女珀耳塞福涅的故事则在她的写作中回响了五十年。诗集《阿弗尔诺》中直接描述珀耳塞福涅的诗作充满了暴力和凄厉。范静哗说,格丽克不仅仅是采用了古希腊传统这一名称,她更多的是把她的个体身份和女性精神感受重新融入到古希腊的传统当中,意义相当于“重铸了传统”。她将抽象化的古典再度具体化为周围活生生的人,使神话世界与现代社会融合。
│她的每首诗都是一条“支流”│
《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把露易丝·格丽克归入“后自白派”诗人中。与“后自白派”对应的是“自白派”,自白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摇滚乐、人权运动与反战以及女性主义的兴起。自白派以个体来写个人化的感受,尤其是隐私性的感受。格丽克的诗同样书写个人感受,极具私人性,但又巧妙地超越了个体,达到了更抽象的层面。
“她的作品就像是一场内心对话。”著名出版人,同时也是格丽克的好友乔纳森·加拉西如此评价格丽克,“也许她在对自己说,也许在对我们说,内心的声音持续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在《诗》中,格丽克提到了自己作为读者时体验过的两种基本诗歌模式:“一种是对读者而言,感觉像是知心好友;一种像是被窃听的沉思。”而她的偏好,从一开始,“就是那种要求或渴望有一个倾听者的诗歌”。
格丽克的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自传性的材料多是她经历的童年生活、姐妹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亲戚关系、失去亲人的悲痛等。但格丽克本人曾反复强调这种私人性绝非传记:“把我的诗作当成自传来读,我为此受到无尽的烦扰。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它们似乎是……范式。”
格丽克有强烈的表达交流欲,但她无意让自身经历成为焦点,更希望受到关注的是作品中人类的苦痛和欢愉。她一直致力于抹去诗歌作品以外的东西,除了1995年早期四本诗集合订出版时她写过一页简短的“作者说明”以外,她的诗集都只有诗作,没有前言、后记之类的文字。格丽克曾说,自己不喜欢接受采访,并非是离群索居,“我是一个很爱社交的人”,只因那些她不得不言说的、真实的迫切大都存在于她的诗作中。
最早向世纪文景竭力推荐格丽克的是范静哗,但由于范静哗的时间受限,另一位译者柳向阳承担了大部分的译文。柳向阳从2006年开始翻译格丽克,在沟通中,格丽克坚决拒绝了出版“诗选”的要求——她希望能一本一本地出。“格丽克特别强调诗集的整体性。”
诗人、作家赵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格丽克诗作的整体性:“她的一本诗集并不是一些诗篇的集合,而是一个流动的整体,就像河流一样,每首诗都是一条支流,汇入到一个整体里,绵延不绝、此起彼伏、暗自呼应。”
与上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辛波斯卡相比,赵松认为格丽克更有种内倾的原初性特征,“辛波斯卡在我看來更知识分子一些,她的思维、想象与写作的方式,对个人经验转化的方式,都是有着清晰的逻辑线索的。假如说辛波斯卡的诗像晃动在水面的光芒与风,那格丽克的诗则更像是渗透到深水层的微光跟水流本身的合体。也正因如此,她的诗明显要比前者更具个人化的神秘气息——在始终都很节制淡定的文字里弥漫不已。”
│以写作拯救自己│
格丽克的中译诗集从开始翻译到出版,时间跨度为十年。除了国内诗歌翻译的出版道路艰难外,与格丽克严谨的要求也有关。柳向阳回忆说:“我大概问了格丽克几百个问题,她也会在我译的稿子上画圈,问一些人物关系上的细节问题,整个过程的感受就是非常严谨。”格丽克小的时候,曾想选择绘画道路,因为自己也“有点小天赋”,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写作:“写作适合小心谨慎的性格,被编辑的可以保留下来。”
读者也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母女关系影响了格丽克的经历与创作。格丽克的母亲是那种家务总管式的道德领袖、政策制订者。她鼓励孩子们的天赋,她读格丽克的诗和故事,读她在学校的文章。母亲的表扬伴着格丽克长大,但严格的母亲并不慷慨赞美。“因为在她的眼里,我和妹妹对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总是不够努力。”
到了青春期的中段,格丽克患了厌食症,她回忆说,这种冲突自行上演,与母亲形成了激烈斗争,“当我开始拒绝食物,当我以暗示的威胁来宣布我拥有自己的身体——她的巨大成就时。”厌食症成为格丽克将自我与他人分隔开来的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让她逼近死亡。幸运的是,在高中临近毕业那年,格丽克开始接受心理分析。格丽克说,心理分析教会自己思考,“教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自己表达中自我下意识地)躲避和删除(的部分)。它给我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自我怀疑转化为洞察力。”和许多以自杀结束生命的“自白派”诗人不同,格丽克没有陷入纯粹的私人化写作和倾诉中,从这个角度看,她的写作做到了超越和拯救自我。
“诗有别材。”柳向阳愿意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这四个字来形容格丽克。范静哗则如此归纳格丽克的写作趣味:面对痛楚或磨难,不会铺陈浓郁得化不开,不大喊大叫,有点浅唱低吟似的轻诉,会细到抓住眼神一闪、细到神经末梢似的细腻,不经意的掩饰或反讽。
后期,格丽克转变了心态,也转变了语言表达风格,尤其是《乡居生活》的舒缓感,有一种谅解一切之后的明亮。在创作上,格丽克一直有意使其艺术手法及取材处于变化中,对她而言,写作像是一场冒险,她总想被带到未知的领域。
获奖后,77岁的格丽克也谈到了“衰老”的话题:“它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对于诗人或是作家来说,这就是无价的。”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