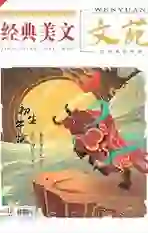母亲
2020-01-14王近松
王近松

母亲用一把锄头,在雪地里将春天刨开,从此刨开另一个纷纷世界。
一
站在大红梁子上喊一声母亲,万山呼应。
在山顶,捡起一块石头往下扔,石头落在地上,又在新的地方安静、沉默。母亲如一块石头,被安排在山间,一生默默无闻,默默无闻地分裂、默默无闻地在河流中行走。
生活如同一条河流,我们都如一块石头,在这条河里随波逐流,拍打着两岸的山崖。惊涛拍岸,可否卷起千堆雪?
二
在海外,母亲早起,将星星赶走。
在村里,母亲起床,将火炉里的火点起,唤醒一个村庄。母亲的脚步声很低,却用一种传统的方式,将村庄、大地唤醒。
炊烟升起,朝阳将村庄冠冕。公鸡扯开喉咙,歌颂着勤劳的人。
烧火做饭、喂马劈柴、饲养家禽,在房前屋后为一个菜园子种上白菜、香菜、莲花白等等,这是一个农村家庭的诗和远方。
母亲,在海外的深山里呼喊着我们的名字,那三长两短的言语,在山间回响。外出求学多年,我们把家从这里搬出去,多年后一个人再回来,依旧觉得有人在喊,站在垭口处。
我也对着不同的角度喊几声。喊几声,就觉得自己释怀了。
三
有一天,我站在鱼池旁,风吹来,水面瞬间皱纹肆虐。风停,那些皱纹又随之消逝或者减少。
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
这些年,我叛逆过,也越过了自己与父母的那道鸿沟,而母亲的额头,如同地壳的板块,在愈演愈烈,皱纹的宽度也越来越让人心酸。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小时候,寄居在亲戚处,父母隔三差五来一次。从那时起,我们将生活变成海洋,我们只是一条条鱼,四处游走成了一种常态。一个人生活在外面,家也就更加遥远。
记得在生物圈,有一种叫三文鱼的物种,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它们就成群结队地按照熟悉既定的路线,从大西洋沿着圣劳伦斯河回到淡水河里。
母亲的一生如此,我们的一生也如此。
寒暑假,我回家、回海外、回黑石,父亲还是那样,不管早晨还是傍晚,泡一杯茶一个人在院里转,看看房顶的蜜蜂;母亲依旧淘米、做饭、炒菜,在那小小的锅里炒着不同的菜,闻不同的味道。炒菜时,母亲将家里所有人的盐量都估摸得清清楚楚。
母亲,在厨房将近三十年,将人间咸淡看得透彻。
四
天黑下来,母亲回家了吗?
在海外,山太高,天似乎比其他地方黑得更快。
十多年前,母亲曾经点着手电,牵着牛将路边草上的露珠打落。对于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不是罪恶,而是生活的节奏。
父亲曾赶过马车、开过拖拉机,这辆车上一直有母亲,再后来有了我们。
在地里,母亲卖力地干着农活,午休都会觉得是浪费时间。从春天开始播种,夏天施肥、除草,秋天收割,她们的时间,被一卷一卷的膜覆盖着,如同地膜上的水珠,很快又被过往蒸发。母亲用一把锄头,在雪地里将春天刨开,从此刨开另一个纷纷世界。
母亲是一个耐性很好、做事极其认真的人,那些没长出的玉米,要么重新种上玉米,要么种上红豆。她不愿她的田园,如陶渊明笔下的“草盛豆苗稀”。
母亲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土地上度过的,剩下的余生也将和土地结下不解之缘。最终,我们又会在地上按着辈分排列。
五
从海外到黑石,房子会变小,步伐会加快,唯有家的温度一如既往。
母亲摆过地摊、卖过水果、卖过零食,用一把秤将善恶称出来,而母亲对于人世的无奈,该如何称?
即使在寒冬,母亲收摊的时间也不会太早,整条街上,像母亲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她们用清晨的哈气、傍晚的忙碌声将一条街的“人情味”表达出来。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空气中除了水分子、尘埃,还有唏嘘的故事,还有各类味道。
那些在街上炸洋芋的人,她们也是母亲,将洋芋去皮,还原了一个个洋芋的肤色,过油,仿佛是要将那些恶念抹杀。那些炸洋芋的油,炼出来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有时也会在伞上汇集,成了油烟。油烟最后都成了尘埃或污垢,母亲还在日复一日地用初心为顾客服务。
街上,少不了卖汤圆的人,她们和面、包汤圆、煮汤圆,圆满了汤圆,也圆满了自己与顾客的情分。
冬天会走,春天会来,灯火会明亮,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那些类似于母亲的身影。
六
我总觉得,此生有一通长途电话,是我要打给母亲的。给父亲打电话,母亲总会在旁边嘀咕:你问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三餐要吃饱,冷了就把衣服加厚一点……
今晚的月光,能否带着我所有的思绪到达故乡,在梦里安抚母亲的担忧?
那些树站立着,只是想告诉我们风何时来、归向何方,母亲也时常站在桥上、站在田埂上目送我。她想告诉我什么,这不是我的母亲一个人在说,天下的母亲都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些故事,尽管故事不同,但爱是相同的。
母亲站立的田埂上,一株鸢尾花开了,花瓣上有着风雨的故事;蒲公英花絮儿随風飞扬,种子散落四方。母亲,站立如同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