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节选)
2020-0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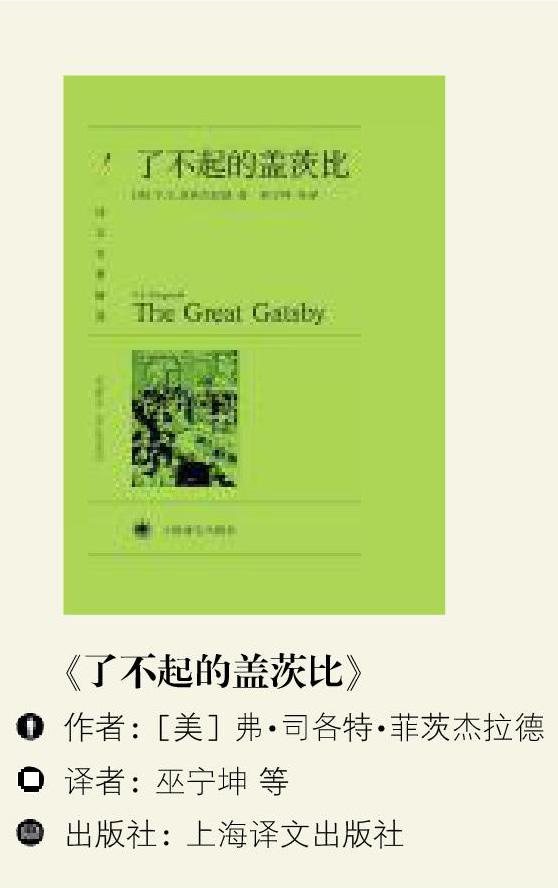

荐读人:李 唐
作品散见于《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热带》,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月球房地产推销员》,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小说奖。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大学以后读的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记得当时读完后心有戚戚,过了很久才从小说的氛围里缓过劲来。我也奇怪:打动我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只从故事的角度而言,它甚至是有点“狗血”和寡淡的:一对多年后重逢的情人,最终因为爱情酿成了悲剧。在如今的言情小说里,比这夸张、曲折的并不少见,可为什么偏偏《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经典?
我认为,这来自小说的情感力度。
简单来说,一部小说的力度往往并不在于其故事性。当然,精彩的故事可以为小说增色不少,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当读者被故事过分吸引时,作品的情感力度或许就被削弱了。
作品的力量构成是多方面的,比如象征性、语言、人物塑造、结构……《了不起的盖茨比》打动我的,主要就是这些方面,尤其是其象征性。
主人公盖茨比,年轻时曾迷恋富人家的女孩黛西。战争结束后,他成了富豪,可仍然心心念念想着黛西,尽管后者已经嫁作人妇。盖茨比渴望纯粹的、没有杂质的爱情,而那种爱几乎只存在于对往昔的追忆以及幻想中。于是,“爱”在这里成了“梦想”的象征。如同那盏绿灯,象征着希望。最终,当黛西开车碾死了丈夫的情妇,揽下责任的盖茨比成为黛西的“弃子”,死于死者丈夫的枪下——盖茨比的梦想破灭了,他为了梦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盖茨比的别墅里曾经夜夜笙歌,可是当盖茨比死后,却只有寥寥数人为他送葬。在世人眼中,盖茨比是个傻子、异类,不值得同情,他们只追求岁月静好和表面的繁华,骨子里却是腐朽不堪的,更不用提梦想——而这正是不切实际的盖茨比的动人之处。
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盖茨比家去时,我是少数几个真正接到请帖的客人之一。人们并不是邀请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车子把他们送到长岛,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们总是出现在盖茨比的门口。一到之后总会有什么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介绍一下,从此他们的言谈行事就像在娱乐场所一样了。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根本没见过盖茨比,他们怀着一片至诚前来赴会,这一点就可以算一张入场券了。
我确实是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一清早,一个身穿蓝绿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的草地,为他主人送来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请柬,上面写道:如蒙我光临当晚他的“小小聚会”,盖茨比当感到不胜荣幸。他已经看到我几次,并且早就打算拜访,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未能如愿——杰伊·盖茨比签名,笔迹很神气。
晚上七点一过,我身穿一套白法兰绒便装走过去到他的草坪上,很不自在地在一群群我不認识的人中间晃来晃去——虽然偶尔也有一个我在区间火车上见过的面孔。我马上注意到客人中夹着不少年轻的英国人:个个衣着整齐,个个面有饥色,个个都在低声下气地跟殷实的美国人谈话。我敢说他们都在推销什么——或是债券,或是保险,或是汽车。他们最起码都揪心地意识到,近在眼前就有唾手可得的钱,并且相信,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钱就到手了。
我一到之后就设法去找主人,可是问了两三个人他在哪里,他们都大为惊异地瞪着我,同时矢口否认知道他的行踪,我只好悄悄地向供应鸡尾酒的桌子溜过去——整个花园里只有这个地方,一个单身汉可以流连一下而不显得无聊和孤独。
我百无聊赖,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的最上一级,身体微向后仰,用轻藐的神气俯瞰着花园。
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我觉得实在非依附一个人不可,不然的话,我恐怕要跟过往的客人寒暄起来了。
“哈罗!”我大喊一声,朝她走去。我的声音在花园里听上去似乎响得很不自然。
“我猜你也许会来的,”等我走到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答道,“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带感情地拉拉我的手,作为她答应马上再来理会我的表示,同时去听在台阶下面站住的两个穿着一样的黄色连衣裙的姑娘讲话。
“哈罗!”她们同声喊道,“可惜你没赢。”这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她在上星期的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两个穿黄衣的姑娘中的一个说,“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儿见过面。”
“你们后来染过头发了。”乔丹说,我听了一惊,但两个姑娘却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了,因此她这句话说给早升的月亮听了,月亮和晚餐的酒菜一样,无疑也是从包办酒席的人的篮子里拿出来的。乔丹用她那纤细的、金黄色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下了台阶,在花园里闲逛。一盘鸡尾酒在暮色苍茫中飘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同座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和三个男的,介绍给我们的时候名字全含含糊糊一带而过。
“你常来参加这些晚会吗?”乔丹问她旁边的那个姑娘。
“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一次,”姑娘回答,声音是机灵而自信的。她又转身问她的朋友,“你是不是也一样,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一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我从来不在乎干什么,只要我玩得痛快就行。上次我来这里,我把衣服在椅子上撕破了,他就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不出一个星期我收到克罗里公司送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你收下了吗?”乔丹问。
“我当然收下了。我本来今晚准备穿的,可是它胸口太大,非改不可。衣服是淡蓝色的,镶着淡紫色的珠子。二百六十五美元。”
“一个人肯干这样的事真有点古怪,”另外那个姑娘热切地说,“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谁不愿意?”我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两个姑娘和乔丹诡秘地把头靠到一起。
“有人告诉我,人家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有位先生也把头伸到前面,竖起耳朵来听。
“我想并不是那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多半是因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
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听过一个人这样说,这人对他一清二楚,是从小和他一起在德国长大的。”他肯定无疑地告诉我们。
“噢,不对,”第一个姑娘又说,“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战期间他是在美国军队里。”由于我们又倾向于听信她的话,她又兴致勃勃地把头伸到侧面,“你只要趁他以为没有人看他的时候看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
她眯起眼睛,哆嗦了起来。露西尔也在哆嗦。我们大家掉转身来,四面张望去找盖茨比。有些人早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事情,现在谈起他来却这样窃窃私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他引起了人们何等浪漫的遐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