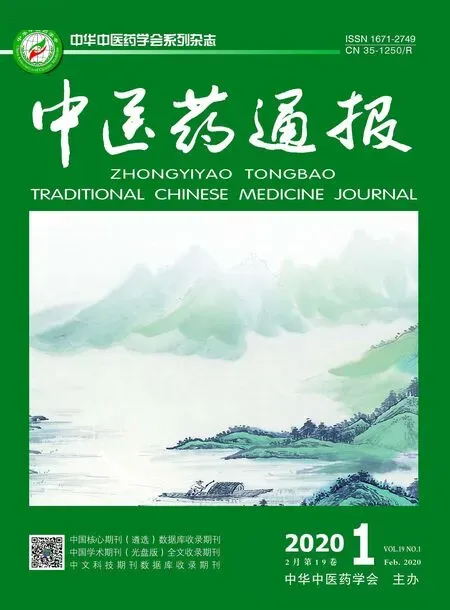龙胆泻肝汤的渊源及临床运用概况
2020-01-13王建青
●王建青
龙胆泻肝汤清肝胆火,利肝经湿热,疗效确切,一经出现便广为流传。虽然其应用在历代医家的临床中不断完善,但关于龙胆泻肝汤仍存有不少争议。今明辨之,以为更好地服务临床。
1 龙胆泻肝汤之“源流”
1.1 龙胆泻肝汤之“源”关于龙胆泻肝汤之源,《方剂学》五版教材做了简要说明,现对其进行进一步补充[1]。
有人认为本方是李东垣方,笔者查《兰室秘藏》所载本方为名同药异,少黄芩、栀子、甘草;有人认为本方出自《局方》,然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未见记载本方。《医宗金鉴》所载,方凡二见,一见于《外科心法要诀》,其方引自《外科正宗》,也是名同药异,少柴胡,多黄连、连翘;一见于《删补名医方论》,其方引自《医方集解》,该书中汪昂注源于《局方》。汪昂认为龙胆泻肝汤出自《局方》,但查无所获,可能是抄录之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从元丰到嘉定,前后经历了约140 多年的修撰,通过诸家之手校订,广纳当时医家及民间有效方剂,多次增补鲜有删减,有南宋、元、明、清各代10 余种翻刻本。像龙胆泻肝汤这样的验方,散佚的可能性甚微。
其后诸家多遵《医方集解》,有《成方切用》《银海指南》《重订广温热论》等,方药与《医方集解》完全相同,都注明方源于《局方》。因《局方》中查无此方,故方源暂用《医方集解》。龙胆泻肝汤由龙胆草(酒炒)、栀子(酒炒)、黄芩(炒)、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酒洗)、生地黄(酒炒)、柴胡、生甘草组成,治肝胆经实火湿热,胁痛耳聋,胆溢口苦,筋痿,阴汗,阴肿,阴痛,白浊溲血[2]。
除此以外,还有人认为龙胆泻肝汤源自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成书于宋1237 年)、《外科精要》(宋1263 年)及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宋1241 年)。查《妇人大全良方》未见记载,而在薛己(明1487-1559 年)《校注妇人良方》有载,较《医方集解》同名方少柴胡一味。另两部书均被薛己所校注和增补过,《外科精要》中的龙胆泻肝汤出现在“愚按”中[3],而“九味龙胆泻肝汤”出现在该书附方中,并明确标注“愚制”[4]。说明这三部书中收录的龙胆泻肝汤均是明代医家薛己添加。
龙胆泻肝汤亦见于李东垣《兰室秘藏》及《东垣试效方》,两书中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后者可能非罗天益整理刊行而是他人拼凑所成,故不作论。《兰室秘藏》成书于李东垣病逝(公元1251 年)前的数年间,25 年后(1276 年)由东垣弟子罗天益交付刊行。书中“阴痿阴汗门”一章中载有一案:“一富者前阴臊臭,又因连日饮酒,腹中不和,求先师治之。曰:夫前阴者,足厥阴肝之脉络循阴器,出其挺末。凡臭者,心之所主,散入五方为五臭,入肝为臊,此其一也。当于肝经中泻行间,是治其本;后于心经中泻少冲,乃治其标。如恶针,当用药除之。酒者,气味俱阳,能生里之湿热,是风湿热合于下焦为邪。故《经》云:‘下焦如渎’,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酒是湿热之水,亦宜决前阴以去之。龙胆泻肝汤,治阴部时复热痒及臊臭。”
原注:此药柴胡入肝为引,用泽泻、车前子、木通淡渗之味利小便,亦除臊气,是名在下者引而竭之;生地黄、草龙胆之苦寒,泻酒湿热;更兼车前子之类以撤肝中邪气;肝主血,用当归以滋肝中血不足也[5]。
自此,基本确认李东垣之方是今龙胆泻肝汤的“前世”。
1.2 龙胆泻肝汤之“流”李东垣之后,该方加减化裁形成清热利湿派和滋阴清热派两派。
清热利湿派在继承原来清热利湿的思路上各有发挥,多用于治疗外科、皮肤科疾病。代表医家有明代薛己的《校注妇人良方》,书中载药比今之龙胆泻肝汤少柴胡,治疗肝经湿热,两拗肿痛、腹中痛、小便涩滞;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所载少柴胡,多连翘、黄连,治肝经湿热之前后阴肿烂赤痛;清代翁藻《医钞类编》中所载少柴胡,多连翘、大黄,治疗缠腰火丹;清代鲍相墩《验方新编》中所载少栀子、柴胡,治疗肝胆经实火、湿热、胁痛、耳聋。
滋阴清热派去该方中利湿药加滋阴药形成滋阴清热方剂,多用于治疗内科、妇科疾病。始于东垣弟子罗天益《卫生宝鉴》,书中所载方较今之龙胆泻肝汤少生地、当归、车前子、木通、泽泻,多人参、天冬、麦冬、五味子、黄连、知母,清热滋阴以治疗胆瘅;明代秦景明《症因脉治》中所载少生地、当归、车前子、木通、泽泻,多黄连、知母、麦冬,治疗肝经伏火,施泄下血;清代竹林寺僧《竹林女科证治》中所载为罗天益方减麦冬而成,治疗暴怒伤肝而动火、产后产户不闭。
2 龙胆泻肝汤证
如果说桂枝汤证即太阳中风证,那龙胆泻肝汤证即是肝经湿热证。正是因为龙胆泻肝汤的创立,才逐步完善了肝经湿热证。《灵枢·经脉》中关于足厥阴肝脉的循行为肝经湿热提供了理论基础。书中提到“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癞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但直至龙胆泻肝汤的产生,才正式确立了肝经湿热证。肝经湿热证首见于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后见于《校注妇人良方》,如前所述,这两部书均被薛己校注过。薛己自著的《外科发挥》中加减龙胆泻肝汤也是用于治疗肝经湿热证,故薛己是第一位提出肝经湿热证的医家。薛己之后《外科正宗》《疡科选粹》(明·陈文治)等医著逐渐确立了肝经湿热证。到清代汪昂《医方集解》龙胆泻肝汤除了治疗肝经湿热诸症,还治疗肝经实火症,而肝经湿热证在5 版《中医诊断学》(1984 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出版)更名为肝胆湿热证。
《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水液代谢与肺、脾、肾、膀胱、三焦关系密切,湿热的产生更多与脾胃有关,言及肝者较少。肝经如何生湿热?清代张秉成《成方便读》提到“夫相火寄于肝胆,其性易动,动则猖狂莫制,挟身中素有之湿浊,扰攘下焦,则为种种诸证;或其人肝阴不足,相火素强,正值六淫湿火司令之时,内外相引,其气并居,则肝胆所过经界,所主之筋脉,亦皆为患矣”[6],从内外两方面作了解释。在李东垣的病案中富人嗜食肥甘厚味及酒,滋生湿热,与风湿并入下焦,散入肝经形成肝经湿热,这与今人产生湿热方式较为契合。
3 龙胆泻肝汤中柴胡、生地黄功效
方中龙胆草、黄芩诸药功效无异议,唯柴胡、生地黄尚有争议。
多数医家认为柴胡在方中为引经药,此种观点始于《兰室秘藏》,今《方剂学》五版教材亦如此解释;部分医家则认为柴胡在方中起疏散清热的作用。成都中医药大学邓中甲教授直言,龙胆泻肝汤中均是入肝经药,何须用引,柴胡就是行使其自身功效。笔者偏于支持后者观点。
《兰室秘藏》中认为生地黄、龙胆草苦寒,泻肝经湿热。吴谦、汪昂等医家认为生地黄起养血补肝作用,因方中苦寒、利湿药偏多,地黄、当归以养血补肝,以免伤肝。笔者以为,龙胆泻肝汤中用地黄绝不是用其滋阴养血作用以防方中苦寒利湿药伤阴,如是为此,白芍酸苦配合甘草酸甘化阴更为合适,或不用生地黄仅用当归一味药足矣,既通血脉养肝血,又祛湿不留邪。若用地黄泻肝经湿热不免有些牵强,地黄泻热之力毕竟有限,干地黄性味甘寒,鲜地黄苦寒,纵是用鲜地黄清热祛湿力也不及黄芩(东垣方中无黄芩)。《神农本草经》:“干地黄,味甘寒。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做汤,除寒热,积聚,除痹,生者尤良。一名地髓。”生地黄既有添精养血的补益作用,又有通经泻热的清泻作用,所以在龙胆泻肝汤中生地黄既可养肝体,又能助肝用。
4 龙胆泻肝汤之“量”
读前人方书,龙胆泻肝汤普遍药量偏小,以龙胆草为例,多用一钱,少至三分,很少超半钱。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7]将宋代权衡的单位量值厘定为1 斤折合约661g,l 两折合约41.3g,10 钱为l两,10 分为1 钱,则1 钱折合约为4g,1分约0.4g。《兰室秘藏》中详细记录了龙胆泻肝汤的药量及煎服法,“柴胡梢、泽泻(以上各一钱),车前子、木通(以上各五分),生地黄、当归梢、草龙胆(以上各三分)。上锉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三盏,煎至一盏,去粗,空心稍热服,便以美膳压之。”看似药量偏小,但将所有药“锉如麻豆大”再煎,采用的是煮散法。《中药药剂学》解释煮散为:中药材粉碎成粗颗粒或粗末与水共煮去渣取汁或连渣共服的液体剂型,能节省药材而又能发挥治病作用,实与今日所用汤剂量相近[8]。该煎煮法兴盛于宋朝,《太平圣惠方》中几乎全用煮散。虽然到明清时期煮散法逐渐回归汉唐时煎汤法,但可能受其影响,龙胆泻肝汤药量一直偏小。该方为苦寒清泻剂,为避免损伤脾胃及耗伤阴液,在不影响药效的情况下医家们刻意用小剂量也是存在的。
5 龙胆泻肝汤应用与研究概况
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龙胆泻肝汤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多个领域,如精神类疾病:失眠、非根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胆疾病:乙肝、药肝、胆囊炎等;妇科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霉菌性阴道炎、慢性盆腔炎等;男科疾病:前列腺炎、睾丸炎、阳痿;五官科疾病:鼻窦炎、中耳炎、口腔溃疡、突发性耳聋等[9]。
龙胆泻肝汤在皮肤科领域应用尤为广泛。朱仁康先生在原方基础上去当归、柴胡,加六一散,增加利湿功效[10];赵炳南先生去当归、柴胡,加连翘、牡丹皮,增加凉血解毒作用,治疗皮炎、湿疹、下肢丹毒、带状疱疹等病[11]。杜锡贤教授则去木通,加金银花、土茯苓、牡丹皮,除了治疗湿疹、疱疹、过敏性、病毒性皮肤病外,还可治疗银屑病、药疹、紫癜、天疱疮等皮肤病及性病,辨证时局部皮疹的红、肿、湿、热及微观病理所表现为细胞内、细胞间水肿以及炎症细胞浸润,都可以用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12]。
现代研究表明,龙胆泻肝汤有抗炎、抗病毒、利尿作用,可改善血液循环及组织的血氧供应,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有提高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作用及显著的镇痛作用[9,13-14]。
在实验条件下,龙胆泻肝汤对小鼠主要的生理生化参数影响不大,不影响肝脏合成功能,对肝脏、心肌及肌肉组织没有毒性作用,反而有一定保护肝功能作用;在相对短时间内(4周)常规剂量服用龙胆泻肝汤对肾功能没有不良作用[9]。拆方实验,龙胆泻肝汤的肾损伤轻于等量关木通(6g/kg),血清肌酐、尿素氮及尿蛋白水平均低于单味关木通组(P<0.05);龙胆泻肝汤去当归、生地黄、甘草方的肾毒性强于龙胆泻肝汤[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