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漫画后面的人
2020-01-12莉莉吴
莉莉吴
我现在的职业,是漫画编剧……
这句话说出口时,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就像是梦话只说了半截,变成了一个影子的梦游。漫画编剧并不等于漫画家,认真地说,我更像是一部漫画作品下的一颗螺丝钉——有我在,很好;没我在,也没关系,换一颗就好了。
可是我并不想当螺丝钉,文人的风骨让我想当举锤子的人,捶碎颅骨,死而后生。
是以,我笔下的画面总是宏大的,写满了少年意气,快意恩仇,仿佛一把无鞘的宝剑,凛冽逼人。然而领导并不喜欢我的脚本,嫌弃它们太平铺直述,不能抓人眼球。最后,他叫我去看看市面上受欢迎的漫画作品,让我去媚俗。
《王子与灰姑娘》《霸道总裁爱上我》《冷面王爷俏皇妃》……这些作品充斥于各大平台的榜单之中,如同琳琅塑料花束,呈现着一种廉价的美丽。我素不喜欢这种快餐作品,如今却要捏着鼻子看下去,写出来,交上去。
公司的编剧众多,常常多人同写一个项目,比稿,然后按评级拿钱。我常常能在比稿时胜过他人,可等到评级时,依然是普普通通、无功无过的B级,仿佛一张无声开合的嘴唇,肆意地嘲笑我平庸的人生。
我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发现自己的工作内容是讨好读者后,我便抛弃了所有的坚持与自矜,写了许多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可即便是这样,我写出来的东西依然不够好,它们看起来花团锦簇,可它们都不是真的,因为“我的花都被吹掉了,可我得忍着”。
美剧《小谢尔顿》中,谢尔顿向父亲抱怨自己的工作,说自己每天为了钱而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然而他的筋疲力尽并没有换来多少钱,因此他觉得很痛苦。而我正在经历这份痛苦。
在成为漫画编剧之前,我做过银行客服,做过网站新闻编辑,皆因为工作需要频繁地与人交往而感到疲累,最终辞职。我想要一份安静的工作,朝九晚五,双休,最好能与写作有关。于是我投了简历,成了一名漫画编剧。
公司很好,我们可以叫老板的全名,可以在公司的按摩椅上休息,每个月都有一次生日会,会提供甜美可口的蛋糕……最令人惊喜的是,公司养了一只美短猫,肥硕慵懒,从不惧人,常常会翻他人的抽屉,偷零食吃。
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氛围,遂暗暗发誓,一定要留下来。
试用期间,我每周要写80页脚本,其中“少年漫”和“少女漫”项目各占一半,情绪要快速地来回切换,不能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最焦虑的时候,我将十个手指的指甲都抠烂了,却因为自己心神不定,丝毫不觉得疼。
太难了。脚本的创作完全不同于我之前的写作,它不需要精巧的比喻与细腻的描述,不需要复杂的布局,它要精简,要浅显,要配合画手的工作,因为它只是工具而已。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试用期的,总之,在转正后,我正式成为一名“少女漫”编剧。然而,公司的重心全在“少年漫”上,我们的《驭灵师》畅销中日韩三国,常年盘踞于少年榜第一的位置,然而“少女漫”却无人问津。
后来,我写了新的少女漫企划,通过,立项,动工,一年后,它在腾讯的人气破50亿,成为当之无愧的“少女漫”第一名。人人都在讨论它,可它并不是我的荣誉,因为它是公司集体创作的,而我只是一颗螺丝钉而已,是最不起眼的那一颗。
我的写作始于倾诉欲,因为孤独,所以想要人听见我的声音。可是漫画编剧不是这样的,它要求我躲在幕后,然后摧毁我引以为傲的一切。
我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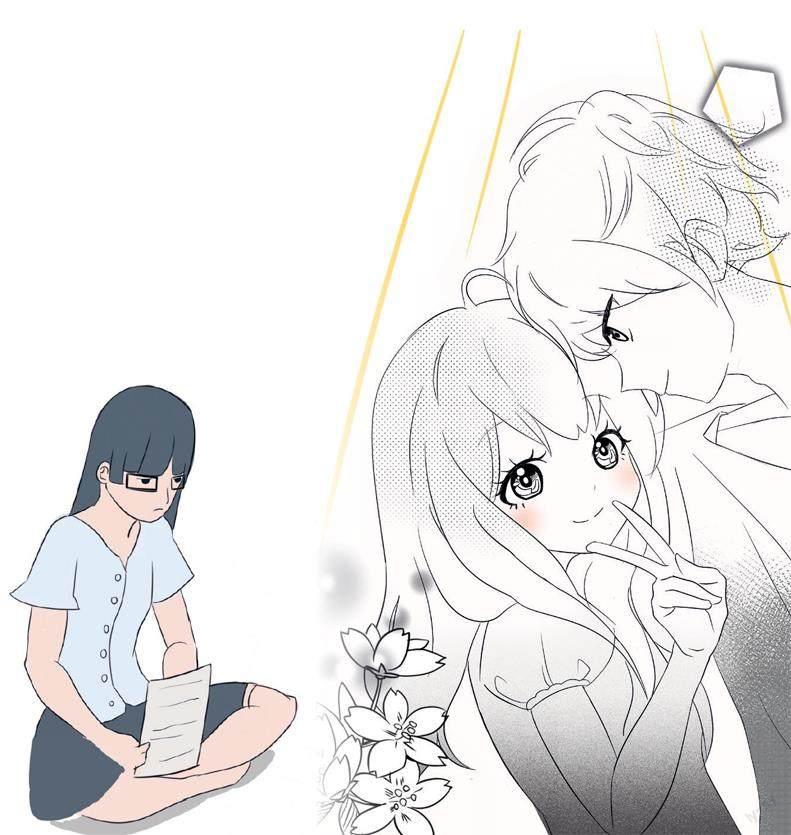
长久以来,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建立在他人的态度之上的:他们说我做得好,我便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们说我太糟糕了,我便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卑由骨里生,万般不如人。”
自从做了编剧之后,我成了幕后的影子,可那份攀比依然如附骨之疽,如影随形。我常常在出评级前感到焦虑,在出评级后觉得沮丧:在我的绩效表上,鲜红色的“B”如同一枚海边的落日,宣告着长夜将至。
可我想要一份A级的人生。
我开始在作品里夹带“私货”。我尽可能地在公司的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情感,让配角拥有我钟爱的特质:沉默、温和、笃定,愿意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切。这份改动很不起眼,偶尔有读者辨识到,夸赞一句,我便会心生欢喜。
有時候我也会想:我会在这个行业走多远?漫画编剧与其他职业不同,它的门槛极低,几乎是识字便可入行,因此极难混出头,哪怕手下有大火的作品,扬名的也只是工作室与画手,与编剧并无关系。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他们甚至不知道有漫画编剧这个行业,以为一切像日本漫画里面一样,一部漫画仅由漫画家和他的助理完成。
可我们是存在的。即便微小、卑弱、粗糙,如同荒野上的苔花,可我们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在思考,在呐喊。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我是漫画编剧,我想,我不仅仅是在谋生。
梁衍军//摘自《中学生百科·悦青春》2020年第6期,王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