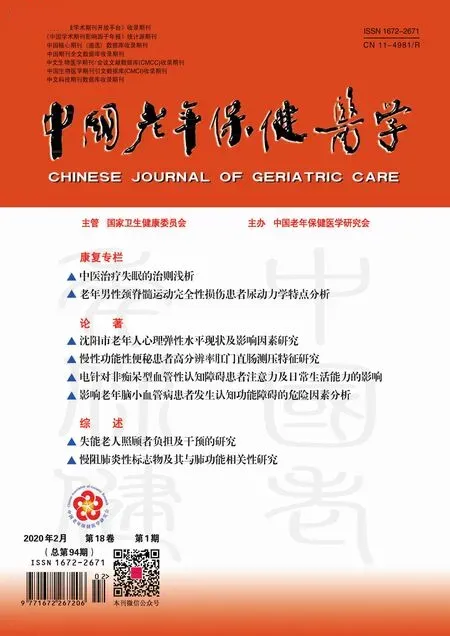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及干预的研究
2020-01-12何青松邱元芝朱海萍
何 香 何青松 谢 绮 邱元芝 朱海萍
作者单位: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虽然我国尚低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但老年人失能问题同样突出。李晓鹤[1]在2010~2060年失能老人动态预测中指出,目前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65岁以上老人平均失能率为20%,我国65岁以上老人失能率为19.17%,推算60岁以上失能老人年增长率为4%,预计2025年失能老人数约7279.222万,之后于2050年后达最高峰,失能老人数约1.29亿。丁华通过对7000多名老年人在2011年至2015年跨年追踪失能率变化的分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中、重度失能老人失能率增长快速,失能程度明显加深[2]。国内外[3,4]研究一致认同:失能老人失能程度越重,愈加重照顾者的负担。这无疑会给失能老人照顾者带来持续性加剧的负性体验,不利于满足失能老人的照顾需求,共同造成失能老人和照顾者生活质量的下降。本文旨在从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现状和需求出发对干预措施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减轻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
1.照顾者负担
照顾者护理负担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Grad和Sainsbury定义照顾者负担的概念[5]为:照顾病患时,家人所付出的代价。George[6]指出:照顾者负担即承担成员在照料病患时带来的心理、躯体、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问题。Zarit将其总结为“照料者由护理的负面影响而经历了失落、社交孤立等消极感受,并遭受长期的精神、情感、社会、身体和经济等方面的不良结果”[7]。综合以上,照顾者负担在我国起步晚,概念方面以国外研究为先导,而负担来源于被照顾者给照顾者在原本的日常生活、心理情感、社会参与等方面带来的改变,我们基本倾向于将这些改变划分为不利的。
2.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现状
现今对照顾者负担现状的研究主要分为问卷调查形式的量性研究和面对面或电话等多种形式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
2.1 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现状的量性研究 国外已有评估和监测照顾者负担的成熟量表,主要是Zarit护理负担量表(ZBI)[8]、照顾者负担量表(CBI)[9],并被国内译制后应用于各种疾病患者的照顾负担,尤其Zarit护理负担量表(ZBI)具有信效度良好、简易、灵敏等优点,应用最广泛。在南昌市对147名社区居家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研究[10]中,照顾者总负担得分为30.01±12.86分,为轻度负担水平,其中,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的照顾者总负担得分为36.47±12.37分,高于其他疾病组照顾者总负担得分;提示应侧重关注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的照顾者负担,与国内外[11,12]研究结果一致。杭州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135名失能老人及其家庭照顾者进行调查[13],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总分为39.56±12.88分,高于居家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总得分,提示应加强对失能老人在院期间照顾者负担的监测。宁夏回族自治区某市社区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研究[14]中,总负担得分为48.32±15.19分,为中度负担水平,高于杭州市医院和南昌市社区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水平,主要考虑失能老人失能程度较重和照顾者也已进入老年期所致。
以上各时期、各地区对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量化研究均采用Zarit护理负担量表(ZBI),体现了国内外对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量化研究的深入,至于负担程度间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但我们应该关注量性研究中对较高负担照顾者人群的指向作用,以筛选急需干预人群或对象。
2.2 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现状的质性研究 Wittenberg Eve[15]通过对49名患有慢性病的家庭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化电话访谈,围绕照顾过程是否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幸福、他们的照顾责任和亲属的健康状况进行访谈。访谈数据采用主题分析,受访者提到他们经历了心理和非健康方面的影响,其次是身体方面的影响,他们表示健康情绪的影响主要为情感表露,非健康影响通常包括日常活动变化和护理提供,并且这些影响有着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胡曾玲[16]在对15名社区失能老人照顾者的照顾负担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的质性研究中,提取出了照顾者多角色冲突、健康受损、心理疲惫、社交自由受限、照顾知识与技能欠缺、与失能老人沟通障碍、突发意外应对困难、社区无障碍设施陈旧等8个主题。
由此可见,国内外对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质性研究相对要少。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照顾者负担的质性研究结果不是单一的消极心理感受,不排除在国外隔代联系没有我国隔代联系紧密的情况下,照顾家人的这个过程也会给照顾者带来心理上情感的满足,这与我国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质性研究结果之间存在让人深思的差异,可认为这是对照顾者负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应忽略挖掘对照顾者有利的影响因素。
3.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干预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失能老人和照顾者都会存在个体的需求,正是因为失能老人的自理能力下降,需求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照顾者,构成了照顾者的负担。有研究[17]表明,照顾者负担与照顾者生活质量存在负相关,即照顾者护理负担的加重会降低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失能老人不能满足的需求越多(即失能老人生活质量越低),照顾者负担越重,照顾者生活质量下降(即照顾者未满足的需求也同样增加)。本研究认为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干预措施也应考虑从失能老人和照顾者亟待满足的需求出发。
3.1 失能老人及其照顾者的需求
3.1.1 失能老人的需求:失能特征[18]包括:①失能主要指影响个体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相关的活动和参与上的表现;②是个体在其生活环境下的健康状况及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③个体有疾病或异常不一定失能,个体是否失能需考虑其健康状况是否导致活动受限和参与限制;④失能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功能或环境的支持度改变时,失能的情况也会跟着改变。老年人也并不是疾病或异常情况下就一定会失能,而是在原本自我或借助功能或环境支持下能满足正常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因老化、疾病或异常等情况造成其自我满足需求的能力下降(即自理能力下降)。
Slaughter[19]发现英国养老机构失能老人平地行走和自我吃饭的需求未满足率为81.5%。王玉环[20]调查援疆汉族居家失能老人表明,满足率最高的需求为人际交流、尊重隐私、倾诉。杜远征则表示城市失能老人与农村失能老人相比较,对独自打电话、洗衣服床单、自己按时吃药、独自乘车外出等事情的未满足率较高。陈申[21]、陈柳柳[22]研究发现,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未满足率较高的日常生活需求是平地行走、上下楼梯、坐车出行、娱乐爱好和社会交往。刘运东[23]则发现失能老人未满足率较高的需求是心理方面,反而未满足率最低的需求是日常生活照料。辽宁省锦州市社区和机构失能老年人调查表明,机构养老的失能老人与居家失能老人相比较,未满足率较高的需求是康复、饮食,但心理方面未满足率则较低[24]。南京市303名社区失能老人进行未满足需求评估量表调查[25]发现,失能老人每人平均有(4.98±3.17)项未满足需求,未满足率最高的5项需求为坐车出行(77.2%)、上下楼梯(73.1%)、娱乐(72.1%)、社交(62.6%)、平地行走(60.1%)。
综上所述,未满足率最高需求的不同主要考虑地区差异的因素,比如援疆汉族失能老人和城乡失能老人;社区失能老人日常生活需求满足率比养老机构失能老人满足率较高,主要考虑社区失能老人照顾者为亲属关系,一般为一对一或多对一的照顾,能较好地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未满足率较高的需求提示研究者要更多关注失能老人在自身或照顾者等协助下实现了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安全需求(平时或坐车出行、上下楼梯)、情感需求(倾诉、人际交流、娱乐、社交)、尊重需求(尊重隐私)的实现,以提高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降低照顾者的负担。
3.1.2 失能老人照顾者的需求:因失能老人自理能力下降,给照顾者在日常生活、生理、心理、经济和医护等方面需求带来改变。
张曼秀[26]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河北、河南、天津等8个省对450例失能老年人照顾者进行需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照护失能老人的知识与技能方面(不适相关知识、安全用药指导、疾病相关知识、康复指导、居家环境安全指导等)和对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服务方面(经济协助、转诊和协助信息、缓解压力指导等)有较高的需求。黄润晗[27]在江苏南通市、新疆博乐市、安徽安庆市以及青海西宁市对303名社区失能老人照顾者的需求调查中发现:在需求来源方面,照顾者对来自社会机构帮助的需求率最高(64.4%),对来自家庭帮助的需求率排第二位(61.1%),其他依次为来自亲戚(41.6%)、朋友(8.9%)和邻居(8.3%)的帮助;在需求内容上,前5位的需求从高至低依次为照顾知识和技能的支持(64.4%)、经济支持(62.0%)、喘息服务支持(42.2%)、家政服务支持及心理支持等。孙柳[28]在徐州市对120名社区失能老人照顾者护理需求调查表明,照顾者在医疗康复方面(家庭氧疗、管路护理、疾病预防、测血糖、康复训练、测血压)、紧急救援方面(病情监测,慢性病急性发作时的现场处理,心肺复苏)的护理辅导需求较强(≥60%)。
在照顾失能老人的活动和过程中,失能老人照顾者突出的需求问题主要有,期望来自社会机构关于照顾知识和技能的支持(特别是对失能老人医疗照顾方面),来自社会机构或家庭的经济支持、喘息服务支持及心理支持等。从提高失能老人护理质量的目的出发,对这些照顾者的照护需求进行干预,有利于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3.2 干预措施
3.2.1 针对失能老人需求的干预措施:为了提高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改善失能老人的自理能力,满足失能老人的个人需求,有研究[29]表明,将介护技术联合序贯护理干预失能老人,尤其是对失能老人进行益智(语言、记忆、思维、认知及定位)、自理能力(吃饭、穿衣、服药、刷牙、梳头及洗碗)、生活处理能力(洗衣、剪指甲、定时如厕、打电话及处理钱财等)训练、功能锻炼(行走能力和平衡能力)等进行针对性需求的设计和实施,能有效延缓老人的失能进程,并将介护技术延续[30]至社区,持续干预失能老人,能提高失能老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徐言明[31]基于现有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按照现有家庭病床管理要求,将家庭病床干预应用至社区失能老人,对失能老人进行至少每周1次,连续6月,提供个案式健康教育、康复指导、心理疏导、诊疗护理等上门服务,明显提升了失能老人以行走为代表的日常活动能力及失能老人和照顾者的主观幸福感。朱燕珍[32]运用积极情绪书写表达干预于社区有一定书写能力的部分失能老人,进行对照研究发现,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得到了有效提高。
3.2.2 针对失能老人照顾者需求的干预措施:对于失能老人照顾者对照护知识和技能的需求,除了依靠传统的社区讲座、宣传海报或手册,已有学者[33]在我国安徽、上海、山西、广东、黑龙江五省对家庭照料者需求投入体现在穿衣、吃饭、照顾外表、帮助如厕、洗澡、与患者交流、帮助使用交通工具、监督老人8个方面,进行针对性有需求的照护技能培训,有效减轻了照顾者负担。也有研究者[26]根据数据网络时代,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对失能老人照顾者提供图文并茂、实用性强、关于失能老人照护知识和技能的健康宣教,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针对失能老人个体特点进行自主选择,反复学习,便利了照顾者照护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值得推广。国外对失能老人照顾者照护知识和技能的干预措施较我国相对成熟,主要包括照顾者角色训练、志愿者教育与家访相结合、基于网络的支持项目等近20种形式[34]。
对于失能老人照顾者的经济需求,日本的干预措施走在我国的前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35]已实施了20年,得到了很好的完善;同时,日本《介护保险法》规定,被保险老人的缴费构成比例由个人和政府共同筹资。老人接受服务过程中,个人支付10%,由被保险人定期缴纳的保险费和政府共同支付90%,这无疑有效减轻了被保险老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2014年我国财政部、民政部联合全国老龄办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36],此项补贴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现,具体实施还未见成效,需要进一步立法保障等完善问题。
对于失能老人照顾者喘息服务支持的需求,国内外的基本形式包括养老院、日间服务等各种机构的暂时托管及养老护理员的上门服务[37]。目前,我国上海[38]、杭州[39]等多地也已开始尝试主要针对经济困难的失能老人家庭提供由政府支付服务费用的喘息服务。失能老人的照料是一个长期又繁杂的工作,家庭照顾者在传统孝道文化及喘息服务宣传不够等因素影响下,再加之地方对喘息服务支持的局限性,喘息服务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对于失能老人照顾者心理支持的需求,常见干预措施有对照顾者进行如讲座、座谈会、家庭访视和电话随访等各种形式的心理疏导、辅导教育[40]。Carrasco[41]以会议的形式向照料者提供控制紧张及压力的方法和认知重建技术。Cheng[42]利用益处发现干预模式,通过照顾者记录、话题讨论、照顾日记等形式,帮助照料者不断发现照顾的益处,降低照顾者的绝望、沮丧等消极感受。李笑晨[43]研究发现,以个案方式对有心理问题的失能老人照顾者进行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的认知重建,提升照顾者的自我认同感,降低照顾者的心理压力,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4.小结
老年人的失能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共性和重点问题。失能老人照顾者的负担成为近年来国内外老龄化、医疗、民生方面的研究热点。现阶段国内外对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已有较丰富的前期理论研究,如照顾者负担的界定、研究工具、影响因素等,对失能老人照顾者负担的干预措施主要为单一需求的健康宣教、技能培训和心理干预方面的研究,缺乏全面、综合的干预措施,呼吁更多的针对失能老人和照顾者综合需求的干预研究,呼吁建立我国健全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