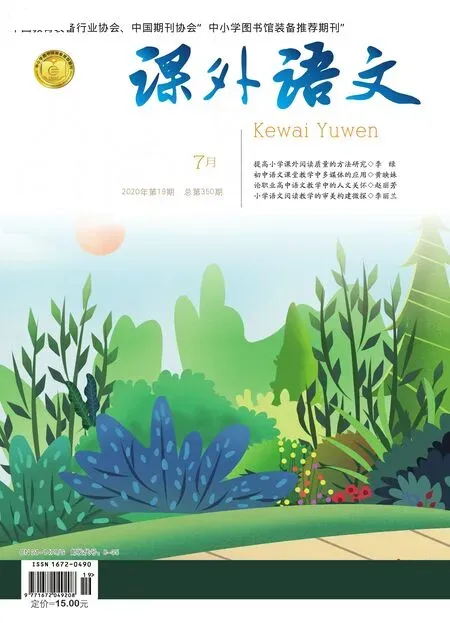语文和谐高效课堂建构探微
2020-01-10刘蔓
刘 蔓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金山高级中学,江苏 苏州 215128)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说:“语文课在整个人生中投下长长的影子,余韵无穷。”的确,语文课对中学生人格的养成、志趣的培养尤为重要。上好每一节课、为学生的发展助力是语文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我的成功与失败
作为一名新晋老师,教学中,我发现班级学生语文水平不高,表情达意能力不强。针对学生的症候,我每周给学生布置一篇阅读,让他们写读后感,课上围绕读本展开讨论。学生的文本分析趋同性高,大词空词满篇,细腻的感受、精准的分析遍寻无着。
于是我设计了一堂不设限阅读的教学课。课上我用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作为引子,引领学生探究谁是凶手。起初学生认为真相只有一个,结果当他们深入阅读时,发现预设失效,疑窦丛生。我引导他们关注叙事,涉案的7 个人提供了7 种叙事,这些叙事相互参照相互矛盾,致使案件扑朔迷离。由此,从文本叙事联想到语文阅读,得出语文解读应该是多元的。想要达到多元的阅读效果,应该去蔽求实,不设限,消解头脑中的定势思维,唤醒自己的感受组织,写出自己的发现、思考、感悟,甚至猜想。
课上我对不设限阅读做了细致说明,更新了学生对阅读材料的认识。阅读材料不再是传统认知上的死文本,它既边界清晰又无限延展。可将其视作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深挖材料内涵,也可以从材料迁移出去,读出广阔的外延。本质上,不设限阅读就是引导学生读出材料的内涵与外延。以《金锁记》为例,读出材料的外延,指提取阅读材料的符号性词语,探究词语的能指所指及词语间连缀所生成的外部指向。比如学生可以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衣饰考察当时上海的着装文化,可以基于小说中的历史信息,文史互证,还可以基于张爱玲对两性心理的刻画,尤其是女人间微妙的心里流动,读出当时上海太太小姐的心理结构。
读出材料的内涵,常规路径是人物形象、写作手法、语言特色、主题探讨。想要读出新意,可以采取四种方式:一是跳出单一文本,联系其他材料进行互文解读或参照分析;二是另辟蹊径,发现他人未发现之处;三是深入开掘文本,发现作者的隐匿情感;四是与自己的经历、与生活的当下相呼应。
学生的反馈积极正面,大家跃跃欲试,试图读出文本的新意。我感觉我成功了。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失败了,课堂上奇谈怪论频出。本意让学生独立思考、读出新意、自由表述,结果演变成了后现代教育对经典文本的肆意歪曲。何以造成如此局面,如何纠正学生肆意误读,成了我的困惑和迷思。
二、做语文教育大师的私淑弟子
疑惑的种子在我心底生根发芽,推动我展开探究。在孙绍振老师①的《读者主体和文本主体的深度同化与调节》中,我寻着了答案。
孙老师提出不管是拥立文本中心论,还是抱持读者中心论,都认为“从阅读到理解是一条直线,没有任何障碍”,忽视了人的预期。预期会使“感知只对目的开放,其余都封闭”。课堂上学生之所以说出各种旁逸斜出、令人费解的答案,是因为“学生主体图式中的当代生活经验和价值的封闭性压倒了开放性”。“阅读就是读者主体、文本主体和作者主体从表层到深层的同化与调节。脱离了文本主体和作者主体而放纵读者主体,就不能不产生奇谈怪论。”②读罢此言,如梦方醒。
针对语文课教改虽花样繁多却未能改变“上和不上一个样”的问题,孙老师提出了“读出经典文本的三个层次”和“两个解决办法”,给我很大启发。
他认为经典文本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显性感知层,即外在的言谈、行为。这一层最浅表,学生可以一望而知,教师应“从学生的一望而知指出他的一望无知,甚至再望也还是无知”,引领学生进入文本阅读的第二层——隐性层。隐形层是“潜在的‘意脉’变化、流动的过程”。在把握上,一要关注完整“意脉”连续性中的曲折性,第二要关注情志的深化,第三层次更为隐秘,指“文体形式的规范性和开放性,还有文体的流派和风格”。
得文本分析之门,还须两个方法——还原和比较。还原,即消除心理预期,推动内心图式的开放,“把未经作家主体同化(创造)的原生形态想象出来”,呈现事物的本真,读出作者驾驭文体形式的才华。光看懂,看明白,还不够,还要追问假设由我来写,该怎么行文。以艺术形象与原生形态、作者叙述与我之叙述的差异,作为分析的切入口,读出经典文本的深度。比较,就是把几个经典文本加以对照分析。孤立地阅读难以深入体会经典作品的神妙,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好地读出含蕴在经典文本中人格与风格的精彩。
孙老师的文章解答了我的困惑,更新了我的教育方法,帮助我找到了语文和谐高效课堂建构的新坐标——回到语文。在正确方法论的指导下,我的教学水平明显提升,课堂上学生的奇谈怪论少了,鉴赏的积极性高了,收获也更多了!
三、回到语文的语文教育
当前中学语文课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面对异彩纷呈的教育大观,北大教授钱理群无不忧虑。在与孙绍振老师对话语文时,钱老表达了对当前语文教育的担心,课堂教学热衷搞形式主义,不解决实际问题,许多学校矫枉过正,乱改一气③。钱老的忧虑不无道理。想要推动课改走向实际,有必要重新思考语文教育的目的。叶圣陶在《教育与人生》④中提出教育的目的是知识传递与人格养成,完全适用于语文教育。实用性与人文性并举,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内涵。从这个内涵出发,要想使语文教育落到实处,应该回到语文。
回到语文指摆脱附着在语文教育上的种种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工具技术,以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深入思考、自由表达,塑造良好的人格为旨归,让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老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打开思路,为他们提供适宜的指导,具体操作是重建语文课堂。
首先,重塑语文课。语文课是发现课、探索课。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⑤。在发现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展开探究。兼具求知和审美,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其乐无穷⑥。
其次,精选读本,在阅读、鉴赏与阐释上狠下功夫。老师引领学生围绕读本展开阅读,和学生一道去探索发现。先动用感官看,再咀嚼细尝,进行知识思辨,辨别结构、主旨,然后深入其境,用整颗心与文本相视,寻求情感的共振⑦。课堂上师生可以就同一题材不同作者的不同篇目展开阅读,也可以围绕同一主题,让学生阐发自己的构思,比较自己的构思与作者的差异,进而体认作者的叙事方式及情怀意绪。还应重视有声阅“读”,把文章的神情理趣、声调读出来,让学生耳与心谋,深切了解文本内涵⑧。
语文教育涉及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是为学生的一生打底子的,堂奥颇深,不容忽视,语文课改必须负重前行,“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想象力’与‘批判意识’”⑨。
注释
①孙绍振,1960 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孙绍振:《读者主体和文本主体的深度同化与调节》,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6 页。
③钱理群、孙绍振:《对话语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5 页。
④叶圣陶:《教育与人生》,张圣华:《叶圣陶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26 页。
⑤陈平原:《“发现”的乐趣——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随想》《书城》,2005 年第12 期。
⑥陈平原:《语文教学的魅力与陷阱》《六说文学教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年,第159 页。
⑦夏丏尊、叶圣陶:《文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294—297 页。
⑧叶圣陶:《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张圣华:《叶圣陶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152 页。
⑨陈平原:《“文学史”的故事》《六说文学教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年,第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