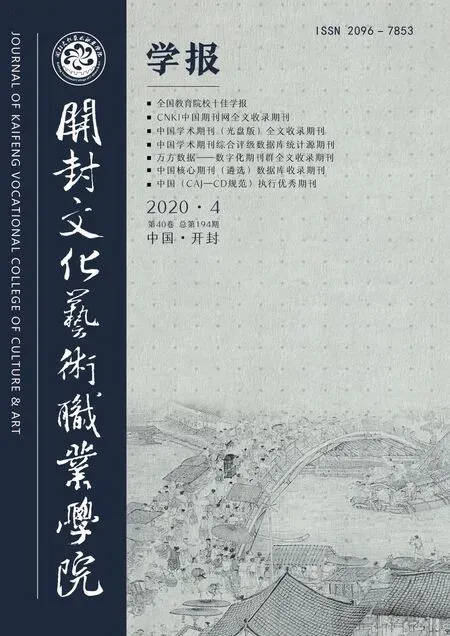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启蒙与救亡的谐奏
——论熊佛西主持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
2020-01-10曾宪章
曾宪章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带领戏剧同人在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进行农民戏剧实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创作观念、题材内容、审美方式、语言风格、艺术实践及其演出效果综合分析,熊佛西主持的农民戏剧实验主要体现了以下基本要素。
一、自然乡村:立足农村贴近农民的通俗戏剧艺术
戏剧由于自身的艺术特征,更易和时代形成紧密联系,这就注定了它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功利职能。戏剧和诗歌一样,是最具有诗性本质的艺术类型,在民主革命时期体现出鲜明的左翼倾向和色彩,形成蔚为壮观的文艺新图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部分潜心戏剧艺术的戏剧家,尽管带有较为强烈的唯美主义及艺术至上的色彩,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艺术应对时代、民众担负的责任。欧阳予倩的戏剧研究所由于不肯为国民党的宣传尽力最终被裁撤;熊佛西在北平曾经因为演剧活动被军阀政府缉捕。在失望、愤恨的驱使下,欧阳予倩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熊佛西则义无反顾地走向农村,把定县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深入探索大众化、通俗化的戏剧艺术。
农民戏剧是大众化、通俗化的产物,属于通俗戏剧。所谓通俗戏剧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评品:戏剧和世俗的观众对象相互关联,在思想艺术上浅显易懂,从表现效果上具有消遣娱乐功能。农民戏剧立足于农村,服务于农民,是职业戏剧向大众戏剧和通俗文艺转变的新路径。熊佛西具有丰富的“国剧运动”和“小剧场运动”经验,他一直致力于新兴戏剧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努力创作满足农民欣赏习惯、符合农民接受能力的通俗戏剧艺术。熊佛西的农民戏剧实验包含戏剧农民化、戏剧化农民、农民戏剧化等多层多维含义,三者相互融合又相互影响。其农民戏剧实验不仅促使农民成为现代戏剧的合格欣赏者,更进一步鼓励并引导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农民成为现代戏剧的创造者。为此,农民戏剧的剧本反映的是农民的真实生活,剧场是广大农村田野间的露天剧场,演员和观众几乎全是农民,观众与演员的流动即是全体农民的流动,农民戏剧彻底地交给了农民。若不考虑剧作者,农民在戏剧中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剧作者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及时充分地吸收了农民的各种合理意见,他们也算间接地参与了剧本创作。由此可见,农民戏剧成功实践了“农民自己演剧给自己看”。
蓬勃发展的农民演剧形势加剧了剧场、舞台与表演多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在加强组建农民剧团、培训演员、指导排练剧目、举办巡回公演的同时,熊佛西及其同人还加强了露天剧场的建设。以都市剧院为代表的室内剧场建筑、镜框式舞台和演剧形式,演员和观众被舞台与观众席明显地分割成界线分明的两个部分,不符合农民戏剧的根本要求。麦场、高坡、庙台等简陋的室外剧场,又与农民戏剧蓬勃发展的现实和长远要求不相适应。单纯的露天剧场虽然与大自然同化,但缺乏戏剧表演应有的建筑形式,甚至可能成为各种新的表演方法的桎梏。由此,熊佛西提出,自建或者改建的露天剧场具有演出优势,并且更为适合农民大众的生活和观剧习惯。农民整天与大自然为伍,辛勤耕作于天地之间,露天剧场演出不会使他们感到生疏。另外,露天剧场与农民剧本的文本达成一定意义内涵的同构。农民剧本简单、完整、鲜明,类型化的人物仅仅作为一种人格力量的代表,人物形象与故事内涵通俗易懂。同时,剧本与农民健壮的体格和粗朴的生命相统一,自然形态的剧场演出又与带有农村生活原色的农民演员浑然一体。于是,在1935年10月,熊佛西指导改建东不落岗村露天剧场,改造后的东不落岗实验露天剧场外观自然优美,总体形状大致呈卵形,剧场外面环植有槐柳,内部则种有两行松树,仿佛是两道短墙,既增加了自然景观,又充满原始的非人工情调。剧场规模更为宏大,较之改建前观众容量大幅增长,增至三四千人。功能上也有所拓展,其主台和副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与天地本色一致。剧场中间是广场,既是观众席,又是演员出入前后台的通道。当演出在广场与前后台之间相互流动时,观众可以在广场中间自由观看,如果演出是在广场中心进行,观众则可以坐立在前后台或者在广场的周围观看,这样就基本消弭了舞台和观众席、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界限,是一种极富有伸缩性的新型剧场。尽管是改建,但是仍然秉承简约实用的原则,着力在剧场规模、空间构造以及舞台设计上使其能够较好地满足农民戏剧演出的需要,剧场的建成最终实现了熊佛西建设规模宏阔、独具特色、功能齐备的露天剧场的理想,也是熊佛西戏剧实验进入新阶段的助力和标志。
这种与自然和农民贴近的演剧环境,使农民成为农民戏剧的观赏者兼具表演者,他们终于能够体验到戏剧艺术的原始魅力和自身蕴藏的艺术潜能,农民戏剧演出成为农民盛大的精神狂欢。“狂欢是一种体制化之前的人类生活,一种非自觉的生命状态。在狂欢当中,人与自然还没有脱离开,首要的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与内在本能从内外两方面使人类在不自由的处境中时时感受原始的生命激情’。”[1]34借助剧场和演剧形式的解放,农民戏剧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农民愉悦身心的特有艺术途径,农民在观看演出和参与表演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虚拟的心理满足,仿佛在触摸和建构常年置身其间的农村日常生活。《过渡》结尾时许多观众兴奋地走上舞台,参加到造桥的行列中,整个演出充满了热烈的气氛,是现场人员的集体狂欢,自然生命的本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宣泄。
二、雅俗共融:民族化导向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雅俗文学是文学母体的两大分支。鲁迅认为,文学是以俗文学为发端的。但是,自从脑体分工后,雅文学日趋正统,俗文学反而逐渐边缘化,难登大雅之堂,经历了雅俗互换和冷热多变的曲折过程。五四时期既是新文学创造发展的过程,也是新文学普及通俗的过程。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的通俗文学日渐式微,新文学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但从读者对象和消费市场来看,在新的社会条件和市场需求下,新旧文学还处于一种相互抗衡、渗透和转化的动态过程中,新旧文学的雅俗色彩和构成比例也在不断适应和随机调整,由此形成新的文学雅俗格局和风貌。
中国话剧来自西洋,整个演剧方法范式都和西洋话剧存在浓厚的精神血脉关联。原初时期的戏剧演出,观众和演员是不分的,演员和观众既有个人的张扬,又有相互之间激情的感染与交流。19世纪后,镜框舞台以其独有的魅力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它将观众与演员明显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缺乏联系的主体。20世纪初始,德国的莱因哈特和俄国的梅耶荷德等戏剧先驱进行了戏剧界回到传统和复归古典的戏剧改革:突破镜框式舞台,打破第四堵墙,抛弃专业性或商业性的剧场,到其他场所开展戏剧表演,追求一种原始演剧效果,并利用台阶和通道促使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观众和演员自由混合来激活人类的戏剧本能,展现人类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这在世界剧坛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复古浪潮。熊佛西早年留学美国学习戏剧,因此,受莱因哈特等“新戏剧哲学”以及梅耶荷德“构成主义”演剧理论的影响较大,其农民话剧的新剧场和新演出法实验就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此种哲学的影响。杨村彬曾说道,他们实验的“新的剧场和演出法是呼应着新的戏剧哲学而产生的艺术方式”[2]。
中国戏剧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大众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戏剧大众化不是割断其对西方戏剧的艺术审美范式的借鉴和联系,不是抛弃中国话剧经过“五四”洗礼而渗透出的现代气息和现代精神,更不是简单地复活传统;而是将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精髓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戏剧。实践证明,戏剧越是发展,越要从民族艺术的沃土中汲取营养,以显现我们民族的活力和彰显民族特色。对此,熊佛西等戏剧家有清醒的认识。农民戏剧实验愈是中国化,就愈要借鉴民族传统的东西。无疑,主要脱胎于西方话剧而又经过创新的农民戏剧,其所创作的剧本、运用的剧场和新式演出法既借鉴了西方现代话剧艺术元素,具有高雅的现代性色彩;同时又兼顾了中国传统戏曲熏陶下的农民欣赏习惯和鉴赏能力,具有鲜明的通俗化和民族化因子。
在剧本创作和戏剧艺术手法上,农民戏剧实验始终和农民具有密切联系,追求中西戏剧艺术的有机结合,又尽力做到艺术上的深入浅出和雅俗共赏。在定县进行戏剧实验时,熊佛西仍然秉承先前“单纯主义”的戏剧主张,在剧情上注重性格鲜明的角色、相对简略的背景、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具体生动的故事,农民剧作一般结构简单,线索明晰,多表现观众喜闻乐见的事物,同时辅之以具有节奏感和美感的繁复动作,亦庄亦谐,富有表现力,也便于观众理解想象。例如,《屠户》中兄弟吵架的动作以及《过渡》中建桥和毁桥的动作,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将传统与现代、雅和俗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熊佛西还善于运用传统戏曲曲调和地方音乐,他搜集了许多民间歌谣,并将其有机运用到戏剧作品中。例如,《鸟国》中的民间曲调和歌声提升了观众的亲切感和共情效果。
熊佛西坚持以农民作为农民戏剧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他善于吸取外国戏剧家的理论和经验,但是从来不简单照搬,始终遵循适合老农老圃的口味等基本原则,实验露天剧场的新建即是如此。露天剧场的改建虽然受到莱因哈特和梅耶荷德等人将马戏场和仓库等作为剧场的启发,但是更多借鉴了民族传统的东西。杨村彬指出,我国古代祈神的祭坛给予露天剧场的新建很多启示。可见,在剧场方面,东不落岗实验露天剧场既回归传统,同时又受梅耶荷德构成主义风格的影响。此外,根据剧场的空间布局,还能制作与环境协调一致、同时具有逼真效果的布景。例如,《过渡》的布景就直接建在舞台上,几何形的平台和构成主义风格的木块直接借自《鸟国》布景,而墙是由干麦秸做成的,又用真的原木制作木筏和脚手架,在蓝天绿树的衬托下,布景看上去只是农村生活的一个自然场景,没有装饰性产生的虚幻意念。相反,观众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联想更能强化生活的真实感受[3]。
通过不断编演农民戏剧,进行剧场和舞台改革,熊佛西还日益完善了“观众与演员打成一片”的新式演出法。虽然是新式演出法,但仍然继承了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比如,河北民间的高跷、旱船、龙灯等。当然,新的演剧法是对西洋话剧和传统民间戏曲扬弃之后的新创造,也是推进实验的重要手段。熊佛西将新式演出法归纳为四种方式:台上台下沟通式、观众包围演员式、演员包围观众式以及流动式。这几种演出方法既相互联系,体现了剧场、舞台、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不同关系,又各有侧重,是追求最佳演剧效果的拓展延伸。总之,分隔台上与台下的“幕线”消失了,演出时利用主台、副台、台阶和过道等的巧妙配合,演员可以表演于台下,观众可以活动于台上,台上与台下、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农民终于体会到自己成为农民戏剧的主人。例如,在《牛》的演出结尾,台下的观众(演员)站起来为王四喊冤,观众席迅速转换成法庭的旁听席,全剧场变为法庭,使观众感觉自己置身法庭中,有些观众还顺着台前的大台阶走上舞台具保并安慰王四。在《喇叭》的演出中,演员从观众中来,也往观众中去,观众不自觉地随演员表演起来,剧场即舞台,观众即演员,场面壮观热烈。熊佛西执拗于戏剧是最民众最民族的艺术信念,在农民戏剧雅和俗、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形成了农民戏剧独特的美学风格。
三、治愚救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谐奏
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的思想口号充斥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启蒙是应社会问题的需要而诞生的思想运动,但不应就此认定它只是成为中国现代‘救亡’思潮的一个‘副部主题’,或被救亡所压倒等,它实际上是作为与‘救亡’主题相并列的另一个主题而存在的,对‘救亡’‘革命’既起着思想上的补充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对革命或救亡的结果、功效进行检验,起着反思与矫正的思想功能。”[4]22唯启蒙才能救亡,因救亡而更应启蒙,启蒙与救亡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双重谐奏。当然,在五四时期,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和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相互促进,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了苦难深重的深渊。“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5]849
熊佛西具有浓厚的启蒙思想,他认为:“我们在定县研究实验,并不是为定县,是要找出一套农民教育与农村建设的方法内容,贡献给国家。”[6]257只有用现代文明理念以及科学知识教育农民,打破他们愚昧、僵化的桎梏,才能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召唤下最终求得人性的解放以及社会的进步。启蒙思想的指导使熊佛西珍视他的农民戏剧实验,将其与创建伟大的新农村文化事业联系起来,执着地颠覆旧文化,构建新文化。在定县的五年时间里,熊佛西和他的同人亲身感受农村生活,深入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创作了《锄头健儿》《屠户》《牛》《过渡》等众多农民剧本。他们的剧作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农村阶级矛盾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农民在反动统治下的痛苦生活,揭示了地主豪绅阶级鱼肉乡民、贪酷残暴的丑恶本质,寄寓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和价值取向,给农民深刻启迪。《锄头健儿》塑造了具有“向上的意识”的青年一代农民健儿形象,传达出“新民”思想。《屠户》以精湛的艺术笔法揭露了地主豪绅阶级贪鄙狠毒的罪恶本质,歌颂了农民群体的力量。《牛》揭露了官绅勾结、共同欺压百姓的罪恶,满怀同情地刻画了农民王四悲剧性的一生。《过渡》则通过造桥来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力量,暗示当时社会的发展转折和进步。戏剧是启迪民智、教育农民的重要文艺工具,农民戏剧的深入过程就是民众思想不断觉悟的过程。熊佛西运用农民戏剧向农民灌输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使农民产生了启蒙者所期望的向上的意识,敢于在黑暗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下勇于斗争,并寻求光明的前途。
别林斯基认为:“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最是充满热情的。”[7]54热爱生活、献身戏剧事业的熊佛西怀着满腔热情和虔诚的信仰投身于戏剧实验中。熊佛西奔赴定县的时间是1932年初,当时“九·一八”事变烽火未熄,山雨欲来,国难当头;而后“一·二八”事变炮声隆隆,战事又起,民无宁日。危亡的国家局势又一次注定了文艺的新使命。抗战时期,文艺工作者自觉地集中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汇入抗日的滚滚洪流。天才的“全能戏剧专家洪深”表现出反帝革命的激进创作倾向[8]106;郭沫若则满怀急切地“要求文艺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9]136;老舍大声疾呼“文艺工作者的理想,尽管可以高远,但写作的题材、对象,最好不要离开现实”[10]213。在抗日的烽火中,救亡成为单向突进趋势下压倒性的一切,而无法顾及艺术上可能的偏失。熊佛西此时也不会置身事外,他明确宣称:“平时戏剧也许是消遣品,也许是象牙塔里的珍宝,但在全面抗日的今日,戏剧应该是武器,应该是枪炮,是宣传杀敌最有效的武器,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最有力的武器。”“他甚至认为,不曾感受过颠沛流离的抗战生活的人,根本无法激发创作主体的深厚感情,也无法歌出流亡者的哀声。”[11]184
可以说,熊佛西抗战时期的戏剧活动是定县农民戏剧实验的延续。抗战初期,熊佛西在成都担任四川省戏剧学校校长,他同四川剧校同人合作,先后写出了《抗战儿童》《中华民族的子孙》《害群之马》《袁世凯》等多部剧作,痛斥强盗暴行,歌颂爱国志士,对于启发民智、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1939年,熊佛西还在四川双流机场为一万多名修筑飞机场的民工演出三幕剧《后防》,一万多名正在修建飞机场的民工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所有的人一起呐喊歌唱,气势恢弘,场面壮观,成为用戏剧进行救亡的经典剧作,发出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抵御外侮的怒吼。为此,晏阳初曾经赞扬熊佛西道:“关于戏剧方面,自从熊佛西同志领导抗战剧团入川后,所表现的成绩颇有可观。熊同志长于创作,在戏剧上的表现,有口皆碑,全川的戏剧空气,为之改良不少。……戏剧不仅是娱乐工具,也是抗战的武器,这一方面的发展,与四川人力物力的动员,当有很大的影响。”[6]23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