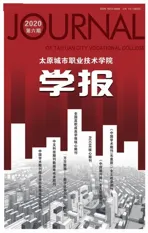论《世说新语》中魏晋酒士的尚情特质
2020-01-09马小琪
■马小琪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饮酒的传统,酒与中国古人的生活与情感息息相关,无论是欢庆相聚、演绎别离,还是传递喜悦、表达哀愁,古人们总离不开酒。从先秦两汉开始,酒在公共社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百礼之会,非酒不行”[1],酒是礼乐秩序的重要体现,无论是祭祀典礼还是宴饮欢聚,酒都起着规范礼度、协调气氛的作用。从汉末到魏晋,酒更多从公共社交转入私人领域,成为自斟自饮的个体行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更多的人以酒来寄托感情,言抒抱负。到魏晋之时,名士们对于酒的酷爱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文人与酒的联系达到了一种历史性的高潮。《世说新语》作为记录魏晋士人言行轶事的不朽之作,其中涉及到酒的描写有六十五处之多,在日常的生活以及交际之中,名士们与酒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酒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之中,他们或醒或醉,借助于酒的特性,展现着特有的时代性情与生命意识。目前对于魏晋名士与酒的关系的分析不在少数,但更多人将笔墨着重于酒与人格特征以及时代风尚的关系,对于酒与情感的分析论述不多。面对魏晋时期特殊的历史状况,魏晋酒士们的情感呈现出一种时代的复杂性,对酒与时代情感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对于我们把握酒的时代意义,完整地理解魏晋士人的情感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酒发展到魏晋,不论是诗酒雅集还是醉卧高蹈,都不仅仅是个体的独酌行为,饮酒之风的盛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度。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任诞23)。所谓名士,是魏晋人追求的一种人格范式,名士需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且“一往而有深情”(任诞42),痛饮酒就是成为名士的重要标准之一。酒因其特性,与魏晋士人的“一往深情”有着重要的关系,从生理因素来看,酒水中的酒精成分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先兴奋后抑制的作用,这种刺激进而影响到了人的心理,身心暂时地自由与放松,使潜藏在深处的情感打开了倾泻的口子,借助于酒,魏晋士人的情感在酒中氤氲开来,而这种酒水中的深情,结合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特点,呈现出一种内敛而狂放的双重特质。
一、情感的收束
魏晋时期,一统王朝分裂,司马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他们独断专权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暴力政权,按政治阵营分类,加紧了对“异端”的清洗;在思想上,采取自欺欺人的经营方式,手上名士之血尚未洗净,仍高呼仁义礼智,虚伪世风盛行,使儒家精神内核名存实亡。面对生存的疲惫与死亡的悲哀,魏晋士人的情感发生了重要的转移,从前对于统一国家的归属感,对统治阶级的拥护感,对于儒家名教的认同感,都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情感转移到了自身,转移到身边的一草一木,形成了一种退守的人生。在这种人生的状态之下,魏晋名士的情感呈现出一种收束的方式,人生的苦闷让士人们产生逃避的意识,他们的情感内转而收敛,借助于酒,在一种内转的情感中完成对生命的安顿。
(一)饮酒避祸
战乱频繁的现实,疫病流行的状况,加之司马氏的残酷手段,使魏晋人多短寿,王病死时,不足四十,嵇康死于司马氏之手,年仅三十九,王弼染病而亡,才刚刚二十四岁。死亡的逼迫,使晋人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心中充满着对于生命终结的哀痛,人们见过的苦难太多,才更加深了对于生的执着。对于死亡和生存的清醒认识,使魏晋士人们产生了普遍的生命意识,他们退缩到个人的小天地中,将感情的寄托归于自身。宗白华认为:“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最大贡献”[3]。正是因为钟情于自身,魏晋人采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于生命的热切渴望和执着追求。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一批士人以醉酒为手段,有意地拉开了自身与政治的联系,在大醉之中远离政局纷争,“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4]。《晋书·阮籍传》中“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5]1359。为避免与司马氏联姻,阮籍宁大醉六十日,终日混沌于酒场,不参与政治站队。为了保全自身,远离政治杀夺,阮籍借醉酒的名义,躲避政客与时局的侵扰,压抑着情感与抱负,在人生道路上,一退再退。南宋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评“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拖于醉,可以粗远世故”[6],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刘伶的“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7]1375。也不过是保身之计罢了。时事的艰辛带给人的只剩人生的苦闷,随身携带一壶酒,借酒佯醉而躲避时代的困境,“死便埋我”也不是真正地无惧死亡,只是对现实有着过于清醒的认识,无可奈何下只能妥协。借助于酒的名义,魏晋士人退回对个体生命的守护,远离世事的逼迫,保有着对生命的深厚感情,在愁苦和绝望中完成对于身体的安顿。
(二)麻痹自身
现实的沉重逼迫,带给魏晋士人的不仅是身体的折磨,更是精神的痛苦。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司马氏一方面借儒家名教精神来管理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大肆屠杀那些真正的礼教维护者,其真正的统治原则不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却以仁义礼教为借口,使魏晋人心浮动。“名教的精神内核已经死亡,只剩下一副扭曲异化了的躯壳在招摇撞骗”[8]。在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之下,魏晋士人对传统礼教的深厚感情发生变异,匡时济世之志得不到施展,死亡的悲剧无法避免。“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面对心灵的疲惫与悲哀,名士们借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在一种朦胧麻醉的状态中完成“有身”到“无身”的超越,这种去身体化的方式,使士人们在朦胧飘然的状态中形神相亲,从而远离现实带给人的巨大悲哀。“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阮籍一方面钟情自身,回避政治以安顿身体,另一方面,也使心灵翱翔于天地之境,借酣醉于酒,达到一种近乎与造化同体的感觉上的境界。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35)。与珍惜生命,饮酒避祸来保全自身的“有我”状况不同,这里的“自远”说的是一种类似于庄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界。酒精的麻痹感,使人的情感体验发生巨大变化,为远离心里的哀痛与无奈,魏晋士人借一种醉的状态,麻痹身体的感知,拉开与沉痛心理的距离,在一种超脱现实的幻觉之中,与天地自然相亲,达到了庄子的“醉者神全”[9]181的天地境界,世俗所累尽数远去,情感与天地相通相容,心灵得到最大程度的安慰。
二、情感的释放
魏晋的时代,“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以及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0],乱世的征伐与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使得魏晋士人的个体意识空前的增强,思想自由驰骋,情感浓烈而解放。面对时代与个体的悲剧,魏晋士人有一种普遍的人生苦闷感,浓烈的愁绪使魏晋士人与酒的关系空前亲密,耽酒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借酒解愁,“以酒浇胸中之块垒”(任诞51)。另一方面,强烈的个体意识也使得一部分人以快意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他们通过畅饮美酒来把玩现在,乐知天命,享受人生,正如王瑶先生在论述魏晋人生活态度时所说的“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望,所以对现刻的生命更觉得热恋和宝贵”[11],对生命的浓厚感情,使魏晋士人醉心于即时的情感体验,着力提高生命的质量。魏晋士人因愁闷与贵生而耽溺于酒,其情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酒的浓烈和清澈的特征产生了冥合关系,这种时代赋予的真挚而浓郁的情感,借助于酒水,展现出生命的蓬勃力度。
(一)情之烈
对于魏晋士人来说,价值体系的崩溃把他们从伦理规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自然之性与生命之情成为首要的关注问题。一方面,人们开始正视自身的情感需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伤逝4)。另一个方面,高压的现实环境对自然性情产生了压抑,感情却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呈现出一种压抑而欲喷薄的状态。在这种现实情况之下,魏晋士人的情感呈现出浓郁而复杂的特点,士人们急需寻找一种方式来完成对情感的释放,一部分名士将目光又投向了酒。从酒的本质特点来看,酒字“从水从酉”,用酉时之水造酒,酒有刚烈之气,酒水的浓烈辛辣与魏晋情感的充沛浓郁,在魏晋士人的情感观照之中完成了相通。
1.此情不隐。对于生命的热情,使魏晋士人的感情真挚动人,跳出礼教的层层束缚,情感洒脱自然,无拘无束。“刘尹、王长史同坐,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品藻44)。心中有情感,便痛快表达,喝到兴尽之处,就起身跳舞,让情绪随酒兴痛快尽情展示,不藏不隐,痛快淋漓。在纵酒享乐之中,名士们借此消减死亡与生存的苦楚,追求着人生的自由主义,“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22)。但生存的困境毕竟围绕,没有人能完全的逃离,被时代所困的阮籍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作着消极的抵抗。阮籍崇尚老庄哲学,带有着老庄仙隐的思想,但其中的隐遁思想却完全没有轻松闲适的情绪,而是充满着人生的苦闷无助,他一方面对于现实失望无奈,另一方面又对人生执着和眷恋,矛盾的情感让阮籍更加的敏感多情。“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5]1361阮籍醉酒驾车,驾着一车的困惑、无奈、痛苦,去远处寻找心中的净土,可车迹绝处,他一无所获,于是他在醉中长啸痛哭,哭自己、哭乱世,也哭那无边无际的痛苦与孤独。这一腔无处宣泄的悲情,借酒的烈性尽情发挥,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人生苦短和功业不遂,而上升到一个时代的悲凉。魏晋士人们将自己的人生安放在这一往深情之中,自主自觉地挣脱束缚,让情感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不被外物牵引,自然流露,一派深情。
2.此情不忌。混乱的时代造就偏激的情感,而当情感偏极时,就顾不得合规合礼,往往产生新奇怪异。《任诞》篇中,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任诞6)。刘伶纵酒大醉,竟脱得一丝不挂,人们讥笑他,他反向调笑人们为什么钻到了他的裤子里。在这里,刘伶借酒起兴纵情,以赤身裸体的姿态,完全冲破了礼法的束缚,毫无顾忌与避讳。在酒醉的时候,他找到的是在现实中无迹可寻的自然,在这自然之境中,他以天地为栋宇,生命的个体与自然的宇宙天地,刹那相通,人从天地中来,到天地中去,完成人生的回环旅程。在这种酒塑造的的境界之中,刘伶才留下那一篇“意气所寄”的《酒德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7]1376不谈政治、不谈人生,只大谈酒的好处,这一位放达不羁的大人先生,在酒所塑造的物我两忘的至人境界中,将人生意义又旨归到了最真实的性情。魏晋时期,人们将生命意识移植到自然之中,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深情”[3]183,与自然相亲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心中充满了与自然的情感体验。“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任诞12)。阮咸同样好饮酒,且更是毫无忌讳,用大瓮盛酒喝酒,有时竟然与猪共饮。但如果从魏晋之际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与猪同饮也是一种情关自然的真诚表现。魏晋士人的多情任情“不是一种一般的感情,而是一种强于日常感受的、最与审美接近的对宇宙人生、对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的特别体验和特有专注的深情”[11]。人们没有任何顾忌地与自然相亲,在自然之中融入最真实情感体验,追求自然且真诚。与“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传统不同,魏晋士人们是完全从现实生活和自身的感受出发去畅快地抒情,这种感情强烈而肆意,有时甚至产生惊世骇俗的效果。跳出清规戒律,避开繁琐礼仪,情感抒发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种情感超越了形式主义,是一种对于人生的重塑,对于人性的完美复归。
(二)情之清
在一个“越名教而任自然”[12]的年代里,面对力不从心的现实,魏晋士人力图越出名教的圈子,远离虚伪的政治,而返归自然的质朴。他们追求一种“清介超逸”的理想人格,力图在现实中走出一条超脱之路。这种对于自然人格追求,一部分士人同样借助酒韵味的自然纯净,进入一种随和纯美的心灵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的追求中,魏晋士人的情感呈现出一种清澈无邪的特点。
1.此情不伪。浓烈的酒麻痹了神经,也解除了一切规范的束缚,没有虚伪客套,魏晋士人的情感呈现出一片真情。《任诞》篇中,“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11)。阮籍丧母,仍然喝得醉醺醺,并且披散着头发随意坐着,有人来吊唁也不按礼行事,整日浑浑噩噩。然而裴令公明白,作为“方外之人”的阮籍,在丧葬之上的我行我素才是真情实感的表达,最沉痛的感情往往来源于默默无言,深情何须礼仪的加成。结合另一则来看“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9)。因为哀伤至极,才会吐出鲜血并“废顿良久”,不按礼不是不动情,痛极才往往超情越礼,做出肆意行为,此情不是做给活人看的,而是出于对于死者的一片真情。在情感与礼教的关系上,太过于拘泥于礼,就会产生矫情,如同酒曲太多,酒味就会发酸而不像酒,过于尊礼,人只会失去感性而成为一个单面角色。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拥有一份真正的感情,“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9]538,情感因真挚而格外动人。魏晋人钟情于自我的真实,借酒后的放肆,将真情的体现脱去虚伪繁琐的外壳,那直达肺腑的深情,才显示出它的深刻与激烈。
2.此情不俗。魏晋士人追求闲情雅致,寄情山水草木,向往清高超逸的人格,感情纯质高雅,这种人生态度,使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化俗为雅,将生活艺术化。“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伤惶,咏左思《招隐》。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47)。王子猷雪夜酌酒,想拜访友人,微醺醉意中兴起而去,到门口后兴尽了,没有拜访又原路返回,这种看上去不可思议的行为正是魏晋士人雅趣的真实写照。这一来一往只是微带醉意后突如其来的心思,不加任何杂质,是完全超出世俗利害的。在这一来一往中,王子猷所追求的只是一种雅致的性情,这种闲适高雅的士大夫情怀,正是魏晋风流的韵致所在。超越人生焦虑,保持心境的平和,将兴趣寄托于生命的享受过程而不是目的,钟情于一种脱俗的情致,在一种超然旷达的追求中,营造人生美的境界,这种通脱天真的情感,体现了魏晋士人对于美的自觉追求,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审美化的人生。
正所谓“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52),对于魏晋士人来说,酒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武器,也是他们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载体。在那样一个感性心灵苏醒的时代里,酒所酿成的醉意,在魏晋的时代,构成了一代士人们的生命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