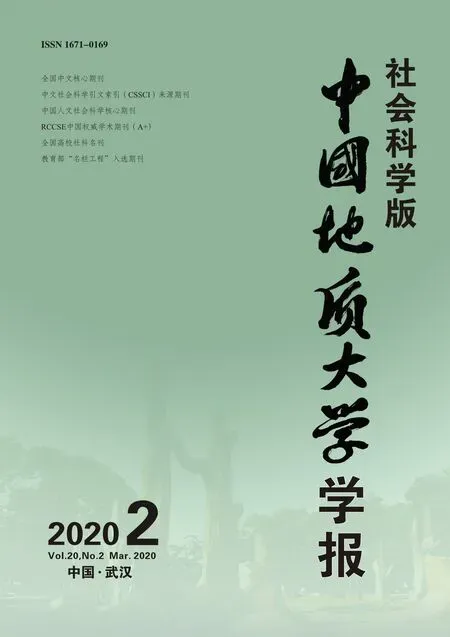构建生态人文主义新型美学
2020-01-08程相占
程相占
一
中国生态美学从1994年正式发端至今已经走过了26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曾经遭受过不少质疑和批评,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来自李泽厚。他曾谈到:“至于以生物本身为立场即完全脱离人类生存延续的所谓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以及所谓超越美学等等,大多乃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较少原创性格,它们都属于‘无人美学’,当然为实践美学所拒绝。”[1](P275-276)这就意味着,在李泽厚眼中,生态美学是一种“无人美学”。笔者已经撰写文章初步回应了李泽厚的批评①参见程相占:《中国生态美学的创新性建构过程及其生态人文主义思想立场——敬答李泽厚先生》,《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为了增强文章的客观性和力量,该文只着重介绍了曾繁仁先生对于生态人文主义的论述。,但由于立意和篇幅所限,那篇文章没有从深化生态人文主义研究的角度来回应李泽厚的批评并展望生态美学发展的理论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生态美学最初十多年是在不了解西方生态美学的情况下独立建构的。从2009年开始,中国学者发现西方也有生态美学并将之介绍到中国,并试图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生态美学史[2]。与西方生态美学相比,中国生态美学总体上至少表现出三个理论特点:第一,自觉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相联系,借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这集中体现在“生生美学”建构上[3](P1-13)[4][5];第二,自觉地将生态文明视为生态美学建构的指导方针,将生态美学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6](P209-219);第三,自觉地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思想纲领,借此批判并努力超越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本文认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和深化途径是,借助生态学及其原理来更加明确地界定生态人文主义的内涵及其性质,进一步探讨它与生态美学建构的内在关系,从而尝试着将生态美学建构为关怀全人类命运、关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关怀美学,也就是一种强调“生态人文精神”与“生态人文关怀”的美学。本文试图表达的基本观点是,生态美学绝非李泽厚批评的那样是“无人美学”,而是一种高度关注“生态人”之健康生存的“生态人文主义美学”,它还将继续沿着这种理论思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①白居易:《与元九书》。生态美学建构不是象牙塔里的纸上学问,而是“为时”、“为事”之作——这个“时”即生态危机时代,这个“事”即拯救生态危机。生态人文主义看到了人类的各种活动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因而奋发努力,试图担负起拯救生态危机的时代重任,在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之中的一个物种的同时,特别强调人类对于生态系统之健康所肩负的重大责任,此即生态责任。生态美学就是根据这种价值立场来重新反思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试图借鉴生态学原理来促成美学的生态转型,从而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生态美学强调生态人文主义这种价值立场,它也可以叫做“生态人文主义美学”。李泽厚将中国生态美学判定为“无人美学”,原因在于他根本不了解生态美学的实际情况。
二
回顾生态人文主义与中国生态美学建构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有的成果仅仅是一个开端②曾繁仁将生态人文主义视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参见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4页;笔者则将生态人文主义作为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之一,称其为“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参见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很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生态人文主义的工作性定义是什么?现有的生态美学著作都没有明确界定这一点,因此急需我们在有效地综合中西人文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站在当代生态哲学的高度明确界定生态人文主义的内涵与性质;第二,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美学的深层关联是什么?这就是要进一步追问:生态美学建构为什么需要生态人文主义理论?我们下面来做一些探讨。
第一,生态人文主义的工作性定义。
在初步借鉴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这里尝试着提出深化生态人文主义研究的如下思路:人文主义的理论性质是什么?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根本局限是什么?生态人文主义如何超越启蒙人文主义而实现其生态转型?这三个问题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我们下面依次讨论。
深入理解人文主义的理论性质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将之视为看待人和宇宙的三种模式之一。英国学者布洛克指出,西方思想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超自然的、聚焦于上帝的模式,将人看成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聚焦于自然的科学模式,把人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模式,它“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7](P12)。这就意味着,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所谓的“人文主义”其实就是与“神学”与“科学”相对的“人学”。这就表明,准确理解西方人文主义理论性质的整体框架是“神学—科学—人学”。
西方人文主义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其萌芽,文艺复兴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启蒙运动时期达到高峰,休谟甚至明确宣称“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基础”[7](P91-92),康德则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视为哲学领域所有问题的最终旨归[8](P24)。启蒙人学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使人类摆脱了宗教蒙昧,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自由由此得到充分张扬。但是,当人文主义成为现代世界的指导性生命哲学时,它就引发了新的问题:由信仰神转而信仰理性的力量和人的能力,相信现代人是全能的,“相信我们随意操纵地球的能力并且不因为这种操纵而受到任何最终惩罚”[9](P8)。当我们反思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时,启蒙人学或曰现代人文主义的上述思想倾向难辞其咎。
有鉴于此,生态人文主义可以简单地界定如下:在继承现代人文主义重视人的能力、尊严和精神自由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学原理重新解释人类天性,将人类界定为身处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位居生物链或食物链顶端、具有反思意识和能力的独特物种,其适当的生态位①“生态位”是生态学的一个专业术语,它用来界定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之中的位置或曰地位,既描述该物种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范围,同时又描述该物种在该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或功能。是维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健康、稳定和美丽。
第二,生态美学的基础命题及其理论延伸。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人文主义对于人的重视就是高扬人类的主体性,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相比,具有理性、意识、情感、自由意志等基本特点,这都使得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加高级、更加优越,从而为人类利用自然、掠夺自然甚至统治自然找到了合理性根据。人一旦被视为脱离自然属性的理性动物,就将造成一系列的二元论,诸如自然-文化二元论、身体-心灵二元论和主体-客体二元论,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无利害观念、静观的审美方式等,都是这种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
针对上述一系列二元论,在生态人文主义工作性定义的基础上,我们这里尝试着提出一个理论命题作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点,这个命题是对于人类物种之特性的生态说明:根植于生态系统之中具身的心灵(Embodied Mind Embedded in Ecosystem)——与任何物种一样,人类也是生态系统孕育的成果,时时刻刻都依赖生态系统的养育而生存;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独特之处是心智(或者说心灵)最发达。心灵并非笛卡尔所说的独立实体,而是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思维功能,因此最恰当的描述是“具身的心灵”。我们可以从这个基本命题来重新理解美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就“审美”的性质而言,它不再是康德所界定的那样,是主体对于自己所建构之表象的感受或情感,而是身心一体的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审美互动(Aesthetic Interplay or Interaction),通常所说的“审美活动”由此得以生态改造而成为“审美互动”;再比如,美学原理通常将“审美态度”作为审美活动的起点,但根据我们这里所说的“审美互动”,人对于生态系统的关怀(即生态关怀)才是第一性的决定性因素,审美互动因而包含着强烈的生态伦理内涵,其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伦理—审美—互动”。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使得审美互动最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简言之,建构生态美学最终不仅仅是为了引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而幸存(“活着”),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肩负对于生态系统的责任而提升精神境界,通过履行自己的生态责任而升华人性,从而使得人类的生命获得意义(“活得更有意义”)。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方向是在深入反思现代人文主义理论得失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生态人文主义,进一步探讨它与生态美学建构的内在关系,从而将生态美学建构为关怀全人类命运、关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关怀美学,也就是一种强调生态人文关怀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