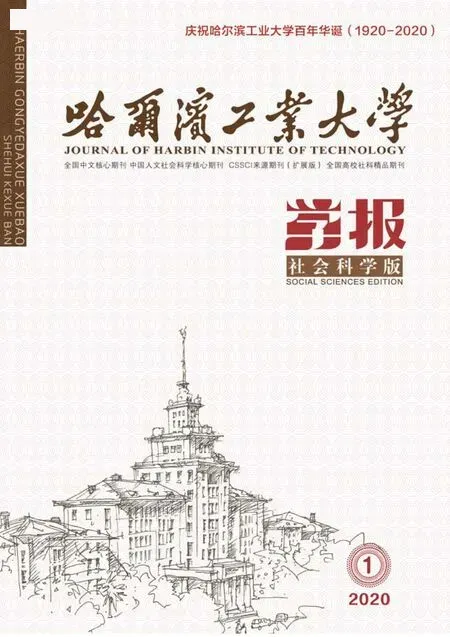“乐经不缺”与周代音乐经典的体系性构成
2020-01-08傅道彬
傅道彬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25)
“六经”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经典,而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六经”,在文献上却只有“五经”。东汉班固谓:“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 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1]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至今仍有学者坚信,《乐经》本不存在,因此也不存在“六经”之说。①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一文(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中说:“‘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文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一部先秦典籍中被屡屡提及的周代重要音乐经典,由于资料及其存在形式问题连其真实性都遇到了学术挑战。《乐经》的存无问题,不仅仅各资料问题,也包含理论问题,认识的盲区也会造成我们对某些资料的视而不见,因此对《乐经》的存无至少应该有这样的追问:
第一,《乐经》的存在形态问题。它究竟只是文献资料,还是只是侧重实践运用的礼乐艺术?
第二,《乐经》文献的多样性问题。《乐经》文献也许不像《诗经》那样简单,它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乐经》是否既包含音乐文本,也包含实践体系,既包含政治制度,也包含理论阐释?
第三,《乐经》的历史流传问题。《乐经》究竟是消失在春秋礼乐文明的式微,或者是秦代暴政的焚烧中,还是《乐经》的流传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乐经》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还是一部静止的历史经典?
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梳理周代的音乐文献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对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理论辨识,以认识《乐经》的文本形式、存在形态、理论内涵。对“《乐经》存无”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周代的艺术与文学的评价,也关系到对周代文化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蕴。
一、关于《乐经》存亡问题的理论争鸣
围绕“《乐经》的存无”,学者们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关于《乐经》的存无及亡佚的时间也疑义纷呈,不一而足。而撮其要,有三种意见应该引起特别注意:
第一,古有《乐经》,渐次消亡。先秦之世,《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礼记》《庄子》《荀子》①《礼记》之《经解》《王制》,《庄子》之《天运》《徐无鬼》《天下》,《荀子》之《劝学》《儒效》,均将《乐》与其他经典并称。及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性之命矣》《语丛》(一)等屡屡提及《乐经》。《礼》《乐》相依,《诗》《乐》并提,《乐》或称经,或称艺,是先秦文献一种习见的称谓。先秦典籍不仅抽象地提出了《乐经》的概念,也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乐经》中经典音乐的艺术形态。《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 《咸池》,备矣。 《韶》,继也。《夏》,大也。 殷周之乐尽矣。”[2]1534《南风》 《大章》《咸池》《韶》《夏》等经典音乐是周代音乐文本的典型样式,其中《韶》乐在《左传》《论语》等典籍中多次提起,尤其是吴季札、孔子等倾听《韶》乐获得的令人陶醉的审美感受让我们具体感受到这种音乐思想与艺术的动人力量。《乐记》甚至完整地描绘出周代《大武》音乐的“六成”结构,让我们对以《大武》为代表的经典音乐有了具体了解。
孔子曾对经典音乐做过整理,《论语·子罕》谓:“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儒林列传》亦谓孔子“修起礼乐”[3]2369。 可见《乐经》存在有相当长的形成和演进历史,孔子对周代经典音乐文本和文献资料做过重要工作。 “生民之道,乐为大焉。”[2]1537有周一代制礼作乐,崇文重艺,而“礼之所至,乐亦至焉”[2]1616。 礼乐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乐礼艺术,周人将礼的教化寓于乐的艺术之中,在诸种艺术形式中,周代音乐文学最受推重,也最为发达。
遗憾的是,随着西周王朝的式微,周代礼乐制度渐渐衰微,乐的经典也渐渐被人遗忘。秦火之后,竟然连基础的文献也难存完璧。《乐经》的衰微,经史学家们认为发生在两个历史时期:一是春秋时郑卫之音的干扰冲击,二是秦火的焚毁。关于“郑卫之音”导致古典音乐的消亡,《史记·乐书》谓:“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3]1038对于歌乐兴盛的西周盛世司马迁与孔子一样是深切怀念的,认为那一时期的音乐由西周宫廷发动,指向人的精神世界,让人振奋,充满力量:“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3]1037。而郑卫之风的兴起,扰乱人的心志,最终导致了西周古乐的衰亡,所谓“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3]1037与司马迁一样,班固也认为是郑卫之音的兴起导致了《乐经》的衰亡,其谓:“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4]1711-1712
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乐经》亡于秦火。《文心雕龙·乐府》谓:“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刘勰认为,除了东周以来的宫廷雅颂歌诗的衰微,秦代焚书坑儒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乐经文献的散佚。《宋书·乐志》直接说“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秦始皇有规模地焚烧“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3]181,诗乐相连,《诗》《书》被烧,《乐经》自然也不例外,秦代对周代音乐经典的毁坏是严重的。
第二,乐本无经,无所谓存亡。《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乐类序》云:“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5]
《四库全书总目》否定的观点有二:一是先秦时并无《乐经》之名,《乐经》之名是后起的;二是最重要的观点是《乐经》之“乐”,是旋律是节奏是演奏的实践技能。张舜徽先生特别赞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认为“此说明通,足成定论”。其《四库提要叙讲疏》谓:
《汉书·艺文志》曰:“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注引服虔曰:“制氏,鲁人,善乐事也。”乐事,即指“铿锵鼓舞”而言。举凡声乐之节奏,歌咏之高下皆是也。悉赖传授演习而后得之,非可以言语形容也。故为之者,但能各效其技能而不能自言其义。《汉志》所云“世在乐官”,与《四库总目叙》“传在伶官”之语意相同,即《荀子》所谓“不知其义,谨守其教,父子世传,以持王公”者也。其不能笔之于书以成一经,固宜。[6]
据此,邓安生认为,“‘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文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 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7]1邓文又从三个方面论证“乐本无经”的问题:一是《乐记》没有言及《乐经》;二是先秦史书与诸子无一言及《乐经》之书;三是秦汉之际的学者无人提及《乐经》。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四库提要》所说的本无圣人手定之《乐经》,“足以发蒙祛蔽,凿破千古浑沌”[7]4。
第三,《乐经》不缺,存于诗礼。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乐经》不缺,《乐经》并未消亡,在周代礼乐文化中诗、礼、乐相互依存,《乐》依附《诗》《礼》而存在。一种流传广泛的意见是诗乐一体,《诗经》就是《乐经》;也有学者认为《周礼·大司乐》《礼记·乐记》等经典文献就是《乐经》。宋人叶时认为诗乐一体,乐本无经,《诗经》亦谓《乐经》。叶时谓:
世儒尝恨六经无乐书,愚谓乐不可以书传也,何则?乐有诗而无书,诗存则乐与之俱存,诗亡则乐与之俱亡,乐其可以书传乎?《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此乐之本乎诗也。乐由诗作,故可因诗以观乐,无诗则无乐,虽有钟磬鼗鼓柷敔箫管,尚遗古人之旧,果可以言乐乎?[8]
叶时的意见对后人影响颇大。人们从诗乐一体,推导出“乐经不缺”的结论。明人刘濂谓:“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余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9]清代学者顾炎武也主张“诗乐一体”的理论,《日知录·乐章》云:“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乐言之也。”[10]267正是从诗乐一体的角度出发,顾炎武认为诗与乐存在着存亡相依的关系,“《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10]265根据顾炎武的主张,近人钱穆认为“《乐》与《诗》合,本非有经”[11]。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乐经不缺”的理论基础是“乐本无经”,既然诗乐一体,诗既乐也,乐亦诗也,本来就没有《乐经》,《诗经》就是《乐经》。清代学者邵懿辰说:“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12]邵懿辰不仅将《乐经》归之于《诗》,又归之于《礼》。与此相类,明朝朱载堉和清代李光地认为《周礼》中的《大司乐》一章就是《乐经》。朱载堉《乐学新说》谓:“汉时窦公献古《乐经》,其文与《大司乐》同,然则《乐经》未尝亡也。”[13]李光地亦谓:“汉书文帝时……出其本经一篇,即今《周官·大司乐》章,则知此篇乃古《乐经》也。”[14]一些学者眼里《周礼·大司乐》即是《乐经》。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乐本无经”的观点,看似“无经”,实则有经,只不过其对《乐经》的理解与人们不同而已。他们把《诗经》《周礼·大司乐》,甚至是《乐记》看作是《乐经》了。明人何乔新谓:“乐书虽亡,而杂出于‘二礼’者犹可核也,《乐记》一篇可以为《乐经》。”[15]清人朱彝尊引用梁斗辉《十三经纬》的观点谓:“孔子删述六经,自五经分,而《乐经》仅存一篇以附《礼记》,全书阙焉。”[16]
二、《乐经》存在的实践形态与文献构成
《乐经》存无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关于《乐经》文献资料的问题,传世文献和近来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有许多关于音乐的记载和论述,《乐经》的存在有丰富文献资料作为支撑,研究、整理及甄别这些文献是周代诗乐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即怎样认识《乐经》的存在属性?《乐经》是一部书,还是一种文献体系?《乐经》仅仅是一种资料,还是礼乐实践过程?《乐经》的种类是单一的艺术的,还是职官、制度、文本、实践、教育、理论等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因此,对《乐经》存在形态的理论阐释,也是《乐经》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关于《乐经》的理论认识应该特别强调的是:
(一)《乐经》的形成是动态的历史过程
所谓乐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音乐,而是与周代礼乐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宫廷音乐。当西周王朝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宫廷音乐也呈现出雍容盛大的气象,而当西周王朝衰败式微时,其音乐也自然表现出萧条冷落的局面。春秋时期与秦王朝时代是周王朝没落直至灭亡的时期,也是周代音乐文化遭受两次重创的历史时期。春秋是以郑卫之风为代表的世俗“新乐”取代以雅颂为代表的宫廷“古乐”时期,而秦代则是对《乐经》文献的摧毁。但是这两个时期都不意味着《乐经》的真正消亡,无论春秋之世是古乐的衰落还是秦始皇对经典的焚烧,都不足以造成《乐经》的彻底消亡。
春秋时代固然是“雅声浸微,溺音腾沸”[17],但那也只是古乐失去往日的辉煌而不是彻底的绝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在鲁国观乐,不仅欣赏到了《二南》《国风》《小雅》《大雅》《颂》等与今本《诗经》相同的音乐,也欣赏到了《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等不见于今本《诗经》的古典音乐。同样,孔子在齐闻《韶》,感叹“三月不知肉味”[18]2482,也证明了古乐在春秋的流传。有秦一代,焚诗灭书,礼乐典籍遭受洗劫,但经典在民间、在各地还有保存,于是有了汉代初年对经典文献的收藏整理,“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4]1701,被破坏的文献典籍得到了初步恢复。“六经”是汉代重点整理建设的文献,而《乐经》也是西汉特别注重的文献。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对《乐经》的整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搜集雅歌;二是恢复乐官;三是整理音乐文献。
《乐经》的形成和传承的历史是在创造、衰微、重建中不断发展的。正因为汉代有乐府制度,有大规模的音乐收集与文献整理,所以汉代宫廷、乡里礼乐活动中都还保留了一些周代乐舞、乐歌。《汉书·礼乐志》记:“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安和也。”[4]1043-1044《隋书·儒林列传·何妥》记隋代博学重臣何妥对秦汉以来经典乐舞的演变作了进一步阐释:“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 至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19]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乐舞。古代中国在王朝更替的历史时刻都有与之适应的盛大歌舞的产生,秦、汉两朝也创作了宏大的民族史诗式的歌舞艺术。而这种盛大的礼乐艺术,既有《四时》歌舞的之类的创新艺术,也有《文始》《五行》之类从古代继承而来的历史乐舞。其中秦始皇将周代《大武》改作《五行舞》,而汉代之初将舜时的《韶》(《招》)改成了《文始舞》。古典乐舞不仅在宫廷保存,民间乡党间的“乡饮酒”“乡射礼”的礼俗活动也得以流传。
王国维指出:“《诗》家之诗,士大夫习之,故《诗》三百篇至秦汉具存。乐家之诗,惟伶人世守之,故子贡时尚有《风》《雅》《颂》《商》《齐》诸声。”[20]事实证明,不仅春秋战国《乐经》并没有消逝,即使秦火以后周代音乐经典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于秦汉社会间。虽然总体说来,《乐经》的流传呈现出衰微的状态,但是还是在运动中艰难生存,是不断破坏也不断建设的过程。《乐经》的艺术不断变换形式,但是作为一种宫廷音乐其基本精神是一贯的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否认《乐经》的存在,或者将《乐经》的消亡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时代的政治原因是不足取的。
(二)《乐经》是礼乐文化的实践操作体系
《乐经》是一个实践性构成,是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运用系统,所以,《乐经》侧重于实践操作,不能将其单纯地理解为文献的形式。“诗之所至,礼亦至焉。 礼之所至,乐亦至焉”[2]1616,诗礼相依,礼乐相依,相互依存,是周人对音乐的根本理解。礼是强调运用的,礼乐不仅仅是文献,而更是寓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体系。
“六经”中《诗》《书》《易》《春秋》偏重于文献,而礼乐二经偏重于实践操作。《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有“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21]1822之说,孔颖达疏谓:“《诗》之大旨,劝善惩恶。《书》之为训,尊贤伐罪。奉上以道,禁民为非之谓义,《诗》《书》,义之府藏也。礼者,谦卑恭谨,行归于敬。乐者,欣喜欢娱,事合于爱。揆度于内,举措得中之谓德。礼、乐者,德之法则也。”[21]1822《诗》《书》属于文献典籍,故归于“府藏”;而礼、乐偏于实践,故归于行事,所谓“行归于敬”“事合于爱”也。
郑樵《通志》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22]625这段话一方面阐释了礼乐相依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礼乐以“用”为主的实践特点。礼乐固然有文献部分,因此其《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六经”;而礼乐又是一种实践技能,因此“礼、乐、射、御、书、数”并称“六艺”。《周礼·地官·大司徒》有“六艺”之教,即“礼、乐、射、御、书、数”,这里的礼乐不是指文献,而是与击射、驾驭、记载、计算等实用技能一起的操作能力。《礼记·王制》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2]1342春秋两季温凉适宜,便于实践,因此教以礼乐;而冬夏两季,或热或寒,不便于室外活动,而利于室内诵读,故教以《诗》《书》。正因为礼乐教育以实践为主,所以礼乐常以演习为主。《礼记·月令》记孟夏之月:“乃命乐师,习合礼乐。……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2]1365-1366《史记·孔子世家》记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3]1548言及礼乐多用“习”“用”,都强调的是礼乐的演习运用的特点。宋代学者王应麟引用胡寅(致堂)的话说:“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23]“礼乐无全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礼乐传承,固然有文献的流传,但其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操作,是具体的应用。以《仪礼》《周礼》《礼记》为代表的礼学经典是礼学文献的重要构成,但这远不是礼典的全部,实践操作才是其核心的内容。礼乐相依,礼经如此,乐经也如此。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谓:“在孔子之时,虽只此《诗》《书》二经,然此二经,孔子并不大注重,其注重的勿宁说是礼、乐二者。此二者实是孔子之道,经书虽然没有,实是一种活的经书,由孔子的一言一行以及其教门人的微言大义,实在此礼、乐的活用。”[24]
与《诗》《书》的典籍收藏相比,礼乐则更突出地表现为朴素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功能。《礼记·乐记》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2]1543,礼乐不仅在祭祀、礼典、外交等重要场合中发挥着稳定秩序凝聚人心的政治功能,也在具体的人生活动中发挥着转移性情浸润人心的教化作用。
(三)《乐经》的文本是丰富而广泛的文献构成
《乐经》的内容是一个体系性构成,从形式上说,既包括以资料性存在的文字记载,也包括了实践性层面的操作系统;从内容上说,既包含文本方面的“六代之乐”“诗三百”等音乐文本,也包含了以《乐记》为代表的理论阐释;既包含了职官制度、宫廷礼仪等政治制度,也包含了乐器功能、乐工演奏等技术性介绍。舒大刚认为:“《乐经》实在应当包括四大部分:讲乐官设置和音乐制度的内容,如《大司乐》;讲具体的乐曲和歌词的,如‘律吕’和《诗经》等;讲音乐演奏场合和制度的,如《仪礼》《礼记》中的‘工歌’、‘师奏’等文献;讲音乐原理和乐教功能的,如公孙尼子的《乐记》《王禹记》、‘刘向记’等。”[25]这实际上也是对《乐经》文献综合性体系性的一种表达。周代音乐的实践性、动态性、综合性的特点,决定了《乐经》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
从音乐文本上说,周代礼乐歌诗是《乐经》文本的基本构成。诗乐相成,“诗三百”所录皆为乐歌,风、雅、颂即是一种音乐分类,《诗经》的编辑正是礼乐演奏的蓝本。在重大的礼乐活动中演奏诗篇,是周代宗教与礼乐生活的通例,《周礼》有“大司乐”之职,教国子以乐舞,乐舞即“六乐”,包含了“《云门大卷》①时下各种《周礼》注本《大司乐》均作“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案此非也。此处音乐是,“周所存六代之乐”,每代有一首乐舞,所谓黄帝曰《云门大卷》,尧曰《大咸》,舜曰《大》,夏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将黄帝乐舞作两首《云门》《大卷》解,甚误,应作《云门大卷》。《周礼·大司乐》在此段文字后又重提“舞《云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云云,没有所谓《大卷》,只六首乐舞,《云门》当是《云门大卷》之简称。《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六乐”的真正意义是时代的记录是历史的象征,按照郑玄的理解“六乐”是“周所存六代之乐”[26]787,“六代之乐”是对六个时代伟大事件的记录和歌颂。新近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保存了成王、周公等西周政治家在“饮至”礼上的歌唱和《周公之琴舞》等诗篇,虽无乐谱,但是通过乐器、典章、形式分析,依然可以描述周代乐歌的一般形态。
从实践层面上说,周代形成了一套与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人生设计等相适应的体系完备的用诗用乐制度。周代礼乐实践体系也是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秩序,通过礼乐实践体现政治的神圣和秩序。天子大飨的典乐隆重而庄严,但其最重要的是体现政治的威严仪式,而不是一般性的宴饮。因此规定酒饮至齿不入口,《左传·昭公五年》载:“设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饮;……礼之至也。”[21]2042行礼时不可倚几、不可饮酒,就更别说进食,参礼者小心拘谨,恭敬有加。飨礼主敬,飨礼过程中设几、致酒,只有仪式意义。
周代礼乐实践贯穿于整个人生过程。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全面介入周人的社会生活,不仅表现在周代天子公卿宗庙祭祀、演耕朝觐等大型的政治活动,也表现在乡间里巷生死婚姻、宴饮聚会等普通的世俗生活。与政治性的宫廷庙廊礼乐活动不同的是,诗乐风雅渗透乡里生活,通常是以朴素的基础的风俗的形式实现。清代学者江永把周代制度、朝聘、宫室、衣服、饮食、器用、容貌等礼制统称为《乡党图考》,是把乡党理解成周礼发生的源头。诗乐精神凭借着乡间里巷的礼乐活动渗透到周代乡人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理论形态上说,《乐经》已经建构起古典文艺理论的基本架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音乐的理论论述,《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有相当多的音乐理论论述,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艺术的思想高度。而近年来大量的简帛金石文献的出土出版,例如清华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简帛文献,丰富了古典音乐理论的内容,显示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广泛的影响。而《礼记·乐记》《荀子·乐论》《史记·乐书》等音乐理论经典,是对古典艺术理论的体系性成果,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最高成就,这一点《乐记》尤其具有代表意义。
诗乐同源,古老的音乐理论也是古老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础是音乐理论。关于音乐理论文献包括三类:一是经典文献中对音乐系统而成体系的论述,代表着古典音乐理论的最高成就。如《礼记·乐记》《荀子·乐论》《吕氏春秋·古乐》《史记·乐书》。二是传世文献对音乐的一般理解和个别的认识,虽然这类文献不是体系性的音乐理论著作,却显示了那个时代对古典音乐的全面认识。如《国语·周语》《左传》《论语》《孟子》《庄子》等。三是近年来出土文献中有不少音乐理论的资料,这是对中国古典音乐理论的丰富与补充。如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特别是上博简《孔子诗论》,具有代表性。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理论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出自不同思想家的论述,但在艺术起源、中和美学、诗学人生、礼乐政治、艺术教育等基本问题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而这些基本理论依然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骨架,即使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仍然与这些传统的理论血脉相连。
在对《乐经》的文献资料简单梳理和《乐经》存在的基本形态理论辨识之后,可以对《乐经》得出以下基本的认识:
第一,《乐经》是存在的。古老的祭祀与宗教活动,也是最早的诗乐活动,从原始仪式到政治制度,《乐经》的形成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第二,《乐经》是独立的。诗乐礼关系密切,但又不可替代。不能简单把《诗》《礼》与《乐》混为一谈。
第三,《乐经》是综合的。不能将《乐经》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文献,或者仅仅将其解释为某种技能,其包含着文本、实践、制度、操作、教育、理论等广泛的内容,《乐经》是综合的体系性构成。
三、宫廷礼乐歌诗与《乐经》的文本形式
关于《乐经》的文本,一个基本意见是《诗经》是《乐经》的文本形态。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著录刘濂《乐经元义》八卷云:“濂谓《三百篇》之诗,以词意寓乎声音,以声音附之词意,读之则为言,歌之则为曲,被之金石管弦则为乐。《乐经》不缺,《三百篇》皆《乐经》也。”[27]朱载堉《律吕精义·外篇》亦曰:“臣尝闻臣父(按:指郑恭王朱厚焥)曰:‘《乐经》者何。《诗经》是也。《书》不云乎。”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之谓也。迄於衰周,《诗》《乐》互称,尚未歧而为二。”[28]《诗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音乐的历史风貌,但并不能因此以《诗经》代替《乐经》。《乐经》的文本应该有更古老的流传历史,有更独特的艺术样式。《乐记》中多处描述了《乐经》的文本形态,却被我们忽视了。按照《乐记》的描述,《乐经》文本有悠久的历史根源,从《诗经》的结集来说应该是一种“古乐”,“六代之乐”是“古乐”的典型样式。这些音乐场面宏大,气势恢弘,呈现出音乐、舞蹈、表演、诗歌相互融合的艺术形态,有强烈的历史传承、礼乐教化和政治示范意义,是《乐经》文本的古老形态和代表样式。项阳谓“《乐经》应该特指周代被奉为经典的、作为雅乐核心存在、所备受推崇的‘六代乐舞’”[29],尽管“六代乐舞”并不是《乐经》文本的全部,但是不可否认这些音乐是周人理想中的音乐经典。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观乐,对《国风》《小雅》等一方面有美学上的欣赏赞叹,一方面有政治上的批评讥刺,甚至对大雅篇章的评论也有所保留,而独对《韶乐》激赏到叹为观止、无以复加的程度:“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 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21]2008联想到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叹,《韶》乐是《乐经》经典音乐的代表作品,季札观乐时《诗经》尚无定本,其欣赏的《象箾》《南籥》《韶濩》《大夏》《韶箾》等并不见于今本《诗经》,可以断定《乐经》文本有更古老、更独特、更盛大的艺术形式,代表着西周盛世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新近出版的《清华简》等记载了许多盛大的上古音乐,特别是以《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为代表的六代之乐,是早期中国礼典音乐的代表形式。对《乐经》文本形式的认识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乐经》文本是尧、舜及夏商周三代的“治世之音”。所谓“治世”,往往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王朝出于上升时期的积极向上的社会状态,流传千古的政治功业也注定产生宏大雄伟的盛大礼乐艺术。《乐记》将音乐分为“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而真正的“治世之音”是“安以乐,其政和”,这与“乱世之音”的“怨以怒,其政乖”和“亡国之音”的“哀以思,其民困”区分开来。周人对音乐经典的理解首先是体现出“平和”的美学精神,平和即是不激越不过度不过于悲伤更不一味哀怨。《国语·周语下》记鲁昭公二十年周景王铸无射大钟,遭到了单穆公、伶州鸠等思想家、艺术家们激烈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所铸乐钟的声音过度,有失平和,违反了“听和而视正”的审美原则。在他们观念中,真正的音乐应该是平和的中正的,所谓“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30],是乐器与心灵之间平静的交流,是政治与艺术完美融合。周代思想家将这样的音乐理解为音乐的本来形态,是盛世积极向上的时代记录和心理反映。
《周礼·大司乐》记载的“六代之乐”,是上古时期的民族史诗,也是真正的音乐艺术经典:“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26]787“六乐”包含了《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六乐”的真正意义是时代的记录,是历史的象征。所谓“六代之乐”,按照郑玄的理解,“六乐”“周所存六代之乐”[26]787。 “六代之乐”是黄帝、尧、舜、夏、商、周六个时代的历史记录,是对六个时代伟大事件的记录和歌颂。郑玄注曰:“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殚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26]787
“六代之乐”完整地记录了上古时代华夏先民图腾崇拜和开天辟地的历史,形象地反映着华夏民族创业之初的重要历史事件,是华夏民族气象恢宏的伟大史诗。反映了上古时代筚路褴褛开天辟地的恢宏历史,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自信和开阔胸襟。这种宏大的代表着部族国家积极向上精神的盛世之音,才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音乐经典。从《周礼·大司乐》看,以“六代之乐”为代表的《乐经》文本是周代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样的音乐经典具有滋养心灵、改变民风的重要作用。《乐记》这样描述经典音乐的艺术形态和思想教化意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2]1536
第二,《乐经》文本是诗歌、音乐、舞蹈、表演融为一体的综合的“大合乐”艺术形式。周人很少将音乐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所谓音乐总是同舞蹈、诗歌、表演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音乐是“大合乐”。“大合乐”也是在《大司乐》中记载的:
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26]788-789
这段文字从三个方面描述了“大合乐”的艺术形态:一曰“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的综合形式。大合乐是比“合乐”包含的艺术形式更广泛更丰富的音乐形态,《仪礼·乡饮酒礼》有“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31]986。 郑玄注曰“合乐,谓歌乐与众声俱作”[31]986。 大合乐除了诗歌、音乐、舞蹈之外,还有表演。表演是颂是容是象,是演绎故事,是叙述史实,大合乐就是后来的音乐舞剧。二曰突出和谐列邦、团结族群、愉悦宾客、安定远方的作用,音乐经典一直强调颂扬和谐,而反对愤怒抱怨,这是《乐经》文本的情感主题。三曰“六代之乐”是大合乐的代表形式。以《云门》祭天,以《咸池》祭地,以《大韶》祭祀四方,以《大夏》祭祀山川,以《大濩》祭祀女祖,以《大武》祭祀男祖,其中洋溢着虔诚的宗教情感。
“六代之乐”随着时代的演进,大都面貌不清了。而《大武》由于是西周乐舞,文献多有记述,凭借有限的资料和先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还原其基本形态。《礼记·乐记》记录的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显现了西周初年整个民族的历史脉络。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2]1542《武》六成的音乐结构,与《史记·周本纪》叙述历史线索正相吻合,是一部提纲挈领的周代发展史,被语言省略的历史事件通过史诗剧的表演形式得以完整的展现和保存。《大武》的叙事结构有开端、发展、转折、高潮,有文戏,也有武戏,有乐舞,也有歌诗,显示出中国古典礼戏已经相当成熟。
第三,《乐经》文本是具有礼乐教化意义的“德音”。经史学家描述的《乐经》不是纯粹的艺术形式,而总具有礼乐教化的意义,在精神深处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是渗透着道德内容的——“德音”。子夏说:“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2]1540德音具有“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的形式特点,而这样的艺术形式充满着“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的激情氛围,实现着“纲纪既正,天下大定”的道德使命,古老的《乐经》文本就是这样的“德音”。“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鎗而已也”[2]1541,真正的音乐是感受其强大的道德力量。
周人认为在天地自然中存在着一种平和而有秩序的旋律,对天地自然节奏的效法就是礼乐兴盛的基础。《乐记》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2]1530正因为如此,周代盛大的政治活动总伴随着宏伟的礼乐仪式,政治的高蹈自信与音乐的悠扬旋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治的礼乐化过程一定程度弱化了政治争斗的残酷,而显示出人性某种程度里的平静祥和,在血与火的冲突中有了一丝脉脉含情的温馨。《礼记·明堂位》记:“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2]1488一个王朝不论以何种方式取得政权,常常宣扬的是偃师修文的主张,而倡导礼乐文明。周人刚刚取得政权,就开始了制礼作乐的历程。《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举行献俘进鼎的盛大仪式:“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终。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钟终,王定。”[32]
武王克殷元年四月,周人灭殷之后,从辛亥日至乙卯日连续五天举行献俘庆祝活动,而整个活动中“籥人”的角色特别值得注意。其实所谓籥人,即乐人,是专职的音乐官员,整个庆贺活动共演奏了《庸》《其》《万》《明明》《崇禹》《生开》等大型音乐歌舞。其中的“庸”,即“颂”。《周礼·春官·视瞭》“颂磬、笙磬”[26]797下,郑玄注曰:“磬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26]797在《仪礼·大射》“乐人宿县于阼阶东”[31]1028一节下郑玄又注曰:“笙犹生也。东为阳中,万物以生。……是以东方钟磬谓之笙,皆编而县之。……言成功曰颂。西为阴中,万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钟磬谓之颂。……古文颂为庸。”[31]1028可见《其》《万》《明明》《崇禹》《生开》等都是表演、歌唱、舞蹈、言语融为一体的歌诗活动,是一个王朝刚刚取得政权,处于上升时期的艺术,充满了某种自信精神与乐观情怀。
第四,《诗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乐经》文本的历史形态。笔者之所以不同意《诗经》即是《乐经》的观点,是因为被经学家称颂的《云门大卷》《咸池》《韶》《大夏》《濩》《大武》等音乐经典广泛流传时,《诗经》还未编辑。《诗经》编辑成书时,属于《乐经》文本范畴的作品早就在宫廷上传播。吴季札观乐时对《象箾》《南籥》《韶濩》《大夏》《韶箾》等经典乐舞称颂有加,孔子称赞《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18]2469,听到这样的音乐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有了“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8]2482的感叹,《周礼·大司乐》将以《韶》()为代表的音乐作品列入了周代贵族教育的必须学习的经典,而恰恰是这部分作品未收入《诗经》,显然《诗经》与《乐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经典。
《乐经》是一种经典,是一种范式,周代思想家们理想中的音乐经典是辉煌时代的盛世之音,是肩负道德教化使命的礼乐“德音”,是音乐、诗歌、舞蹈、表演综合的艺术形式。而《诗经》辑录的作品有三分之二属于“变风变雅”,孔子对这部分作品极力斥责,孔子心目中的音乐经典是“六代之乐”一类的治世之音。孔子将《韶》《武》与夏代历法、殷商车骑、周代冕服,看作一个时代礼乐文明的最高象征,《韶》《武》之音才是符合其政治理想与审美追求的音乐经典。而孔子丝毫不掩饰其对郑风的反感,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18]2525,竭力攻击“郑风淫,佞人殆”。深受孔子影响,子夏也把“郑卫之风”看成是扰乱心志的“溺音”,《乐记》曰:“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2]1540显然,孔子及其门徒对《诗经》的心态是矛盾的,不是其理想的《乐经》文本。《诗经》是春秋时期便于城邦贵族交际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礼乐蓝本,而不是《乐经》文本的典范形式。
但这也不是说《诗经》与《乐经》完全无关。《雅》《颂》之音,是周代经典音乐形式,也最为孔子等推崇。季札观乐,称赞《大雅》:“广哉,熙熙乎! 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21]2007而又以“至矣哉”这种音乐的最高境界评论将《颂》乐,称赞其:“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21]2007
近期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对《颂》《大雅》的评论十分吻合。《孔子诗论》第二简谓:“《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屖,其歌绅而荡①“其歌绅而荡”句中“荡”,马承源等整理作“箎”,按,非也。根据上下文应作“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鲁国观乐曰:“美哉,蕩乎,乐而不淫。”以荡表示《豳风》音乐的赞美,应与此义同。,其思绅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33]与季札一样,孔子也以“至矣”概括了《颂》乐达到的崇高思想和审美境界。夏即雅,这里的《大夏》即《大雅》,孔子也以“盛德”称誉其思想内容。《诗经》中的《大雅》(正大雅)和《颂》的部分反映了上古时期治世的气象,体现了儒家的音乐理想,经过孔子等人的整理依然保留了《乐经》文本的历史风貌。虽然这是西周礼乐文明衰落时期的作品,但也体现了孔子等进步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是他们对西周以上音乐经典的怀念与追求。
从《大雅》《颂》的艺术形式可以追索《乐经》文本的原始形态。本质上说《雅》《颂》是一种宫廷艺术。一般的即兴的诗歌创作,往往是个人的朴素的简单的。而《雅》《颂》属于周代的礼乐歌诗,属于集体的邦国的政治的,而礼乐歌诗气势宏伟、规模庞大,形式复杂,必须依靠强大的王朝政治来支撑。即兴的朴素的原始诗歌因为有了强大西周王朝的政治支撑而成为代表周代艺术的典型形式。但也应该意识到正因为歌诗的本质是一种宫廷艺术,其艺术风格、审美形态、结构样式都带有宫廷政治和礼乐文化的特色。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谓:“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22]865道出了雅颂音乐的宫廷政治属性,宫廷政治是典乐艺术的政治保证。
从礼乐文明出发,《乐经》文本只能是从属于宫廷“合乐”艺术,是体现中正平和审美理想的“德音”,是反映一个王朝上升时期的“治世之音”。
四、“成均之法”:《乐经》的职官与实践形态
《乐经》并不简单是文本构成,更是一种礼乐实践体系。《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等以六代之乐为代表的音乐经典并不见于今本《诗经》,恰恰反映了上古音乐经典的实践特征。“六代之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重在实践,不是《诗经》这种文献所能容纳的。礼乐相依,礼重在实践应用,乐也重在实践应用。
诗乐运用是中国早期音乐的根本特征。“万物有灵”观念导致了上古时代普遍的祭祀风俗,天地鬼神、日月星辰、山川风雨无不被虔诚祭祀,而最早的礼仪音乐就产生于祭祀的舞台上。
祭祀是一个王朝神圣的礼典仪式,也是盛大的诗乐舞台。远古的诗和最初的《诗》都是诗、乐、舞结合的视听综合性艺术,《诗》主要以乐章的形式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典礼。演礼之时,乐舞伴奏,配之以诗,在特定的场合举行并表现为一定的仪式。这种具有使用功能的乐舞是古老的《乐经》文本。在周代乐官中,大司乐职掌“成均之法”,所谓“成均”,即是“成韵”,行使着演绎诗乐的政治使命。
《周礼·大司乐》:
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26]788-789
《礼记·中庸》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2]1629郊社是天子祭祀天地神祗之礼,禘尝是祭祀先祖之礼。《诗经·周颂》中的诗篇正好与此对应,《毛诗序》谓:《清庙》“祀文王”;《天作》“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祭祀天地”;《时迈》“巡守告祭柴望”;《执竟》“祀武王”;《思文》“后稷配天”;《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丰年》“秋冬报也”;《雍》“禘大祖”;《载见》“诸侯始见乎武王庙”;《有客》“微子来见祖庙”。天地四望、列祖列宗,四时农耕都有相应的宗教礼节,也有与之适应的祭祀歌舞,这些祭祀乐歌,诗乐互用,统一于礼,不仅仅体现为宗教的神圣情感,更潜藏着文化与艺术的丰富象征意义。
《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间也。”[2]1457“声”是一种特殊的宗教语言,沟通天地,交流人神,悠扬神圣的乐曲构成了一个通向神灵世界的畅想空间。这里的声,不是简单的声音,而是声与乐舞融为一体,便是乐歌。《诗经·商颂·那》是早期祭歌的代表形式: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 顾予烝尝,汤孙之将。[34]620
此诗描绘的是规模宏大的乐舞表演,以鼓声为主,有鞉鼓、庸鼓,辅之以管声,伴之以宏大的《万》舞表演,商汤的子孙们隆重纪念祖先,嘉宾助祭,一派和乐。而这里的“万舞”表演,充满尚武精神,耐人寻味。后世文献中所常见的“万舞”,《诗经·邶风·简兮》有对“万舞”舞者和舞容的描述:“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34]308
《墨子·非乐篇》中说齐康公兴“万乐”,对“万舞”舞容也有描述:“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穅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绣”[35]。 对“舞容”“礼节”和“仪节”的要求决不亚于对乐舞内容的要求。可见“万舞”是带有军事训练、显示力量、充满尚武精神的乐曲,这种舞蹈融入宗教盛典中表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在周代政治性用诗用乐活动中有着严格的政治要求。《周礼·春官·乐师》: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敎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敎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凡乐成,则吿备。诏来瞽皋舞,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令相。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令相,如祭之仪。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乐出入,令奏钟鼓。凡军大献,敎恺歌,遂倡之。凡丧陈乐器,则帅乐官,及序哭,亦如之。凡乐官掌其政令,听其治讼。[26]793-794
整个西周宫廷上下无不行走在一种音乐旋律中,君王行走的旋律是《驺虞》,快步的旋律是《采荠》。而射箭的时候,君王《驺虞》的节奏,诸侯是《狸首》的节奏,大夫是《采蘋》的节奏。宴饮之间,军旅大献,无不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旋律。一方面把周代贵族的言行纳入音乐的旋律之中,一方面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
周代用诗用乐有一个严格的礼乐制度和庞大的官职系统。围绕礼乐歌诗,周代宫廷建立了一系列严格而完备的礼乐制度体系。周代歌诗制度从上古的“典乐”制度而来,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集典礼文本、官制乐器、典礼仪式、艺术理论等一套完备的礼乐文化体系。在周代宫廷中,音乐越来越体现出职业化、专业化的特征,因此《乐经》与一般的文化经典不同的是,具有强烈的专门化特征,这正是《乐经》实践性特征的表现。
事实证明,作为“六经”之一的《乐经》,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乐经》不是简单的一本书,而是一个体系。具体说来就是:以“六代之乐”和《诗经》为代表的文本形式;以礼乐活动为代表的实践体系;以大司乐为代表的职官系统;以《乐记》等为代表的理论体系。《乐经》在形成过程中汇聚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和审美意蕴,成为潜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乐经》作为文化支撑,所谓“诗”“礼”之类,就没有了艺术和审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