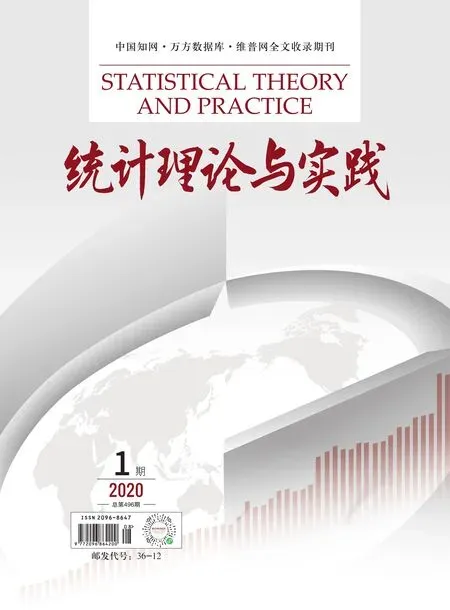经济测度遭遇“系统外部冲击”的颠覆性风险
——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应该得经济学诺奖吗
2020-01-08邱东
邱 东
经济测度是为了减少人们所研究对象在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事物自身的不确定性除了通常被关注的“随机不确定性(Random uncertainty)”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模糊不确定性(Fuzzyuncertainty)”。客观事物本身构成存在不可截然分解的成分,当人们确定研究对象范围时,就同时将与该对象相联系的某些因素排除在外,但这些因素实际上仍然在影响着所确定的对象。笔者将其概括为系统外部冲击,如果我们完全忽略之,所得到的测度结果实际上会有偏误。如果偏误过大,就会造成认知的颠覆性扭曲。本文专门探讨“系统外部冲击”对经济测度的可能影响。
一、引子:实证模型优劣取决于“约等于”对“等于”的逼近度
实证研究需要经济测度为其提供数据基础,而经济测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研究对象的边界确定,即“测度什么①作为经济统计学“数量规律学派”的主张者,天津财经大学肖红叶教授特别强调“测度对象”的确定问题。(What should be accounted)”?研究不能漫无边际,需要确定一个系统作为特定对象,从而就同时产生了“系统外部冲击”问题——被划在系统外的因素对测度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产生显在和潜在的冲击,再大的专家也躲不开这种困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②众所周知,威廉·诺德豪斯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消息传来,多数经济学者为这个迟到的颁奖而兴奋,毕竟,诺德豪斯早就被公认为杰出的经济学家,这次总算实至名归。不过也有“不和谐”的声音:认为选择这个时机把诺奖授给诺德豪斯不过是政治上的对冲,特朗普总统等美国政客在环境事务上的主张与欧洲精英们大异,需要用学术力量抵消其负面影响,也表明一种政治正确。政治是非的判断因人而异,本文无意充当“此案”的判官。,这里要阐述的是,即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也不例外,都可能隐含一种颠覆性的经济测度陷阱:遭遇“系统外部冲击”就可能面临巨大的认知风险,因而需要从经济统计学角度对诸多经济数量实证研究进行方法论层面的专业反思。
笔者一直强调经济数量方法的“机理研究”,对宏观经济统计三大主要内容(经济测度Economicmeasurement、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ing与国际比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笔者概括之为MAC)而言,不仅应该明了方法问题——“如何测度(Howquestions)”,更应重视高层次方法论问题——“为什么如此测度(Whyquestions)”,尤其要警示经济测度中面临和隐含的种种陷阱。而宏观经济统计并不是抽象的方法论研究,实证之实,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研究对象,即“测度对象(The target of measurement)”或解决“测度什么”的问题。这里,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不过是一个引子,最典型地说明了“系统外部冲击”所带来的测度陷阱。
从基础概念看,系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方法。通过层级关系划分构建系统和子系统,可以深入地把握测度对象,将其在系统中定位,进而得到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进步——更好地把握某个子系统及其在母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而模型便是人们刻画系统和子系统数量关系的基本工具。
任何计量模型,都须具备等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把等号放进模型,为了等式能够成立,任何模型都包含系列设定、假设和前提。笔者多次强调一个观点——假设与前提是模型有效性的边界:在假设与提前划定的范围内,该模型有效,如果假设前提与现实差异过大,则模型所得结果就可能沦为一种对实际经济问题的“伪计量”,看似大厦巍峨,实则海市蜃楼。
测度影响对策,认知风险导致行为风险。“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①见南北朝刘庆义《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四种风险的叠加,如果后三种(瞎马、夜半、深池)危险都出现了,那第一种危险(盲人)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视力尚存,也是心智有问题——选择性失明。如果真的心明眼亮,怎么会任凭那三种风险同时出现?然而古往今来殷鉴比比,先哲并非空想,而是对社会现实中“系统风险叠加状态”的一种概括性记录。
经济学本来只能是、也应该是一种有限理性,但模型表现出来的往往是貌似精确的结论。这是人们误解“科学性”使然,似乎只有精确的才是科学的,岂不知当对象本身处于模糊状态时,赋予其精确的描述,就笃定是人工雕琢处理的赝品。从社会视角看,这也是模型构建和使用者的功利性指向使然,数值精确性越强,模型越受追捧。当下流行实证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于,极度轻视计量模型的经济统计学基础,没有意识到或坦诚地交代和暴露其“测度、核算与比较(MAC)”所面临的种种缺陷(很多还是基因上的缺陷),听任社会各界遭受误用经济学信条及其实证结果的风险。以经济统计的基本问题为例,下文阐述经济测度显在或隐含的“系统外部冲击”。
二、GDP“六字母公式”包含的系统外部冲击
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模型中以Y标示)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②GDP应该是国民核算的“基础指标”,而不是好多人所指称的“核心指标”,GDP总量统计还是很初级的,国民核算的中心议题应该是结构分析。,在Y=C+I+G+(E-X)这个简化模型中,(E-X)是世界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贸易差额,其数值大小隐含了他国与该国的一种外部经济联系。GDP这个“六字母公式”看着很简单,只用到数值的加减法,实质上却很难测度得清清楚楚。难度并不在计算,而在于指标边界的“模糊不确定性”,这与数理统计强调的“随机不确定性”还有区别。正是因为GDP指标内在构成项目的边界含混性,(E-X)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经济战的第一战役。
国家间不仅仅在贸易差额的数量大小(经济作用力度)上有争议,甚至连作用方向都不确定。如若集中关注国际交易利润流向,由于产品定价上的产业链纵向不平衡,贸易差额越大,穷国受到的长期损失可能就越多③本来贸易差额只是两国贸易买卖额的多少之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利用人们对经济统计意识不强的弱点,将其与“两国间谁获利更多”画等号,精明的商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国人切不可受此类鼓噪裹挟,对该指标作歧义解读。。然而,这个焦点入不了主流经济学的法眼。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富国,穷国往往只有接受的份儿,但富国经济学将自己的认知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很少考虑到穷国的特殊条件,更无视富国给穷国带来的外部负面影响。在早年德国崛起时,这种经济学认知上的争议就曾产生于德国与英法之间。前车之鉴,史书言之凿凿,新兴国家切不可掉以轻心。
GDP往往是经济活动活跃程度的反映,在经济实践中未必就真能实现为“增加值”。发达国家将低端工厂外转到新兴国家,只是给了穷国打苦工的机会,退一步讲,即便国际市场的定价合理,国际交易利润也主要被跨国公司据为己有。如果再把定价中的垄断隐形获利考虑进去,穷国的经济身份其实相当卑微。而且,隐含在这种纵向链条中还有另外一种成本外移,即富国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又将“非清洁生产”和垃圾等推出国门,进而在环境责任上居于道德高地。如果我们对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链位”①笔者2020年在《迪顿新论超越GDP——敢问路在何方》中首次提出这个反映国家间竞争格局的概念。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国家间竞争格局没有冷静的判断,就容易沉醉于“GDP幻觉”②英国金斯顿大学史密斯博士提出的概念,参见John Smith.The GDP Illusion-Value Added vs Value Capture.Monthly Review,July 2012。之中,而系统外部冲击的“漏测”为这种梦幻涂上了玫瑰色。
此外,GDP定义为增加值,但这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实践中需要将该经济统计的方法制度落实到位,才能达成指标设计的初衷,才能切实地反映客观经济关系。如果“中间消耗”剔除得不干净,存在漏测问题,那么GDP就难以真正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成果(增加值),这也是系统外部冲击扭曲指标的一种体现。我们可以用直线模拟曲线之法来理解这种冲击影响。显然如果我们用多段直线代替曲线,就可能比用一段(或少段)直线的替代更接近现实,直线与曲线的离差就不只是在平均意义上减少。
三、绿色GDP的双重计价陷阱
绿色GDP的设计初衷是重视资源和环境因素,弥补GDP的测度缺陷。但是它的计算无非是一种“收入等价法(Income equivalent method)”:在常规 GDP 上做增减调整,添加资源环境因素对经济产出的正面作用,去掉资源环境因素对经济产出的负面影响。
绿色GDP是否可行,关键在于对资源环境因素影响方向和力度的测度,或者说如何给资源环境因素定价,这是第一个计价陷阱。试想,如果将环境污染因素的价格定得足够高,采用“强可持续性”原则的一票否决思维,那所有经济生产的价值都可以被抵消掉,绿色GDP可能为负值。这种测度结果意味着应该中止所有经济活动,此种数据指向能被社会和各国政府接受吗?只要采取笔者倡导的“推极归谬法”③将某种主张推向极致,看看其后果能否被承受或被接受?,就可以知道绿色GDP所隐含的测度风险,究竟妥当与否,大有批判空间。这里,任何人都无法给出一个无可辩驳的资源环境因素定价,社会面临的实质是一个没有最优解、次优解也很难确定的问题。看上去绿色GDP只是加加减减,但要确保“经济意义上的可加性”却难上加难,难到任何一种处理都可以被否定的程度。
绿色GDP的另外一个计价陷阱就是国家间的成本效益分配。资源可转移,环境无国界,这个地球还没达到只用清洁生产就能维系的地步。富国标榜使用清洁能源,生产清洁能源设备时的污染却留在了穷国。富国还堂而皇之地将垃圾和非清洁生产输出到穷国,所以,“污染发生国”与“污染最终责任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笔者早就指出④参见邱东(2008)《享用烤乳猪的贵族有资格斥责后厨残忍吗?》一文,收录于《偏,得以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邱东、陈梦根《中国不应该在资源消耗问题上过于自责——基于“资源消耗层级论”的思考》,《统计研究》2007年第2期。,贵族有钱在豪华餐馆享用烤乳猪,但没有资格指责后厨的垃圾肮脏,也不该埋怨厨师耗用食材过多。
四、SNA的 “国外”账户意味着什么
在国民核算体系(SNA)中,包含了五个经济主体账户,居民户、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外”。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账户设计从被核算的经济体着眼,所谓“国外”与人们的日常理解不同,仅仅指世界各国与该经济体相关的经济活动,至于他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则并不包含其中,某外国与其他外国的交易也不在其中。实际上,核算时是做了一个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经济体,本经济体和他者,于是所有外部世界与被核算经济体的经济联系都归纳在“国外”账户之中。与居民户、企业、政府等真实主体账户不同,这个主体账户实际上是一类特定经济活动的集合,是“虚拟主体账户”。
关键在于,为什么SNA需要人为地设计出这样一个虚拟的经济主体账户?主要有两个方面理由,一是确保该经济体内部的经济核算平衡关系,二是确保各国核算加总与全球核算的平衡关系。“国外”账户定格了他国对该经济体的所有外部作用,一个非常基础性的规范定义,否则,SNA就无法成为一个平衡系统,其中的各种核算等式关系也无法成立。可见,“国外”账户在概念上保证了核算体系的完整性,如果核算结果要免于“系统外部冲击”,就需要将“国外”账户项目搞清楚。
社会现实中,国家始终是一个利益分配单位①这一点往往是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明明是从发达国家视角产生的经济学分析和综合,却将之作为普世的理论向全世界推广。,因而也就必然是经济测度的基本单位,但是这个“国”如何来界定,却是一个需要经济统计深入探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测度中,存在着究竟遵循“国民原则”还是“国土原则”的选择。最开始国民核算的所谓“核心指标”是GNP②即现在的GNI,名称改变实际上体现了对“三方等价原则”的反思,强调生产与收入的差异性。另外,也应该视为“基础指标”而非“核心指标”,因为那种认知属于“GDP中心主义”的理念。,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完成了从GNP到GDP的转变。为什么需要改变经济总量的基础指标?正是因为受到了“系统外部冲击”:由于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股票市场交易的国际化,原来以“国民”角度界定国家边界的方法难以奏效。经济统计从来都以可行性为基准,退而求其次,只好选择相对比较容易界定边界的“经济领土”作为“国”属划分的依据。
五、SNA“中心框架+卫星账户”模式的出路
迄今为止,国民核算账户SNA一共有四个主要版本:1953年版、1968年版、1993年版和2008年版。由于需要核算的内容越来越多,从1993年版开始,SNA采用了“中心框架+卫星账户”的包容性模式。
拓展反映经济现实与保持国民平衡核算,是两种相悖的要求。采用“做加法”的方式摆布核算结构,实际上是在二者之间搞妥协,一方面尽可能满足测度经济现实的需要,保持国民核算的对象相关性;另一方面又能达到起码的专业统计标准,保持核算体系的内部一致性。问题在于,各卫星账户所针对的特定内容也需要纳入SNA核算,但又无法与中心框架的核心内容等量齐观,因为中心框架以外的核算内容并不具备经济意义上的“可加性”,只好开辟一系列核算卫星账户,作为“另册”处理,矛盾似乎得以缓解。
而接续的问题在于,需要添加的卫星账户越来越多,每个卫星账户本身体量也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多的专家看重“环境与经济核算系统(SEEA)”,并一直谋求将之正式列入SNA中心框架。按照这个趋势,SNA所谓的中心框架很容易失去其本来意义。当经济测度与核算的重心从经济生产转向社会福利,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要,SNA原有非常精致的核算框架就难以保持其优越地位,核算相关性竟成了问题,核心地位也难以维系。
这是核算内容受到生产因素之外的系统外部冲击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出路何在呢?SNA实际上遭遇到MPS当年同样的困境,核算范围究竟如何界定?需要认真面对。所谓“超越GDP”实质上就是“超越SNA”,相当大的变革趋势。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大家做了多年研究,撰写出版了两次经济测度报告③两份报告的名字过长,取三位领衔专家名字的首个字母,笔者分别简称之为“SSF经济测度报告”和“SFD经济测度报告”。,然而,在SNA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系统外部冲击”的问题上,两份经济测度报告并没有给出逻辑一贯的解决办法,测度机理尚未真正打通④笔者撰写出版了《经济测度逻辑挖掘:困难与原则》(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的第一本),将“SSF经济测度报告”所涉及的测度问题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出来。。
六、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新兴国家为什么不能照搬套用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非常流行,好多人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混淆了“能用”与“好用”。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不同国家面临的“系统外部冲击”不同。
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同,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发展约束(系统外部冲击)不仅不同,而且往往可能恰恰相反。发达国家可以将低附加值生产(往往表现为低效率生产)乃至非清洁生产转移到国外去,而新兴国家不仅很难进行这种负外部性转移,反而需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落后产能,作用一正一反,对整体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相当大。
同样的发展计量模型,在不同国家应用时所面临的要素约束不同,如何估价不同方向和力度的系统外部冲击,应该成为重要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他们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外部冲击或可忽略;对新兴国家而言,不仅存在“链位”相近国家对产业“机会”的竞争,还面临全球价值链高端国家的垂直式打压,外部冲击可能使其他内部因素的影响大大减弱。采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时,如果仅仅考虑经济体内部诸要素影响的分解,模拟结果的经济意义恐怕荡然无存。
发达国家提高生产率,技术创新是最大瓶颈,但对新兴国家而言,并不是技术瓶颈突破了,就可能实现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技术创新过程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的打压;另一方面,即使技术瓶颈突破后,在市场推广上也会受到强国的毁灭性限制,创新很难最终实现。这种市场环境对弱国的外部性冲击,是一般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所忽略的,而新兴国家则需要在经济计量中重点加以考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的5G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美国的全力限制,这种灭顶性的系统外部冲击,对中国本土的5G技术应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七、气候变化经济学能不能将全部外部冲击都纳入计量模型
气候变化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群的新成员,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赫赫战果。作为已经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界取得突出业绩的学者,感召于人类命运前途,威廉·诺德豪斯教授另辟蹊径,开创了经济学家族这一新分支。威廉·诺德豪斯开发了“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IAM)”及其衍生品,事关诸多核心计量工作,比如:确定基准表明气候变化及其幅度;将气候变化归因到诸因素,首先是自然因素(太阳辐射、大气环流)与人为因素的两分;估计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模拟减少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作用,等等。
然而,需要深入辨识的问题太多:地球外部空间对地球的气候影响究竟如何?是使地球变暖还是趋寒?相对于宇宙演变的时长而言,人类迄今所掌握的地球气候变化数据是不是极小的样本?人类真的有能力将外空间影响全部纳入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吗?地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分析”计量吗?就两大系统交互动态作用的成本和收益而言,其时间和空间边界究竟如何界定?其各种分项可以加总吗?这些疑问都应该是该项研究获得意义的基本前提,如果定义域没有明确,定义能够完备吗?如果没有明确的释义,模型的等号真能成立吗?而相对于外部冲击的巨大不确定性,模型具体处理的精细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地球在宇宙空间非常渺小,人类在太空中的地位呢?自然就更不值得一提①试想,大象从蚂蚁身边踩过,而后蚂蚁得知大象怀孕,内心便十分负疚,将其视为自己的过失,岂不贻笑大方?。如果大系统与小系统极不相当,所谓“地球转暖”就面临根本性疑问了:“转暖”即意味着原来存在着所谓正常的温度,根据什么做此判断?谁能具备确定地球温度标准的资格?当我们断定“地球变暖”“气温升高”时,其实内在地设定了一个参照系,比如选定1765年(工业革命开始)为基准年份,将其气候选定为所谓未变暖、未升高的状态,也即将其“自然化(Naturalize)”和“正常化(Normalize)”。这种选定是否武断?是否尊重自然和历史?
退一步看,即便地球真的转暖了,到底是人类过度消耗的后果,还是地球自身气候演变周期的趋势表现?如果是前者,又如何在富国和穷国间分配责任?如果是后者,就说明人类自视过高②假设外星空存在着高智能族群,他们会不会像我们嘲笑蚂蚁那样嘲笑我们?。当人类采取限制碳排放等环境保护措施时,其实是将地球气温的变化“人为化(Artificialize)”“问题化(Problematize)”,似乎气候变化就是问题,就是人为造成的环境灾难。
由于外部冲击的不确定性,与任何其他气候变化的风险估算一样,“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及其衍生品都必然引起争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美国NBER的马丁·威茨曼,还有伦敦金斯顿大学的斯蒂夫·基恩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异议,争论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未来、对穷人,还有对生物圈的损益究竟如何“折现”,尽管威廉·诺德豪斯聪明绝顶,且数十年潜心集中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但在某些学者眼中,“诺德豪斯损害函数”大大低估了人类面临的生态风险。
1966年,竺可桢教授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100周年纪念会时首次发表英文稿《APreliminaryStudyon the Climatic Fluctuations During the Last 5000 Years in China》。1972年他在《考古学报》第l期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教授主要采用“物候方法”,将中国5000年气候变化分为8个温暖和寒冷交替的时期。而后,龚高法、ZhangJiacheng、张丕远、满志敏、葛全胜等学者在这个领域里又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学者这些成果给我们的启示是:(1)通过与国外相关研究对照,可以发现全球气候变化的传导路径,而且,地球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区虽有差异,但大致同步。(2)地球并非越来越暖,或越来越寒冷,而是呈现着一定幅度的周期变化。(3)中国东部20世纪不是过去2000年中最暖世纪。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的中国也并不比古代更热,典型的反例就是,甲骨文研究表明,商王武丁在河南猎获一头大象,表明当时河南的气温相当暖和。河南简称豫,寓意是什么?
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是否参考了中国学者的上述信息呢?除了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关信息又如何呢?“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的设计者应该具备弹出地球看地球的天外平台,至少应该具备“地球总统”的视野,然而这恰恰就是此类模型的最大短板。
退一步看,即使地球变暖了,对内陆国家、对俄罗斯、加拿大和北欧国家是不是收益大于损失?如果这些国家的净收益之和大于赤道附近国家因地球变暖的净损失之和呢,人类应该怎么选择?
还可以做一个设问,如果地球进入冰河期,人类能不能尽力加大碳排放以减缓气温的下降程度?在地球气候变化上,人力和自然之力较量,谁是赢家?如果无法断定这个问题,怎么就可以断定人类碳排放是地球转暖的系统性因素呢?
总之,在地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影响的问题上,“系统外部性”的冲击最难把握,测度的不确定性最大。
八、测度系统外部冲击的风险值得重视
且把眼光从外空间收回,即便在地球上,人类也未必就是主宰。借助工具优势,我们对很多植物和动物为所欲为,可是对微生物呢?人类敢断定自己真的占据优势吗?此次新冠病毒不就给全人类上了惊醒一课吗?
这个星球哪里就一定是人类说了算?微生物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人类真是出类拔萃的生物,还只是微生物的寄生工具而已?有学者指出,我们愿意吃某种食物其实并非出自“己愿”,而是我们胃肠里的微生物喜欢那种食物。真要是那样,人类与外生物的边界究竟怎么划?这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容易,外部冲击原来就隐藏在我们的身子里!细思恐极,颠覆认知。
回到社会领域,极而言之,经济计量中没有等号。实际经济关系往往应该是“不等式”,而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取巧用“等式”加以表示,因此即便我们的假设前提成立,等号(=)也不过是约等号(≈)的代理,为了简便或条件所限,我们将约等号拉直,仅此而已。模型所表达为“确是(Exactlybeing)”的概念和关系,事实上都是“约是(Approximatelybeing)”。关键就在于事务的内外边界无法绝对地划分,在于所谓“系统外部冲击”无法全部纳入计量模型。不管模型在形式上多么精确,本质上最优也仍然只能是“差不多先生(Mr.Almost)”。而且由于真值未知,能不能成为“差不多”的模型,很多时候无法确知。所有“结论”实际上都顶多只能是“小结”,历史还在延伸,事务本身还没有完结,何结论之有?
还有一个系统外部冲击导致不确定性的实例,应该提出加以警觉: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结论被国内外多数经济专家坦然接受。岂不知,ICP只是进行国际经济比较的一种方法,并非天经地义,其方法论还存在相当多值得深究的问题,哪怕已经成为全球标准,也应该系统地深入检讨。要害在于,ICP的比较方法建立在“纯价比假设”和“等价比假设”等基本假设基础上,无法在国家间找到“同质产出”进行比较,忽略了发达国家产出中隐含的高质量因素,系统性地高估了其价格,低估了其实际产出,相比而言,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高估了其实际产出①参见邱东《国际经济比较中的购买力平价与市场汇率之辩》,《中国统计》2020年第4期。作者还撰写了《国际比较(ICP)何以可能?》(列入了“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专门就其方法论提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批判。。
九、经济测度,人类一直在路上
由于系统外部冲击,经济“测度、核算与比较(MAC)”很难达成预设的标准,并没有理想模型,人类一直在路上。这里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该建立“多元化系统观”。“子系统”和“母系统”的表述便于理解系统的内部关系,但也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容易成为“视觉主导的系统观”,将母系统或子系统的关系固化,大圈套小圈,大球套小球②耳朵和眼睛让我们聪明,也容易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懒惰,更注意视觉听觉传递的信息,而不作或少作“深度加工”——综合与分析。。现实社会中,系统关系非常复杂,系统间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叉。所谓母系统与子系统的界定,往往是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研究视角,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分析框架。如果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发生变化,子系统和母系统的关系就相应发生变化。
第二,重视“指标口径”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第23章“一国收入的衡量”③这里的“衡量”即Measurement,笔者主张将之译为“测度”,因为“度”的含义对经济指标的认知更为重要。中强调:“重要的是,要记住GDP包括了什么,而又遗漏了什么”。这里,曼昆所强调的就是GDP的指标口径问题。有的人以为,一个指标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这算什么学问呢?要害在于,为什么包括和不包括,这里藏着大学问。“系统外部冲击”最终往往通过“指标口径”表现出来,所谓“口径”就是指标的外延定义,不可小觑。
第三,注意“系统外部冲击”与“外部性”影响的区别。在经济学中,“外部性”是一个基础概念,是行为主体对他者造成的非市场化影响,如果这个影响是正面的,受益者无须承担费用,可以搭便车;如果这个影响是负面的,行为者无须承担补偿费用,可以转嫁隐形成本。由此可见,外部性概念的要害在于“非市场化”,从行为发生角度看是一种附带结果,而“系统外部冲击”包括了行为主体间的直接作用,范围应该比“外部性”更广,二者有时需要严格加以区分。
第四,注意提升经济统计研究的“增加值”。笔者讲述了这么多经济测度问题和陷阱,并不是主张放弃测度,而是着重指出,经济研究者不能过分渲染自己的实证成果。应该意识到经济计量出现理想结果的稀有性(如果不是人为调试出来的结果),应该坦白地承认研究固有的基础性缺陷,应该让他人将已有的研究当成“中间产出”,而不是“最终产出”。真正的学者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研究的增加值,而不是把研究形式化,做出八股文章,即便套用“洋八股”便于高中SCI,也于中国高质量发展无补,没有经济统计对中国国势、国力、国情的基本判断,我们就无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和规划,就无法扬长避短。谨慎测度,打好坚实的数据基础,方能在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