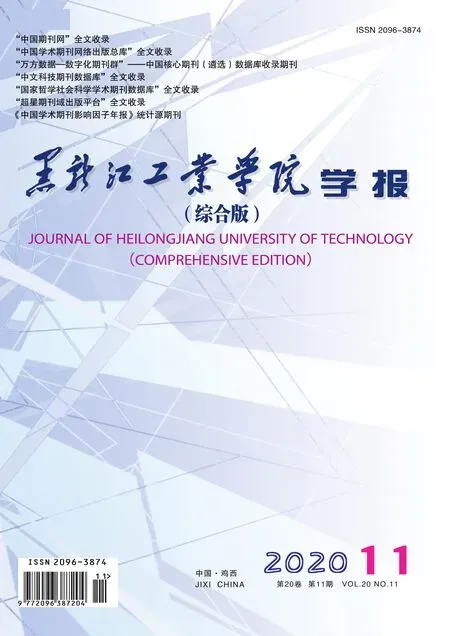战时解放区文艺出版与新旧之间的女性形象
2020-01-08吴春云
吴春云,赵 坤
(1.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山东青岛266061;2.山东大学,山东青岛266237)
作为中西文化竞争的阶段性结果之一,五四时期是现代思想启蒙的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品赞美自由的、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同时也抒写她们独特的敏感与苦闷。因此,我们看到的新文学景观中既有子君、莎菲,又有祥林嫂、“为奴隶的母亲”,这新旧两种女性同时作为新文学书写的典型对象延续到左翼文学中。如果说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受众大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那么到了延安解放区,受众就自然转变为毛泽东所言的“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1940年前后,正值张闻天主管中共中央文化宣传工作,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创作环境,知识分子都拥有着后来无可比拟的宽容待遇。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后也希望激发创作活力,甚至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这样充满质疑之声的文章。从受众的接受程度和1942年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应来看,《解放日报》《谷雨》等刊载的作品无疑影响很大,这也从侧面透露了文艺报刊与延安“新女性”形象之间某种隐秘的关联。
一、延安文艺出版环境
因政治文化宣传工作与革命战争、教育人民等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报刊书籍的出版工作受到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办的《解放》周刊创刊;1940年3月25日,边区党委机关报《边区群众报》开始出版。其后,《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1月15日创刊)、《中国青年》(1939年4月16日创刊)《中国妇女》(1939年6月1日创刊)、《共产党人》(1939年10月20日创刊)、《中国工人》(1940年2月7日创刊)、《中国文化》(1940年2月15日创刊)等一批新报刊纷纷出版,形成了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1941年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以及应对边区经济困难的需要,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一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并成为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份大型日报。1946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1948年6月15日,该刊与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合并,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另外,1939年12月(一说为1940年春),华北新华日报社和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合并,由报社发行部在麻田村成立了新华书店;为配合整风运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过大量整风文献;出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后更是名声大振。
因早期人才、物资方面匮乏,1939年以后,延安的文学刊物才陆续创办。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会刊《文艺战线》创办,周扬任主编。1940年,何其芳等诗人建立延安新诗歌会,遂有《新诗歌》创刊;丁玲、萧军、舒群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文艺月报》创刊。1941年,周扬主编的《中国文艺》创刊;1941年11月15日,延安文抗的机关刊物《谷雨》创刊,共出6期。同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文艺》作为专栏发刊,每期占据八分之一版面,丁玲担任文艺副刊主编。截止到1942年3月11日,“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但由于办刊期间多次因所刊出的作品受到批评,引起诸多方面的不满。专栏主编丁玲因此被调到文抗,由舒群担任主编。后《解放日报》又撤销了“文艺”专栏的刊头,改第4版为各种综合性副刊。创作环境相对自由、知识分子受到重视与优待,因而自1941年1月始,至1942年《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撤销之前,是解放区文学活动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谷雨》创刊后,由舒群、丁玲、艾青、何其芳、萧军等组成编委,也集中了延安最重要的一批作家,刊载文学作品、介绍文艺理论。因经历了延安文艺自由论辩和整风运动,因而由《谷雨》也可一窥作家们的思想和话语的转变。丁玲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也希望激发创作活力,牵头撰写了大量延续五四风格、充满质疑和批判的杂文。当然,延安妇女问题的大讨论、有关女性形象的作品发表,作家性别诉求的表达,也不完全局限于文艺类刊物。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妇女解放”思想也因战时形势而成为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以上都为各类报刊对根据地内外的批评与暴露以及本文所涉及的性别书写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期也创造出大量的文学“新人”形象,比如金桂(《传家宝》)、孟祥英(《孟祥英翻身》)、折聚英(《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杨小梅(《新儿女英雄传》)等。同时,解放区也塑造了不少经典的“旧人”形象,既有被压迫的,比如喜儿(《白毛女》);也有被批判被改造的,如“三仙姑”(《小二黑结婚》)、金桂婆婆(《传家宝》)等等。此外,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也颇有成就,比如陆萍(《在医院中》)、丽萍(《丽萍的烦恼》)等。正是在这些作品的女性角色勾连出的谱系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史上女性形象塑造的一次重要转折。
二、新旧之间的延安女性文学形象
显然,解放区最初塑造的众多女性文学形象,其实是新旧杂陈、形象多面的。只是这些形象或多或少都有些变形。五四形成的新文学传统将反封建争自由植入到作家的思想里,在初到解放区之后,作家们一时间无法转变观念,尽管他们也积极响应解放区塑造文学新人的号召,将批判现实主义转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达,但在具体的文学表述中,往往受到五四文学观的深入影响。所以呈现出的延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在刻意为之的表达与无意识观念的摩擦中,共同呈现出一种女性“无性化”的特征。五四时期到延安时期,知识女性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五四’一辈文艺家对主体性自我的辩难,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萌芽。‘我’不论是个体小我或是国家社会的大我,原来竟是有性别之分的,不能以一中性(男性)的修辞叙述,一语带过。”鲁迅先生笔下的子君婚前发出“我是我自己的”的声音来表现个体独立的价值认同;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说出“我要,我要使我快乐”来表现一个苦闷新女性的欲望;冯沅君笔下的维华说出“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来表现冲破桎梏渴望和对甜蜜爱情的热烈追求。而到了左翼文学时期便慢慢发生变化,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下,个体情感的抒发、理想的追求都让位于家国、革命与战争,于是“革命+恋爱”的书写模式在三十年代非常流行,如丁玲在长篇小说《韦护》中对于革命战胜恋爱的书写中,可以看到她开始转变莎菲式的困惑,主人公丽嘉在爱人因革命事业而离开自己之时,也决心走向革命。到了解放区文学,知识女性的形象发生着变形,追求自由与自我要让位于国家民族的危机,女性个人意志的书写被逐渐淡化。
《解放日报》所刊发的涉及女性的作品中,作者更多的是通过表现女性生存的困境来揭示解放区的社会问题、婚恋与妇女政策。这种揭示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变化对女性经济力量的需求,因而出现了一些从“被压迫”转变为“革命战士”的新人形象,新的社会政策成为她们改变命运的契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的女性立场与性别关怀,因而在有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处在两难抉择中的女性,她们的身体在回归家庭与走向社会之间发生着难以调和的冲突。1941年9月16日,温馨的短篇小说《凤仙花》发表于《解放日报》,文中的主人公凤儿来帮公家人“我”带孩子,起初十分胆小,满脑子都是旧的观念且不愿接受任何新改变。在“我”的引导和帮助下、青年队的影响下,凤儿渐渐看到自己与青年队里其他人的不同,进而生出转变的意愿,从一个“土包子”一步步改变自身:剪发、放脚、讲卫生,逐步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最终勇敢反抗父权的控制,对打骂她的继父喊出“你!你压迫我!我不由你!我不愿在家里”的声音,与旧社会伦理最终决裂。最后,凤儿主动要求并正式参加了八路军,一个受继父打骂不敢言语的旧女性最终转变为革命队伍中的新人而且是女战士。同样的还有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解放日报》,1943年3月30日),根据真实人物的经历,塑造了一个苦命女性终翻身的形象——折聚英。“她三岁上死了爹,就凭寡妇妈妈受苦过日子。”九岁就跟着家里人逃荒,在全家挨饿的情况下送她去做了童养媳,然而在丈夫家里也是受尽压迫,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还差点被卖掉。要成亲的那天,在女宣传员池莲花的鼓励下,折聚英坚定了去参加红军的想法,在这过程中她摆脱了夫家的折磨,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后来逐渐成长为抗日妇女先锋、边区女参议员,原先的婆婆家也对她态度由恶转喜。虽然大篇幅描写了折聚英在娘家和公婆家里悲苦的生活,但也有着一种乐观的精神在其间。在对折聚英形象的塑造中,作者注重其思想的转变与犹豫后的积极行动对完成人物翻身成长历程的重要作用,她改变前后身边的环境、人物都仿佛是两个天地。这些妇女的解放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在她们遭受苦难的岁月里会出现一个革命的领路人,凤儿遇见了帮助她改变外表与思想的雇主,折聚英遇见了女宣传员而知道了可以投身革命,加上她们自身的思想觉悟或者说反抗当前境况的决心使她们最先成长为“新人”,她们的解放都是以革命斗争和区政府解放妇女的政策为前提的。新的社会到来使得她们得以翻身解放、吃饱穿暖,得以挣脱旧式婚姻对自己的折磨,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还有部分作品是写老年妇女对革命的支持和对士兵们生命的保护,过往经历未明但却思想进步、具有奉献精神,这类妇女实则更符合战时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作者往往只截取了一个战士与主人公短暂的交流片段,体现出劳动人民对战士们的深情、对前线战事不遗余力的支持。崔璇在1945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短篇小说《周大娘》中,主人公周大娘是个将近五十岁的寡妇,还是一个妇救会主任,二十五岁的儿子已经参加了八路军。为了保护偶然见到的一个伤兵,她勇敢地同敌人周旋,还不惜放火烧毁了自己的房子。伤兵想帮忙救火抢救一点东西,但出于安全考虑周大娘“硬将他搀走,离开那个闪着火光的房子”。这里的周大娘是一个愿意为抗战的胜利奉献一切的女性,她身上的勇敢胜过男性,时常让人忘记她的五十岁妇女的身份设定。同类型的还有高朗亭的《雷老婆》(《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雷老婆热情地招待负伤的“我”,全力保护“我”的安全,面对白军的搜捕,不似雷老汉的“不自然”,她镇定而机智,使“我”得以保住性命。
知识女性的形象也可在本时期的作品中见到,但无疑是发生了变形的。1942年3月,葛陵的短篇小说《结婚后》发表于《解放日报》,小说中,妻子马莉抱着正满月的孩子坐在床上跟前来祝贺的朋友们欢快地聊着天,丈夫杜廉在给大家准备午餐。看似喜悦的氛围掩盖下是两人婚后的苦闷。马莉曾是一位知识女性,曾在大学里读书,而且善于弹钢琴。同那个时代无数个怀着激扬的革命理想奔赴延安的学生一样,马莉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说:“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经过两个月的恋爱,原本无意结婚的马莉嫁给了从事文艺工作的杜廉。尽管不是接受组织安排而结婚的,但她的婚姻生活仍然令自己感到窒息。婚姻、生育孩子中的一切琐事磨灭了一个知识女性对革命的热望,却留下了对爱情的遗憾。这样的生活无疑是一部分来到革命圣地女学生共同的命运,在理想与家庭的矛盾中产生永久的迷惘与挣扎。雷加的《孩子》于1941年6月24日发表于《解放日报》,其中涉及了儿童的保育问题,“新人”生母与“旧人”养母同样真诚爱着孩子,但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矛盾痛苦。主人公尹棠是“我们机关里的女同志”,因为无暇照顾孩子而托给当地百姓家抚养。因“那个妇人不满意了每个月十块钱的报酬,要求再领十斤麦……”,索性把孩子抱了回来,然而孩子并不愿意面对这个亲生母亲。后来查明孩子得了气管炎,养母赶来看望,尹棠又“为了孩子怨恨她”。孩子熟睡后,尹棠幻想着等病好后孩子可以去干净健康的托儿所。故事并未交代尹棠的具体身份,从目前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以及对农村百姓家庭育儿方式的反感来看,多半是奔赴延安的青年女性。既不愿局限于家庭,也恐惧于孩子只亲近养母。同时,孩子的养母作为一个“落后”农村妇女,对于钱粮看似有所“过分”的要求也反映出当时衣食不足的艰苦条件;四十里路赶来看望却不得,“一副热望的脸凝住了,接着搐动了”又见其对孩子的珍贵情感,物质与情感的矛盾交织,也正体现出一个囿于家庭生计的农村妇女所承受的挣扎痛苦。
三、叙述的调整与自我改造:以丁玲为中心
丁玲在延安完成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这些故事中几乎都涉及女性角色甚至以女性作为主角,其结局都可见作者的挣扎和迷惘,贞贞怀着希望踏上了去延安治病和学习的路;陆萍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医院再去学习;何华明的妻子继续在名存实亡的婚姻里煎熬。女性的身份使她坚持女性的立场,意识形态的变化又使她不得不放弃女性的立场。1941年6月,丁玲的小说《夜》发表于《解放日报·文艺》。文中何华明的妻子,她甚至不像文中出现的另外两名女性一样有名字,比丈夫大十二岁的她容颜已老、身体也不再适合生养、不能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面对她的哭泣,何华明想的只是“这老家伙终是不成的,好,就让她烧烧饭吧,闹离婚影响不好”。文中也隐藏着一个女性视角,这是一个被丈夫嫌弃的女性,没有爱也没有儿女,没有进步的意识和反抗的思想,甚至在她的悲剧的生命里已经看不到任何一丝希望。这些作品多被认为是丁玲反抗精神的部分回归,也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独特感知与关怀。
丁玲所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于1941年发表于《中国文化》,小说中身为作家的“我”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而被送到霞村暂住修养,尽管“实际上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在霞村“我”遇见了曾被日军抓去当军妓的地下情报员贞贞,她回到村子里被村民们议论纷纷,唯恐避之不及。在“我”的进一步了解中发现,贞贞原本有机会早点逃离火坑,但经由我方军队的劝说自愿重回敌营获取情报。敌营归来的贞贞无法忍受家人和村民们的非议,也拒绝了曾经的恋人夏大宝,决定接受党的安排——去延安“治病”和学习。在这个故事中,贞贞是被叙述的对象,而叙述者“我”同样是重要的一方,作为女作家的“我”与贞贞的对话可以看作与一个革命者的对话。作者虽没有写出“我”经历过什么,但可以想见,那让我“病”的并不会是什么愉快经历,再加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修养、一个女性独特的性别体验,故与村里人的嗤之以鼻不同,“我”对贞贞的情感是同情且理解和心疼的。在未见面贞贞之前听到村民的议论便已让“我”心生反感,“我忍住了气,因为不愿同他吵,就走出来了,我并没有再看他,但我感觉得他又眨着那小眼睛很得意的望着我的背影。”“我”除了一重作家身份到底还经历了什么?为何身体已经复原了却被送来“休养”?“政治部的嘈杂”又是指什么?“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将又见着她的,定会见着她的,而且还有好一阵时日我们不会分开的。”作者似乎为贞贞安排了一个光明的出路,可是那里既容不下“我”,她的命运又真的会比“我”好吗?战争已然对她、对“我”造成的摧残,不会随着走向延安结束,不会随着抗战胜利结束,最广大的“人民”依然站在她的对面。“我们所见的,是叙述者游移于各类角色所代表的立场间,企图包容彼此的矛盾,却终究更无奈地泄露其破绽间隙。”她们二者之间仿佛是“休戚与共”的关系,“贞贞的出现俨然具象化了她(丁玲的‘我’)‘身为女性’所特有的期盼与恐惧、希望与挫折。女性革命者的道路比男性走得更为艰苦”。所以这里的知识女性已经不再是五四时期无所畏惧地追求自由或是抒发苦闷、表达欲望的新女性了。她们的行为、言语、思想或许不得不向着革命话语的期待方向发展,但五四时期接受的思想和教育经历深深影响着她们,宏大的革命目标无法解决女性的实际生存痛苦,也无法解决她们写作上的困境。
同年,丁玲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发表于《谷雨》第1卷第1期,主人公是年轻的产科医生陆萍,从上海的产科医院毕业后辗转来到延安的“抗大”念书,“为了党的需要”,她被安排到延安一座刚成立的简陋乡村医院后。受过良好教育的她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知识分子的身份并没有使她得到更多的重视,这里的院长“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而她也没有选择尽快适应这里简陋的设施、卫生条件和歪风陋习,而是站出来与这里的环境做抗争。起初,“成为习惯的道德心”使她总是把别人该做却不做的工作认真做完,后来她开始与这里的环境作斗争。“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但她因此已经成为医院里的“怪人”,被大多数人投以异样的目光。“而她呢,她不管……她替她们要求清洁的被褥,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她们要图画、书报,要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是典型的五四精神的余音在解放区的回响,也是精英与大众化意识的冲突。
如果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与“革命者”对话的身份,那么陆萍的知识分子形象就变成了革命者本身。陆萍注定是失败的,而陆萍们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就暗示了延安文学的语境里,五四文学思想的尴尬。陆萍的这场挣扎,就像五四时期那群想要冲破一切桎梏的启蒙者一样,充满热情想要唤醒民众,但民众的麻木和守旧使人无奈到绝望,最终反而使自己陷入迷惘的窘境。原本“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但在与一名士兵的谈话中,她得到了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解释,似乎是想开了、妥协了,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医院再去学习。黄子平将这结局解读为延安知识分子被政治话语所驯化,“至此之后,‘时代苦闷的创伤’就在丁玲笔下消失了,或者说,‘治愈’了”。贺桂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作品中呈现出了一个五四式的主题,即‘独异个人’和‘庸众’之间的对比。这种落差表明,置身乡村民众之中的丁玲并未能自发地感受到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的革命性,相反,她所受的知识教育和感受世界的情感结构使她可以轻易地看出民众和粗糙的革命组织本身的问题,从而下意识地进行着自我/他者的区分,将知识分子(或类似人物)和乡村民众的距离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距离正是陆萍与医院冲突的根源。”然而丁玲本人解释此篇创作是一个在左翼文学中极为常见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成长叙事,并不是一个与集体存在冲突的个人最终被规训的故事。但文学阐释无疑是随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发生意义的转移与新变的,黄子平和贺桂梅的解释在逐渐成为主流并逐渐知识化的过程中,也准确地表达了五四话语在延安话语的文化处境。
结语
在丁玲等女性作家手中终究未能完成的对延安新女性的想象,最终在赵树理、孙犁等男性作家笔下“完美”呈现。赵树理笔下翻身做主的基层干部孟祥英(《孟祥英翻身》,1943)、金桂(《传家宝》,《人民日报》,1949),在新社会中不仅要做家庭中的女人,亦可充当公共领域的“男人”。孙犁1945年于《解放日报》发表了其短篇小说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小说以清新质朴、充满诗意的笔调塑造了水生嫂、大菱等勇敢而又具牺牲奉献精神的完美女性。1949年5月,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开始于《人民日报》连载,主人公杨小梅本是受欺辱压迫的媳妇,在党的指引帮助下,逐步克服种种困难,成长为革命女干部;与“思想落后”的丈夫离婚后也收获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婚姻。“新人”杨小梅几乎是延安文学中女性成长历程的一个浓缩,涵盖其面临的困难,也指出其“光明的出路”,最终符合了共和国对女性“去性别化”的终极想象。延安新女性形象的建构在建国后文学中依旧延续其影响,成为“莎菲”到“柯湘”之间的重要过渡。最终性别话语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世纪之初有所觉醒的女性的声音在民族家国的宏大叙事中再次喑哑,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在林白、陈染的作品中得到“报复”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