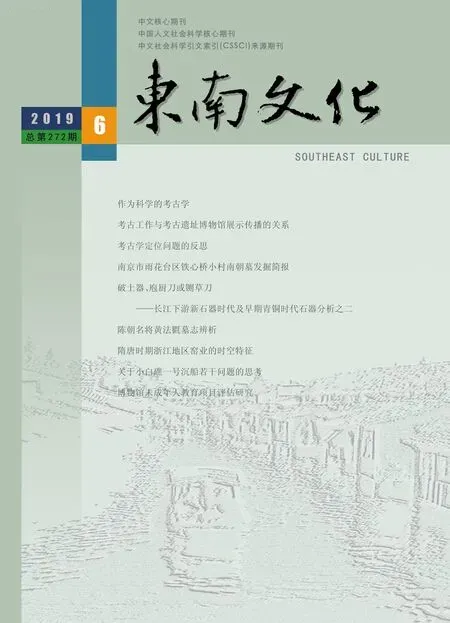“阐释性展览”:试论当代展览阐释的若干问题
2020-01-08周婧景
周婧景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一百余年来博物馆文化的重大变迁,使曾将藏品放在首位的博物馆,如今把观众置于中心,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其影响。“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作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展览。它与“非阐释性展览”相区别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使观众参与。当前我国创建此类展览至少面临缺乏整体性、过度依赖文献、习惯说教、难以建立关联和重视方式创新五方面问题,可从通用标准、所处阶段、观众研究和教育模式四方面进行归因,并据此提出围绕物、人和传播技术及其关系的三大原则和确保整体性、贯彻逻辑性、致力特殊性等的七维度模型,以创造观众相关联的真实体验,促使其实现理解、思考及情感关联,进而吸引新观众和提高重复参观率。
一、导言
早期博物馆通常政府预算充足,主要职责是收藏和研究。当前至少75%的博物馆都是二战后创建的,数量激增导致政府资助显著下降,其他收入则不断增加,如个人、基金会、企业捐赠及自营收入等,博物馆不得不“俯身”关心社会大众。同时,随着民族主义和政治独立运动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民主化变革,博物馆蜕变成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社会价值最大化成为其首要目标,服务对象由此不断扩大,多元化需求受到重视。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无论理念还是实践均出现革新。理念上,从“藏品首位”走向“观众中心”,史蒂芬·威尔(Stephen E.Weil)将其概括为从关注“‘博物馆对社会大众的期望’到‘社会大众对博物馆的期望’”[1]。实践上,几代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变化:从优先考虑展示物件,到强调传授物件相关知识,再到重视物件之于观众的意义构建。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革新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我国产生影响。博物馆需重建与观众的关系,以彰显其在现代生活中的独特价值。
在此背景下,“阐释性展览”应运而生。它主张纳入观众视角,促成观众参与,已从“减少实物展示,增添辅助展品及语词符号系统”等无意识的阐释现象,变成需有意识加以概念构建的研究对象。鉴此,本文以“阐释性展览”为研究对象,在语义学和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进行概念界定,并围绕此类展览在我国实施的困境提出针对性的原则及对策,以推动阐释性展览在探究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及通用做法方面的学术对话和理论自觉。
二、博物馆学视野下阐释性展览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阐释概念的界定:从教育活动波及主要业务
“阐释”(interpretation)一词从语义学来看,前缀inter代表在“在……之间”;词根pret=value,代表“价值、估价”,引申为“表达”。因此,interpreta⁃tion的字面意义为(信息)由一方向另一方/多方的表达[2]。此概念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但相关研究则始于20世纪的哲学领域。博物馆学有关阐释的文献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并呈现两大特点:从文化遗产进入博物馆领域,从其教育活动波及主要业务。
在美国,博物馆教育活动也被称为“阐释”[3]。更准确地讲,这种“阐释”实践最早出现于美国教育活动的口头陈述中[4]。文献研究则始见于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的《阐释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一书,他指出“阐释”是“通过使用原始物件、一手经验或解释性媒介来揭示意义和关系的教育活动”[5]。20世纪60年代,美国波士顿儿童博物馆(Boston Children’s Museum)馆长迈克尔·斯波克(Michael Spock)为“火炬手”(carried the torch)项目创造出“活动开发者”(pro⁃gram developer)头衔,又被称为“阐释规划者”(in⁃terpretive planner)[6]。可见,最早的阐释基本指向教育活动,教育人员身为阐释者(interpreter)是与观众互动的催化剂。
然而,阐释的对象和范围却在不断演进,由此引发内涵的嬗变。1986年,戈登·安巴克(Gor⁃don Ambach)指出所有博物馆活动(包括收藏、保护、展览)都是“阐释性的”[7]。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P.Alexander)等也认为博物馆阐释包括展览、青少年活动、公众项目、出版物等[8]。面对这种深刻的改变,阐释概念应如何重新被界定?以贝弗利·瑟雷尔(Beverly Serrell)[9]、美国国家阐释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10]等为代表的观点指出阐释应带有鲜明的观众取向,强调与观众发生联系,取决于观众的参与及其程度。综上,笔者认为博物馆领域的阐释是指采用某种沟通媒介,向观众传播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过程。媒介包括博物馆一切活动,目的是促使观众身心两方面参与。
(二)阐释性展览概念的界定:以观众参与为标准的展览类型
1939年,美国芝加哥艺术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馆长丹尼尔·卡顿·里奇(Daniel Catton Rich)首次在馆内开辟美术阐释馆(Gallery of Art Interpretation)。瑟雷尔指出所有类型的博物馆都能找到阐释性展览[11]。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为此设置展览阐释高级主任(Senior Director of Exhibition In⁃terpretation)[12]。丽莎·C·罗伯茨(Lisa C.Roberts)认为展览本该是一种阐释行为,但有些专业人士无法认识到[13]。沈辰、黄洋、李林、刘守柔等也论及展览的信息阐释问题[14]。究竟何谓阐释性展览?以瑟雷尔[15]、罗伯茨[16]为代表的学者均指出阐释性展览是为观众提供意义构建内容和方法的展览,观众由此获得非标准的个性化体验。结合他们和前文界定的阐释概念,笔者认为“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展览。“展览要素”包括实物及其组合、辅助展品及其组合、语词符号系统等,“身心参与”的结果即为个人意义构建。而“非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说教信息,仅用作物件识别或欣赏的展览。可见,区分两者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使观众参与。
事实上,关于展览分类问题已有学者做过不少有意义的研究,如严建强根据展品收藏政策、研究重点与深度及设计布展方法不同,将展览分成器物定位型和信息定位型[17];陆建松依循展览的传播目的和构造迥异,分成审美型和叙事型等[18]。阐释性展览的分类思考与此两种分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区别在于前两者注重发掘展览本体的内涵,而后者则侧重于探讨展览服务对象的参与。那么其与参与性展览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首先,参与性展览重视观众如何参与、参与程度及其主动性。而阐释性展览更强调观众参与的效果,不仅关注其身体参与,更注重认知和情感的参与,目标是创造观众相关联的真实体验,促使其实现理解、思考及情感关联。其次,正如《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一书所言“西蒙的研究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参与式博物馆体系,但实际上‘参与’是一个新近概念,此前国外博物馆界尚无系统研究”[19]。而“阐释”进入文化遗产领域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有关阐释的概念、原则、要素等问题,文化遗产、博物馆等相关领域已有过系统研究,笔者通过对诸如此类内容的回溯和分析,发现其对我国当代展览阐释的启示与借鉴,并尝试据此构建策展模型,以期与参与性展览的知识建设和实践做法形成互补、共进。
三、我国策划阐释性展览面临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博物馆博物馆性的变化和博物馆化的拓展,通过传播说教信息以识别或欣赏物件的非阐释性展览不再是主流。一批博物馆开始按主题组织物件和策划展览,物件选择更多虑及是否揭示主题、能否重建信史、可否透物见人,而非是否价值连城,阐释性展览因此悄然问世并获得发展。尽管博物馆的阐释内容在加深、手段在丰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有阐释意愿的展览尚保留着非阐释性展览的痕迹。展品选择和内容构成并非服务主题阐释,而是借主题统摄之名行精品展示之实。这种过渡时期不同展览类型交织的现象,反映的是转型期策展人理念与实践的革新,也是其由被动无意识追随到主动有意识创建的必然历程。当前我国策划阐释性展览主要面临五方面问题。
(一)忽视阐释的整体性
强调观众体验的整体性是阐释性展览的特征之一。如蒂尔登所言,阐释须面向整个过程而非任何阶段[20]。阐释性展览应有明确主题,主题下设各级传播目的,展览要素均应服从传播目的,以保证融为一体。在我国通常看到这样一类展览,它们传递的“名义信息”庞大,部分乃至所有展品都具有很强的阐释性,但彼此缺乏关联,为非程序化信息,事实上观众获得的“实际信息”极为有限。这类展览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各自为政,内容丰富,却一盘散沙。即便观众对每件展品及其组合所阐释的信息都能领会,整体认知仍是雾里看花,难以借助完形心理学明白策展人在内容建构上的传播目的。
(二)主要依赖文献,而非实物所载信息
迈克尔·贝切尔(Michael Belcher)认为“只有展览能提供一种对真实、可信物件的可控接触”[21]。拥有三维物质构件的实物是博物馆最为核心的资源,也是阐释的主角。然而,当前我国展览尤其文化文物类展览,策展时仍过于依赖文献而非实物,将二维的符号表征直接转化成三维的视觉呈现。随着史学研究的日渐成熟,这类展览趋于同质化。如何基于实物及其物载信息构建与文献研究并行的实物研究系统,以打造异于他馆的个性陈列,通过证经补史的差异化视角无限接近那个真实的世界,成为置于我们面前的难题。
(三)习惯于百科全书式地说教
“说教并非阐释,阐释的目标是启发和激发。”[22]当我们试图依靠超负荷信息来吸引或打动观众时,会发现两大困难:一是过载的说教信息会花费观众大量时间,也会占用展览很多资源与空间;二是当我们将自己所认为的重要信息向观众传播时,他们未必感兴趣,甚至会因信息压迫而选择放弃。当前展览虽出现以观众为中心的初步转向,但将藏品置于首位的理念仍根深蒂固,且存在有趣的博弈现象。一方面对物载信息解读尚未深入,一方面部分策展人倾向于将研究成果缺乏同理心地直接呈现给观众,导致展览出现大量专业名词、术语,如器名、科属等,表现为百科全书式地说教,缺乏科研向科普的转化。此类展览中,观众面对晦涩的海量信息感到困难,无法将专业知识加工成能理解的信息而多选择直接跳过。
(四)难以与观众建立关联
蒂尔登提出“只有展览内容和个人背景相联系的阐释才是有效的”[23]。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展览,因策展人不太了解观众,难以采取他们可识别的方式吸引其注意,因而无法有效构建与观众的关联。而非阐释性展览只专注于提供知识和事实,通常无视观众及其关联。以两段说明文字为例,如国内某展品说明牌“中国造歼—6歼机是中国仿制苏联米格—19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1961年12月开始仿制,1963年9月首飞、12月定型,1964年装备部队,多次改进改型,形成歼—6飞机系列”。这段文字尽管符合科学逻辑模式,但只是完成知识输出,不邀请观众参与,难以建立彼此联系。对比同类展品——美国西雅图历史与工业博物馆(Museum of History and Industry)“B—1水上飞机”展品的说明牌写道:“想象这是在1919年,你正在新的B—1驾驶舱内,准备将木材、电线和钻机运往维多利亚,飞机正以每小时80英里运行,发动机在你耳边咆哮。你不知道,你将要改变历史”。博物馆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模式,邀请观众将自己设想为飞机驾驶者并发挥想象参与到故事情境中,促使理解并激发情感关联。
(五)重视方式创新,而非内容阐释
实物展品作为历史遗留物,其保存与收藏常带有偶然性[24],因此碎片化物证无法与流动的历史形成一一对应。如果想真实再现那个远去世界,尤其在物证缺失的历史早期,需依赖多样化的传播方式。而传播载体通常是辅助展品,它们为系统阐释促进理解而制作,主要包含“造型物”和“信息传达装置”两类[25]。当前的传播方式已突破单一视觉传达,展览要素异质性增加,体验层次更为丰富。为完整阐释而补缺的思想及创新传播方式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却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首先,辅助展品的设计和制作单纯以艺术性、审美感为目标,忽视内涵赋予和价值启蒙,甚至放弃科学性和真实性。其次,新颖的传播方式受到策展公司和博物馆青睐,他们渴望借助高新设备和技术博得眼球,一味迷信极限的感官刺激。然而,此种方式的创新与物件内容阐释相关性不高,甚至出现“为秀而秀”的两张皮问题,展览即使能让观众获得新奇的身体体验,也转瞬即逝,难以邀请大脑参与,从而关联内容、实现理解并获得启发。
四、阐释性展览的策划:促使观众参与以提升展览传播效应
产生上述五方面问题的原因可归为四点:第一,虽然近几十年围绕展览理论和实践已出现一批优秀论著[26],但总体而言,针对通用标准的系统探讨尚且不够;第二,由于起步晚,不少专家策展人或职业策展人还处于摸索成长阶段,策展专业性仍待提升;第三,观众研究及其成果应用不容乐观,策展时容易“想当然耳”定义观众,对其认知特点和学习行为相对不熟悉;第四,策展人成长于应试教育模式下,当博物馆首要功能被确定为教育时,容易习惯性地落入灌输式教育的窠臼。
自公共博物馆时代以来,因藏品物载信息在原载体上具有唯一性,吸引着一代代观众慕名而来。三百多年过去了,尽管这种价值判断未变,但对其价值的认识却在加深:不再囿于藏品物质外壳所携带的外显价值,而是发现藏品内蕴更核心的文化价值,促成与之关联并建构意义。然而困难的是,展现在观众眼前的物件多为静态、瞬间和内蕴的非耗时表达,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观众难以看明白。因此,阐释性展览不仅要揭示展品丰富生动的物载信息,还要将其二次转化为观众能感知的多元表达,同时需将两者在空间语境下予以合理的重构和组织。如果说非阐释性展览只是冷漠地呈现,观众的参观方式是欣赏式观察,那么阐释性展览则是热情地邀请,观众的参观方式是参与式理解。一场精彩的阐释性展览必然是贯彻非正式教育理念;深入了解观众想法、需求和偏好,制定认知、情感和体验目标;去芜存菁地择取主题与内容,从内外部给予藏品和研究支持;充分熟悉空间形态下的认知与传播技术,为不同公众创造优质的实体体验。它带来的将是展览内容构成和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更是博物馆和观众主从关系颠覆的一场革命。若能根据我国当前困境,抓住其中的核心内容,纲举目张地提出对策,将有助于站在观众倡导者视角将他们融入展览故事中,实现从被动访问到主动参与甚至合作生产,以促成理解和情感联接,革新“观众中心”流于形式的旧貌。为解决这一策展新时代所涌现的新问题,笔者尝试提出策划阐释性展览的三大原则和七维度模型,以提升展览传播效应。
(一)策划阐释性展览的三大原则
在策划阐释性展览时,首先应考虑采取怎样的原则以明确策划此类展览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博物馆相关领域对“阐释原则”的最早研究同样出自《阐释我们的遗产》一书,蒂尔登提出“阐释的六点原则”[27]。实际此书出版后,蒂尔登还发表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文章,萌发出五条新的“阐释原则”种子[28]。除蒂尔登外,亚历山大也围绕“良好的阐释”作出思考并提出“五大要素”[29],但在笔者看来,其探讨的同样为阐释原则问题。
无论是蒂尔登的十一条原则,还是亚历山大的五条原则,它们均包含阐释的目的、对象、内容、方式和作用等内容,并已将服务对象或展示对象的特殊性考虑在内,如针对儿童和特殊人群及围绕自然的阐释。两位学者的系统性观点虽相隔数十载,但仍具备较强的适用性。因此,笔者借鉴蒂尔登强调的阐释方式和亚历山大主张的阐释内容,提出阐释性展览围绕“物、人和技术及其关系”的三大原则。
第一,传播中的物是阐释的主要信息基础。内涵涉及其本体、衍生和流转信息;主题包括艺术、历史、自然和科学;对象涵盖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和非物质的。它们均可被阐释,需系统、深入地加以研究。
第二,传播中的人是信息阐释供给的对象。通过对前期的动机、期待、类型等,过程中的行为和心理,结果的所感所思所获,来展开长期调查、评估或研究,并将结果应用至阐释。
第三,传播中的技术促成人与物互动,人参与其中达成理解的媒介。应依靠实物及其组合、辅助展品及其组合、语词符号等,致力于物和人的相关性及介入方式的多样性,来帮助实现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性和层次性。
原则不能被奉为教条,须因博物馆性改变而更新。本质上这些原则唯一不变的内核可被浓缩成一条——爱。“对自身存在的爱,对大众而非个人的爱……和对沟通的爱”[30]。
(二)策划阐释性展览的七维度模型
1.确保展览的整体性——制定并贯彻传播目的
展览展出什么,由传播目的决定。瑟雷尔指出“一切背后皆应有一个传播目的”[31]。有效的传播目的能聚焦、说明和约束展览的性质和范围,为策展团队提供明确目标,又可作为评估依据。因此,当展览具备各级传播目的时,策展团队才能拥有一个共同标准,用来指导展览要素的取舍、组织和表达,使之成为具备逻辑性和凝聚力的整体。什么是传播目的?它是有关展览内容的一种表述,一个完整有效但不复杂的句子由主语、谓语和结果构成[32]。它能阐明主语是什么样或怎么样的,否则就会失去对策展团队的指导意义。如美国纽约科学馆(New York Hall of Science)的“演化与健康”(Evolution&Health)巡展将传播目的确定为“每一次适应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但传播目的并非展览主题、产出或目标[33]。如“该展览有关宋代市民生活”,这是展览主题;“该展览围绕狗日常的一天呈现生物学信息”,此为展览产出;“观众将通过展览增进对海派文化的了解”,则是展览目标。它们均非传播目的,因为都未明确表达主语是什么样或怎么样。如何制定有效的传播目的?达成共识非常重要,传播目的通常需由整个团队反复讨论和编辑,而非简单投票或主策人决断,以便成员真正理解并达成共识。在整个策展中,团队需将传播目的置于显见位置,以提醒展览要素不偏离传播目的。
2.贯彻展览的逻辑性——内容结构令观众感到清晰
非阐释性展览可只主张从审美意义上对物件或组合进行欣赏,彼此不存在逻辑关系。但阐释性展览则致力于观众对展览内容的理解,需将物证组合在某一主题下,脉络清晰且层次鲜明地呈现给观众。可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是内容组织的逻辑性,策展人应熟悉单个及系列物件的基础及关联信息,提炼出贴切而富有个性的主题,确立内容框架并选择故事线,编写各级传播目的,选择合适的展品,撰写说明文字,将物件碎片化信息整合成有意义的系统叙述;其次是空间表达的逻辑性,从思维导图、概念图、泡泡图、草图、模型到比例图,团队应持续记录对展览的想法,确保其在空间设计上的一致性,将文本内容转化为物理形式,成为展览内容良好的实体阐释者。另外,策展人需清晰地向观众阐明展览结构。即使一些观众对展览系统性不感兴趣,也可在时间限制内自由选择参观;同时也会有一些观众希望在有限时间内根据预设动线来体验,掌握传播目的,理解展览内容。观众研究表明,若观众了解展览结构,按既定顺序使用,则会花更多时间,收获也更大。如美国大屠杀博物馆(Holocaust Museum)的展览根据受控的线性顺序策划,引导观众通过电梯先到顶楼,然后按时间逻辑了解战争、集中营等故事直达底层,期间还会经历恐惧、震惊和悲伤的情感之旅。强调逻辑性并非主张过分理性化,而单纯追求知识输出,不存在观众相关性的输出即使符合逻辑性,也不属于阐释性展览。
3.致力于实物的特殊性——富含个性的阐释信息源自实物本身
长期以来,策展依托文献的现象较为普遍。一方面实物研究仍较薄弱;一方面文献相对完善、容易获取,且不易产生错误。展览因而成了文献乔装打扮后的再次登场,实物只不过是点缀其中的物证。为此,需从三方面改善:第一,树立以实物及其研究为主要信息源的策展理念。当前部分展览中实物与文献的主从关系出现倒置。而展览作为媒介的特殊性在于借助实物系统重构古今自然、社会及文明,它是独立于符号化世界的证据呈现,与文献系统“犹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34],虽视角不同、取材各异,但却能证经补史。同时,实物所载信息虽然碎片化,但却鲜活生动,阐释若基于这些极富生命力的信息,将有效避免同质化。三宅泰三(Taizo Miyake)提出了“物件剧场”(object theater)概念,以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皇家博物馆(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对此概念之运用为例,在展示西北海岸面具中,该馆于一个巨大的壁柜内批量呈现展品。当观众坐到长凳上时,特定面具亮起,并以第一人称口吻述说自身内涵及创造和使用它们的意义[35]。通过“真实物件”的阐释与传播,展览极具公信力与震撼力,易于吸引观众进行多层次参与。第二,制定藏品规划。现有藏品可能是馆方经年累积的结果,且最初创办人对其价值判断已与今天的判断大相径庭。对一个资源无限的博物馆而言,当然藏品越多越好;但资源有限是绝大多数博物馆面临的窘境,此背景下选择哪些藏品入藏就相当重要。博物馆应根据使命宗旨制定藏品规划:明确已有物件、所需物件的地点,如何使用可令公众受益。我们知道展览通常有两种规划方式:一种是先确定展览主题,再寻找藏品;一种是始于藏品,从藏品中构建主题。无论哪种方式,藏品都是信息阐释的源头,为了尽可能接近于系统和完整的阐释,博物馆都需要预先作出相适应的藏品规划。正如《美国国家博物馆标准做法及最佳实践》中指出藏品规划未来应像藏品管理政策一样成为必要文件[36]。第三,重视藏品专家和主题专家,将他们培养成职业策展人,抑或职业策展人须得到专家的智力支持。藏品专家或主题专家深入接触藏品,拥有丰实的专业知识,需培养他们专业知识科普化及藏品阐释的能力。职业策展人是传播专家,并非研究专家,因此需找到特定领域的专家给予智力支持,如物质文化的信息解读、筛选和重构。国外艺术博物馆还出现了“客座策展人”,其来自大学或其他博物馆,成为流动的藏品专家或主题专家,该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4.建立观众的相关性——构建与各类型异质亚群观众之关联
“如果观众无法理解或建立展览与自身的联系,他们将选择跳过”[37]。因此,应摒弃传统的填鸭式教育理念,创建展览要素与拥有不同特征的异质亚群观众之身体、认知和情感关联。策展人发现策展已困难重重,若要与观众构建联系,则难上加难,但不能以此推卸责任,可从两方面努力。第一,提高展览自身的阐释性。首先,策展者无需担心观众在参观中是否学到新知识,而更应关注创建的内容、运用的方法和使用的材料是否已尽可能丰富。无论拥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观众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入方式”。博物馆要做到使观众在时间有限且缺乏专业受训的情况下依旧看得明白、体验舒适。其次,针对重点内容,致力于打造观众身、心和环境三位一体的有机阐释系统,促成认知和情感的相遇[38]。最后,探索相关性的实现方式。如“B2C”(Business-to-Consume)中的“个人定制”,过程中观众会因拥有专属感而获得归属感。以美国大学橄榄球名人堂(College Foot⁃ball Hall of Fame)为例,观众步入展厅后即被要求输入名字和大学信息,当其漫步展厅参加各种互动时,如扮演新闻主持人,屏幕上就会出现主持人即观众名字,获得个性化的定制体验。此种关联不仅是事实的联系,更是情感的连接。第二,尝试改变观众,在他们正式观展前通过强制性介入来弥补相关性的不足,如宣传营销、展厅内前置视频。总之,始终寻求不同学习目的、方法及模式的共同倾向,探索建立相关性的通用做法,藉由空间形态的多元感知与符号表征获得阐释成功。
5.探索展览的包容性——确保不同人群的多种需求被顾及
《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及最佳做法》规定博物馆“应努力具有包容性,为不同人群提供参与机会”[39],阐释性展览即是如此。为此,首先要认识到展览功能多样化的趋势。当前多元文化格局中,阐释性展览作为一种传播与学习媒介,功能已日趋丰富,不但能培养相关学科兴趣,还能承担促动社会变迁的责任[40]。具体而言,阐释性展览(尤其临展或特展)的功能可拓展为小微故事的叙述者、非主流或亚文化的发声场、争议性问题的交流平台及前沿科技的试验场。如美国洛杉矶的失恋博物馆(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的展品主要由失恋者匿名捐赠,每件展品都讲述了分离故事。该经历是人类共有的,博物馆让这种经历变得不再孤单,为受伤者疗伤的同时也启蒙人们采用恰当方式处理情感问题。其次,邀请观众倡导者或教育人员进入策展团队,确保不同人群的多种需求被顾及。丽莎·罗伯茨(Lisa Roberts)在《从知识到叙事:教育者和变革中的博物馆》(From Knowledge to Narrative:Educators and the Changing Museum)中谈道“教育工作者使展览更具包容性”[41]。20世纪80年代,美国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的卡罗琳·布莱蒙特(Carolyn Blackmon)创造了“团队工作法”(team approach),主张策展团队中要包含一名教育人员。其重要任务是为观众整合所有资源,如必要的信息被清晰表达,学校的课程标准被考虑,不同兴趣和年龄的人被吸引等,从而使观众的收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指导观众目标的实现[42]。
6.强调展览的粗放性——各年龄段的观众都会被具象展项所吸引
尽管观众水平层次不齐、学习风格千差万别、学习过程及结果都不受控,但“所有年龄段观众都会被更具体、不抽象的展项吸引”[43]。约翰·杜威(John Dewey)、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乔治·海因(George Hein)、约翰·福尔克(John Falk)和林恩·迪尔金(Lynn Dierking)等学者由此创建了体验式学习(experimental learn⁃ing)、建构主义教育(constructivism education)和情境学习模式(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等理论框架。鉴此,阐释性展览需探索服务于多数观众的“通用标准”,使用他们能理解和参与的方式。其一,寻找介入的起点。因观众多为外行或初学者,策展人既可通过反过程找到当初激发自己兴趣的起点,也可根据观众研究获知观众对该主题的初始想法,将自身想法、展品及学术资料中复杂的抽象概念变成可被感知的具体故事和三维呈现,以点燃观众对展览主题的好奇和激情。其二,探索常见的共同点。瑟雷尔提出若要吸引观众参与,应掌握他们在行为学和人口学上的相似点,如观众会阅读简短标签而非长标签、受欢迎的展项能吸引所有类型观众等[44]。这种共同点的发现除了实践层面的经验积累,更依赖学术层面的实证研究。如西文体系下阐释性说明标签的恰当字数为20~75个单词,美国底特律艺术博物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据此在改陈时,把标签从150个单词减少到50个,原来只有约10%观众阅读说明标签的现象很快得以改善。
7.推动展览的评估性——让观众的反馈成为展览创建和改善的一部分
阐释性展览要求纳入观众视角,故反馈在此类展览中尤其重要。《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及最佳做法》指出“博物馆要对自己的藏品阐释活动进行有效评估,将结果用来规划和改进活动”[45]。传统的非阐释性展览易于以审美为导向,评估会因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而难以深入。但阐释性展览却带有明显的认知和学习特点,受益情况可被评估,且评估结果能为策展带来实质性改善。为此,首先要重视对这类展览的评估。其次,掌握国际上展览评估的成熟理论、方法及程序,鼓励多学科介入,开展问题导向的系统评估。同时,分析我国展览评估的既有起点和优劣势,以发现问题、成因并找到对策。再次,当前我国此类展览水平参差不齐,并非均已达到评估要求。因此,现阶段宜优先开展提升展览质量的前置评估,而欧美国家的博物馆早期也先采取前置评估以掌握观众兴趣、动机,获取他们在传播目的、主题和内容上的反馈,使之亦成为展览故事的一部分。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微生物博物馆(Micropia museum)在筹建的十年间,前往学校、社区开展大量前置评估,最终为观众创造出易于理解的科普体验。最后,建立开展评估的财务保障系统。我国展览费用通常包括前期和制作费用,缺少评估费用;而欧美各国展览创建时评估费用占5%、调整和修改费用占10%[46]。虽然目前我国定级、运行等评估中均涉及社会反馈内容,但仍没有突出其应有的权重,展览评估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未来需探索符合国情的展览评估制度、程序及资金分配方式。
五、余论
正如文章“导言”中所述,欧美博物馆数量的攀升导致政府资助的显著下降,而我国数量增长的峰值较欧美滞后约50年。2018年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期间,国家文物局也表示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增多,使财力需求越来越大,未来将更多着眼博物馆的质量发展,通过动态的行业评估来精准实施免费开放政策[47]。因此,提升展览的阐释质量和水平,增强展览对观众的吸引力和持续作用力迫在眉睫。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往单纯传播知识和事实的非阐释性展览已难以满足观众成长性需求,因为观众能轻松查阅与物件有关的知识和事实。而以促成观众身心参与为本质特征的阐释性展览由于能提供观众相关联的真实体验,使他们按个性化需求自由选择学习,有助于展览被各类观众有效使用,推动个人意义建构,以吸引新观众和提高重复参观率。这类展览不再只是陈列一堆没有生命、毫不相干的文物,而是通过以“物”为载体的信息共享体,在现实社会中扮演积极角色,如激发观众学科兴趣和潜能、优化家庭或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团结等。它契合当前博物馆积极入世、追求文化民主化和发挥社会纽带的宏伟目标。
随着阐释性展览现象的出现,对其概念的建构、问题的聚焦及对策的探讨,在以观众为本的策展时代,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尝试在界定阐释性展览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策划此类展览面临的缺乏整体性、过度依赖文献、习惯说教、难以建立关联和重视方式创新五方面问题,从通用标准、所处阶段、观众研究和教育模式四方面进行归因,并据此提出围绕物、人和技术及其关系的三大原则和确保整体性、贯彻逻辑性、致力特殊性等的七维度模型(图一),希望对策划这一初具规模的展览类型有所助益。然而,这些无疑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但正是通过不断的挑战,博物馆才能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吸引观众纷至沓来,致力于充实、改善公众的生活品质,为建造一个充满人性、文明的和公正的社会发挥力量。
[1]〔美〕史蒂芬·威尔著、张誉腾译:《博物馆重要的事》,台北五观艺术2015年,第29页。
[2]周婧景、严建强:《阐释系统:一种强化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新探索》,《东南文化》2016年第2期。
[3]〔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玛丽·亚历山大著,陈双双译:《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9页。
[4]Beverly Serrell.Exhibit Labels,An Interpretive Approach(Second Edition).Rowman&Littlefield,2015:20.
[5]Freeman Tilden,edited by R.Bruce Craig.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fourth edition,expanded and updated).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7:42.
[6]Polly McKenna-Cress,Janet A.Kamien.Creating Exhibi⁃tions:Collaboration In the Planning,Development,and Design of Innovative Experiences.Wiley,2013:26-27.
[7]同[3],第285页。
[8]同[3],第289—303页。
[9]同[4],第19页。瑟雷尔认为“阐释目的是以积极、启发和有意义的方式为观众整体体验作出贡献”。
[10]同[5],第29页。美国国家阐释协会指出“阐释是基于使命的沟通过程,该过程在观众的兴趣和资源的内在意义之间建立情感和智性联系”。
[11]同[4],第19页。
[12]刘婉珍:《博物馆观众研究》,三民书局2011年,第10页。
[13]同[3],第258页。
[14]沈辰、何鉴菲:《“释展”和“释展人”——博物馆展览的文化阐释和公众体验》,《博物院》2017年第3期;黄洋:《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信息诠释与展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李林、陈钰彬:《国际性临时展览的跨文化阐释方法初探》,《东南文化》2019年第1期;刘守柔:《历史展示与文化阐释——美国历史住宅博物馆相关问题探讨》,《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15]同[4],第19页。瑟雷尔提出“阐释性展览是指让观众有机会参与展览环境,了解展览开发人员的目标,并找到与展览有关的个人意义的展览”。
[16]同[3],第258页。丽莎·C·罗伯茨指出“它是虚构者试图表现出一个物件所可能阐述的故事”。
[17]严建强:《新的角色新的使命——论信息定位型展览中的实物展品》,《中国博物馆》2011年第Z1期。
[18]陆建松:《博物馆展示需要更新和突破的几个理念》,《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
[19]〔美〕妮娜·西蒙著、喻翔译:《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译者序。
[20]同[6],第31页。
[21]Belcher.Exhibitions.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转引自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学会译,博伊兰帕特里克主编:《经营博物馆》,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22]同[5],第31页。
[23]同[5],第31页。
[24]同[17],第5页。
[25]〔日〕高桥信裕著、王卫东译(未刊稿):《新版·博物馆学讲座》,第9卷《博物馆展示法》,日本雄山阁2000年版。
[26]如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陈列艺术》,文物出版社1997年;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曹兵武、崔波:《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学苑出版社2006年;陈同乐:《光的艺术:光在陈列艺术中的应用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宋向光:《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姚安:《博物馆策展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徐乃湘主编:《博物馆陈列艺术总体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齐玫:《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策划与实施(修订版)》,文物出版社2015年;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
[27]同[5],第31页。
[28]同[5],第34页。
[29]同[3],第286—287页。
[30]同[5],第31页。
[31]同[4],第7页。
[32]同[4],第7—9页。
[33]同[4],第10页。
[34]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98年第10期。
[35]同[6],第177页。
[36]湖南省博物馆译:《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及最佳做法》,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37]同[4],第50页。
[38]周婧景:《具身认知理论:深化博物馆展览阐释的新探索——以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为例》,《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
[39]同[36],第58页。
[40]同[1],第21—22页。
[41]Lisa C.Roberts.From Knowledge to Narrative:Educators and the Changing Museum.Smithsonian Books(First Edi⁃tion),1997.
[42]同[6],第27—28页。
[43]同[4],第50页。
[44]同[4],第50页。
[45]同[36],第57页。
[46]〔奥〕费里德利希·瓦达荷西著,曾于珍等译,张誉腾校:《博物馆学——德语世界的观点(实务篇)》,台北五观艺术2005年,第138页。
[47]引自中经文化产业在第八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期间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的专访,[EB/OL][2018-12-04]http://www.sohu.com/a/279605747_160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