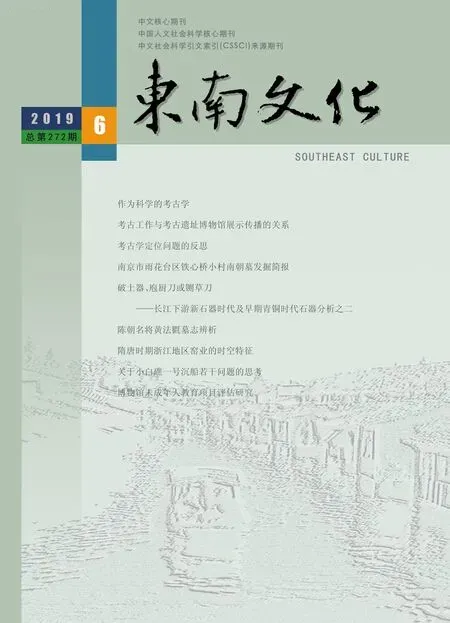江南地区明墓出土受生牒研究
2020-01-08任江
任 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内容提要:据已公布考古资料,江南地区的明代墓葬共出土三件受生牒。它们是受生寄库信仰的物化体现,与佛道教、方志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并有所补充,为探讨明代江南地区佛道教忏仪和民间丧葬习俗的渗透、交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
受生(寿生)寄库信仰自宋元以来在我国民间出现并流行至今,其核心内容为:人的灵魂在冥司借到受生钱后才能得以受生为人,在世为人需要及时通过焚烧冥钱(冥财、纸钱)、诵念经文等斋供经忏方式还纳受生钱,否则将遭遇种种横祸,还可以生前预先将冥钱寄存在冥司的府库架阁中,以获取死后的种种福报。佛教、道教、民间宗教接受吸纳了受生寄库信仰,并发展出内容不同、互有影响的经典、科仪,推动了受生寄库信仰的传播推广。佛教典籍收录两种《佛说受生经》[1],约成书于宋元时期。俄藏黑水城文献A32金代文书保存有一部写本《佛说受生经》[2]。道教典籍也收录两种《受生经》,一题为《灵宝天尊说禄库受生经》[3],另一题为《太上老君说五斗金章受生经》[4],约成书于宋元时期。由佛道教《受生经》衍生出的科仪、文书、宝卷还有很多尚存于世。目前侯锦郎[5]、索安[6]、大渊忍尔[7]、葛希之[8]、萧登福[9]、刘长东[10]、丸山宏[11]、山田明广[12]、侯冲[13]、韦兵[14]、钟晋兰[15]、方广锠[16]、张贤明[17]、姜守诚[18]、蒋馥蓁[19]、宋坤[20]、谢聪辉[21]等中外学者从宗教学、民俗学等领域入手,对该信仰的产生背景、思想源流、经典科仪、文书制度、风俗文化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江苏省江阴市、太仓市以及上海市嘉定区都曾有明代墓葬出土与受生寄库信仰有关的实物材料——受生牒,只是还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仅黄景春在其专著中略有涉及[22]。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明墓所出受生牒的形制、性质、内容、所属宗教、牒主身份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等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受生牒实物材料的发现与分布
据我国已公布的考古资料,目前江南地区仅在江苏省江阴市、太仓市以及上海市嘉定区的三座明墓发现过受生牒实物材料。江阴市其行政区划与明代的江阴县相当,当时属常州府管辖。太仓市、上海嘉定区大致与明代的太仓州、嘉定县对应,当时均属苏州府管辖。在多数场合下,明清时期的常州、苏州两府可纳入“江南”这一地理概念予以讨论。以下按受生牒实物材料所出墓葬的年代,由早及晚逐一介绍。
江阴市叶家宕墓地M3出土一件纸质受生牒。M3为竖穴浇浆单室墓。受生牒与衣物疏一起置于墓主尸体的腹部,其上再置一香袋。香袋已朽,原装于袋内的檀香散落在牒、疏之上。受生牒为黄色纸页,折成袋状,宽11.5、高18.5厘米。纸页正中钤方印,再于其上书写牒文。印痕朱文,九叠篆,印文为“寿禄福持之印”。牒文墨书,楷体,五行,内容为:“存日答还受生阳牒二道,计还」受生钱二遍,酬答上项原借冥」钱。伏望」冥官照鉴,庶无沉滞,速判亡」魂生方净界者。」”(图一)袋内还装灰黑色纸灰。衣物疏纸质,疏文曰:“今具……香袋一个,内有信香十六块,受生牒二道。”简报编写者据墓葬、随葬品的形制将M3时代定为明代早期,又据随葬纸质信札,推测墓主乃周溥[23]。
上海嘉定区李新斋(即李汝节)家族墓地M1李汝节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纸质受生牒。该墓也为竖穴浇浆单室墓,时代为万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1581年1月18日)。受生牒置于李汝节妻子程氏尸体的胸部,牒上有一布荷包。荷包两面原有字,文字已漫漶不清。牒为麻色册页,共3页,宽26、高52.5厘米。封面左上角、右下角各有一长方形题记框,框内书写墨书题记。左上角题记为“预修帮库文牒”(“帮库”可能是当地对“寄库”的一种俗称),右下角题记为“给付生身受度信女程氏收执”(图二)。左上角题记框之下、边框之上钤有一朱色方形戳记,文字已漫漶难辨。内页牒文内容为:“庚年五十岁本命戊子宫,七月十九日卯时建。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家启建正一预修寄库道场,凭仙经堂道士沈永忠出给预修寄库受生文牒一道。”末页内容为:“万历五年九月○日,积功成胜天尊,正一教道士沈永忠率领玄众一坛,恭就本县依仁乡十二都 历八都土地界花园山居启建灵宝。”[24]
太仓市黄元会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纸质受生牒。该墓系竖穴单室墓,时代为崇祯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640年1月12日)。受生牒置于黄元会妻子徐氏尸体左手下方。牒为黄皮纸封套,面上书写牒文。牒文墨书,楷体,1行,内容为:“给付诰封恭人徐氏随身受生文牒一道,收执为照。”套内装有一张空白宣纸包叠的纸灰[25]。
上述三件受生牒实物材料出土地点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时间涵盖明早期至晚期。两件受生牒明确出自竖穴浇浆墓,另一件可能也出自竖穴浇浆墓。牒主的性别男女皆有之。
二、受生牒的形制与性质
按照佛道教、民间宗教填还受生寄库法事活动的仪轨科仪,僧人、道士及法师要出给一式两份具有契约性质的文牒,作为缴纳受生钱或预交冥钱的凭证。其中一份随同冥钱一起焚烧上缴冥司库官收领,称之为“阴牒”;另一份交付填还受生寄库者保管,称之为“阳牒”。牒主死后到冥间,执阳牒与库官收领的阴牒相勘合比对,才能领取受生钱或冥钱[26]。
此前学界对于阳牒的使用方法并不十分清楚,这里略作说明。清代至民国时期,不同地区的方志、道教文献显示:牒主生前举行的填还受生寄库法事活动结束时,僧人、道士将阳牒交付牒主本人保管。牒主死后,其家属需再次延请僧人、道士举行法事活动焚化阳牒,阳牒的灰烬随同牒主尸体下葬,以示牒主亡魂可以借此随身携带阳牒进入冥间。下举几例,略示一斑:清同治年间,四川酉阳州(治今重庆酉阳县)僧人、道士为乡村富民举行预修填还受生寄库斋,阴合同于法事活动期间焚化,阳合同则待牒主“既死则请僧道至家,扶尸坐于堂,僧道对之,以锅烧红焙焦阳合同,缝入小布囊,系死者衣襟上,言带赴地下,于库官处以合同校对,则可收取库钱也。”[27]清光绪年间,贵州遵义府(治今贵州遵义市)道士寄库填还受生所用《开库牒》记曰:“阴阳合同文牒二道,阴牒当时随笼焚化,阳牒给付亡人随身收执,于今某日临终之时焚化。”[28]清代,福建宁化县(今福建宁化县)道士开库道场使用的《开库道场疏式》记曰:“已旦夕,当蒙法师某给有合同阴阳文诰二本,□将阴诰随符箓、经财化呈岳﹝司﹞府标题架阁,次留阳诰在身收掌。今已云亡,理宜焚缴付亲魂而执证。”[29]清末至伪满时期,奉天(今辽宁沈阳市)太清宫道士为信士举行填还受生斋时,要给出“受生阴牒”“受生阳牒”各一份,阴牒于法事活动期间焚化,阳牒则由牒主带走,待其死时焚化并随其下葬[30]。民国时期,江西某地道堂“三军堂”寄库填还受生所用《开库牒》对于阴阳牒用法的记载与前引清代遵义府的《开库牒》基本相同[31]。
周溥受生牒自铭为“受生阳牒”,程氏、徐氏受生牒牒文均有“给付某氏收执”的字句,它们应与填还受生法事活动交付牒主的阳牒有关。
周溥、徐氏受生牒形制相同,同为封套型。明清时期,用于封装疏类文书的纸质袋状包装被称为封套、封皮。明嘉靖时期,官员进呈皇帝的密疏即以封套封装[32]。程氏受生牒为册页型,内页、末页出现多个举行填还受生法事活动的时间,应是将代表多次填还受生法事活动的文牒装订成册。
与佛道教文献著录的受生寄库牒书仪文检相比较,这三件受生牒牒文仅寥寥数语,字数要少很多。而现代重庆民间丧礼填还受生仪式所用阳牒牒统(封套),其正面文字主要内容为某人于某时某地建预修填还道场,阳牒给付某人随身收执[33]。程氏受生牒内页、末页牒文接近该牒统前半段文字,徐氏受生牒牒文接近牒统后半段文字。也就是说,程氏、徐氏受生牒牒文接近封套文体。
周溥、徐氏受生牒与阳牒有关,形制同为封套型,内装纸灰,表面牒文与书仪文检不相符,后者牒文接近封套文体。联系到前引清代酉阳州僧人、道士以布囊装阳牒灰烬的做法,这两件受生牒应与布囊的作用相类似,封套内的纸灰是他们生前分别保管的“二道”“一道”阳牒焚化后的遗物,被焚化的阳牒应该是填还受生法事活动交付牒主符合书仪文检格式的原件。推测周溥、徐氏死后,僧人或道士将周、徐二人生前保管的阳牒原件焚化,并把阳牒纸灰装入封套内,封套表面再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注明,随同牒主尸体一起下葬。因此以上两件受生牒实物实际上是内装阳牒原件纸灰的牒套,可视为阳牒原件焚化后的替代品。李汝节夫妇合葬墓内未发现纸灰,但程氏受生牒牒文接近封套文体,这种册页型牒有可能仍为阳牒原件焚化后的替代品。
三、受生牒内容与所属宗教
周溥受生牒“速判亡魂生方净界者”一句似与佛教的净土信仰有关。弘治《江阴县志》记载佛教僧人参与民间丧礼的七七度亡追荐斋包括“还受生”仪式[34]。明清时期,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佛教较之道教的势力要强大很多。乾隆《江阴县志》称当地僧人不下数千人,其中又以应付僧(瑜伽教僧)居多,道士则仅有数十、上百人[35]。因此,周溥受生牒可能是瑜伽教填还受生法事用品。由牒文“存日答还受生阳牒二道,计还受生钱二遍”一句,可知周溥生前两次预修填还受生。瑜伽教科仪书《佛说受生因果宝卷》成书时间不晚于明初,记曰:“传至本人四十以上、五十以下,交生之日,命请僧众善友于家,礼请三宝证盟,依经填还。……在生者三次填还。”[36]依此记载,周溥生前预修填还受生尚欠缺一次,具体原因则不得而知。
另外,周溥受生牒与内装檀香的香袋共出于墓葬内同一位置。据衣物疏疏文,此檀香即“信香”。江西广丰县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郑云梅墓出土两件已朽毁的纸质冥途路引、一件纸质西方公据。同时墓主尸体左手执一券,券尖上书“玉帝”两字,其下左右两侧分书两行字,右为“一片真香朝”,左为“两个环券谒阎君”[37]。张勋燎认为“玉帝”应与“一片真香朝”相联,是道士书写神祇的提行格式[38]。道教授箓仪式授受双方以金环、券契告盟,后来有时将这类传度券契称之为“合同环券”[39]。路引与券契在性质上有一定相似性。因此,墓券券文“两个环券”应指该墓的2件路引。由此券文可推断,周溥墓内“信香”与郑云梅墓的“真香”应是功用相同的物品,是死者灵魂持受生阳牒或路引朝礼冥司官吏时随身携带以示虔诚的物品。
程氏受生牒牒文出现“正一预修寄库道场”“正一教道士”等词语,无疑是道教正一派填还受生斋醮用品。据同墓出土的程氏墓志记载,程氏生于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十九日,卒于万历七年(1579年)。受生牒内页、末页出现三次填还受生斋醮的时间。第一次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一月。这一年程氏33岁。第二次为“庚年五十岁本命戊子宫七月十九日”。以程氏生年推算,她五十岁时应为万历五年(1577年)。《太上老君说五斗金章受生经》要求填还受生应于斋主“本命之日”举行。此次斋醮选择在程氏五十岁生日当天举行,当遵从此经经旨。又依该经,程氏本命为戊子宫,命属中斗十二气,受生本命钱为12万贯,应向冥司第一库完纳。第三次为万历五年九月。如据《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收录的“化受生寄库钱合同牒”[40],此次启建的“灵宝”道场可能是“灵宝生身受度预修黄箓大斋”。预修黄箓斋一般于正斋第二日晚上举行受生醮[41]。而清中叶以来浙江磐安县正一派道坛“树德堂”的火居道士所做的“填还受生给牒醮道场”有多种异名,如“预修填还受生度厄保安道场”“预修填还度厄植福道场”“灵宝预修供王诵经礼忏填库延生道场”等等[42]。显然,单独举行的预修填还受生斋醮也可称之为灵宝道场。徐氏最后一次填还受生可能是预修黄箓斋期间举行的受生醮,也可能是单独举行的预修斋醮。
第一、三次填还受生的组织者均为仙经堂正一派道士沈永忠。仙经堂位于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南翔镇白鹤寺(即南翔寺)以南,宋元时期由王氏祖宅改建而成。明景泰三年(1452年)重修。清乾嘉时期,又增修玄武殿、山门[43]。明清时期,还兼作嘉定县西境的土神祠[44]。民国时,仙经堂占地一亩五分,有房屋16间[45]。清人程天泽作诗称颂仙经堂“何年羽士閟仙经?符箓犹传此最灵”[46]。仙经堂由私宅改建而成,规模较小,道士以符箓见长,还供奉非道教的地方神祇。近代南翔镇道士都是正一派,并不出家,依靠香金及做法事收入为生[47]。明初整饬宗教,将全国汉地僧人分为禅、讲、教三派,道士分为全真、正一二派。瑜伽教僧、正一派道士民间化、世俗化倾向严重。他们活跃于乡土社会,专职为民众提供各类消灾解厄、度亡追荐服务[48]。道士之有家室者,称为“火居道士”。考虑到仙经堂的规模、供奉神祇等情况,沈永忠的身份很有可能是火居道士,平日斋醮活动遵从正一派科仪。
第三次填还受生的地点“花园山居”可能是位于南翔镇的三老园。牒文称花园山居地处“依仁乡十二都历八都土地界”。南翔镇隶属嘉定县的第十二、十三都[49]。牒文“十二都”后缺二字当为“十三”。程氏公公李文邦在镇内开辟了一处园林别业,因园内有三株枫、柏、桂老树,故名三老园[50]。
徐氏受生牒牒文更加简略,无法由牒文判断其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用品。据徐氏棺内所出买地券券文,黄元会、徐氏夫妇二人的丧礼由其子黄锴[51]经办。黄元会平生“喜黄老家言”,好“读道书”[52]。四库馆臣认为黄氏所著《仙愚馆杂帖》一书“多剽掇佛、老浮谈,而于服食修炼尤所笃信”[53]。同时黄元会尸体胸前放置一枚与道教神仙思想有关的明仿汉十二时辰规矩铜镜,而徐氏尸体在相同位置放置一枚属于道教《三皇经》系统的五岳真形符铜镜,具有辟邪压胜的功能[54]。如受到其父信仰道教的家庭氛围影响,黄锴有可能以道教色彩浓厚的铜镜及道教受生牒为父母随葬。因此,徐氏受生牒很有可能是道教用品。
四、受生牒牒主身份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俗
从随葬信札内容来看,周溥属于儒生士子阶层。程氏丈夫李汝节(1526—1576年)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登州府(治今山东蓬莱市)同知[55]。李氏家族世居南直隶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李汝节之父李文邦青年时期举家迁居嘉定县,以经营棉布生意为生[56]。李氏家族的这一支后来成为该县的富绅望族,有“门第子孙之盛,几甲于吴中”[57]、“里中李氏,累世贵盛,文章誉望高天下”[58]之誉。程氏是李汝节的正室,同样出身于歙县的商人家庭,封宜人[59]。徐氏丈夫黄元会(1577—1627年)为万历年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使。徐氏(1579—1633年?)是黄元会的正室,封恭人[60]。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三件受生牒牒主为儒生士子与官员妻室两类人。
儒生士子、官员妻室墓葬内发现受生牒固然与江南士绅阶层流行具有良好密封性的浇浆墓不无关系,但更与江南及周边地区长期以来植根于民间的风俗习惯有着必然联系。南宋天台宗僧人钱塘县(治今浙江杭州市)籍的宗鉴、四明(庆元府,治今浙江宁波市)籍的志磐均声称当时民间流行预修寄库[61],可能源自他们对其生活地域社会现象的切身感受。宋元时期,杭州保俶塔寺每年春季举行大型的受生寄库斋会,出现“公子王孙倾城出,姆携艳女夫挈妇。……居然红裙湿芳草,亦有瑜珥落宿莽”的盛况[62]。南宋时,杭州民间流传一杨姓老妪生前勤于预修寄库死后得到丰厚回报的故事。部分儒士对这一故事持否定态度,称“十王寄库之有无,则不待智者而后知”[63]。明代文献不乏关于受生寄库信仰的记载。南京市雨花台区采集到一方正统元年(1436年)内府内官监太监王景弘地券。券文出现一位作为后土与亡者买卖土地的中间人“两来神”田交佑。田交佑是《灵宝天尊说禄库受生经》所记酉年生人的本命元辰[64]。前引江阴县民间丧礼三七斋要由僧人主持“还受生”。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市)一些妇女流行入庙烧纸锭,称“先是寄之冥司,死得用之”[65],实则是在寺庙里举行预修寄库法事活动。秀水县(治今浙江嘉兴市)居士张守约笃信弥陀净土,所撰《拟寒山诗》嘲讽烧纸钱寄库者为“痴人”[66]。明末莲池大师祩宏生于仁和县(治今浙江杭州市),在杭州云栖寺驻锡四十余年,所撰《正讹集》对迷信寄库的世人予以劝诫[67]。清至民国时期,受生寄库信仰在杭州、乌程县(治今浙江湖州市)、磐安县(今浙江磐安县)、青田县(今浙江青田县)、太仓州(治今江苏太仓市)、川沙县(约今上海浦东新区)、青浦县(今上海青浦区)、宝山县(约今上海宝山区)等地民间仍十分兴盛,民众或生前预修寄库,或丧礼时填还受生,兹不赘述。清道光以来,民间宝卷《洛阳桥宝卷》宣演与受生寄库信仰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在吴方言区,流传甚广,版本众多[68]。
以上所论江南地区明墓出土的三件受生牒是继宋明道三年(1034年)《明道三年福建路建阳县普光院众结寿生第三会劝首弟子施仁永斋牒》[69]之后,保存完好、时代明确、出土背景信息丰富的受生牒实物材料。通过对其形制、性质、内容、所属宗教、牒主身份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推断出它们分属佛道教用品,发现其实际使用形态能够与佛道教、方志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并有所补充,弥补丰富了佛道教文献关于受生寄库法事活动的记载,具有传世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这3件受生牒实物材料为探讨明代江南地区佛道教忏仪和民间丧葬习俗的渗透、交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
(附记:本文得到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彬教授的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亦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衷心的感谢。)
[1]a.佚名:《诸经日诵集要》卷中,《嘉兴大藏经》第1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164—166页;b.佚名:《新编卍续藏经》第8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598—599页。
[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7—337页。
[3]《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第915—916页。
[4]《道藏》第11册,第418—420页。
[5]Hou,Ching-lang,Monnaies d‘offrande et la notion de trésoreie dans la religion chinoise,Mémoires de I’IHEC 1.Collège de France,1975.
[6]Anna Seidel,Buying One's Way to Heaven:The Celestial Treasury in Chinese Religions,History of Religions 17,no.3/4,1978.
[7]〔日〕大渊忍尔:《中国人の宗教礼仪·道教篇》,风响社2005年,第388—396页。
[8]Gates,Hill,Money for the Gods:The Commoditization of the Spirit,Modern China,no.3,1987.
[9]萧登福:《由道佛两教〈受生经〉看民间纸钱寄库思想》,《宗教哲学》第3卷第1期,1997年。
[10]刘长东:《论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与接受——以掠剩神信仰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1]〔日〕丸山宏:《道教仪礼文书の历史的研究》,汲古书院2004年,第323—370页。
[12]〔日〕山田明广:《台湾道教仪式文书之差异——台南与高屏地区的比较》,徐兴庆编《东亚文化交流与经典诠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第287—292页。
[13]侯冲:《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96—425页。
[14]韦兵:《俄藏黑水城文献〈佛说受生经〉录文——兼论十一—十四世纪的受生会与受生寄库信仰》,《西夏学》(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99页。
[15]钟晋兰:《客家乡村的丧葬仪式调查——以宁化县龙虎村的“做香火”为例》,《客家研究辑刊》2011年第2期。
[16]方广锠:《随缘做去直道行之——方广锠序跋杂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41—142页。
[17]张贤明:《融合与吸收:从佛道〈受生经〉看中国树形象演变》,《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8]a.姜守诚:《明清社会的寄库风俗》,《东方论坛》2016年第4期;b.姜守诚:《佛道〈受生经〉的比较研究(上)》,《老子学刊》(第九辑),巴蜀书社2017年,第3—20页;c.姜守诚:《佛道〈受生经〉的比较研究(下)》,《老子学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17年,第33—60页;d.姜守诚:《“寄库”考源》,《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1期;e.姜守诚:《道教寄库醮仪考释》,《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4期。
[19]蒋馥蓁:《道教的“受生填还”仪式:以四川〈广成仪制〉为中心的考察》,《民俗曲艺》2016年第194期。
[20]宋坤:《填还阴债与预寄珍财——古代“受生”“寄库”观念考辨》,《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
[21]谢聪辉:《道坛传承谱系建构的资料与方法研究:以台湾、福建田野调查为例》,《道教学刊》总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90—220页。
[22]黄景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70—571页。
[23]江阴博物馆:《江苏江阴叶家宕明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8期。
[24]a.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14—122、238—239页;b.黄翔:《上海嘉定区李新斋家族墓发掘简报》,《上海文博论丛》2011年第2期。
[25]苏州博物馆考古组等:《苏州太仓县明黄元会夫妇合葬墓》,《考古》1983年第3期。
[26]a.侯冲整理:《受生宝卷》,《藏外佛教文献》(第二编第1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b.明·如德辑:《雅俗通用释门疏式》卷九,三益堂明刊本;c.同[13],第430—431页;d.同[3];e.明·周思得编:《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三六,《藏外道书》第17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77页;f.《吴氏文检·延生库牒》,《庄林续道藏》第19册,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274页。
[27]清·王鳞飞等纂:《(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志》卷十九,《四川府县志辑》第48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765—766页。
[28]作者自藏清抄本《填还申奏牒劄》,出自贵州遵义市,道士苏德真抄录,是寄库填还受生科仪的文检汇编。
[29]作者自藏清抄本《灵宝九幽拔亡斋醮行移》,出自福建宁化县,道士李应灵抄录,是灵宝派度亡斋醮的文检汇编。
[30]〔日〕五十岚贤隆著、郭晓锋等点校:《道教丛林太清宫志》,齐鲁书社2015年,第86—89页。
[31]作者自藏民国抄本《填还写本》,传出自江西抚州市,是寄库填还受生科仪的文检汇编。
[32]明·杨一清著、唐景坤等点校:《杨一清集·密谕录》卷五,中华书局2001年,第995页。
[33]胡天成:《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54页。
[34]明·黄傅等纂:《(弘治)江阴县志》卷七,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35]清·蔡澍等纂:《(乾隆)江阴县志》卷三,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03页。
[36]同[26]a。
[37]秦光杰等:《江西广丰发掘明郑云梅墓》,《考古》1965年第6期。
[38]张勋燎:《江西、四川明墓出土的道教冥途路引之研究》,《中国道教考古》第5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1349—1350页。
[39]a.《道法会元》卷一七七,《道藏》第30册,第140页;b.《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卷下,《道藏》第28册,第521页。
[40]宋·王契真授、元·林灵真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三百十三,《道藏》第8册,第747—750页。
[41]《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道藏》第7册,第33—35页。
[42]徐宏图:《浙江省磐安县树德堂道坛科仪本汇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第41—46页。
[43]a.明·韩浚等纂、何立民点校:《(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8页;b.清·张承先著、清·程攸熙增订、朱瑞熙标点:《(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44]同[43]b卷十、卷十一,第158、191页。
[45]民国·陈传德等纂、徐征伟点校:《(民国)嘉定县续志》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05页。
[46]同[43]b卷十,第157页。
[47]南翔镇志编纂办公室:《南翔镇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5页。
[48]a.《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九,《明实录》第1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109—3110页;b.明·宋宗真等编:《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道藏》第9册,第1页。
[49]明·陈渊等纂、陈兆熊点校:《练川图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50]a.清·吴桓等纂、赵文友点校:《(嘉庆)嘉定县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02页;b.同[43]b卷十一,第163页。
[51]买地券录文“黄错”应为“黄锴”。
[52]a.明·姚希孟撰:《棘门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67—672页;b.清·王昶等纂:《(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二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6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8页。
[53]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14页。
[54]张勋燎:《江苏明墓出土和传世古器物所见的道教五岳真形符与五岳真形图》,《中国道教考古》第6册,第1797—1830页。
[55]a.同[24]a,第114—122页;b.《(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二十八,第468页。
[56]a.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56—457页;b.明·徐学谟撰:《归有园稿》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5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57—558页。
[57]明·程嘉燧撰:《松园偈庵集》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第738页。
[58]同[43]b,卷十二,第194页。
[59]同[24]a,第114—122页。
[60]同[52]。
[61]a.宋·宗鉴集:《释门正统》卷四,《新编卍续藏经》第130册,第808页;b.宋·志磐撰:《佛祖统记》卷三十三、《通例》、《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8年,第129、132、320—321页。
[62]a.宋·吴自牧撰:《梦梁录》卷十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00页;b.元·方回撰:《桐江续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5—486页。
[63]宋·沈某撰:《鬼董》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396页。
[64]祁海宁等:《南京“王景弘地券”的发现与初步认识》,《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
[65]明·陶奭龄撰:《小柴桑喃喃录》卷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制缩微卷,明刻本。
[66]a.明·张守约撰:《拟寒山诗》,《嘉兴大藏经》第33册,第716页;b.清·彭希涑述:《净土圣贤录》卷八,《新编卍续藏经》第135册,第352页。
[67]明·祩宏撰:《莲池大师全集》,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4084—4085页。
[68]a.陆永峰:《民间宝卷的抄写》,《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b.钱铁民:《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21—1522页。
[69]同[13],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