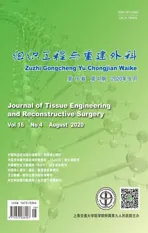载药微球在肿瘤与非肿瘤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2020-01-07罗兰杨希林晓曦
罗兰 杨希 林晓曦
【提要】 近年来,载药微球(Drug-eluting beads,DEB)因其对血管的栓塞作用和释放药物的靶向性而在介入治疗领域广受关注。大量研究证明,载药微球可以延长药物的活性,提高稳定性,维持一定的血药浓度,从而使药物的释放效果更为理想。载药微球发展至今,其种类、性能正不断地丰富并优化。在肿瘤治疗中,载药微球的栓塞化疗已应用于治疗肝、肾、胃肠、乳腺等部位的肿瘤;在非肿瘤疾病的治疗中,载药微球亦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我们相信,载药微球是一个极具前景的研究领域,利用其结合分子靶向药物可能会实现多种疾病的治疗突破。
微型包囊技术(Microcapsulation)简称微囊化,系利用天然的或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囊材)作为囊膜壁壳,将固态或液态药物(囊心体)包裹而成药库型微型胶囊(Microcapsule)。若药物溶解和/或分散在高分子材料基质中,形成骨架型(Matrixtype)的微小球状实体则称微球(Microsphere)。微囊和微球的粒径属微米级,而粒径达纳米级的分别称纳米囊和纳米球,均可以作为给药系统应用于临床。
近年来,微球和微粒作为载体材料在生物医学和生物工程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另外,相关研究使得许多新型给药系统成为了可能。因此,微球/微粒系统中药物的释放和靶向性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微球/微粒以高分子材料作为载体,不仅能够控制药物以一定速率释放而实现长效目的,还能保护药物,尤其是蛋白质、多肽类药物免遭破坏,还有掩盖药物的不良口味、减少给药次数和药物刺激、降低毒副作用等功能。同时,亦可对生物体的生理指标给出反馈,并凭借其生物相容性被器官组织的网状内皮系统所内吞或被细胞融合,使得药物浓集于靶区形成靶向药物释放体系,进一步提高疗效。因此,通过选择合适的高分子包裹和给药途径能够延长药物的生理活性,提高药物的稳定性,维持一定水平的血药浓度,从而使药物的释放达到更为理想的效果,以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
本文将介绍载药微球(Drug-eluting beads,DEB)的起源与发展,并对载药微球在肿瘤治疗与非肿瘤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进行总结与讨论,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参考。
1 起源与发展
1960年,Luessenhop等[1]将甲基丙烯酸甲酯微球应用于颅内动静脉血管畸形患者的治疗中,这是微球在临床上最早的应用。1978年,含抗肿瘤药物的乙基纤维素微球研制成功,首次将药物加载于微球上,实现了化疗与栓塞的结合[2]。
理想化的载药微球应具有以下特点[3-4]。①粒径大小适宜,可通过微导管进行递送,且有多种粒径规格可供临床按具体血供情况的差异进行选择;②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不会引起人体免疫应答或排斥反应;③载体颗粒间不易聚集堵管,给药难度低,且不会黏附聚集于给药装置上;④药物的载量可满足治疗所需的剂量;⑤能以可控的方式在病灶内靶向释放药物,达到并维持局部治疗的有效药物浓度。
为了使载药微球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大量研究从药物的性质、囊材的选择、微球的粒径等不同方面进行设计并付之于实验。囊材上,从天然高分子材料(如明胶、壳聚糖、海藻酸盐、白蛋白等),到半合成高分子材料(如羧甲基纤维素、醋酸纤维素钛酸、乙基纤维素等),再到便于工业化制备的合成高分子材料(如聚酰胺、聚乙烯醇、聚乳酸等)。具体到临床应用上,根据不同的疾病,微球的粒径也可供选择。目前,载药微球主要有生物降解型和非生物降解型两大类。生物降解型囊材的优点在于无毒、成膜性好、化学稳定性高,但是在药物的释放效率上无明显差异[5]。聚酯类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生物降解的合成高分子。临床上应用的一般为非生物降解型载药微球,主要有DC/LC-Beads©(BTG, Biocompatibles UKLT)、HepaSphere©/QuadraSpheres(Merit Medical Systems)、Embozene TANDEM(CeloNova BioSciences)和LifePearl(Terumo)[6],均能够通过离子交换进行药物装载。
1990年,HepaSphere研制成功[7],并被命名为SAP(Superabsorbent Polymer Microsphere),于1992年首次应用于临床,2006年11月被FDA批准用于栓塞治疗。HepaSphere由聚乙烯醇丙烯酸吸水性共聚物组成,是一种生物相容性好、亲水的非生物降解型微球,弹性良好,可压缩直径的80%,水合后直径增大为原来的2~3.5倍,在人血浆中可增大4倍,与血管内皮紧密接触并随行,从而达到完全性栓塞的效果。HepaSphere通过加载正电荷蒽环类化疗药并缓慢释放,有效提高了局部化疗药物浓度,降低外周血药物浓度。干燥状态下规格有30~50 μm、50~100 μm、100~150 μm、150~200 μm等几种。2004年,DC/LC-Beads研制成功,是一种基于聚乙烯醇的微球栓塞剂,由N-丙烯酰胺乙醛衍生物制备而成,利用阴离子磺酸盐通过离子交换机制将带正电荷的蒽环类药物(如多柔比星、阿霉素、伊立替康、吉西他滨等)加载于微球上,用于治疗多种恶性高血管性肿瘤[8]。微球直径主要有70~150 μm、100~300 μm、300~500 μm、500~700 μm、700~900 μm等五种规格,载药量为5~45 mg/mL,在药物释放中保持球形, 患者6个月内可接受3~4次化疗栓塞治疗。
CalliSphere(苏州恒瑞迦俐生生物医药科技公司)[9]是我国生产的第一种微球产品。CalliSphere是一种表面光滑、带有电荷的有色聚乙烯醇栓塞微球,属于国家三类无源植入性医疗器械,易通过微导管,具有良好的弹性,可压缩至50%,可通过细小血管以达到终末栓塞。直径主要有100~300 μm、300~500 μm、500~700 μm、700~900 μm、900~1 200 μm等五种规格。动物实验证明,该微球是一种组织相容性好,无致畸或致癌作用的理想栓塞材料。随后,多项临床研究使用CalliSpheres载药微球成功栓塞治疗多例不可切除肝癌患者。
Du等[10]用新型材料初步研制出的HAMs微球可通过离子交换机制携带多柔比星等药物,动物实验证实了其对肾动脉的栓塞化疗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期待载药微球更大的可能性。
2 载药微球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初,动物实验证明了可降解淀粉微球(DSM)通过栓塞血管治疗肝癌的可能性[11-12]。动脉栓塞术的成功使我们不难想象,微球加载药物后对栓塞治疗疗效的促进或许是巨大的。事实亦是如此。化工产业和介入治疗技术发展至今,针对难以手术治疗的肝脏肿瘤,栓塞化疗这一治疗方式已成为首选。
载药微球之所以广泛应用于肿瘤的栓塞化疗,是因为其具有以下优点。①微球对肿瘤组织毛细血管网的栓塞更为完全,直径小于12 μm的微粒可到达终末毛细血管,直径更大的微粒则会被一级毛细血管网截获,而常用的微球制剂的直径一般在100~900 μm;②微球中药物不断向肿瘤区扩散,使肿瘤区的药物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浓度水平,降低体循环中的药物浓度,故可提高药物的治疗指数。另外,肝脏由于接受门静脉和肝动脉的双重供血(正常肝细胞的血流70%~90%由门静脉供应,而肿瘤组织的血流95%由肝动脉供应),使得栓塞化疗既可以破坏肿瘤细胞,又能尽量减少对正常细胞造成损伤,相较于传统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c-TACE,即使用碘化油与化疗药混合乳液动脉内化疗后进行选择性血管栓塞的治疗方式),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治疗方法。载药微球介入的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DEB-TACE)相较于c-TACE可以显著减少化疗药物到达全身循环所需的剂量,同时还能显著减少化疗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13]。
1989年,Yoshikawa等[14]利用可降解淀粉微球和局部热疗联合化疗栓塞治疗不能切除的肝癌,结果发现,DSM栓塞化疗与动脉内灌注化疗具有几乎相同的适应证,提示DSM栓塞化疗是治疗不能切除的肝癌的一种有效方法。随后,Yamamoto等[15]对45例不能切除的肝癌患者进行射频容性热疗联合动脉化疗或化疗栓塞治疗,其中22例患者分别接受了一次性和持续的抗肿瘤药物灌注,11例患者接受了碘油化疗栓塞,其余12例患者接受了可降解淀粉化疗栓塞微球(DSM)。结果显示,患者生存时间延长,且无明显严重副反应。另外,DSM对血流的抑制作用非常敏感,是与肝癌热疗相结合的极佳栓塞剂。
相较于c-TACE,载药微球介入的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由于可以提高肿瘤栓塞部位的药物浓度,并降低外周血的药物浓度,因此,术后肝外不良反应(如发热、乏力、恶心、脱发等)发生率较低。多篇荟萃分析综合比较了DEB-TACE和c-TACE的疗效。Huang等[16](7项研究,n=700)以及Xie等[17](6项研究,n=652)证明了DEB-TACE的客观疗效明显优于c-TACE。2016年对9项研究(866名患者)进行的另一项荟萃分析中,尽管与c-TACE相比,DEB-TACE的客观疗效相似,但其完全缓解率和总生存率显著提高[18]。Chen等[19]对1 832例患者(DEB- TACE:n=822,c-TACE:n=1 010)进行分析,结果表明DEB-TACE治疗显著改善1年、2年和3年总生存率,且1年、2年无复发生存率。另外,DEB-TACE术后常见不良反应(如发热、 乏力、腹痛、恶心、脱发、骨髓抑制等)发生率亦低于c-TACE。
临床上,除了肝癌以外,载药微球的栓塞化疗也已应用于治疗胃肠、泌尿系、乳腺、脾脏、肺脏等部位的肿瘤,大量研究表明,载药微球可促进肿瘤组织的坏死、缩小甚至消失。
Okamoto等[20]使用选择性动脉内灌注丝裂霉素C(MMC-mc)微球对20例患者进行了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治疗,靶点为肾、肝、前列腺、膀胱、子宫、乙状结肠、道格拉斯腔和骨,发现14例患者可测量的最大肿瘤直径减少30%以上,5例减少10%~30%,1例减少10%,所有患者在治疗初期均有症状体征的改善,8例肾癌、膀胱癌、宫颈癌患者术后疗效显著且全身毒性反应轻微。结果表明,MMC-mc化疗栓塞术是一种有效的术前或姑息性治疗方法。Kramer等[21]用人血清蛋白将柔红霉素盐酸盐与巯基嘌呤制备出磁性微球,并试用于治疗胃肠肿瘤,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载药微球在非肿瘤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Luessenhop等[1]用微球成功治疗颅内动静脉血管畸形,使得微球栓塞这一方式给许多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思路。而具有栓塞效果与药物治疗作用的载药微球,不仅在肿瘤治疗中成为研究热点,在非肿瘤疾病的治疗研究中也开始崭露头角。
1996年,Beaujeux等[22]首次使用栓塞微球(Embosphere)成功治疗了面部、脊髓和颅内动静脉畸形的病例。Keigo等[23]对25例有症状的面部(n=5)、上肢(n=8)和下肢(n=12)动静脉畸形患者采用SAP-MS颗粒(丙烯酸钠和乙烯醇共聚物)经动脉栓塞治疗(TAE)。对联合外科手术干预获得的标本进行组织学分析,并对临床结果进行回顾性评估。结果显示,20例患者(80%)通过单纯栓塞治疗(n=17)或联合手术(n=3),症状改善。经TAE治疗后,采用手术切除或截除的方法完全切除1例唇部及2例指动静脉畸形。弥漫性上肢(n=1)和下肢(n=1)AVMs的症状不受控制。SAP-MS颗粒治疗TAE后无神经损伤和皮肤坏死。组织学上,SAP-MS颗粒穿透损伤内血管,并顺应血管腔而导致血管闭塞。由此证明,微球经动脉栓塞治疗对某些症状性AVMs是合适的,但弥漫型、浸润型AVMs的治疗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动静脉畸形研究领域目前的主要瓶颈在于:一方面,无水乙醇被广泛有效地用于治疗低流量畸形(静脉和淋巴管),而对于高流量动静脉畸形,并发症发生率高达10%,包括短暂的神经性发作和皮肤损伤;另一方面,单纯的物理栓塞剂治疗动静脉畸形通常效果不佳,术后复发率超过90%。因此,在复杂的、难治的血管畸形相关疾病治疗领域,亟需寻找一种安全有效、精准靶向的创新治疗方式。Jubeli等[24]开发了一种聚合物基材料作为栓塞剂和药物贮存器,材料由线性丙烯酸酯共聚物的乙醇溶液和载有抗血管生成剂舒尼替尼的纳米球组成,并用兔角膜新生血管模型体内评价其抗血管生成活性,且在绵羊模型上测试了动脉栓塞的效果。结果成功证明了这种新的血管栓塞系统与抗血管生成药物原位给药相结合的可行性,是一种极具前景的治疗动静脉畸形和高血管化实体瘤的方法。
除了动静脉畸形等血管畸形相关疾病,多项临床研究表明微球还可用于前列腺增生、症状性子宫肌瘤、出血性疾病(例如咯血、胆源性出血)等疾病的治疗。
微球介导的前列腺栓塞术是利用微导管将栓塞微球注入前列腺中,籍由阻塞前列腺动脉使肥大的前列腺组织缺血萎缩,从而达到减少前列腺体积及减少尿路阻塞的目的。Hwang等[25]分别用非球形聚乙烯醇颗粒与微球对9例有下尿路症状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前列腺动脉栓塞术以比较疗效。其中,4例患者使用了非球形聚乙烯醇颗粒(250~355 μm)进行栓塞,5例患者则使用微球(300~500 μm)。结果这9例患者的动脉造影显示双侧前列腺动脉均成功栓塞。与非球形聚乙烯醇颗粒组相比,微球组患者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生活质量、前列腺体积(总体积和过渡区)和最大尿流量均有较大改善。栓塞术前和术后随访的经直肠超声图像显示,PAE术后相较于术前,前列腺体积明显缩小。因此,微球介入的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是一种可行、有效、安全的治疗有下尿路症状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方法。
在其他疾病领域,Ge等[26]为探讨栓塞微球对子宫肌瘤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的影响,收治育龄妇女子宫壁内肌瘤128例行栓塞术治疗,同时随机抽取128例健康育龄妇女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VEGF水平,采用免疫组化方法研究VEGF在子宫肌瘤中的表达。结果显示,患者组血清VEGF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与治疗前相比,患者组治疗后3个月子宫肌瘤直径明显缩小,治疗6个月后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和月经血容量显著增加。这一结果表明,与子宫切除术相比,栓塞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有望成为替代子宫切除术的理想选择。程钢等[27]将72例患者分为两组:一组行支气管动脉双栓塞,双栓塞组先用明胶海绵微球(0.5 mm×0.5 mm)、红霉素和高渗氯化钠混合液栓塞终末血管,再用明胶海绵颗粒(1 mm×1 mm)栓塞支气管动脉主干;另一组行单次明胶海绵栓塞。经2~4.8年随访,治愈率双栓塞组83%,单次明胶海绵栓塞组61%,两组治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从而证明微球介入的支气管动脉双栓塞术对咯血患者有明显的远期疗效。另外,Horák等[28]利用聚甲基丙烯酸羟乙基酯(PHEMA)颗粒,对18例胆源性出血患者进行了选择性肝动脉分支PHEMA颗粒栓塞。这种低创伤的方法可以完全控制出血,或者至少可以减少两倍以上的术中失血。对闭塞血管的组织学研究表明,血栓附着在颗粒上,并由聚合物的多孔结构加固。栓塞后出现高凝反应,因此可以纠正止血系统中的低凝状态。
4 总结与展望
不同于肿瘤领域,载药微球在非肿瘤疾病治疗领域的应用较少,因为多数非肿瘤疾病已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和治疗体系,大多数疾病的诊疗指南已可满足医患的主要需求,而载药微球介入治疗这一创新治疗操作要求高,基础研究少,治疗造成的并发症难以预料。事实上,多项研究表明,载药微球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有着强大的作用。虽然目前将载药微球与更多药物进行结合的设想大多处于动物实验阶段,但实验结果显示出的积极结论,揭示了载药微球栓塞方面的新方向,也为许多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同时,也有研究探索联合多种治疗方式的综合治疗手段在临床中的应用,近年研究已证实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联合栓塞治疗可使中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获益,提示DEB-TACE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可以扩展到更晚期的肝癌[29],说明了载药微球结合分子靶向药物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在非肿瘤疾病如血管畸形相关疾病领域中,载药微球这一新兴治疗方式所带来的靶向物理栓塞作用与药物打击作用的联合效益令人期待,如能突破目前常规手段存在的治疗瓶颈,则开创一种安全有效、精准靶向的治疗方式也成为了可能。
载药微球栓塞技术在国内应用较晚,只有短短数年的时间。关于微球的使用规范和操作规程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同时在临床治疗中,应尽量发挥载药微球的优势,减少治疗过程中并发症的发生,有些并发症是致死性的。这一新技术若应用得当,实现精确的靶向性(Targeted)、良好的吸收性(Absorbing)、灵活的调节性(Customized)、真正的载药性(Eluting),并合理应用,经导管介入的化疗栓塞治疗领域必将取得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