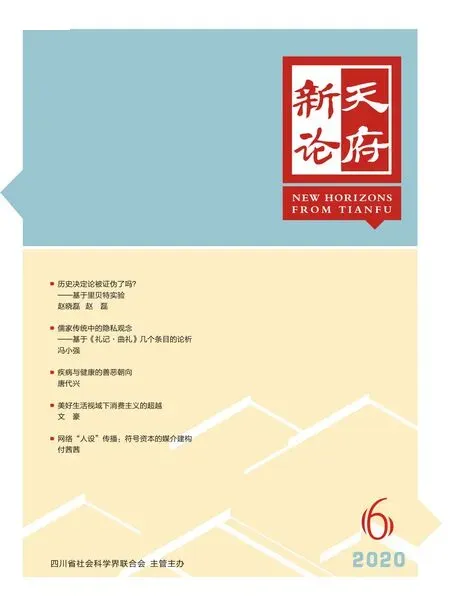走向诠释的社会学理论
——从“地方性知识”谈起
2020-01-07邓钦文
邓钦文 向 帅
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1)《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参见Http://www.godcom.net/hhb/.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
一、法律: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地方知识”
1983年,为了对《文化的阐释》中所提及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明晰,克利福德·格尔茨出版了《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一书。作为一位拒绝选择唯物或唯心立场,也拒绝接受实在或实证标签(2)纳日碧力戈:《格尔茨文化解释的解释》,见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6年,“代译序”,第iv页。的作者,格尔茨将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集中在“文化诠释”处。在格尔茨眼中,人类社会呈现出多种样态,而对其进行理解的方式则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格尔茨认为,若把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些事件看作自然事实,它就会被视作单纯出于情感冲动的行为,而将其视作文化事实时,则其或许可以被称作社会结构“最完美的形式”。(3)以格尔茨笔下的巴厘岛斗鸡事件为例,这一独具特色的事件为当地的政府所不容,当地政府视其为“原始、倒退、不进步的行为”来加以严格禁止,但当作者“身在其中”(in)后,发现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周边参与,斗鸡行为都含有内涵丰富的隐喻和自成体系的社会结构运作模式。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巴厘岛的斗鸡行为根本无法禁绝。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84-528页。但对事件的深描并不容易,首先要求人们抛弃既有的看法,放弃作为一个看客从外部去理解所观察到的事件。若非如此,观察者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无法理解”——将在事件中的行动者视作为白痴、野蛮人等非理性的人——的境地。为了避免此种倾向,研究者当然要进入事件之中,进入行动者的群体中,“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无法独自行动”(4)维特根斯坦语,转引自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要想进入群体当中,自然需要和群体中的人打交道,而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其行为的动机、手段、目的正逐渐呈现。当我们可以完整地、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去描述一事件时,对“理解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中第一重意义上的“理解”便做到了,这种理解要求研究者在不削弱群体自身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其常态。在这一层面上,格尔茨要做的事是清晰明确地将人类学研究的事业以一种经验的方式展开,他回避了普遍哲学式的呈现方式,转而投入一个社会文化的语境当中,把“特定类型的现象放在能够引发回响的联系之中”(5)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页,第261页。。而这,就是“地方知识”。
《地方知识》一书从开篇到结束,大多以直白的行文对当下的普遍主题进行了反思。其中,许多词语被严格限定在一个较之“人类社会”来说更小的范围:“从土著的观点”、“一种文化”、“反思”和“比较视角”。这些谨慎的措辞似乎将这本人类学研究文集变成了一篇篇“民族志”般的文章。但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为了能够让读者真真切切地抛开前见,进入作者为我们构建的语境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跳出自身狭隘的想象,并把目光投往更深的地方。
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曾对法律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人,稳定,恒常……对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时代,它是唯一的法律,永恒的、不变的法律。”(6)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可见,法律在其诞生之初,便已被刻下“普遍性”的印记。同样,在概念法学派那里,法律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概念衍生、组合而成,最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层层叠叠”的法律,亦能覆盖住所有人的所有行为。法律,作为一种人类理性的产物,自然地适用于所有人类。
格尔茨却并不这么认为,“和航海、园艺、政治和诗学一样,法律与民族志都是地方性的技艺:他们都凭借地方知识来运作。”(7)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页,第261页。格尔茨对这种近乎“离经叛道”式的论断当然也有疑虑,因此他将范围牢牢地限制在了“事实”之上,并强调其不是在呼吁把法律的意义关注到社会习俗之中,也并非要以人类学的发现来纠正司法推理。他例举了巴厘岛上的一位居民Regreg的遭遇来说明一些对的、现代的、高明的理念、概念、规定会在某些既有环境中遇上完全无法施行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证明法律,特别是司法领域中的法律事实没有跳出“人为造成”的范畴、真实存在着的法律和法律事实也绝非是结构严谨的凭空想象(8)按照格尔茨的话来说,法律都是“对真实加以想象的独特方式之一部分”,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71页、第288页。,格尔茨对伊斯兰的哈克(haqq)、印度教的达玛(dharma)、马来人的阿达特(adat)三个概念进行了考察。最终,格尔茨得出了结论:法律是地方知识,而非不受地方局限的通则;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建设性的而非反映性的,或者说不仅仅是反映性的。(9)该处的原文为:law is local knowledge not placeless principle and that it is constructive of social life not reflective, or anyway not just reflective。此处结合了邓正来版和杨德睿版的翻译。如果法律只能在一个精心设计好的社会中运行,那未免过于荒谬。
为何格尔茨如此肯定法律甚至于文化都是一种地方知识呢?这当然不是盲目的直观经验所致。若将视野从法律扩大至“社会”这一概念当中,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则要从社会理论的起源和转变谈起。
二、传统社会学二元叙事模式
(一)“人”与“社会”的分离
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经有“人”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下的人往往隐藏于“社会”的背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polis)乃是一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赋予人以身份,城邦由其公民组成,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同时,城邦被认为是自然的产物,只有居住于其中、参与城邦政治生活,被城邦赋予“德性”之人才可被称为“人”。城邦是“最崇高、最权威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追求至善的共同体”(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第4页。,在此种意义上,人是“属于城邦的人”,城邦本身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个鄙夫”(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第4页。。不论是超人还是鄙夫,都不能被称作一个“人”。在古希腊,并没有自然人这种说法,更不存在所谓抽象意义上的人,人依附于城邦而存在,其自身内涵是混沌的。
人作为一种依附性存在的看法,在17世纪的笛卡尔处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笛卡尔哲学的第一条原理即是:我想,所以我是(存在)(12)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页,第27页。。笛卡尔从认识论入手,由于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感官所蒙蔽,所以他抛弃了所有感性认识;甚至为了防止我们的认识被各种先在或后至的想法困扰,就连“我”的思想也一并抛弃。如此一来,所有的认识都可以被拿来抛弃——检验,唯一剩下的就只有“我想怀疑其他事物的真实性”(13)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页,第27页。是确实存在着的。“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既然这种思想没有脱离“我”的思考,其必然需要依附于一个存在着的“我”。尽管“我”的形体可以被怀疑甚至是不存在,但作为理性的“我”却是可以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而存在着的。
至此,笛卡尔的理性个人主义下的“人”通过其形而上学展现了出来,“人”作为一个认识主体,不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就可以独立地存在。既然人的理性就可以证明人的存在,那么人就不必、更是不能再隐藏于城邦、宗教、团体之下,其作为一个理性的观察者,自然可以主动地去考察、研究“于我之外”的事物,去发现真理。
笛卡尔此番思考的目的是为了给科学研究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外在的经验需要经过理性的涤荡才能被称为真理。而其背后隐含着的二元论思想也在此时呼之欲出——人类不是被动地接受着世界,而是可以主动地对世界施为,既然“社会”是于“我”之外的东西,那么人们也可以对社会进行考察。
(二)惊奇——对“社会”概念的觉醒
既然人可以对社会进行考察,我们就仍需思考,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思考何者为社会?难道人们对“社会”这一概念的研究是偶然得之?若真是如此,社会研究就不应开始,或者早早就已经陷入了停滞。
彼得·伯格提出,大惊奇(big surprise)是人们对社会的重要感觉之一。他以幼年时期的经历在记忆中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来佐证作为一种“惊奇感”的经验是我们对社会产生认识时的第一种感觉。(14)Peter L. Berger& Brigitte Berger,Sociolog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6,pp.14-15.对“社会”的这种感觉或许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维柯对启蒙运动时的“理性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他在承认经验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 “惊奇感”是人类认识的重要动因。“惊奇是无知的女儿,惊奇的对象愈大,惊奇也就变得愈大。”(15)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15页。因为惊奇感的存在,原本无知的人类对认识的对象产生了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则驱使着他们对对象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而知识,就产生在这一过程当中。维柯引入对神话时代的描写,远古祖先把天上的雷电视为神灵,把现在的世界看作“大洪水”之后的产物,原始人类则区分为“巨人”和“教化民族”。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诗和神学的起源。(16)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12页、第117-119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也许会发现这部分内容的背后竟隐含着一种神圣意味,亦因这种神圣感的存在,人们才意欲探索这个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世界。而当“神圣感”投向作为群体存在的人类自身时,“社会”——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存在——其雏形也就慢慢地显现了出来。
这种实在的、有形体的社会在涂尔干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原始部落时期,每个部族都会有自己的图腾。这种在器具和形体上对图腾表现的狂热追求,是为了确保其宗教生活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有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并激起后者心中的神圣感,社会同时有其自身的目的,并通过人来协助其目的的实现。有趣的是,尽管这种社会将人本身的兴趣置之不顾且要求人成为其“仆从”,但在人们心中,社会仍然是他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人在面对社会时的态度是心悦诚服而非反抗,其中的原因正是社会有着强大的道德权威,它是一个受到尊崇的对象。社会对人有一种力,这种力能够“自动地引发或抑制我们的行为,而不计行为的任何利弊后果”,这种力源于人在面对社会时的神圣感,并激发了人心中的尊崇之情。(17)E.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第278页。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道德实体,将人们笼罩于其中,它的神圣性给人以近似迷狂的感觉并借以宗教的形式所展现,也因为有这种令人着迷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团结。(18)团结的原因兼有内外两种因素,作为道德实体的社会对人的命令(如图腾、仪式)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激发了尊崇感的力同样贯通在人的内心,并成为了人“存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涂尔干以集会为例说明: “我们在集会上变得抑郁冲动,情绪激昂,而这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所难以维系的。等到集会解散,我们发现自己重又孑然一身,回落到平常状态,我们就能体会出我们曾经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了。” 参见E.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
更进一步说,社会并非形而上的玄思,“社会事实”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由团体的信仰、倾向和习俗等构成,能够对个人的行为方式加以约束,并通过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固有存在。为了更有力地证明社会是一种“实在”,涂尔干采取了科学的立场,强调“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19)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5页。。抛弃了会导致不确定倾向的心理因素,尽管社会事实可能会展现为个人的想法、能力和行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社会”。
(三)社会结构——对“社会”概念的进一步考察
涂尔干的社会研究暗含着一条信息:“人”与“社会”不是混沌一体,二者有着鲜明的视域分野。笛卡尔已为人与社会奠定了二元对彰的哲学基础,涂尔干的研究则更使人们能够大胆地去探索“社会”的奥秘。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主张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社会。源自语言学的“结构”概念自其诞生之初就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而经过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宣言后的社会学研究正好需要一种抛弃个体情感的理论来对其进行指导。因此,“结构”的概念成了支撑社会学研究内容的基础性概念。(20)叶启政:《行动-结构的困境》,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75页、第176页。向结构转向的社会学研究将注意力着眼在系统(system)的社会表现形式上,这一观点普遍认为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类似,是由诸因素(要素)组成的一个巨大整体,如经济、法律、伦理等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对要素的考察也必须将之放入社会的整体之中,不能将它们单独拆解。同时,各个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乃客观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构成了社会秩序。而社会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透过社会表象,发现社会的构成要素及其因果关系,并将其结构方式向大众加以呈现。以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例。其将行动系统拆分为行为的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四个子系统,其中的社会系统又可以拆分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共同体这四个部分,而用来对行动系统的各部分进行整合的则是系统的四个功能:适应功能、目标实现功能、整合功能与文化维持功能,此即帕森斯著名的“AGIL模型”。帕森斯认为,正是由于行动的“功能-系统”的结构存在,人们才能够在一个社群中进行行动并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人的行为作出预期和协调。(21)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毋庸置疑,帕森斯的社会结构模型是相当精巧的。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设计了一套囊括人类社会所有行动者的理论,甚至将其放置在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进程当中,“宏大理论”在帕森斯处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包括帕森斯在内的所有结构主义社会学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过于看重社会结构的作用以至于处在社会下的人们仿佛不存在自己的意志,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受社会控制的看似自愿行为。自中世纪开始就备受关注和强调的自由意志居然在结构社会学处遭到了取消,而且这种根源于实用主义、强调经验的可证性立场的社会理论居然否定了经验在认识上的优先地位。(22)这种理论中的矛盾性是隐晦却深刻的。倘若人是在社会结构中被塑造,那么就无法回答人们本身在做选择时那种充满了自主与自信的意志,正是这些源于“意志”的行为,才又给予行动者以新的认识。同时,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例行之事”(routine),这种例行之事是严格的理性选择之产物,正是因为人的理性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会做出相似的选择,稳定的社会结构才得以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根源于其实际上是意志为实现自身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是“意志”的外在显化,那么它又如何能对意志加以控制和塑造呢?这或许也能够解释成一个韦伯问题:人们在追寻这个世界的意义的过程当中丢失了意义。因此,“社会结构”理论实际上无法应对和解释社会现实当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现象。由于缺乏对现实的回应能力,此般理论也只能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丧失生命力,最终止步于教科书当中。(23)关于对帕森斯的这类评价,可见于乔治·瑞泽尔:《古典社会学理论》(第6版),王建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叶启政:《行动-结构的困境》,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社会学研究开始强调社会的反身性(reflection)、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以及个人行为自由的偶然性和社会客观环境形成的偶然性等概念,通过增加差异的因素、强调人类意识的能动作用来激活社会结构的活力、消解“社会”之于人类而言的优先地位。这种类型的社会学理论相较于其前辈来说显得更加温和也更具灵活性,人类摆脱了社会“巨灵”的控制,转而以一种心理建构的方式来与外界共同建构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社会结构”变成了“结构下的社会”。这种社会理论有以下几个命题:一是就一个结构而言,其仍然表现出系统的特征,组成它的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动;二是就处于结构之中的模型而言,任何一个模型都隶属于一组变化,其中每一种变化都可以再对应另一个模型,并且这些变化终将组建成为一组模型;三是无论模型的要素如何改变,处于结构当中的模型变化都是可以被预测的,并且被建构出来的模型能够解释人类社会可以被观察到的全部事实。(24)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组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结构下的社会”理论承认了现实社会变动不居的特性,“结构”是存在于社会之上的动态建构,它欣然接受作为要素的人类意识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观点——这使其克服了“社会结构”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僵化”问题和令人悲观的情感基调。
但问题并未就此得到解决。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结构下的社会”,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一个存在于人自身之外的“巨物”——这在社会结构理论处是作为“理性存在”的社会,在结构下的社会处则直接显示为“理性”、“意识”、“无意识”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人们并没有真正从“二元对立”的场景中走出来,甚至从未逃离出缺乏意志和情感的“理性”的掌控。更为致命的是,当这些社会理论遇到其未曾接触过的社会形态时,它们绝大多数将后者贬斥为“原始的”、“落后的”、“程度较低的”社会。这种极具“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无疑有极大的不公正,而其中暗含的欲将人类社会同质化的倾向则更应被警惕。
本应作为主体的人类却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文明的愈发繁荣而表现出不可遏止的客体化倾向,社会理论甚或人类群体正面临着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危机。
三、走向诠释的社会学理论
面对“客观化”的倾向,后现代主义者喊出了“人文性已死”(the death of humanity)的口号。诚然,若一个人要对外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主体,其方法是求助于某种具体的社会外在表现时,二元式的社会学理论又怎能彰显人的高贵性和独特性?
(一)结构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困境
“将自身的存在求诸外在表现”的方法体现出鲜明的结构(特别是语言结构)色彩,而造成的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主客二分的二元叙事模式带来的根源性矛盾外,还在于人们认识自身与社会的方法论。传统社会学所强调的那种抛弃无法被实证的个人情感与个人倾向的研究使其成果只能呈现为纷杂多样的现象,若想对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现象进行加工,抛弃了个人立场的社会学理论也只有重新诉诸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实体,它可以是“社会”、“结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当社会学研究走到这一步时,科学的实证主张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垄断了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专断地规定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手段得出的人文研究之结果才是能被认可的。或许是源于过往研究在经验上的有效性,人们不曾对其提出质疑。但如今,陷入僵局的社会学或许已经发展到了需要寻找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另一条出路了:抛弃实证主义的模式,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断裂开来,前者不再是什么居于人文科学之上的研究范式,“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特殊地方,也不存在一个阿基米德点,在那里可以生产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的知识”(25)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导言第23页,第14页。。
(二)从认识论转向的诠释学
诞生于经典文本解释的诠释学研究在狄尔泰处进入了精神领域,“理解”不单是对追求文本客观性与确定性所作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把握人心理的世界。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诠释学在狄尔泰处被赋予了与自然科学相比拟的地位。除了对自然物的“说明”与精神的“理解”作出区分外,狄尔泰同时强调,由于人表现了自己生存的符号,所以人与人之间并非完全陌生,通过对符号的理解可以达到对人之精神的理解。
在确立了“理解”的诠释学方法后,诠释学的认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历史文本的记载确实超出于个人之外,但是构成其内容和基础的却是“经验”。这种经验是人的活动,是“生命的历史过程,它的范例不是固定的事实,而是那种使回忆和期待成为一个整体的奇特组合。”(26)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这一观点消弭了历史与个人之间那条原本不可逾越的界限。对历史进行理解则需要回归自身,自我的不断展现又成为了历史组成的一部分。既然历史不再是客观的外在自然物,人与历史都处于互构的过程当中,二者通过这般方式展现自身,诠释学也从认识论过渡到了存在论。
至此,诠释学不再是作为探明客观、正确的历史内容的方法,而旨在对人文科学建构之基础的存在进行说明。“那个存在者,即仅仅通过理解而生存的存在着的存在模式是什么”(27)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导言第23页,第14页。,转向存在论的诠释学对存在论基础的探讨是在存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进行的,因而主体问题在诠释学中也不再是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了,相反,它击垮了认识主体将自身视作客观尺度的自命不凡。“理解”的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它不再拘泥于发现文本或者理解他人,理解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去揭露由现象所指示的存在可能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理解”开放出了无限的可能。
(三)诠释学向社会学的扩张
既然诠释学已经从关于文本的解释转向对存在的理解,那么其能够覆盖的领域必然超出了原有的范围。既然诠释学已经完成了从文本到精神领域的迁移,其向着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进发也似乎是应有之义。
为了证明这种“扩张”的正当性,对一组概念的研究是关键,即“文本模型”和“有意义行为”的互通。毫无疑问,文本自诠释学诞生之初就是后者最为经典的关注对象,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行为——这一社会科学最为关注的对象——理解成文本模型,则决定了诠释学理论运用在社会科学上的可能与边界。
诠释学沟通“文本”与“行为”的方法是巧妙的,它并没有生硬地把这一组概念进行牵连,二者的联系依靠的是作为中间节点的“事件”。“事件”概念最先与语言学相关联,由于“言语”和“语言”的区分,“事件”表现为“当人们说话语时所产生的事”。(28)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3页。因此,事件即具备了言语那种当下的、暂时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当“我”在说话时,“我”的言语必然指向了另一个人,一个在当下进行交流的人。因此,在对话中,说话者的意向通过言语传达给另一个人,又因为倾听者与说话者处在同一时空中而共享话语所需要的场景,从而使言语的意义能够在二者之间流转并且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也就是说,在言语当中,意向和意义是交杂在一起的,他们通过对话传达给对方。但也正因其意向和意义的杂糅,言语只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时空与情景中进行理解并实现有效沟通,这些转瞬即逝的“事件”当然远远无法满足人类进行稳定交流的需求。因此,“言语”就必须成为“语言”,“意义”也要超越“事件”。
语言与言语的区别是显著的。与带有强烈个人倾向的言语不同,语言更像是一种“社会结晶”,“它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29)语言源于言语活动,但其自身具有鲜明的特性:其一,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是个人以外的东西;其二,语言较言语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也使得“语言”可以为人们所研究;其三,语言具有同质性,它表现为一种符号系统,系统的内部组合形成了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四,语言的形成虽然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很大的关联,但当语言形成之时,其就成了个人之外的东西。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37页。。语言有固定的模式,其编码、解码方式皆依循一定的准则。正因为这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已成为在我们经验当中的深刻烙印的语言所具有的确定性,当我们符合于某一语言的要求时,我们所说的内容才能被理解,意义才能被洞悉。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的说话方式与语言规则相符合,那么我们想表达的内容即可超越时空的限制、超越共同情景的要求来传达给对方。因此,语言从言语中脱出,并不再拘泥于对话的形式。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意义”超越了“事件”而获得了其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正因如此,意义可以进入文本当中,并向读者开放。
除了可以将“言语”视作“事件”外,“行为”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传达意义的行为由行动者做出而传达给接收人——这同样也是一个在同一时间、杂糅了意向和意义于其中的“事件”——而对行为中蕴含着的意义的理解也只有与行动者处于同一时空、共享情境的接收者才能理解。但无论行为表现为何种形式,总有一套基于经验而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当中通行的行为模式,也正因这种模式的存在,人们才能够对行为进行理解、预测,才能够共享某一行为的意义。(30)将行为与言语进行比较分析的另一进路体现在保罗·利科将文本标准应用于行为的论述中。在利科笔下,由于行为与言语存在结构上的相似,“行为具有以言表意行为的结构,它拥有某种可以被认同和再认同为同一的命题内容”,所以行为意义可以与行为事件相分离。“行为自身——即作为有意义的行为——可以成为科学的对象。”参见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5-171页。既然“言语”由于进入了书写的文本中从而消除了其作为对话的“事件”之特性,那么,倘若我们把“行为”也视作文本的话,“行为”作为一种“互动的事件”,其欲表达的意义也就超越了行为自身。因此,对行为的理解就如同对文本的理解一样,二者都被囊括进了诠释学的任务当中。
(四)走向诠释的社会学
正如言语被记录而固定在文本中一样,行为被铭刻下来后就融入了历史当中。因此,诠释学对行为的理解必将涉及对历史的解释。
对历史进行何种解释,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论上的问题。这种通常看来并无甚问题的主客二分观念到了诠释学处却显得并没有那么简单。伽达默尔在谈论主体与存在之时提到了“游戏”的概念。他认为,尽管游戏者知道自己是在进行着游戏,但是只有游戏者专注于游戏之时,游戏本身的意义才能显现,“谁不严肃地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31)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第136页,第141页。因为游戏的存在方式不允许参与者像对待客体对象一样随意地对待游戏——参与游戏必须专注——游戏者就必须投入游戏的过程中去。在此过程中,游戏的魅力体现在它对游戏者的吸引上,游戏者遵从游戏的秩序以使游戏继续进行,“游戏超越游戏而成为主宰”(32)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第136页,第141页。,一种“被动式而含有主动性”的游戏意义在游戏的过程中体现了出来,游戏也就超越了游戏者而成为主体。同时,在游戏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游戏以自我表现(Selbstdarstellung)的方式存在着,这种表现指向了游戏的观赏者。观赏者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所以他们是“最真实感受游戏”的人,游戏的意义也更容易对他们展现。“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33)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第136页,第141页。通过这种方式,游戏将观赏者也囊括进其自身当中,当观赏者在理解游戏意义的时候,他们和游戏者的区别就从根本上被取消了:游戏者进入游戏当中,通过游戏活动展现游戏意义;观赏者处于游戏之外,通过游戏者的行为来感受、理解游戏。二者共同以游戏的意义内容去意指(meinen)游戏本身,而游戏本身也正是在这进行和被观察之中构建起了自身的存在。
通过对游戏概念的理解,诠释学取消了认识论中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二元对立的基本关系,从而消弭了二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巨大鸿沟。更重要的是,这种源于存在论的诠释学基本立场中暗含着“平等”的思想:当我们面对某一事物并企图理解它时,我们要放弃自视为主体的自大,转而以平等且温和的态度去面对它们,并以期获得对后者的理解。也正因持有这种拒绝理性认识主体的预设,诠释学才能摆脱自命不凡的认知主体将自己视为客观性之尺度的理论困境,也才能从理解中开放出更多的可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社会视作一个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巨型“游戏”,处在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人兼具玩家和观赏者的双重身份。过往的社会学研究者们常常站在一个客观观察者位置,意图从外部观察社会,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发现和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来寻找社会的意义之所在。如前文所述,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其结果却与当初预期相去甚远。因此,走向诠释的社会学在面对人类社会时不妨进行这样一种尝试:坦然面对人类在其生存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进入社会生活当中、亲历纷杂的社会现象,将所欲求的意义问题化之为一个又一个的理解。
当问题进入对社会的“理解”时,诠释学同样能够对其给出答案。在对事物进行理解时,诠释学摒弃了所谓“绝对客观”的立场,它在承认前见对认识有着塑形作用的同时将后者视作为一种基础,这种看法有助于摆脱“诠释学循环”所带来的恶性效果,“决定性的事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一循环”(3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9页。。这种存在论上的诠释学循环要求人们回到事情本身。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更重要的不是捕捉某个意欲追求的对象之幽灵,而是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学会在对象中
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实现自己和他者的统一。(35)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第385页。
关于围绕视域(Horizont)概念展开的研究能更好地说明这种统一过程。在伽达默尔笔下,与人类认识紧密相关的视域不再仅仅是一个为前见所控制的僵化界限,它作为一种“处境”,更关涉人们作出判断的最基本能力。也正因视域的双重性特征,它要求我们在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检验我们的前见,如此一来, “现在的”视域就在不断的形成过程中实现了于“我”的统一。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同样是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面对社会时,我们的过往经验往往决定了自身对社会的第一感觉、最先的认识,而当我们在对社会进一步探寻与解析当中,只有在承认社会的真实和多样性的前提下才能不断地检视我们的经验,并形成新的认识。对“社会”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形成了于“我”的统一,这种理解超出了“我”个人的狭隘,承认了其他差异性理解的多样性,并且一同与其他的理解向着更高层次的意义之可能开放出去。(36)这种“良性的”诠释学循环在保罗·利科处或被转化成了说明与理解的关系问题。“从理解到说明”旨在表达一种解释较其他解释具有竞争性的优先地位,从而它比其他众多的解释更为优越,因此解释具有了确定性。“从说明到理解”则表明人类意欲追寻的对象其解释不是封闭的,我们能够从中开放出众多的解释可能,并因之释放出“有活力的意义”。这二者的沟通形成了一个良性的诠释学循环,而这亦是诠释学“不可逾越的知识结构”。参见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明安、张剑、李西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第183页。
四、结 语
承认经验的有限性意味着正确认识到人类生存的真实状况,这种认识能够消除我们自视为主体的那种狂妄自大。同时,正因内容不尽相同的有限经验投射至多样的社会,才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经验与社会理论。就社会理论而言,或许正如叶启政提到的,当下的社会理论或许应当另寻哲学基础,甚至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要开始寻找另一条探索路径的地步。(37)叶启政:《观念巴别塔——当代社会学的迷思》,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25页。诠释学正好给出了这样一种探索的方式。“关于理解的理解”从来都承认多样性,其中蕴含着的平等意味更是反对且着力破除任何“中心主义”的立场与理论。对社会的诠释迫使解释者们不断地回到出发点去检视自己的立场和前提,通过持续性的反思脱去欲使其理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魅力。走向诠释的社会学不再奢望能够就一套理论、一种方法来回答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它以更为包容的态度面对经验世界的多样性。旨在探索他者独特经验的诠释学无疑能够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开启一条新的道路,从而丰富“关于人类普遍经验的认识”(38)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3页。。正是在这种“启发”的过程当中,社会的意义随之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