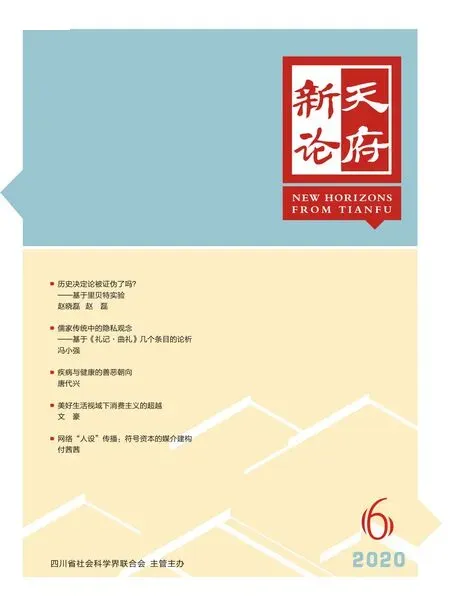历史决定论被证伪了吗?
——基于里贝特实验
2020-01-07赵晓磊
赵晓磊 赵 磊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中,历史究竟是“决定”的,抑或是“非决定”的?这个问题始终都是历史观当中争论不休的基本命题,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所在。(1)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历史决定论上的分歧,笔者将另文讨论,此处不展开。换言之,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见证了不同历史观的此消彼长。迄今为止,有关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与历史非决定论(historical indeterminism)的争论,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精神决定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精神决定论,即认为人类历史是由超越历史的某种精神(上帝或神秘的理念)决定的。(2)因果决定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因果决定论。因果决定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上的机械决定论——拉普拉斯决定论是其典型,也称之为“拉普拉斯之妖”(2)拉普拉斯之妖(Démon de Laplace),是指由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于1814年提出的一个科学假设。拉普拉斯假设: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宇宙中某一刻所有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自然构成的物件的位置,那么就能够使用牛顿的力学定律来推测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科学地说明过去以及未来。;另一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辩证决定论。(3)历史非决定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史决定论被日益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所否定,历史非决定论从此成为历史观的主流。
在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争论中,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分歧:如何看待人的自由意志?关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以及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由此引发的哲学思考源远流长。众所周知,作为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者,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 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指出: “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现实性的反思形式。关于他,亚里士多德说过,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页,第205页。同样为人们熟知的伊壁鸠鲁(Epikurs,公元前 314年—公元前270年),作为典型的历史非决定论者,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被学界公认为西方第一个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则是自由意志论的代表人物。正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说: “从历史上看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 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并且每个人都以激烈的论战方式驳斥相反的观点。”(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页,第205页。值得注意的是,伊壁鸠鲁正是通过强调偶然性、自由意志以及原子偏斜运动的方式来为历史非决定论辩护的。至于自由意志究竟何以可能,伊壁鸠鲁以及他的信徒都没有给出明确和系统的说明。(5)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根据俞吾金先生的考证,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 第一个对自由意志问题做出了系统的思考,他把人的自由意志看作是上帝赐予人的一种选择权利。(6)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人道主义的广泛传播,理性呼唤并确认了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开始冲破上帝(神性)的束缚。但尽管如此,自由意志的“自由”始终是有着束缚的自由。比如,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区分了“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并给出了自由意志的存在空间。(7)在康德看来,自然因果性受到外来原因影响,所以是“他律”的;而自由因果性是由理性独立地起作用的,所以是“自律”的。既然是“自律”的,那么自由意志就有它自己存在的空间。然而,康德并没有把自由理解为意志的任意性,而是理解为意志对道德法则的无条件服从。参见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是先验的,但它并非随心所欲的,因为自由意志的基础是道德法则。康德由此框定了自由意志的范围,即“理性为自由立法”。值得注意的是,18—19世纪的伟大哲学家,比如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自由意志并不能随心所欲,而且都是在必然性的前提下来把握自由意志的,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8)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由意志的作用,但他始终将这种作用严格限制在历史必然性给定的范围之内。(9)唯物史观并不否定人的自由。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观完全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自由观。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绝不是随心所欲的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论主体的意志如何自由,这种自由依然都是“被决定”的。换言之,“社会意识”所展现出来的自由归根结底是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参见赵磊:《自由六问——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不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来看,还是从《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来看,马克思属于历史决定论者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马克思对此有明确无误的阐述)。
在20世纪以前,确认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资格主要来自哲学与历史学,即把自由意志定义为:或是上帝赐予的选择权利,或是人类对必然性的认识能力。总之,不论自由意志是上帝赐予的,还是锁定在必然性中的认识能力,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始终摆脱不了某种宏观力量(上帝或者必然性)的支配。直到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发展起来以后,随着“波粒二象性”和“不确定性原理”为历史非决定论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依据,自由意志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推崇自由意志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试图在拒斥因果关系(必然性)之后,为历史非决定论提供量子力学的科学根据。(10)比如,张华夏否定历史决定论的理论依据,就来自量子力学(张华夏:《决定论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用俞吾金先生的话说:“毋庸置疑,‘测不准原理’为当代非决定论的兴起及相应的新思维方式的流行奠定了理论基础。”(11)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不仅颠覆了自然科学的传统认识,而且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以至于历史非决定论几近成为今天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通识。比如,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明确宣布,自己坚持历史非决定论的立场,并将历史决定论等同于白日做梦。再比如,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宣称:没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12)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关系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概括而言,历史非决定论的根据主要源自两个理论:一是滥觞于人道主义高扬的人的主体性,它从理性上确认了个人的自由意志(13)“非决定论” 解释宇宙中所有现象的逻辑是:要么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来解释自然界,要么从人的自由意志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所以,人们通常也把历史领域中的“非决定论”称为“自由意志论”(theory of freewill)。;二是滥觞于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与“不确定原理”,它从微观世界的性质上拒绝了历史决定论。大致说来,现代以前是历史决定论盛行的时代(14)虽然历史决定论都承认历史必然性,但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对于“必然性”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农业社会把历史决定的主体归结为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秘的精神,而工业社会把历史决定的主体归结为内生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现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则是历史非决定论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那么,历史决定论是否真的被当代科学的发展颠覆了呢?关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是否颠覆了历史决定论,笔者另有专文分析(15)赵晓磊,赵磊:《“不确定性原理”何以被误导?》,《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此处不赘述。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即便当代科学为历史非决定论提供了量子力学的实证依据,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当代科学也为历史决定论提供了神经科学的实证依据。换言之,断言当代科学已经证伪了历史决定论,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遗憾的是,量子力学提供的实证依据在社会科学界早已家喻户晓,可是神经科学提供的实证依据在社会科学界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神经科学的实验做一些介绍和评论。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里贝特实验;第三部分,讨论科学实验的意义;第四部分,分析自由意志的主客观依据;第五部分,结语。
二、里贝特实验
否定历史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人的行为要受到自由意志的支配或影响。自由意志对必然性的消解作用,一直都是学界拒绝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理由。所谓自由意志,通常是指人们在多种行为变换的可能性中做出自我选择的能力。如果人们具有自我选择的能力,则可以认定存在着自由意志。(16)自由意志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独立于先前的心理和生理条件的、非决定论的自由意志,二是指在多种行为变换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的一种能力机制,三是指独立于外部限制却依赖于行动者内部动机和目标的、自我决定论的自由意志。参见刘毅:《自由意志概念的演变及其含义辨析》,《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虽然自由意志被认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禀性,但是晚近以来的神经科学实验却对自由意志的存在提出了挑战。随着现代神经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大脑的实证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科学家通过实验装置确切地发现,大脑神经的反应先于有意识的意志。其中,最为著名的实验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里贝特(B. Libet,1916—2007)的神经科学实验,即“里贝特实验”。
传统的观点坚信,自由意志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神经科学看来,如果自由意志真的存在,那么,一个人在其大脑的“准备电位”(17)指大脑的运动区域的预备活动,即readiness potential, 简称 RP。之前或者开始之时,他就应该出现有意识的意志(conscious will)。这个有意识的意志就是命令或决定人们做出实际行动的根据。因此,如果神经科学能够在实验上证明有意识的意志早于“准备电位”开始的时间,那么,自由意志的存在就得到了确认。反之,如果有意识的意志是紧随“准备电位”之后才产生的,那么,自由意志是否真的存在,就是一个问题。因此,确认有意识的意志的时间与大脑的准备电位开始的时间,进而回答人类有意识的意图是否能够决定人的实际行为,就成为里贝特实验的任务和目的。令人惊讶的是,里贝特实验的结果显示,大脑神经系统的反应先于有意识的意志出现。这个结论的冲击力在于,它是基于科学实验基础之上得出来的结论,而且这一实验结论还在以不同的方式被重复。换言之,在所谓的自由意志作出决定之前,人的行为选择其实已被决定了。因此,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幻觉。对于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观感觉的人而言,这个结论是难以被接受的。
其实,早在里贝特实验之前的1965 年,德国神经学家汉斯·赫尔穆特·科恩胡博(Hans Helmut Kornhuber) 和吕德尔·迪克(Lüder Deecke) 对脑电活动的实验观察就已经发现,大脑神经活动的启动明显先于有意识的自由意志活动。他们的实验结论是:人的意志活动不是自主的,而是由无意识的脑活动引起的。科恩胡博和迪克的实验结果并不支持自由意志存在的观点,因而直接挑战了人们的日常直觉。在这之后,美国心理学家本杰明·里贝特在1982年所做的实验(里贝特实验),进一步明确提供了能够证伪自由意志的实证依据。里贝特认为,科恩胡博和迪克的实验要求被试者通过按下按钮的方式来确定产生自愿行动出现的时间,可是这种按下按钮的自愿行动会影响对自愿行动出现时间的精确测试。所以,必须设计一种更加精确的实验方式来优化科恩胡博和迪克的实验。这个优化的实验就是著名的“里贝特实验”。(18)有关里贝特实验的内容,笔者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肖根牛:《里贝特实验的解读与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3期;李恒威,李恒熙:《论里贝特的有意识心智场(CMF)理论》,《哲学分析》2013年第4期;董蕊,等:《自由意志:实证心理学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11期;亓奎言:《自由意志的神经基础》,《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5期。
里贝特实验的内容大致如下:实验要求被试者随意移动一根手指, 同时将手指的肌电反应和前额叶的脑电反应记录下来。被试者的任务是在每次移动手指时, 报告自己体验到“想要移动”意图时相应的光点(时间)位置。被试者面前放置了一个类似于钟表的示波器,示波器的屏幕呈圆形,屏幕上有一个光点顺时针运动。屏幕边缘刻有刻度, 刻度之间的时间差为 107毫秒。当被试者出现有意识的行动意图时(比如想要移动一根手指),要求他注意时钟上此时对应的时间,并在实验结束后报告这一时间。在另外一种状况下,当被试者确实做出弯曲手腕的运动时,要求他向实验者报告屏幕上钟的位置,从而确定他做出这个运动的时间。通过计算机的触发器,实验者将被试者大脑最开始的“准备电位”记录下来。里贝特对9个人进行了40次测试,得到的结果惊人的相似:被试者报告的行为意图先于行动约204毫秒, 而准备电位又先于行动约535毫秒。这说明,在被试者知觉到行动之前的300毫秒左右, 大脑就已经产生了准备行为的电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测试的误差,里贝特认为,应该让被试者在对实验内容毫不知情的背景下进行测试,以免被试者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或暗示。经过反复测试,里贝特发现,无论被试者是否知道实验内容,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惊人的一致:(1)自由的自愿行动(freely voluntary act)发生之前,被试者的大脑有一个明确的电变化,即“准备电位”,它开始于行动之前的550毫秒;(2)被试者在准备电位开始之后的350—400毫秒,但在实际行动之前的200毫秒,觉知到了行动的意图;(3)人的意欲过程(volitional process)是无意识启动或无意识生成的;(4)有意识的功能仍然可能控制行动的输出,它有可能否决这个行动。由此可见,人类行动主观意图的出现,比大脑无意识的活动滞后约500毫秒左右,比实际的动作发生提前约200毫秒左右。对于这个实验结果,里贝特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导致一个自愿动作的过程是在有意识的动作意志出现以前由脑无意识启动的。这暗示:自由意志——如果它存在——不会启动一个自愿动作。”(19)本杰明·里贝特:《心智时间: 意识中的时间因素》,李恒熙、李恒威、罗慧衣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三、科学实验的意义
里贝特实验确认了科恩胡博等人之前的实验结果。其科学含义是:在人的自由意志做出决定之前,其实大脑已经无意识地做出了决定。对于人的行为选择而言,只有生理层面的“无意识”决定,才是真正做出具有因果关系的、实质性的决定。因此,人们所意识到的“自我决定”或“自由意志”其实只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事后理性化”的幻觉。如此而已。
里贝特实验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它不仅给心理学和法学造成了巨大冲击,而且相当程度上颠覆了自我认知的经验常识,从根本上动摇了强调自由意志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于每个人的主观体验而言,自由意志恰恰是自我存在的根据,否定了自由意志,也就否定了自我,所以,里贝特实验的结论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也就不奇怪了。比如,在2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心理学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被问询者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中。而跨文化研究则显示, 来自美国、中国香港、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成人均倾向于拒绝“世界是被决定的假设”。(20)董蕊,等:《自由意志:实证心理学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11期。
很多学者,尤其是哲学家,并不认可里贝特实验的结论。其中,最典型的批评是指责里贝特把自由意志归结为“物理现象”而不是“心智现象”(“意识活动”)。比如,鲍曼斯特以弹奏钢琴为例,批评里贝特实验缺乏对意识活动的领悟。鲍曼斯特认为,里贝特实验就如同要求某人展示他的钢琴水平,但是又不能发出声音,最后只能通过观察他的动作先后顺序和测量钢琴发出的声波,来推断琴声是否由钢琴键所决定。(21)Roy F.Baumeister, “Understanding Free Will and Consciousness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in Psychology,”Free Will and Consciousness,edited by Roy F.Baumeister and Alfred R.Me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31.所以有学者批评:“里贝特的神经学实验只是呈现了自由意志发生的一个方面而已,并不能由此来推断自由意志的发生是否由在先的神经活动引起的。”(22)肖根牛:《里贝特实验的解读与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3期。还有学者批评说:“神经科学的脑成像技术是建立在可观察的数据基础之上的,无须也无法表述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所以仍然需要解释从经验的‘是’到规范的‘应该’的必要性。”(23)马兰:《自由意志是虚幻的吗? ——神经科学的视角与哲学反思》,《江汉学术》2014年第6期。对于里贝特实验的结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可以证明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 而哲学家却强烈要求科学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结论。(24)Smith, K., Taking aim at free will, Nature, 2011,p.477,pp.23-25.
尽管对里贝特实验的批评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遗憾的是,这些批评的依据大都只是逻辑上的论证(25)比如,有学者从规范性的逻辑推导出自由意志的必要性:“意识的功能之一就是把这种概念化的内容或者信号呈现给行动者,让行动者在出现行动意图之前就对行动的对象有某种理解,这种理解一定是处于推论的规范网络之中,因为无论意识所提供的理解还是意志所做的反应,都处于推论的网络之中,而且都表达了一种推论承诺,意识的理解形成了信念,它是一种理论推论,是对掌握相关信息和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推论结果,而意志的反应表达的是一种实践推论,它是以信念的承诺为前提”(肖根牛:《里贝特实验的解读与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3期)。,而缺乏实证的检验。问题在于,科学的结论不仅仅要有理性的逻辑推导,还要有实证的客观验证。不论自由意志是怎样支配“心智现象”的,它都不可能是一个悬置了“物理现象”的纯意识过程。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表明,意识现象能够离开人脑而存在。(26)颅内生理学的观察证明,只有与脑中适当的神经活动相关时,有意识体验才会出现(李恒威,李恒熙:《论里贝特的有意识心智场(CMF)理论》,《哲学分析》2013年第4期)。正如神经科学家所言:“理性”和“意识”也是由大脑皮层“决定”的,所以并不存在“彻底无(神经层面)原因的自由”。(27)包利民,孙仲:《人学新科技群、历史决定论与中道自由》,《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1期。换言之,自由意志并不是一个可以免于经验实证检验的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人们可以从逻辑上拒绝历史决定论,但却不能无视里贝特实验对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否决性检验。人们可以指责里贝特实验只是刻画了“物理现象”,忽略了“心智现象”。但是,这种指责若要有说服力,就必须为“心智现象”提供实证检验,而不能仅仅给出“心智现象”的哲学思辨或“意识活动”的逻辑猜想。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来自各方面的对里贝特的批评,神经科学家在里贝特实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比如,凯勒(Keller)的测试结果发现,无论是在某种自然状态下(或在无意识运动状态下),还是在里贝特所做的实验状态下,两者的准备电位时间基本一致,都是在有意识的意志反应之前0.5秒的时候开始的。美国神经科学家哈迦德和艾莫尔(Haggard and Eimer) 在1999年重新做了一次类似于里贝特的实验,尽管该实验对准备电位的过程与 W(有意识行动意图)的出现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有疑问(28)有关的实验发现,有意识的意志可能有充足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执行行动的意图。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意志有否决的能力或“自我控制”能力,尚需进一步研究(肖根牛:《里贝特实验的解读与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3期)。,但也发现了与里贝特类似的结论,即准备电位出现的时间早于有意识的意志出现的时间。不久前,神经科学家松、布拉斯、海因策和海恩斯等人(Soon, Brass,Heinze & Haynes)改进了里贝特的实验任务, 并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对被试者进行了全脑扫描。结果发现, 被试者做出的行动决定要比真实的行动提前约1秒, 而在被试者做出行动决定10秒左右的时候, 他们的额极皮层(frontopolar cortex)和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两个区域便产生了与决策有关的脑活动。这说明,无意识的脑活动要先于被试者产生决策意识长达10秒之久。换言之,在有意识的决策之前,额极皮层和顶叶皮层就已经在开始编码信息并做出选择了。这个实验有力地巩固了里贝特实验做出的结论。再如,简纳罗德(M. Jeannerod)把里贝特的实验扩展到更复杂的行为中去(比如让被试者画素描)。他由此得出以下结论:自由意志是一种事后现象(post hoc phenomenon)。换言之,自由意志是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巧合产生出来的一种幻觉,并由此建构起来的一种因果叙述。(29)亓奎言:《自由意志的神经基础》,《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5期。总之,神经科学的各种实验不过是重复验证了里贝特的结论而已。
四、美丽的错觉
尽管神经科学的实验不断证伪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但是人们仍然难以接受这些实验的结论。大量研究表明,人们之所以坚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对自由意志有着强烈的主观感受,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相信自由意志存在的个体,会对其心理功能产生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对自由意志的态度会影响个人的幸福感、身心健康、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对待生活的情绪。比如,倘若伴侣关系之间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那么双方都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关系稳定性和幸福感。(30)Knee,C.R.,C.Lonsbary,A.Canevello and H.Patrick,“Self-Determination and Conflict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89,No.6,2006,pp.997-1009.总之,“个体感到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是有用的,而不必从理智上明白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即使是否认自由意志存在的心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31)刘毅:《当代心理学观照下的自由意志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基于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发现决定论是正确的而否定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存在,我们仍然应该让人们继续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32)刘毅:《当代心理学观照下的自由意志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比如,史密兰斯基提出的自由意志“幻觉论”强调,大多数人以为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问题是澄清这些幻觉会导致消极的个人情绪和社会后果,因此,那些知道自由意志并不存在的人,应当为他人着想而保持沉默。(33)Smilansky,S.,“Free Will,Fundamental Dualism,and the Centrality of Illusion,”in R. H. Kane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Free Wil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489-505.
其实,坚信自由意志的存在不仅具有自我感觉的主观依据,而且也有着人脑功能的客观依据。在一项研究分裂脑部手术的病人所产生的后遗症的实验中,认知神经科学家加扎尼加(Mo Gazzaniga )发现:“我们的大脑是按照‘我们’的指令工作,而不是其他方式”,所以大脑必须对造成的“错误的自我”负责。(34)Gazzaniga M. S., The mind’s pas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p.56,p.56.因为,正是大脑的机制促使人们相信,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有自我意识的根据和理由。依据“人脑分左右大脑半球来处理外在信息”这个事实,加扎尼加做了如下实验:把一堆图片摆放在一名脑部分裂的病人面前(这些图片是这个病人曾经看见过的场景),加扎尼加要求被试者指出哪一张图片和他之前看到的图片相配。实验发现,当被试者的右手指着一张鸡的图片时(这张图片与左半脑之前看到的鸡爪有关),被试者的左手却指着一张铲子的图片(这张图片与右半脑所看到的雪景有关)。当加扎尼加要求这个脑部分裂的被试者解释自己的矛盾反应时,他并不是回答:“我不清楚为什么我的左手会指铲子”,相反,他的左半脑立即编出并说出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鸡爪配鸡,所以你需要一把铲子来清理鸡舍。”(35)Gazzaniga M. S., The mind’s pas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p.56,p.56.加扎尼加认为,左脑的语言中枢是大脑的诠释模块,它的作用就是针对自我所做的一切行为而给出理由和评价,即使它根本无从得知“自我行为”的真正原因或动机,也还是会及时做出反应。(36)马兰:《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年第5期。
这个实验的科学含义在于,即使神经科学已经揭示出自由意志可能并不存在,但在人们正常的脑功能中,仍然会固执地存在着强烈的自由意志的感觉。换言之,即使神经科学的实验已经证伪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也很难说服人们消除自由意志的幻觉。因为,人脑的结构具有某种促使我们相信自由意志“是有效的”机制。(37)比如Wegner 认为,意志是一种体验, 而非原因。他就此提出了“表面上的心理因果关系理论” (theory of apparent mental causation):当人们将自己的意向(thought)解释为他们行动(action)的原因时, 人们就体验到了自由意志(conscious will)。参见董蕊,等:《自由意志:实证心理学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11期。对此,有学者充满悲剧色彩地说:“即使我们对自由意志和自我的信仰缺少可信的科学支持,也有理由不允许神经科学来决定人们对于自由意志和自我的信仰。”(38)马兰:《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年第5期。在很多学者看来,自由意志是个人的自主性和尊严的前提,如果人们不相信自由意志, 认为自己的性格和行为是被预先决定的, 那么,可能就会丧失对生活的控制感, 甚至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所以,自由意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39)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Vohs, K. D., Lambert, N. M., Fincham, F. D. & Brewer, L. E., “Personal philosophy and personnel achievement: Belief in free will predicts better job performance,” Social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1,No.1,2010,pp.43-50.此外,人们之所以难以接受历史决定论,还有一个基于道德或法律的原因:倘若自由意志并不存在,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呢?换言之,如果人们的自由意志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那么,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所做的或想做的事负有责任,并予以谴责、赞扬、奖赏或惩罚, 还有什么意义呢?(40)参见徐向东:《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我们认为,即使科学实验证伪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就不再需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违反既定的公序良俗甚至违法行为负责。正如卡恩所说:“如果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由已知或未知的、能确保其发生的前提条件引起的又如何呢?在那种情况下,似乎没有人在精神上应对其行为负责。但没有人应在精神上对其行为负责,并不意味着人不应该在法律上对其行为负责。正如当一只疯狗威胁到我们,就必须把它从我们中带走以确保我们的安全一样,威胁我们的人也应该从我们当中带走,以确保我们的安全。即使疯狗不能在精神上为其行为负责,把它们隔离开来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同样,即使心理不正常的人不能在精神上为其行为负责,把他们隔离开来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此,即使处在一个没有人能在精神上为其行为负责的世界里,我们还会有法律制度、法庭、罪犯和监狱。”(41)斯蒂芬·M. 卡恩: 《人有自由意志吗?》,时光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1999年第4期。所以,尽管自由意志可能是一种错觉, 那也是一种有益的错觉。换言之,即使自由意志是一个谎言,它也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五、结 语
自从20世纪20年代“不确定性原理”在学界滥觞以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否定历史决定论的思潮已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时代主流。然而,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互联网、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虚拟现实、脑机接口等为代表的前沿性科技的发展,为历史决定论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和实验依据。这些前沿性的科学依据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最新人学科技群”为历史决定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42)比如:其一,人工智能的研究表明,日益普及化的人工智能,其运行机制是被既定的程序所决定的,这个事实为决定论提供了人工智能的理论依据;其二,新的演化理论表明,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必须服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这个事实为决定论提供了演化过程的理论依据;其三,来自Wegner 的意志错误归因研究、Bargh的无意识启动研究以及 Baumeister 的自我损耗研究等行为实验的结果,同样支持了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的假设(包利民,孙仲:《人学新科技群、历史决定论与中道自由》,《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1期;董蕊,等:《自由意志:实证心理学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11期)。,二是神经科学的实验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在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争论中,虽然参加讨论的学者涉及了哲学、神学、物理学、法学、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但是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从实证的角度而言,只有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和实验,才能为相关争论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科学证据。换言之,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与其说是一个思辨哲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证科学问题。正是由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为证伪自由意志提供了大量的实验依据,以至于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对自由意志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哲学、法学或者物理学,而是来自心理学。(43)Tait,G.,“Free Will,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ADH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Vol.7,No.4,2003,pp.429-446.
其实,心理科学一直有着否定自由意志的传统。早期的心理学有着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比如美国的行为主义物质决定论。在行为主义阵营里,无论是华生、赫尔,还是托尔曼,这些行为主义学者都否认人类行为的目的自决性,强调物质和环境因素是驱动人的行为的唯一决定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并不赞同把心理和行为原因归结为由某种外在的物质性力量所驱使,但他仍然否定行为的意识自决性,强调“精神能”(力比多)对于人的决定意义,从而成为纯粹的精神决定论的领军人物。无论是物质决定论还是精神决定论,这一类行为主义心理学都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行为决策的目的性和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心理学虽然反对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决定论,但却强调人类行为总是被社会关系、话语体系和文化历史决定着的,所以骨子里依然是决定论者。在后现代心理学者看来,虽然心灵、自我并非某种“精神实体”,或者像现代心理学者所宣称的那样,呈现出某些“稳定的结构、倾向或特质”,但它们本身仍是一种社会的、话语的建构。进化心理学虽然拒绝现代心理学有关外源或内源的决定论逻辑,但仍然认为人的行为是被进化机制所决定的,而决定人的行为的进化机制则来源于人类祖先的遗传性或选择性。不过,进化心理学有意识地与遗传决定论划清了界限,主张人的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比起现代心理学而言,进化心理学对决定论的态度似乎并没有那么鲜明。真正为自由意志辩护的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但即便如此,积极心理学仍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决定论倾向。与人本主义心理学过于强调自由意志不同,积极心理学在主张自由意志的同时,也强调了人的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所以,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相比,积极心理学只是温和的自由意志论。(44)况志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基于心理学视角》,《心理学探新》2008年第3期。
比起其他领域的学者而言,为什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专业人士更倾向于接受历史决定论呢?受过神经科学和现代心理学教育的学者之所以比非专业人士更容易接受历史决定论,其知识结构上的原因在于,神经科学和现代心理学在以下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人格和行为不过是外界环境与先天遗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心理现象不过是人脑的功能展现,再高级的心理活动最终都决定于人脑。比如神经科学家法拉赫(Mo Farah)认为,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所有的行为百分之百由脑的功能决定,脑功能是由基因和经验的相互作用决定的。”(45)转引自马兰:《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年第5期。精神病学专家唐克雷迪(Lo Tancredi)声称:“我们的道德观念随着对神经科学的理解而改变,在神经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将来人们的观点会有更多的改变,减弱人们对自由意志的相信。”(46)转引自马兰:《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年第5期。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即使是那些有自由意志倾向的学者,可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决定论。”(47)刘毅:《当代心理学观照下的自由意志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在我们看来,神经科学的里贝特实验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神经科学并没有把自由意志当作哲学或神学问题来讨论,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并努力通过实证检验来给予解决。在科学的语境中,未经验证的理论至多也只是某种信念或信念系统而已——不论这些信念是多么符合人们的常识。正如里贝特所说:“我的态度始终如一:永远别太在乎那些思辨的、未验证的理论。”(48)B. Libet, Mind Time: Th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虽然里贝特实验并没有为否定自由意志提供终极判决,但是,里贝特实验的价值就在于:它对那些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判决提供了相反的实证检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非决定论”者以现代物理学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现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是“决定论”的信仰者。在《大设计》一书中谈到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时,霍金说:“事实上,它也是所有现代科学的基础,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则。”(49)蒙洛迪诺,霍金:《大设计》,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22页。如此评价“决定论”出自对现代物理学和量子力学有着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