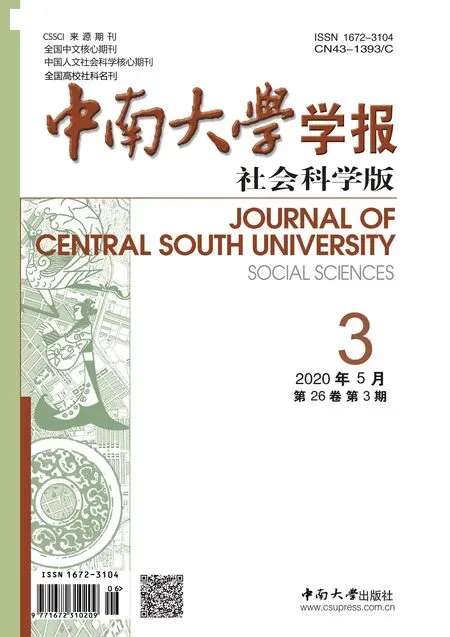艺术体制论源流新释
——从贡布里希到阿瑟·丹托与乔治·迪基
2020-01-06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一、艺术体制论的主流看法及其问题
艺术体制论被认为是当下最具有阐释力的艺术观点①。无论欧美还是国内,在主流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叙事中,阿瑟·丹托是艺术界理论的代表人物,受他启发的乔治·迪基则是艺术体制论的创建者②。沃特伯格、斯蒂芬·戴维斯、马克·西门尼斯等欧美学者一致将艺术体制论看作是乔治·迪基独创的理论成果③。“所谓的‘艺术体制’的提出被公认为是迪基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例如《美学百科全书》便为之专设条目。”[1]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大辞典》认为,迪基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提出独创的‘习俗论’(institutional theory)”[2](567)。彭锋也认为,丹托1964年发表的《艺术界》“阐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界理论”,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迪基就致力于建构他的艺术体制理论,用艺术界来界定艺术,可以说是当代艺术理论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给艺术下定义的先驱者”[3]。作为一种艺术定义,艺术体制论的确是由美学家丹托和迪基发展而来的。不过,更全面地看,将丹托、迪基视作艺术体制论的奠基人和创建者的观点却值得商榷。率先结合语言学、社会学致力于思考现成品艺术提出的理论难题,系统阐释艺术体制论或艺术习俗论的,既不是丹托也不是迪基,而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他才是被忽视的当代艺术体制论的奠基者。
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证,“institution”的拉丁语词源“statuere”意指建立、创设、安排。到16世纪中叶,“institution”的普遍含义是指用某种方法确立的惯例(practices),因此它与“convention、custom”(惯例、习俗)语义相通④。至20世纪,“institution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词,用来表示一个社会中任何有组织的机制”[4](242−243)。可见此词含义复杂,可译为制度、机制、机构,且兼有惯例、习俗之意。艺术总是特定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的产物,可以说,自有艺术起就有艺术体制。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艺术体制有不同的面貌和存在方式。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以教会为主体的艺术赞助制度到18世纪已逐步转化为致力于吸引批评家注意、招徕顾客的艺术展览制度。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艺术体制论才进入西方主流学界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缺乏对艺术体制的洞见和思考。18世纪之前的“古典时期”暂且不论,当时“现代艺术体系”尚未确立⑤。19世纪,马克思已经将艺术品视为一种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精神生产,丹纳则提出了考察艺术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因素论。20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学派、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探索也包含着关于艺术体制的丰富思考。不过,整体而言,20世纪中叶之前,艺术研究的核心是表象与形式问题,艺术体制问题尚未凸显,相关理论思考相对而言也缺少自觉性和系统性。“只有当先锋派艺术挑战了规范、毫无美感可言的时候,外部体制才被暴露出来。”[5]20世纪中叶之后,艺术生产的体制问题才逐渐得到普遍重视和系统讨论。与之前相比,此后的艺术界既面临着不同的艺术问题,也拥有不同的理论视域。首先,艺术体制论的提出源于20世纪先锋派的艺术变革与艺术实践,尤其是现成品艺术提出的理论挑战。其次,伴随着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学者们在20世纪上半叶尤为关注艺术内部的“结构形式”,在20世纪下半叶集中关注艺术外部的“体制话语”。艺术体制论成为当今艺术阐释的主流理论,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学术思潮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有关。艺术研究在这种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其中的一个重要桥梁是贡布里希。主流学界所谓的艺术体制论,专指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丹托和迪基发展而来的主要致力于阐释现当代艺术的艺术体制论。我们可将这一理论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贡布里希的“语言学图式论”。
二、被忽视的奠基人:贡布里希及其艺术体制论
英国学者海伍德认为:“体制理论是一种类社会学理论,它是在现代主义、以及此前的类型连同支撑这些类型的批判理论的衰落和瓦解的压力下,由美学家和哲学家发展而来的。”[6](12)这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显然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对艺术体制论的贡献。早在丹托和迪基之前,贡布里希已经创造性地结合语言学与社会学,从艺术体制论的角度阐释艺术,包括现当代的现成品艺术。贡布里希运用体制理论阐释艺术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后来他又在1960年出版的《艺术与错觉》、1974年发表的《名利场逻辑》中进一步完善了它。然而,几乎没有人将艺术体制论与贡布里希联系起来,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被学界忽视了。
在1950年发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一文中,贡布里希追溯了16世纪中叶以后风景画在欧洲兴起的原因。他认为,风景画的兴起不仅与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有关,也与艺术理论家的批评实践有关,“如果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理论,我们所了解的风景画是绝不可能发展的”[7](130)。贡布里希不是说艺术理论创造了风景画,毕竟风景画出自艺术家的画笔,但他强调,没有艺术理论家的参与,就没有风景画的兴起。在此文中,贡布里希将正在兴起的风景画视作一种新的艺术制度的出现与确立。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风景画成了绘画和印刷品的公认的题材。我们从杨·布吕格尔[Jan Breughel]或H.约丹斯[H.Jordaens]画中的艺术商店和收藏家的“陈列室”内看到,“纯”风景画是交易中的常备货物。正是这一时期,凡·曼德尔[van Mander]在他的说教诗中用整整一章专门描写了这一重要的艺术分支。风景画变成了一种制度[institution]⑥。[7](131)
在16世纪的欧洲,风景画逐渐从其他画种中独立出来。贡布里希认为,这既离不开艺术家的创作,也离不开艺术理论家的批评阐释与观看者的需求,总之,离不开当时的整个艺术界,他将这些统称为艺术制度。当风景画从其他画种中独立出来,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绘画题材,成为一种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常备货物,这不仅改变了艺术分类,改变了审美风尚,也改变了艺术市场结构,一种新的艺术制度便随之确立了。这是贡布里希首次提出一种较为系统的艺术体制论,而且它也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社会学实践。当然,他在此处阐释的并不是现当代艺术,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景画。
当代美学与艺术理论的核心命题,是艺术的界定和价值评估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解释平常的“现成品”嬗变为带着光晕的“艺术品”的问题。这是丹托、迪基乃至无数艺术理论家为之殚精竭虑的根本问题。贡布里希应该是20世纪最早从艺术体制论出发对现成品艺术给予比较系统的解释的理论家。在1951年发表的《木马沉思录》一文中,贡布里希以孩子的木马游戏为喻,猛烈抨击包括再现论、表现论、抽象论等在内的任何本质论的艺术定义。他不厌其烦地援引语言学理论,将图像学比作视觉艺术研究的语言学[8](28)。他借助木马游戏进一步阐述了艺术体制论,并首次对毕加索用现成品提出的艺术定义难题做出了理论回应。事实上,木马之喻不是贡布里希的发明。早在1905年,维也纳语义学派的创始人海因里希·贡柏兹在《论自然主义艺术的一些心理条件》中就提到,在孩子的游戏中,一根普通的木棍变成了木马。贡柏兹尝试从语言学角度对木马游戏作出解释,他最终将艺术的意义追溯到特定的社会习俗和文化惯例⑦[9]。
贡布里希认为,作为艺术的木马,只能被理解为特定社会的艺术体制中发生的一个行动、过程和事件,它出现在小孩的骑行游戏之中。没有孩子的骑行游戏,木马不是马,只是墙角里的一根木棍而已;没有人们的艺术活动与游戏,杜尚的《泉》不是艺术品,它只是商店货架上默默无闻的小便池。重要的不是木棍,而是孩子的骑行游戏;重要的不是小便池,而是成人的艺术游戏。贡布里希耿耿于怀的木马,不过是他日思夜想的现代艺术,更确切地说是现成品艺术阐释的理论难题。
我们称为“艺术”的那个奇怪的领域像个镜子厅和回声廊。其中每一种形式都能唤起无数的记忆和后像[after-images]。一个图像一旦成为艺术,它马上就成了一种新的参考框架,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它必然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就像玩具是幼儿园的一部分那样。如果(正如我们可能设想的)一位叫毕加索的人,从陶器转向木马,并且把这些出自怪念头的产物送去展览,我们可能把它们理解为一些示范,一些讽刺的象征之物,理解为对于粗陋事物信仰的表白,或理解为是自嘲——不过,即便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必定也有一件事无法做到:他不可能使我们获得木马对它的第一位创造者所具有的含义。[8](28−29)
事实上,艺术体制论不仅适用于阐释现当代先锋艺术,也适用于阐释一切时代的艺术。贡布里希所举的“一位毕加索”的例子,也可以换成杜尚或安迪·沃霍尔的例子。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创作了千万种形态各异的艺术品,被现代人统称为“艺术”。要真正理解一件艺术品,人们需要把艺术理解为一个行动、过程、事件,这个事件同时包括艺术家(小孩)、艺术品(木棍)、艺术再现对象(马),还包括读者/观者,因为读者/观者赋予作品不同于艺术家的含义。然而,只是思考以上参与艺术事件的四要素仍然不够。毕竟,杜尚的《泉》不同于拉斐尔的圣母画,《泉》这样“一个图像一旦成为艺术,它马上就成了一种新的参考框架”。人们需要思考的就不是小便池本身,甚至不是将小便池送去展览这一艺术行为或事件,而是需要思考这一行为事件得以产生和被接受的“参考框架”。贡布里希将之称为制度(institution),有时称之为习俗或惯例(convention)。“所有的艺术都是‘制像’,而所有的制像植根于替代物的创造,甚至‘错觉主义的’艺术家也必须从人造的东西即‘概念性’图像的惯例(convention)入手。……他无法径直地‘模仿一个物体的外形’。”[8](25)换言之,作为人工制品,艺术首先与人们植入其中的观念、与使用它的习俗惯例紧密相关,而与其再现对象是否相似倒无关紧要。
在1960年出版的《艺术与错觉》一书中,贡布里希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艺术体制论。除了核心概念图式之外,惯例或习俗(convention)、制度(institution)、情境(situation)等词汇也以极高的频率在书中反复出现。贡布里希想把艺术制度论统一于他的“图式论”之中,但是源于康德美学的“图式”概念显然更加偏向于指称艺术内部的形式因素。因此,当强调超越艺术品之外的语境和社会因素时,他就更多地使用“上下文”“情境”“制度”“惯例”这些词汇。他说:“我们通常不会认为半身像是再现砍下来的一个头;我们理解这个情境是什么,知道这是属于称为‘半身像’的那个社会习俗或程式的东西,甚至在我们还不曾长大成人时就熟悉半身像是什么。”[10](67−69)人们并不把半身像看作断臂残肢,而是将之视为完整的人物形象。这与半身像本身的形式无关,而与制作和使用它的社会习俗有关。此处所谓的社会习俗或程式,显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艺术社会体制。贡布里希深受贡柏兹、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游戏论”影响,主要将艺术体制理解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游戏规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而不是实体性的制度机构。当贡布里希使用“institution”一词时,是指一种社会化的艺术体制或文化惯例;而当他使用“convention”一词时,有时是指基于历史用法形成的艺术外部的文化惯例,有时是指艺术品本身的“程式”,其意义类似于中国戏曲的程式。
20世纪70年代,贡布里希进一步完善了艺术体制论,更加强调作为一种情境逻辑、社会关系的艺术制度决定着艺术品的生产、消费、理解和感知。这集中体现在他1974年发表的《名利场逻辑》中。贡布里希重申,他认同波普尔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并提出一种他称之为“名利场逻辑”的艺术社会制度论,用来替代黑格尔以理念论和历史决定论为核心的艺术观。他大篇幅地引用了波普尔的观点:
我毫不赞同这些“精神说”。……我觉得这些精神论至少能表明存在着一块真空,存在着一个有待填充的地带,用较有意义的东西去填充它是社会学的任务。……还可以包括对“情境逻辑”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除了这种情境逻辑之外,我们还需要像社会运动的分析那样的东西,或许把它作为情境逻辑的一部分来看待。我们需要根据方法论上的个体论来研外部游戏的制度语境既相互限制、相互影响,又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他都将之纳入图式论之中。贡布里希结合语言学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体制论,并且将之奠定在社会学、历史学的多元学科视野之中,为现当代艺术的阐释以及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从“图式论”到“艺术界”:贡布里希与丹托
迪基坦承他受到了丹托1964年发表的《艺术界》的启发,因此,丹托常常与迪基一起被视为当今艺术体制论的代表人物[13](158)。可是,与迪基正面承认受到丹托影响的坦诚态度相比,丹托本人就没有那么诚实了。事实上,一直以贡布里希的批判者形象示人的丹托,其艺术界理论深受贡布里希图式论的启发。遗憾的是,丹托始终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
在1983发表的《贡布里希》一文中,丹托公然宣称贡布里希的观点过时了,“贡布里希不知疲倦地试图去解释的,以及他提出的主要问题的整个历史的可能性,就是错觉艺术。然而,错觉主义在有些时候并不是一种艺术目标”[14]。丹托不仅把贡布里希塑造为认同艺术就是再现的错觉主义者,而且极力贬低他的思想价值。“他所说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或艺术创作没有多大影响,对那些求助于他的著作、并认为这些著作有助于理解本世纪令人困惑的艺术的人们,也没有价值”[14]。然而,贡布里希不仅从未说过艺术是再现,而且一贯反对任何关于艺术的本质定义。有趣的是,在晚年的代表作《美的滥用》中,丹托似乎有意向读者透露其艺术界理论与贡布里希的图式论之间的联系,虽然他并未提到后者的名字,“当我于1964年写了我的第一篇艺术哲学文章时,我是根据当时的思维模式构思的,那种思维模式以科学哲学和语言理论为特征,它们主宰着当时的‘受尊敬的’哲学”[15](2)。
丹托1964年发表的第一篇艺术哲学文章,正是启发迪基提出“艺术体制论”的著名论文《艺术界》[16]。那么,丹托构思这篇论文所根据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丹托没有明说,只说它主宰着当时“受尊敬的”哲学,“以科学哲学和语言理论为特征”。事实上,它是指贡布里希1960年出版的《艺术与错觉》,这部被贡布里希称作“视觉图像的语言学”的著作不仅深受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影响,而且包含着难以尽述的语言学内容,虽然它更多时候仅仅被学界视作一部视觉心理学著作。丹托熟悉波普尔一切科学观察都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他在1981年出版的《寻常物的嬗变》中究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制度,观念可以得到传播并感染个人。……我们的个体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模式[individualistic and institutionalist models]诸如国家、政府、市场等这样的集合体不但要用像科学和工业进步这样的社会运动的模式去加以充实,而且还要用政治情境的模式去加以充实。[11](63)
贡布里希特意提到,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十四章“社会学的自主性”中更充分地阐述了上述观点。波普尔写道:“如果不参照我们的社会环境、不参照社会制度及其运行的方式,我们的行动就不能获得解释。所以,制度主义者可能认为,将社会学还原为对行为的心理学的或者行为主义的分析,是不可能的。”[12](155)同波普尔一样,贡布里希认同制度主义者的观点,拒绝将社会学还原为个人化的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分析。贡布里希将艺术制度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试图在特定社会的情景逻辑中考察艺术行动及其运行方式。众所周知,贡布里希与波普尔是终生挚友,两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他甚至在《艺术与错觉》一书中说,“如果本书中处处可以感觉到波普尔教授的影响,我将引以为荣”[10](第一版序言)。在《名利场逻辑》中,贡布里希用波普尔强调的微观的“情境逻辑”和“社会制度”去替代黑格尔宏大的理念论,提出一种关于艺术的“名利场逻辑”的社会学阐释,将艺术家和艺术品置入一种制度主义模式、社会运动模式和政治情境模式之中,其艺术体制论已经发展为一种系统的艺术社会学理论。
贡布里希提出艺术体制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语言的看法。他认为语言是我们置身其中最重要的社会惯例和文化习俗;而图像作为一种视觉语言,也是社会惯例或文化习俗的产物,也具有建构社会惯例和文化习俗的功能。整体而言,作为图像语言学,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既包括艺术内部的形式语言游戏,又包括艺术外部的制度语境游戏。木棍之所以能够在儿童游戏中被转化成飞驰的马,一方面与木棍能够被轻巧地跨上去的形式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与赋予马可以被骑上去的人类社会习俗有关。要理解木棍在孩子游戏中如何被创造为“木马”,孩子与观众不仅需要知道木棍所“再现”的马这种动物,而且需要拥有关于马的文化习俗和社会活动方面的知识。这些关于马的知识和习俗又与我们的语言息息相关,“我们的语言中还有过去封建时代铸造的隐喻,把chival-rous[骑士风度的]说成是horsy[马一样的]”[8](22)。可见,语言学是贡布里希思考艺术的基本框架,艺术内部的形式语言与写道:“我引用了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口号,所谓没有解释就没有观测,根据这一观点,科学观测充满了理论的负载,假如有人相信科学是绝对公正的并追求中性的描述,他就等于是放弃了从事科学的可能。”[17](153−154)熟悉波普尔这个观点的丹托不会不知道,深受波普尔影响的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系统阐释了他的图式论,认为“没有一个艺术家能摒弃一切程式‘画其所见’”[10](第一版序言),而画家的程式就像科学家的理论一样,是对于现象客体的一种理论化的描述或解释。
正如波普尔认为没有离开理论的观察一样,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理论本身的演进,即“猜想—反驳”的过程。贡布里希认为,没有离开图式的观看,艺术的发展首先是图式本身的演变,即“图式—修正”的过程。我们没法离开图式去观看,所有的观看都是解释,甚至我们对于现实的观看也直接由图式所形塑,因为“根本没有不带解释的现实;正如没有纯真之眼一样,世间也没有纯真之耳”[10](440)。显然,图式是一种由视觉语言所规范、形塑的感知方式和观看方式,而这种感知方式和观看方式本身就包含着对观看对象的理论解释。观看从来不是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行为,而是一种由图式(视觉语言)建构出来的图像话语和视觉解释活动。“对那些要求绘画看起来有如自然的无知庸人,这又是当头一棒。他们的要求毫无道理。如果观看[seeing]都是解释,那就可以论证各种解释方式都是同样地有理有据。”[10](359)丹托受此启发,将这个观点挪用到现当代艺术阐释领域,认为一件现成品之所以能够嬗变成艺术品,而与之在外观上完全无异的另一物品则不是艺术品,这完全是由艺术界的理论解释决定的。“在艺术中,每一个新的解释都是一次哥白尼革命,我的意思是说,每个解释都建构一个新的作品,即便被解释的对象仍然是同一个,就像天空在理论的转型中保持自身的不变一样。”[17](154)丹托这一理论的直接来源,正是受到波普尔科学哲学影响的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正如卡尔·波普尔所强调的,每一个观察都是我们对大自然所提出的某一个问题的结果,而每一个问题又都蕴涵着一个尝试性的假说。我们之所以要寻找什么东西,那是由于我们的假说促使我们期待某些结果。……对科学活动方式的这种描述非常适用于艺术中的视觉发现史。事实上,我们总结出图式和矫正的公式,所说明的正是这个程序。”[10](387−388)
丹托承认受到“以科学哲学和语言理论为特征”的哲学思维模式的直接启发,但他没有指明这种思维模式源自贡布里希,因此,要想确证二人的思想联系,我们还需要其他论证。比较丹托的《寻常物的嬗变》和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读者不难发现,两本著作不仅分享了“知觉”“图式”“概念图式”“解释”“识别”等大量核心概念,而且《寻常物的嬗变》的多数观点都可以在《艺术与错觉》中找到直接来源⑧。丹托还在书中提到一个木马的比喻,并用它阐释自己的艺术界理论:
想象的边界同时就是知识的边界,与此类似,解释的边界同时就是知识的边界。想想一个小孩能拿一根棍子做什么:它可以是一匹马,一枝矛,一杆枪,一个玩偶,一堵墙,一艘船,一架飞机;它是一件无所不能的玩具。……一个小孩能把一根棍子想象成一匹马,其前提条件是他知道一些关于马的事情,他对马的知识的界限,就是他的游戏的界限。[17](157)
小孩之所以能把一根木棍变成马,他首先得知道有马这种动物,也知道马可以被骑上飞驰而去。丹托关心的不是木棍、木马或者马,而是艺术及其定义问题。当他说“对马的知识的界限,就是小孩子的游戏的界限”时,他其实是在说,“对于艺术的知识的界限,就是艺术界的游戏的界限。”简言之,艺术就是艺术界的人根据他的知识将一个普通物品解释成艺术的游戏,就像小孩根据他的知识将一根普通的木棍解释成马的游戏。事实上,这只实质上只是一根木棍的木马,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丹托的著作中。早在1964年发表的《艺术界》中,丹托就提到了它,他借用小孩的木马游戏来回答布里洛盒子这样的现成品提出的艺术定义难题。丹托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艺术史、艺术理论的相关知识,“如果他不能达到这个程度,他将永远不能看到艺术品:他将像一个把棍子只看成是棍子的小孩”[16]。显然,木马就是丹托眼中的现成品艺术,木马就是艺术界理论的直接思想资源。可是,这只“特洛伊木马”在帮助丹托清晰阐释艺术界理论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一直意欲隐藏的理论来源。如前所述,丹托的木马之喻源于贡布里希1951年发表的《木马沉思录》,后者在文中不仅借木马之喻提出了艺术体制论,而且也用它来解释现成品艺术。只是贡布里希使用的例子是“一位毕加索”的现成品,而丹托的例子是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
细心阅读丹托的《贡布里希》(1983)一文不难发现,丹托一面极力贬低贡布里希,一面对他的《艺术的故事》(1950)、《艺术与错觉》(1960)、《秩序感》(1979)、《图像与眼睛》(1982)等著作进行评述[14]。这说明丹托不仅极其熟悉贡布里希的观点,熟悉他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密切关联,知道他对于语言学的倚重,而且时刻关注着他的最新学术成果和研究动向。以贡布里希批判者自居的丹托,其实非常清楚贡布里希的学术贡献和思想价值,甚至在2004年出版的《美的滥用》中,丹托还念念不忘贡布里希“以科学哲学和语言理论为特征”的“思维模式”给他造成的“影响的焦虑”。
丹托的很多观点(包括艺术界理论在内)虽然直接受益于贡布里希,但两人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目标却有重大差别。贡布里希将任何时期的艺术都视作特定社会的艺术体制的产物,否定艺术可以被定义;丹托主要关注20世纪的现当代艺术,试图重建艺术的定义。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深刻把握了“所知”和“所见”的辩证关系,兼顾了艺术的符号性和视觉性。相较而言,丹托凸显了“所知”或话语符号对艺术的建构,而有忽视艺术的视觉性之嫌。丹托的艺术界在根本上是艺术史的知识和艺术理论,他将艺术完全看作理论建构的产物,这既取消了艺术的物质性、视觉性,也取消了艺术指涉现实的可能性,艺术成了彻底虚拟的空符号。丹托走向了彻底的非实在论,这是他与贡布里希的根本差别。贡布里希坚持图像符号的虚拟性和对于现实的建构性,但他没有走向否定艺术物性、否定艺术具有再现现实的可能性的非实在论。丹托将艺术品看作是理论阐释的结果,艺术成了理论对象而不是感知对象,也就造成了哲学对于艺术的剥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与贡布里希的艺术体制论相比,丹托的艺术界更加关注现当代艺术现象,凸显了理论阐释对于艺术品的意义生产,也突出了当代艺术的符号特性,但也更加狭隘和封闭了。
严格来说,丹托的艺术界并不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艺术体制论,而只是一种关于艺术的美学定义或理论阐释。与丹托一样,迪基也试图重新定义艺术以解决当代艺术阐释难题,他进一步发展了丹托的艺术界理论,提出了艺术体制论,使得艺术研究的社会学视域更加凸显。
四、走向艺术社会学——迪基的艺术体制论及其批判
迪基坦承丹托对他的启发,“丹托在其著作《艺术世界》中,虽然无意界定艺术,却指出了任何界定艺术的努力都必须遵循的方向。……他的话指出了特定的艺术品所存在的复杂结构,指出了艺术的‘制度性’”[18](107)。迪基于1971年旗帜鲜明地提出艺术体制论,被理论界推举为艺术体制论的提出者、开创者。但他后来面对各种批评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最后用惯例(convention)替代了体制(institution)一词,将他的艺术体制论修改为艺术惯例论或艺术习俗论。迪基的艺术体制论仍然是一种试图为艺术提供定义的艺术哲学,而不是真正的艺术社会学实践。
受到丹托的启发,迪基于1969年开始创建被学界称之为“艺术制度论”的观点,并于1971年、1974年、1984年进一步完善和修订它。1971年,迪基在《美学导论》中首次明确提出“艺术制度论”,“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一件人工制品;(2)代表某一社会体制[艺术界(the art world)]而行动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授予其被欣赏的候选品资格”[19](101)。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引发了热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批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要点有两个:一是艺术界并不完全是一个正式的、实体性的社会组织,它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体制”;二是无论艺术界是不是一个具有实体性的社会组织,说某个或某些人代表艺术界授予艺术候选品资格,使一件物品成了艺术品,这夸大了某个或某些艺术界人士的作用,难以令人信服。面对诸多批评,迪基在1984年的《艺术圈》中将这个观点做了不小的修正和补充:
(1)艺术作品是一种创造出来展现给艺术界公众的人工制品。(2)艺术家是理解性地参与制作艺术作品的人。(3)公众是这样一类人,其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准备好去理解展现给他们的对象。(4)艺术界是所有艺术界系统的整体。(5)艺术界系统是一个框架结构,以便艺术家能够把艺术作品展现给艺术界公众。[20](80−82)
从这个定义可见,迪基不再仅仅强调艺术界的某个或某些人赋予一件物品作为艺术候选品的资格,而是强调艺术品、艺术家、公众和看不见的框架结构共同构成了“艺术界”,由这样一个作为社会制度存在的“艺术界”共同决定什么样的物品能够成为艺术。在《艺术的体制理论》一文中,迪基不仅对自己的“艺术制度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也对他1984年的艺术定义进行了更加全面的阐释。虽然如此,迪基的这个定义仍然被沃尔海姆、卡罗尔等人指责为循环论证,或者是夸大了艺术界团体在赋予物品艺术资格中的作用。迪基前期的理论可以称之为艺术制度论(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而他在1984年就基本放弃了使用制度(institution)一词,而改用惯例或习俗一词(convention)。“这体现出了迪基对习俗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结构的浓厚兴趣,也就是说,他所关注的是与行为方式、艺术活动规则有关的习俗惯例。”[1]虽然学界把迪基当作艺术制度论的代言人,但他最后更加认同的是艺术习俗论。这两者之间虽然有一致性却也有不小的差异。在迪基看来,“艺术品是艺术,这是因为它们在一种体制语境中占据位置”[21](115)。一个物品能够成为艺术品,不在于艺术体制授予其资格的社会活动,而在于艺术置身其中的社会习俗。
迪基最后将“艺术体制论”修改为“艺术习俗论”,使论点更加严谨、更有说服力,但这也使得他的观点更加接近贡布里希的观点。对贡布里希而言,艺术的体制语境既是一种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遗产。与迪基试图用体制理论定义艺术不同,贡布里希认为体制论或习俗论只能提供一种研究艺术的方法或视野,而不能给艺术提供统一的解释、唯一的定义。当然,也是由于拒绝建立统一理论体系的唯名论立场,使得贡布里希这方面的贡献不够凸显、罕有人知。
很多美学界的学者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艺术体制论把研究重心从艺术内部的结构形式转向外部广阔的“艺术界”,打开了艺术研究的社会学视野。丹托和迪基被视为这一理论的代表,被视为当代“艺术哲学的社会学转向”的标志性人物[22]。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丹托和迪基虽然分别提出了艺术界和艺术体制论,但他们仍然致力于为艺术提供抽象的本质定义,而没有展开真正的艺术社会学研究。“哲学家倾向于从假想的事例进行论证,丹托和迪基所说的‘艺术界’这块骨头上并没有多少肉,仅仅是为了表达他们想表达的观点而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前提。”[23](149)与之相对,贝克尔盛赞艺术史家对于艺术社会学的贡献,“众所周知,最好的艺术社会学中的一些作品是由非社会学家创作的,比如米歇尔·巴克森德尔和巴巴拉·史密斯”[22]。虽然没有看到贡布里希对艺术体制论的直接贡献,但贝克尔已经发现贡布里希特别注重从习俗、惯例等方面去解释艺术。事实上,作为巴克森德尔的老师,贡布里希不仅是传统艺术史向新艺术社会史转向的关键人物,而且对艺术哲学的社会学转向贡献良多,他不仅启发了丹托,更是先于迪基提出了艺术体制论。总的来说,丹托的“艺术界”和迪基的艺术体制论都只是一种类社会学的艺术定义,而不是真正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作为美学家的丹托和迪基更愿意从概念出发去定义艺术,而不是从具体的史实和社会情境出发去考察艺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批判他们的理论“多骨而少肉”,可谓一针见血。
彼得·伯克认为,贡布里希是微观水平上的文化史的杰出践行者,“最重要的是,贡布里希有时从集体的角度把艺术描述为一种制度或者一种语言,或者更传统地描述为一组风格和画种,却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发展那些观念”[24](20−22)。确实,贡布里希并未充分发展他的艺术体制论和艺术社会学,这方面的史学和理论贡献分别是由巴克森德尔、布尔迪厄等人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虽然如此,无论从艺术哲学的理论构建还是从艺术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上来讲,贡布里希都堪称20世纪70年代前后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社会学转向的直接源头之一,艺术体制论的真正奠基人。这也是被尊为新艺术史开启者的巴克森德尔不断强调他深受贡布里希影响的根本原因⑨。而对艺术社会学具有突出理论贡献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则坦承他受到巴克森德尔的启发[25](299)。贡布里希从艺术史实践出发对艺术体制论的理论建构,构成了不同于丹托、迪基从艺术哲学角度阐释艺术体制论的复调叙事。艺术体制论的复调叙事互为表里,时有交叉,共同塑造了当今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主流形态。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却只看到后来的“流”,而没有看到前面的“源”,这是我们要重新探索艺术体制论的原因。
艺术体制论并非一两个美学家孤立地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而是不同学科的理论家进行思想对话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当代艺术体制论并非美学“独奏”,而是语言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合奏”。这些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声音,构成了不同于丹托和迪基从哲学美学角度探索艺术体制论的“复调叙事”。20世纪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学术研究越来越强调跨学科的综合性和对话性。贡布里希对艺术体制的思考同时综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理论方法,这本身便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复调叙事”。保持理论的“复调”性质和“对话”状态,是贡布里希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立场;也由于其理论方法极其多元,他成了一个很难被简单归类的史学家和理论家。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他对艺术体制论的实际贡献,更不应该忽视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交锋,因为,学术研究就是在理论对话、观点碰撞、思想交锋中推陈出新的。
注释:
① 彼得·基维、戴维斯、马克·西门尼斯等人都认为,艺术体制论是当代艺术诠释的主流理论。美国学者诺埃尔·卡罗尔编著的《今日艺术理论》也反映了这一点。参见彼得·基维:《美学指南》,彭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戴维斯:《艺术诸定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诺埃尔·卡罗尔:《今日艺术理论》,殷曼楟,郑从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虽然迪基后来修正了自己的理论,用惯例替代了体制一词,但学界公认迪基的理论贡献还是艺术体制论。
③ 参见沃特伯格:《什么是艺术》,李奉栖,张云,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6−232页;戴维斯:《艺术诸定义》,韩振华,赵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0−165页;马克·西门尼斯:《当代美学》,王洪一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④ 关于convention(惯例、传统、约定)的考察,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8−89页。
⑤ 我们认同克里斯特勒的观点,将18世纪视作“现代艺术体系”的确立时期。1746年,阿贝·巴托在《归于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中将“实用艺术”与“美的艺术”明确区分开来。1750年,“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出版了《美学》。1764年,“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出版了《古代艺术史》。1790年,康德出版《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宣告完成,“知、情、意”三分在认识论哲学上得以确立。
⑥ 原文将institution译为“惯例”,这里统一译为“制度”。贡布里希认同维特根斯坦“语言的意义即用法”的观点,拒绝对institution、convention等语词进行定义。根据贡布里希的用法,institution明确地是指一种社会化的艺术体制和文化惯例,而convention一词意义更为复杂,他有时是指外在于艺术品的体制、习俗、惯例,有时是指艺术品本身的“程式”,其意义类似于中国戏曲的程式。这个语词有凸显历史文化传统对艺术的决定性影响的意味。
⑦ 贡柏兹从语义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是游戏活动创造了艺术或图像的意义——是骑行行为使得男孩子的木棍变成了“木马”,是呵护的动作使得女孩手里的汤勺变成了“孩子”。贡柏兹显然已经清晰地知道,要想确定一个图像的意义,并不能只考虑该图像与其“再现”对象的关系,而且要考虑该图像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使用。
⑧ 重点参见丹托《寻常物的嬗变》的第5章“解释与识别”,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的第三部分“观看者的本分”。参见阿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1−167页;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216−348页。
⑨ 巴克森德尔在多种场合和著作中强调他是贡布里希的学生,深受他的影响。参见Michael Baxandall.Words for Pictures:Seven Papers on Renaissance Art and Criticism,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reface,X;巴克森德尔:《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殷树喜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