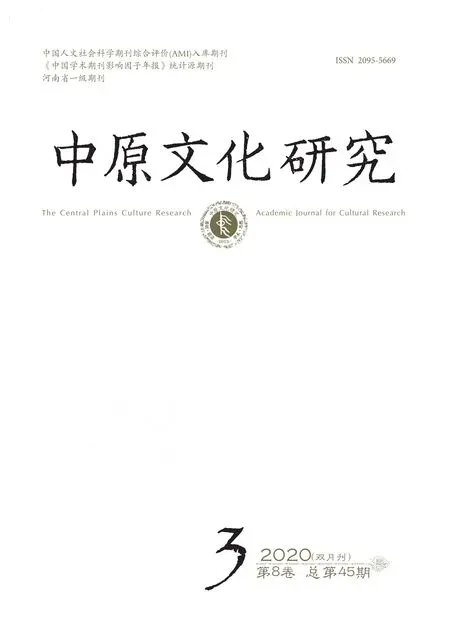清代早中期黄河决溢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变迁述论*
2020-01-06田冰
田 冰
清代黄河水患一如明代,灾害范围之大几乎遍及河南东部、山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同样,清代每年所需漕粮仍然与明代一样,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仍是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自江苏邳州至淮安有近百公里的运道要借助黄河,黄河仍然是漕运能否畅通的重要保证。由于明末清初连续40 多年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患严重影响到清王朝京杭大运河的正常漕运。乾隆后期,黄河水患日益严重,不得不“借黄济运”,至嘉庆道光年间治河无术,黄河下游河道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改道东流后,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终于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清早中期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顺康年间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分布
顺康年间,黄河决溢在河南、山东、江苏境内都有发生,既影响了张秋运河,也影响到济宁以南运河。顺治时,黄河决溢以河南最为严重,治理举措以堵塞决口为主,保证漕运畅通;康熙时,黄河决溢以江苏最为严重,朝廷在全面治理黄河的基础上,开挖新运河,从根本上改善漕运状况。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北徙前,基本上维持明末的河道,没有大的变化,即“由开封经兰、仪、商、虞,讫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宁、邳、宿迁、桃源,东经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①。由于明末清初连续40 多年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在顺治执政的18年间,有9年曾发生决口,且集中在河南境内,甚至有1年2 处决口的。其中影响到漕运的大的决溢有:顺治元年(1644年),“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兰阳入运河,田产尽没”②;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河决流通集,一趋曹、单及南阳入运,一趋塔儿湾、魏家湾,侵淤运道,下流徐、邳、淮、扬亦多冲决”①(按:原文误为“淮阳”,根据《清史稿·杨方兴传》校改);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河决荆隆朱源寨,直往沙湾,溃运堤,挟汶由大清河入海”①;顺治九年(1652年),“河决封丘大王庙,冲圮县城,水由长垣趋东昌(今山东聊城),坏平安堤,北入海,大为漕渠梗”。屡堵屡决,溃水从长垣趋东昌,阻滞运道。到康熙年间,黄河决溢呈加剧之势,尤其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前,黄河下游几乎无岁不决口,大都在山东曹县以下河段,且集中在江苏境内,甚至有1年多达3 处决口的,对漕运造成严重威胁。其中对漕运影响最大的一次当属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黄、淮并涨,“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高邮之清水潭,陆漫沟之大泽湾,共决三百余丈”③,淹了淮、扬七个州县,致使淮水涓滴不出清口,“蓄清刷黄”失去了作用,黄河河道更加淤垫,运河也淤积严重。据当时勘察河情的人说:“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河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河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二三尺矣。河淤运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底矣。运淤,清江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④由此可见,河道、运道淤积是多么严重,漕运不通已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当时虽正在平定三藩,军用浩繁,但康熙帝毅然下了治理黄河的决心,于十六年(1677年)调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并把“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上,用以时时提醒自己,下决心治理黄河,改善漕运。
其实,清建国伊始,统治者就把治理黄河提上议事日程,首先堵塞明末河决开封的口门,使黄河回归故道。面对屡堵屡决的黄河,当时不少朝臣连上奏章,请勘九河故道,想让黄河改道北流走所谓禹王故道,即流经今河北平原,在今天津市南部入海。而时任河道总督的杨方兴陈述黄河不能改道北流的原因,他说:“元明以讫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在宿迁境)二百余里,必借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今乃欲寻禹旧迹,重加疏导,势必别筑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以晓然。且河流挟沙,束之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九,则水缓沙集,数年之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⑤顺治帝非常认同杨方兴的治河保漕策略,并运用到治河实践中。顺治年间治理黄河的重心区域在河南境内,主要举措是塞决口、筑长堤,“于上游筑长缕堤遏其势,复筑小长堤塞决口,期半年蒇事”⑥。此处所谓的上游也就是在河南境内的黄河两岸。取代杨方兴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继续践行杨方兴的治河之术,连续堵塞了河南的阳武、祥符、陈留和江苏山阳等处决口,在治理黄河上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对黄河水患和漕运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康熙十五年前黄河下游几乎无岁不决即是明证。
靳辅上任后,首先与其幕僚陈潢一道“遍阅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害”⑦,认识到“盖运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变迁,而河道之变迁,总由向来之议河者多尽力于漕艘行经之地,若于其他决口,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殊不知黄河之治否,攸系数省之安危,即或无关运道,亦断无听其冲决而不为修治之理”,提出了“治河当申全局,必合河道、运道为一体,而后治可无弊”④的治河保漕主张。全面治理黄河,靳辅提出的所谓“治河之道,必当申其全局”,就是针对黄河流经的不同地域存在的具体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综合治理。他针对黄河自清江浦到入海口300 多里的河道内,淤积甚为严重,采取“疏浚筑堤”的办法,“大挑清口、烂泥浅引河四,及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创筑关外束水堤万八千余丈”,既疏通了下流河道,又能利用淮河以清刷黄;当时黄河两岸20 多处决口,洪泽湖高家堰30 多处决口,他针对决口位置和大小,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将小口门一一堵合,最后堵在了清河杨庄大口门,使黄河归入正流;针对江苏砀山以下至睢宁间的河段狭窄,不利洪水下泄,沿用潘季驯修减坝的办法,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增建许多减水闸坝,各闸坝分出的水经过沿程落淤澄清后均入洪泽湖,再由清口入黄河,助淮以清刷黄;针对江苏徐州、邳州以下重要城镇多滨临大河,险工颇多,不得不严加防守,采取“埽、逼水坝、引河”多举措并用;他针对河南境内黄河在整个下游所处的位置,认为“河南地在上游,河南有失,则江南河道淤淀不旋”,在康熙十六年修筑兰阳、仪封、商丘月堤及虞城周家堤的基础上,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修筑“考城、仪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⑧。在靳辅治黄的多种举措中,以筑堤防为要务,他认为“堤成则水合,水合则流迅,流迅则势猛,水猛则新沙不停,旧沙尽刷,而河底愈深……治河者,必以堤防为先务”⑨的作用。在他主持治河的11年中,非常注意“坚筑堤防”,在黄河、淮河、运河两岸大力整修了千里长堤,增强了防御洪水的力量。
继大规模治理黄河后,清代通过开挖新运河从根本上改善漕运状况。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明朝万历年间开泇河的基础上,自骆马湖西侧凿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粮船北上,出清口后,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以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中河开通后,江苏境内的运道基本上脱离黄河,大大便利了漕船往来。康熙在二十八年(1689年)春,南巡河工至宿迁支河口,向随从的诸臣说开中河的好处,“此河开后,商民无不称便”,同时也指出中河存在的弊端,“河道关系漕运民生,地形水势,随时权变。今观此河狭隘,逼近黄岸,万一黄堤溃决,失于防御,中河、黄河将溷为一”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河位于黄河之东,靠着黄河,两河并行南流,不易展宽,里运河及骆马湖之水俱入中河,逢水大时存在河决隐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大雨引发的中河决口即是明证。此后的30 多年间,治黄保漕的重心是如何保障中河安流,使漕运畅通。针对中河隐患主要来自骆马湖水涨之时,采取措施控制骆马湖水涨,解除对中河的威胁。后来,河督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难以筑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张鹏翮任河督时,“见新中河浅狭,且盛家道口河头弯曲,挽运不顺,因于三义坝筑拦河堤,借用旧中河上段、新中河下段合为一,重加修浚,运道称便”。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因“仲庄牐清水出口,逼溜南趋,致碍运道,诏移中河运口于杨家庄,即大清河故道,由是漕盐两利”⑪。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不再担心黄河倒灌运河入洪泽湖。经过此番整治,除黄、淮、运交口处外,运河和黄河脱离关系,不再借黄济运,进一步便利了漕船往来。
尽管开挖中运河以后,黄河、运河只剩下交汇处的清口上下河段,然而用“牵一发动全身”来形容黄河对运河的影响也不为过。作为黄、淮、运汇合处的清口,是漕船出入运河的咽喉,“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⑫。朝廷也认识到治黄在清口的重要性。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行视清口、高家堰后,告诸臣说:“洪泽湖水低,黄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水无以出,泛溢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⑬指出治河应以深浚河身为要,三十九年(1700年)张鹏翮总理河道,康熙帝又告诫他说清口一带“黄河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⑭是治河的关键。由于黄河河床淤高,运河口受到拦隔,妨碍漕船的通行,同时水位抬高后,淮水不能出,起不到以清刷黄的目的,漕运也要蒙受影响。张鹏翮认为董安国所修的拦河坝,“拂水之性,以致黄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流不通,上流溃决”⑮。于是拆除拦河坝,堵塞了马港口及时家码头决口,大河仍是从云梯关以下入海,因而海门大通。康熙帝赐名大通口(按:《清史稿·河渠志》误作大清口,其他史书均记作大通口)。同时加培高家堰,堵塘梗六坝(按:六坝为武家礅、高良涧、周桥、古沟及东、西唐梗,共六座减水坝,均在高家堰大堤上),“使淮无所漏,悉归清口”,又开洪泽湖出口处之张福、裴家庄、张庄、烂泥浅、三岔及天然、天赐等七条引河,“导淮以刷清口”,“于清口筑坝台一座,逼水三分入运、七分敌黄”⑯。复于清口上游南岸整修挑水坝一座,在北岸陶庄开挖引河,导使大河北行,以免倒灌清口。从此10 余年不能东流的淮河,奔涌而出清口,会黄河入海,漕运无阻。
二、雍正至咸丰五年前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分布
由于康熙年间治黄保漕取得显著成效,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后黄河安澜10 余年。到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黄河连年决溢,且决溢地点多向上游转移,即河南境内,尤其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十一年(1722年)黄河在河南武陟境内决口,大溜北趋,经滑县、长垣、东明,夺张秋运河,由大清河入海;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七月、九月黄河分别在河南中牟、武陟、郑州境内决口,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设东河总督,驻武陟,管辖河南河务;于雍正七年(1729年)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加大治河力度,使黄河水患在雍正后期、乾隆前期相对减缓,对漕运影响也不大。到乾隆后期,黄河决溢已日趋严重,黄河、淮河、运河交汇处的清口上下河段淤积严重,不得不“借黄济运”,也就是引黄河水入运河,以确保漕船通行。嘉道年间治河无术,河道运道都到了无可收拾的程度。道光初年,试行海运;咸丰三年(1853年),海运以为常。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改道东流,漕运时代至此结束。
雍乾嘉道年间的黄河水患主要发生在河南、江苏两省境内。雍正、乾隆两朝73年的时间,见于《清史稿·河渠志》的黄河决溢年份有20多个。上起河南,下至山东、江苏,沿河各省均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决溢。其中河南决溢的年份占三分之一左右,武陟、郑州、阳武、中牟、祥符、兰阳、仪封、睢州、考城等地均曾决口成灾;江苏决溢的年份为三分之二上下,决过的地方计有砀山、丰县、沛县、铜山、睢宁、邳州、宿迁、桃源、清河、阜宁等地,尤以铜山、睢宁两地决溢的次数最多。嘉庆、道光两朝55年,见于《清史稿·河渠志》的黄河决溢年份也有20 多个。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发生在河南与江苏两省境内的决溢年份几乎差不多,尤其嘉庆年间几乎无岁不决,加之自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借黄济运”,致使运道淤积更加严重。这一时段对漕运影响较大的黄河决溢有:乾隆三年(1738年)秋,黄河水涨灌入运河,持续到次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黄河水入运,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往开临黄坝,以泄盛涨,并疏浚运河淤浅”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黄河决清江浦老坝口,一夜之间口门“塌宽至一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黄如运,板闸关署被冲,滨运之淮、扬、高、宝四城官民皆乘屋”[1]32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黄河倒灌洪泽湖、运河。嘉庆元年六月,河决山东丰县,刷开运河余家庄堤,“水由丰、沛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各湖,穿入运河,漫溢两岸,江苏山阳、清河多被淹”⑱;嘉庆八年(1803年)九月,河决“封丘衡家楼,大溜奔注,东北由范县达张秋,穿运河东趋盐河,经利津入海。直隶长垣、东平、开州被水成灾”⑱;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黄河在北岸之棉拐山决口,下穿邳州、宿州运河。因棉拐山下皆顽石,冲刷不动,复溢南岸萧县之李家楼,溃成巨口。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黄河决武陟马家营,大股由原武、阳武、延津、封丘等县下注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河道淤积更为严重⑲。尤其是清口一带上下河段,自乾隆后期淤积日益严重,难以漕运,自乾隆五十年开始借黄济运,当时的大学士阿桂履勘清口一带河工后言:“臣初到此间,询商萨载、李奉翰及河上员弁,多主引黄灌湖之说。本年湖水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远。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全借黄水浮送,方能过淮渡黄,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设法调剂,似可衔尾遄行”,“借黄济运,自此始也”⑳。不但清口一带“借黄济运”,到嘉庆九年(1864年),山东段运河浅塞,也“借黄济运”,引黄河水入微山诸湖以预蓄,以利漕运。然而自此以后,“黄高于清,漕艘转资黄水浮送,淤沙日积,利一而害百矣”㉑。到嘉庆十三年(1808年),淮、扬运河300 余里浅阻,当时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称:“近年运河浅阻,固由叠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河底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㉑道光四年(1824年)十一月,大风决开高家堰十三堡,引发黄水倒灌,冲坏石堤一千余丈,河督张文浩被夺职。当时的侍讲学士潘锡恩认为“蓄清敌黄,相传成法。大汛将至,则急堵御黄坝,使黄水全力东趋,今文浩迟堵御黄坝,致黄河倒灌,酿成如此巨患”㉒,同时陈述借黄济运之弊,“若更引黄如运,河道淤满,处处壅溢,恐有决口之患”。总之,自乾隆后期尤其是嘉庆以后,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还有历年“借黄济运”,漕运已无法维持,到道光六年(1826年),两江总督琦善调查清口情况说:“自借黄济运以来,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如线……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㉓次年开始试行海运。咸丰元年(1851年),河决丰县,山东被淹,漕船改由湖陂行。咸丰三年(1853年),漕粮改由海道运至天津,“自是遂以海运为常”㉔。
雍正至咸丰五年前黄河水患也没有得到遏制,愈发恶化;漕运也没有保住,最终废弃,而是以海运取代漕运,这跟治黄保漕的时空变化以及治黄保漕的举措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大的黄河决溢主要发生在河南境内,雍正帝加大了治理黄河的力度,时任河道总督的齐苏勒也谨守靳辅成法,继续沿用“疏浚修筑”之法,重点在黄河、运河两岸增修大堤,他会同副总河嵇曾筠大修了河南黄河两岸大堤,使“豫省大堤长虹绵亘,屹若金汤”㉕;在江苏境内兴修了“黄河自砀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口,纵横绵亘三千余里,两岸堤防崇广若一,河工益完整”㉖。齐苏勒还针对具体河患,在守成基础上开创治河新法。譬如,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河决江苏睢宁朱家海,东注洪泽湖。他在朱家海增筑夹坝月堤、防风埽,并于大溜顶冲处削陡岸为斜坡,在斜坡上悬密叶大柳枝,以抵御大溜之汕刷。经过夏季数次水涨水落后,大溜回归中间河道,斜坡柳枝沾挂泥渣,都变成了沙滩,化险为夷,不劳民伤财,这成为以后治理河崖陡岸的措施㉗。其实,削河崖陡岸为斜坡并在其上置密叶大柳枝之举只能说缓解一时的水患,从长远看只能抬高河床,加剧河患。在黄河水患愈演愈烈的时代,清政府有顾住上而顾不住下的尴尬。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黄河大涨,自江苏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涌南下,冲塌多处大堤,致使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五尺。乾隆帝就认为雍正年间治河重点在河南,而没有疏通徐州以下河道,于是令江南、河南两省督抚暨两总河共同商议对策,并移南河副总驻徐州专职督率。由此可见,乾隆帝加大了对江苏境内黄河的治理力度,从中也折射出徐州以南黄河水患持续加剧对漕运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时任南河总督的高斌及后来的白钟山遵循靳辅、齐苏勒、嵇曾筠等人的遗规,注意整修堤防埽坝,及时堵塞决口,使乾隆前期黄河没有发生太大灾害,运河在不断修筑过程中还能通航。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黄河在清河老坝口决溢,倒灌洪泽湖、运河。自此以后,黄河轮番在江苏、河南境内决口,大流多次注入洪泽湖,造成湖底不断淤高。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洪泽湖水量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督河官员干脆来个顺水推舟,“借黄济运”;至嘉庆九年,因山东运河浅塞,也“借黄济运”⑳。从中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到了治河无术的窘境。嘉庆八年(1803年)因睢州、桃源接连决口,河督黎世序甚至一度畏罪投河自尽,说明当时河督已经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道光六年(1826年),“蓄清敌黄”、筑堤“束水攻沙”等治黄措施此时都已失效。道光七年(1827年)以后,淮水基本不入黄。此时黄河大堤失去“束水攻沙”的作用,整个大堤情况如河东总督张井之言:“臣历次周履各工,见堤外河滩高出堤内平地至三四丈之多。询之年老弁兵,佥云嘉庆十年以前,内外高下不过丈许。闻自江南海口不畅,节年盛涨,逐渐淤高。又经二十四年非常异涨,水高于堤,溃决多出,遂至两岸堤身几成平陆。现在修守之堤,皆道光二、三、四等年续经培筑。其旧堤早已淤与滩平,甚至埋入河底。”由于河底连年垫高,“城郭居民,尽在河底之下,惟仗岁请无数金钱,将黄河抬于至高处”。他认为:“今以堤束水,仍守旧规,而水已不能攻沙,反且日形淤垫。”㉘因此,他感叹地说:“臣愚则以为古今治理,久则穷,穷则变,变则通。今日治河,可谓穷矣。即使不以人力变之,河亦必将自变。”㉙所谓“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不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㉚,更显出河道愈决愈淤、愈淤愈决的趋势,黄河下游河道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借黄济运”也就无法实施。
余 论
清咸丰五年以前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山东济宁与江苏淮安之间仍要借助黄河行运,故黄河下游的状况决定运河是否畅通、漕粮能否运达京城,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难解难分。其实,明代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以前,黄河决溢主要发生在河南境内,以北决为主,直接影响到山东张秋运河,也造成徐州以南黄河水量不足而难以行运。于是在黄河北岸和开封府黄河两岸修筑双重大堤,杜绝北流,解除了黄河水患对张秋运河的威胁。弘治十八年后,黄河水患转移到豫、鲁、苏交界一带,徐州上下河段是重灾区,直接影响到山东济宁至淮安段运河,潘季驯加固黄河下游两岸大堤用以“束水攻沙”与开挖新运河以避黄河水患成为明代后期治黄保漕的主要举措[2],并且为清代治河者所遵循。清代治黄保漕的举措基本沿袭明代,采取堵塞决口、筑堤“束水攻沙”、开挖新运河、筑闸坝等措施,即是康熙年间治河成就卓著的靳辅也是如此,这主要局限于对黄河特性的认识和治河技术。靳辅的幕僚陈潢介绍黄河特性说:“中国诸水,惟河源为独远。源远则流长,流长则入河之水遂多。入河之水既多,则其势安得不汹涌而湍急哉!况西北土性松浮,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也。”接着陈潢又明确指出黄河决溢具有明显的季节特点,“河防所惧者伏秋也……每当伏秋之候,有一日而水暴涨数丈者,一时不能泄泻,遂有溃决之事,从来致患,大都出此”。在谈到治河时,他说:“河之性无古今之殊。水无殊性,故治之无殊理……惟有顺其性而利导之之一法耳。”“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㉛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清代在治河技术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明清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下游河床抬高加快,而且下游所处区域的气候特点是夏秋常暴雨,加剧了黄河决溢的爆发,依靠筑堤“束水攻沙”是不可能根除黄河水患的,只能说一处发生决口,大堤加高加厚,就会在大堤薄弱地带决口,明清两代黄河大堤的修筑及黄河决溢的分布情况即是明证。面对河道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的局面,清政府走到了治河无术的窘境,不得不顺其“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于咸丰五年黄河终于在兰阳铜瓦厢决口东流,结束了南流的历史。
黄河自金章宗改道南流至咸丰五年改道东流,然而,明前期(弘治十八年以前)黄河就多次在北岸决口,北流的一支横穿山东张秋运河后,东流入海,破坏了张秋运河的正常漕运。同时,也影响到徐州以南的运河水量,因为徐州以南的运河是借助黄河行运的,黄河北决使徐州以南运河水量有时减少到难以行船的程度,如正统十三年(1448年)秋,黄河在新乡县八柳树决口,“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徐、吕二洪浅涩”㉜。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大决于开封及封丘金龙口(按:荆龙口),入山东张秋运河,次年奉命治河的户部侍郎白昂报称,这次决口后“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㉝。清代黄河北决情况仍然很严重,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淦根据黄河当时情况,提出开减河引水入大清河的主张时说:“自顺、康以来,河决北岸十之九。北岸决,溃运者半,不溃者半。凡溃其道,皆有大清河入海者也。”㉞由此可见,无论黄河北流还是南流,都会对运河形成威胁,而南流能够保障徐州上下运河水源补给源源不断以保证河流行运。因此,明清两代人“保河南流”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①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16 页。②《清史稿》卷二七九《杨方兴传》,第10109 页。③《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19-3720 页。④《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20页。⑤《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16-3717 页。⑥《清史稿》卷二七九《杨方兴传》,第10110 页。⑦陈潢原论,张霭生编述:《河防述言·审势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5页。⑧《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20-3721 页。⑨《河防述言·堤防第六》,第579 册,第760 页。⑩《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一》,第3774 页。⑪《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一》,第3775-3776 页。⑫《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第3770 页。⑬《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三三,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庚午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3 页。⑭《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一《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 册,第30 页。⑮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五三《河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3 页。⑯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百《工政六·河防五》,张鹏翮《论治清口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5 页。⑰《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第3783 页。⑱《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31 页。⑲《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36 页。⑳《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第3783-3784 页。㉑《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第3784页。㉒《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36 页。㉓《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第3786 页。㉔《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第3788 页。㉕康基田:《河渠纪闻》十八,《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 辑第29 册,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1997年版,第376 页。㉖《清史稿》卷三一○《齐苏勒传》,第10622 页。㉗《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24-3725 页。㉘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卷六二《河水》,民国三十一年(1941年)水利委员会铅印本,第1611 页,。㉙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卷六三《河水》,第1649 页。㉚魏源:《魏默深文集·古微堂外集》卷六《筹河篇上》,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国学扶轮社铅印本,第1 页。㉛陈潢原论,张霭生编述:《河防述言·河性第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9 册,第753 页。㉜张廷玉等:《明史》卷八三《河渠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5 页。㉝《明史》卷八三《河渠一》,第2021 页。㉞《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第37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