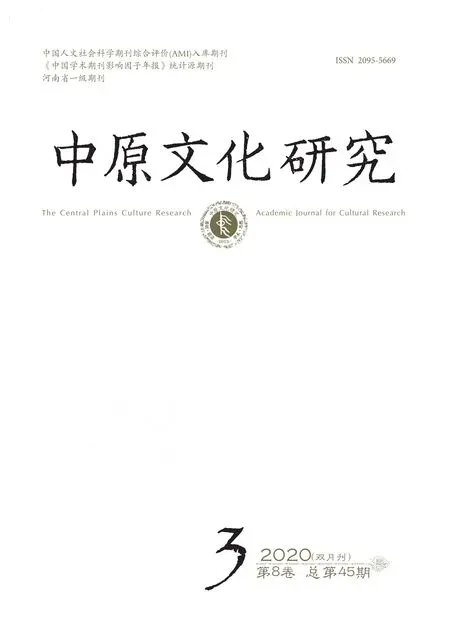再论王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
2020-01-06王泽应
王泽应
人类伦理文明建立在许多伦理思想家创发性学术致思和理论建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其实际运用和不断检测的价值积淀和精神凝聚。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只有那些既具有独特精神风骨和价值内涵,同时又发现了某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借鉴性的伦理思想,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其世界意义。相当一批思想家基本局限于其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在思想史的谱系内有所体现之外,很难对人类道德生活的现实化和理想化产生深度冲击和价值再造。但总有一些具有深刻哲学智慧和价值洞察力的伦理思想,可以与人类道德生活的实际需要和人类伦理文明的精神建构,发生最为直接的理论关联。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明末清初王船山的伦理思想于其在世时“声影不出林莽”,可在200年后却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船山伦理思想在砥砺志气,陶铸人格,激励人们在救世与救心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影响到国外,生发出超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魅力。
一、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界说
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既具有引发世界范围内伦理思想更新或进步的功能,也可以在精神实质和价值建构上为后世提供不断认同和掘发的思想资源和核心理念。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圣哲大师们的伦理思想,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卓越建构。西方近代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肇始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和道义论伦理思想,不仅培育了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而且也借助全球化、市场化和通讯技术的改善获得了世界范围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世界意义的特质。就中国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而言,除了雅斯贝尔斯在言及“轴心时代”的孔子、老子、墨子等圣贤的思想建构及其世界传播与影响外,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如朱熹、阳明等思想,因其自身独特的精神特质,也获得了在儒学文化圈的有效传播与世界影响。而明清之际王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既与其“别开生面”的思想建构密切相关,更与其经历几百年后的汰选、掘发不无关系,更与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趋势高度契合。这种内在的关联确证着船山伦理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学术价值和文化魅力,也印证着船山本人“吾书二百年后始显”①,“五百年后吾道大昌”②的自我预言。
船山伦理思想可谓具有集思想建构与价值传播,特别是为后世提供融可掘发性因素于一体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已开发同时又开发得最为不够,且具有极大可待开发价值的范例或文本。与船山大体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如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帕斯卡尔,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大都提出了颇具世界意义的伦理思想。比较而言,船山伦理思想无论是在思想本身的体系性,亦或观点的深刻性、超迈性,都要高出很多。就船山伦理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理趣甚深而言,堪比康德或黑格尔。就其伦理思想的启蒙意义和人民性而言,亦可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相媲美。就其伦理思想的人本性和主体性而言,似乎可与英国近代格林、布拉德雷的“自我实现论”竞雄。正因为如此,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侯外庐在《船山学案》中均对其有较高评价。从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的个体层面而言,像船山这样主张既超越功利论的不足又超越道义论的局限,既超越群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偏弊又超越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孤陋,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方能胜乎其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船山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之前,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精神实质的伦理思想类型或范式。
二、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确证
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既源于世界伦理文化的深刻需要,又源于船山伦理思想的独特建树,这种建树有着既顺应人类道德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亦能够引领这种潮流,从而使其世界意义亦如船山本人所深切感知和把握到的“五百年后,吾道大昌”的精神自信和价值远瞻。船山伦理思想是中国明清之际“横空出世”的一座精神高峰,有着“汉宋诸儒齐退听”的超拔伟岸之处。就其大者而言,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贵我的道德主体性和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
船山反对“无我论”并提出了“贵我论”,坚持认为自我是道德的主体和依托,“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1]内篇,418。如果道德生活没有了自我和自我道德主体性的支撑,那怎么可能去体认天理和发扬道义呢?须知,无论是体认天理亦或是弘扬道义,乃至珍生务义都必须建立在人的自我道德主体性的基础之上,舍弃了自我的道德主体性或主体的价值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伦理道德呢?“于居德之体而言无我,则义不立而道迷。”[1]内篇,418在船山看来,无论是体认性之理亦或彰显性之德,都需要确立自我的主体地位和弘扬自我的主体性。“性之理者,吾性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论其所自受,因天因物而仁义礼知浑然大公,不容以我之私也。性之德者,吾既得之于天而人道立,斯以统天而首出万物,论其所既受,既在我矣,惟当体之知能为不妄,而知仁勇之性情功效乎志以为撰,必实有我以受天地万物之归,无我则无所凝矣。”[1]内篇,418就此而论,那些倡言“无我”的人其实就是在抽空道德的主体,进而使道德陷入一种无主体的泥潭,本质上不是弘道而是“贼道”。自我是道德生活的主人,自我意识是道德生活之所以能够开展的重要因素。没有了对“我”与道德生活的自觉认识和反思,人就很难真正自觉地体认并遵循道德。积极地体认自我是道德生活的主人,并为之主动去遵行、创造道德,才能既促进道德生活的进步,又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完善。人通过体认、弘扬道德既彰显道德的主体性,又促进人自身的道德化发展,使人由一种自在动物变成一种自为动物,由对道德的自发性发展到自觉性和自由性。人的自我的不断生成和发展,是同人弘扬自己的主体精神、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是人自己弘扬主体性、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价值确证。人能够在弘扬自己道德主体性的同时,不断地自我修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造就一个理想的道德自我。“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则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远矣!”[1]外篇,434船山的“我者天理大公之所凝也”,彰显了个体道德主体性和自为性,与亚里士多德和近代英国格林、布拉德雷的“自我实现论”,及康德的“意志自律”或“人为道德立法”,有着精神实质的一致性。
与“贵我论”相映成趣的是船山“依人建极”的思想。船山“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思想,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亦体现在人与道或德的关系之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既是自然界的产儿,又是作用于自然界的灵性之物,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人类在自己所开辟的天地之中,“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从而开始了人类自己的文明发展历史。就人与道或德的关系而言,船山认为,人是道德的主体而不是道德的客体。如果没有人,贯穿天地万物的“道”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何况“道”功用的发挥还必须“以人为依”。船山还认为“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作为“人之独”的人道能够实现“以人道率天道”,从而弥补天道的不足。这是一种具有“破块启蒙”意义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相比,也丝毫不逊色,而且在“以人道率天道”的视域上有着高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地方。
(二)“理欲合性”的人性论和“人欲之各得”的天理观
船山伦理思想具有世界意义的地方,还在于他对人性作出了颇具近代意义的理论界说,他不仅将人性视为“日生则日成”的“生之理也”,提出了“继善成性”的理论命题。而且就人性的构成和内容,亦作出了既超越自然主义又超越德性主义的理论界说,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的辩证结合。声色臭味之自然属性与仁义礼智之道德属性,都是健康的人所需要的。声色臭味之自然欲望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具有“厚其生”的功能,仁义礼智信之道德属性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具有“正其德”的功能,两者的结合形成健康丰富的人性。船山的“理欲合性说”是对宋儒“性二元论”的批判性超越和创造性发展,他不是将人的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截然对立起来,而是将其辩证统一起来,认识到两者的辩证统一才能形成健康的人性。船山的理欲合性不只是理欲两种属性的和合,而且蕴含着天理寓于人欲之中,人欲之中有天理等要义,即“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2]卷八,911。离开人欲而去抽象地论说天理,乃是佛教“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的谬说淫词,本质上是对人之正当需要的否定,含有后来戴震所言的“以理杀人”。
在船山看来:“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2]卷四,639船山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2]卷四,639的命题,将“各得”的人欲纳入“天理之大同”的道义论谱系加以论证,从而极大地凸显了芸芸众生基本而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绝不是反天理或不道德的,极大地消解了“禁欲主义”伦理思想的合理性,同时又避免了类似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纵欲主义”伦理思想的偏颇和片面性。所谓“人欲之各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正当的尊重和满足,都能各得其所。“人人之独得,即公也。”每一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相应的满足,就是公道公义的实现,天下的公欲其实就是“人人之独得”的汇聚和实现。没有完全脱离“人人之独得”的所谓天下之公理。人们都有食色的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需求,这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基本要素。精神生活及其伦理道德都是建筑于此一基础之上的。“饮食男女,皆性也;理皆行乎其中也。”[3]362真正的伦理道德其实就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其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利益的“各得其所”和“得其当得”。
(三)“生民之生死,公也”的价值设定和“古今之通义”的价值准则
船山伦理思想在价值设定和价值准则上,凸显了“生民之生死,公也”[4]卷十七,669和“古今之通义”的价值内涵,而在“天下为公”的价值设定中又自然而正当地肯定了芸芸众生的生存权益和利益诉求,从而使得“公”成为一个既涵盖无数个人利益又保障个人利益的价值理念,避免了因凸显“公”而否定民众之“私”的公私对立论陷阱,也防范了那种一味地尊崇个人利益而忽略“生民之生死”的利己主义伦理观。船山伦理思想重“公私之辨”,主张“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4]卷末,1177。并提出了“公者重,私者轻”的价值命题,倡导人们自觉地维护公利、公道和公义,强调“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5]519。
但是,船山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强调,又有别于历史上的那种一味地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整体主义或国家主义,它是一种纳“生民之生死”于公共利益评价的民本主义,是一种关注和置重民生福祉的民生主义。船山之“公”,公在为民生利益论证和代言,公在彰显芸芸众生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它不同于西方近代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确立一条鸿沟,也不是一味地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或优越于他人利益之上,而是从聚合、兼顾和平等的意义上,凸显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船山的“生民之生死”是同其“人欲之各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都需要得到尊重和满足。“各得”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而是大家都得到满足。这里蕴含了个人利益对他人利益的同等尊重和兼顾,在价值导向上既不是利己主义,也不是利他主义,而应该是一种“己他两利主义”或“共利主义”。
更有意义的是船山提出了“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6]535的思想观点,实质上提出了关于道义的价值层级论和价值序列论,这就意味着“一人之正义”相对于“一时之大义”而言无疑是私的,而“一时之大义”则是公的,人们在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上应该肯定“一时之大义”而不是“一人之正义”。同理,相对于“古今之通义”而言,“一时之大义”又是私的,只有“古今之通义”才真正具有公共利益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如果我们把“一人之正义”看作一种底线伦理,那么“一时之大义”则是一种中线价值,“古今之通义”无疑是一种“终极价值”或“最高价值”。船山伦理思想,以“公天下”立论批评“孤秦”“陋宋”,认为民族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高于“一人之正义”和“一时之大义”的“古今之通义”,并认为“古今之通义”是最高级的道义和至善,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必须而且应该去努力维护、拼死保卫和世代相传的根本的伦理大义。
(四)“珍生务义”的人生价值论和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
“贞生死以尽人道”是船山人生价值伦理的基本命题,也是其基本价值取向。船山认为:“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7]卷六,1034“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生者,所以舒天地之气而不病于盈也。”[7]卷二,869人的生命是大自然的杰作,人应该珍惜天所赋予人的生命,好好地活着并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人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珍生”的层面上,因为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义”。船山主张把珍生与务义结合起来,并认为这既是“合天德”亦是“尽人道”。“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7]卷二,890“存生之理”和“顺生之几”包涵了“珍生”与“务义”两方面的内容,此即是“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8]363。
船山特别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人的独特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就在于人有伦理道德和对道德价值的追求,认为君子是“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的人物,亦即把讲道德发展到极致的人物。在船山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君子存之,则小人去之矣;不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小人之为禽兽,人得而诛之。庶民之为禽兽,不但不可胜诛,且无能知其为恶者,不但不知其为恶,且乐得而称之,相与崇尚而不敢逾越。人是天地万物之灵,能够“健以存生之理”,“动以顺生之几”,在体天恤道中实现“竭天”“率天”“造天”进而新造自己的性命,并且认为“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普通的百姓也能够率天造命,新造自己的生命、运程,并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船山的理想人格既重建功立业、激浊扬清的豪杰,更重“立德立功立言”有机圆融的圣贤,并认为“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乱世之大权也”[9]479。在一个人格沉沦的时代里,大多数庶民往往是“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四肢而心不灵”[9]479的浑浑噩噩人士。这样的人格既无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严重妨碍了社会道德生活的进步。王船山主张拯救浑浑噩噩的世俗生灵,故此提出了豪杰的人生理想,并认为只有先成为豪杰,然后才能朝向圣贤。王船山强调圣贤与豪杰的统一,圣贤代表的是一种对儒家理念的坚定信仰、对儒家道德的率先垂范、对儒家文化的创业垂统的具有最高理想的人物,是立德、立功、立言合于一体的理想人格;而豪杰则体现为具有勇敢的气质、经世的能力、开拓的精神等特质的英雄人物。人们的道德生活,既需要豪杰,更需要圣贤,是一个超拔流俗而朝向“豪杰”进而向着“圣贤”目标不断前进的过程。
三、船山伦理思想世界意义的独特神韵和影响
船山伦理思想以立乎其大,研精于微和着眼于远,而自成一家之言,其对大道大德、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精湛论述,凝聚成“尽人道而合天德”“贞生死以尽人道”和“以人建极”的人本主义传统,内化成“志道据德”“珍生务义”的尊道贵德主义传统,积淀为始终着眼于“天下为公”并以“古今之通义”为至上价值的道义主义传统,再辅之以继善成性、理欲合性、命受性生的人性论传统。“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的实践伦理学传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信念伦理传统,不仅已经在近代发生了极其重要的“破块启蒙”的作用,而且自会有某种跨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价值魅力,必将对人类伦理文明的行稳致远发挥历久弥新的功能效用。
船山伦理思想“贵我”而重“人极”,将道德主体的自我建构及其以人为本,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杨昌济视船山“我者德之主”的人本主义有着与近代英国格林、布拉德雷自我实现的伦理学暗合或具有精神一致的地方,以此来确证船山伦理思想的近代价值。杨昌济在其著作《论语类钞》中指出:“王船山曰:‘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船山重个人之独立如此。”[10]253认为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为人子对父母尽的孝道,以及为人臣对君主尽的忠道,绝对不只是简单地尽义务,而是体现个体对认同道德法则的自觉践行,是出于个体内在精神自由和道德主体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船山的这一思想与康德将绝对命令内化为个人意志自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即是说,任何客观的道德义务,如果没有主体自身的自觉体认和接纳,很难获得真正的道德价值。只有将道德义务内化于心灵的价值认同,并出于自觉的行为践行时,才有真正的道德意义。这是道德之为道德,而不同于宗教和法律的独特之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杨昌济从王船山重个人之独立性而发展出“贵我论”,并将其与“通今论”合而并论,此即他倡导的贵我通今之相互发明。杨昌济指出:“吾之所谓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意。吾以为是则力持之,举世非之不可顾也;吾以为非则力避之,举世是之不敢阿也。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必国家中多如斯独立之人格,然后此国家对于世界可成为一独立之国家。”[11]246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培养独立之思想,养成独立之人格,才能造就独立之国家,进而推动形成主体性的道德生活。
船山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人性的健康生成与人欲的正当满足和实现,内涵身心健康和谐以及普世与共享等因素,较早地认识到了“人欲之各得”和“人欲之独得”之于天理道义的意义,凸显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相互尊重、相互结合的伦理必要性,有着超越近代英法的功利主义论和德国的道义论,并将其合理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的精神特质。谭嗣同对船山的理欲合性说深表认同,强调没有人欲也就无法发现天理,因为天理寓于人欲之中,没有离开人欲而独立存在的纯粹的天理。船山的理欲观既反对禁欲主义或遏欲主义,又不主张纵欲主义,本质上是主张尊重每一个人都共有的基本欲望,或者说给正当的欲望以合理的尊重,同时对那些非共有的非基本欲望则主张予以必要的范导和节制。这样的欲望观恰恰是近代理性主义伦理观所崇尚和追求的。
船山伦理思想在义利观上既重义利之分,亦重义利之合,凸显出义利并重和以义制利的价值特质。诚如张立文先生指出:“船山希望融合自然的‘正德'与‘厚生'之间的关系,即义中寓利,利中含义;义不离利,利不离义,既说明利益的合道德性,又发明义利的和合性。其间他既主张以义制利,又反对以义灭利;既主张义利相兼,又反对重利轻义。倡导义利相辅相成,融突和合。”[12]367船山的义利观不独对义利关系作出超越前人的深刻论述,更有意义的是区分了不同层级和类型的“义”和“利”,他将“义”区分为“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并借助“公者重,私者轻”分析这三种不同层级“义”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凸显“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价值导向的合理性。他将“利”区分为“生人之用”的共利和“人欲之私”的私利,主张尊重“生人之用”的共利,压制“人欲之私”的私利,亦即在利益的追求、满足和实现中,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有机地联系起来,抵制那种为了一己之私伤害他人利益、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当王船山区分利的不同类型时,虽然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语言,但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与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区分“自爱”与“自私自利的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萧萐父、许苏民认为:“讲清了合理的‘自利'与‘滞于行质'而‘攻取相役'的自私自利的区别,是王夫之的一个重要思想贡献。”[13]357萧萐父、许苏民还认为,就船山“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而言,堪比康德“为道义而道义”的道义论,“而在另一方面,当他强调义利统一、‘利于一己'归根结底对自己‘不利'的观点时,也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又颇接近于18 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爱尔维修等人的观点”[13]360。整体上看,船山的义利观含有超越近代功利论和道义论对立藩篱,又将其合理的思想因素有机统一,这是船山义利学说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所在,也彰显了船山义利学说的高明性和超越性。
船山伦理思想十分重视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及操守、气节的拱立,有着将志道据德与居仁由义结合起来,既推崇豪杰又渴慕圣贤的理想人格论特质。这是一种既立足于现有又改造现有和超越现有的人生伦理学和价值伦理学。杨昌济从船山伦理思想中受到很大启发,总结出人应该是有理想、气节和人格的社会动物。人既需要英雄豪杰的精神气质和建功立业的禀赋,也需要朝向德功言合一的圣贤精神和圆满人格。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曾受老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对船山思想颇感兴趣,他在《讲堂录》中写道:“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14]589毛泽东记录了杨昌济老师对王船山“圣贤—豪杰”型人格的论述,同时还对之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凸显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船山伦理思想的影响经历了由湖南到全国,进而再到全世界的过程。近代湖南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波又一波救亡图存的运动,成为“革命摇篮”和“伟人故里”,是同其发现船山、研读船山,特别是弘扬船山伦理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立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近现代湖湘仁人志士,不仅活化了船山伦理思想,而且也使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获得了本土资源的支持和依托,进而使近代湖南成为中国新思想孕育的热土、新伦理激荡的中心。郭嵩焘在《船山祠碑记》中论及建立船山祠的目的时说:“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又将有人光大先生之业。”[15]1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以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为湖南精神的总代表,其中王夫之地位最尊。维新志士谭嗣同有言:“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6]又说,“衡阳王子,可谓大雅宏达者矣,而其言曰:君子之立论,有不必相通而各自成一道。”③其《论艺绝句》诗曰:“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汪魏龚王指江都汪中、邵阳魏源、仁和龚自珍、湘潭王闿运,他们都是近代开风气的优秀人才。谭嗣同认为,如果要使中国思想文化的天地曙光再现万物复苏,那就要靠像王船山这样的南岳春雷去唤醒。谭嗣同在“南岳一声雷”下自注曰:“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年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16]77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受其师杨昌济先生影响,多次到船山学社去听讲座,并在《讲堂录》中抄有多处王船山语录。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毛泽东一度居住在船山学社,并利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湖南培养了一批志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产主义战士。
近代以来,船山伦理思想不只在湖南,而且在全国都发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指出,王船山的理欲观“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演出”[17]735。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受船山伦理思想影响甚深,他在《说林上》指出:“明季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18]116不仅推崇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豪杰精神,而且将王船山《黄书》视为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源泉。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自固族类,是没有资格谈什么仁义道德的。熊十力自述少年在“身心无主,不得安稳”的彷徨之际“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19]7。船山“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既凸显了我对于“道”的主体担当和价值自觉,也强化了个体生命因弘道而具有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之意义,这些使年少的熊十力深觉人生应有的价值和生命的神圣担当。当一个人将自己与弘道的事业联系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建构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个体的生命因此更具有率天载义、体天恤道的价值意义。熊十力概括船山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20]83-84,可谓确当之论。钱穆曾经指出:“船山言欲不可遏,故非主纵欲也……蓋欲之不可纵,一犹乎其不可遏。惟真知乎性天之道者,则无所谓纵,亦无所谓遏矣。”[21]120-121船山的理欲观既不主张遏欲或禁欲,亦不主张纵欲,而是主张导欲和节欲,亦既尊重和满足正当的欲望或各得的欲望,又对那些非正当的欲望予以必要的范导和节制,使其在天理的范围内活动并接受其宰制与规约。
船山伦理思想,不仅在湖南,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正在产生并且必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德国学者卫尔赫勒的《王夫之思想中的国家与精英》(1968年版),英国学者麦穆伦的《热诚的实在论者:王夫之生平以及政治思想导引》(1992年版),前苏联学者布罗夫的《17 世纪中国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1976年版),美国学者布莱克的《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人与自然》(1989年版)和布拉索文的《理学家的生态人文主义:对王夫之的新诠》(2017年版),法国学者谢和耐的《物之理:论王夫之哲学》(2005年版),日本学者松野敏之的《王夫之思想研究》(2010年版),韩国学者金容沃的《王夫之哲学》(1982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等,以及其他学者发表的关于船山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学术论文,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刘纪璐教授的《王夫之的道德情感论对当代哲学的启示》(《2019年中国(衡阳)王船山诞辰4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日本久和山口的《存在から倫理へ--王夫之「尚書引義」の哲学》,(《东方学》1979年第1 期),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船山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研究。特别是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崛起进程的加快,船山的思想可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受到重视,成为世界研究中国哲学伦理思想的窗口和再造人类文明的重要因素。(本文题目为“再论”者,基于笔者1992年在“王船山逝世300 周年衡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论王船山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时至今日笔者作“再论”,以期在原基础上更一步推进。是否有所超越,请求诸位方家教正。)
注释
①欧阳兆熊撰《王船山先生轶事》有言: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弗能及……先生尝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令子孙藏弆甚谨。参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王船山先生轶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 页。②刘人熙有诗:衡阳王子真天人,遗书万卷妙入神。自诡五百生名世,可有三千拜后尘。并在诗后注曰:王子同县人朱进士松云,述王子之言曰:五百年后,吾道大昌。参阅周寅宾编:《刘人熙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③参阅《船山全书》第16 册,长沙:岳麓书社版,第72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