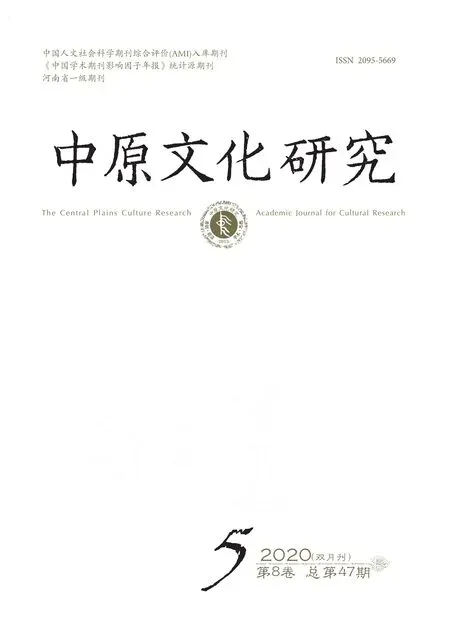“安大简”《诗经》为子夏西河《诗钞》*
2020-01-05张树国
张树国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以下简称“安大简”《诗经》)是目前出土的唯一先秦时期《诗经》楚文字钞本,于近期整理出版,无疑是上古文学研究领域的盛事,与古文经《毛诗》隶变而来的今传本《诗经》相较,存在大量异文,学界出现了很大争议,可以预计会成为《诗经》学乃至上古文学研究的热点①。在此之前出版的“上博一”《孔子诗论》记录了孔子评论《诗经》风、雅、颂的文字,据笔者统计,提到52 篇的篇名,同时也记录了一些诗句,但没有一篇完整文本。“安大简”《诗经》原简自标序号,编号从“一”至“百一七”,除去阙简、阙文外,存诗共57 篇,为传本《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秦风》《魏风》《鄘风》《唐风》,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本《魏风》六篇改题为《侯风》,又将《唐风》九篇改为《魏风》,引起学界热议。笔者将“安大简”《诗经》与学界公认为可信的“郭店简”《缁衣》以及“上博一”《孔子诗论》等篇引《诗》相对照,认为“安大简”《诗经》是可信的出土文献,也发现一些待解难题。有学者认为既然用楚文字抄写,当出自战国楚人之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很频繁,如东周、三晋等北方文献南传而为楚人抄写已非个例,“安大简”《诗经》也不例外,成为新的《诗经》公案。
一、“安大简”《诗经·国风》选本结构及问题的产生
“安大简”《诗经·国风》主要由“六风”组成:
(一)《周南》简20 标注“周南十又一”,与今传本相合。传世本《麟之趾》之“麟”简文中写作“”,很值得注意,后文有说;
(二)《召南》14 篇(简21-41),篇目全。阙文很多,仅《殷其雷》《江有汜》两篇完整。传世本《驺虞》在简文对应位置诗句为“从乎”,为《诗经》首见,后文有说;
(三)《秦风》10 篇(简42-59),篇目全。
(四)阙简60-71,竹简信息完全阙失。
(五)《侯风》6 篇(简72-83),《侯风》之名为首次出现,即今传本《魏风》6 篇:《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整理者黄德宽认为《侯风》可能是《王风》之“误置”,此说存疑。
(六)《甬风》(简84-99),简99 题“甬九白舟”,《甬风》即今传本《鄘风》,当为9 篇。传本《鄘风》10 篇,黄德宽认为“简本《鄘风》九篇不含《载驰》篇”[1]3,是正确的。至于为何没有《载驰》,后文有论。
(七)《魏风》10 篇(简100-117),均为传本《唐风》,无阙简。今传本《唐风》共12 篇,《杕杜》《葛生》《采苓》不见于简本。
“安大简”《诗经·国风》用战国楚国字体抄写,57 篇诗只有《柏舟》《葛屦》两个篇名,其他55篇未标题名,说明当时简本使用者对《诗经》题名稔熟于心,是在《诗经》祖本即全本的基础上进行抄录的,笔者为论述方便,简称为《诗钞》,与隶变《毛诗》而来的传世本出现如此大的不同,看来不是随意的丛钞,而是有选择性的,具有一定功用目的,不能不令人对战国时期类似《诗经》之类经典作品的流传形态产生更多的联想。这个选钞本存在诸多学术之梗,不见于《诗经》学史,成了一连串新的个案,本文梳理于下:
首先,今传本《魏风》六篇何以命名为《侯风》?又为何将今传本《唐风》九篇改为《魏风》?在《诗经》文献中从来没有相关信息,为首次出现。
其次,《诗经》楚钞本除了阙失12 支简的“某风”外,何以只选《周南》《召南》《秦风》《侯风》《甬风》《魏风》六风,而未选其他八(九)风?与传世《毛诗》相比较,次序上出现的新变意味着什么?
最后,除了诸多异文之外,何以不选《鄘风·载驰》《唐风·葛生》等诗?
下面借助于“上博一”《孔子诗论》及一些出土文献探讨《诗经》祖本及“安大简”《诗经》的来源问题,而《侯风》是确定“安大简”《诗经》性质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侯风》源于子夏西河传《诗》
在探讨“安大简”将《魏风》改为《侯风》这个问题之前,笔者据“上博一”《孔子诗论》等相关出土文献探讨一下《诗经》祖本的形成及流传问题,尤其对孔门《诗》学传授及孔子死后弟子散之四方,子夏西河传《诗》问题进行探讨。
“上博一”《孔子诗论》记载了孔子对《诗经》邦风、大夏、小夏、讼的系统解说②,是对《诗经》的最早诠释,标志着《诗经》研究的发端,意义重大。《孔子诗论》为残编断简,失去了多少内容难以估计,其中提到的《诗经》篇名,笔者按照原整理者的简编顺序重新统计,《邦风》27 篇,《大夏(雅)》1 篇,《小夏(雅)》21 篇,《讼(颂)》3 篇,除去有争议的作品篇名外,《孔子诗论》中提到邦风、雅、颂类篇名共52 篇,诗题基本都能在今传本《诗经》中找到出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删诗,将“古者《诗》三千余篇”删成三百五篇,成为《诗经》学史上一大公案。《孔子世家》:
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2]1345
孔子本人未提到删诗之事。《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安国曰:“篇之大数。”邢昺疏引《正义》:“案今《毛诗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内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数。”[3]5346孔子所谓“诗三百”即今《毛诗》传本三百零五篇。“内六篇”为“笙诗”或“笙曲”六篇,即《由庚》《崇丘》《由仪》《南陔》《白华》《华黍》,分别隶属于《小雅·鹿鸣之什》和《南有嘉鱼之什》,《毛诗序》认为六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4]898,实际上“笙诗”属于“标题音乐”,在仪式中与《关雎》《葛覃》《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间歌”交替相续,在《仪礼·燕礼》《乡饮酒礼》中都有记载。从《孔子诗论》52 篇题目来看,孔子所谓“诗三百”与传本《毛诗》隶古定而来的《诗经》文本很接近,是《诗经》学史上的“大传统”。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均以“诗三百”作为祖本,齐、鲁、韩三家以“今文”即隶书传授,《毛诗》为赵人“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以“古文经”传授,二人为赵地河间人,“古文经”载体可能是三晋文字。《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子卒后“七十子”去向及儒术的传播: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2]3786
子夏在孔门四科中以“文学”知名,与《诗经》传播有关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又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2]2676-2677。《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在“卜商,卫人,无以尚之”之“无”字上有疑脱,覆宽永本《家语》有“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习于《诗》,能通其义,以文学著名。为人性不弘,好论精微”之句[5]148。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据此可推子夏生于公元前507年。
据史料记载,子夏籍贯有三说:一是卫人,除《孔子家语》外,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6]160云云;二是温国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卜商”条下,裴骃《集解》:“《家语》云卫人。郑玄曰温国卜商。”司马贞《索隐》:“按:《家语》云卫人,郑玄云温国人,不同者,温国今河内温县,元属卫故。”[2]2676三是魏人,《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章下,孔疏引《仲尼弟子传》“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7]2778云云。以上三说是可以理清的,温国(今河南温县)本为东周畿内国苏忿生之邑,郦道元《水经注·济水注》:
济水于温城西北与故渎分,南经温县故城西,周畿内国司寇苏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周襄王以赐晋文公。[8]636
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勤王,周襄王“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于是始起南阳”[9]3952。自此后温地属晋。据河南学者高培华所论,在“铁之战”后则属魏,子夏出生在春秋晋国温邑,等到“退老西河”之时,则是魏国温邑,绝非西汉诸儒所谓“卫人”说[10]54。
孔子73 岁去世时(公元前479年)子夏29岁。《史记》传注所谓“子夏居西河”“子夏为魏文侯师”当在子夏离开鲁国之后,去了魏国西河之地传授《诗》。“西河”多有异说,钱穆认为当在河济之间的安阳③,高培华则认为子夏“退老西河”就在“温邑”,其地就在齐鲁之士称为“西河之上”的“河济之间”[10]54,这是正确的见解。子夏在《诗经》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传,未有章句。”[11]12子夏为孔子《诗》学嫡系传人,曾作《序》题解《诗经》,“口以相传,未有章句”,表示子夏《诗序》写成以后,儒者基本上用言语传授,而未以“章句”进行解释并书于竹帛。《序录》记载《毛诗》在汉初之前授受之迹,有两条线索,云: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一云名长。校勘云:“长”作“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字子西,鲁人,曾参之子)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郑玄《诗谱》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11]13
这两条线索虽有所不同,但认为《毛诗》源自子夏则是一致的。从孔子—子夏—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构成了《诗经》传授的“大传统”,具有“祖本”地位,子夏就拥有这个“祖本”。竹书写本时代的典籍基本上是单线传播的,“安大简”《诗经·国风》应是在“祖本”基础上抄录改编的钞本,呈现选择性、改编性很强的特点,突出体现为将《毛诗》中的《魏风》改名为《侯风》,将《唐风》改名为《魏风》。就改编的功用效果和直接目的来分析,最大受益者无疑就是战国初年的魏国,这些重大改动是与魏文侯始“侯”之事以及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的经历分不开的。《吕氏春秋·开春论·察贤》:
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12]586
这三人当由魏文侯之弟魏成子引荐,《史记·魏世家》记李克之语,“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2]2225。《韩诗外传》第六章作“此三人君皆师友之”[13]88,“东得”句证明子夏居于“河济之间”的温邑(今河南温县)西河,而非郑玄所说“自龙门至华阴之地”。段干木身世见于《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诱注:“驵,廥人也。”毕沅曰:“《注》廥疑与儈通。”[12]93《说文解字系传》:“廥,刍藁之藏。从广,會声。”[14]192上说明段干木是管理刍藁仓库的小吏出身。《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12]53子夏为魏文侯师,《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2]2223,其西河讲学与魏国宗室尤其是文侯的支持分不开的,杨宽认为子夏“居西河教授当在文侯在位之初期”[15]126。孔祥骅认为子夏开创了“西河学派”,与孔子“洙泗学派”之间存在“亲缘与变异关系”[16],可备一说。
《史记·魏世家》:“桓子之孙曰文侯都。”《集解》引徐广曰:“《世本》曰斯也。”魏文侯之名见于清华简《系年》简116、117:“魏斯、赵浣、韩启章率师救赤岸。”魏文侯在位有“三十八年”及“五十年”两种说法,对其始侯之岁的考定对确定《侯风》问题最为关键。《史记·魏世家》:“三十八年……文侯卒”,《索隐》:“《纪年》云五十年卒。”[2]2226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晋敬公”条下“六年,魏文侯初立”注云:
《史记·晋世家》索隐引“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案《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由武侯卒年上推之,则文侯初立当在敬公六年,《索隐》作“十八年”,“十八”二字乃“六”字误离为二也。[17]599-600
钱穆、杨宽同意王国维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公元前446年)说[18]123[15]122。《史记·晋世家》记晋出公之后为哀公,无敬公,而《纪年》有敬公而无哀公,两者孰是?清华简《系年》简111、112记载:“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戉(越)命(令)尹宋盟于巩遂,以伐齐。”[19]14“晋敬公十一年”为魏文侯五年,可证《纪年》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史记》在叙述战国初年史实时,因为材料不足,难免出现某种疏失。
当魏文侯元年即晋敬公六年之时,子夏62或63 岁在西河讲学,并受魏国宗室厚爱,为魏文侯师,其媚附魏文侯为其制礼作乐也是顺理成章。子夏为高寿之人,其卒年未有确载,高培华依据卜氏族谱提出子夏87 岁、101 岁、107 岁三说[10]69,可资参考。“安大简”《诗经》将《魏风》改为《侯风》,又将《唐风》改为《魏风》,并选择《周南》《召南》《秦风》《甬风》以及完全阙失的“某风”制成魏国新乐,因此“安大简”《诗经》应称为“子夏《诗钞》”,其具体改编年代应是魏斯始侯之年,即公元前446年左右,是为魏文侯制礼作乐服务的,这一历程笔者下文续论。
三、子夏《诗钞》与选诗动机
《礼记·乐记》记载子夏与魏文侯论乐之事,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注谓“魏文侯,晋大夫毕万之后,僭诸侯者也”[20]71,说明晋敬公六年,魏文侯始称“侯”之时并未得到周天子及众诸侯的承认,后来韩、赵、魏三家联手攻打了齐、楚、秦诸大国,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朝于周,获得周天子承认,三家才正式立为侯[21]。魏文侯所以厌倦雅颂古乐,因为古乐所歌颂之神明为周室而非魏家的祖宗。子夏因此对雅颂古乐、郑卫之音以及战国新乐进行了解释。除此之外,子夏特别提到“溺音”:
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20]71-76
“燕女”之“女”当作“安”,楚文字中形近易讹。“安大简”《诗经》没有选录雅颂古乐,没有郑卫之音以及宋音与齐音,这与子夏对《诗》乐的解释分不开的。在《乐记》中,子夏向魏文侯阐述了制作新乐即“德音”的理想,所谓“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同时利用钟、磬、鼗、鼓、椌、楬等打击乐,配合埙、篪、竽、笙、箫、管等吹奏乐以及琴、瑟等丝弦乐器,制作所谓“德音之音”的仪式乐章。在这些“德音”之器外,配合相应舞蹈道具,应用于宗庙朝堂之上,收到宗教政治的效果,“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20]71-76。从《乐记》子夏对魏文侯问乐来看,子夏《诗钞》应是名之为“德音”的魏国新乐诗歌文本。
(一)改《魏风》为《侯风》:魏文侯之新乐
子夏将今传本《魏风》改为《侯风》主要媚附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前身在传世文献中记载很清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中》:“魏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受封于毕,其后国绝。裔孙万为晋献公大夫,封于魏,河中河西县是也,因为魏氏。”[22]2655毕万为魏文侯之高祖,晋献公时始封于魏(今山西省芮城县北)。《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毕万随晋献公灭耿、灭霍、灭魏,后“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将古魏之地封给毕万。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八“魏”条:“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受封于毕,裔孙万仕晋,封于魏,至犨、绛、舒,代为晋卿。后分晋,为诸侯,称王。”[23]1191毕万将古魏变为新魏。魏文侯为毕万之后,三家分晋后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云:
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9]4357下
季札乐评为后人假托,通过赞美《魏风》而美化魏君,而不是讽刺魏君。据研究《左传》“季札观乐”出自吴起。吴起学于子夏,曾为魏文侯重用,为其夺取秦国西河之地,并成为西河守。孔颖达《春秋序》叙述《春秋左氏传》的授受之迹,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9]3695,清人姚鼐《左传补注序》云:“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24]18-19童书业《春秋左传作者推测》认为姚鼐之说“似非妄说”,《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25]354,可能即《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26]187。“左氏”见于《战国策》“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条记载,“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魏赎之百金,不与。乃请以左氏”,注谓“左氏,卫邑”[27]1166。
今传本《魏风》据《诗小序》所云均为“刺”诗,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葛屦》序云:其君俭啬褊急,《汾沮洳》序云:刺俭也。《园有桃》序云:俭以啬,是魏俗俭啬。”[28]1536《魏风》中《伐檀》《硕鼠》公认为“刺诗”,均见简本《侯风》,为什么魏国君臣不怕“刺”,却反而命名为《侯风》呢?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诗小序》后起,出自东汉经师卫宏,当子夏选《诗》之时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美刺”之说;以《魏风》多“刺”是《诗小序》之语,出自后世解经家,并非战国《诗经》所固有。古魏及毕万之后的“新魏”历史上同处一地,“古魏”之风当然成为新魏之国风,而为子夏重新命名为《侯风》。
(二)变《唐风》为《魏风》:以魏代晋
简本《魏风》即今传本《唐风》,“唐”源于古帝唐尧。“唐风”即“晋风”,《唐·蟋蟀诂训传第十》引陆(德明)曰:
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尧、夏禹所都之墟,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晋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为晋,侯至六世孙釐侯名司徒,习尧俭约遗化,而不能以礼节之,今将本其风俗故云唐也。[4]765
孔颖达《正义》:“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4]765《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2]1978以地在唐尧所居之地,故始封君叔虞为唐侯、唐叔;以其地南有晋水,故唐叔虞之子燮父改名之为晋。故《诗》“唐风”实即“晋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云: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28]1536
杜预注:“晋本唐国,故有尧之遗风,忧深思远,情发于声也。”《会笺》引王念孙说,引文“遗民”当作“遗风”[28]1536。那么子夏将《唐风》改为《魏风》意欲何为?主要是为媚附魏文侯所谓“德音”的需要。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其都城安邑即唐叔虞始封地所谓“禹都安邑”者也。当时晋国公室已经全面式微,敬公前任国君晋出公竟然被智伯、韩、赵、魏四卿赶出晋国,死在路上。敬公为智伯所立,韩、赵、魏杀智伯,尽并其地。三家之中,魏文侯最强,分晋以后也承袭了晋称,因此也就无所忌惮了。孟子记载梁惠王之语“晋国天下莫强焉”(《孟子·梁惠王上》),此“晋国”即指魏。但子夏将传本《唐风》九篇改为《魏风》,却未选《唐风》中的《杕杜》《葛生》《采苓》,主要是由于这三首非子夏所谓“德音之音”,如《杕杜》“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葛生》“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为女子哭坟之诗;《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云云,诗句有犯忌之处,自然也就不合“德音”的标准了。
(三)《周南》《召南》:文德之基
“安大简”《周南》11 篇、《召南》14 篇与传本《毛诗》相比,异文较多,最有争议的无疑是《召南·驺虞》之“驺虞”作“从乎”,简40:
传本《毛诗》作“彼茁者葭,一发五豝,于差乎驺虞”,整理者认为“郙”“豝”古音帮纽鱼部,音近相通;认为“驺虞”当从简本读“从(纵)乎”,意谓放纵、放生[1]98,这一说法存在争议。“驺虞”为天子之乐,《墨子·三辩》:“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孙诒让注谓“《书》《传》中‘驺虞’字多作驺吾”[29]24。《驺虞》为周成王所作,因此作为天子大射礼中的专用仪节,如《周礼·春官·大司乐》“王射令奏《驺虞》”,《乐师》“凡射,王以《驺虞》为节”,《钟师》“凡射,王奏《驺虞》”,《射人》“以射法治射仪……王乐以《驺虞》”,《礼记·射义》:“天子以《驺虞》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贾谊《新书·礼》:
《诗》云:“一发五豝,于嗟乎驺虞。”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30]215
可见西汉初贾谊引《诗》尚作“驺虞”。阜阳汉简《诗经》收录《驺虞》竹简图样,据胡平生先生释文,S018 为“豵,于嗟驺虞”,见《驺虞》第二章:“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31]3《驺虞》古已有之,材料多得是,而“从乎”仅见于“安大简”。为什么子夏要将“驺虞”改为“从(纵)乎”?因为“驺虞”是天子之乐,当时东周天子虽已成为名义上的精神存在,但诸侯还是不得不有所顾忌自己的德行。
《周南》《召南》在孔门诗学中占有突出地位,为歌颂周文王“南国之化”的重要作品。但体现子夏《诗钞》“二南”取风之义者,应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9]4356上
周文王为魏氏祖先毕公高之父,而文王之号谥与魏文侯昭穆相同,因此子夏选择“二南”为魏国乐章之首,一方面表达“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之意,另一方面借重季札乐评发挥“始基”之义,媚附魏国初建之文侯功绩。
(四)秦风尚武,立国之本
子夏《诗钞》全选《秦风》10 首。秦立国于两周之际。《史记·秦本纪》记载,当周平王东迁之时,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以秦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2]230。秦襄公为秦仲之子,始建秦国。《汉书·地理志》:“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二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秦风声调见诸《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9]4357上古音夏、雅相通,《诗经》大小雅,“上博一”《孔子诗论》称“大夏”“小夏”。秦国据有西周故地后,秦风具有西周雅乐特征,为王朝正音。秦国立国以后,从秦穆公开始谋求向东发展,但为强晋阻挡,双方展开多次大战,一直延续到战国。《史记·秦本纪》记秦孝公曰: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2]256
秦厉公之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公元前477)子厉共公立”[2]820,《六国年表》“(公元前476)秦厉共公元年”[2]830,《索隐》:“悼公子,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2]837这段时间正是魏文侯斯用事之时,攻夺“河西地”者为吴起,并被任命为西河守。秦国与“三晋”为仇雠敌战之国。“诗钞”选《秦风》意在砥砺志节、思启封疆、不忘仇雠在侧,与《乐记》中子夏论乐一致。
(五)甬(鄘)风即卫风,属国之风
“安大简”84-99 为《甬风》,简99 题“甬九白舟”,“甬风”即今传本《鄘风》,当为9 篇,未选《载驰》。《汉书·地理志下》:“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鄁,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32]1647-1648竹添光鸿《会笺》云:“武王伐纣,分其地为三监。三监叛,周公灭之,更封康叔,并三监之地,故三国尽被康叔之化者。”[28]1533当武王灭商以后,以殷之故地封给纣王之子武庚,在纣城周围设“三监”即管叔、蔡叔、霍叔监管。颜师古注“三监”云:“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庸,东谓之卫。”[32]1648王应麟《诗地理考》:“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武王丧,“三监”与武庚叛,周公东征平定之后,乃封康叔于卫。康叔为武王同母弟,始食采于康,后徙封卫。《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观乐: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29]1533
从历史渊源上来分析,可知《鄘风》即卫风。《礼记·乐记》记子夏对魏文侯问云“卫音趋数烦志”,非“德音之音”,何以选用《鄘风》九篇?这是由战国初期魏、卫两国关系决定的。《汉书·地理志下》记春秋时卫懿公为狄灭后,齐桓公封卫文公、戴公于大河之南曹、楚丘之地,“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32]1647。清儒陈启源云:“郑《谱》谓纣城北为邶,南为鄘,东为卫,楚丘与漕二地皆见《鄘风》,在河南,足征卫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33]81卫自文公、戴公以后居于故《鄘风》之地。战国时期,卫为魏之属国,《史记·卫康叔世家》:“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张守节《正义》:“属赵也。”[2]1939注误,当属魏。《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76年)魏献子”栏下“卫出公辄后元年”,《索隐》:“二十一年,季父黔逐出公而自立,曰悼公也”[2]837;“(公元前450年)魏”一栏中记“卫敬公元年”,《索隐》:“悼公黔之子也”[2]848-849,可见卫国为“三晋”魏国之附庸。子夏《诗钞》选择《鄘风》以代《邶风》《卫风》,主要从卫国迁都所在为周初故鄘地,同时又为魏国附庸国的角度考虑的。值得注意的是,子夏选择《鄘风》中婚姻恋爱甚至是“淫诗”的《墙有蒺藜》(今本作《墙有茨》)、《鹑之奔奔》,但却遗弃了许穆夫人所作《载驰》。这一著名爱国诗篇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即公元前660年,卫为狄人所灭,齐桓公“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9]3880下。《诗序》:“《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4]674诗篇首句云: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4]674
从诗篇可见许穆夫人的爱国情怀,但不一定能入子夏《诗钞》。《诗钞》是在魏文侯始立为侯,正忙着制礼作乐的背景下开始编选的,之所以遗弃《载驰》,主要是由于首句“归唁卫侯”这一“吊人失国”之语有伤及属国之处,同时对新造诸侯国来说也非吉祥之语。
综上所论,“安大简”《诗经》应是子夏为魏文侯师之时,为满足其始侯之际制礼作乐的需要,选编“诗三百”中的“二南”《秦》《魏》《唐》《鄘》等“六风”以及完全阙失的“某风”,将《魏风》改名《侯风》、将《唐风》改为《魏风》,以媚附魏文侯,这个《诗钞》编选时间应在魏文侯始侯之岁。从其积极意义上来分析,表现了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利用古老经典经世致用的精神;但子夏媚附统治者,选编并篡改“诗三百”的行为,背离了孔子《诗》教初衷,尤为正统儒家所不齿。《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晚年“丧其子而丧其明”之后,曾子见子夏并怒斥之:“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孔疏:“既不称其师,自为谈说辩慧,聪睿绝异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与夫子相似。”[7]2777-2778当然尚无法推断这是否与子夏《诗钞》有某种关系。《荀子·非十二子》:“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郝懿行注:“嗛,犹谦也,抑退之貌。”[34]126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荀子所谓“子夏氏之贱儒”当指子夏学派。而“安大简”《诗经》不见于载籍,也未流传下来,主要是出于子夏改羼,缺乏应有的生命力。
注释
①因“安大简”《诗经》新出,此前已有一些文章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7 期;徐在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序文》,《文物》2019年第9 期;李松儒《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对读三则》,《出土文献》2018年第1 辑;姚小鸥《安大简〈诗经·葛覃〉篇“穫”字的训释问题》,《中州学刊》2018年第1 期等。②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③钱穆《子夏居西河在东方河济之间不在西土龙门汾州辨》介绍,“西河”有三说,一为《史记索隐》所谓“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说,郑玄注《礼记·檀弓》谓“西河自龙门至华阴之地”;二为《太平寰宇记》所谓“郃阳、韩城”说;三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之“西河”,在卫地,《隋图经》云:“安阳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12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