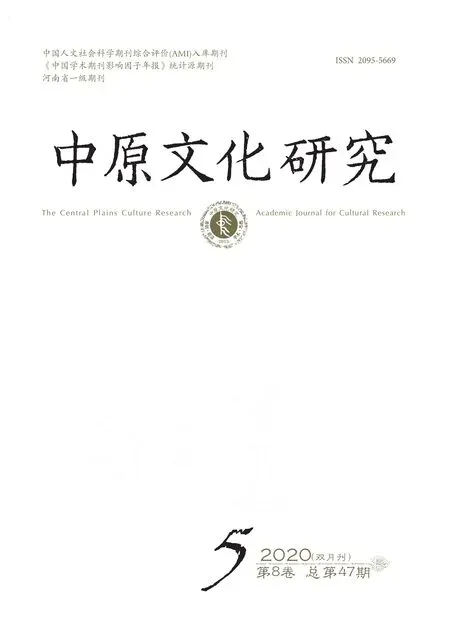胡风浸润:五代时期北中国的胡文化探析
2020-01-05刘广丰
刘广丰
唐末五代,是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在地域上又以北中国为主。其时,中国北方生活着大量的游牧民族,他们不但形成各种政治势力,也在文化上给中原汉族带来巨大的冲击,从而造成当时胡汉文化的冲突。而在这些游牧民族中,对中原影响最大者,当是后来在五代建立了三个王朝的沙陀。沙陀本生活在西域地区,后来在多次迁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沙陀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迁居中原后,汉族文化确实给沙陀共同体内的北方民族带来巨大的影响,从而促使他们出现汉化的倾向①。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北方民族也有自身的文化,这些文化中有些也许在汉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变淡,但有些则植根于民族基因中,这决定了他们不能很快地汉化,或完全融入汉族之中。甚至,在长期的交往中,这些胡文化还会反过来影响并改变汉人的文化。文化的冲突不但表现在族群之间,也会在一些沙陀贵族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一方面想接受汉文化,试图改变自己胡人的形象,甚至改变自己的姓氏和郡望,以求融入汉族文化圈②;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改变不了自身的文化习俗。胡人的习惯,在小至日常生活,大至国家政治决策中,都能体现出来。于是,文化的内在冲突,也是五代沙陀贵族,尤其是沙陀君主的一种特征。
一、沙陀共同体与北中国的胡文化
沙陀自宪宗时来归,至五代时期形成沙陀共同体,融合了北方地区,尤其是河东及代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沙陀共同体中所保留的北方民族文化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沙陀来到中原之时,保留着自身的民族语言。据《新唐书》记载,黄巢之乱时,江西招讨使曹全晟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跟黄巢战于荆门,他们用五百沙陀马匹作诱敌之计,“明日,诸将(贼将)乘以战,而马识沙陀语,呼之辄奔还,莫能禁”[1]6455。这里所谓的“沙陀语”究竟是何种语言,史无明载,不过当时的沙陀共同体已经大体形成,而民族共同体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乃共同的语言。沙陀本身是“西突厥别部”,又与回鹘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共同体内部有大量的突厥人、回鹘人与粟特人,他们的族源大致是相同或相近的。故这种沙陀语,应该是突厥语,或在突厥语基础上发生变异所产生的一种口音。上述的材料也说明,在进入汉人地区70 多年后,沙陀人依然在使用自己的语言。
到了五代,这种北方游牧民族语言依然在使用。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曾经用“胡语”(一曰“边语”)在战场上与契丹人对话③。此外,他当上皇帝之后也喜欢用胡语跟出身游牧民族的大臣谈话,例如康福。根据姓氏,康福可能是昭武九姓胡人,据记载:“福善诸蕃语,明宗视政之暇,每诏入便殿,咨访时之利弊,福即以蕃语奏之。”④首先,所谓“诸蕃语”,似乎表明康福所会的蕃语很多,但事实上,这些蕃语很有可能都是基于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口音,否则以康福一名武将,不可能通晓多种不同源的语言。其次,明宗与康福的对话,大多围绕“时之利弊”,而作为一名武将,康福有何时之利弊能够告诉明宗呢?笔者认为,明宗很有可能是问康福关于治内北方民族的事情,因为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他必须对蕃汉人群作出平衡。由此推测,当时北方民族内部之间的交流应多用蕃语而非汉语,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康福为何非要用蕃语来回答明宗的问话,因为他打探而来的消息大多是通过蕃语而来的,直接讲述总会比翻译准确。在沙陀共同体里面,通晓北方民族语言的也不止康福一个,如李克用的义子李存信“会四夷语,别六蕃书”[2]713,再如后晋时之安叔千,也曾用胡语跟耶律德光对话。胡三省认为:“安叔千,沙陀三部之种也,故习胡语。”[3]9455以此推测,沙陀共同体中多数的北方民族之人,应该都会胡语。
(二)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从某种崇拜中逐渐产生的,它既反映某一族群对于自然的理解,也反映他们对一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沙陀共同体中的北方民族也有其宗教信仰,其中最典型的是突厥神崇拜。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时,曾经“幸龙门之雷山,祭天神,从北俗之旧事也”。而明宗也曾“幸白司马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以及“祭蕃神于郊外”[2]438,525,530。两段文字对比,可以推知庄宗时所谓的天神,应该就是明宗时的突厥神。而所谓“北俗”,应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具体而言,则应该如《周书·突厥传》所言:“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祭祀天神。于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木,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4]910由此可知,突厥对自然的崇拜非常广泛,除首重太阳外,其余山川大泽,均可以神格化而崇拜之。换言之,这种突厥神崇拜,并非一神,而是自然神化后的诸多神灵。史书中对于五代突厥神的崇拜所言甚少,但沙陀统治者山川祠庙的祭祀,却比汉人统治者为多[5]254-355,可见其入主中原后,仍然持续其敬神,尤其是自然神的习俗。当时在沙陀共同体内,突厥人所占的比例不少,其他如回鹘、昭武九姓等,也与突厥的族源相近,故突厥神应该就是共同体内北方民族比较普遍的信仰。
除突厥神崇拜之外,佛教应该是沙陀共同体内尤其是贵族阶层比较普遍的宗教信仰。《宋高僧传》里提到,李克用把一名和尚蓄养于府内,又听从其妾曹氏之言,放其自由[6]145。不但李克用如此,其他沙陀统治者均有交往僧人的表现。如五台山僧人诚慧,不但被李克用封为国师,李存勖即位后,更“诏赐紫衣,次宣师号”[6]692明宗长兴四年(933年)七月,“命中使押绢五百匹,施五台山僧斋料”。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敕:“河阳、邢州潜龙旧宅,先令选名僧住持,宜赐院额。其河阳曰开晋禅院;邢州曰广法禅院。”四年(939年)二月,又因天和节,“僧尼赐紫衣、师号者一百有五,寺宇赐名额者凡二十有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5]550-552。而又据《册府元龟》记载,后唐一朝,从庄宗到末帝,驾幸龙门佛寺祈雨、祈雪的次数甚多[5]1244-1248。
有学者认为,沙陀人笃信佛法,是他们接受中原文化的表现,因佛教乃是中原宗教[7]103-108。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完全正确。其合理之处在于,沙陀贵族所接触的佛教,确实有中原佛教,如上文提及的“开晋禅院”“广法禅院”等,显然就是中原禅宗的寺院。然而,佛教本身并非中原产物,乃来自天竺,而沙陀人进入中原之前,未必就没有接触过佛教。他们在吐蕃生活过十几年,而佛教正是吐蕃的国教。只不过在进入中原后,在佛法鼎盛的大环境下,沙陀人对于佛法的信仰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罢了。沙陀人对于佛教中毗沙天王的信仰,正好说明这一点。《旧五代史·武皇纪》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巵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惟武皇从容而退,繇是益自负。[2]332-333
这种记载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其后的沙陀统治者的经历中,毗沙天王也不断出现。如后唐末帝李从珂在藩邸时,即有人说他“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窃喜”[2]643。再如后晋高祖石敬瑭在晋阳起事,被唐将张敬达围城,援兵未至之时,他就曾向毗沙门天王“焚修默而祷之”[2]988。三位皇帝均与毗沙天王扯上关系,说明对这位佛教神灵的崇拜在沙陀人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而毗沙天王的勇武形象,隐然是崇武的沙陀人王权的象征。据王颋教授的研究,这种信仰最早发源于西域于阗国,后来传播到吐蕃,又来到中原[8]19-36。由此可知,沙陀人对毗沙天王的崇拜,有可能直接源自西域,也有可能在吐蕃时即接受了这种信仰。
此外,一些沙陀君主虽然信仰佛教,但他们更倾向于跟西域、天竺的胡僧交往,而非跟汉族僧人交往。如李从珂“遣供奉官郑延遂往凤翔,诏胡僧阿阇黎”。又石敬瑭时,敕旨:“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卫国大菩提寺三藏陀阇黎赐紫,沙门室利缚罗宜赐号弘梵大师。”其后,“于阗国僧曼哥罗赞常罗赐紫,号昭梵大师”[5]551。由此更加可以证明,沙陀人对于佛教的信仰有多重来源。
(三)其他习俗。除语言和宗教外,沙陀人还保留了很多北方民族的习俗。
第一是扑祭。所谓“扑祭”,是指“扑马而祭”,简单说,就是杀死马匹以作祭祀,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习惯。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人死后,“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4]910。至五代,沙陀贵族也多有以马匹来祭祀的,如晋高祖石敬瑭驾崩后,出帝石重贵“遣右骁卫将军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西山扑祭,用北俗礼也”。而不久,石敬瑭之母刘氏逝世,出帝又“使石德超扑马于相州之西山”⑤。除文字记载外,出土文物同样能够说明沙陀人的这种习俗。考古人员在山西代县的李克用墓中,即发现有马骨存在,这说明李克用下葬时,也有实行这种扑马之祭[9]188-198。
第二是传箭,这同样是缘于突厥人的习俗。据《周书·突厥传》记载:“其征发兵马,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4]910而至唐朝时,西突厥分为十部,亦以箭为信,谓之“十箭”[10]5183。至五代时期,以箭为信的习俗依然保留在沙陀共同体之中,所谓“传箭,蕃家之符信也,起军令众则使之”[2]519,由此可见,箭可以成为军事行动的信物。早在后唐建立前,沙陀晋军围攻幽州刘守光,后者即“遣人传信箭一只,乞修和好”[2]382。再如后晋时,石敬瑭曾“遣内班史进能押信箭一封,往滑州赐符彦饶”[2]1003。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外,李克用“三箭遗誓”的故事一直广泛流传[11]397,说明箭矢除了可以作为军事信物外,也可以作为意志、愿望传递的信物,而且这种信物在沙陀人眼中非常重要。
第三是火葬。在读五代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战争中兵败者往往会引火自焚⑥。自焚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避免尸体被敌方侮辱,但却不能完全解释五代宋初之时,为何多选择自焚。如后唐兵败,末帝李从珂自焚,一起自焚的还有明宗皇后曹氏。但曹太后的亲生女儿乃石敬瑭之妻,即便她要与国家共存亡,作为女婿的石敬瑭也不会侮辱她的尸体。故此,笔者认为,这应该跟北方民族,尤其是西域诸族的葬俗有关。跟中原流行土葬不一样,西域民族往往喜欢火葬。《宋高僧传》云:“西域丧礼,其太简乎?或有国王酋长,倾心致重者,勿过舁之火葬。”[6]44西域诸国中,采用火葬的国家甚多,如回鹘北面之结骨(又称黠戛斯),其人死后,“刀剓其面,火葬收其骨,逾年而葬”[12]1784。再如突厥,其人死后,亲属除扑马祭祀外,还“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4]910。沙陀贵族在进入中原之后,是否有延续火葬的习俗,史无明载。相反,沙陀帝王若非兵败身死,大多都是采用土葬的。然而,明宗之女、石敬瑭之妻李氏的经历说明,在五代沙陀人里依然存在着火葬的习俗。契丹兵南下后,李氏与出帝石重贵等后晋皇室俱被掳至契丹,她在契丹病重时曾说:“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在她去世之后,确实是被火葬的。石重贵的生母安太妃也说过相似的话:“当焚我为灰,南向飏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其死后则是“毁奚车而焚之,载其烬骨至建州”,也是火葬[11]179,180。由此可见,沙陀人尽管入主中原成为统治者,但他们的火葬习俗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感叹道:“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而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11]125这虽然是出于其华夷之辨的成见而故意夸张的说法,但也说明,五代沙陀三王朝中的胡人并没有彻底地汉化,他们与中原汉人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如此,胡文化反而在某些方面影响并改变着汉文化的面貌。
二、沙陀集团的胡文化认同
沙陀人在西域的时候,一直以游牧的方式生活。自沙陀金山之后,沙陀首领一直担任金满州都督,所谓金满州,乃“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10]1647。进入中原后,他们也没有立即摆脱游牧的生活方式,于是,范希朝“为市牛羊,广畜牧,休养之”[1]6155。后来他们所居住的代北地区,自出雁门关后,一马平川,有广阔的草原地带,至今仍有大量的牧民在那儿牧羊。李克用的一位义儿李存信,即被称为“代北牧羊儿”[11]142,可见在唐末五代之际的沙陀人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方式。即便是后唐建国、首都定于洛阳后,沙陀统治者依然认为羊马为其生存之根本。庄宗李存勖曾对左右说:“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2]1200明宗李嗣源也说过“某蕃人也”[14]2454这样的话。由此可见,尽管沙陀统治者采用了汉族姓名,甚至第一个沙陀王朝号称继承了唐朝正统,但他们依旧认同游牧文化,并且认同自己“蕃人”的身份。
有很多讨论沙陀汉化的论著,都会引用一个例子,以说明当时北方胡人对汉人身份的认同。据《旧五代史·康福传》记载:
(康福)在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衾而坐。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2]1201
据此,作为胡人的康福并不喜欢被称为奚人,当然,康福也不是奚族人,而认为自己是唐人。在今天的语境中,唐人往往与汉人相通,故研究者很容易以此认为康福不承认自己胡人的身份,而主张自己是汉人。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史料中所载之事发生在康福镇天水(即秦州)之时,当在后唐清泰年间,而后唐奉唐正朔,故康福此处所指之唐人,乃指沙陀统治下的后唐之人,而非汉人。事实上,康福本人十分想成为沙陀人,在上引文之下,有另一个故事云:“复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2]1201其对沙陀之倾慕溢于言表,而这也更加说明,他所认同的身份是沙陀。这一点得到欧阳修的确认,在《新五代史·康福传》中,当康福听到“锦衾烂兮”之语时,他的回应是:“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11]515康福并不是孤例,同样的例子还有李克用的义儿李存孝,原名安敬思,应该属于中亚昭武九姓胡人,但在一次战争中,他自称“沙陀之求穴者”⑦,可见他对沙陀身份的认同。
胡人认同胡文化以及自己蕃人、沙陀人的身份,本身就说明五代时期的北中国胡风盛行,尽管胡人汉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但他们汉化的程度则有深有浅。甚至,有一些汉人在长期接触胡人之后,反而认同了部分胡文化,产生了汉人胡化的现象。在沙陀政权的蕃汉军中,由于长期共同的军旅生活,汉人将士被勇悍的胡人同化的现象十分明显。例如霍彦威,他是汉人将领,也曾长期服务于后梁,投降沙陀之后,他即沾染胡风。天成二年(927年)十月,明宗亲自率兵讨平汴州(今河南开封)朱守殷之乱,事后,霍彦威使人进箭一对以作祝贺[11]506。如前所述,传箭乃突厥之俗,霍彦威身为汉人将领有此行为,只能说明他不但认同这种习俗,而且以之为荣;若再深究其根由,则可知传箭之俗在当时的蕃汉军中甚为盛行。
中国北方地区胡化,除了对唐末五代的军事、尚武精神及军队蕃汉混杂等现象有影响外,还涉及到其他方面,比如胡人文化对中原血缘伦理关系的冲击。如李克用所收养的义儿,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汉人,他们“衣服礼秩如嫡者六七辈”[2]367。其中李嗣昭更是以汉人身份,成为李克用的“元子”,被写在后者的墓志铭中⑧,这是一种血缘拟制,在传统的汉人文化圈里是非常少见的⑨。在后唐统治者的义子当中,胡化程度最高的,应该是李嗣源的养子、后唐末帝李从珂。他本姓王,为镇州平山人,其母魏氏于景福年间被在平山作战的李嗣源掳掠为妾,而李从珂也因此成为李嗣源的养子。由于长期跟随养父李嗣源生活于戎马之中,李从珂作战也相当勇悍,庄宗李存勖就曾经说过:“阿三不徒与我同年,其敢战亦类我。”[11]71可以说,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以及身边的胡人兵将,给李从珂这个汉人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大的。他后来在凤翔起兵造反时,即“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到达长安后,又“率京兆居民家财犒军”。即位称帝后,他又“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赏军”[2]628,632。所谓“率”者,乃“括率”之意,亦即搜刮。李克用时代曾经纵容兵士在战争中掳掠地方百姓[3]8692,这是北方胡人惯常的行为,此时李从珂搜刮三地百姓的财物赏军,与李克用之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政府的搜刮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当然不及纵容士兵掳掠,但如此一来,士兵的欲望又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们造谣云:“去却一菩萨,扶起一条铁。”[2]634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闵帝李从厚小名为菩萨奴,但军士们以此作比喻,认为他仁弱如菩萨,而新帝李从珂则刚严若生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李从厚即位时不过二十岁,《资治通鉴》对他评价云:“闵帝性仁厚,于兄弟敦睦,虽遭秦王忌疾,闵帝坦怀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无嫌,而朱弘昭、孟汉琼之徒横生猜间,闵帝不能违,以致祸败焉。”[3]9243从此评论可以看出,李从厚其实是一忧柔寡断之人。他虽长期被明宗外放于藩镇,但却因年纪尚小,几乎未曾经历战斗,缺乏一种领导者的气质。李从珂则不然,他久经战阵,杀伐果断,如康义诚、孟汉琼等人,即便投降,他也毫不犹豫地杀掉[3]9240,9241,9244。李从厚跟李从珂的差别,还可以从他们面对失败时的表现看出来。当大势已去之时,李从厚选择逃离京城,而此举实际是放弃自己的正统及根据地。李从珂则不然,清泰三年(936年)当战事不利后,他即在京城自焚而死,与后唐共始终,而随之焚毁的还有后唐的国玺[11]187。无论如何,李从珂保存了自己的正统。就上引事例而言,身为汉人的李从珂比流淌着沙陀血液的李从厚更像一个沙陀武士。无怪乎傅乐成先生认为,李从珂的“气质盖已同于胡人矣”⑩。
必须指出的是,五代北方地区汉人对胡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并非单纯因沙陀人入主中原,事实上,从唐朝中后期开始,这种现象就已经发生。比如河东北部的代北地区,在沙陀人到来之前,就已胡汉杂居,当地“纵有编户,亦染戎风,比于他郡,实为难理”[14]72。这足以证明,此地的胡化程度早就已经很高了。不过沙陀人的到来,确实也加深了北方地区的胡化现象。河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太原在唐中后期时与代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同书对太原地区风俗记载云:“其人有尧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嫁娶送死,例皆奢靡。”[14]69这说明,至少在沙陀人入主太原之前,这里依然信奉儒家思想,而贵族们也缺乏胡人刚强直爽的豪气。然而,自李克用率沙陀人入主太原之后,北方胡人的势力也深入河东地区的核心地带。而随北方胡人而来的,当然包括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至北宋太宗时,北汉政权依然存在,且建都于太原,宋人直接称其为“沙陀”,可见其俗与中原汉族之异[15]9124。至徽宗时,河东地区依旧保存火葬之俗,说明这种与汉人“例皆奢靡”葬俗不相符合的胡人之俗一直保留在民间[16]652。
除上述现象外,五代中国北方在政治与社会上的胡化现象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五代皇帝多为军阀起家、枢密使权重于宰相,以及五代礼崩乐坏等等,均是胡化现象的表现[17]。这说明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人胡化不应被忽视。不过文化的融合是双方互动的,胡人汉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也非常突出,而这种胡化与汉化交相出现的过程,也让一些北方民族统治者出现了内在的文化冲突。
三、统治者内在的文化冲突——以后唐庄宗为例
中国历代汉文化与胡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在农耕文明中,农民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下,才能有效生产。若国家分崩离析,战乱频仍,即便风调雨顺,也有可能颗粒无收。故此,稳定是汉文化圈最为珍视的状态,所有文化、道德与价值观,都是为这个状态服务的。游牧文明则不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该文明下的民族、部族有非常大的流动性,他们的生存空间并非固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然而,当他们去到另一个地方想要落脚生存时,就不得不面对当地的部族——如果不能打败对方,他们将不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同样,他们也随时面临着外来的挑战——保卫已有的空间,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侵略与被侵略,已然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与此同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他们为生存而斗争的对象。因此,武力就成为他们最尊崇的价值,因为在这种随时准备竞争的空间里,武力决定一切。于是,他们所有的文化、道德、习俗也都服务于这种尚武的价值,如突厥人的“贱老贵壮”,沙陀人的“左老右壮”,都是一个道理[4]909,[1]6156。再如唐末年,李克用纵容沙陀军队侵暴河东良民,这在汉人看来当然是破坏稳定的生活环境,是极大的罪恶,但在沙陀人看来,却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方式[3]8692。
入主中原后,胡汉文化的冲突不但表现在外部,统治者自身也有内在的文化冲突。沙陀统治者与其他北方民族有所不同,他们以避难者的身份进入中原,而在势力不断发展之后,又以汉人唐朝为正统建立自己的政权,故他们不得不塑造自己的汉人形象。对内,他们表现出对汉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在外交上,他们宣称自己是汉人,也称自己建立的政权为中国。然而,由于骨子里的胡文化早已根深蒂固,两种文化在统治者内在的人格里发生碰撞,使之成为文化的冲突体。最典型的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从表面上看,他在沙陀统治者中汉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不但略通《春秋》大义,还通晓汉人的诗词歌赋,并且热爱汉族的戏曲文化。然而,骨子里的胡文化,却让名为后唐君主的李存勖表现得更像一个胡人。
第一,他崇尚武力,好战。这种好战不是喜欢发动战争,而是喜欢那种沙场杀敌的兴奋感觉。在梁晋争霸的时候,李存勖常常亲自率兵赴前线作战,这是胡人酋长常做的事情。对于胡人部族而言,首领的作用就是身先士卒,带领部族抢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李存勖的祖父朱邪赤心,就常常在敌阵中出生入死地战斗,被誉为“赤马将军”;而他的父亲李克用更是十五从军,威震天下[2]332-333,[1]6156。李存勖同样在很年轻地时候就随父亲出入于战阵之间了,他作战非常勇猛,曾让后梁太祖朱温嫉妒不已:“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豕犬尔。”[2]369此时的李存勖虽未称帝,但却俨然一方势力之首领,在传统汉族文化的观点看来,承担更为重要责任之人亲自上阵杀敌乃是以身犯险,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资治通鉴》记载了一次战场上的对话,充分体现出汉人与胡人之间对于君主或首领在战斗中所起作用的不同看法。天祐十五年(918年)晋军大举南下,与梁军在杨刘(今山东东阿北)对峙。李存勖几次亲自率兵挑战,但都遇到危险,差点丧命。知道消息后,他的盟友王镕与王处直均来信劝他说:
元元之命系于王,本朝中兴系于王,奈何自轻如此!
李存勖笑对使者曰:
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
很明显,王镕与王处直所看重的,是统治者的责任,李存勖一旦因战争而殒命,则推翻朱梁,复兴唐室无望矣。但对于李存勖而言,天下必须是打出来的,而且得自己打,这本身就是一种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居帷房以自肥”是他嘲讽王镕的话语,然而对于汉人而言,君主应居中运筹帷幄,冲锋陷阵是将军们的事情。类似的话李存勖手下的汉人大将李存审也跟他说过[3]8956-8957,他的观点其实跟王镕等人一样,身为领袖不宜轻出作战,以致身蹈险境。然而,李存勖已经把战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正是游牧文化中尚武精神的体现。
第二,李存勖的一些个人爱好,也与尚武精神有关,例如狩猎。狩猎必须掌握骑马、射箭甚至搏斗等技能,而大规模的狩猎也需要众多狩猎者之间的相互配合,这些都跟军事作战有关。故此,游牧民族也会把狩猎作为军事训练的活动。李存勖之父李克用就曾以强悍的狩猎者形象出现在史书中,据《旧五代史》记载,他在一次狩猎中“连贯双雕,边人拜服”[2]333。由此可见,北方民族对于某一英雄人物的信服,乃源于其武力,而狩猎则是武力的表现方式之一。李存勖作为李克用之子,本身也非常热爱狩猎。据《册府元龟》之记载统计,从他建立后唐至其败亡,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狩猎的次数达到19 次之多[5]1261。以狩猎作为娱乐休闲的方式,其实并无不可,因此历代帝王,无论胡汉,基本都会有狩猎的活动。然而,在汉族士人看来,这种休闲方式不宜过多,尤其是对于皇帝,因为君主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政务上来。然而,后唐建国后,庄宗已经没有多少御驾亲征的机会,战场上杀敌的快感只能在畋猎场中获得补充。故此,在他眼里,狩猎比政务、民生等都重要。同光三年(925年),水灾严重,两河地区,流民布道,就连士兵也不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往往殍踣”,“百姓愁苦,号泣于路”,但即便面对这样的局面,庄宗还跟刘皇后“荒于畋游”,而且为了狩猎,还“责民供给,坏什器,彻庐舍而焚之”[11]145。
除狩猎外,庄宗还喜欢打马球(击鞠),这是一种需要在马上配合的运动,故此也很受北方游牧民族欢迎。据研究表明,唐代西域已经很流行这种运动[18]。沙陀人喜欢打马球的习俗不知是否源自西域,因为至唐朝时,马球已成为贵族们喜爱的休闲运动,无论是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还是远至幽州、荆州等地,均有毬场⑪。打马球如果只是作为一种休闲运动,当然不会引来非议,然而,当马球运动与中原礼仪发生冲突时,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则被突显出来,庄宗自身内在的文化冲突,也被表露无遗。据记载,庄宗在邺都(今河北魏县)即位时,经占卜,认为魏州毬场吉利,于是在那里建起了“即位坛”。延至同光三年,庄宗再幸邺都,定州王都来朝,于是他决定毁掉即位坛而重新复原毬场,以备打球之用。当时的邺都留守张宪上奏曰:
即位坛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风燥雨濡之外,不可辄毁,亦不可修。魏繁阳之坛,汉汜水之坛,到今犹有兆象。存而不毁,古之道也。[2]912
庄宗起初也同意另外修建毬场,但久久未能建成,眼见王都将至,他一怒之下,下令毁掉即位坛而复原毬场。这个故事透露出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在庄宗即位时,欲沿用汉族礼仪,故有在毬场建即位坛之举,这可以说是他慕求汉文化的表现,“祭接天神受命”,也算是一种政治拟制。但另一方面,两年后当他重临邺都之时,却一意满足自己打马球的欲望,而忽视礼仪,更不迷信所谓的不祥之兆,这又是其游牧文化的体现。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庄宗喜欢汉文化只是表面的,有些汉文化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但他对另一些文化的遵循则只是出于政治需要,他根子里认同的,依然是游牧民族的胡文化。
第三,轻视农耕文明。庄宗乃是以李唐皇室的身份建立后唐的,政治拟制以及正统传承均要求他接受汉文化,并维护农耕文明;然而,骨子里的胡文化认同,则让他处处表现出游牧民族的本性,甚至从心底轻视农耕文明。上文谈到的狩猎,如果偶尔为之,是一项有益的休闲运动,但经常性的狩猎,则是胡文化的一种表现,庄宗恰恰就是如此,而且在狩猎过程中,他对农耕的藐视表现无遗。据记载,当时广州人何泽为洛阳令,“庄宗出猎,屡践民田”,于是何泽伺机劝谏庄宗曰:
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敛疲民以给军食。今田将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赋,吏何以督民耕?[5]6292,[11]647
何泽的话明确告诉庄宗,在农耕社会里,庄稼是政府大部分的收入,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依其而运转,皇帝本就“暴敛疲民”,如果还“恣畋游以害多稼”,则租赋无所以出,百姓也不愿耕作。如此一来,社会就会动荡,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就会动摇。畋猎与民田,这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直接碰撞,一个“屡”字,说明庄宗这种因狩猎而破坏民田的事情没少发生。何泽的劝谏得到庄宗的正面回应,从而停止狩猎。但更多规谏、建议则被无视,劝谏者甚至有性命之忧。中牟县令就曾因庄宗游猎破坏民田而挡马切谏,差点被庄宗杀掉,幸得伶人敬新磨以诙谐之语慰解庄宗,才得幸免[11]399。同光二年(924年)五月,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奏言事,其中有云:“请择隙地牧马,勿使践京畿民田。”但得到的回应是“皆不从”[3]9044。马是游牧民族的显著标志,也是他们主要的作战工具。从薛文昭的奏章看,当时朝廷牧马已损害京畿民田⑫,这又是一次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但庄宗依然选择藐视后者。尽管他已经是中原之主,并继承汉族李唐的法统,但他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
余 论
五代乃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彼时北方民族不断汉化,但汉人同样也接受并认同某些胡人文化。事实上,当沙陀王朝尚未崩塌之时,他们依旧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而作为统治民族,沙陀人的习俗多多少少也会影响生活在北方的汉人。胡风浸润的一个表现,就是沙陀统治者对胡文化的认同,并由此导致他们内在的文化冲突,当中最突出者,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不管是否出于政治需要,庄宗对某些汉文化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他喜爱汉人的诗词戏曲,也愿意采用唐朝的一些政治制度。然而在本质上他的文化归属依然是游牧文明之下的胡文化,故此,他依然认为自己就是蕃人。在尚未建立后唐前,他的胡文化优越感可以在战争中得到满足;在建立后唐后,胡人的性格让他未能以稳定发展为目标,反而耽于田猎与享乐,甚至破坏民田,忽视民生,用人为政倒行逆施,不但不受汉族百姓待见,同时也得罪了赖以崛起的武人军功集团,导致他享国三年,即被推翻。可以说,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庄宗身上完全失去平衡,并造成激烈的冲突,让他无所适从。相较而言,后唐第二位皇帝李嗣源尽管也认同胡文化,但在游牧与农耕的平衡上,他比庄宗做得好的多[19]。
胡文化不但出现在五代沙陀王朝中,而且沙陀人的一些文化习俗,也可以在宋代的社会文化中找到痕迹,如火葬之俗。当然,宋朝政府是反对这种葬俗的,因为这违背了儒家厚葬的伦理,这本身也是文化冲突的一种体现[16]652。当然,若得到政权的支持,文化的流行也会变得相当迅速。众所周知,宋代饮食中,羊是最主要的肉食[20]58-61。据史料记载,宋朝宫廷“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并将之规定为祖宗家法[21]16。之所以能够成为祖宗家法,乃因从宋太祖开始,赵氏皇室的宴饮即喜欢用羊肉。如赵匡胤宴请从吴越来朝的钱俶,即以羊作“旋鲊”,“至今大宴,首荐是味,为本朝故事”[22]107。一些学者把宋代吃羊肉的习惯,归因于政府推动、传统羊文化的影响,以及宋人对羊食用及医药价值的推崇[23]。这些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宋代并非中国第一个汉人王朝,为何“尚羊”的饮食习俗单单出现在宋代而不是之前的朝代呢?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北方民族的文化入手。宋太祖一家乃出自五代沙陀集团,他父亲赵弘殷曾侍后唐庄宗麾下,自己也在唐明宗时出生于“洛阳夹马营”,成年后,在后汉时随郭威征讨李茂贞[15]1-2。由此可知,赵氏一家长期生活在沙陀人的军旅之中。而沙陀人的饮食,恰恰是以羊为主食的。唐庄宗曾言:“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2]1200马是作战工具,羊则是生活必需。赵宋建国之后,朝廷大臣中尚有很多河东、代北之人,北方民族之人也不在少数,故此,羊作为主要肉食的习俗,也被赵宋皇室继承下来,这种口味的改变,本身就是汉人接受胡人文化的结果。
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单线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先逐渐形成适合于中原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吸收融合适合于中原文明的其他外来文化。文化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时代的发展、空间的突破,本身也是促成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而融合与冲突,则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今展示于世的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几千年来各民族文明融合的结果,而这种过程也将继续。五代时间虽短,北中国的空间也有所局限,但其时以沙陀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与汉族的融合,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路径,相信也能为今天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带来启示。
注释
①关于沙陀汉化,可参见王旭送《沙陀汉化之过程》(《西域研究》2010年第3 期)和《论沙陀的汉化》(《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 期)、李鸿宾《沙陀贵族汉化问题》(《理论学刊》1991年第3 期)以及任崇岳的《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及其措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 期)。不过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者都只是论述沙陀为统治中原地区而采取的汉化措施,而未能提及胡汉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傅乐成《沙陀之汉化》(载氏著《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虽然提到李从珂胡化的问题,但其主旨,还是逐个挖掘皇帝的汉化措施。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载《文史哲》2005年第5 期),探讨了五代的民族融合和宋初民族色彩的淡出,而“语境消解”的概念,也为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角度。王义康《沙陀汉化问题再评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 期)指出,沙陀并非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汉化,他们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习俗和习惯。樊文礼《“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 期)从汉人的角度论述了五代士人对沙陀人的认同及其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②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另文论述,详见拙论:《唐末五代沙陀汉化问题再探——兼论沙陀政权的民族政策》,将刊发于《中国与域外》第四辑。③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5《明宗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85 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70,贞明三年八月甲午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939 页。④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第1200 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6《康福传》,第514-515页。⑤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一》,第1068 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9《出帝纪》,第90 页。⑥如后唐末帝李从珂,在被石敬瑭围攻之后,自知不能退兵,即“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燔于玄武楼”。再如后晋时安从进造反兵败后,也是自焚而死。又如后汉李守贞据潼关而叛,兵败之后,“举家蹈火而死”。至宋初,扬州李重进、泽州李筠等,均是兵败“赴火死”。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8《末帝纪下》,第668 页;卷98《安从进传》,第1305 页;卷109《李守贞传》,第1441页;脱脱:《宋史》卷1《太祖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 页。⑦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53《李存孝传》,第714-715 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58,大顺元年九月壬寅条,第8523 页。⑧见卢汝弼:《故唐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晋王墓志铭》,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6 页。⑨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也的确有收养义儿或养子的习俗,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于传宗接代的,而第二种,则是与五代义儿相似的情况:官宦之家招收义儿以增强实力,如三国时候吕布之于董卓、刘封之于刘备。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家主与家将之间的关系,而所谓的血缘拟制,只不过是为了增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无独有偶的是,无论是吕布抑或刘封,他们攀认义父的行为,均不被时人认可,或直接被敌对的政治家利用。如王允即曾对吕布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而孟达也曾经至书刘封曰:“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肉而据权势,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也。”其后,吕布杀其义父,而刘封为义父所杀,可见他们关系之疏离,更遑论如五代某些义儿养子那样,继承家业地位,或至少进入义父的核心集团。见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7《吕布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0 页;卷40《刘封传》,第992-993 页。⑩参见傅乐成:《沙陀的汉化》,载氏著:《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38 页,尤其是第332 页。⑪参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10《宴享二》,第1197 页;卷177《姑息二》,第1969 页;卷196《建都》,第2192 页。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页。⑫笔者在史书中没有找到庄宗在京畿地区养马的明确记载,但有记载说他明确委任康福为马坊使。《旧五代史》没有交代康福养马的地方,而只是说李嗣源为乱兵所逼而背叛之时,康福正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牧马。而《新五代史》则直接认为康福养马的地方是相州。此外,康福为朝廷养马的规模不小,《旧五代史》说他为明宗资助了几千匹马,而《新五代史》则认为是两千匹。河南地区属于中原核心地带,主要以农耕为主,如此大规模养马,对田地的破坏是可想而知的。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第1200 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6《康福传》,第5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