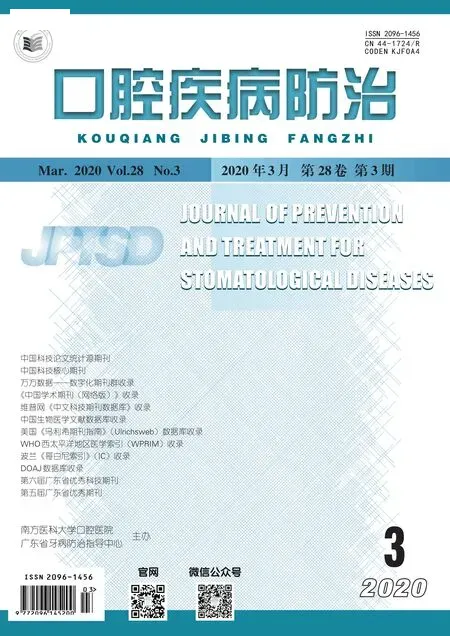口腔微生物与食管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2020-01-04王春萌洪丽华王渝张志民
王春萌,洪丽华,王渝,张志民
1.吉林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吉林 长春(130021);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内镜中心,吉林 长春(130021)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有两种常见的病理分型,即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大多数食管癌患者在就诊时往往已达到末期,因此致死率很高,在大多数国家,食管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15%~25%[1]。引发食管癌的风险因素有很多,包括饮食习惯、营养状态、BMI指数、吸烟、饮酒等[2]。然而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食管中微生物的情况也可能成为风险因素之一。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对食管微生物的研究已证明食管不是一个无菌的场所,但细菌数量较少,且种类与口腔中细菌相似,因此推断食管细菌的来源可能是吞咽引入的短暂停留的微生物[3]。但随后的研究又证实食管的细菌不是仅仅从口腔中吞下的临时菌群,而是一个能够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独特的固有菌丛[4]。食管微生物如何与宿主进行相互作用,口腔微生物在其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能够通过检测口腔微生物的变化来防治食管癌,研究者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本文将口腔微生物与食管癌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 口腔微生物与食管微生物
口腔是人体微生物种类最复杂,数目最多的部位之一。当微生物群落与宿主处于平衡稳态时,在外源性致病菌的入侵时起到生理性屏障作用;关系失衡时可诱发多种感染性疾病。更为重要的是,口腔微生物可作病灶,与全身系统性疾病关系密切。而食管因其在解剖结构上便与口腔相连续,所以在微生物组成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口腔微生物的影响。
食管与消化道其他部位不同的是,它并不能存储食物,而是食物从口腔到胃的一个通道,这也就导致其细菌在数量和种类上要远远低于肠道——食管和胃的内容物每克含101个细菌,而到结肠及肠道远端每克含1 012个细菌[5]。随着检测技术手段的发展,Pei等[6]通过对正常食管进行16s rDNA鉴定,鉴别出6门共95种细菌——厚壁菌门(69.6%),拟杆菌们(20.2%),放线菌门(4.3%),变形菌门(2.2%),梭杆菌门(2.2%)以及TM7门(1.4%)。虽然口腔与食管中的细菌种类与基本一致,多为链球菌、普氏菌、韦荣氏球菌,但由于该研究是对正常个体的食管分别进行鉴定且每个个体的鉴定结果基本一致,说明食管中的菌群并不仅仅口咽部细菌的定植,而是一个具有稳定特点的生物群落。
食管的细菌多样性降低与食管鳞状异常增生有关。食管内微生物种类更少的个体更容易发生食管鳞状上皮异常增生。然而,Yu等[7]所进行的横断面研究不能区分究竟是由于食管中微生物丰富度的降低导致了癌的发生还是仅只是对癌的发展有影响。食管细菌多样性的作用,还需要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证实。不仅仅是食管中微生物被证明与癌的发生发展有关,口腔的细菌多样性降低也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有关。Chen等[8]研究发现食管鳞状细胞癌受试者唾液的细菌多样性与对照组相比总体呈下降趋势(P<0.001)。这说明在食管癌发生及发展过程中,食管中细菌多样性受到口腔菌群影响,而菌群多样性下降的原因以及在恶性肿瘤发生中如何作用仍需进一步探讨。
2 口腔常见微生物与食管癌关系
2.1 牙周红色复合体
已有临床随访研究表明,牙周炎与食管癌的发生存在一定关系[9],那么,作为牙周病主要致病菌,红色复合体,即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福塞坦氏菌(Tannerella forsythia)与齿垢密螺旋体(Treponema denticola)是否对于食管癌的发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呢?
Narikiyo等[10]在对20例食管癌组织进行检测,在16SrDNA特异性PCR扩增的产物中,45%为齿垢密螺旋体,日本、中国、法国及意大利食管癌组织中齿垢密螺旋体检出率为38%~46%。Peter等[11]对81例食管腺癌及25例食管鳞癌患者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并设立健康对照组,通过16SrRNA基因测序鉴定口腔细菌,结果发现福塞坦氏菌的丰度与食管腺癌的发生高度相关(95%CI:1.01~1.46),牙龈卟啉单胞菌的丰度与食管鳞状细胞癌相关(95%CI:0.96~1.77)。且在PLCO试验中的患者,口腔牙龈卟啉单胞菌,福塞坦氏菌,齿垢密螺旋体的丰度与食管腺癌相关。
食管癌中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相关检测是近几年来才逐渐开展的。2016年,Gao等[12]通过免疫组化实验以及荧光定量PCR检测发现,在食管癌组织中,牙龈卟啉单胞菌的检出率(61%)、其主要毒力因子牙龈蛋白酶(gingipains K,Kgp)的表达率(66%)以及16SrDNA的检出率(71%),均远远高于邻近组织及正常组织。此外还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在食管癌组织中的存在,与癌的分化程度、淋巴结的转移以及TNM分期呈正相关关系。2018年,Gao等[13]对96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50例食管炎患者以及80例健康人群的血清牙龈卟啉单胞菌lgG和lgA抗体水平进行了测定和评价,发现食管癌中这两种抗体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抗体水平的高低与食管鳞状细胞癌的预后密切相关,两种抗体水平均高的患者预后最好。
2.2 草绿色链球菌
草绿色链球菌是人体的重要正常菌群之一,常分布于上呼吸道、胃肠道和女性生殖道,以口腔分布为最多。草绿色链球菌包括5个主要菌种:变异链球菌(S.mutans)、血链球菌(S.sanguis)、唾液链球菌(S.salivarius)、轻型链球菌(S.mitis)和米勒链球菌(S.milleri)。大部分草绿色链球菌的菌种都可从口咽部检测到。
早在1998年,Gagliardi等[14]就揭示了草绿色链球菌(Viridans streptococci)是正常食管最主要的细菌之一。到2013年,Norder等[15]通过对40名健康个体的口腔及食管黏膜的拭子样本和活检样本进行体外培养及半定量检测,确定草绿色链球菌在食管中的检出率高达95%~98%。且虽然口腔细菌数量高于食管,但在细菌种类上是高度相似的。作为厚壁菌门之一,它占据了食管细菌总量的39%[6]。
Sasaki等[16]在对15例食管癌组织中的咽峡链球菌进行了Southern印迹杂交和PCR检测,Southern印迹杂交显示11例阳性(73%),而PCR则检测到14例阳性(93%)。随后,Morita等[17]采用实时定量PCR的方法对食管癌和口腔癌中的咽峡链球菌进行检测并设定检测值为10 ng以测定其感染程度。18个食管癌样本中有8个(44%)达到可检测指标,而38个口腔癌样本仅有5例(13%)达到可检测指标,且食管癌中咽峡链球菌的基因水平明显高于口腔癌,最高值达到口腔癌中咽峡链球菌水平的10倍。此外,他们还发现食管癌患者唾液中咽峡链球菌水平也高于健康个体[18]。Narikiyo等[10]在对20例食管癌组织进行16SrDNA特异性PCR扩增的产物中,45%为齿垢密螺旋体,25%为轻型链球菌,12%为咽峡链球菌,10%为群集链球菌,5%为化脓链球菌,而在正常组织的扩增产物中,55%为轻型链球菌,20%为齿垢密螺旋体,13%为咽峡链球菌,5%为唾液链球菌。此外,在对中西方国家食管癌患者16SrRNA基因检测中,食管癌患者咽峡链球菌的检出率在69%~91%,证明食管癌组织中的咽峡链球菌并非独立存在于某一人种。并且,它们能够通过引发炎症反应和促进肿瘤进程发挥作用,施行根除治疗有可能降低肿瘤复发率。
链球菌在食管癌中的作用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研究,2017年,Nayfe等[19]首次报道了1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食管黏膜破裂,鳞状细胞癌引发菌血症,随后发生中间链球菌脑脓肿的病例。这进一步证明,草绿色链球菌广泛存在于食管正常组织和病变组织中,但是否在恶性肿瘤中发生促进作用,仍需更多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2.3 具核梭杆菌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是革兰阴性专性厌氧菌,是口腔中最常见的常驻菌之一。
近几年,学者们发现具核梭杆菌与食管癌也有一定关系。2016年,Yusuf等[20]报告了22个具核梭杆菌感染病例,其中有17例具核梭杆菌是唯一可疑致病菌,7例为原发性恶性肿瘤,而其中3例为食管癌,1例在诊断为具核梭杆菌感染后30 d内发生死亡。Yamamura等[21]对具核杆菌与食管癌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食管鳞状细胞癌300例,食管腺癌12例及其他类型13例行定量PCR检测,23%(74/325)的样本中检测出具核梭杆菌DNA且食管癌组织中表达水平远远高于正常食管黏膜。此外,具核梭杆菌DNA阳性率与肿瘤分期明显相关,并与癌症特异性生存率显著相关(HR=2.01;95%CI:1.22~3.23;P=0.003 9),具核梭杆菌阳性患者比阴性患者的肿瘤特异性生存率低。因此,具核梭杆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评价食管癌预后的生物学标志。此外,该团队利用DNA微阵列数据进行的KEGG富集分析,表明以上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具核梭杆菌的数量与趋化因子CCL20的表达相关,它可以通过激活食管癌的趋化因子,增加肿瘤的侵袭性[5]。该团队最近的研究是将20例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与20例正常食管组织进行石蜡包埋后进行qRT-PCR检测,其中5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1例正常食管组织检测到了具核梭杆菌[22]。虽然目前已有的研究还很少,但还是能够说明具核梭杆菌与食管鳞状细胞癌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至于具核梭杆菌是否是致癌因素还是仅仅起到促进作用,通过何种机制进行作用的,还需要更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以及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3 微生物对食管癌可能的作用机制
目前,对于微生物与食管癌机制的研究较少,但学者们发现,食管癌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增多,其产物脂多糖及内毒素等可能参与了宿主的固有免疫过程[23]。脂多糖作为一种免疫活性成分,激活核转录因子NF-κB经典炎症信号通路,引起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IL-8、TNF-α表达增加;它还可激活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和环氧酶(cyclooxygenase,COX),降低食管下括约肌蠕动频率,增加食管癌患病风险[24]。其中,诱导iNOS和COX-2表达的通路可能从触发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开始。TLR是一种跨膜非催化性蛋白质,可以识别来源于微生物的具有 保 守 结 构 的 分 子。TLRs1、TLRs2、TLRs3、TLRs4、TLRs5、TLRs6、TLRs7、TLRs9均可在食管上皮细胞中表达,这可能与食管癌的生长转移有关[23]。由于目前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并不多,对于口腔相关微生物对食管癌的研究也仅停留在相关性研究方面。因此,要想进一步通过监测口腔细菌来预防和治疗食管癌,并通过相关机制来寻找治疗靶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4 结论与展望
人类宿主和细菌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各种微生物与宿主之间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体[25]。在消化道中,平衡的细菌种群能够健全黏膜免疫系统,维持内环境的稳定。因此,在维持正常的生理环境和进行正常的生理功能过程中,食管菌群平衡的改变可能引起食管疾病甚至食管癌。
食管癌是消化道最严重的恶性肿瘤之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食管癌发病率有显著差异。虽然尚不明确细菌感染和食管癌之间的联系,但以上研究表明口腔菌种的感染可能会导致某些高危人群发生食管恶性病变[26]。然而,以上的研究缺乏对于二者因果关系的探讨,因此要想明确某种口腔细菌对于食管癌的作用,均需要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追踪病变进展过程中微生物组的纵向变化,并且通过干预手段实现对菌群变化的监测[27]。此外,还需要在流行病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和生物信息学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学科合作,以加深对口腔微生物组和癌症风险关系的理解。针对口腔细菌在食管癌致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将有助于对疾病的深入认识,通过对相关标志细菌水平的检测评估患者的患病风险,病变程度以及预后情况,有利于临床策略的制定以期得到更好的食管癌临床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