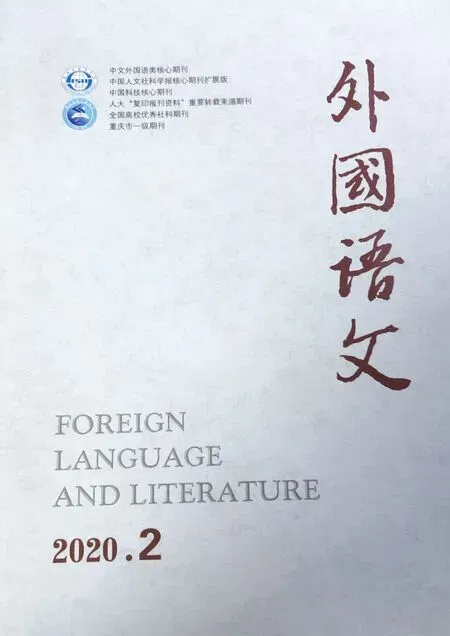论爱伦·坡《厄舍府的倒塌》中罗德里克的理性崩溃
2020-01-03方志彪
方志彪
(海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0 引言
欧洲认知文学批评的代表Michael Burke和Emily T. Troscianko在《认知文学科学》一书中指出了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批评的双重任务: (1)换一个维度去关注很可能业已成型的问题;(2)用开拓的视野去促进新问题的产生 (2017: 1-2)。换句话说,认知诗学一方面用认知的方法对现有的文学问题或者结论重新解释,探究原因背后的缘由,另一方面发现新的形式和意义,发现和探讨文学的新问题。本文选取第一个维度,从认知生态批评的角度解析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厄舍府的倒塌》。对于这部经典的短篇小说,很多研究聚焦主人公罗德里克·厄舍的“神经不安”“精神错乱”“歇斯底里”等症状形成的原因。尚必武认为原因是“其理性解体,非理性占了上风”( 2005:64),唐伟胜认为原因是“物的力量战胜了理性”( 2017:7)。本文则从认知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从社会认知和寻路认知两个维度,分析“物”(既包含房屋、树木等物理环境,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剥夺了罗德里克的理性,导致他与厄舍府一起崩塌。
1 认知生态批评观——心智与环境的互动
认知文学批评发展至今,已经建立起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修辞学等多个范式,认知生态批评也作为理论工具出现,《厄舍府的倒塌》就是这种认知批评的重要对象之一。该小说有一个显著的文本现象:爱伦·坡认为短篇小说创作应该“不浪费一个字”,但却使用大量篇幅对厄舍府外部和内部环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唐伟胜,2017: 7),由此可见环境在该文本世界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该故事强调“物”的灵性,这种灵性不是自发产生,而恰恰是人类意识、认知的投射,非人类的环境因为人的存在和行动才有灵性。对于环境描写较多的文本而言,运用认知生态批评范式予以分析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其核心在于探究心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
生态批评是一个外延宽泛的词,总体上指的是以环境为导向的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 (Buell, 2005:138)。虽然生态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种严肃文学的分支学科以来,与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批评范式一样具有政治责任,但是与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生态批评的焦点在非人特性上,其他学派的关注点则落在人类本身(Easterlin, 2012: 90)。在美国认知文学批评理论家南希·伊斯特林(Nancy Easterlin)看来,虽然生态批评与其他最近的一些学派一样,呈现出未被承认的、生机主义价值观(activist value)与知识特权(intellectual prerogatives)之间的冲突,生态批评还面临一种特殊的挑战——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问题(90)。传统的生态批评关注文学与环境,但只是把环境看作人类活动的背景,并刻意回避人的意识和心智问题,而伊斯特林提出认知生态批评范式,把环境与人看作一个统一体而非对立物,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性,二者的地位是等同的。从深层次讲,传统的生态批评理论重心在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认知生态批评理论强调进化和心智的认知过程。
伊斯特林建构认知生态批评范式的核心目的之一在于说明:对人类心理和进化机制的了解是建立在对与非人类实体关系的动态、连贯描述的基础之上的;要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形成连贯统一的描述,既要理解这种关系的流动性、多变性,还要理解建构、表征环境过程中人类感知、认知、体验的核心作用。这是认知生态范式的认识论基础。伊斯特林一直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心理学文献被传统的生态批评所忽略 (93)。这一点也是认知生态批评竭力纠正的,因为很多心理学成果可以运用于生态文学研究,如环境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等。生态批评的话题,包括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以及景观研究(landscape studies),均可从心理、意识、感知、认知等角度切入。伊斯特林认为,既然认知批评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对非人类的自然世界价值的认识并增强人类尊重自然环境的意识,那么探讨心智与非人类之间自然而积极却又麻烦的关系,则可以阐明人类对环境态度(热情、关爱、厌恶、冷漠)的形成原因,这非常重要(93) 。简言之,伊斯特林构建的认知生态批评的观点是人类关系和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环境的态度。反过来讲,人类对环境的认知又会影响人际关系及社会认知能力。
2 罗德里克社会认知能力的丧失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指的是“让一个人理解人际世界、按照人际世界的要求行动并从中获益的过程和功能”(Corrigan et al., 2010: 3)。“心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的建构物。”(Leidhmair, 2009:184)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总是与他人、与社会产生关系,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人的心智也具备社会属性。之所以将社会认知纳入认知生态批评,原因在于伊斯特林对于“环境”的外延提出了新的见解。认知生态批评把环境定义为“感知自我以外的所有人和事物”,非我的他者皆为环境,人类意识、社会和自然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环境已经上升到了前景地位,所起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烘托人物的意识,而是直接具备了主体性意识(agency),有了自己的身份。
从认知生态批评的环境观来看,《厄舍府的倒塌》的情节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人物——“我”、罗德里克以及罗德里克的妹妹玛德琳小姐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该文本中的环境包含物理环境和人际环境(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物理环境指的是厄舍府的室外场景和室内摆设等;社会环境指的是罗德里克与“我”以及与玛德琳的亲疏关系。在开篇,叙述者“我”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厄舍府的感受: “不知为什么,一看见那座房舍,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不堪忍受的抑郁……望着眼前的景象——孤零零的房舍、周围的地形、萧瑟的垣墙、空茫的窗眼、几丛茎叶繁芜的莎草、几株枝干惨白的枯树——我心中极度的抑郁真难用人间常情来比拟,也许只能比作鸦片服用者清醒后的感受:重新堕入现实生活之痛苦、重新撩开那层面纱之恐惧。我感到一阵冰凉、一阵虚脱、一阵心悸、一阵无法摆脱的凄怆、一阵任何想象力都无法将其理想化的悲凉。究竟是什么?我仔细思忖。是什么使我一见到厄舍府就如此颓丧”(9)(1)本文所引用的爱伦·坡短篇小说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的中译文均选自《爱伦· 坡暗黑故事全集(上)》,曹明伦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9-23页。。从嵌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角度看,心理现象既与人类内在的神经系统有关,又与身体和环境有关。在以上引文中,“孤零零的房舍、周围的地形、萧瑟的垣墙、空茫的窗眼、几丛茎叶繁芜的莎草、几株枝干惨白的枯树”等多重负面消极意象并置起来,直接刺激人的神经,内嵌于人的大脑,触发身体和情感的剧烈反应。这种环境让心智正常的叙述者“我”都无法忍受,对于本已精神分裂的罗德里克而言,更是雪上加霜,让他难堪重荷。认知人类学家斯蒂芬·卡普兰(Stephan Kaplan)和蕾切尔·卡普兰(Rachel Kaplan)指出,人对环境中的意象形成的反应表明了一种自我在场景中的投射。不单单是某些意象(起伏的土地、树、水、悬崖和动物、其他的人),还包括这些意象之间的关系,都能触发一种特定的情感-认知反应(Easterlin, 2012:122)。此场景中并置的意象——房、树、窗的悲凉与阴森是叙说者“我”恐惧情感的投射,更预设了主人公消极的情感-认知反应。
在刚进入厄舍府不久,叙述者“我”对于宅院这个环境意象与居住在里面的人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 “想到这宅院与宅院主人公认的特性完全相符,想到这两种特性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可能相互影响,我不禁认为,这是这种家业和姓氏都一脉单传的结果,最终造成了两者合二为一……在当地乡下人的心目中,这名称似乎既指那座房舍,又指住在里面的人家”(10)。宅院与主人公特性完全相符,身份上合二为一。叙述者“我”认为是“家业和姓氏一脉单传的结果”,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在认知生态观看来,这种统一的根本原因是环境与人共享身份(a shared identity)。环境与人的共享身份关系还有多处体现。在论及绘画时,爱伦·坡这样描写:“画面表明那洞穴是在地下极深处,巨大空间的任何部分都看不到出口,也看不见火把或者其他人造光源,使整个画面沐浴在一种可怕的不适当的光辉之中”(15)。这里的环境描写暗示主人公没有出路,没有光线就没有希望,他内心只能是暗黑一片。这里印证了“我与他之间越来越亲密的相处使得我越来越深入他的内心深处,也使我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我想让他振作起来的一切努力都将毫无结果,他那颗仿佛与生俱来就永无停歇地散发着忧郁的心,把整个精神和物质世界变得一片阴暗”(14)。 自然环境本可以成为人摆脱恐惧、焦虑和忧愁的媒介,但是厄舍府的环境,已经具备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这种身份与居住者的身份结合为一体,也就不具备让罗德里克摆脱困境的功能。
在故事中,自然环境的压抑与人文环境的疏离共同作用于人物,二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具备同一性,共同塑造人类主体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自我感与环境捆绑在一起,自我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对环境的感知”(Easterlin, 2012: 124),反过来,环境又会左右人类情绪与感知。人类环境的疏离,长期的孤独,唯一亲人长时间被病魔缠绕,无法与之交流,加上焦虑,让痛苦的罗德里克无法自拔。 “虽然他犹豫再三,但他还是承认那种折磨他的奇特的忧郁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一个更自然而且更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在这世上仅有的最后一位亲人,他多少年来唯一的伴侣,他心爱的妹妹长期以来一直重病缠身,实际上也已病入膏肓。”(13)两个病人本应该共患难,通过彼此内心的交流来寻找慰藉。但是,爱伦·坡笔下的玛德琳小姐和罗德里克没有说过一句话,留给后者无限的孤独。这种失去亲人的孤独感直接导致其家园感的丧失。根据人文地理学家Antonio Cristoforetti的考查,“家园包含并且完成个人的自我形象和身份感。家园是一种现实结构的主要固定参照点。因为与身份、秩序、根、依恋、私密和安全相联系,家园不光是提供一种支撑,而且是定义自我过程中的一种转变场所。这种观点有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和进化研究的支持”(Easterlin, 2016: 230-231)。亲人之间没有交流,无法形成人类生存所需的家园归属感,无法形成对心智健全、健康有利的依恋感,其结果必然是主体身份弱化,没有能力去同环境互动,没有能力形成个人健康必须的根本条件,罗德里克成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被动接受者。这种被动反过来作用于人际关系,剥夺他正常的社会认知能力。
罗德里克虽然患有心理疾病,其理性(认知)能力并未完全丧失,内心深处知晓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能够帮助他康复。但是,他没有选择主动地改善与邻近环境(immediate environment)的互动,即在厄舍府改善与妹妹的交流,而是舍近求远,试图通过“我”这位朋友来缓解症状,治愈疾病。在给我的信中,他说“极想见到我这个他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知交,希望通过与我相聚来减轻他的疾病”(10)。但是事与愿违,因为“我”对罗德里克知之甚少,虽然“我”答应前往,但是也只是“听从了这个我认为非常奇异的召唤”(10)。由此可以推定,作为社会环境一分子的“我”与罗德里克并未形成可以充分信任和依靠的稳定关系,双方都不具备读解对方的心智能力,即一种能够理解自己以及周围人的心理状态的能力,这些心理状态包括情绪、信仰、意图、欲望、要求与知识等。这种能力的缺失,使“我”的到来成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我”的登场没有帮助罗德里克恢复理性,充其量也只起到了延缓其崩溃的作用。
3 罗德里克寻路能力的丧失
“寻路”一词为凯文·林奇在《城市的形象》一书中首次提出,指的是主体在城市环境、景观中构图及确定方向的行为(Tally, 2013: 71)。伊斯特林将寻路纳入认知生态批评,解释文学人物旅行导航过程中的认知过程。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总是以寻路者的身份感知环境,获取环境信息以及评估与他者交往的能力。寻路能力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社会关系和物理处所中协调自我,为自我构图的能力(Easterlin, 2012: 142)。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共同作用于人的心智。伊斯特林在分析《藻海无边》时指出,心理失向(psychic disorientation)的一个维度就是感知失常,表现为不能依托语境对环境的感性印象和理性判断进行理解(Easterlin, 2012:144)。罗德里克心理失向的第一个表现是感知受损。爱伦·坡对于罗德里克的感知能力作了如下描述:“一种病态的敏锐感觉使他备受折磨,他只能吃最淡而无味的饭菜,只能穿一种质地的衣服,所有花的芬芳都令他窒息,甚至一点儿微光都令他的眼睛难受,而只有某些特殊的声音以及弦乐器奏出的音乐才能不会使他感到恐怖。”(13)伊斯特林指出,丧失了对自己感知能力的信任会导致心理紊乱以及自我与他者(人类他者和物理环境)边界的崩溃,其结果是人正常生活所需的认知建构过程丧失(Easterlin, 2012: 138)。主人公的感知虽然敏锐,但是已经有病态趋势,变得不可靠。味觉、触觉、视觉异常,只有特殊的声响才能维系他的听觉。这种病态的感知显然无法让他自信,所以他对“药物治疗不抱希望”,这种结论也必然引起他认知建构能力的丧失。
叙事能力丧失是罗德里克寻路心智受损的另外一个表现。伊斯特林指出:“人类是一种寻路的、跨越远距离却又是以家为中心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叙事能力(narrativity)因为其主体力量而一直保持着充满活力的状态:为思维和社交构型,成为人类成员之间的纽带,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规划移动。”(Easterlin, 2012:139)换句话说,人类通过叙事来获取知识、评估环境、规划行动。叙事是生存之本,是寻路、导航的基础。在《厄舍府的倒塌》故事的开头部分,罗德里克的叙事能力比较正常,能够“快活而热情地对我表示欢迎”“向我谈起邀请我来的目的,谈起他想见到我的诚挚愿望,谈起他希望我能提供的安慰”。但是,叙述者“我”逐渐发现他“断断续续、语义含混的暗示”,看出了他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接着,罗德里克“不再关心或者完全忘了他平常爱做的那些事情,现在总是匆匆忙忙、歪歪斜斜、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19)。说话语义含混说明叙事能力已经退化,这导致了罗德里克漫无目的地在多个房间走动,表明其寻路导航能力遭到破坏。到故事的高潮部分,即“我”给罗德里克读兰斯洛特爵士的《疯狂的约会》时,他精神极度紊乱,“嘴唇在颤动,仿佛在无声地念叨着什么”,后来“突然疯狂地一跃而起,把嗓门提到尖叫的程度,仿佛正在做垂死挣扎”(23)。这些情节说明,罗德里克不仅自己无法理性地进行叙事,而且连接受别人叙事的能力都已经丧失。从认知生态的角度看,这是“叙事运动破坏导致人类基本生存模式崩塌”的症状(Easterlin, 2012:138)。
身居厄舍府的罗德里克寻路能力的下降和叙事能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心理创伤症状,若要修复这种创伤,必须通过记忆等认知手段给空洞的空间赋予意义,将其转换为场域(place),即负载人类意义的处所。创伤学家Michael A. Godkin指出,对于克服消极的自我感知和无根感,场域记忆的重要性尤为明显(Easterlin, 2017: 840)。 场域记忆的唤起,一方面需要在环境中主动地重塑自我形象和身份,因为物理环境往往是自我的延伸;另一方面,需要环境中的他者投入情感,与创伤者形成情感共鸣(emotional resonance),以唤起积极的记忆元素。故事中的厄舍府,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是一种衰败的形象,人类的情感和记忆早已抽空,而罗德里克弱化萎靡的心理状态业已找不到走出阴霾的方向,至亲的妹妹玛德琳也无法帮助其恢复场域记忆。伊斯特林说:“人类系统的断裂会给危险的物理环境施加更强大的能量。”(Easterlin, 2016: 240)罗德里克遭到破坏的寻路能力和叙事能力将原本断裂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恶化,其必然结果是加强了“危险物理环境”——厄舍府的破坏力量。这种力量压制着罗德里克的情感,扭曲其理性,让他始终束缚于这种枷锁之中直至崩溃。
4 结语
罗德里克社会关系的破坏引起其社会认知能力的缺失,厄舍府这一物理处所又持续不断地对居住其中的人施加邪恶的影响,双重束缚的夹击让罗德里克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局。他在空间中找不到方向,无法协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丧失了正常心智所拥有的构图能力,丧失了寻路认知能力。最终结果是罗德里克感知和情感的认知能力在厄舍府这一空间中产生了移位,环境吞噬了他的理性,毁灭了他认为“不过是一种很快就会逐渐痊愈的神经上的毛病”这种幻想,让他倒在了注定会坍塌的厄舍府的残砖碎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