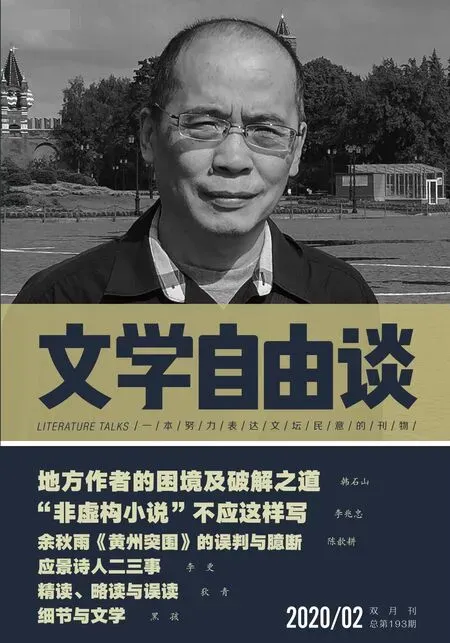绕得远及其他
2020-01-02肖舜旦
□肖舜旦
在2020年第1期的《文学自由谈》,读到一篇我觉得很“绕”的文章,就是李更的《走得近及其他》(以下简称“李文”)。
何以说“绕”呢?就是看过之后,只感觉作者绕来绕去,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当然,不明白就不明白吧,碍你什么事?可又有些不甘心,因为文章里提到了王安忆以及她的如同“天书”的长篇——《匿名》,而我偏偏对这部小说有不少困惑,也就很想看看作者的具体观点,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启发。不料,李文有时明明绕到了王安忆,绕到了《匿名》,不知怎的又转瞬闪了,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无奈,只好再三捉摸。这实在有些郁闷。
李文开篇第一句“走得近并不完全属于开后门”,围绕“走得近”就说开了,可谓开门见山。文章从“走得近”是一个“褒义词”开始正面说理,然后再反面立论,列举了一些文艺圈里“走得近”的反面例子,又落到了“怎么进入文学史”上,而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必须与那些评论家、文学史的编写者以及“作协主席副主席”等“走得近”。
叙述到这,似乎并不“绕”,李文确实在中规中矩议论“走得近”的问题。接下来,提出了一个设问:“有没有完全不在乎这一切的作家呢?”作者回答道:“有。”并引出了王安忆和她的《匿名》。读到这里,我有些懵了:原来,前面的“走得近”全是铺垫,主体应该是写了一部“别人读不下去的书”的王安忆!
随后,李文又详细介绍了那则百度新闻的主要内容——关于《匿名》质疑争议的“罗生门”现象。看得出来,李文对《匿名》的印象不错,认为这些质疑争议虽然不免有些负面的成分,但对她作品的营销起到了较好的广告作用。
文章到这里,已经接近五分之四的篇幅了,可我还是没看到李文对《匿名》的正面表态,只是从这段话里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旅行者提起来,巴黎有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伦敦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王尔德,而上海,有我们的王安忆。”——怎么样?真有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意思了。只可惜,没有分析说理,只怕难以服人,更不要说,这个结论崇高伟大得让人难以置信:王安忆竟可与雨果、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诸大师相提并论?
在文章剩下来的五分之一强的篇幅里,我很希望看到李文对于这个论断的一些起码的分析说明,但没想到李文却依然“绕”兴不减,费了好多笔墨,才又“绕”回到王安忆,给《小鲍庄》《长恨歌》挑了毛病。到了最后,李文峰回路转,“绕”到了一个新境界:“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安忆彻底抛弃了她的小清新,抛弃了让读者有阅读快感的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描写,变得越来越大师状了。”
这不免让人莫名其妙:王安忆在李文中的角色定位怎么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一番思考后,我似乎明白了一些“玄机”:大概“小脚老太”是说《小鲍庄》《长恨歌》,而“越来越大师状”的,则是《匿名》。
为什么《匿名》是一部有“大师状”的作品,李文并没有起码的分析说明。如果从李文结尾的断语来推测,难道只要是“彻底抛弃”“让读者有阅读快感的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描写”,写成了一部“别人读不下去的书”,就可以算是“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本”了?就算是一位“成熟”的“大师”了?
如此“大师”,如何服众?如此定性,岂不荒唐!
我以为,《匿名》是不是一部“大师状”作品,它让人“读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只需挑几个简单的问题来讨论一下,就应当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本质特点。
关于《匿名》,王安忆曾多次在媒体上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比如她坦承:“这次我的这个小说,确实是一个野心”,“我很想写一种文明的再生,文明的循环和周期状态”。她还说过,在写作过程中,她的教授同事陈思和一直鼓励她“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甚至可以“写大段的议论,不用照顾读者的心情,不管读者是否能读得懂”。可见,《匿名》的创作“野心”,确有些“大师状”的初衷,但定位却不免有些“失策”,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主题过于宏大艰深,而自我感觉却良好无匹,膨胀自大,只剩唯我独尊,视读者如草芥蚁虫了。
为了写出所谓的“文明的再生,文明的循环和周期状态”的主题,王安忆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一黑道团伙绑架了一位老人,但事后发现老人是无辜的。怎么办?放回去吧,担心事情败露,干脆杀人灭口。但执行者于心不忍,手下留情,擅自把他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山荒野,让他自生自灭。王安忆打算通过这位老人在原始山野环境中的独立生存过程,来体现“文明的再生”主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实在过于轻率幼稚了。
关于文明的产生或再生,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就是:一种文化、文明的产生——哪怕是一个细微的文化习惯或文明约定,也需要一个基本的群体融合以及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概念不说要以千百年计,至少也得几十年的积累才有可能产生吧?鲁宾逊当年在荒岛上生存了二十多年,也没谁认为他在那里再生了一种文明,而这位老人被绑架后“失忆”了,只不过独自在山里生活了一个冬天而已,怎可侈谈“文明的再生”?
如果从真实的现实生活角度看,可以说整个故事纯属胡编乱造。试想,来自大上海的一位六十七岁的老人,没有任何野外生存经验,突然间被丢弃到与世隔绝的荒野大山中,几乎没有任何食物储存,没有一件冬衣,连一个可供安身避难的山洞都没有,只有原先山民留下的几堵残垣破壁暂时栖息。因为地形太险恶诡谲,如同迷宫,老人根本走不出去;这也是黑道人物把他扔在这里自生自灭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老人如何生存下去?小说中写到了下雪、冻雨这些恶劣的天气,他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怎么可能如作者想象的那样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开始了所谓人类的“二度进化”,开始了一种生物由“单性繁殖进化到双性繁殖之后,再继续进化到单性繁殖”这样一种“文明的再生,文明的循环和周期状态”的科学进化历程呢?如果不是作者异想天开的“哲人”狂想,老人早就应该尸骨难存了,何来什么“文明的再生”?
由此可见,所谓“文明的再生”完全是一个虚妄造作、莫名其妙的伪命题,是一种完全背离事理逻辑的想当然的概念化图解。“深奥”的深处其实只有虚妄,“科学”的虚假外衣里隐藏的,只是一个装腔作势的“文学”“野心”。
说到装腔作势,还可以再提及作品中多次出现过的一类极其荒谬的细节。大概作者认为既然是表现文明的再生,就必须得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东西,才显得有内涵。于是,小说家居然让这个失忆老人,在深山荒野与绑架者黑道人物哑子来了一场“文字游戏”。当然,老人作为一名来自上海的退休人员,识文断字自属正常;但黑道人物哑子不过一个在山野里被人收养长大的孤儿,因聋而哑,从没上过学,虽说热衷于认字,但也只能是一些常用字而已。因为两人无法用语言交流,只能以书写文字的方式进行,这在情理上也说得通。但是,两人书写的是些什么文字呢?如老人写一个“灶”,哑子竟然写一个“釜”,接着又炫耀性地写了“箸”“钵”,甚至连“稷”“箬”“蕨”“茱萸”都写出来了。此外,两人居然还可以区分词性,一个写名词,另一个则写动词,写到后面,两人竟然兴奋至极……真不懂王安忆何以竟然会让两人在山里玩起了“汉字书写大赛”?这难道就是“文明的再生”的产物?《匿名》里对这一类的文字游戏有不少描写,出现了大量古奥陌生,让人应接不暇的古汉语字词、名称、典籍、典故等。
至于《匿名》如何“深奥”得会让“别人读不下去”“读不懂”,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
就这样,你懵了,闹不清从哪里来这么多的水,足以填满所有犬牙交错中的空缺,连一条线的缝隙都不错过。沙土间的渗漏也要充实。镇定下来,极尽目力,隐约看见水的边际,齐整的,平滑的,显然是特殊材料,就像盘山公路的那种。将天然材料的性能各自提炼,取长补短,加以混合。唯有人工,才能做到这样单一的坚硬度。还有直线,也是出自人工。……现在,你看见这一片水被有效地拦在边缘内,就知道是人力所为。因为透露出强烈的用心,只有人的用心,才会如此单一和集中,目的性明确。这围截起来的水域,名字叫做水库。
这算不算一段让人抓狂的奇葩文字?作者本意大概是要向读者顺便介绍一下水库的景色和特点,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读了这段文字,读者大概就会明白《匿名》之所以会被人称为“天书”的原因了。
我把这种叙述方式称为“学院体论文的语言表述在小说叙述语言上的再现”。原以为学院体论文的表达方式只适合在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中派上用场,没想到在本该通俗易懂的小说体裁上依然可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类似的表现方式在《匿名》里可说俯拾即是,这应该就是《匿名》让人读不懂、读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想问问李更先生,这就是王安忆“变得越来越大师状”的明证?
还有,像李文这种没有任何实质性评说,而只有贫嘴式的饶舌、东拉西扯的闲聊、莫名其妙的论断的评论文章,究竟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