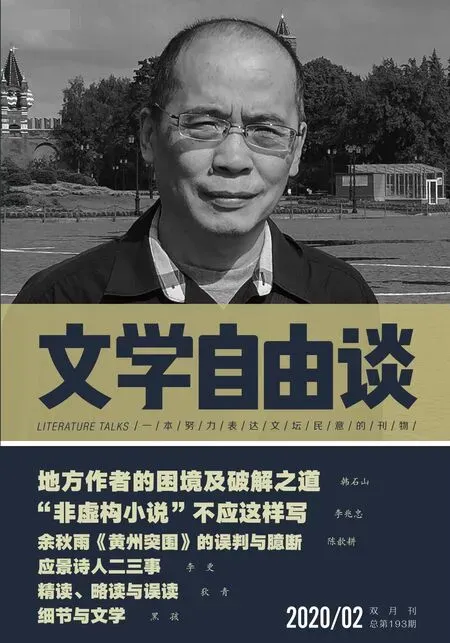我有三个小秘密,让我告诉你
2020-01-02冉隆中
□冉隆中
今天来到昆明海贝滇池ONE学校,我给大家分享三个小秘密。
第一个秘密:我很害怕走上这个讲台。
为什么害怕?因为我心里有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有压力?因为我是一个高龄父亲。我有多高的年龄?这么说吧,我和我的孩子——也就是这套书里的主人公冉潇然,两人加在一起,刚好七十岁,冉潇然的年龄只占其中十分之一。大家猜,我应该是多少岁?
我这个年龄,不是当爷爷而是当父亲,这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因为我的同代人都当了爷爷,我却要重新当一个父亲,要陪伴一个孩子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要带他去排队打预防针挂急诊,要接送他上幼儿园、小学,要随时面对别人误将爸爸当爷爷的尴尬……想想都害怕。所以,当孩子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不要让我去开家长会。可是,后来,我却忘记了这个协议,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不仅不害怕,而且还勇敢地站在大家面前,讲述我陪伴冉潇然成长的故事。
为什么?因为爱。
我对孩子的爱,让我克服了恐惧;孩子给我的爱,让我获得了力量。每一个家庭,基于血缘和亲情的爱,卑微而真实;我们的社会,超越血缘和亲情的爱,博大而崇高。这两种爱,都值得拥有和赞美。在这套书里,就充盈着这两种爱。
我笔下写的这两种爱,不是主题先行,而是生活使然。我是跟着孩子爱的足迹、爱的成长,以及孩子与父母、孩子与社会、孩子与大千世界爱的互动,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去记录、去书写的。
记得书中主人公冉潇然第一次到天津时,刚满三岁,是我带着他去的。当时他妈妈去了北京读书,孩子上昆明的幼儿园才几天,而我接到天津的文学批评刊物《文学自由谈》的通知,让我去领奖——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刊物在创刊三十年设立的一个奖,我偏偏就像买彩票中大奖一样获奖了!喜出望外之余,我却有一点担忧:孩子怎么办?征得主办方同意,我领着孩子就去了天津。飞机还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上空盘旋,孩子的脸颊就紧紧贴在舷窗上,搜寻着地面某个目标。我知道他在找什么——就在那次去天津的两个月前,那里发生了巨大灾难:一些消防员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当时孩子正在狂热地做着消防英雄梦呢!我告诉孩子,那场大火早已经熄灭了,火灾现场在天空是不可能看见的。孩子眼睛红红的,样子萌萌的,问我,到了天津,爸爸你可以带我去看看那里吗?我看《消防员山姆》学到了好多消防知识,我可以去跟天津消防员叔叔分享一下吗?那样下一次遇到大火,他们就可以不牺牲了是吗?面对孩子连珠炮似的发问,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回答他哪一个问题、答应他哪一件事好。但是我知道,这个孩子心中爱的种子正在发芽,我要做的,就是适当为那颗刚刚发芽的种子培根浇水,呵护有加。
那次天津之行后不到半年,孩子又去了天津,而且一去就是将近两年。天津师大幼儿园所在的西青区姚村,成了孩子在天津的栖息地。那里开春后流淌的小南河,村里热闹的小广场,比邻的霍元甲老宅,以及房前开花结枣的枣树、屋后三天两头的集市,都印下了孩子成长深深浅浅的足迹,也成了我观察他心中的爱不断萌芽生长的最佳现场。书里好多篇什,就写在天津姚村那所略显简陋的出租屋里。
在《打枣记》里,我写了孩子对姚村环境一段十分有趣的观察:
因为我无意中跟大文豪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我就对房前屋后这两棵枣树格外注意起来。
春天,迎春花开过了,地上的小草探出头了,带刺的光秃秃枣树,终于也发芽了。米粒儿大的新芽很害羞,就像迟到的学生站在教室门口,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可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这是超市门口卖大馒头的高奶奶说的。无非就是枣树发芽来晚了点儿,不也来了吗?
白色的枣花跟鸭黄的枣树芽一样,也是细细的、悄悄的。每次我去广场都要从枣树跟前路过,我使劲儿用鼻子嗅,也没闻到枣花一点香味儿。它们也真是太普通了!打那以后,我就没太注意房前屋后这两棵枣树了。直到有一天,它们结出了许多果实,才让我感到吃惊:原来,我们吃的大红枣,是这个样子啊!一开始,都是青皮的,有点儿微微的光泽,慢慢地就有了微微的红斑点。我想,到了它们全部红了,肯定就是熟透了。可是,小枣儿就偏不红给我看!向阳的红一些,背阴的就不红;朝上的红一点。朝下的就不红。也许是北方的枣树太多了,这两棵品种又不好,枣儿长不大,一直以来根本没人搭理它们,也就我对它们上心,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对它们说过跟大文豪一模一样的话!
《打枣记》《慢车回昆明》《星星月亮太阳的孩子》……书里好多篇什,被一些学校当作范文,反复分析欣赏,谬赞为不矫情的真“美文”。其实没那么好,也就是有真情自然流露的两种爱而已。
那就让我们像寻宝一样,在字里行间去寻找那些爱的片段、爱的篇章吧——
第二个秘密:我很想念书中这个孩子。
是的,就是书中这个名叫冉潇然的孩子。我是他的父亲。我为什么要想念他,而不是二十四小时随时陪伴在他身边呢?
因为,我陪他到三岁多的时候,他就离开我,到陌生的城市去学习生活了。他到了北京、天津、上海——他去的这些城市,是中国最早的三个直辖市。如果算上孩子的老家重庆,那么,他跟中国全部的直辖市都有了关联。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书里确实有很多篇幅写的是天津、上海、北京这几座城市的故事,但并不是因为这些城市比孩子出生地昆明“高大上”,而是因为他三岁多后去到了这些地方,去当了他妈妈的“保护人”——他妈妈到这几座城市读硕士、博士,孩子说他不放心,就去这些地方“保护”他的妈妈去了。孩子的愿望很幼稚,也很真切,他确实是带着小小男子汉要保护女人的强烈愿望去的。至于最后到底是谁保护了谁,以他的年龄和认知水平,暂时是分不清楚闹不明白的。但这同样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
由于时空的分隔,我很想念书中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同样十分想念我。孩子想念父亲的方式是很特别的,一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二是希望父母永远不要变老。这两个希望却是与每天发生的生活事实背道而驰的:小班、中班、大班……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五十八、五十九、六十……我也一天天在变老。因此,孩子的很多困惑、很多纠结,都与这两个希望在打架。现实中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会耽于幻想,一会儿想着放假去天山“绕绳垂降”,为他妈妈“盗取”长生不老的仙草;一会儿又在从上海到昆明的绿皮火车上,担心着他的爸爸在等待中突然变老……
第三天,天亮的时候,昆明终于到了!我见到远远跑来接我的老爸了!老爸真的变老了,都怪慢车,还绿皮呢,再绿我也不愿意坐了,就是给我一路都吃哈根达斯,我也不再坐了。因为,我舍不得老爸在等我的时间里变老!我爱爸爸,我爱妈妈——你们都不要变老!
爸爸一把抱起我,说,重了!放下我一量,又说,高了!
妈妈说,都是想你宝贝儿子想的!回家一称一量,还真重了,身高达到一米二了!妈妈觉得奇怪,上车还量过不到的呀?怎么下车就到了?
所有人都以为,人长高是在不知不觉中,那是因为你没坐过慢车。
我记得,在我牵挂和想念的那些日子,在我一个人呆在昆明,想念他,想念到不行的时候,我会打一个“飞的”,飞到孩子所在的城市去看望他,去陪他上学、放学,陪他踢足球、看博物馆……但是我也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怎么办?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他的成长经历记录下来,一点一滴,就成了这三本小书。可以说,这三本小书就是我们彼此想念的结晶。孩子的想念、纠结、矛盾,成为我创作素材最生动的资源;我对孩子的想念,则成为我写作这套书的全部动力。可以说,是彼此的想念和牵挂,成就了我进入儿童文学场域的创作,而想念和牵挂的背后,还是那一个字:爱。
第三个秘密:我不能说出这个孩子背后的秘密。
这个孩子,阳光,聪明,经常语出惊人。记得有一次在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家里做客,孩子在沈石溪夫妻面前,滔滔汩汩讲起了安徒生,讲起了《夏洛蒂的网》,讲起了《西游记》,讲起了《鲁滨逊漂流记》,甚至还讲起了印度国大党和甘地“非暴力运动”的主要观点……此时,距离潇潇上小学还有三四个月时间。孩子强烈的表达欲望和恰到好处的讲述,让动物小说大王很吃惊。他们夫妇由衷地伸出大拇指,为眼前这个“小屁孩儿”点了大赞。
可是,也是这个孩子,你知道他从诞生伊始,就遭遇过多少曲折委屈吗?他成长的背后,掩藏着多少我不能说出来的秘密?是的,是秘密。最大的秘密,就是他居然是这片土地上不准出生的人!这些秘密,可能要到他长大了,要到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进步了,如果我还有说话的机会、能力和需要,我才能对孩子、对社会,大大方方而不是遮遮掩掩地说出来。
如果说爱是我写作的动力,那么,秘密也是,而且是藏得更深、持续更久的原动力。可是秘密总归是秘密,只能暂时藏在心底,压抑在笔端。这构成了我书中的叙事障碍。一些地方,我自己看了,都觉得结结巴巴、扭扭捏捏,那些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只言片语,让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别扭。但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话题,我且打住!
但是我还是十分怀念那段时光——无论四岁、五岁,还是六岁、七岁,孩子不在我身边的这段时光,我和他,经历了彼此的想念,以及各种“锻炼”。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孩子妈妈外出参加活动了,活动现场不允许使用手机。关在家里的孩子无法跟妈妈保持联系,只好用视频跟我连线,让我看着他做作业,看着他自己找面包充饥。几千里以外的我,一直靠视频帮助他战胜恐惧,直到深夜,他妈妈终于回到他身边为止。
这套小书中,大量篇幅写了孩子这几年中的迁徙以及我的奔波。孩子一会儿北京,一会儿天津,一会儿上海,我的注意力就跟着孩子的迁徙而移动。他栖居的城市,成了我每天“天气预报”关注的所在——这几乎是中国所有家庭老人的共同爱好。我什么时候也变成老人了?我的孩子明明才四岁五岁六岁呀?我在心理抗拒着自己生理上变成老人的事实,在行动上更是不愿意加入老人的行列。我所在的城市,凡六十岁即可享受公交免费、地铁打折、部分公园免单……可是我迄今仍然坚持不去办理相关手续。所在单位每到节假日,对离退休“老干部”总有各种照顾,比如接送出行游览、开会免费吃喝、到家送油送粮、进门嘘寒问暖……可是我一次也不予搭理。人家邀约却不见回应,次数多了,也就懒的再通知了。我倒落得在心里继续“装嫩”,说话语气、行事方式,包括身段视觉,都尽可能与小儿子保持一致。到我写作这几本书的时候,也就比较自然地贴近了人物原型,成就了原生态记录和零距离书写,让读者感到这是一本不掺水不使假的真童书。
当然,所有写作都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性地书写记忆,一定是以选择性遗忘为前提;选择性地进行描述,一定是以选择性回避为前提。我选择性地书写了我和孩子之间在想念和惦记中的某些温暖,比如《我的爸爸才是一个真傻瓜》里,有一段冉潇然的“口头作文”:
我的爸爸才是个真傻瓜。你在昆明,眼睛却总盯着我和妈妈生活的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我们在哪一座城市,你就会看那座城市的天气预报,比我和妈妈还先知道,第二天会不会有雾霾,出门要不要戴防霾口罩,衣服该怎么穿,你总是在头一天睡觉前,用视频或电话告诉我们。
你只要有空,就会提前订好机票,来到我们生活的城市。你坐的飞机总要在中间停留一下。我告诉爸爸,你太傻啦,飞机起降是最危险的,为什么不买可以一次飞来的呢?你笑着说,多一次停留,爸爸就可以多看一个城市的风景,这不是很划算吗?我就不戳穿爸爸的谎言了!你其实就是抠门儿!我记得,有一次你在一个中途停留的地方,停的时间太久了,却不愿意在机场买一碗泡面吃。到了我们在上海的家,你饿得摇摇晃晃的,一进门就瘫在地上了!妈妈说,就算省钱,也不能拿命去省啊!你也不争辩,因为,你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可是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你知道了,当天夜里就赶到了上海。我在输液床上才睁开眼,就看见你站在我面前,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你告诉我,这一次机票,可以飞来飞去四趟了。我知道一贯抠门儿的爸爸又心疼钱了,你说,不是心疼,是肉疼。看着你呲牙咧嘴的样子,我笑得流出了眼泪。
大家说,我的爸爸是不是才是个真傻瓜?
读到这样的段落,我会自己把自己感动得眼眶潮湿。
当然也会书写到孩子的一些疑惑,以及我的一些尴尬,比如《我的大东北》:
我觉得大人中间埋藏着一些秘密,虽然我像柯南大侦探一样,有指南针、探测器和好多装备,我还是看不穿这些秘密。唉,为什么会这样啊!
每次去东北,我们都要经过哈尔滨,有一个叔叔会开车来机场接我们。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叔叔,很晚了,他还在我们房间里,赖着跟我妈唠嗑。我就坐到他们中间去,告诉叔叔,我要睡觉了。这个癞子叔叔才走了。妈妈后来说,潇潇你做的对,但是你不要给爸爸说。这又是为什么啊?
这样的困扰,不仅对一个四岁的孩子以及孩子的父亲会构成疑惑和尴尬,天底下,哪个家庭或者哪个年龄段的人如果遇到,不是同样也会困惑和尴尬吗?
书里的秘密和“梗”其实远不止这些。还是让老师和同学,让愿意走进这套小书的读者,自己在阅读中慢慢寻找和感受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