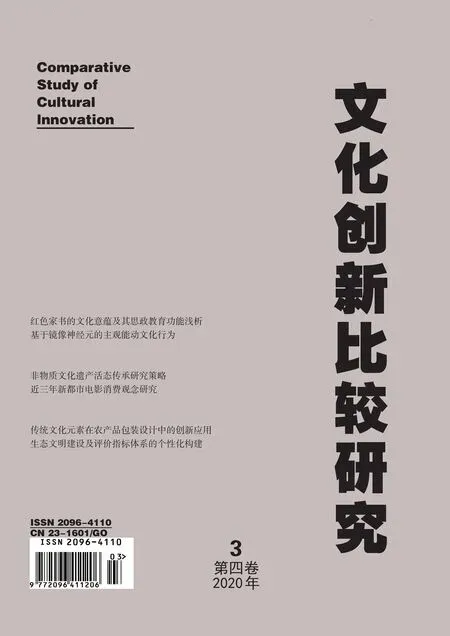五味川纯平的中国东北体验与文学创作
2020-01-02王硕
王 硕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116044)
1 五味川纯平与中国东北
1916年五味川纯平出生于中国大连,从小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并由中国人乳母照顾。17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此,而后辗转日本和中国半工半读。在大学期间,五味川纯平熟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书籍,并对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思想便印刻在了他的心中。同时他也参加了左翼运动,还因此受到了当局的镇压。1940年进入“满洲”一家大型军需公司工作,三年后成为矿山劳务管理人员。后来由于阻止对中国工人的处刑,被宪兵队收押,随后被发送到前线,成为了一名士兵。此后的两年便一直在靠近“苏满”交界处的地方进行军事训练等活动。1945年8月13日,五味川纯平所在部队与苏联正式交锋,日方全军覆灭。包括五味川纯平在内仅有4名存活者。同年12月拖着半残之躯回到了辽宁鞍山。可以说五味川纯平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是在中国东北度过的,对于中国东北五味川纯平更加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曾表示自己从来不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差别。
不同于那些“国策文学”作家,他的作品中较为明显地洋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彰显着对公正合理的追求,体现着对日本殖民侵略的批判与反思。而且,与一般日本殖民地作家不同,五味川纯平是上过战场的作家,是感受过最真实的血雨腥风的作家。他曾亲眼目睹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残暴行为,体验过在战争状态下军队中的人情冷暖,亲眼见过战败后日本人进行返迁的悲惨场景。因此,其对于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那场殖民侵略战争的相关描写与叙述,更具有真实性。同时,对于人性的描写与剖析也更加细致。劳务管理者、士兵、逃亡者,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身份的背后是三段作者无法忘怀的中国东北体验。而作者也以人道主义为线索,将三段经历联结到了一起,创作了《做人的条件》这部作品。
2 矛盾纠葛的劳务管理体验与创作——人道主义的开端
1940年五味川纯平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了位于鞍山的“昭和制钢所”。三年后,他来到了弓长岭(小说中为老虎岭)的矿山做劳务管理工作。在这里他的身份是殖民地的管理者,也就是所谓的“一等国民”。但他并没有以“一等国民”的身份自居,更没有像其他日本人同僚一样去虐待中国工人。而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努力为中国工人争取合理的基本权益,言语行为间无不体现着人道主义关怀。他提交了《中国人劳务者待遇改善》建议书,以谋求对中国工人的待遇合理化。与其他管理者不同,他并没有一味地追求产量而置工人的生死于不顾,而是在改善工人的待遇的基础上去提高产量。
小说当中“梶”所提交的《殖民地劳务管理诸问题——以老虎岭的劳务情况为例》这一报告书便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提出的。 报告书围绕着“将人作为人来对待”这一主题,谋求中国工人的待遇改善。但是部长却对这份报告书提出了疑问。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只有压榨支那劳动者,这个大企业才能有效运转,没错吧?”
“是这样的”
“那你的言论从根本上说不就是矛盾的吗”
(中略)
“......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不矛盾,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吧”(五味川纯平,1963:18)
即使知道战争与人道主义本就是相悖的,即使明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梶”还是跟随自己的内心,以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身份对殖民地的不平等进行干预。
在小说中,“梶”作为殖民地中唯一的人道主义者,早已看透了殖民地的种种不平等与对中国人的剥削。把工人们的宿舍安排在环境最恶劣的地方;现场监督的妻子可以明目张胆地拿走30斤的白面,而中国人劳务者“陈”却四处寻求无果;日本人军官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无度地挥霍着本属于中国人的资源。不仅如此,对中国工人施加暴力也是家常便饭。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是怎么了?”
“应该是在现场作业时被岡崎打了”
被害者的脸布满了血,早已分不出眼睛和鼻子。
“快送诊所去!”(五味川纯平,1963:128)
看到这个场景,“梶”的心中极度愤懑,看着被抬走的工人,他大喊了一声“岡崎那个家伙!”第二天他便到所长那里去控诉岡崎的卑劣行为。并提出了提高工人工资,加强工人的安全保障等建议。但是他的这些行为并没有受到上级的认可,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的支持。
战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本就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在这种不同于寻常的极限状态下,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在“梶”的周围充满了残暴的殖民者,在他们中间独树一帜的“梶”想要坚守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便显得力不从心。而最终他的这种对于人性的守护,成为了他被召集入伍的导火线。由于阻止处刑中国工人,他被宪兵队逮捕,严加拷问,并被免了职直接发配到了军队。
以“一等国民”自称的日本人,将中国人视为肮脏、低贱的存在。当然,“梶”是日本人,是所谓的“一等国民”。但尽管如此,他不得不直面他内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从大学时期开始便有了左翼的倾向,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于日本这种殖民行为,他虽不得不接受,但很难去理解。所以他进入公司后,不惜违反“国策”,去守护中国工人。但是,任凭他再怎样守护,“监视工人在矿山的工作”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殖民政策的响应,这根本就是一种殖民行为。正如学者所说,对被奴役、被压迫的被殖民者来说,殖民者就是殖民者,没有“好的殖民者”或“坏的殖民者”的区分(柴红梅,2015:244)。所以,“梶”完全逃不出“殖民者”这一身份,其对中国工人的守护也是有局限性的,不过是殖民者的施舍罢了。
3 厌恶抵抗的军队体验与创作——人道主义的动摇
1943年11月五味川纯平应征入伍。他的身份也由此发生了转变,从殖民地的管理者变成了一名二等兵。他的任务也从之前的劳务管理变成了“听从指挥”“接受命令”。在军队当中,人是无法拥有自己的意愿的。只要进到了这个抹杀人性的系统当中,压迫与折磨便接踵而至。关于这一点,五味川在他的纪实性小说《虚构的大义》中这样说道。
“悲惨才刚刚开始。此时的男人们不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们被溶解,被铸形,按照一贯的要求被塑造成士兵的模样。”(五味川纯平,1973:15)
而他们的塑造手段便是内务班炼狱般的体罚和挑战人体极限的军事训练。对于军营来说,军事训练的严苛无可厚非,但内务班的无理要求便是五味川无论如何也无法妥协的。入伍第二年五味川被任命为新兵助教,他秉持着不体罚新兵的原则,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认为所谓的“内务教育”是无用的,自己无法理解那些无理的要求。(所谓“内务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对新兵的体罚手段。即以内务管理为由,对新兵进行过分的打骂和羞辱。)但是,其他的老兵并不会这么想。笔者认为,那些毫无人性的体罚与训练是老兵们释放压力的一个宣泄口。由于军队里的等级序列制格外分明,因此几乎所有新兵的命运都是相同的,那些现在的老兵当年亦是如此。他们想把曾经作为新兵受到的屈辱全部奉还,但可惜物是人非,报复对象便成为了下一批新兵。如此往复,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但这时便出现了一个试图阻断这一循环的人,他便是五味川纯平。他尝试从改变内务班人员配置入手,将新兵所在的内务班中的老兵全部调离,以此净化内务班环境。但这样一来便是正面挑战军队中的固有规则,且直接触碰到了老兵们的尊严。从这时起,他与老兵之间的摩擦便没有中断过。被侮辱被施加暴力也成了家常便饭。在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描写。
“毫不留情的拳头迎面打来,梶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倚在了饭桌旁,鼻血喷涌而出。
‘把血擦了!’
乾大声说道。这并不是关心,只是为了继续施暴而做的铺垫。这些梶都明白。他拿卫生纸塞住鼻子,为了能够呼吸,便张开了嘴巴。小野寺脱下了鞋子,用力地抽了梶一下。
‘把嘴张开!张大点!’
小野寺试图将鞋子塞进梶的嘴里,梶下意识地把头转向一边。但不知是谁从身后摁住了他的头部,身体也被牢牢固定住动弹不得。小野寺硬把鞋子塞进了梶的嘴里。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五味川纯平,1963:576)
就像这样,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梶”一次又一次地被老兵折磨。他虽是人道主义者,心中虽充满着正义,但他毕竟还是普通的人。他单枪匹马追求内务改革,独自一人庇护着管辖的新兵。可对于整个军队的生物链来说,他依旧是处于底端的那一个。在军队中他不再是“一等国民”,仅仅是一个必须服从命令的士兵。他也不再具有所谓的“权力”,没有了支配别人的条件。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梶”渐渐有了老兵的模样。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梶的目光没有从高杉身上离开。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眼神已经和内务班里故意吹毛求疵的老兵的眼神有了几分相似,”(五味川纯平,1963:604)
在对新兵进行训练时,他不自觉地摆出了老兵的姿态,在言语和眼神上都变得冷漠且严厉。“站起来!”“把头给我抬起来!”“快点继续前进!”(五味川纯平,1963:604)这时的“梶”,已经渐渐脱离了真实的自己,他已经被溶解在了军队的“熔炉中”,被铸形成了独属于军队的“上等兵”。
至此,“梶”的人道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动摇,他不再拥有当年作为殖民地劳务管理者的坚定的人道主义信心。军队的长时间压迫,使他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变化。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点人道主义,但在战争至上的大环境下,在军队的无理压迫下,他已不敢再轻易挑战权威。这不是“梶”的懦弱,是他作为人天生具有的自保心理。这是战争对人的改变,它使人放弃了原有的坚定信念,使人一点点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资格。
4 绝望与无策的战败体验与创作——人道主义的崩坏
1945年8月13日,在“苏满国境”,曾号称“无敌”的关东军遭受惨败。五味川纯平所属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包括他在内仅剩四人。从那天起,他们便开始了逃亡生活,横尸遍野的山地中绝望前行。男女老少的动作全部定格在了去世的前一秒,就那么错乱地搭在一起。五味川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手里紧紧握着豆壳的孩子、抱着妻子的老人、女人、男人......就那么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那”(五味川纯平,1971:191)这样的场景,五味川走了一路也看了一路。
经过110天的逃亡,他终于坐上了去往鞍山的车。而他坐的那辆车,和当年他作为劳务管理者时接收中国工人时,押送工人的那辆极为相似。当时的他早已从“一等国民”跌落为“战败弃民”。他不再具有任何的支配权力,甚至不再具备作为人的权利。国破家亡,在已经不属于他们国家的土地上,他已不再拥有人权。为了保存性命,他烧杀抢夺,摇尾乞怜,苟延残喘地拼命活着。
在小说当中,“梶”这个标榜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用他曾经握笔杆的右手掐死了突然发疯的兵长,刺死了巡逻的哨兵,无情殴打了可怜的返迁女人。不仅如此,他还将魔爪伸向了无辜的中国人。
“在这数十天里,屡次向无辜的住民施害,不管有没有必要,在无形的犯罪记录册上,应该有几条,甚至几十条关于他的犯罪记录。”(五味川纯平,1963:905)
他早已不是为了保护中国人而与权威对抗的“梶”了。他已不是由于国策被强制犯罪,而是变成了带有自主意识,且毫无罪恶感的杀人狂魔。就这样,他不断地用他人的性命来延续自己的性命。在冬日的旷野中飘荡了数日,他来到了“满人”的村落。身穿军装的他马上引起了村民的注意。了解到他是日本人之后,村民们便将心中所有的愤懑都倾倒在了他的身上。
“一口浓痰被吐到了脸上。紧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梶被打倒在地,混着鼻涕眼泪的脸被摁在地上。他不是因为疼痛或痛苦而哭,也不是因为难为情。眼泪仿佛是知道一切都变成了徒劳,自己跑了出来。”(五味川纯平,1963:1027)
就像原文所说,那眼泪不是因为“痛苦”或“难为情”。笔者认为,那是“悔恨”的泪水。首先,自己历经万千险阻,不惜变成杀人狂魔,拼命逃亡,但最后还是沦落到被抓起来暴打的地步。其次,自己一直以来标榜的人道主义,随着战败开始持续崩坏,虽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
逃出村落后,他在漫天的大雪中继续前行。躺在雪地中,他想象着回到家的喜悦。最后,旷野中多了一座由雪堆成的小丘。“梶”的双眼合上的瞬间,一直以来的人道主义也随之宣告死亡。
前文也有所提及,在五味川的实际体验当中,他本人后来平安回到了鞍山。后来也安全返迁回国。但在小说当中,主人公“梶”却死在了旷野中。在笔者看来,作家给“梶”以这样的结局,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在战败之后,得以成功返迁回国的人本就占少数,大多数人都死在了半路。这样写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
其次,作者写的写作意图就在于探讨在某种极限状态下作为人的条件。而通览全书可以发现,虽然有很多对抗战争,挑战权威的描写,但归恨到底作者想表达的是战争对于人性的抹杀。作者以人道主义为线索,借用主人公的身体去探索在战争这种极限的状态下,人还有没有作为人的资格;在无休止的压迫下,人的心理与行为还能否维持正常的运转。
此外,作者作为“满洲二代”,对于中国始终抱有着愧疚之情。他曾在公开的场合发表演讲,批判日本的卑劣行径,认为日本是“不知廉耻”的国家。而他也是想借主人公的死,向世人展示战争的罪恶,向各位读者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5 结语
竹内好曾表示《做人的条件》这部作品“与大佛次郎的《归乡》川端康成的《古都》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作为战后作品的畅销书,其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篇幅之长,情节之生动,更在于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战争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同时以较为客观的眼光审视了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对于战争他进行了深刻地反省,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对于日本殖民者施加给中国人的痛苦,他已经较为清晰地认识到,并通过文学书写较为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而对于我们来说,同样需要正视历史,不能忘记那15年阵痛,对于日本殖民者的丑恶行为与虚伪嘴脸要强烈批判,但同时也不要忽略那些如五味川纯平那样的“满洲二代”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