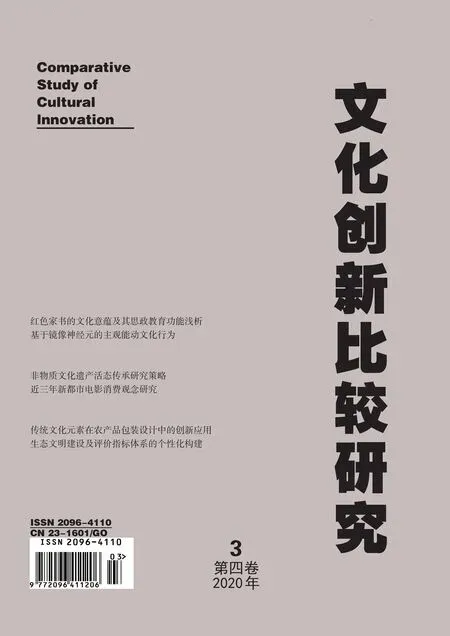一个虫体人心的现代童话
——解读卡夫卡《变形记》
2020-01-02吴登洋
吴登洋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西赣州 341000)
卡夫卡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现代派文学大师,他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影响了几乎所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超现实主义从中窥见到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表现主义看重其运用梦幻与直觉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存在主义文学则从中看到了个体追求的困境与徒劳,荒诞派戏剧则发现了有关荒诞人生中荒原人不得拯救的惨况与异化,黑色幽默索性沿着其描写“反英雄”与可怜虫的道路继续推进。Kafka(德语即“洞穴、穴鸟”之意)这一词语本身就含有受到挤压与逼迫的意味儿,作为一个符号它也恰恰印证了卡夫卡本人焦灼、恐惧与充满困境的一生。当这种卡夫卡式的困境投射到文学创作中时,就表现为障碍、威胁、恐惧、变形与荒诞——这既是卡夫卡内心世界的表征,更是现代世界的寓言与启示录。因此,如果说卡夫卡为我们开启了洞察现代人异化与荒诞境遇的一道闸门,那么他的《变形记》可堪称这方面的杰作。
1 悖谬式生存与荒诞的真实
《变形记》写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蜕变为虫继而凄凉死去的故事。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上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吓跑了前来催促他上班的公司秘书主任,并两度吓晕了自己的母亲,气坏了父亲,一时间全家陷入空前的恐慌与经济的窘境当中。虽然最初尚有妹妹的细心饲养,但时日迁延,忙于赚钱养家的妹妹很快也变得粗心敷衍起来。尽管格里高尔一次次努力地尝试着重新走入人的世界,但结果只是导致更大的麻烦与灾难,最终,他为全家人所厌弃,在一天夜里带着对家人的深情爱意悄然死去。而父亲、母亲和妹妹却如释重负,欢欣地去度假,规划着家庭还算光明的未来。尽管卡夫卡如福楼拜一般,以一种近乎客观漠然的语调讲述着这一切,但小说内里所透射出的阵阵寒意仍直渗人心,凄楚而悲怆。在现实世界中,人变为甲虫是荒诞不经的事,没有人会将其当做真实,然而文学作为对人的生活的表现与虚拟性重构,无疑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反映出人的精神与心理的变形与扭曲。因此,我们理当以寓言的方式来读解这一现代的童话并探寻其背后所涵容着的现代社会与人性的质素。
小说开篇便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一种莫名的灾难感突如其来,令人震惊不已。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格里高尔的变形呢?接下来,叙述者只是讲格里高尔如何费力地挣扎着起床和对先前烦人的工作与专横的上司的不满,丝毫不提及变形的前因后果,并且自始至终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总之,祸从天降,人物一下子跌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境地中,无论怎样努力、挣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毁灭,犹如《审判》中的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被两名警察莫名地逮捕,不管怎样申诉、呼告,最终仍毫无缘由地被无情处死一样,灾难与荒诞强大的异己环境瞬间将人捕捉裹挟。这种开篇式叙事空缺所造成的突发性,作为卡夫卡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恰恰烘托出了个体的渺小与人生的不可把握性。
尽管读者早已不胜惶恐,但格里高尔本人似乎并不是十分恐惧。在一刹那的惊异与一番挣扎过后,他所想的只是:
“‘啊,天哪’,‘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起床这么早,’‘会使人变傻的。人是需要睡觉的。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贵妇人。比如,我有一天上午赶回旅馆取回订货单时,别的人才坐下来吃早餐。我若是跟我的老板也来这一手,准定当场就给开除。也许开除了倒更好一些,谁说得准呢。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得五六年——可是我一定能做到。到那时我就会时来运转了。不过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因为火车五点钟就要开了。”
透过这些大段的内心独白与心理描写,我们看到,格里高尔不是在担心此时变形的身体,而是独自在心中对工作与老板发泄着积蓄已久的强烈不满,并且本能地抗拒着起床,似乎在他看来,变形倒是一件好事儿——终于可以暂时不去上班了。在这里,格里高尔精神上是分裂的。一方面他强迫自己立刻起床去上班,一方面又因身体的不适不自觉地贪恋着床。如果说前者是其意识的表现,那么后者则是其潜意识真实心迹的流露。是的,为了还债,为了赚钱,为了面包与生活,“我”现在必须起床,尽管这多么让人不情愿。赚钱、还债、养家,在这重重重压之下,格里高尔犹如一架被公司机械地驱使着的机器,无日无之地工作。但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格里高尔厌烦透了这份工作,可他又必须十二分地去爱他的工作,真可谓“爱恨交织、难舍难分”!这种悖谬式地生存剧烈地撕扯着格里高尔的情感和理智、心灵与肉体,最终,他不堪重负,变成了一只甲虫,逃离开了这份既爱且恨的工作。从这重意义上说,格里高尔身体的化而为虫正是他内心潜在意图的幻化以达到从当下世界、非人化世界的逃逸。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填补格里高尔变形原因这一叙事空缺了。其实,格里高尔的所思所想与所经历的生活现实不正是我们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吗?在经济主宰一切的社会与时代里,工作、金钱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脉,而以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实体、权力集团则成为个人自由与生存的强大异己性存在,它们拿捏着我们的命脉,犹如野兽掐住了我们的脖子,迫使人对之俯首帖耳,牛马般劳作。这正是经济与金钱对现代人的深度异化。在现实生活中,重压下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变形来逃逸,但却可能因残因病甚至自杀来求得解脱。因此,格里高尔的变形作为对现代社会的表征,作为一种荒诞性实在,又何尝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精神幻化与历险呢?这种悖谬式生存也就成了包括卡夫卡在内的现代人的不可抗拒的宿命。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加洛蒂曾经说:“一切真正的艺术作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卡夫卡的小说正揭示了现代人一种真实的生活处境——卡夫卡式——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障碍重重、亦真似幻,充满孤独与恐惧、荒诞而又极其真实的生活处境。
2 世界即障碍与情感之维的断裂
格里高尔的变形使得他成为人虫同体的一个“怪物”,——在甲虫的躯体内涵容着一颗人的心灵,尽管他不可避免的具有了某些虫性甚至一度步入了去人化道路,但终归他的人性、人情占据了主导。他虽然身为甲虫,却有着先前做人时的感情甚至变得更为细腻。尽管蜷缩于黑暗的角隅,却在“心里感到很自豪,因为他能够让他的父母和妹妹在这样一套挺好的房间里过着满不错的日子”;尽管“没有人会来看他了”,但他已在心里“从容不迫的考虑他该怎样重新安排生活”。他甚至整整一夜“一直沉浸在担忧和渺茫的希望中”,认为“目前他必须静静地躺着,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不管是夜晚还是白天,格里高尔都几乎不睡觉。有一个想法老是折磨着他:下一次门再打开时他就要像过去那样重新挑起一家的担子了……”即使身遭父亲的重创,生命垂危之际,单是听到妹妹的琴声,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向所有人宣布他早就下定的要送她进音乐学院的决心,而不容任何反对的意见。这哪里是虫啊,这分明就是人呀!
成为虫人的格里高尔以一颗善良而炽热的心时刻关注着家庭的生计与妹妹葛蕾特的未来,不可谓不虫心良苦。为此,他不遗余力一次又一次的跨越自己的房门试图表达自己的满腔责任与对家人的关爱,期望重新成为萨姆沙家庭的经济支柱,然而结果却一次甚于一次激起更大的冲突。先是吓跑了衣食父母——公司的秘书主任,继而两度吓晕母亲;尽管他表现的很乖,希望父亲把他当做听话体贴人心的儿子,但也只是不断招致父亲的盛怒、驱赶与武力威胁,并最终被父亲的一颗苹果砸下致命伤;先前还很单纯的妹妹对他倒还悉心,可一旦步入社会挣钱养家,性情就渐渐变了,由敷衍而至暴躁,并率先叫喊一定要把“这个怪物”弄走。一方是火热的心,一方却是憎恨、愤怒、驱打与抛弃。这种鲜明的对比,在让人为格里高尔无限哀伤的同时,更使人看清了所谓的亲情的实质。格里高尔至死也不明白,自从他变为甲虫的那一天起,他的世界就已经变了。他和家人早已人虫两界,他只能蜷缩在自己的房间角落里,他的房间的那道门也已成为人虫两界间的阈阀。当初工作出差的日子里,晚间他总是锁上房门以暂时逃逸出喧嚣的世界,而当变为甲虫彻底逃离工作摆脱挣钱养家的责任后,那道门就成了他无法穿越的障碍与间隔。在卡夫卡的眼里,世界即障碍,“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那么对格里高尔来说,又何尝不如此呢!不过,“门”只是横亘在他与人界沟通途中的一道有形障碍而已,真正导致灾难的无形障碍正是那语言。他能听懂人们间的一切话语,可他的“虫话”却无人能晓,尽管他自己觉得说地字字清楚。不被人懂,自然就被认为不懂人话,即使表现得很乖也无济于事。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说,语言即囚笼。这一遭遇在现实生活中也已屡见不鲜,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及至人种之间由于语言隔膜所导致的歧视、对立与冲突难道还少吗?就此而言,格里高尔三次跨出房门的举动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味,同时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甲虫的外形、语言的隔膜注定了格里高尔任何与家人的沟通都是徒劳的,注定了他将永远被锁闭在自己的甲虫世界与躯壳中,孤独而焦虑。虫就是虫,怎么可能与人生活在一起呢!起码父亲就是如此看待的。不能说在内心里他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没有丝毫的怜悯与关爱,他也很焦急并因此疲惫虚弱了许多。但在格里高尔面前,父亲表现得总是那么威严、冷酷、野蛮、暴力,不是顿脚、嘘嘘叫着驱赶,就是用苹果进行轰炸,以至在格里高尔看来,父亲“简直像个野人”。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冲突再次映射到了萨姆沙父子之间,父亲作为严厉、专横的形象成为格里高尔与众人沟通的又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世界即障碍,格里高尔摆脱不了身上的壳,更穿透不了世间一切有形无形的膜,死,成为了他唯一的选择。
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了;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卡夫卡这里所说的绳索,即包含了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情感关系以及人们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其中,亲情之维与经济之维构成了一个人生存的根本性维度,前者系缚于人生活的港湾——家庭,后者则主要捆绑于人生存与奋斗的战场——社会生活与所属经济体之上。格里高尔一旦变形,即意味着完全丧失劳动力,在以公司秘书主任为代表的经济权力集团的眼里,他早已没有了任何工具价值可资利用,因此格里高尔的任何哀告也不可能感动其心,自然也就被砸了饭碗,丢掉了这份养家糊口的差事。就这样,格里高尔与社会之间的经济之维顷刻间断裂。按理,一个丧失劳动力的人如果能得到亲情的护卫,那么他也足以重新面对生活走完余生,但格里高尔的境遇却并没有那么乐观。最初,妹妹还能“饲养”着他,母亲也希望他快快康复,可当全家人都奔忙于家计挣钱时,格里高尔就渐渐地被视为了累赘与废物。当他对家人尤其是对妹妹爱得愈发深沉之时,正是家人对他憎恶到了极点的时刻。从变形到惨然死去,不能说家人对格里高尔没有感情没有照顾,可我们发现,家人越专注于挣钱就越憎恶他。可见,在经济与金钱的步步逼攻之下,亲情在步步龟缩;在经济这只无形的大手剧烈地撕扯之下,亲情之维渐渐扭曲、变形,越拉越紧,终于“啪”的一声断裂——“对着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分不是了。”“‘她说得对极了。’格里高尔的父亲自言自语的说。”“‘葛蕾特,到我们房间里来一下。’萨姆沙太太带着忧伤的笑容说道,于是葛蕾特也不回头来看看尸体,就跟着父母到他们的卧室里去了。” 格里高尔的变形犹如一面透镜,洞照出了父母慈爱妹妹温顺可爱的温馨氤氲下家庭关系的脆弱、虚伪与冷酷。当一个人不再能挣钱甚至需要人照料之时,即使在家人的眼里,他也只是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废物,随时都有可能被割断亲情的绳索坠入无底的深渊。一切都是利害计较,一切都是金钱关系,只可惜可怜的格里高尔致死也没能明白。在经济、金钱为轴心的世界里,亲情也只是穿着华丽的骷髅——你瞧,格里高尔死后,“萨姆沙先生和两个女人立刻离开楼梯口,回进自己的家,仿佛卸掉了一个负担似的”;“他们决定这一天完全用来休息和闲逛”,“于是他们三个一起离开了公寓,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这样的情形了,他们乘电车出城到郊外去。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只有他们这几个乘客。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谈起了将来的前途……萨姆沙先生和他太太在逐渐注意到女儿的心情越来越快活以后,老两口几乎同时突然发现……她已经成长为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的少女了……他们心里下定主意,快该给她找个好女婿了……在旅途终结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而此时,格里高尔干瘪的甲虫尸体早已被老妈子处理掉了。真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卡夫卡以浓烈的喜剧气氛收尾,却更烘托出了无比惨烈压抑的氛围。
3 童话的模式与反童话的主旨
作为一篇优秀的现代主义小说,《变形记》无疑开拓了现代小说创作与表现生活的维度。它以整体框架的荒诞与细节描绘的真实相融构,即在人变为虫而至死亡的历程中,细腻地展示了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心理活动与生理特征以及家人对他的态度变化,不可谓不生动传神,让读者信以为真地认同了格里高尔变虫这一“事实”,并随同他的情感波动与虫命遭遇而起伏。但基于现实经验逻辑的牵引,读者似又明显地意识到这种变形的不可能。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以变形的手法来展开叙述呢?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作者正是为了制造一种陌生化的疏离感,从而拉开与现实世界和日常状态的距离,以便更好地透视日常世界当中脉脉温情面纱下的森森白骨。也即是说,只有在背离了常态、扭曲畸变的状态下,才能更加真实深刻地展示微笑与关爱的表皮下所潜藏着的人性的冰冷与自私。这是一出资本主义统治世界——外在世界与人心世界——的悲剧,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金钱挤压“爱”以后所必然出现的现代人的悲剧。确实,“资本主义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附属关系的体系……资本主义是一种世态和一种心境。”
其实,卡夫卡运用人兽(虫)变形模式来创作,并非首创,相反,这是一种古老而悠久的文学表现手法。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之《奥德修纪》到古罗马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再到后来的《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等等,这样的写法不胜枚举。在中国文学当中,从神魔小说到写花妖狐媚鬼怪著称的《聊斋志异》,尤其是其中《促织》一篇,更是将人体变形文学母题与变形手法的运用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唯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没有魔法或是神力,只有那一觉醒来似梦非真突如其来的变形。那么卡夫卡的这篇《变形记》,在展开这一母题运用其手法时到底有何独特性呢?其实,独特性正在于这篇小说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这样的经典童话构成一种互文指涉关系和童话平行结构模式,从而彰显出强烈的反讽效果与深刻的批判力度。
《格林童话》中有这样三个故事——《十二个兄弟》、《七只乌鸦》和《六只天鹅》,而《安徒生童话》中则有一篇《野天鹅》,虽然后者改编自前者,但四个童话却展现出了相似的情节模式与价值指向。它们共同讲述了大体相似的故事:从前有一群哥哥和一个最小的妹妹,他们是一个国王的儿子和女儿。哥哥们受到父亲诅咒或是继母的魔法或者由于小妹妹善意的过错而变成了乌鸦抑或天鹅,当小妹妹懂事以后,便决心要找到并解救哥哥们以使他们恢复人形。于是小妹妹在一位老奶奶或者星星的指点下,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找到了哥哥,但要解救他们,则必须许多年保持沉默不许说话甚至不能笑,在规定的时间到来前,哪怕一个字说出,哥哥们也会即时死去。她必须为哥哥们每人纺织一件特别的外衣,直到他们披上身变为人形为止。为此,美丽的小公主从此以后就织啊织啊,在嫁给一位王子并受到王子母亲的诬陷与迫害后,依然不作辩解默默地纺织,即使在监狱里,在被当做女巫押赴刑场烧死的路途中,她依然干着手里的活儿,最后感动上帝,哥哥们得以变回人形,而她自身也因此得救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尤其在《七只乌鸦》这篇童话里,小妹妹更是勇敢非凡惨烈异常。她不小心丢了星星送给她打开玻璃山大门的鸡腿,但为了要救哥哥,“这位心地善良的小妹妹,掏出一把刀,狠命割下了自己的小手指,然后把小手指插进了锁孔,总算运气好,门给打开了。”小姑娘终于见到了乌鸦哥哥们,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拯救与欢乐幸福,顷刻间便化解了魔法,于是兄妹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飞越与沉沦——甲虫启示录
从创作论的角度切入,我们不禁疑惑:卡夫卡何以要塑造出一只不能飞行且行动迟缓而笨拙的大甲虫形象呢?甚至我们也可以设想,格里高尔为什么没能化为一只瓢虫或者蝴蝶之类的昆虫呢?其实,这一切都是卡夫卡有意为之。因为如果那样,就将意味着对生活的飞升与超越,因为瓢虫、蝴蝶都有着轻灵的特性和灵动的诗性,而笨拙缓慢的甲虫则是下于生活的。格里高尔的壳扁平、坚硬得像铁一样不能飞翔的特性,正是现代生活重压所致的一种隐喻。在重重压力之下,以格里高尔为代表的现代人时时都为生活所沉重挤压,只能异化如大甲虫般费力地蹒跚于人生的路途上,又何来轻松与灵动可言呢!所以,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是永远也不可能飞起来的。也正因此,扁平的甲虫才有了挤压、挣扎与蜕化的内质,这也恰恰印证了“卡夫卡”——穴鸟——这一名字的寓意。至此,我们忽然明白:噢,原来人确实是会变成可怜虫的!而一旦成为可怜虫,等待它的将是被抛弃、孤独、恐惧、饥饿与死亡。可以说,卡夫卡正是通过将荒诞植入现实的手法,以格里高尔异变为虫体人心的甲虫继而孤独死去的悲剧命运率先奏响了现代“非英雄”与小人物的哀歌。《变形记》作为对现代人饱受经济压榨被异化以及人际扭曲的烛照,无疑具有寓言般的深刻与反童话的内蕴,它启示人促动人以近乎绝望的沉思,去睁眼看清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