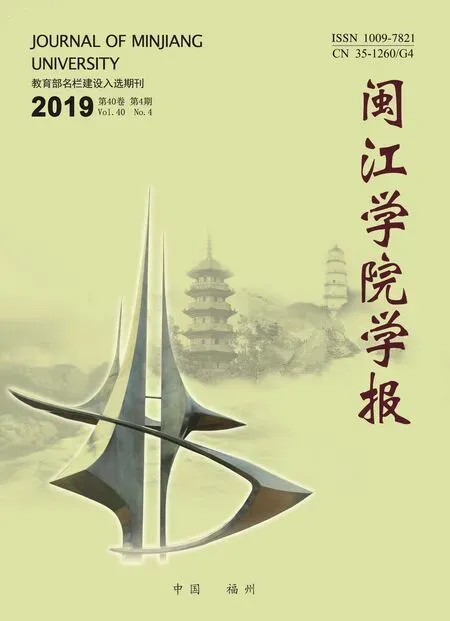钱谦益《天童塔铭》之争考论
2019-12-30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天童塔铭》之争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僧诤事件,诚如陈垣《清初僧诤记》所考,总共发生两次:一是费隐通容与木陈道忞之争,此论争因徐之垣撰写之《全身塔铭》而起;二是木陈道忞与继起弘储之争,此论争因钱谦益初撰之《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后文简称《天童塔铭》)而起。其中,第二次僧诤更受学界关注,除陈垣外,连瑞枝、孙之梅等多有考索(1)详参陈垣《清初僧诤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2页;连瑞枝《钱谦益与明末清初的佛教》,台北: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3年,第107-118页;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1-216页。。受材料限制,钱谦益的《天童塔铭》初稿未见学界征引,请铭原因、请铭始末、论争始末、后续影响等诸多问题亦有重新考察之必要。现以新发现钱谦益《天童塔铭》初稿等材料为中心,稽考相关史籍载记,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再作考释,谨请方家諟正。
一、请铭始末
晚明临济宗中兴主将密云圆悟圆寂后,王谷撰有《行状》,徐之垣撰写《全身塔铭》。在其弟子费隐通容经营下,唐世济撰写的《遗衣金粟塔铭》,由吴麟徵篆额,崇祯十六年(1643)刻石;韦克振撰写的《道行碑》,亦于顺治五年(1648)刻石。可以说,有关密云圆悟生平事迹及懿行功德的碑记石刻堪称完备(2)《行状》《全身塔铭》《遗衣金粟塔铭》《道行碑》等文见《密云禅师语录》卷十二(《嘉兴藏》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又:木陈道忞有《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见《布水台集》卷十六(《嘉兴藏》第26册)。。时隔十余年之后,木陈道忞为何再次邀请钱谦益重新撰写第二碑,成为我们考察的首要问题。
木陈道忞请钱谦益重新撰写塔铭,首先是看重其文坛名望。木陈道忞自云:“不孝幼为诸生,习制艺,即知海内有以文鸣世,如老先生其人者矣。继行脚游方,间从碑铭传志间见先生一二古文词,益叹先生之文,非徒咀英而吐华者,其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者与?去岁因贵乡许子,得广读先生《初学集》,益如横开武库,如深入宝山,如吴季札之观乐,至韶而止。窃谓非胸藏万卷,眼碧秋空,不可读先生之文。”[1]395可见,他在学习科举文字时,深知钱谦益以文名世。出家后行脚游方,阅读钱谦益的碑传文字,对其赞叹有加。顺治十四年(1657),木陈道忞阅读《初学集》后,对钱谦益更是钦慕不已:“抑先生岂徒以文哉?明治乱,植人伦,故先生之文,为不可企及也。”[1]395密云圆悟的塔铭虽有徐之垣等人旧作,因名望、文采等各种原因,“先师之道德终暗昧不彰”[1]395。从徐之垣《全身塔铭》来看,他以天童之兴废称赞密云圆悟的佛教功绩,在木陈道忞看来,缺乏对整个明代佛教史的全局观照。《全身塔铭》中大量羼入密云圆悟的语录话头,编排失次,颇为支离。费隐通容对徐之垣的《全身塔铭》颇为不满,故而引发了他和木陈道忞的论争,即有关《天童塔铭》的第一次论争(3)具体经过参见陈垣《清初僧诤记》,第34-34页。。几经权衡后,身兼文坛盟主与东林党魁的钱谦益,成为木陈道忞心目中重写密云禅师塔铭的不二人选,“窃谓人如先师,非先生之文不足以光扬至赜;文如先生,非先师之人不足以焕若昭回”,“矫俊伟如先师者,先生岂有爱焉?末后光明,点出笔尖头,俾伊照天照地,非不孝一人之幸,实天下后世学者之幸也。”[1]395
其实,木陈道忞请钱谦益撰写塔铭,亦有深层次的个人因素。据纪荫《宗通编年》卷三十一、三十二载,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七日,密云圆悟在天台通玄寺去世后,天童寺住持屡经变换。如崇祯十六年(1643),木陈道忞继席天童寺。顺治三年(1646)秋,费隐通容接替木陈道忞继任住持。顺治七年(1650),林野禅师接替费隐通容继任住持。顺治九年(1652)冬,牧云通门接任天童寺住持。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木陈道忞再次接任。在崇祯十六年(1643)至顺治十四年(1657)的十四年内,天童寺住持五易其主。重新请人撰写塔铭,借发扬先师品行德业巩固其在同门中的威望,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除了文坛名望外,钱谦益亦为江南佛教界著名的护法金汤,入清后又专意于佛经注疏,其《楞严经疏解蒙钞》等佛经著述,在教内外反响颇巨(4)参王彦明《〈楞严经疏解蒙钞〉考论》,《新国学》2015年刊,第117-139页;《〈楞严经疏解蒙钞〉的文献学价值》,《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1期,第67-71页。。因此,经他撰写之塔铭,自然极具影响力。僧诤发生后,木陈道忞在写给祁季超的信中称“西遁固信山翁决不幸虞山舞弄笔舌而雌黄天下也”[1]396,也透露出其个人目的。
为此,顺治十五年(1658)冬,木陈道忞派弟子山晓本晳带着他的信札,以及密云圆悟的行状、年谱等生平史料,来到常熟请钱谦益撰铭。对此,钱谦益云:“越十有五年戊戌,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上之铭。”[2]1 257钱曾亦云:“戊戌冬,天童密云禅师嫡子道忞具师行状、年谱,请公为塔上之铭。”[3]2 432出人意料的是,钱谦益以“抱痾,又方在忧戚,都不见客”[2]414为由,委婉地拒绝了木陈之请。所谓“忧戚”者,指钱佛日早殇。《桂殇四十五首》序云:“桂殇,哭长孙也。孙名佛日,字重光,小名桂哥,生辛卯孟陬月,殇以戊戌中秋日。”[2]455钱谦益一族人丁不旺,晚年痛殇长孙,悲戚之情可以想见。遭到拒绝后,木陈道忞只好请同门师弟牧云通门从中调解。其《复古南牧和尚》云:“虞山与弟素未谋面,亦以半纸腐文,遂辱千里神交。去岁仰体江上,与兄夙念,敬遣晳首座以先师铭,再徵椽笔。会伊抱痾,又方在忧戚,都不见客。及接弟书,欣然出相劳苦,诘弟行藏,竟日坐谈不备也。诺以浴佛就稿。”[1]414钱谦益与牧云通门是同乡,现存《有学集》收录了他写给牧云通门的《恤庐诗》《牧云和尚全集序》等诗文,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在牧云通门的调解下,钱谦益勉为其难,答应明年浴佛节交稿:“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4]350木陈道忞唯恐钱谦益中途变卦,顺治十六年(1659)春,再派山晓本晳常驻虞山,专候钱谦益的塔铭文稿。其《复古南牧和尚》道出个中隐忧:“仍期晳子先往,顷已在虞。虞山虽健忘,想不能忘诸此矣。”[1]414《柬牧斋钱虞山》其二亦称:“再遣山晓拥篲龙门,恭傒奎璧伫雨迟云,惟高空其沛然早及之。春风尚寒,有冀颐神善摄,长为南邦文献。”[1]396在木陈道忞、山晓本晳等人的反复督促下,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七日,钱谦益《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终于撰写完成了。令钱谦益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塔铭引发了木陈道忞、继起弘储两派僧徒的纷争。
二、论争始末
钱谦益所撰之《天童塔铭》由于语涉密云圆悟与其弟子汉月法藏的纷争,招致了汉月法藏嗣法弟子继起弘储的强烈不满。他会同僧团弟子,就此与木陈道忞和钱谦益反复商讨。
首先,继起弘储通过张有誉与钱谦益斡旋,促使钱谦益修改《天童塔铭》。从钱谦益的《己亥夏五十有九日,灵岩夫山和尚偕鱼山相国、静涵司农枉访村居,双白居士、确庵上座诸清众俱集,即事奉呈四首》来看,顺治十六年(1659)夏,继起弘储会同熊开元、张有誉(号静涵)、王廷璧(号双白居士)、释鉴青等僧俗弟子前往虞山拜访钱谦益。上述诸人中,促使钱谦益修改塔铭的是张有誉与王廷璧。钱谦益《有学集》收录的《答张静涵司农第一札》《再答张静涵书》《三答静涵张司农书》等三封信札,便为集中商讨之作。《答张静涵司农第一札》云:“顷承慈诲,谆谆启迪,因为开函一笑,语双白曰:‘此是静老方便说法,劝我放下屠刀也。’却苦两日前付山晓小师赍去,不得重与台慈商搉删定。”[2]1 385可见,《天童塔铭》初稿完成后,王廷璧携带张有誉的信札找到钱谦益,希望他进行删改。钱谦益修改完成后,经王廷璧、山晓本晳带给木陈道忞。钱曾云:“《天童塔铭》稿出,灵岩弘储和尚为汉月法嗣,见之,急挽静涵司农,两致手扎于公,力请删改。公不得已,为易其文。”[3]2 433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在信札中反复申明,其《天童塔铭》是依据行状、年谱直陈史事,不敢妄加增改,“通篇叙次,援据行状、年谱,不敢增益一字”[2]1 385。
其次,王廷璧携带《天童塔铭》修改稿和相关书信,找木陈道忞兴师问罪。木陈道忞反而向继起弘储问责,认为继起弘储身为晩辈,若对《天童塔铭》有所不满,理应由他找钱谦益修改,不应让张有誉接洽钱谦益。言外之意,继起弘储不应忽视木陈道忞“师叔”之身份。如《复灵岩储侄禅师》云:“先老人塔铭,去秋始讬虞山属笔。七襄之报,诺以今夏浴佛节为期。中间词锋有碍汉兄和尚,则山僧都未省览。老侄既阴得其事状,何不移牍山僧俾为删改,乃假手张静翁斡旋钱牧老,抑复何也?”[1]396针对祁季超的责问,他以类似之语回应:“犹子中如玄墓、如灵隐,即犹孙中如豁堂、如仁庵辈,走一使持片楮焉而问山僧,岂可不手勒八行,专人请改?矧灵岩之与山僧,犹称当世籍咸者乎?见不出此,乃规为布置,斡旋虞山,又动劳足下之管城君,是谓无识,且昧山僧。”[1]396
王廷璧的轻慢之举,成为木陈道忞问责的另一借口。其《复灵岩储侄禅师》云:“枯骨寒原,远烦玉步,或有媟慢,得不深山僧之罪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犹多。改定铭词,谨依双白口谕,如命施行矣。”[1]396《复西遁超道人》亦云:“双白远来,多媟慢,乞为山僧修饰,弗备。”[1]396对此,钱谦益也深表忧虑。他希望张有誉等人从中劝解,或请他人与王廷璧同行,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其《再答张静涵书》云:“双白为法猛利,腰包渡江。羽书旁午,戒行不可不早。又须一二好衲子结为伴侣,方便首途。”[2]1 387《复灵岩老和尚书》亦称:“双白素心苦行,白衣中哪有两人?但嫌其聪明流动,如水银抛地,方圆不定,须和尚痛下钳锤,为设一死关,勿令出虎丘寸步,乃可望其竿头转身耳。”[2]1 394此外,参与调解者尚有牧云通门。他希望木陈道忞原谅继起弘储等人的少不更事:“铭塔一事,旧冬尔商,遂成少不更事。然为人后者,发扬先人光明,不一而足。念是或可恕也。”[5]
在钱谦益、张有誉等人调解下,涉事双方最终和解。诚如钱谦益所云:“上座归来,数日内再接张静翁手书,谓天童、邓尉两家子孙,已成水乳。”[2]1 388
三、《天童塔铭》异文
此次僧诤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钱谦益的《天童塔铭》书写了不利于汉月法藏的言辞,其原稿自然成为考察此事的关键。陈垣对勘《密云语录》所附塔铭与《有学集》塔铭后云:“至顺治十六年,木陈又请钱谦益为之,今附《密云语录》后。尝取与《有学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体无异,惟法嗣十二人,《集》为列举,此为常例,《语录》则一一叙入矣。又请铭一节,《集》单作忞公,《语录》则作忞公、门公,门公者牧云门,木陈不敢自专,引牧云以为重,盖所以塞同门之口,知前此费隐之诤为有效也。”(5)陈垣《清初僧诤记》,第37页。陈垣先生所论木陈道忞请铭时间为“顺治十六年”,实误,详见前论。此外,《塔铭》又见于《天童寺志》(杜洁祥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522页),前题云:“勅赐慧定禅师密云悟和尚塔寺之南山幻智庵右,宗伯虞山钱谦益撰铭序曰”诸字,《塔铭》底本系钱谦益修改稿,对勘后发现,两文文字差异共有81处,除避讳、通假及因字型相近、字音相同所出现的常见性差异外,重要者有五。一为易《有学集》“天其或者假借碪锥,助扬水乳,用纵夺为正印,化同异为导师,于人何有,于师何有”一段文字为“天其或者假发难端,激扬真说,握提婆之正印,化同异为大通,于人何尤,于物何有”。二为详列法嗣十二人之名单,其云:“嗣法如大沩如学、邓慰法藏、梁山海明、径山通容、金粟通乘、宝华通忍、龙池通彻、天童道忞、雪窦通云、鹤林通门、善权通贤、天童通奇十有二人,皆亲承炉鞲。”三为“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属余为塔铭”,《寺志》本作“介子裁书介鹤林门公属余为塔铭”。四为“用以副忞公之请”,《寺志》本作“用以副忞公、门公后先之请”。五为《寺志》本文末署云:“海门弟子虞山蒙叟钱谦益槃谈谨造。”究其原因,二为补充进入嗣法十二人之具体名单,此为塔铭创作之通例;三、四两处明确补入第一次请铭系黄毓祺遣钱谦益同乡牧云通门请铭,黄氏所选可谓得人,亦见钱谦益此次塔铭写作之前因也。可见,陈垣对校之文,实为钱谦益塔铭成稿。至于初稿如何,陈氏概不得而知。周法高所编《足本钱曾牧斋诗注》,以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初学集诗注》《有学集诗注》为底本影印出版,比钱仲联整理的《钱牧斋全集》多出注文3 931条,极具文献价值。其中,钱曾在《己亥夏五十有九日灵岩夫山和尚偕鱼山相国、静涵司农枉访村居,双白居士、确庵上座诸清众俱集,即事奉呈四首》其四“法海何因起墨兵”中的“墨兵”二字下详录初稿、成稿之文字差异,为重新考察僧诤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现择要迻录如下:
戊戌(1658)冬,天童密云禅师嫡子道忞具师行状、年谱,请公为塔上之铭。己亥(1659)二月七日,公制《塔铭》成,末后著语云:“稗贩弘多,智惠轻薄。花箭突发于室内,疑网交络于道旁。于是乎三玄三要,辨析三幡;七书三录,折冲四战。状称相轧者,至为狂詈,为凶短折,为吐红光烂尽,斯则弓折矢尽、树倒藤枯之明验也。师不借彼之锋镝,则金翘之威神何由穷搜于海底?彼不犯师之彀率,则波旬之气势何由竭尽于藕丝?天其或者倒用魔印,逆宣正法,于彼何尤,于师何有?”公意盖有所指,此文之原本然也。《塔铭》稿出,灵岩弘储和尚为汉月法嗣,见之,急挽静涵司农,两致手扎于公,力请删改。公不得已,为易其文云:“后五百年,斗争牢固,机锋激射,妨难弘多。师以慈心接之,以直道御之,以正理格之,以妙辨摧之。消有无于三幡,穷玄要于四战,务使其霜降水涸,智讫情枯而后已。初虽摄折多门,终乃镕融大冶。事有激而济,理有倒而相资。非铁石之钻磨则火光不发,非峡崖之束斗则水势不雄。天其或者,似借碪锥,助扬水乳。用纵夺为正印,化同异为导师,于人何尤?于师何有?”凡易一百二十六字。此文之改本然也。[3]2 432-2 433
详览初稿、成稿文字,虽同为批评晚明禅林流弊,但初稿的个体指向性更强。举凡“花箭突发于室内”“三玄三要,辨析三幡;七书三录,折冲四战”及“状称相轧者,至为狂詈,为凶短折,为吐红光烂尽”诸语,涉及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师徒矛盾(6)按:“状称”一句,是源出于木陈道忞的《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其云:“其与师轧者,至为狂詈,为凶短折,为吐红光烂尽。真枯竭无余,无可奈何,而大慈摄受之心,师终无间也。”(见道忞《布水台集》卷十六,《嘉兴藏》第26册,第370页上。)。据《三峰和尚年谱》记载,汉月法藏(1573—1635)十五岁辞别父母,在扬州德庆院出家。十九岁获得度牒,二十九岁从云栖株宏受戒。天启四年(1624),五十二岁的汉月法藏至金粟寺拜谒密云圆悟,请求印可。天启七年(1627),密云圆悟正式传衣钵于汉月法藏[6]203-213。然而,师徒间的禅宗思想与修持路径并不相同。汉月法藏因参阅高峰原妙的《高峰语录》《临济三玄要》而发悟。在披读惠洪觉范的《临济宗旨》后,“宛然符契,如对面亲质”[6]153,“因见寂音尊者著《临济宗旨》,遂归心此老,自谓得心于高峰,印法于寂音,无复疑矣!”[7]天启五年(1625),汉月法藏着手编撰《五宗原》,探寻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沩仰宗、法眼宗五家宗旨,发扬如来禅而轻视祖师禅。他在临济宗的棒喝传统外别寻旨趣,以“三玄三要”作为勘验禅机的枢要。在师法与师人之间,他更强调师法的重要性。如《五宗原》云:“师有人法之分,心有本别之异”,“良以师必因人,人贵法妙,分宗列派,毫发不爽。故传法之源流,非独以人为源流也。”[8]此与独揭临济宗旗纛、重视师资传统的密云圆悟持论相悖。
汉月法藏的《五宗原》在晚明禅林中反响颇大,时人褒贬不一。如万历三大师之一的憨山德清曾婉言相劝:“公如真实为人,切不可以偈语引发初机,直使死偷心泯知见为第一着,庶不负此段因缘耳。若曰如来禅、祖师禅如何如何,皆饾饤耳。”[9]当然,真正引起晚明禅林轩然大波的,是来自密云圆悟及其僧团弟子的强烈批驳。据纪荫《宗统编年》卷三十一载,崇祯八年(1635)“三峰藏寂后,一时怂勇者有三辟、七辟之刻。”[10]崇祯十年(1637),汉月法藏晚年追随弟子潭吉弘忍撰《五宗救》,为《五宗原》辩护。崇祯十一年(1638),密云圆悟亲自撰写刊刻了《辟妄救略说》,“名义上批辟弘忍‘妄救’之作,实指法藏在《五宗原》中‘妄执’‘临济宗旨’”[11]。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密云圆悟圆寂后,此次论争才告一段落。
钱谦益与汉月法藏同在常熟,相交甚早。万历四十五年(1617)春,憨山德清至云栖凭吊袾宏,返归吴门时,应巢松慧浸、一雨通润等人之请游天池,“将行,弟子洞闻、汉月久候,钱太史受之亲迎至常熟”[12]。钱谦益《憨山大师曹溪肉身塔院碑》亦载:“万历丁巳(1617)□月,大师东游涖三峰,然灯说戒。汉月师请坐堂上,勘辩学人。余与汉师左右侍立。诸禅人鱼贯而前,抠衣胡跪,各各呈解。大师软语开示,应病与药,皆俛首点胸,礼拜而退。”[2]1 255随着密云、汉月在禅法修持理念上的分途,加之汉月法藏与洞乘法闻在住持破山寺期间的纠葛,钱谦益对汉月法藏的态度陡变,甚至将其直斥为海内三妖之一。如《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云:“天丧斯文,余分闰位,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后有传洪范五行者,固将大书特书著其事应,岂过论哉!”[13]在与黄宗羲的信中,钱谦益直接点出:“自国家多事以来,每谓三峰之禅、西人之教、楚人之诗是世间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陆沉鱼烂之祸。今不幸言中矣!”[14]因此,在《塔铭》初稿中斥汉月法藏为“波旬”,指责他“倒用魔印,逆宣正法”,实际反映出他对汉月法藏一贯之态度。正因文中个体指向性太强,措辞过于激烈,进而引起继起弘储等人的强烈反对。在张有誉等人调解下,钱谦益最终改易文辞。成稿文字虽弱化了初稿的个体指向,但蕴含于中的批判精神依然未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改而未改”。正如钱谦益所云:“恭承慈命,再三绎,既不敢护短凭愚,亦未尝改头换面,点笔之余,恰与初心符合。焚膏呵砚,不免沾沾自喜。因思法门纲宗与文字血脉,此中大道理,合是如此。”[2]1 387又云:“因将《塔铭》原稿再一点检,但是文字中槎牙头角之语,改窜数行耳。是中君臣宾主,眼目历然,殊非媕阿两可,自附调人。更于老人激扬提唱,一片苦心,重为洗发。所谓颊上三毫,传神写照,未必不差胜于元文也。”[2]1 388身为族孙兼弟子的钱曾,深谙钱谦益的此番苦心。他在“墨兵”条后注文中说:“详公语句,郑重命笔,不相假借如此。然公生平撰述,初非党枯竹、仇朽骨、有私意存乎其间也。予编次《有学集》,于《天童塔铭》原本改本并列之而不敢逸其一者,盖不忍负公手稿付嘱之意,亦以见点定之际,原无一字出入,初未尝媕婀两可,自犯岐舌之规。”[3]2 433-2 434钱曾并存初稿、成稿文字,借此为钱谦益正名,可谓不负其师托付遗稿之苦心,亦为重新解索此桩公案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
四、《天童塔铭》之争的影响
《天童塔铭》之争在诸方调解下最终平息,钱谦益初稿、成稿之文字差异及其写作苦心,亦借钱曾之注文而大白。然而,此事对钱谦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僧诤发生期间,便有乘机兴师问罪者。钱谦益称:“《塔铭》稿出,有人自武林来,盛言磨刀镞矢,势焰汹汹,谈已辄为口噤手战。仆应之曰:‘吾文之写于胸,犹弹丸之脱于手也。弹丸脱手,手中无复有弹丸矣。文字写胸,胸中无复有文字矣。彼将寻声问影,觅弹丸于吾手,不已愚乎?’其人茫然而去。”[2]1 390当远在岭南的天然函昱请钱谦益为其师宗宝道独撰写塔铭时,钱谦益以此为例说道:“向为天童作铭,略说少分,诃谤蜂起,付之瑱耳。铭诗末云:‘拗折拄杖,抛掷拂子。余与老人,觌面伊始。’连这老汉也与他劈头一棒,见者都不觉,懡而已。此文一出,逆知诸方唾骂,更甚往时。古人金汤护法,不惮放舍身命。知我罪我,何足挂齿。”[2]1 391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次论争,加深了钱谦益与继起弘储间的往来,为他融入清初遗民僧人群体提供了助缘。从现有资料来看,僧诤发生前,钱谦益与继起之间并无往来。自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十九日,继起弘储率领僧团弟子在拂水山庄拜访钱谦益后,二人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同年九月,钱谦益本想赴吴门,“践腰包扣访之约”[4]334后因“军声初解,干戈充斥”而未能成行,只好约王廷璧等人“献岁发春,便当枢衣纳屦,长侍法筵”[4]335。顺治十七年(1660)春,钱谦益亲赴灵岩,再践前约(7)参见《有学集》卷十《灵岩方丈迟静涵司农未至》(《有学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11页),《灵岩呈夫山和上二首》(《有学集》卷十,第512-513页)。。顺治十八年(1661)春,钱谦益致书继起弘储、王廷璧等人,希望他们资助按指契颖刊刻《嘉兴藏》。同年九月,钱谦益八十寿诞。此前,他已向王廷璧、继起弘储寄去辞寿小笺,继起弘储依然以老藤如意相赠。钱谦益《老藤如意歌》序云:“余年八十,灵岩和上持天台万年藤如意为寿。余识之,曰:‘此金华吴少君遗物也’歌以记之。”[2]605康熙元年(1662)冬,钱谦益感继起弘储孝亲之举,作《报慈图序赞》,借机宣扬忠孝佛性论(8)参见《报慈图序赞》(《有学集》卷四十二,第1 425-1 426页)及《与继起和尚书》其四(《牧斋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36页)。。康熙三年(1664)二月初八,继起弘储诞辰,钱谦益作《寿量颂为退和尚称寿》以祝之。钱谦益去世后,继起弘储升堂说法以示纪念:“虞山宗伯生忌,门人请对灵升座。蓦拈拂子曰:即此物,非他物,天上下独尊,偏大千共仰,是竺士大仙之心。大宗伯牧斋钱公之一灵,对三贤十圣说法身,以为极果,其实不无缘起,不有缘灭。道是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道是远,秪在目前。心既如是,法亦如是。一沤生波澜,始六入、十二因缘、十八界,乃至八万四千法门,有什么限际?喝一喝,曰:‘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间,知音复是谁?’”[15]继起弘储以子期相比,以天地间知音相许,算是钱谦益在《天童塔铭》之争中的意外收获。